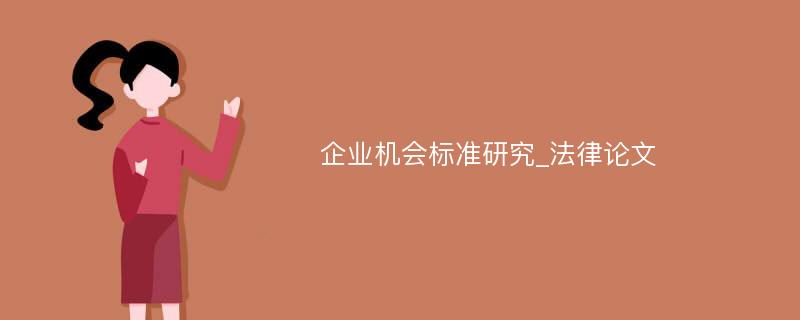
公司机会准则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准则论文,机会论文,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司机会准则(corporate opportunity doctrine)是英美国家公司法中的一个重要理 论。在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中并没有所谓的公司机会准则,与之相仿的是董事竞 业禁止制度。但竞业禁止制度与公司机会准则所禁止的是董事的不同行为。在英美国家 ,董事除了根据公司机会准则对公司负不得篡夺公司机会义务外,尚负有不与公司竞争 义务;(注:不与公司竞争问题,请参照L.C.B.Gower,D.D.Prentice,B.G.Pettet.
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5th),Sweet & Maxwell,1992.P.564—57 2;Harry G.Henn & John R.Alexander.Laws of Corporation,West Publishing Co.198 3.P.457—458.)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只有董事竞业禁止义务的规定,而无不得篡夺公 司机会义务的规定。(注:如《德国股份法》第88条、《日本商法》第264条、“台湾公 司法”第209条、我国《公司法》第61条。)今天的日本、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学 界对导入公司机会准则的呼声越来越高,司法实践也进行了一定的尝试。为更好地保护 公司利益,防止董事利用在公司中的特殊地位以权谋私,有必要加强对公司机会准则的 研究,为我国导入公司机会准则进行理论上的准备。
一、董事忠实义务与公司机会准则
一般来说,大陆法系国家认为董事与公司是一种准委任关系;英美法系国家认为董事 与公司间是一种准信托关系。但无论是准委任说,还是准信托说,均认为董事对公司负 有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注意义务要求董事对公司事务尽普通谨慎之董事在相似情况下 处理相似问题所应有的注意;忠实义务要求董事“积极维护公司利益,禁止从事损害公 司利益的行为”[1](P.237)。注意义务是对董事“称职”的要求,忠实义务是对董事“ 道德”的要求。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责任受经营判断准则的保护,且可进行事前限制和 事后免除;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责任一般不得限制或免除。可见,与注意义务相比较, 忠实义务“更严格且客观,其最重要的原则是董事负有竭尽忠诚地为公司工作并诚实地 履行职责的义务,即以对公司不断且绝对的、无条件的忠诚为内容”[2](P.375)。
法律对董事设置如此严格而绝对的忠实义务,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是 ,通过赋予董事很高的忠实义务来平衡董事的权力与责任,从而保护公司的利益。随着 公司所有与经营的分离,特别是在“董事会中心主义”代替“股东会中心主义”后,董 事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3](P.154),为了防止 董事滥用权力,必须有一定的机制予以抗衡。“根据传统的公司法思想,除了法律,没 有任何别的东西能防止董事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注:见
Adolph A.Berle and Gardiner C.Means.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the Machillan Co.,1933.P.221.)虽然现在许多学者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认 为,除了法律,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如公司收购、社会评价降低、再次受雇困难等非法 规因素也能影响内部人的行为。但是,即使是反对前述传统公司法思想的人也不能否认 下面这一事实:公司的内部人,由于控制着公司,所以拥有将公司的资产价值转归自己 的事实权力。而这种事实上的权力使得非法规因素对内部人行为之制约的不力及对受害 人救济的无能。正如易斯特布鲁克与费斯切尔所说:“忠实义务问题经常涉及一次性的 、大额的贪污侵占行为,对这种‘拿了钱就跑’的行为,通过市场进行事后的惩罚是不 够的。”[4](P.297)因而,只有通过法律使董事对公司负有高度忠实义务,才能很好地 约束董事的行为,更好地保护公司利益。
然而,如果公司法仅仅是原则性地规定董事对公司负忠实义务,则这种规定仍然是很 软弱的,其对董事行为的拘束也仍是有限的。这是因为,董事与公司间是一种不对等的 法律关系,董事具有以自己的行为改变公司的法律地位的能力,而公司则必须承受这种 被改变了的法律后果,即董事处于一种相对优势的地位,公司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 [1](P.151)。在此种情况下,公司的权利极易受侵害,而又因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作为 弱势一方的公司有时甚至不知其权利已被侵害或者虽然知道权利被侵害却无法证明。为 加强对公司利益的保护,法律必须禁止董事实施那些可能危及公司利益的行为。为此, “不仅要从原则上,更重要的是要从具体规定上,尽可能杜绝一切董事违反忠实义务事 件的发生,维护公司的利益。”[5](P.15)因此,为确保董事对公司的忠诚,公司法要 求董事不得与公司进行未经许可的交易、不得为自己或他人进行与所任职公司相同或类 似的营业、不得篡夺公司的交易机会。这即是董事的自我交易规制义务、竞业禁止义务 、不得篡夺公司机会义务。其中,董事不得篡夺公司机会义务就是由公司机会准则确立 和发展起来的。
公司机会准则产生于英美判例法,它是指这样的一项准则:禁止公司受信人(注:严格 地说,公司的受信人除董事外,还包括经理、秘书等其他高管人员。本文主要研究公司 机会准则所确立的董事不得篡夺公司机会义务,故非经特别指出,均以董事为研究对象 。)将公司拥有期待利益、财产利益或财产权利的交易机会,或从公平角度言应属于公 司的交易机会予以篡夺自用。(注:关于公司机会准则,可参见Black Law Dictionary( 6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1990.P.340.)从严格意义上说,公司机会不是公司 的资产[6](P.515)。但是,公司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存在,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 化是其存在的原因和目的,公司营利目的的实现只能通过一系列的交易行为来实现。如 果没有交易机会,就不会有公司的交易,更不会有公司营利目的的实现。因而交易机会 对公司来说意义重大,可以说,交易机会是一种不是财产的财产。正因如此,英国法院 在裁决中经常将公司机会或公司信息作为公司的所有物(belongings),即公司的“财产 ”(property)或“资产”(assets)来对待。(注:关于公司所有物,参见L.C.B.Gower,D .D.Prentice,B.G.Pettet.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5th),Sweet & Maxwell,1992.P.564.)因此,董事作为公司的经营者,不能任意篡夺公司的交易机会 ,就像其不能任意侵占公司财产一样。但是,交易机会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司财产 ,故不能以规范董事侵占公司财产的法律规则来规范董事篡夺公司交易机会。这就为“ 公司机会准则”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
二、公司机会准则的历史演进
(一)公司机会准则在美国的发展
公司机会准则主要起源于美国[6](P.561)。在美国,学界一般认为有关公司机会准则 的最早判例是1900年的Lagarde v.Anniston Lime & Stone Co.案[1](P.270)。(注:12 6 Ala.496,28 So.199(1900).)该案确立了董事不得篡夺公司拥有利益或期待利益之机 会这样的准则。其后,在1939年的Guth v.Loft Inc.案(注:23Del.Ch.255,5 A.2d 503 (1939).)中,特拉华州最高法院率先提出了判断“公司机会”的“经营范围”标准。特 拉华州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对从事特定业务的公司来说,当其面临一个其具有实 施该机会的基本知识、实际经验和能力的机会时,只要从逻辑上和本质上说,该公司具 有实施该机会的经济实力,且该机会符合公司的合理需要及扩张要求,我们就可以说, 该机会在公司的经营范围之内,该机会是公司的机会。”(注:23Del.Ch.255,5 A.2d 5 03,514(1939).P.514.)虽然在本案中,被告利用了原告的资金和设施,但是,法院意见 却明确地暗示,即使没有被告利用原告资金和设施这一事实,被告仍会被认为篡夺了原 告的机会。(注:关于公司机会,见William L.Cary,Melvin Aron Eisenberg.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rporations (fifth edition),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80.P.595.)在1948年的Durfee v.Durfee & Canning,Inc.案(注:323 Mass.187,199,80 N.E.2d 522,529(1948).)中,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采纳了《白兰廷公司法》中关于判断公 司机会的下述观点:公司机会准则的真正基础,不应当存在于任何期待或财产利益之概 念中;而是存在于,“当公司的利益需要保护时,受托人利用机会这一特定事实所具有 的不公正性”。(注:关于判断公司机会的标准,参见William L.Cary,Melvin Aron Eisenberg.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rporations(fifth edition),the Foundation Press INC,1980.P.595—596.)这即是判断公司机会的“公正性”标准。
从公司机会准则在美国的发展史看,“公司机会”标准从“利益或期待”标准到“公 正性”标准的演变实际上是越来越严格。但是,公司机会准则的适用在美国越来越严格 的趋势也非一成不变,最近,公司机会准则在美国一些州的适用即出现了缓和的趋势。 如在Broz v.Cellular Information Systems Inc.案(注:Del Supr,673 A2d 148(1996 ).)中,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即认为董事无须就利用公司既无利益亦无能力实施的机会对 公司负责。
(二)公司机会准则在英联邦国家的发展
在英联邦国家,公司机会准则被认为滥觞于衡平法上受托人的信义义务规则。该规则 产生于1726年的Keech v.Sandford案,(注:(1726)Sel.Cas.Ch.62.)其确立了“除非委 托人明示同意,受托人不得利用其地位谋利”的规则[1](P.265)。受此影响,英联邦国 家在董事利用公司机会方面一直采取非常严格的态度。从1916年的Cook v.Deeks案(注 :[1916]1AC 554.)到1967年的Regal(Hastings)Ltd.v.Gulliver案,(注:[1967]2 AC 134.)法院采取的都是严格执行公司机会准则的立场,其坚信的是:“衡平规则之所以 要那些利用受信地位牟利的人负责,决不是因为这些受信人有欺诈行为,或缺乏诚信… …那些利用受信地位获利的人无论多么诚实,多么善意,其均不能逃脱对其获利负责的 命运。”(注:[1967]2AC.)但在1966年的Peso Silver Mines Ltd.v.Croper案中,(注 :(1966)58 DLR (2d)1.)加拿大最高法院认为在公司考虑了一个机会并诚实地拒绝这一 机会后,董事可用自己的资金实施这一机会。可见,随着商业企业变得日益复杂,
Regal案所确立的严格规则就有些不合时宜了,在一些英联邦司法管辖区,该规则并没 有得到持续和严格的贯彻。特别是最近30年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一些法院倾向于放 弃原来那种绝对禁止受信人利用公司机会的立场。因此,在英联邦国家,篡夺公司机会 准则已从严格禁止董事利用公司机会发展到有限制地允许其利用公司机会。
(三)日本、德国引入公司机会准则的情况
在日本,传统公司法理论并不承认公司机会准则,但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一些 学者主张借鉴美国的作法,认为对董事利用自己在公司中的地位,将公司与第三人间的 交易机会转为己用,既不属违反《日本商法》第264条规定的竞业禁止义务,也不属违 反《日本商法》第243条之1第3款规定的善管注意义务,而有必要承认此为忠实义务的 独立存在[7](P.203)。
在德国,《德国股份法》第88条明确规定了董事的竞业禁止义务,但是受英美法律的 影响,公司机会理论也逐渐导入。根据德国股份法,董事负有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实施 侵害公司利益之行为等一般的诚实义务,禁止篡夺公司机会的义务被认为是这种一般诚 实义务的一环。《德国股份法》第93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董事会的成员……对于其 因在董事会内的活动所知悉的机密事项和秘密,特别是营业或业务秘密,应保持缄默。 ”董事如违反此种义务,利用公司的情报和秘密从中获利,则应当赔偿公司因此所受损 失。从判例上看,德国法院适用公司机会理论判决的案件也零星可见[8](P.94)。
三、公司机会的认定
董事在担任公司职务期间,必然会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交易机会。这些交易机会,有的 是因董事在公司中所任职务而获得的;有的是董事以其他身份所获得的;有的是董事代 表公司或他人有意识地努力而获得的;有的是偶然得到的。董事对这些机会,哪些可自 用,哪些不能利用,否则就会构成篡夺公司机会?这首先得看该机会是否是公司机会, 只有该机会属公司机会时,才存在篡夺公司机会的可能,可见,准确判断一个交易机会 是否属公司机会是正确适用这一准则的前提。美国判例法上认定公司机会的标准有三个 :
1.“利益或期待”标准。这是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在Lagarde v.Anniston Lime & Stone Co.案中提出的标准。在该案的判决中,法官指出,公司董事或高级职员从第三 人处购得的财产无须转移给公司,除非该财产是“公司拥有既得利益的财产,或公司基 于现有权利而享有期待的财产,或者……董事或高级职员的干预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公 司实现设立公司之目的的财产。”(注:126 Ala.496,502,28 So.199,(1900).P.201.)
因此,所谓“利益或期待”标准,是指涉及公司拥有既得利益,或公司拥有基于现有 权利而享有期待,或会影响公司设立目的之实现的机会。“这是美国判例法确定的判断 公司机会标准中最为宽容的标准”。(注:关于公司机会标准,见William L.Cary,
Melvin Aron Eisenberg.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rporations (fifth edition),
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80.P.594—595.)
2.“经营范围”标准。该标准主要是Guth v.Loft,Inc.案确立的。根据“经营范围” 标准,公司机会必须与公司现在或未来的经营范围密切相关,某一机会与公司经营活动 之间的联系越密切,就越有可能构成公司机会。
3.“公正”标准。依这种标准,如果根据特定的事实,公司董事或高级职员利用某一 机会对公司而言是不公正的,则这种交易机会即属公司机会。它“纯以公平、公正的道 德尺度予以衡量”[9](P.249)。较之“经营范围”标准,这是一种更欠客观性的标准。 (注:关于公司机会标准,见William L.Cary,Melvin Aron Eisenberg.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rporations (fifth edition),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80.P.59 5.)在Durfee v.Durfee & Canning,Inc.案中,法院为“从特定的事实来判断什么才是 公正的和衡平的道德标准”列举了七项要素,即:(1)该机会是否具有特殊的或独特的 价值,或者说它是否为公司业务发展所必需;(2)该机会是否是基于董事或公司高级职 员这一职位所知悉;(3)公司是否积极地追寻这一机会,如果是,那么公司是否已放弃 这一努力;(4)该董事或高级职员是否有明确的职责为公司获得这一机会;(5)为取得或 开发这一机会,董事或高级职员是否使用了公司的资金或设施;(6)他利用这一机会是 否使得公司处于不利地位,他是否有将此机会转售给公司的意图;(7)公司是否有足够 的能力、财力及其他条件来实施这一机会。(注:R.C.Clark.Corporate Law,Little,
Brown & Co.1986.P.228—229.)
在这三种标准中,“利益或期待”标准虽被认为是美国法院早期所采用的标准[9](P.2 49),但其并未在后两标准出现后即失去适用余地。根据该标准认定的公司机会较为狭 窄,不利于公司利益的保护。为克服此缺点,“在实践中,法院在界定‘利益或期待’ 时倾向于采取灵活的方式,……有时也会对公司设立目的作扩大解释,以保护公司利益 ”。(注:如Abbott Redmont Thinlite CorP.v.Redmont(475 F.2d 85,89(2d Cir.1973 ))案及Morad v.Coupounas(361 So.2d 6,8(Ala.1978))案。)
“经营范围”标准的优点是客观性强,简单明了。但由于某一机会与公司经营范围间 关系之紧密程度之判断本身是主观的,故“经营范围”标准本身也非纯粹客观的标准, 也含有主观的成分。而且,“公司经营范围”本身是一个不甚准确且极易引起争议的概 念。再者,“经营范围”标准不区分机会是否是公司所追求,是否是董事因其在公司中 之职位而获得的,而是纯以机会与公司经营范围的紧密程度来判断,有时亦欠公允。因 此,为克服此缺点,在适用这一标准时,有的法院认为只有当机会涉及到公司已经拥有 既有利益的财产或涉及公司因既有权利而产生期待的财产,或机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 公司经营过程时,该机会才属公司机会[10](P.410)。
“公平”标准的优点是符合衡平法的精神,其缺点是过于主观,有时欠操作性,不利 于指引当事人的行为,也不利于法院对纠纷的裁决。
在当今的美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判断一个机会是否是公司机会时,最常用的做法是 将“经营范围”标准与“公平”标准结合起来进行判断[10](P.410)。这种综合的标准 ,其实包含两个标准:一个是“经营范围”标准,该标准用以决定公司对某一机会是否 具有合法利益;一个是“公平”标准,该标准是在公司对某一机会具有合法利益时,用 以判断董事是否可以利用该机会[10](P.410)。(注:笔者认为,该实践恰恰说明现代美 国法院倾向于运用“经营范围”标准来认定公司机会,因为在所谓的“综合”标准中, “公平”标准主要被用于判断董事是否可以为自己利用某一公司机会。)而在特拉华州 ,法院经常采用的方法是,根据机会到达公司董事或官员的不同方式采用不同的标准: 如果董事或官员以其公司董事或官员的身份被提供某一机会,则根据“经营范围”标准 来判断这一机会是否是公司机会;如果董事或官员以其私人身份被提供某一机会,则只 有在该机会对公司而言是重要的,或公司对该机会具有“利益或期待”时,该机会才是 公司机会。(注:关于公司机会,见William L.Cary,Melvin Aron Eisenberg.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rporations(fifth edition),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80.P .596.)
在美国,除前述由判例创立的标准外,美国法学所在1992年《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 建议》中提出的认定公司机会的标准也是很有影响的一种。该建议第5.05条规定,公司 机会是指以下任何一种从事经营活动的机会(包括取得或运用合同权利,或其他有形财 产或无形财产):(1)在担任公司重要高级职员或董事之场合,通过通讯或其他方式获得 的下列机会:(A)与其履行作为重要高级职员或董事的义务有关,或者相关情形足以使 其合理地相信,机会的提供者期望其将该机会提供给公司;或者(B)通过使用公司的信 息或财产所得到的,该公司重要高级职员或董事根据合理判断应该相信这一机会是对公 司有利的机会;或者(2)对于公司专职的重要高级职员或常勤董事来说,其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某一机会与公司正在从事或合理期待从事的经营活动密切相关。
英国在其1979年修改公司法的草案中曾于第44条第4款对“相关信息”和“相关机会” 的定义作了规定,其实质与美国法学所的前述规定见解相仿,但该草案后未获通过。
根据法律创设公司机会准则的初衷,参酌美英等国的立法、司法与学说,我们认为, 应将公司机会界定为:提供给公司的,或公司董事、经理在执行公司职务过程中获得的 、与公司经营活动相关的,取得或运用合同权利、其他有形财产或无形财产的各种交易 机会。析言之,公司机会有两种,一种是由第三人直接向公司提供的机会,如第三人直 接向某公司提供的向该公司出售某种产品或从该公司购买某种产品的要约;一种是第三 人向公司董事、经理提供,但属于公司的机会。对前一种公司机会的认定比较容易,问 题是,在机会是直接向公司董事、经理提供时,如何判断这些机会是否属公司机会。为 准确认定后一种公司机会,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1.能成为公司机会的只能是取得或运用合同权利、其他有形财产或无形财产的交易机 会。除此以外的机会不是公司机会。例如,某董事代表公司参加救灾募捐会,该次募捐 活动既不公布捐款人名单,也不予任何奖励,则如该董事未将捐款机会让给公司而用自 己名义,以自己的金钱捐了一笔款,则该董事的行为不构成篡夺公司机会。
2.公司机会只能是董事、经理在执行公司职务过程中获得的交易机会。董事、经理在 就任前或卸任后所获得的交易机会固然不是公司机会,就是现任董事、经理,其在与执 行公司职务无关的时间和场合获得的交易机会,即使与公司经营活动密切相关,也不应 认为是公司机会。(注:但是,如果相关信息或交易机会是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获得, 则即使该董事辞去董事职务,其也不得擅自利用该机会,特别是在辞职是受利用这一机 会驱使或影响时更是如此。此外,对“执行公司职务过程”应作广义理解,不仅包括在 执行公司职务期间,而且包括虽非执行公司职务期间,但以公司董事的身份行事时。这 样,即使在董事辞职后,其如以过去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的地位或身份而不是以新地位或 身份获得某交易机会时,该机会仍属公司机会(见L.C.B.Gower,D.D.Prentice,B.G.
Pettet,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5th),Sweet& Maxwell,1992,p56 8)。)但这仅对该交易机会的提供者只泛泛将机会提供给董事、经理的情形而言的。在 机会是由第三人直接向公司提供的场合,即在机会提供者明确表示机会是提供给公司或 根据机会提供者可推定的意思可认为其是想将机会提供给公司的情形下,则无论机会是 在与董事、经理执行职务有关的场合,还是在与董事、经理执行职务无关的场合向董事 、经理提供,该机会均属公司机会。
3.公司机会必须是与公司经营活动相关的交易机会。需指出的是,公司机会是与公司 “经营活动”相关的交易机会,而不是与公司“经营范围”相关的交易机会。这是因为 ,“经营范围”是比“经营活动”外延更为狭窄的概念。如认为公司机会是与公司经营 范围相关的交易机会,则会大大缩小公司机会的范围,不利于对公司利益的保护。所谓 公司经营活动,是指与公司实现其营利目的相关的所有活动。但是,由于“经营活动” 不像“经营范围”那样明确,故其在适用过程中存在如何判断某一交易机会是否与公司 经营活动相关的问题。为此,我们应当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例如:(1)公司是否就 取得该机会进行过谈判;(2)该交易机会是否首先向公司提出,或首先提供给作为公司 管理人员的董事;(3)董事获得这一机会是否是基于其在公司中的地位;(4)董事是否使 用了公司的设施或财产去实施该机会;(5)公司对该机会需求的程度[10](P.411),等等 。当机会是公司努力争取的,或机会是首先提供给公司的,或公司的资金曾被用于实施 机会,或寻找公司机会过程中利用了公司的设施或人员,这种机会当然是公司机会。( 注:关于这一问题,见Harry G.Henn & John R.Alexander.Laws of Corporation,
WestPublishing Co.,1983.P.463.)
四、董事不得利用公司机会的例外
公司机会准则仅禁止董事篡夺公司机会,而非绝对禁止董事利用公司机会。恰恰相反 ,在规定公司机会准则的国家和地区,其法律均允许董事在特定情况下利用公司机会, 这即是董事不得利用公司机会的例外。
对于董事面临的一个交易机会,如该机会不属于公司机会,董事当然可以运用;如该 机会属于公司机会,而公司有能力实施也愿意实施,则董事当然不能运用。问题是,如 果董事面临的一个机会属于公司机会,而公司又不愿运用或不能(包括法律不能与事实 不能)运用时,董事可否加以运用。
(一)董事利用公司不愿运用的公司机会问题
所谓公司不愿运用的公司机会,是指当一个机会由董事提供给公司,而公司董事会或 股东会经决议拒绝利用该机会时,该机会便成了公司不愿利用的公司机会。在普通法国 家,一般认为,在公司拒绝运用某一公司机会时,董事可以为自己利益而利用该机会。 但对董事为自己利益利用公司不愿利用之机会的条件,现代公司法和学说主要有两种态 度:一种是只要是公司放弃的机会,董事即可为自己利益加以利用;一种是只有在公司 放弃机会并同意董事为自己利益加以利用时,董事才可利用。
前一态度的代表是1992年美国法学所制定的《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第5.05条 的规定。根据该规定,董事或重要高级职员不得为自己或相关人利用公司机会,除非: (1)首先将机会提供给公司,并向公司决策者披露该公司机会和利益冲突的所有重要事 实;和(2)公司以下述方式之一拒绝了该公司机会:(A)在全部重要事实披露后由无利害 关系董事批准公司机会之拒绝时,批准此项拒绝的董事的行为必须符合第4.01条(d)款 规定的经营判断准则;(B)在全部重要事实披露后由无利害关系股东批准或追认时,此 种拒绝不构成浪费公司资产;(C)如果一项拒绝不是依照前两项规定之标准,或不符合 公司规定的其他有效条款,董事或重要高级职员利用该机会对公司而言是不公正的。
后一态度的代表是英国判例和学说。根据这种观点,在公司允许董事利用某机会,即 公司不仅放弃而且同意董事利用某一本属公司的机会时,董事才可利用。(注:关于这 一问题,见L.C.B.Gower,D.D.Prentice,B.G.Pettet,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5th),Sweet& Maxwell,1992.P.570.)在英国,有观点认为,当公司高级职 员要利用公司放弃之机会时,公司董事会即可作此种同意;但当公司董事要利用公司放 弃之机会时,只能由股东会决议或所有有表决权股东的一致协议做出。然而,考虑到并 非公司所有董事均要利用公司放弃的机会,只有个别董事欲利用该机会,故从效率角度 考虑,应认为董事会有权做出此种同意。这一观点得到了英国枢密院的支持。(注:如
Oueensland Mines Ltd.v.Hudson([1978]52 A.L.J.R.379,P.C.)案。)在信息披露方面 ,与美国法学所在《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中的要求一样,在英国,董事要取得 利用公司放弃机会之许可,需在公司决定是否利用机会的决议作出前充分披露其利益。 如果董事会决议同意董事利用某机会时,该董事并未披露其利益,则董事会的同意决议 须提交股东会进行批准。在股东会进行此项批准时,该董事仍需就重大事实进行披露。 (注:关于这一问题,见L.C.B.Gower,D.D.Prentice,B.G.Pettet,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5th),Sweet& Maxwell,1992.P.570.)
从英美两国的立法与司法看,对董事利用公司放弃之机会,该两国均要求向公司决策 机关披露重要事实,并由无利害关系董事或股东进行决议,(注:须指出,在过去,董 事披露有关公司机会的信息及决策机关放弃公司机会皆需正式进行,即董事须在董事会 或股东会上披露信息,机会的放弃须以决议方式作出。英国至今仍坚持这一传统,但在 美国则出现了相反的判例。例如,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在1996年的Broz v.Cellular Information System,Inc.案中明确地放弃那种要求董事正式披露有关公司机会的信息 、机会拒绝需以正式决议作出的立场(见Deborah A.Demott,the Figure in the Landscape:a Comparative Sketch of Directors' Self-interested Transactions,(1 997)62 Law and Contempo rary Problems 244,245)。)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证公司放 弃运用公司机会之决议是公司真实的意思。由于英国不仅要求公司放弃公司机会,而且 要求公司同意董事利用公司机会,董事才能利用公司放弃之机会,故相对美国而言,英 国法关于董事利用公司不愿利用之机会的条件更为严格。不仅如此,英国法关于董事利 用公司不愿利用之机会的规定在适用中更为明确,更不易产生歧义。例如,根据美国法 学所的建议,如果一个董事在公司就放弃某机会进行表决时,他并无利用该机会的打算 ,只是参加董事会并投票同意公司放弃该机会,但在决议通过后,他又利用了该机会, 则其行为构不构成篡夺公司机会?这在实践中极易产生争议。鉴于公司机会准则是董事 不可分割的忠实义务之一部分,笔者认为,对董事利用公司不愿利用的机会,应规定严 格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公司利益。因此,将来我国公司法对董事利用公 司不愿利用的机会进行规定时,可借鉴英国的做法,规定:如果董事要利用公司放弃的 机会,须得到公司的同意。当然,这种决议其实是一种自我交易,因而决议的做出应符 合自我交易的规定[10](P.411)。
前面讨论的是在公司就放弃某机会做出决议后,董事能否运用该机会的问题。然而, 现实中大量的情况是,当某个机会被提供给公司后,公司既未表示要实施该机会,也未 就放弃该机会进行决议(当然此处仅指公司实施该机会既无法律障碍,也无事实障碍, 对公司实施机会有障碍时董事是否可利用的问题容后详述)。在这种情况下,董事能否 运用该机会?对此,有人认为,“为保护依法运用公司拒绝的商业机会的董事起见,公 司机关应在商业机会允许的合理期限尽快就其是否拒绝某一商业机会做出决议;若在商 业机会的最后有效期临近时,公司仍然未置可否,则应推定公司拒绝运用该机会。”[9 ](P.252)然而,笔者认为,虽然“对所有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之争论的人而言,他们最为 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确保公司本身利益的情况下,最为恰当地发挥公司董事的企 业进取心”[6](P.515),虽然在根据公司机会准则解决董事利用公司机会问题时也应注 意处理好保护公司利益与发挥董事积极性的关系,但无论是完善公司治理问题,还是适 用公司机会准则,应牢牢把握住的一个前提是:公司利益是第一位的,董事的进取心是 第二位的,鼓励董事进取心也是为促进公司利益服务的。因此,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不 能为激发董事进取心而牺牲公司根本利益,否则只能是一种本末倒置、得不偿失的做法 。很显然,在一个公司有能力实施之机会的最后有效期临近时,如公司未就是否实施该 机会做出表态,就推定公司拒绝运用该机会,从而董事即可自由运用的做法是很不利于 公司利益的保护的。如果法律允许这种推断,则董事便可以种种借口推迟公司对是否利 用机会进行决议,从而达到将公司机会为己所用的目的。
(二)董事利用公司不能运用的公司机会问题
对一个在法律上是公司机会的机会,公司并不一定都能够实施。这种不能,既包括事 实上的不能,也包括法律上的不能。前者如公司不具备实施某一交易机会的财力、人力 ;(注:有人认为,当交易对手不愿与公司交易时,也为事实上不能的公司机会(见
Robert W.Hamilton,the Law of Corporations,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页;陈景 菁:《论董事篡夺公司机会之禁止义务——兼论我国<公司法>中相关制度之完善》,载 《学术交流》2000年第3期)。对此,笔者以为,当交易对手不愿与公司交易时,该机会 便不属公司机会,董事当然能够运用。)后者如公司利用该机会将构成违法行为或越权 行为。
从实际发生案件的情况看,董事经常以公司没有财力实现某一机会为理由为自己利用 公司机会进行辩护。因此,在这里,我们先就董事是否可利用公司因财力不足而不能利 用的公司机会进行探讨。
从英国判例看,法院的立场是:当公司因财力不足不能利用某一机会时,董事不能利 用。这从英国关于篡夺公司机会的经典判例Regal(Hastings)Ltd.v.Gulliver案即可窥 见一斑。在美国,对董事能否利用公司因财力不足不能利用的公司机会这一问题,存在 着完全相左的判例。在Irving Trust Co.v.Deutsch案(注:73 F.2d 121(1934).)中, 联邦第二巡回法院驳回了被告以原告没有财力利用机会,因而自己可以利用该机会的抗 辩。但是在A.C.Petters Co.v.St Cloud Enterprises案(注:1 Minn.261,222 N.W.2d 83(1974).)中,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认为,“在公司欠缺财力利用某一机会时,公司官 员没有特别的义务用自己的钱资助公司利用这一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董事利用公司机 会不存在对公司机会的篡夺”。从各州的立法看,对此问题态度也不统一,如纽约州法 律规定,即使公司没有财力运用某一机会,董事也不得利用;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认为, 当公司无财力运用某一机会时,董事可以利用;而俄勒冈法律虽规定,当公司无财力运 用某一机会时,董事可利用该机会,但其所指的“公司无财力运用某一机会”,仅指公 司陷于支付不能时。在允许董事于公司无财力运用机会时利用该机会的地区,公司无财 力运用机会的证明责任在董事一方。(注:关于公司无财力利用机会问题,见Dennis Campbell.Liability of Corporate Directors,Lloyd's of London Press Ltd.,1993.P.619.)从学界观点看,美国学者多认为董事不能利用公司因财力不足而不能利用的机 会。如汉密尔顿认为,“董事经常以公司不能筹措到实施机会的足够资金为由为自己利 用公司机会辩护。但这种抗辩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允许董事这样做的话,则董事可能 不会为公司利益尽其最大努力。”[10](P.412)汉恩认为,“如果公司没有财力实施一 个机会,董事和公司高级职员当然没有义务用自己的钱帮助公司实施该机会。然而,董 事和公司高级职员应当尽其最大努力帮助公司获得必要的资金。如果他们未尽其最大努 力而是自己利用了这一机会,则不能以公司无财力实施该机会因而该机会便不再是公司 机会为由进行辩护。即使董事和公司高级职员尽了最大努力以帮助公司筹集必要的资金 ,但最后并未成功,他们也不能自己利用该机会,即使是利用该机会的一部分也不行。 ”(注:关于公司无财力利用机会问题,见Harry G.Henn & John R.Alexander.Laws of Corporation,West Publishing Co.,1983.P.464.)
笔者认为,对公司无财力实施的机会,董事不能仅以公司无财力实施为由便篡为己用 。否则,对能够赚钱的公司机会,公司将会“永远”没有财力实施,公司利益将处于任 董事宰割、毫无保障的境地。如果对某一机会公司确无财力实施,而公司董事又欲利用 该机会,则可根据自我交易规则,由公司同意董事利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董事才可 利用公司无财力实施的机会。
对公司不能实施的其他机会,笔者认为,只有当此种不能导致该机会不再是公司机会 时,董事才能自由利用。否则,如董事要利用,仍需取得公司的同意。这是因为,除非 该机会本身是一个事实上不能或法律上不能的机会,否则公司都可通过各种方法克服其 不能,从而利用公司机会,如果公司董事有权运用其任职公司不能利用的商业机会,则 董事势必不会努力促成公司克服此种障碍,从而不利于保护公司利益;而对一个本身在 事实或法律上不能的机会,如以摘星星或杀人为标的的合同,董事也不可能利用它。
五、董事违反公司机会准则的法律后果
董事违反公司机会准则,将公司机会篡夺自用,当然会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此法律 效果,有对外效果与对内效果之分。对外效果,是指董事违反不得篡夺公司机会义务利 用篡夺来的公司机会所进行的交易本身的效力如何;对内效果,是指董事违反不得篡夺 公司机会义务在其与公司之间所发生的法律上的后果。
(一)对外法律效果
一般认为,董事违反不得篡夺公司机会义务而实施交易行为本身并不因董事违反义务 而无效。这一点与董事违反自我交易规制义务的法律效果不同。董事违反自我交易规制 义务而实施的行为,可因公司或股东的申请被宣告无效或可撤销,此为各国通例。(注 :《日本商法》第266条、《韩国商法》第398条、美国《1984年模范公司法》第8.31条 等。)董事违反不得篡夺公司机会义务实施的行为与违反自我交易规制义务实施的行为 ,同为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而进行的行为,为何法律在其对外效果上的态度截然相反。 这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自我交易 中更好地保护公司利益。在董事自我交易中,公司是交易的一方当事人,由于董事在交 易中可能牺牲公司利益,如果公司仅得对董事行使归入权或请求损害赔偿,由于损害赔偿并不能在完全意义上弥补损害[11](P.9),而宣告交易无效或撤销交易所具有的恢复 原状的功能能在更大程度上弥补损害,故赋予公司以请求宣告交易无效或撤销交易之权 ,可更好地保护公司利益。在董事违反不得篡夺公司机会义务的场合,受害公司并非交 易一方当事人,如强行规定此种交易无效或可撤销,则一方面会极大地危及交易安全; 另一方面,由于交易双方有时均是该交易的受益人,其没有动力申请撤销交易,也不会 主动执行无效的认定,这在实践中有时就根本不具可行性。
(二)对内法律效果
董事违反不得篡夺公司机会义务的对内法律效果,即董事篡夺公司机会的责任。关于 董事篡夺公司机会的责任,在普通法国家主要有三种:赔偿受害公司因机会被篡夺所遭 受的损失;交出因篡夺公司机会所实现的利润;将董事篡夺公司机会实现的利益视为为 公司设立的拟制信托。(注:关于这一问题,见Harry G.Henn & John R.Alexander.
Laws of Corporation,West Publishing Co.,1983.P.465.)要违法董事交出因篡夺公司机会所实现的利润及将董事篡夺公司机会实现的利益视为为公司设立的拟制信托,相当 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归入权,故从公司角度来说,对违反不得篡夺公司机会义务的董事, 其有两种权利:归入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
六、我国导入公司机会准则问题
在现代社会,信息就是金钱,机会就是财富。公司营利目的的实现必须仰赖对一个个 交易机会的把握。交易机会之于公司的重大意义,无庸多言;董事不得篡夺公司机会的 道理,不言自明。问题是,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之下,有无必要导入公司机会准则,如 何导入?
(一)我国应否导入公司机会准则问题
由于不得篡夺公司机会义务是为保护公司利益所必须赋加给董事的一项义务,故对我 国应否导入公司机会准则这一问题的回答就取决于我国现行法是否包含了对董事篡夺公 司机会行为的规制。纵观我国公司法,可能与董事篡夺公司机会行为有关的条文主要有 两条,一条是《公司法》第59条第1款的规定;一条是《公司法》第61条第1款的规定。 前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地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 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后条规定:“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者 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从事上述营业或 者活动的,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即前者是董事忠实义务的一般规定,后者是董 事竞业禁止义务的规定。
忠实义务的一般条款不足以防范董事篡夺公司机会,对此前已述及,故我国应否导入 公司机会准则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竞业禁止义务的规定是否能够包含不得篡夺公司机会 义务。对此,我们认为,虽然这两种义务规范的对象存在许多重合,但它们是一种交叉关系,而不是属种关系。诚然,董事有可能通过篡夺公司机会的方式与公司竞业,但董 事篡夺公司机会并非均用于与公司竞业。如,某董事在替公司寻找商业用地时,发现了 一块地段好、价格便宜的土地,于是便为自己买下该土地用于建造住宅。此时,该董事 的行为并不构成竞业禁止义务之违反[8](P.111),但其行为明显违反了不得篡夺公司机 会义务。再如,董事在任职期间得到一个交易机会,于是立即向公司辞职,并在辞职后 利用了该机会,则其行为也不构成竞业禁止义务之违反,但该行为却违反了不得篡夺公 司机会义务。可见,违反不得篡夺公司机会义务不一定同时违反竞业禁止义务。同样, 由于董事与公司的竞业行为虽然有时也表现为篡夺公司机会,但并不一定表现为篡夺公 司机会,如某董事虽为他人进行与所任职公司相同的营业,但其并没有篡夺该公司的机 会,故董事违反竞业禁止义务并不一定违反不得篡夺公司机会义务。因此,不得篡夺公 司机会义务与竞业禁止义务不是种属关系,而是交叉关系。
正因如此,仅仅依靠竞业禁止义务并不能惩罚所有篡夺公司机会的行为,(注:国内学 者张开平先生也认为,我国《公司法》第61条第1款之规定“不足以禁止董事‘篡夺公 司机会’的行为”(见张开平:《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第312页)。)也不能很好地保护公司利益,防范董事败德行为的发生。因此,为更好 地保护公司利益,我们有必要导入公司机会准则,确立董事的不得篡夺公司机会义务。
(二)我国如何导入公司机会准则问题
由于我国《公司法》已规定了竞业禁止制度,故需公司机会准则防范的仅是竞业禁止 制度所不能及的违反忠实义务行为。不仅如此,公司机会准则确立的不得篡夺公司机会 义务与竞业禁止制度确立的竞业禁止义务在设立宗旨、法律后果方面具有许多相同的地 方,这就决定了我国将来导入公司机会准则时,并不需要专门规定单独的公司机会条款 ,只需在《公司法》关于竞业禁止义务之规定的后面加上一款即可,即将“董事、经理 篡夺公司机会的,亦同。”作为《公司法》第61条第2款。(注:当然,这得建立在我国 公司法关于竞业禁止义务的规定,如事实披露、竞业许可程序、归入权的除斥期间等均 得到完善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