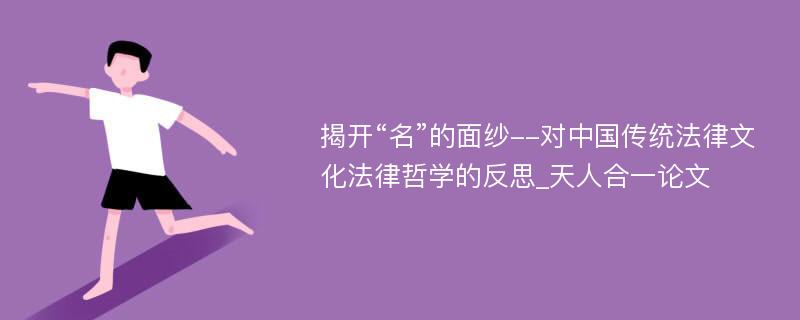
揭开“名分”的面纱——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法哲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文论文,名分论文,中国传统论文,面纱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一兔走百人逐”与“明代的大礼议之争”
“名分”仿佛一个魔法棒,可以带来名利、身份、荣誉、地位等,“名分”甚至也是王权统治合法化的根基。似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名分”情结,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分如此重要,于个人而言,是个体“人格”的象征;于统治者而言,是其合法性的根基;于国家而言,是社会秩序稳定和国家繁荣昌盛的前提;于社会而言,是伦理体制和律令规范的价值标准。“名分”何来如此大的魔力,还需从源头上揭开名分的面纱,以便从法哲学的意义上进行反思与批判。
“名分”与法律的关联始于战国时期的“法术之士”提倡的“定名分”,即制定并推行国家的法令制度。①《商君书·定分》讲:“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民皆愿愨而各自治也。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②
“名分”这个概念是两个单独的概念“名”和“分”的合称。最初主要是指社会成员根据不同的角色、身份而遵循的各种规范。经过历史的演进,名分已从微观(个体交往)的“定分以止争”,以确定“土地财货男女之分”,③ 大到关涉皇权的合法性了。明嘉靖年间发生的“大礼议”事件,前后持续20余年,16名大臣被“廷杖”致死,受牵连下狱的四品以下官员达134人之多。④ 这就是历史上经典的“名分”之争。事件的大致缘由、过程和结果是:正德十六年,武宗皇帝猝然而逝,其在世既未生子立嗣,又无同父兄弟。皇位由谁继承?于是,如何既合儒家礼法又能保证最高权力的顺利过渡成为朱氏皇族和满朝文武亟待解决的难题。内阁首辅杨廷和以《皇明祖训·法律》中“兄终弟及”的规定为依据,提出迎立武宗叔伯兄弟朱厚熜入继帝位。杨廷和的迎立主张得到慈寿皇太后(武宗生母)的准允,形成定策,以武宗“遗诏”和太后“懿旨”的名义公布天下。于是,朱厚熜入嗣帝位,是为世宗,年号嘉靖。但是世宗并不是以皇太子而是以外藩亲王入继帝位的,而且不属于孝宗—武宗这个宗支,这样就在封建礼仪上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是只继帝统,还是既继帝统,又继宗统?是仍为亲生父母之后,还是过继给伯父孝宗、伯母慈寿皇太后为后?如何追尊亲生父母的封号?等等。在嘉靖皇帝亲自发动之下,举朝上下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规模巨大、旷日长久的争论。⑤ 经过朝廷两派宗法理论之争到党派政治之争,最后以嘉靖皇帝“对父亲的追尊无以复加,自己的皇权登峰造极”⑥ 的结果,大礼议从而宣告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牵连无数人官爵、甚至性命的礼仪大战,仅仅是为了“名分”之争。杨廷和以继统又继嗣的封建宗法制度之正统理论论证世宗皇位的合法性,另一派提出继统与继嗣的根本差异,以封建礼法中的“孝”为理论论证皇位的合法性。两者虽然都是论证世宗皇位的合法性,但是两种理论的后果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的帝统还是宪宗—孝宗—武宗这一宗系,只是因为传至武宗而中断,需由小宗兴献王宗支的朱厚熜入继帝位。他就必须由小宗兴献王宗系改入大宗孝宗宗系。而小宗入嗣大宗,旁支入承正统,又必须立为大宗之后,成为大宗之子,而改亲生父母为伯叔父母。这样世宗必须入继孝宗宗系,而改成自己的父母为兴献王、兴献王妃为“皇叔父”、“皇叔母”,自称“侄皇帝。后者则以“孝”的理论为基础通过“更定祀典”(包括尊天地、亲祖宗、教天下、祈五谷)达到“以子帝父”,维护自己的正统帝位。⑦
从上面两则案例可以看出“名分”事小,小到涉及“一兔”的归属,而“名分”事大,大到关乎皇权的合法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宗法制度、礼乐制度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名分制度,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制”社会,中国的法制就是宗法制度。所谓的“人治”、“法治”其实都是治人,对僭越身份、名分的人进行惩治以恢复身份等级制度。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就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⑧ 因此礼对具体的个人而言就是名分制度,包括血缘名分与社会身份;礼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皇权的合法性基础。礼要求体制内的每一个人都自觉地遵守并维护名分规则、各负其责、各安其分;礼也要求皇权的统治是合乎“名分”的正统统治,否则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直接影响其统治的权威性和稳定性。那么为什么“名分”会如司马光曾指出“名分虽小,其事关重大”呢?⑨“名分”如何能维系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是如何构建整个社会秩序的?它又如何能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元概念”⑩ 的?甚至它又是如何能成为中国人内心挥之不去的沉重的情结,做个好事也得要有个“名分”,就连没有“名分”的汽车也跑不远。在中国,从人到物无不打上“名分”的烙印,官场排名、职称职位、家庭朋友、现代的科研成果、就连做志愿服务也得有个“名分”。(11)“名分”神秘面纱的背后到底包含着怎样的内涵?我们先来看看“名分”概念的内涵。
二、“名分”的含义及其理论根据
“名”,《说文解字》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思是古代人夜间走路,暗不相见,说出自己的名字以避嫌。可以看出“名”的最初含义是指人或事物的名字或名称。后来经过发展,“名”代表了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身份和位置,如国家管理系统的君、臣、公、侯、卿、大夫,家庭领域的父、子、兄、弟、夫、妇,职业领域的士、农、工、商等;(12)
“分”,《说文解字》云:“分,别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别物也。”邹昌林根据对古礼的研究指出:原始人们在集体狩猎之后,要根据氏族内不同人的不同贡献、需要对兽肉进行分配。(13)“分”字的本义为分割、划分、分别、分配等,“分”(读一声:动词)的结果即“分”(读四声:名词)是指份额。“分”在最初反映了古代人们对资源的一种分配原则和制度。在后世中,所分之物演变成土地、物品以及标志社会身份和权力的礼器。司马光指出:“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14) 这里“分”是指某种身份或出于某一社会位置的个体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如君臣上下之分、男女之分、职业之分等等。(15) 对于个体而言,不同的个体根据不同的位置和身份、血缘有不同的“名分”,同一个个体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名分”也不相同,不同的“名”对应着不同的“分”。在传统中国,即使是最细微的角色概念都是与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这些宏观命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等任何一个角色都关涉社会秩序和制度规范。
“名”对统治者的重要性最初是由孔子提出来的,根据《论语·子路》篇的记载,孔子在对子路问政的时候回答:“必也正名乎。”(16) 原因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礼记哀公问》中有类似记载。(17) 孔子强调“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规定了一个人的意义,人的意义源自于其名,为政的首要问题就是要使得社会各阶层的人名符其实,各安其分,各有与自己名份相符的名称和角色要求,所以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8) 而且孔子认为:“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19) 理由是什么呢?孔子解释说:“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20)“名”在这里主要指爵号、名位、官职等社会角色的名称,它代表着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与地位。“器”指与角色身份相适应的器物,代表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应享受到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同时“名”、“器”与“信”、“礼”、“义”、“利”之间具有内外勾连关系的。(21)
既然正名如此重要,那么怎样才能确定每个个体的“名分”呢?孔子提出了名实相一致的原则。那么如何才能名实相一致呢?董仲舒提出“名”作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起源于天地自然秩序,根据天地自然的秩序规定人类社会的秩序,作为人们判断是非的依据。(22) 所以要想把“名分”制定好,就要求按照自然秩序的性质(包含物性和人性)和运行规律,通过“裁物定分”达到“分之以其分”。孟子将完美地履行社会规范视为人之本性的真实体现。“守分”就是“循理”,对合宜恰当之“分”的遵守即是对“理”的遵循。“理”是“道”的具体化,而“分”作为“理”的一种体现,也同样是道的具体化。(23) 后世将“名分”当作人之必然命运的思想也导源于此。(24) 这里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哲学观。天地、自然、人、社会、家与国都是浑然一体、同源同构的。正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 人们通过研究自然、分析人的“名分”的内在逻辑,自然秩序与人类秩序的原理是同构的,都是“道”(既是天道又是人道)。
总之,“名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含义是社会角色和角色规范,在整体上则体现了传统社会的秩序构架和制度内容。这种秩序构架和制度内容在本质上是对自然秩序的摹拟,对自然界不同物种之间差异关系的一种摹拟。如同石头、树木、飞鸟、野兽都各有自身的存在规律一样,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这些社会角色也被看成是有着天然不可违抗的行为规范。人们都应当按照自身的角色规范行事,违反了角色规范就像石头说话、树木走路一样是对自然之道的违背和侵犯。正是通过这种秩序设计,传统中国社会才构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社会管理方式。“名分”思想就是对这种管理方式的理论设计和论证,而以“名分”为核心的社会管理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成为“名分”思想探讨的主要内容,也是“名分”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26)
三、“名分”的理论对中国法文化的影响
既然“名分”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中每个个体的社会角色(身份、地位等)以及与角色相应的规范(权利义务等),那么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和社会运转来说,如何制定“名分”,并使“名分”得到广泛的认可是极其重要的。具体而言,这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制定“名分”的原则与价值标准,即用中国古代的哲学观阐述“名分”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二是,“名分”的具体内容,为每一个个体提供行为准则和规范,如文章开头的“一兔走百人逐”的案例正是说明“定分”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性,战国法家慎到解释说:“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27) 三是,保障“名分”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教化和惩罚两种手段。这分别可以相当于现代法治社会的三个方面:第一方面相当于现代法治社会的宪政和法治原则的论证和确定;第二方面相当于现代法治社会的立法;第三个方面相当于现代社会的司法和执法。当然三个方面的内容和原则以及价值标准是完全相异的,只是在形式上具有某种可类比性。具体而言“名分”作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元概念具有以下特征:
1.制度法律以宗法精神为价值指导。中国传统法律的特点是以礼入法,名分入律。郑定教授在《论宗法制度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指出:“唐律名例篇(总则)中区别尊卑、长幼、亲疏等级名分规定适用法律的不同规则。无论刑法、民法、诉讼法都区别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不同名分,规定了不同的法律责任和不同的权利义务。”(28) 法律不仅授予家长、族长种种特权,如对财产的支配权、子女的主婚权:《诗经·南山》说:“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家长、族长等本身可以是执行法律,甚至制定相应的惩罚。在这个意义上,家长、族长本身就是法律的代言人。凡家庭中有关户婚、田土、斗殴等民刑案件,以及子孙族人的违法(包括国法、家法)事件,总是先由家庭自己处理。祠堂作为宗族法庭,族长作为实际上的第一审裁判者,进行裁判,并依家法判处和执行不同的惩罚。比如闽县林氏族夫规定:“我族……如有忤逆泽伦,凶横无忌之徒,该父兄投鸣户首族长,捆送人祠答责。”(29)
2.名分在律法上体现为伦理纲常的礼教。梁治平先生认为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中表达了两个命题:第一,中国古代社会是身份社会;第二,中国古代法律是伦理法律。(30) 这种社会的特色就是法律的权利义务的分配与承担是由个人的身份来决定的,名分构成了伦理纲常的根本。法律规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31)“父而赐子死,尚安敢复请?”(32) 到了唐宋律,虽然父母杀死子孙皆处徒罪,但如果子孙系犯教令而杀之,需要较故杀罪减一等。(33) 再比如,子女对父母须以恭敬顺从为本,常人相骂不为罪,但是子孙骂父母、祖父母却是犯罪,按唐宋明清法律当处绞刑。总之,家族高于个人,名分终于责任,依此原则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34)
3.同罪不同罚皆因“名分”相异。法律区别尊卑、长幼、亲疏确定了各种不同的刑事责任。中国传统法律的处理原则是:以尊犯卑,其罪轻于常人,服制愈近,其罪愈轻;反之,以卑犯尊,其罪重于常,服制愈近,其罪愈重。如唐律规定,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等近亲属,不论既遂未遂、已伤未伤,皆斩;谋杀绍麻以上尊长,未遂者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而谋杀常人未遂者仅徒三年。相反,祖父母父母杀子孙,其罪责远轻于常人。关于侵犯财产的犯罪,《唐律疏议·贼盗律》载:“盗缌麻、小功亲财物者,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而凡人窃盗,不得财笞五十,一尺杖六十,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每五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35)
4.“名分”之礼对王权具有合法性认证的功能。“在古人的观念,忠孝相提,君父并举,视国政为家政的扩大,纵没有将二者完全混同,至少是认为家、国可以相同,其中并无严格的界限。”(36) 家庭的律令最高原则为孝,国的律令最高原则为忠。忠孝原则通常相通,即国家相通,忠孝相通。正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37) 以孝悌为根本原则的伦理纲常是与代表国家权力的皇权相统一的,“忠”本身就是最高的孝,忠孝在最高原则上是一致的,只是在一般的孝和最高的孝(即忠)之间发生冲突。(38) 这个时候看起来是国与家相冲突了,个体的伦理与国家的原则相互冲突了。其实是国家的伦理原则自我相冲突,因为自然血缘和情感具有偶然性和特殊性,而不具备作为原则所必备的普遍性和一贯性。而正是从对冲突的解决中,我们可以看出基于“名分”的宗法伦理的本质,即维护君权的工具。既然如此,一切个体权利不过都是工具而已,即便这个个体权利是符合伦理纲常的,它只要与君权相冲突,也必须被消除。“据历代法律,凡罪涉谋反、谋叛、谋大逆等直接危及皇权、国家的情事,什么容隐、子孙不得告父母、子报父仇,都化作乌有,犯者定严惩不贷。本人身首异处还算是侥幸,弄得不好还要株连三族、九族。”(39) 这里很直白地表述了一个理念:所谓以家的伦常为基石的名分以及由此而制定的国之律法,不过都是手段而已,所谓家国一体只是用以纲常名教以及相应的律令为手段来服务于“王”。“名分”因而成了一个合理化和正当化的工具,甚至连君王也不能违反“名分”,与“名分”不相符合的王权是不正当的。这就是为什么嘉靖皇帝要追封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皇帝,而朝廷的大臣们不惜以牺牲身家性命的代价加以反对,其实都是为了“名分”的正当性,嘉靖皇帝争取“名分”是为了其王权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而朝廷大臣们维护“名分”是为了维护封建纲常的稳定。虽然各自的理由不同,但是其实都是争的一个“名分”。因为名分是能够将自己的行为和利益正当化和合法化的工具。(40) 尽管明嘉靖在表明自己继位合法性上采取了与汉光武不同的名分认证和礼仪,但只是“名分”的质料(具体内容)不同,而要符合“名分”的这一形式是一致的。所以皇位继承必须“名正言顺”,必须以基于血缘伦理礼仪制度的“名”去正皇位继承的“实”,从而获得并巩固民众对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信念,这一切不过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建立最高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普遍思路。可见“名分”之礼对王权具有合法性认证的功能。(41)
总之,中国的礼法包罗万象,凡伦理纲纪、礼仪习俗、法律政令、无不包含于其中。而西方的“法”概念不管是拉丁文:Jus,德文Recht还是法文Droit本身含有公平、正义、权利等内涵,而中国的“法”的概念并没有内涵着这些理念,相反“法”只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术”。
四、“名分”制度之反思与批判
很容易看出中西方法文化有一个出发点的不同,西方的“法”及“法治”本身内在的要求正义、权利等理念,而这些内涵不断地历史演化,发展成“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权力制约”“分权制衡”等自然法的观念。而中国传统法理念的出发点是“君权”,是巩固统治的一种工具,本身并不具备正义公平权利等内涵。“法的工具主义”本质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走出“法律工具主义”。“法治”是治国手段,“手段”即“工具”(如“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42),表明“法”本身并不具有“目的性”或“本体”的意义。(43) 所谓的“德治”、“法治”、“人治”其实都是治人,都是治理之术,将名分制度与百姓的日常经验进行贯通,使之成为一种生活自觉,“日用而不自知”,产生一种强大的惯性力量使名分制度中的个人对之形成一种制度性依赖,如此形成一种天然秩序。(44) 但这一切表象不过是中国古老的哲学观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律法上的显现。
本文最后主要从法律文化、制度上做法哲学反思。也就是反思: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是一个身份社会、法律为什么是一种伦理法律,制度为什么是宗族制度,君为什么要围绕“名分”来统治,而民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名分”统治?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天人未分”之朴素自然哲学观;第二“情感本体论”;第三;“人格的他定:关系论”,最后导致个体意志、个体自由的取消。而且这几个方面都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一)“天人合一”与“天人未分”
“天人合一”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从先秦到晚清,“天人合一”一直都是哲学家们宣扬的理念。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45) 的书。汤一介先生认为《郭店楚简》把《易》看作是一部讲“天人合一”的书,因为《易经》本来是一部卜巫的书,它是人们用来占卜、问吉凶祸福的。向谁问?向“天”问,所以说《易》是一部“会天道、人道”的书,阐明的是“天道”和“人道”会通之理。(46)《说卦传》里面也讲:“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情,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即用“阴阳”对应“天道”,用“刚柔”对应“地道”,用“仁义”对应“人道”,把天地人统一起来看都表现为“乾坤”。刘立夫先生将天人合一的内涵概括为:1.天人相类、天人同构;2.天人一体;3.天人同性:天之性及人之性;4.天人同理,“天道”即“人道”。(47) 天人相类、天人同构,就是用天道来说明人道,同时又反过来用人的感情来移情于自然。
其实“天人合一”命题主要的根源还是天人未分(主客体未分、思维与存在未分)的思想。从逻辑上看,所谓“合一”,那就有个前提,就是“有分”、“有异”、“有二”、“有间”,如张载说“如非有异则无合”、“凡物必两而后可以言合”。(48) 是不是只要提出了“天人合一”就有主客二分了呢?其实不然。儒家学者在说明其“天人合一”理论时,经常使用“本”、“原”、“初”、“大人”、“仁者”等一些限制性字眼,严格规范其使用范围。(49) 只有“仁者”、“大人”、“圣人”等才能“浑然与物同体”、才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50) 也就是只有认识到“天道”的圣人们才能天人合一。苗润田教授将“天人合一”的内在理论分为“本然、实然、应然”三种径路,认为天人合一是本然,而天人二分是实然,圣人经过教化而达到的天人合一为应然。(51) 这种划分是很有道理的。但应然的天人合一还是回到了“本然”状态,也就是回到天人未分的状态。故实际上还是讲天人未分的状态才是最本然的,最应该追求的,才是最核心的思想。如“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董仲舒);“天人之本无二”、“天人一物”(张载);“天人无间”、“天人一也”(程颢)、“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朱熹);“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王阳明)。
而天人未分思想的本质是思维和存在未分、主体与客体未分,导致认识论与价值论的混沌一体,求真即为求善,求善即为求真,如此一来,认识论上的“真”(真理)隐去了,变成了价值论上的“真诚”(善),最为真诚的当然是自然,所以人要回归自然,人之本性即为自然,而人道必然要遵循天道。既然人道是天道决定的,那么当然“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52) 人间的政治秩序合理与否,伦理纲常正常与否均可以从天那里得到验证。甚至连人的性命、祸福皆出于“天”。(53) 人生之意义就在于体证“天道”,人生之价值就在于成就“天命”。人的一切都是被决定的,被自然决定,被根据自然(血缘、地缘)而规定的伦理纲常所决定,人的自我意识及一切自由天然地被取消了,或者根本没有苏醒。
(二)“情感本体论”
前面将“名分”制度的根源追溯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自然哲学观,其实中间还有一个过渡,一种方法论上的过渡,就是这个“名分”的根源在这种哲学观,而这种哲学观又是通过一定的方法或方式制定下来的。这种过渡方式从逻辑上说是一种不周延的类比方式;从修辞学上,是一种移情方式;从方法论上讲就是“情感本体论”。比如黄帝内经:“天圆地方,人头圆而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54) 就是用“天”来类比人。而董仲舒则用人的感情移情于自然:“春气暖者,天之所以爱而生之;秋气清者,天之所以严而成之;夏气温者,天之所以乐而养之;冬气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55) 用人的“爱”、“严”、“乐”、“哀”的情感移情于自然。而天人一体,是因为天人同质,同质皆因同源,源自“气”。最后中国哲学实质上是一种“气”的哲学。董仲舒说:“人之受命于天,取仁于天而仁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56) 把天比作人的曾祖父。中国古代朴素的自然哲学观,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以自然为标准,一切以血缘为标准,一切以祖先为标准,这也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一切向后看,向祖先看的特点,难以形成超越和创新的思想。
情感本体论是美学上的一个说法,但是正如邓晓芒教授说:“中国人对任何事情都采取一种情感态度。”(57)“移情”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思维方法、一种中国特有的“逻辑推理方式”。而情感已经不是个体情感,是一种“制度性情感、伦常性的情感”。(58) 那么这种情感制度化之后,就是一种“名分”的情感,也就是按照“礼法”、“名分”规定好的情感,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被承认的情感。而制度化的情感是根据血缘关系制定的,包括阴阳、孝悌、天地、男女、乾坤,这些都是自然生殖方面的血缘性情感。(59) 如“乾为父,坤为母”,“乾坤者,万物之男女也;男女者,一物之乾坤也”。(60)
为什么中国的这种情感不是一种个体自然(这里的自然情感是还没有经过制度化的私情感)的情感,而是一种“名分”的情感呢?因为“情感”属于“人道”的一部分,而人道服从天道、天理,凡是不符合天道、天理的情感皆为非法的情感,什么是符合天理、天道的情感呢?那就是根据血缘、地缘关系(通过自然的移情)规定伦理纲常,然后制定的“名分”情感。
既然“人之受命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那么服从祖宗(孝)、服从天子(忠),就是服从天道、天理。所以中国传统的律法主要是宗法即祖宗之法。“个体”(私)情感与“名分”情感有差异,就需要教化,所谓教化的“教”实质上就是“孝道”的驯化。“名分”制度就是根据人们能够体验的情感将血缘关系制度化。如集封建法律之大成的唐律共五百多,其中直接以血缘关系主题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文有七十多条。再如“准五服而治罪”的原则。如伦理纲常的“伦”即人伦,也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特点就是交往主体之间的自然血缘联系,而君臣、朋友是通过移情的思维方式而拟血缘化或泛血缘化。郑玄注“伦理”曰:“伦,类也;理,分也”(《礼记正义》)。所以伦理最终要确定的是人伦(血缘)关系中的“名分”。
(三)“关系论”与人格的他定
“名分”对“民”(这里是指个体)如此重要,以至于关乎“民”作为一个人的根据。那么这种文化认同和人格的自我认同的根源在哪儿呢?根据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观,当然根在“天道”,但是“天”何言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天道”不言,那么就由“人道”来“名”了。那么这个“名”要符“实”,就要符合“仁”、“义”了。“仁”简单说就是“二人关系”。(61) 冯友兰提出孔子正名学说的含义时说,“名”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在语言名称上的反映。(62) 也就是说,个体自身没有独立性,个体的根据和人格是由一种关系决定的,是先定的,是他定的(也就是被决定)。个体被消融在关系中,被消融在群体中;或者说,个体与群体合一,与关系合一,最后才能达到天人合一。个体被淹没在群体中,群体代表了一种自然关系,但是这种自然关系与兽群(如牛群、马群等)不同就在于个体遵守各自的“名分”、坚守各自在关系中的“位置”而不僭越,群体已经成为了一种以名分为基质的社会模态关系。
个体的人格就被“名分”所决定,本质上是一种人格的他定。就像“人道”被“天道”决定一样。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源在于主客体未分,天与人未分,个体与群体未分。个体没有被自我(主体)当作客体(对象)来反思,而是被一种关系来决定,当然首先是被一种血缘关系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就不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因为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以及独立的个体人格,只有一种不同的等级关系。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一种自由的契约精神。因为契约精神的首要前提就是个体的平等以及独立的人格意识。
所以“名分”不仅仅是一种统治者的统治借口,而重要的是“名分”是使个体意志(包括君主的这个个体)取消的根源,“我是谁?”无论是天子还是庶民,这个问题是自我意识觉醒的第一个追问与反思。笔者认为“自我认识自我”是个体人格(笔者将人格界定为以自我决定性的资格与能力为基质的同一性表象)的第一次觉醒。但是这个觉醒无疑是王权统治的一柄利器,直刺王权统治的心脏,直接后果就是挑战皇权统治的正当性。所以“名分”是皇权统治的一个盾牌,“你是谁?”你就是“名”与“分”,就是你所代表的“名分”。我是“天子”这也是“我”的名分,名分就是“我”的统治的正当化根基。如果不符合天子的“名分”,那么统治当然就是失去了合法性和正当性,如前文中明代的大礼仪之争也体现了这种逻辑思路。所以孔子认为统治者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正其名。并且就连“君”这个个体同样也不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名分”于统治者来说,如其说是他统治的正当化借口,倒不如说是人性结构中的自欺性。那么“民”如何能认同这个“名分”的他者定位呢?靠教化与律令。“名分”于是成为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一个元概念,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影响至今的一个基本概念。
注释:
① 参见丁小丽:《孔孟荀“名分”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10页。
② 《商君书·定分》。
③ 《商君子·来民》。
④ 《明世宗实录》卷41,嘉靖三年七月戊寅条。转引自俞荣根、徐燕斌:《名分之礼与王权的合法性认证》,载《法学家》2007第6期。
⑤ 参见张显清、明嘉靖:《大礼议——起因、性质和后果》,载《史学集刊》1998第4期。
⑥ 前注④,俞荣根、徐燕斌文。
⑦ 参见前注④,俞荣根、徐燕斌文。
⑧ 《资治通鉴》卷一。
⑨ 参见前注⑧。
⑩ 唐丽玮:《名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元概念》,载《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6期。
(11) 看看下面一些文章的标题就能明白“名分”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想获得“国家认定”名分必须身手不凡》,载《经济参考报》2006年10月13号第1版;顾土:《沉重的名分感》,李胜:《科研成果为何非得讨个“名分”》,载《深圳商报》2006年9月6日第A09版。孙荣飞:《名分难求小产权房“善后”陷决策困境》,载《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12月18日第A3版。谭雨:《为讨名分90民办教师六上法庭》,载《中国教师报》2005年8月17日第A1版。陶峰:《文化纯不纯,“原来在名分”》,载《解放日报》2007年9月25日第2版。王眉灵:《有“名分”志愿服务免尴尬》,载《成都日报》2008年12日6日第A2版。管德泳:《没有名分的车还能跑多远》,载《中国企业报》2001年07月10日第6版。
(12) 参见前注①,丁小丽书,第3页。
(13) 参见邹昌林:《中国礼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1-83页。
(14) 参见前注⑧。
(15) 参见前注①,丁小丽书,第3页。
(16) 《论语·子路》。
(17) 《礼记哀公问》: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
(18) 《论语·颜渊》。
(19) 《左传·成公二年》。
(20) 同前注(19)。
(21) 参见前注①,丁小丽书,第22页。
(22)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记载:“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为言,真也。故凡百讥有黮黮者,各反其真,则黮黮者远昭昭耳。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于是非也,犹绳之审于曲直也。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已。”
(23) 参见前注①,丁小丽书,第11-13页。
(24) 参见前注①,丁小丽书,第22页。
(25) 《老子》第二十五章。
(26) 参见前注①,丁小丽书,第14页。
(27) 《吕氏春秋·慎势》。
(28) 郑定、马健兴:《宗法制度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载《法学家》2002年第2期。
(29) 《民国福建闽县林氏四修支谱》卷二《林氏族规》。转引自前注(28),郑定、马健兴文。
(30) 参见梁治平:《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0页。
(31) 《清律例》二八。
(32) 《史记》八七,《李斯列传》。
(33) 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页。
(34) 参见周雪峰:《中西理性概念差异及其对传统法理念的影响》,载《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35) 参见前注(28),郑定、马健兴文。
(36) 参见前注(30),梁治平书,第8页。
(37) 《论语·学而》。
(38) 参见邓晓芒:《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载《学海》2007年第1期。
(39) 参见前注(30),梁治平书,第22页。
(40) 嘉靖皇帝的理由是:嘉靖即位是直接承明太祖之皇统,而不是继孝宗或武宗之嗣。他们解释说,世宗奉武宗遗诏即位,“则陛下为宪宗纯皇帝之孙,孝宗敬皇帝之侄,兴献帝之子,武宗之弟,伦叙当立,秩然不待文饰者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自祖宗列圣而传之武宗,孝宗不得而私也;武宗无嗣而传之皇上,武宗不得而私也,此正所谓兄终弟及,而不必为后者也。夫天下者,受诸其兄者也,既不必为其兄立后,又何必追为其伯立后乎?”他们旨在论证嘉靖帝不改嗣大宗而继位的合法性。参见桂萼:《太傅桂文襄公奏议》,卷一,《清正大礼疏》;《明世宗实录》,卷三八。而杨廷和等大臣们的理由是:只能尊崇一个大宗,一个正统,惟有如此才能维护封建纲常。追尊兴献王为皇帝等等,是越礼犯分之。
(41) 参见前注④,俞荣根、徐燕斌文。
(42) 《管子·七臣七主》。
(43) 参见周雪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生命力:开放性》,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44) 参见前注④,俞荣根、徐燕斌文。
(45) 《太史公自序》。
(46) 参见汤一介:《论天人合一》,载《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2期。
(47) 参见刘立夫:《“天人合一”不能归约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载《中国哲学》2007年第2期。
(48) 《正蒙·乾称》,《困知记》(卷下)。
(49) 参见苗润田:《本然、实然与应然——儒家“天人合一”论的内在理路》,载《孔子研究》2010年第1期。
(50) 《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阳明全书》卷26,《大学问》。
(51) 参见前注(49),苗润田文。
(52)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53) 如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性自命出,命由天降”。《礼记注疏·中庸》“天命之谓性”,注曰:“天命,谓天之所生人者也,是谓性命”。孟子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54) 《素问·宝命全行论》。
(55) 《春秋繁露·王道三通》。
(56)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57) 邓晓芒:《中西文化心理模式分析(续)》,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58) 参见前注(57),邓晓芒文。
(59) 参见邓晓芒:《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9页。
(60) 《西铭》,《周易集注·原序》。
(61) 参见前注(59),邓晓芒书,第58页。
(62)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