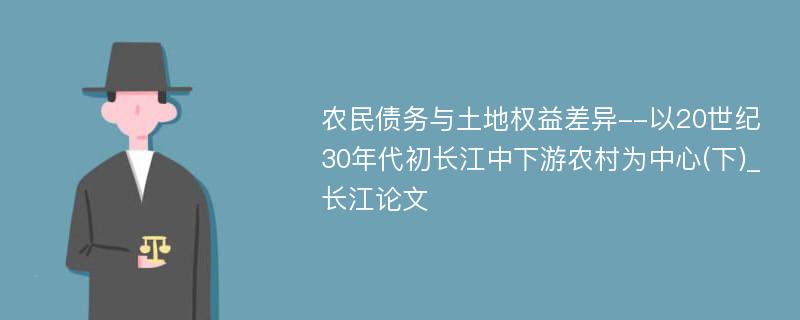
农家负债与地权异动——--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中下游地区论文,地权论文,之二论文,农家论文,异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六、宏观层面的地权集中考察
上文通过中、微观层面的农户阶层变化,论证了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地权的集中趋势,下面再以省为单位,对农户阶层变化进行宏观考察。关于省级农户阶层变化,学者们经常引用的是《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国民政府主计处编制的《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中的有关数据。现在依据这两个材料,把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阶层变化情况制为表6。
表6 20世纪60提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阶层变化(%)
类 别 佃农增减
自耕农增减
半自耕农增减
年 代 1931—1936 1931—1937 1931—1936 1931—1937 1931—1936 1931—1937 资料来源
湖+3
-6+3
(1)
南+3 -3 -6 -1 +3 +4(2)
湖+1
+3-4
(1)
北+1 -4 +3 +9 -4 -5(2)
江-6
+3+3
(1)
地 西-6 -8 +3 +3 +3 +5(2)
安-3
+1+2
(1)
区 徽-3 -8 +1 +6 +2 +2(2)
江-4
+5-1
(1)
苏+8 +12-11 -17 +3 +5(2)
浙-1
-1+2
(1)
江-1 -3 -1 +4 +2 -1(2)
平 均
-1.67 +0.83
+1.28
(1)
+0.33-2.33
-1.83+0.67 +0.5
+1.67(2)
资料来源:(1)《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8—730页;(2)国民政府主计处编:《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正中书局1942年版,第6—7页。
由表6可见,按照《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数据,佃农阶层1931—1936年平均减少1.67%,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分别增加0.83%和1.28%。按照《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根据《农情报告》第6卷第6期农户阶层变化数据和金陵大学调查数据加权平均编制),佃农和半自耕农1931—1936年分别增加0.33%和0.5%,自耕农减少1.83%;1931—1937年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分别增加0.67%和1.67%,佃农减少2.33%。从表6我们还可以看出,只有湖南和江苏分别依据《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表现为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符合地权集中的结论。而其他各省无论根据那种材料,农户阶层变化都显得非常混乱,而且基本上是佃农阶层减少,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阶层增加,据此似乎应该得出地权分散而不是地权集中的结论。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假象。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隐蔽性,即地权转移的幅度和转移的过程都不是十分清晰,必需经过认真辨析,才能看清其面目。
首先,自耕农占有田地数量变化与地权异动。表6只是反映了农户阶层变迁状况,而没有反映各阶层农户土地占有数量变化状况,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农户阶层变化——比如自耕农比例有所增加,就遽然得出地权分散的结论,30年代前期一部分自耕农“身份”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却减少了,即成为笔者所谓的“虚名自耕农”。例如,据调查,1928—1933年常熟7个村中农占地平均减少1.105亩,崇德8个村中农占地平均减少0.17亩。(注: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3页;《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1页。详细情况参阅《江苏省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附表。又,我们不能轻视小农丧失少量的土地的意义,对于占地本来就不多的小农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经济损失。)无锡自耕农占田面积30年代前期急剧缩小,全县10亩以下土地所有者,1922、1927、1932年分别为38.35%、41.5%和50.3%。(注:唐文起:《抗战前江苏农村土地所有权浅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据1937年7月调查,常熟全县80%的土地为地主所有,自耕农、半自耕农所有土地不及20%,每户农家所占耕地平均约为3—5亩,有的往往只有数分而已。(注:李若虚:《常熟县地政局实习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99辑,第52166页。)所以即使在有的地区,自耕农数量确实较多,但由于大多数自耕农占有土地面积缩小,地权仍然趋于集中(注:参见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此其一。如前所述,有的地区农户田地抵押借贷后,虽然名义上仍然是自耕农,实际上已经成为佃农,但是在农户阶层统计上,这种变化还没有能够反映出来,此其二。凡此都说明从某一个角度上说,自耕农阶层些微增多,并不一定就说明地权趋于分散。此外,表6还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是依据《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数据,还是依据《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绝大多数省份半自耕农阶层比例上升,应该主要视为自耕农失地所致,因为30年代前期由雇农和佃农阶层上升为半自耕农的可能性非常小。
其次,通过农户阶层变化分析地权异动,必须考虑30年代前期农民大量离村因素。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近数年来水旱频仍,无地农民无以聊生,弃耕而流亡者为数甚多,佃农减少,自耕农之比例即相形而似有所扩大,实则并无增加”(注: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49—46150页。),章有义先生也有类似提醒(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0页。)。据1933年调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家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总农户8%、10.2%、6.7%、7%、4.3%和2.7%,据1935年调查,上述六省占地5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农户离村总数53.3%、50%、44.6%、30.1%、52.1%和62.8%,占地5—10亩离村农户分别占农户离村总数23.3%、33.3%、25%、35.4%、36.5%和28.2%,两者合计,占地10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离村农户总数76.6%、83.3%、69.6%、65,5%、88.6%和91%。(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886—887页。)根据上述数据计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六省5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总农户4.26%、5.1%、2.91%、2.1%、2.24%和1.69%,5亩至10亩离村农户分别占各县所报告总农户1.86%、3.39%、1.67%、2.47%、1.56%和0.76%,10亩以下农户全家离村者分别占各县所报告总农户6.12%、8.49%、4.58%、4.57%、3.8%和2.45%。由此可见,所谓“全家离村农户”基本上为占地10亩以下农户,如果把这个数字加入各省佃农或者半自耕农占总农户百分比,则可以看出佃农和半自耕农阶层所占比例明显增加,说明地权趋向集中。
又次,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在一定时期内,农村劳动力总量和各阶层劳动力数量分配应该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各阶层劳动力变化也可以侧面反映地权变化状况。据陈正谟调查,30年代前期浙江浦江“年来农村经济破产,农人生产不易,因之,农工特增。最近,减低工资亦无雇主。”(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4页。)嘉兴雇农各处都有增加,原因之一是“本地农村经济衰落,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复沦为佃农,一部分沦为雇农,无形中增多雇农之数量”(注:冯紫岗编:《嘉兴县农村调查》,浙江大学1936年版,第100页。)。江苏武进因为农工过剩,造成工资低落。(注:张履鸾:《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金陵学报》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第24页。)安徽泗阳“农工太多,其原因大多由于前年(1931年)大水为灾,农村经济濒于破产。一般平民为维持生活计,不是卖地,即是借债,以致多数自耕农及佃户一变而为农工,以谋生活。”(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6页。)湖南沅江县农工“近三年(1931年以来)来总是呈现太多。其原因由于农村经济拮据,捐税繁多,致使失业者众,小农户亦变为雇农了。”(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6页。)据1933年调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雇农分别占各该省农村人口11.09%、6.04%、10.87%、8.24%、8.78%和9.27%(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70页。),这个比例明显高于从前(注: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49—463页。)。总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雇农普遍增多,主要由小农失地破产而来。
最后,表6中的农户阶层变化数据只具有相对意义。表6没有一一列出农户阶层历年变迁状况,如果分析其历年变动情形,真可谓漏洞百出,我们以《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中农户阶层变迁略作评论。(注:参见国民政府主计处编《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6—7页。)先看佃农阶层变化情况。江苏佃农1932—1933年上涨14%,1933—1934年又下降5%;江西1933—1934年减少16%,1934—1935年增加5%;湖南1935—1936年增加3%,1936—1937年又减少6%,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年之内佃农阶层发生如此大的变动,实在令人费解。自耕农阶层变动状况也是如此。江苏1932—1933年自耕农减少19%,1936—1937年减少6%;江西1933—1934年增加11%;湖南和湖北1936—1937年分别增加5%和6%;江苏1936—1937年减少6%;浙江和安徽均增加5%,一年之间,自耕农阶层如此大起大落,恐怕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1933—1934年湖南半自耕农增加5%,江西增加5%;湖北1935—1936年减少5%;安徽1933—1934年增加8%,1934—1935年减少5%,同样很难做出有力的解释。此外,《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两个材料关于同一省份某一阶层农户同时期内的变化,相互之间出入太大。例如,依据上述两种材料,1931—1936年江苏佃农分别减少4%和增加8%,自耕农分别增加5%和减少11%,半自耕农分别减少1%和增加3%,凡此,都不容易得到合理的解释。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必须说有关30年代前期农户阶层变迁数据只具有相对意义,只有结合其他材料综合运用,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七、地权集中的特点
通过上文论证,笔者认为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地权处于集中时期,并且具有较为明显的特点。
首先,从地权集中的规模看具有普遍性和不剧烈性。
所谓普遍性,第一个方面是就地域而言,地权集中不是个别地区的现象,而是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都存在这种情况。当然,普遍性并不是说各处地权集中程度是均衡的,事实上,各地互有差异,大概而言,江苏和浙江两省地权集中幅度高于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四省。第二个方面是就农户阶层而言,它涉及的范围广泛,不仅自耕农及其以下阶层农户丧失土地,而且一部分中小地主也加入了失地人群。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30年代前期受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中国农村破产,农民普遍贫困化,农户负债比例大幅度攀升,在生存第一原则的支配下,小农只有把自己最大的资产——土地作为度过难关和活命的凭藉,于是一部分小农抵押、典当乃至绝卖土地,从而引起地权集中。
刘克祥先生认为20世纪20年代,约有30%—40%的农民完全没有土地,60%—70%的有地农户约占有全国40%—50%的土地,其余50%—60%的土地为地主、富农占有(注: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中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3页。);但是30年代前期11.8%的地主、富农占有61.7%的土地,而占人口88.2%的中农和贫雇农,占有38.3%的土地,其中占人口66%的贫雇农,占地比例为17.2%,所以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恶性集中。在这里刘克祥先生是就30年代前期全国范围地权集中程度而言的,至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笔者以为地权集中是事实,但是并没有形成土地兼并狂潮,没有达到“恶性集中”的程度。
按理,既然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其幅度就应该是很大的,地权演变成恶性集中的可能性很大,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从表6看,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阶层并没有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其次,从各地地权变化状况也看不出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分配达到了恶性集中的程度。(注:另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06—717页。)例如,据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江苏、浙江农村调查,尽管农户负债比例很高,自耕农及其以下阶层农户丧失了土地,但是地权转移并不是非常剧烈。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浙江各县农村调查后认为,土地“转移情形并不十分显著”(注: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8页。)。江苏盐城“农田买卖情形,近来不甚活跃”(注: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40页。)。江都县1931年以后,因为粮价与地价猛跌,土地买卖减少。据第九区某中人说,1931年以前,他做土地买卖中人,“年可得佣金三、四百元,民二十年以后,年约得佣金二、三百元,去岁(1933年)竟无土地转移之事实矣”(注:吴致华:《江都耕地分配》,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6辑,第34792页。)。泰县1931—1934年间,因农村经济恐慌,土地“买卖关系,几乎全成停滞状态,虽纵有转移情形发现者,亦不过作债务之抵押”(注:许荣肇:《江苏泰县土地概况调查》,《金大农专》1936年10月秋季号。)。常熟的“田产转移比较停滞,这是近年来都市膨胀,农村偏枯情形下必然发生的现象”(注: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7页。)。湖北大冶30年代前期土地买卖呆滞,“因为在迭经兵祸之后,有钱的不愿再买地,无钱的就更不用说了”(注:李若虚:《大冶农村经济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2辑,第21041页。),所以地权很分散。因为经济衰落,30年代前期黄冈土地买卖也不如从前活跃,地权转移受到限制。(注:潘沺:《黄冈县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0辑,第31138页。)湖南湖田地区出现小地主驱逐大地主,小经营排斥大经营现象,地权也趋向分散。(注:彭文和:《湖南湖田问题》,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75辑,第39390页。)
之所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地权没有出现恶性集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土地所有者和富有资产者转移投资对象。时人评论道,虽然30年代前期“中国地权分配实不平均,地权颇见集中;不特如此,而且有渐渐愈趋不平均之势,即地权有渐渐集中的趋势”,但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大土地所有者卖地和有资产者投资工商业而不愿投资土地,所以“在最近几年中,长江流域并无显著的土地集中趋势”(注:吴文晖:《现代中国土地问题探究》,《新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1934年冬季号)。)。据曹幸穗先生考察,抗战前江南地区土地投资的年纯利润为8.8%,而工商业平均利润率分别为30.2%和31.4%,前者明显低于后者,所以“最富有者对购买田地已不感兴趣”(注: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总之,社会经济中心转移的宏观背景是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没有出现恶性集中的深层原因之一。
第二,国共战争的影响制约了地权转移。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民运动的高涨和中共开展的土地革命,地主饱受冲击,往往视土地为祸源和累赘。例如有的评论说,“‘赤区’的存在,以及各省各县农民抗租抗捐行动的频发,对于田产的转移,已经给予严重的威胁……(地主、富农)非但不敢买进田产,倒反尽力将自己所有的田产相机出卖。这种情形在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省最为明显。”(注:陈翰笙等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湖北地主“怵于过去因田买祸”,30年代前期土地“即使每亩价值一元或二元,也无人问津”。(注:湖北省民政厅编印:《湖北县政概况》第4册,1934年,第1134页。)不仅战区如此,风声所及,连长江下游地区的江浙地主也怀有同样心理,对买进土地持有戒心。
第三,限制地权大幅度集中的最主要原因是30年代前期农村破产,自然灾害频仍而猛烈,农民负担加重,土地收益大幅下降,换言之,30年代前期农村经济危机自身限制了地权大幅度集中。农村经济危机期间,虽然土地供给市场急遽扩张,为地权转移和土地兼并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危机同时也造就了一个相对萎缩的土地需求市场。因此,农村经济危机一方面提供了土地兼并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土地兼并。当时的情况是有地者人人皆欲出售土地而活命,从而形成土地市场供大于求,以致有地卖不出去的局面。这种状况在两个方面极大地限制了地权集中的程度,一是使有机会出售土地的农户减少,二是使农户能够卖出的土地数量减小。(注: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06—717页。)总之,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的畸形性限制了土地集中的幅度。
此外,小农零星细碎地抵押、典当直至绝卖土地的复杂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土地丧失速度,限制了地权集中程度;30年代前期小农普遍贫困化,由于担心贷款的安全性,高利贷者不肯轻易放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权集中程度;同时即使在农村经济危机期间,影响地权分散的因素,诸如诸子均产、小农力农致富等因素仍然继续在发生作用,凡此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地权的恶性集中。(注:参见夏明方《对自然灾害与旧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制度相互关系的再思考》,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
其次,从地权异动之后的土地流向看,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农村地权是在社会各阶层之间不停地流转的,虽然从前土地兼并的钱财一般也来自农业部门以外,即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也非常强(注:参见[美]德·希·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119页。),但是没有达到30年代前期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土地大量流入城居地主手中。上文所述何廉、方显廷所说浙江农村“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且此少数人非土著”,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而且这绝非个别现象。30年代前期由于平民地主、富农,尤其是专靠收租的地主日子越来越难,他们受到多方面的冲击,有时也是入不敷出,不得不典当、出卖部分土地,所以农村小地主对自耕农及其以下阶层农户丧失的土地吸纳能力有限,相当一部分土地流向资产雄厚同时又与农村有着较为密切联系的城居地主手中。尽管30年代前期土地收益减少,有钱人不愿收买土地,但是土地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流入若辈手中。(注:参见左楷康《中国地权分配的动向》,《社会经济月报》第3卷第7期,1936年7月。)据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江苏盐城沙沟镇一带,农民破产,纷纷典卖田产,而买主多为在外之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地主。(注:董成勋编:《中国农村复兴问题》,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186—187页。)江苏“铜山县四乡(尤其是近郊)土地,已大多集合在少数城市大地主手中”(注:铜山民众教育馆:《八里屯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教育新路》第12期,1932年12月。)。据金陵大学30年代前期对江西、安徽、湖北地权异动之后土地流向的调查,同样显示相当部分土地流入城居地主手中。(注:参见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编印《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制度》,1936年,第78—79页。)据土地委员会对30年代前期地权分配状况调查,承典土地者“商逾十之二,余为士绅地主等。可见土地逐渐转移于非农民手中。”(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第1编,“财政经济”(7),第48页。)
第二,30年代前期土地兼并者相当比例为政府官员,尤其是基层政权官吏占有相当比例。近代中国政权的性质越往基层,封建性越强,赤裸裸的掠夺性越明显,保甲长、乡村长、包税人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强占或“强贱买”土地,更具有血腥味。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向社会基层延伸政权,农村官吏多了起来,自然也就增加了彼辈买田置地、乃至强行霸占土地的机会。据对无锡518个村长中的104人调查,91.3%为地主,7.7%为富农,1%为商人。(注:陈翰笙著、黄汝骧译:《现代中国土地问题》,《中国经济》第1卷4、5期合刊,1933年8月25日。)江苏邳县、常熟的村长和乡长相当多是地主兼高利贷者。(注: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62页。)徐州包税人李西堂包收丰、沛、萧、砀、铜5县酒池税捐,因此发了大财,“六、七年间即买地近六百亩”(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地主罪恶种种》,无出版时间,第31页。)。铜山县因苛捐杂税不断增加,差役也获得从中肥私的机会,“三年以来购置田产三十至四十亩左右”者比比皆是。(注: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黎明书局1935年版,第2页。)之所以在土地收益减少而负担加重的形势下,基层官吏还愿意收进土地,一是因为其土地来得容易,二是因为他们能够“利用地位的优越,苛捐杂税可以逃避,田赋可以飞洒诡寄”而继续获利。(注:刘承章:《铜山县乡村信用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90辑,第47749页。)
其实,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往往是一体的。正如钱俊瑞所说,这些新兴的土地兼并者“在城镇里面就是银行钱庄的存户,甚至就是他们的股东,同时还是商号、当铺的老板;在乡村里他们是收税吏,小店铺和高利贷的主人。当然除此以外,他们又是乡村行政上的领袖。”(注:《钱俊瑞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页。)他们身兼多种角色,并互相转换,以最有利的方式购买田产,逃避税捐,成为地主阶层中的骄子。总之,“简单地说,中国的新式地主,大多是身居都市远离土地的贪官、污吏、军人、高利贷者及重利盘剥的商人”(注:左楷康:《中国地权分配的动向》,《社会经济月报》第3卷第7期,1936年7月。)。
最后,从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在20世纪上半期地权分配变化中的地位看,此次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
关于近代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变化,一般认为,“清代中叶以后地权有较快的集中趋势,但经过太平天国运动,长江流域几省地权分散,自耕农大量增加,70年代以后军人、商人地主兴起,地权再趋集中”,“大约到19世纪末,土地占有状况基本上与战前相同”(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90页。),进入20世纪以后,地权分配总体上逐渐趋向分散。笔者认为20世纪上半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分配变化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20世纪初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晚清军功地主继续存在,加上民国初年又出现一批大小军阀地主,所以地权基本维持在19世纪末期集中的状态和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年代中前期农村经济好转,地权有所分散。(注:例如20年代物价上扬,茧价高涨,江南农村经济较好,有余资购买田产而成为自耕农的贫农不在少数。参见丁沧水《近代嘉湖地区土地关系的变化》,《湖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张履鸾《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金陵学报》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20年代中后期,湖南、湖北、江西受大革命洗礼,农民运动兴起,土地革命高涨,地主深受打击,纷纷逃亡或者转移投资对象,从而使得长江中游地区并且连带下游的江浙地区,因政治形势影响,地权也有所分散。20年代末期以后,尤其是30年代前期,地权再趋集中。并且,笔者认为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程度达到了20世纪上半期的最高峰,此后地权渐趋分散,所以我们说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抗战爆发后,长江中下游局部地区汉奸勾结日伪,强占土地,地权有所集中。(注:参见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浙江省农村调查》,1952年,第3—8、180—184页;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安徽省农村调查》,1952年,第38—40页。)但是大部分地区地主在日伪统治与国统区政权苛捐杂税的逼压下,或者破产流亡,或者分散资产以减轻负担(注:战争来临后,随着大量地主逃亡,一部分债务往往也就不了了之;为了逃避赋税,抗战爆发后,富户分家比例明显增大,参见[美]马若孟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88—89、127—128页。),相当比例的地主成为富农乃至中农,地主阶级新陈代谢激烈,占有土地呈分散的趋势。同时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反而使得小农回赎30年代前期典押土地的可能性增大。(注:参见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第80页。费孝通先生也认为抗战时期货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清理债务,虽然这会引起纠纷(《内地农村》,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193页)。)还有就是抗日根据地经过土改,地权自然分散。所以,总体上看,抗战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地权趋向分散。抗战结束到全国解放时期,地权变化进入较快的分散时期,尤其是1947、1948年以后更加明显,这主要是因为解放战争波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国共双方决战前景已经基本明朗,一部分地主、富农纷纷转移财产,出卖土地,导致地权继续分散。(注:参见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页;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2—603页;樊树志《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11页;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江苏省农村调查》第185、206页。)
八、余论
地权是农村社会的全息元,土地买卖与地权异动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可以反映农村社会多方面的变化,但这里仅就其对农户通融资金和农家生计的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对于自耕农及其以下阶层占有少量土地的小农来说,土地是生存之根本和衣食之源,一般情况下,绝对不肯轻易出售。但是在遭遇突发事件,生计困难,无以为继的时候,他们只能抵押、典当、出卖一部分甚至全部土地,负债度过难关。经过若干年的辛苦劳作,省吃节用,幸运的话,再加上风调雨顺,政局稳定,他们有可能赎回自己抵押或典当的土地,甚至还可以增置一定的土地。如果此后又遇到突发事件,就再次抵押、典当或者出卖土地,如此往复不已。(注:参见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129页;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土地买卖与社会再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所以,对于小农来说,土地具有财富蓄水池,或者说银行存款的作用,有钱则买(存款),无钱则卖(取款)。从某一个角度上讲,小农拥有的几亩薄田就是在不断的抵押、典当、出卖、回赎或买地、抵押、典当、出卖这个过程中循环实现的。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看,我们不必把小农抵押、典当甚至绝卖土地看成是死路一条。
如上所述,小农抵押、典当乃至出卖土地是为了暂时摆脱困境而采取的一种万不得已的方法,同时也可以视为通融资金的一种方式,但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小农这种传统上赖以解决困难的办法变得不灵验了。小农通过典押土地渠道通融资金变得非常滞涩,其主要表现是土地买卖交易大幅度减小,农村地权转移几乎全为债务关系所致。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的非常态,对于小农生计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20世纪30年代前期全国范围内地价暴跌,但是,奇低的地价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土地交易。(注:必须指出的是,土地买卖交易减少与农家负债失地不仅不矛盾,反而说明农户是在更悲惨的条件下失去了土地。)江苏盐城“低廉的田价并不能招揽得多量主顾,田地还是和不能脱售的商品一样,禁锢在贫农的手里日趋硗薄”(注: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40页。)。因为经济贫困,武进“农民被迫而售田者日多,而城市间因商业萧条,与银根奇紧,愿意投资土地者亦不多”(注:李范:《武进县农村信用之现状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第46895页。)。1930年以后,武进“农人稍有储蓄者,见土地之纯收益减少,不愿再购买土地,以作土地投资之用,宁可将多余之资金,置之高阁,或乘机放高利贷款”(注:李范:《武进县农村信用之现状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第46939页。)。宜兴“往日以土地为财富之源泉,竞相投资于土地,今则裹足不前,反投资于工商业,甚至将资金藏于地窖,或收回一半债金,而清偿债务”(注:徐洪奎:《宜兴农村信用之概况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第46258—46259页。)。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浙江农村调查后认为,“所有原来投向土地的购买资本,因鉴于农村露骨地在崩溃着,非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是绝对裹足不前了”(注: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8页。),例如长兴县30年代前期地价大跌,“与前相较,仅值半价,尚无人过问”(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11页。)。安徽天长县南乡和盱眙东乡地价下降50%,仍无人购买。(注: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上册,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第82、89页。)萧县农村中有钱人,30年代前期不再买地,“以免水旱之灾,赋税之累,除做可靠的买卖——买新卖陈以外,便放高利贷”(注:佚名:《萧县农村剪影》,《农林新报》第438号,1936年10月21日。)。江西万载1931年以前,上等田“每十把之地价可售三十元,今(1933年)仅在十元以下求售,尚无雇主”(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12页。)。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土地市场状况对农户通融资金和农家生计的影响,至少有两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地权变化中现金交易减少,土地市场极度萧条,农家虽有几亩薄产,但却很难脱手出卖,小农只能坐以待毙。据杜岩双在浙江调查,乡农告知他,“一村每年土地之转移,常在二十亩左右,但自民十八以后,土地交易实为绝无仅有之事,尤以民二十年以后为甚,土地转移事鲜,则中农通融资金之路隘”(注:杜岩双:《浙江之农村金融》,《申报月刊》第3卷第9期,1934年9月15日。)。由于贫农、中农破产,虽然他们尽量压低价格,但还是无人承买,“结果,留在他们手里的田产,也只能当作一文不值。同时,因为卖不得现金益发枯竭,因此生活更难维持”,所以“这种田产转移的停滞非但没有停止了农民的破产,倒反扣住了农村大众的咽喉”。(注:钱俊瑞:《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4年8月秋季号。)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当“大多数小农连受剥削受掠夺的机会都被剥夺者剥夺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农村经济危机最深刻最尖锐化的时期”(注:夏明方:《对自然灾害与旧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制度相互关系的再思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第324页。)。
其次,小农地权异动一般都要经过抵押、典当直至绝卖几个步骤,本来这个过程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土地转移过程中,经过这三个步骤,小农所受的损失特别大。30年代前期地价跌落,土地抵押、典当借款随之降低,但小农却要付出高昂的利息,借贷利息和土地抵押、典当能够借到的款数成反比例增长。据调查,江苏12县平均,土地抵押价格仅占地价46.8%,土地典价占54.5%。(注: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29页。)据对湖北5县调查,土地抵押价格占地价50%左右的情形最多,土地典价占地价一般为80%。(注:程理沺:《湖北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666—45667页。)据李金铮先生考察,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土地抵押借款比1920年代减低了15%—30%。(注:李金铮:《民国乡村私人、店铺借贷的信用方式——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之所以出现土地抵押、典当借款降低的现象,除了土地价格普遍下跌外,还因为债主深知农村经济凋敝,农户普遍负债,无以为生,于是他们借小农急需用款的心理,极力压价,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以极低的代价掠取小农的土地。于是,小农往往是以低廉的价格抵押、典当土地,而在付出高昂利息之后,最终却丧失了土地(注:例如江苏南通由借贷而典卖的上等田价只相当于中等田的价格,而中等田典卖的价格只相当于下等田的价格(湛然:《南通的农村》,《新中华》第2卷第6期,1934年3月25日)。),所以小农还不如直截了当地绝卖土地,所获价钱反而比将土地抵押,进而典当,最后绝卖所获的价钱多。但是小农一般都不肯轻易一次性绝卖土地,总是希望有一天经济状况好转,能够赎回祖遗的几亩薄产。对此,同时代的学者不无讥讽地哀叹道农民这种保留土地的方式不仅骗过了死人,而且也骗过了活人。
总之,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普遍负债、地权趋于集中、土地市场清淡、地权非常态异动等多重看似矛盾的现象交织在一起,说明中国农村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的严峻形势,也昭示了中国农村孕育着巨大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不经过剧烈的社会动荡,不足以解决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