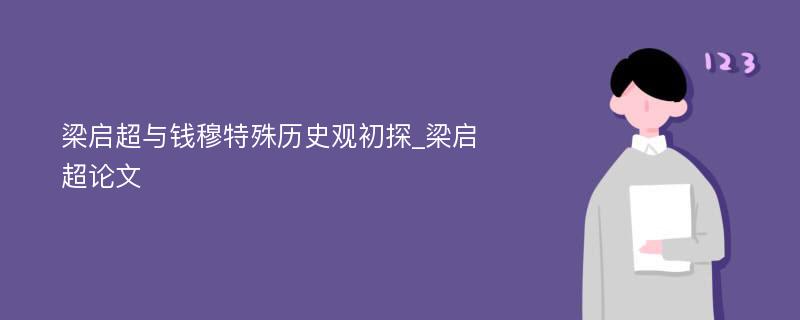
梁启超与钱穆的专门史观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钱穆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425 (2007)02—0068—04
梁启超(1873—1929)和钱穆(1895—1990)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们分别著有同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其同名作还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在19世纪20—30年代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将二者及《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合并出版,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则在1960年代于香港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在1980年代台北再版时又增加《略论治史方法》和《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两文。毫无疑问,上述两部《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我国上世纪中前期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重要成果。
梁启超和钱穆在各自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都论述了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尤其梁著的补编与钱著的大部分内容,又着重探讨了专门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包括“中国历史研究法”、“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三部分,前两部分主要讲通史研究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后一部分主要谈专门史研究法。而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由八讲组成,除了第一讲论通史研究法及附录的两文外,其余部分分别谈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和文化史的研究法。学术界以往对梁、钱二人的专门史观较少关注,而如今专门史的研究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态势,因此,研究他们的专门史观就很有借鉴和启迪意义,尤其能促使我们理性地对待和从事专门史,促使专门史研究科学地发展和繁荣起来。本文拟就梁启超和钱穆二人的专门史观念进行探讨,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二
梁启超和钱穆都是从部分和全部、特殊和一般,尤其是从专门史与普通史关系的角度来解读专门史的。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章《史之改造》中较早提及专门史:
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1]38。
梁启超把历史分为专门史和普遍史,不只是从部分与全部关系角度表明二者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所讲的专门史是与普遍史或文化史相对应的,是明了全部历史的基础。要做好普遍史,当然首先要作好专门史。后来,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绪论》和“总论”的第3章《五种专史概论》中,进一步明确了专门史的内容和意义:
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其(专史)内容又可分为五项:
(一)人的专史……
(二)事的专史……
(三)文物的专史……
(四)地方的专史……
(五)断代的专史……
虽然专史并不只此五种,然粗略分类,所有专史大都可以包括了。
梁启超对专史基础性地位的认识前后基本上一致,而对专史的具体划分则有所变化,趋于完善和严密。起初,他对专门史的划分似乎缺乏通盘性考虑。所列举的文学史、美术史等恰恰处在后来的“文物的专史”之下,而哲学史则处在“文物的专史”之下的“学术思想史”下面一个层级,又名为“道术史”。当然,后来的划分未必很恰当,如“文物的专史”与其下的“文化专史”的区别和联系如何?如此分类,文化的内涵岂不更加狭窄!与他的广泛或狭义的文化概念能否统一起来?其内在的矛盾是明显的。
梁启超之所以如此强调和划分专门史,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基于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史学观念的更新。在中国史学史上,无论记言记事,还是编年纪传;无论通史,还是断代史,应该说都相当成熟和发达。但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形态和思想的变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思潮的流入,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史学产生激荡[2],传统史学的弊端日益暴露,传统史学已经难以担当时代的重任了。梁氏所处的20世纪初年正是一个动荡和剧变的时代,他的历史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此实为他所说的近代史学的两大进步之一——“主观的观念之革新”[1]。早在1901年刊布的《中国史叙论》中,他认为旧史学是写“一人一家之谱牒”,并“以一朝为一史”,而新史学则“探索人间全体运动之进步”,“探索运动进化”,实际上也就是以人群、时期的观念代替个人、朝代的观念。次年,他又发表《新史学》,对旧史学大加鞭挞,指出旧史学的四弊、二病、三恶,并且深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进一步认为,历史叙述进化、人群进化的现象及其规律。而至1920年代,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赋予历史更为全面的涵义,“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1]1。因此,历史的观念变了,考察历史的角度变了,历史对象的重心变了,研究和记叙历史的方法和体裁自然也应随之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弊端,迎接时代的挑战,使传统史学获得新生,孕育出新的通史和专史。梁启超从人类文化的角度,以进化的观点,运用归纳的方法,在批判旧史学中建构新史学,也就是他说的“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
二是继承和发扬传统史学的结果。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是异常尖锐、非常深刻的,但又深得其精髓,并加以继承创新。古代史书和史学的缺点很多,除上文所指的“四弊”、“二病”、“三恶”外,他还多次揭批,如说“彼时学问未分科”,“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事迹分隶凌乱,其年代又重复”,等等[1]1、4、19。这些缺点确是我国传统史学存在的问题,但又可以从传统史学中获得营养和启迪。梁启超说:“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知)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例如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等,畴昔认为史中重要部分,其后则渐渐与史分离矣。”[1]32 尽管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从史学分离出去,成为专门之学,而这种分离却昭示出史学本身分门别类研究的必要,形成专门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传统史学的不足,他提倡“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1]34。也就是说,使专史与通史相应有机地发展起来。其实,我们只要从梁启超所列的人、事、文物、地方、断代专史及其论述来看,他确是分别从传统的纪传、纪事本末、典章政书、方志、断代史中获得启示,并逐步发展而来。这正如钱穆所讲的,“任公以旧学加入新思想”[3]自序2。由上可见,梁启超是在批判继承传统史学和迎接西方文化思潮挑战的结合中来建构他的专门史的。
三
钱穆所讲的专门史,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和文化史,与梁启超的专门史分类相比较,只有人物、文化(文物)相同相近,其余至少从名称上看已有很大的区别。这还只是外在的,内在的则是他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和对文化史的重视,比较接近现代的专门史分类。这是与梁启超专门史区别较大的地方。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开宗明义地说:
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4]自序1。
这种对史学意义的追寻,与克罗齐、柯林武德的“历史观念”倒有几分相像之处。其实,他的追寻是一种文化的探究。在他看来,文化是最有意义可以追寻的,文化是至高无上的,“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4]168 故而,他十分重视文化史,并把文化视为各史的共同对象,尤其是文化史:
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之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4]自序1,2。
这种对文化的重视,对意义的追寻,在钱穆的各种专史论述中都有体现,如政治史中强调制度背后一套理论和思想,社会史按照士吏身份划分阶段,经济史重视儒士和儒家的经济观点等。也许如此,钱穆总觉得自己的学问要比梁启超高明精细,他说:“惜任公为学,未精未纯,又不寿,年未六十即辞世,此诚大可惋悼矣。”[3]自序2 此言颇有抑他扬己的嫌疑,不可全信,但也反映了他们学问风格和历史观念上的差异。
钱穆认为,研究专门史还要会通明变,重视通史。他对《通典》、《通志》的会通精神予以极高的褒扬,“自唐杜佑作通典,于断代史之外,又有通史。此又为中国史学一大进步。通典为书,即从马、班之书志来,取材相同,用意大别。朝代易,而制度相承,此亦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也”[3]113。“郑樵《通志》,尤为体大思精,求有以通天人之际,藏往开来,而非前史体例之所能限。”[4]158 也有学者指出:“历史研究要求会通和明变,要做到通与变的结合,这是钱穆论历史研究的首要方法。”[5] 所以,历史研究应该从通史至专史,再由专史而通史,而专史则应在会通明变的前提下展开,这与梁氏的“明专门而后明通史”的观点较为相近,但也有差别,其中对会通、通史的推崇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
先对普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类以求。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看,然后再加以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4]10,18。
这是研究的理路,而非研究的历程,目的是“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4]11。也就是说,不是每个研究者先把通史研究好,再去研究专史,而是在总揽通史大体或心中有历史大体的前提下去研究专史或从具体问题开始,否则,就会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如钱穆所说:“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4]153 真正的做法是,“不妨分途、分期、分题、分类,各就才性所近,各择方便所宜,乘兴量力,只莫以为自己便是史学正宗,只此一家,别无分出”[4]11。可见,把握通史主要是掌握方向和大势,而真正入门和立足还在于专史。
钱穆强调从文化、通史的角度研究专史,又由专史而通史,以见历史大体。这一方法思路的形成,应该是梁启超时代学术文化背景的延续和发展的结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尤其是进化论对梁氏影响很大,而到20世纪20—30年代以后,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日益加深,尤其历史文化学派对钱氏影响较大,至40—50年代后他所处区域西风、西化日盛,中学日衰,他说:
政府播迁来台,而一切情势皆大变。中国旧文化、旧传统、旧学术,则已扫地而尽。治学则务为专家,惟求西化。中国古书,仅以新式眼光偶作参考翻阅之用,再不求融通体会,亦无再批评之必要。则民初以来之新文化运动,亦可谓已告一段落[3]自序4。
钱穆对此深为不满,但并不拒绝西学,而是会通中西,批判继承,寻找挽救中华文化和历史传统的途径,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通史性的专门史研究方法。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的中国通史和专史研究的发展[6],也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和利用的历史资源。
总之,梁启超和钱穆的专门史观,是一种对我国传统史学以及近代西方历史文化批判和继承的结果,尤为重视史学传统的继承、融合和革新,强调专门史研究的通史意识和文化意识,具有创造性意义。当然,他们的专门史观又有一定的差异,梁启超相对实证实在些,强调与传统史体、史法的渊源关系,而钱穆则较为理性,突出文化和哲学的探究。这种专门史的思想和理路,对我们今天研究专门史,完善专门史学科,无疑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2006—0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