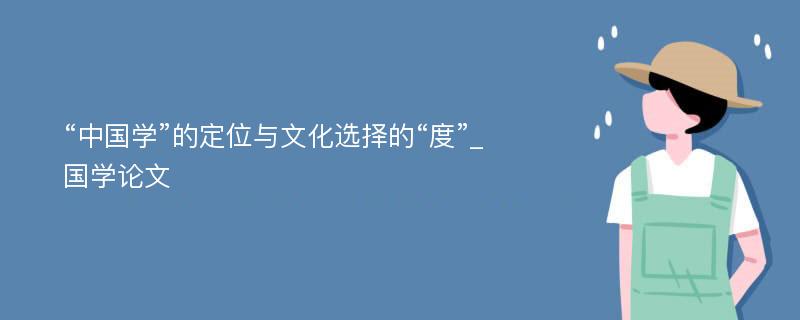
“国学”的定位与文化选择的“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国学”热已成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究其原因,当然非常复杂,所以对这一现象的认识产生冲突也就很自然。对一般社会上的热潮姑且不论,因为如媒体的炒作显然有商业目的,就从精英文化阶层看,也有极大的分歧。
极力主张弘扬国学,在当今中国有很多值得重视的现象。如大规模编纂《儒藏》,各地纷纷开办国学研究院、国学讲习班,特别是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甚至正式招收全日制本科生,这就把国学纳入到正规的官方教育体制之内了。其他民间性质的国学班、读经班应该更多。来自官方的举措还有,大办孔子学院,据报道,自2005年7月以来,孔子学院已达140多所,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根据计划,到2010年,全球孔子学院将达到500所。此外,前些时,北京数十名博士生联名抵制洋节,显然也是国学热潮中的极端表现。
另一方面,对国学也有持极力否定态度的,这以舒芜先生为代表。舒芜先生明确反对提倡国学的潮流,他认为,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清朝末年到“五四”以来,保守势力抵制科学、民主的一个借口,完全是顽固保守、抗拒进步、抗拒科学民主、抗拒文化变革的一个东西。不仅如此,他还从根本上否定“国学”这一概念,认为国学是既顽固透顶又含糊不清的概念,他认为如果每个国家都讲自己的国学,那就热闹了,世界上的学科就分为英国国学、法国国学、德国国学……尼日利亚国学、尼加拉瓜国学等,而文学、哲学、史学、法学等全都没有了,那成了怎样的一个世界呢?①
这两种倾向可以说是判若水火。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我想,过犹不及。对于国学,正确的态度不是复活,也不是灭杀,而是应当给国学一个准确的定位,将其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因此,对当前过分的国学热潮,应当泼冷水,比如教小孩子只读四书五经,恢复私塾的教育方式,显然不可取,因为这在改变了的时代氛围中事实上是行不通的。至于舒芜先生指责的“媒体上津津乐道的所谓国学”,“有的一张口就错误百出,也在电视上大言不惭地谈国学”,自然更是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媒体、电视上的国学,实际上是复杂的主流意识、复古心理以及商业炒作纠缠在一起的一个文化怪胎,因为国学与大众传媒不是一回事,国学与普及传统文化也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应当和这样的国学热潮保持距离。然而,另一方面,我认为国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学科,是可以成立的,舒芜先生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其实,舒芜先生的说法并不新颖,早在1929年,何炳松就发表题为《论所谓“国学”》的文章,提出“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口号,其理由有四:一是来历不明,二是界限不清,三是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四是以一团糟的态度对待本国的学术。② 但是,这种极端的态度,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后来关于国学的讨论,国学自身的发展,都没有受到影响和阻碍。而且,有些否定国学的理由,和国学本身并不相符。比如,舒芜先生说国学是晚清以来保守势力抵制科学民主的借口,就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早期大力宣讲国学的章太炎,晚清以来一直是激进的革命党人,无论怎么看也难以将其归入保守势力中去。又比如,舒芜先生在彻底反国学的同时,表白了自己一生的一个坚定的信念:反儒学尤反理学,尊五四尤尊鲁迅。这里牵涉两个问题:一是舒芜认为所谓国学是什么,其实就是讲儒家的那点东西,封建的那些价值观念,所以他反国学必反儒学,但实际上把国学等同于儒学及封建价值观,是不符合事实的,下面再说。二是他认为鲁迅最反国学,所以反国学则尊鲁迅,但实际上鲁迅对国学的态度如何呢?鲁迅曾经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③《流沙坠简》1914年出版,是罗振玉、王国维的重要著作,主要内容是根据法国人沙畹书中的照片,选录被英国人斯坦因盗走的敦煌文献,大部分是汉简,少量的帛书及晋代以后的简帛,在简帛文后作释文和考释。鲁迅在这里围绕国学来感叹真假学者的区别,可见,鲁迅并没有简单地反国学,而是反假国学,不反真国学。事实上,鲁迅本人的国学造诣不必多说,在国学网第一次国学大师评选中,十名国学大师,鲁迅恰恰与王国维,都是赫然在列的。
给“国学”一个准确的定位离不开对“国学”本身的认识。
“国学”一词,由谁最先提出,一时难以详细考证。大体上看,所谓“国学”、“国粹”,是清末时由一批旅日学者从日本引进的,主要有邓实、黄节、章太炎等人。当时日本学者提倡国粹、国学,是针对明治维新的“欧化”政策,具有保守主义色彩。同样,中国人提倡国学、国粹,也是具有针对西风东渐的背景。不过,在中国,国粹与国学似乎不完全相同了,国粹偏于保守主义立场,国学则更多着眼于学术本身。因此,所谓国学,相对于新学而言,应指旧学;相对于西学而言,当指中学。如果排除国学所带有的针对西风东渐的保守主义的文化背景,它作为一种学科概念的提出,其实是有着时代的必然性的。为什么呢?因为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在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之下,西方的学术文化主宰全球,整个学术文化的学科划分随之发生变化。而我们知道,东方和西方的学科划分是有很大差异的,差异的基础是范式不同,库恩认为,任何科学都是建立于某种范式的基础之上,范式是什么呢?范式是科学和前科学、非科学的区别,也就是科学共同体按照一种共识、遵循同样的规范从事研究活动,而这种长期积累的共识、规范的基础,其实表现了这一共同体对世界构成的看法。扩而大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其实也可以用范式来解释。中西学科划分的不同,其实也就是对学术文化世界构成的看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学科划分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而西方的学科划分则是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物理学、化学等,这两种学科划分基于两种不同的文明背景,反映出对学术文化构成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现在要用西方的学科划分标准对中国传统的学术加以划分,实际上就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分割和重整。面对这一形势,中国学人实际上面临两大难题:第一,是中国学术文化的安顿问题。要用新的学科划分标准对传统学术进行彻底的分割和重整,那么有着数千年辉煌文明史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其实将不复存在,对此,无论保守的或是革命的中国学人都是不能接受的(作为革命党人的章太炎为什么要大倡国学,显然不是偶然的),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先进与落后的强烈反差中,不接受西方文明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样的两难境地中,就需要一个新的空间来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一个安顿,既是文化的安顿、学术的安顿,也是心灵的安顿、自尊的安顿,而这个用以安顿的空间就是国学。第二,是具体操作的困境。如前所说,中西学科的划分基于不同的文明背景,因此,要把中国固有的学科全都取消,全部分割或归并到西方的学科中去,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不仅是中国的学术,就连一些东方其他国家的学术文化,也是很难完全归并到西方学科体系中去的,比如印度学、埃及学、土耳其的“突厥学”,等等,所以即使到现在的欧美大学之中,往往在东方系中设立相应的专门课程。就具体学科而言,无法归并的例子实在太多,所以为什么说中国传统学术是文史哲不分,其实是无法分。举个例子,假如要把中医学归并到西医学中去,问题就很大,西医学的基础是化学、解剖学,如果说,中医中的中草药,用化学的方法来分析其药理属性,提炼其有效成分,尚属可行,那么,中药剂中的药引,有时就无法用化学的方法来分析。至如经络学说,是中医治病的重要基础,但就无法用解剖学找到依据。中医诊断,讲究阴阳五行、表里寒热综合把握辩证施治,也是很难在西医病理学上找到解释。特别是针灸的补泻手法,更是不可思议。可以说,正是在现代学科划分的背景上,中学西归的困境中,国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概念被提了出来,因此说,国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学理上的成立,应该是有依据的。
由上所述,可见国学作为中华文明的积淀,既是历史地存在的,又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中国学人在现代学科重新划分中的应对智慧和策略的体现,因此,国学决不是像舒芜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而是有着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的学科。基于清末以来“国学”的传播历史,我们可以从被人们公认的国学大师的观点出发,来讨论这一问题。
在国学大师中,曾被人称为20世纪最大的儒者的马一浮先生曾有一篇文章专为国学正名的,题名《楷定国学名义》,在这篇文章中,马一浮认为,谈论国学应当先楷定国学名义,而“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所谓“六艺之学”,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儒家六经之学。如果仅由此看,马一浮所说的国学,就和舒芜所批判的国学“其实就是讲儒家的那点东西”差不多了,但其实,马一浮同时又强调“六艺统诸子”、“六艺统四部”,因此,马一浮所谓的国学,实际上是指以经学为中心的中国的传统学术,这是有别于西方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固有之学术,具体地说,就是包含在经、史、子、集四部之中的小学(文字学)、经学、诸子学、文学、史学,而并不包括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方面的其他学问。
在公认的国学大师中,更早的更权威的当为章太炎。那么,在章太炎看来,国学是什么呢?章太炎一生大倡国学,多次公开演讲国学,他最早倡导国学之时,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前的1910年以前,因为1910年,章太炎的著作《国故论衡》在日本出版刊行。此后,章太炎先生又出版另一部重要的国学论著《国学概论》,晚年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有关国学的演讲,则整理为《国学讲演录》。章太炎的这三部著作都是直接谈论国学的,本质的精神和具体的内容都是完全一致的。从章太炎这些著作中所谈论的国学看,具体的也就是指中国传统的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
章太炎之后,钱穆也著有《国学概论》一书,该书完成于1928年,与章太炎的《国学概论》同名,但其体例和主旨却有不同。关于这一点,钱穆在书前《弁言》中明确加以说明,他说“时贤或以经、史、子、集编论国学,如章氏《国学概论》讲演之例”,在说明以章太炎为代表的以四部之学论国学的现状后,特别标举自己不按这种体例讨论国学,而是重在论述“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可见其著书的目的是写一部中国学术思想史,重在史的发展变迁,重在把握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进程。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查看钱穆《国学概论》的内容,就可以知道他心目中的国学是什么,该书共十章,分上下篇,上篇七章,依次为:孔子与六经、先秦诸子、赢秦之焚书坑儒、两汉经生经今古文之争、晚汉之新思潮、魏晋清谈、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下篇三章,依次为: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最近期之学术思想。可见,作为一部学术思想史著作,他是按时序先后来安排全书的体例和结构,但是,所论述的具体内容,显然是传统的经学、诸子学,以及考据学(含小学)。虽然外延更狭窄一点,但是和章太炎所谓的国学的内涵,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除此之外,与国学相关的还有一个“国故”的概念。是由胡适大力提倡整理国故而产生很大影响,胡适认为中国传统学问很复杂,有很多问题缠绕不清,所以需要整理国故。对国故加以整理,本身就是一个学术的概念,所以又叫国故学。那么,国故和国学是什么关系呢?有人认为,整理国故是科学的,而国学则是顽固保守的,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其实,从胡适本人的言行看,他所谓的国故和国学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可以说,国故就是国学的另一种称谓而已。胡适自己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胡适在1919年下半年发表《论国故学》的文章,提倡“整理国故”。后来为了进一步宣扬这一主张,他又创办了《读书杂志》、《国学季刊》,作为整理国故的舆论阵地,来促进国故学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词中,曾经给国故下过定义:“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其实,在胡适之前,章太炎就已使用过国故概念,他最早的一部国学论著就叫《国故论衡》,后来再有《国学概论》、《国学讲演录》,如果对照章太炎的这三部书,也可以很清楚地说明国故与国学是一回事。
我们通过对清末以来国学的传播历史的梳理,以及对国学大师心目中的国学的分析,完全可以看出,国学并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而是有确定所指的,国学既不是像舒芜所说的“只是儒家的那点东西”那样狭隘,也不是指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那样宽泛,应该说,国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学科范围内的学术的一个统称。而晚清以来的学者、文化精英,为什么要如此大讲国学,并以国学替代中学以抗衡西学,乃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学科的学术才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精神所在,也是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根本依据所在。中国文化向来讲究整体观念,如果要像西方学科分类那样,把它细分到各个具体学科中去,那么,中国特色的学术文化将支离破碎,其精髓将不复存在。在这样的意义上看,国学的提出不仅是科学的、合理的,而且也是具有生命力的,仍将长久地存在下去。
鉴于以上对国学的认识,我想,我们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学人,在当今的时代再来讲国学,显然不应该或者一味地崇扬,或者一味地否定,而最重要的,是应当给国学一个恰当的定位。以时代性和科学性为坐标,国学究竟应当在哪里定位?我想,根据我们对国学的认识,国学应当是一种学术的定位,也就是说,讲国学的方式,是学术的方式,可以自由探讨,讲国学的范围,是学术的范围,也就是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人员,而不是全社会。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体现,一些专业人员用毕生的精力去从事研究,对传承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应当受到国人的崇敬,而一般的中国人,学习一些古代的知识,懂得历史,受古代文学的陶冶,对增长自己的智慧,提高自己的素养,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但那不是国学的任务,而是传统文化普及的任务。因此,大众传媒、电视,可以作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但不宜大谈国学,因为大谈国学,不是大众传媒的任务,也不符合国学的定位。所谓学术超男学术超女现象,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也是一种不可能持久的现象。当然,话说回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的体现,国学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是紧密相关的,讲国学当然离不开整个传统文化,但是,两者毕竟不是完全等同的,特别是性质和受众的不同,两者应当是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的。所以,给国学一个准确的定位,仍然是必要的。
给国学一个定位,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可以给我们操作这件事情提供一个“度”。度,对任何事物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度是什么?度就是过犹不及,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庸之道。但是遗憾的,在中庸之道的故乡,现代以来却不仅彻底地误读了中庸之道的真义,而且离中庸之道越来越远,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了一个度,形成一种运动性思维,学术文化也是如此。从五四运动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整风运动、肃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四清运动、思想改造运动、评法批儒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登峰造极了。这样的运动性思维,运动化方式,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失度,不是彻底否定,一棍子打死,就是不分良莠,任意提倡拔高,这种教训极其深刻。比如,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是不错的,但砸烂孔家店,甚至殃及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就显然太过分了,这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发展到极端,其危害实际上已经不仅仅在于文化领域了。另一个极端,近些年提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本来也没错,但一旦过分,就会出现良莠不分、泥沙俱下,造成民众心态的故步自封,甚至迷信泛滥,伪科学盛行,比如很多气功大师、特异功能、算命算卦都是打着易学的旗号,这样的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糟蹋。而这两种极端的表现,都是缺少一个度的结果。
给国学一个定位,给传统文化一个度,对近二十几年的文化热进行反思,乃至于对今后的文化取向的选择,我觉得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两次大的文化热,非常值得思考。第一次文化热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在长期闭关锁国之后,国门猛然打开,国门内外的巨大差距一下子展现在国人面前,自然形成唯洋是务的心态,文化界在饱受专制之苦之后,更是如此,对外来文化的吸收简直有点饥不择食的味道,什么老三论、新三论,甚至全都搬到古代文史的研究中。这次文化热,对国内“左”的思潮进行了强力冲击,对当时的思想解放,应该说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缺乏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评价,这次文化热的主调逐渐变味了,变成了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以《河殇》为标志,以蓝色文明取代黄色文明,甚至有人主张彻底消灭传统文化。这样的极端表现,显然失去的文化健康发展的基础,所以这次文化热很快退潮,也就是必然的了。第二次文化热,从九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现在。这一次文化热,相对第一次,应该说理性了很多,其基础是建筑在对中西文化都有一个理性认识、分辩其优劣的基础之上。所以这一次文化热是以重视传统文化为特征的,从现象上看,组织了很多有关传统文化的讨论会,出版了大量的有关传统文化的研究丛书,实际上与前一次文化热的价值取向恰恰相反,也可以认为是对第一次文化热所出现的偏向的纠偏,是反其道而行之。这样的价值取向的文化热,对于纠正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倾向,应该说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所谓过犹不及,也出现了所谓矫枉过正的现象。这就是对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方面不加分析地加以盲目鼓吹,任意拔高其作用和意义。像前面提到的易学的庸俗化、神秘化,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除此而外,比如,对于儒学,也超出了学术的范围,许多人无限拔高儒学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许多人大量地论证儒学对发展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甚至举例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国的飞速发展,就是因为儒学的关系。甚至学术圈中也在大谈儒商。其实,这些说法都是似是而非的,都是缺乏根据的任意拔高。如果说,儒家思想可以促进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在世界上中国用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达两千年,为什么不是中国率先进入工业现代化行列?再者,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受儒家文化影响,确实是事实,但那也是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的事,为什么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迅速发展呢?显然都不是这么回事。至于儒商之说,我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伪概念。儒是一种思想学说,商是一种行业,如果从事商业的人受到儒学影响就可叫儒商,那么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当然也可叫儒什么;如果儒学思想影响了商人,就可以叫儒商,那么其他各种思想学说影响下的商人,则也自然可以叫道商、佛商、伊(伊斯兰)商、基(基督教)商等等,这显然是十分可笑的。
所以,对文化的态度,如果不分对象,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没有一个合适的度,结果将会是非常危险的,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轻则使一个时代的文化呈现庸俗混乱,重则使一个民族的文化失去健康前行的方向。
注释:
①舒芜《“国学”质疑》,《文汇报》,2006.6.28。
②何炳松《何炳松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82页。
③鲁迅《热风:不懂的音译》,《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