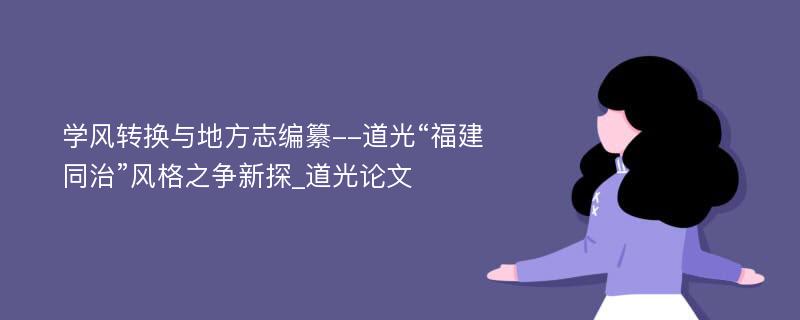
学风转变与地方志的编撰——道光《福建通志》体例纠纷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志论文,地方志论文,体例论文,学风论文,道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5.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7)02-0074-06
道光《福建通志》(以下简称“《道光志》”)的修撰围绕体例问题引发了一场范围颇广的论争,险些使已经完稿的《道光志》付诸东流。关于这场纠纷,以往人们多关注矛盾双方存在的私人恩怨,于双方所涉及到的体例之争,却少有深入系统的分析。事实上,若把《道光志》的体例之争置于嘉道年间的福建学界,乃至全国学界的大背景下考察,我们便会发现,这场纠纷其实与当时闽省正在发生的学风变迁有着内在的联系。从这一角度分析,对于我们认识通志编撰与学风变迁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也正是本文以这场论争为考察对象的原因所在。①
一、道光《福建通志》的编撰及其纠纷的发生
有清一代,福建总共编了四部省志:其中康熙朝一部,由郑开极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编撰;乾隆朝两部,分别由谢道乘在乾隆二年(1737)和沈廷璋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编撰;最后一部即本文所讨论的《道光志》是道光年间由陈寿祺负责总纂的。该志的编纂始于道光九年(1829),历时六载,于道光十四年(1834)编就,共有400余卷,篇幅上大大超越了前两部。之后,《道光志》遭遇封存、删改和停滞,直到同治十年(1871)才由致用书院山长林鸿年主持付印,前后间隔了42年之久。其历时之长,影响之深,使得围绕《道光志》的纠纷成为清代修志史上一桩罕见的公案。
《道光志》的编撰由陈寿祺首倡,他认为旧志多舛误,应该重修。当时恰逢贡院修缮完毕,余钱万余缗,于是陈建议用此余款续修新志,得到了总督孙尔准的同意。②开始拟请李兆洛担任总纂,李没有应允,就改聘陈寿祺。修志局设在魁辅里(今鼓楼区吉庇路)刘氏祠堂。当时参与修纂者共18人,其中有高澍然、冯登府、张绅、王捷南、陈善、沈学渊、汪晨、陈池养、林晨英、翁吉士、刘建韶、林彦芬、丁汝恭、赖其恭、张际亮、罗联棠、饶廷襄、何治运等。陈寿祺亲自主笔儒林、文苑、天文分野、山川形势等传,其余交分纂负责。参与编纂的人员都是当地或者外聘的有学之士,不少人是曾跟随陈寿祺在清源、鳌峰书院学习的弟子。陈寿棋十分看重此次修撰,晚年为通志花费了大量心血。在志稿即将完成时,陈寿祺病逝,高澍然继任总纂。随后,分纂陈善等人将陈寿祺列入《道光志·儒林传》。
志稿完成后,当局议付印之时,梁章钜③诸人突然联名提出异议,指责志稿存在“五大不善”:一儒林混入:二孝义滥收;三艺文无志:四道学无传;五山川太繁。④并总督程祖洛、学政陈用光提出重审要求,得到应允。由是《道光志》“毁志之祸”酿成。
围绕着通志问题,以梁章钜为首的反对派与以陈寿棋之子陈乔枞为首的维护派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陈乔纵及陈寿祺的门人周凯、张际亮等曾倡绘《鳌峰载笔图》,大做文章,反击梁章钜,后起的状元林鸿年又附和其中,引起福建文人分成两大派。在斗争中,他们互相攻讦揭短,焦点集中于梁章钜与陈寿棋之间的私人恩怨。加之梁章钜与总督程祖洛私交甚笃,而陈寿祺与学政陈用光也曾有过节。后人很自然地就把纠纷归因于私人恩怨的直接原因。⑤但是,实际上,双方所争论的实质问题,乃在通志体例得失的不同评价,这与当时闽省所发生的学风变迁有着内在的联系。表面上恩恩怨怨的背后,隐含着激烈的门户之争。
二、道光《福建通志》的编撰特点与纠纷的关系
嘉道年间的闽省正经历一场影响颇为深远的学风转变。其主要内容是经世致用思潮与汉宋并重的学术风气兴起。在新兴的学风影响下,《道光志》的编撰思想与体例与前两部福建通志有很大的不同,从而也引起有不同学术主张间的学者的争论。这场争论在陈寿棋在世时就已开始。因此,若要探讨这场纠纷的来龙去脉,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总纂陈寿祺的学术主张与《道光志》的编撰特点。陈寿祺(1771-1834年),字恭甫,又字苇仁,号左海,又号珊士,晚号隐屏山人,闽县人。嘉道间闽省新学风的代表人物。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曾充广东、河南乡试考官,授记名御史。弃官归籍后,先后主讲清源、鳌峰书院。陈寿祺出朱珪门下,博学多才,学术造诣深厚,经学、小学、文辞学等靡不深究,著述颇丰,为清代福建学界罕有,是清代学坛有一定影响力的“通儒”。归里讲学后,陈寿祺有心振兴乡学,改变福建学术落后的局面。他在省会书院提倡研习考据之学,培养诸生学习经学的兴趣。通过一系列的努力,陈寿祺在福建奠定了研治考据学的基础,并培养出一批汉宋并重的弟子。⑥他所主持编纂的新志,在体例与内容上也充分显现了其主张汉宋并重,突出通经致用的思想,比如,把《道学传》归入《儒林传》,注重《山川志》等,而这些恰恰成为引发纠纷的直接原因。
1、《道学传》的废立问题
在通志反对者所提出的质疑中,“道学无传”的问题最大。《道学传》创自《宋史》,目的是将宋濂洛关闽诸学者从儒林中移出,别立《道学传》以示尊崇理学。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明代。但在康熙年间编《明史》时汉宋两派学者为是否设立《道学传》发生过激烈争论,最终主张取消的一方占了上风,因此清修的《明史》中没有延续《宋史》的做法。⑦之后乾隆时《钦定续通志列传》也未再立道学传。
陈寿祺学宗汉学,但主张汉宋兼学。⑧拟定《道光志》体例时,他坚持旧志《道学传》不符史例,应予取消,将之分入《儒林传》,他说:
儒林纪传经授受之源流,类而叙之,以明家法。……道学之名创自元人,古无是称,不可以为典要。且道外无儒,儒外无道,道之与儒将何分判?宋史道学之外复有儒林。东菜、西山摈诸程朱之外。入附出污,岂能郅当?……舍儒何以为道?舍学何以为儒?紫阳大贤,百世尊仰。然平心而论,正与游、夏伯仲,使紫阳而在,亦未敢自谓驾二贤而上之也。必欲因仍宋史之旧,道学、儒林歧而为二,乖违旧章,失所依据。欲崇道学,转蹈不经,恐徒供通人之窃笑耳。⑨
考虑到朱熹在闽学的地位,陈寿祺又建议仿效《蜀志·诸葛忠武侯传》的做法,在朱子传中另立篇章,明其理学传承关系,以彰显朱子在闽学中的地位:“详叙篇目,别其体要,使学者有所考焉,则不必立道学之名,而大儒之宗旨定矣。”⑩
但是,福建学者一直以“闽学”传人自傲,取消道学传在他们看来等同于否认“闽学”,“无道学则濂洛关闽无闽”。因此取消《道学传》的做法遭到闽学者激烈的反对。甚至连门户之见不是那么严格的梁章钜也无法接受:
吾闽旧省志中仿立理学一传,陈恭甫诋斥不遗余力。近因续修省志,欲遂删之。都人士皆不谓然。余谓道学莫盛于宋,濂洛关闽之统,实朱子集其大成,海滨邹鲁之风自前代即无异议。故他史可不传道学,而《宋史》则应有;他省通志可不传道学,而闽志不可无。(11)
在他看来,陈寿祺“墨守汉学,其排挤宋儒是其故智,而不知门户之见非可施诸官书。”(12)陈寿祺在学术观点上主张汉宋兼采,并未“墨守汉学”,但其改变朱子学独尊的做法仍无法逃脱门户之见的指责。
时任福建学政陈用光(13)也反对陈寿祺的做法。陈用光出身桐城派,其学术观点本就与陈寿祺不同。在来闽任学政之前,他就曾因门户之见与陈寿祺有过矛盾。两人早年在国史馆共事时,陈用光要求把其师朱仕琇与姚鼐列入《儒林传》。而陈寿祺的古文观受他的经学观影响,偏于汉学家法,以经史水平为重,对文辞不作过多要求,恰与桐城派相对注重文辞、轻经史的特点背道而驰。因此,陈寿祺对二者的评价都不甚高,拒绝了陈用光的要求。(14)在《道光志》体例上,陈用光认为只有另立《道学传》才能凸显朱子的地位(15),坚决反对陈寿祺取消《道学传》的做法。这样,学政与地方学者联手,一起对新志体例提出质疑,给通志编撰人员很大压力,继任总纂的高澍然被迫辞职。高辞职时言,“道学名传,创于元史臣之撰《宋史》,由未谙史例,妄生枝节也。”(16)陈的门生弟子也为其师抱不平。出其门下的林昌彝言,“按《宋史》创立道学列传,别于儒林,其意欲以尊崇周、张、程、朱,不知道外无儒,儒外无道,欲示尊崇,转生歧异,徒贻学者口实。”(17)另一门生刘存仁则言,“‘道学无传’,考河南、陕西、湖南通志皆不列道学,则闽志之无传,亦不自闽志而始也。”(18)
2、“儒林传”的人选问题
梁派反对的另一理由是“儒林混入”,其中主要是《儒林传》的人选问题。陈寿祺去世后,总纂高澍然与分纂陈善等人把陈寿棋列入《儒林传》。以经学研究称于世的陈寿祺,死后被列入鳌峰名师祠,并入国史儒林传。入本省通志《儒林传》,在陈派看来可谓名至实归。但梁章钜等人反对把陈寿祺列入《儒林传》。高澍然在辞总纂书中,认为梁章钜等人提出“儒林混入”一条,实质是要阻止陈寿祺列入《儒林传》,他说:“顷闻省中诸公务举通志稿不善者五事,诉于列宪,请发稿公勘。诸公是举,因故太史陈恭甫先生入儒林传,托志稿发难,而释憾于先生也。”(19)说到底,对方反对陈入《儒林传》其实就是否定陈寿棋在经学考据研究方面的成就,也就是否定汉学家的成就。不仅如此,我们从梁章钜的言说中还能见到其它内容。梁章钜曾因陈寿祺未将其师郑光策(20)列入《东越儒林传》颇有怨言:
近陈恭甫修撰《东越儒林文苑传》,近人如林钝村、官志斋、郑在谦、陈贤开辈,皆列名其间,而先生独不与,……或曰编修为孝廉时,曾修后进谒见之礼,先生素仰其文名,而欲进之道,毅然以乡先达自居,勉之以修己之学,济物之功,而戒其勿以风流自赏,适中编修之忌,遂衔之不释。果而编修亦褊人尔,所论传又足据乎。(21)
由上引文可知,梁的理解也是陈乃出于私怨才把郑排斥出他所负责的“儒林传”,加上郑乃梁之岳父,有这一层关系,使人更容易联想到当事人之间的个人恩怨问题,有学者由此认定梁章钜反对《道光志》的缘由乃是陈寿祺未把郑光策列入“儒林传”。
陈派则认为梁氏之所以反对陈寿祺入儒林,乃是因为陈寿祺曾写诗微讽过梁氏的豪宅,二人由此结怨。陈寿祺的高足张际亮言:“……方伯昔与师无隙,因大起园亭,侈丽入霄汉,师贻书规劝,遂成嫌怨。”(22)后来致用书院院长谢章铤也持此意见。(23)
但笔者认为这场纠纷不单源于当事人之间盘根错节的私人恩怨,与双方在陈寿祺入选“儒林传”所持标准方面的分歧也有很大关系,这更值得我们去考究。陈寿祺认为能否选入儒林传就看传主在经学研究上的造就如何。他曾为国史馆纂东越《儒林》、《文苑》两传,并言:“《史记》综括数千载,文起黄、农。而儒林一传亦专取汉世经师,援兹比方,是成一道”(24)。在编撰《道光志》之时,陈寿棋仍坚持这一主张:“盖汇传所以表经师,专传所以尊名臣,其有经术足以综诸家,节义足以范一代,推而扬之,使异于章句之师。”即入儒林传要有“传经授受之源流,类而叙之以明家法”的功绩。(25)高澍然等人列陈寿祺入儒林也是以此为理由:“……先生学在传经、遗书,何为乎不可儒林?”(26)这样,重事功而轻著述的郑光策未被收入儒林传似乎与陈寿祺的选人标准相关。而梁派坚持郑应入《儒林传》主要是看重郑在经世事功方面的造诣。郑光策原是福建省会书院鳌峰书院的名师,开启了嘉道间鳌峰书院乃至闽省经世之学的风气,培养了梁章钜、林则徐等闽省名臣,在省内声望颇高。郑光策与陈寿祺先后在闽省倡导经世之风,但又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取向。郑光策学宗朱学,他虽不反对习考据之学,但不主张把时光耗在经学著述上,而应优先考虑现世上有所作为,立一番事功。至于经学著述,乃是在事功无望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盖成己成物为圣贤之正传。至万不得已,始独善其身,思有所传于后。”(27)陈寿祺则取通经致用的途径,把崇尚经学看成是扭转士风人心的捷径,他认为“善风俗在正人心,正人心在厉行义、尊经学。”(28)郑、陈的不同见解,造成梁、陈等在儒林传人选等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这也反映了在学风变迁过程中,用传统的《儒林传》标准来容纳新学风气下出现的不同人物,并非一件易事。民国年间,陈衍在《儒林传》外,另设《儒行传》,以区别对待陈、郑二人,使二者的成就都得到肯定。但毕竟在一般人眼中,《儒林传》仍代表着更高的肯定。
陈寿祺在《儒林传》人选标准问题上的主张,还有一层考虑,即通过这一标准,就能把闽省在经学研究上有一定造诣的学者列入《儒林传》,以此为闽省的汉学先行者在福建学术史上争一个地位。诸如林一桂、万世美、谢震等其他人,在梁派看来,他们仅仅是在文辞方面有所造诣而已,都不符合入《儒林传》的标准,于是加以反对。(29)但在陈寿祺看来,林一桂等人凭借经学研究上的造诣完全可以入儒林。林一桂、万世美、谢震等人都是清代闽省经学研究的开拓者。例如,谢震“笃学耆古,熟三礼。治经持汉学,好排击宋儒凿空逃虚之说。”(30)陈寿祺早年曾经与之共创殖榭,倡通经复古之学。早在为国史馆纂《东越儒林后传》时,陈寿祺就把林一桂等人作为闽省礼学研究的后进附入《官献瑶传》后以彰显之。
3、山川地理志的繁简问题及其他
梁派所抱怨的“山川太繁”,其实是陈寿祺重视考核舆地研究的结果。他认为“地理则山川、关隘、海防、水利宜详毋略,虽岛澳而考稽必审”(31)。故而一反旧志山川仅载名胜的做法,改为形胜,“重其要害,详其扼险,考其支流,略其吟眺,”(32)使之更趋实用,也就造成梁派所谓的“山川太繁”。陈寿祺亲纂形胜志。而地理志乃前传所未有,负责分纂《地理沿革考》的王捷南出身陈寿祺门下,精于经史、金石之学。其书成后,陈寿祺带病披览,评价颇高:“此书考订精确,非独足备桑梓掌故,尤治史学地理者之一助也。通志成否未可知,子此书宜先刊之。”(33)。在《通志》结局未知时,王捷南先行刊印山川志传世,名之曰《闽中沿革表》。在陈派看来,批驳通志对于山川地理记载过繁琐似无道理。高澍然言:“山川志区十郡二州山川而二之,名二十四本,每本多者三十余篇,合之不及十本,亦不为繁。又古方志一名图经,主舆地言也,主舆地故详山川,岂好繁哉?是皆好为讥弹无当于事实也。”(34)重视山川舆地是汉学家治地理的特点,也是乾嘉以后地方志编撰的一个普遍做法。因此,《道光志》体例上的这一特点,同样与嘉道间考据学在闽省的兴起有着直接的联系。
从后来《道光志》修订的结果来看,陈寿祺所重视的方言考、经籍志、金石志、职官表等,都被大幅删改。而这些内容恰恰也都了反映《道光志》的考据学特点。《道光志》由凤池书院山长魏本善修订,其主要修改内容为:(1)儒林传中剔除出林一桂、万世美、谢震三人,郑光策、陈寿祺都入《儒林传》。(2)道学复立传。(3)艺文仍无志。(4)山川删繁就简。(5)孝义照旧。全书由原稿四百卷,缩为二百七十八卷,其被删部分有高澍然的《福建历朝宦绩录》、《闽水纲目》、王捷南的《闽中沿革考》、陈善的《福建(清)列传》、何治运的《方言考》、冯登府的《闽中金石志》、张绅的《福建(宋)列传》、刘存灵的《山川图记》一部分及凡例。又把经籍志由十六册缩为六册。[35]这些做法无疑淡化了《道光志》的汉学色彩,与陈寿祺的初衷相去甚远。
总之,道光福建通志的“毁志之祸”的发生,除了矛盾双方的恩怨之外,与双方的学术见解,汉宋门户立场也有很大的关系。林则徐曾言:
海内经师叹逝波,乡邦文献苦搜罗。匡刘未竟登朝业,何郑俱休入室戈。神返隐屏生岂偶,编传左海好非何。者番归访金鳌岫,倍感前型教泽多。(36)
林则徐称陈寿祺为“经师”,称赞其搜罗乡邦文献的功绩,并引用东汉何休、郑玄今古文论争的典故宋喻这场纠纷,从诗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其中存在的学术门尸之争。其实,单从学术观点来看,学宗汉学的学者对《道光志》的评价与传统闽省学者迥然不同。时隔多年后的同治年间,福建第一所专修朴学的致用书院院长谢章铤十分推崇《道光志》,把《道光志》功败垂成视为嘉道以后闽省学界一大憾事,(37)他认为此志大有利于朴学研究之用,“……其中最可惋惜者,如职官表,综核可参六典;经籍志,派别可寻家法;方言考,通转可悟小学;其他类此者甚多,今则不遗一字矣。”(38)对《道光志》评价的提升,正反映出闽省学风所发生的变迁。
三、道光《福建通志》的命运与嘉道福建学风的转变
围绕着《道光志》的体例纠纷,不仅是当事人间的恩怨问题,更反映嘉道闽省学术变迁中不同学术门派及其观点间的冲击。通过对《道光志》体例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特点与嘉道闽省学风的转型密切相关。乾嘉汉学鼎盛时期,福建学者墨守朱子学,有意识地排斥汉学,这种风气使福建学界落后于全国水平。陈寿祺等人希望改变这一局面,并且力图扭转乾嘉以来闽省社会人心风俗日益凋敝的趋势。他在世时不遗余力地为振兴闽省的学术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件事:其一为仿效阮元设诂经精舍以及学海堂的做法,在主持闽省的文教重心——省会鳌峰书院12年间,通过改革书院的招生方法以及各项规章,培养了一批汉宋兼学的弟子,正式开启了福建的汉学风气;(39)其二就是主持重修福建通志。陈寿祺在鳌峰书院汇聚并培养了不少在经学、小学、舆地等方面的人才,为总纂《道光志》提供了方便。他在鳌峰的不少门生弟子,如王捷南、丁汝恭、赖其恭、张际亮等人都参与《道光志》编撰。其他如何治运、高澍然、冯登府等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陈寿祺思想之影响。他们是嘉道学风变迁的受益者,不但为陈寿祺完成一部在当时学者看来体例与内容颇为完备、有裨实用的通志提供了智力支持,也是继续发扬新学风的身体力行者。如前谢章铤言,《道光志》在《职官表》、《经籍志》、《方言考》等内容上于朴学研究大有裨益。然而,这些体例上的突破若要在闽省学风转变之前出现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嘉道闽省学风的转型也正体现在这些方面上,并为后来闽省学者在相关领域有所造诣奠定了基础。最好的例证就是同光以后何秋涛的边疆史地研究,而其师陈庆镛正是陈寿祺的门生。
在《道学传》的废立和《儒林传》的人选问题上,陈寿祺力主取消《道学传》,并有意利用编撰新志的机会,表彰汉学先辈,专门为林一桂、万世美、谢震等人列传,以此为闽省汉学开拓者在清代福建学术史上赢得一定地位,进而改变朱子学在闽省“学术史”上独尊的局面。在郑光策应否列入《儒林传》问题上,则反映了嘉道闽省两种不同经世思想取向的矛盾。郑光策重视事功,而陈寿祺重视著述。由此,两种观点在《儒林传》人选问题上发生矛盾。这反映了学风转型过程中,相应的评价标准随之发生变化,旧有的《儒林传》似乎已难以同时涵盖两种取向的学者。陈寿祺摒弃郑光策的做法引起梁章钜等人的不满,当时的闽省督抚也出面干涉,最终致使道光通志未能顺利刊行,还几乎散失。
但是,随着经世之学与汉宋并重的新学风流行,陈寿祺振兴福建学术的努力与功绩逐渐为闽人所认同,他对闽省汉学研究先辈的追溯,也大体为本省学者接受。同治年间,《道光志》在左宗棠的支持下,终于在致用书院得以刊行。但此通志几经删改,已与原稿相去甚远。民国年间陈衍修民国《福建通志》,在体例与编写方法上遵循陈寿祺的做法,艺文虽立志,内容不收诗文,全录书目,道学仍无传,儒林区分为儒林、儒行两门,郑光策仍被剔除出儒林传,改入儒行,林一桂、万世美、谢震三人又恢复入儒林,把梁章钜等人当时所持的“不善”五点,统统翻了案。(40)区分儒林为儒林、儒行二种,解决了旧有《儒林传》难以同时容纳嘉道后经世事功与经学研究二类乡贤的问题,但对于改入《儒行传》的郑光策来说,地位似仍稍委屈了一点。
有清一代的学界,汉宋门户之争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其中纠葛着复杂的人脉关系。关于《道光志》纠纷事件,除了以往学界关注的“道学传”废立问题外,有关“儒林传”的人选问题、山川、方言、职官各志等问题也多多少少反映了嘉道闽省学风由独尊朱学到汉宋并重过程中所发生的学术与人脉之争,折射出了嘉道间闽省学风转变之时,闽省学术转型的先行者与传统朱子学势力的矛盾。因此,通志体例之争乃是我们了解当时人的学术观点、思想观念的一个窗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嘉道以后闽省乃至全国的学风转型。
注释:
①相关研究成果请参见:林家钟:《道光〈福建通志〉纠纷始末》,《福建史志》1988年第1期;官桂铨:《林则徐〈题鳌峰载笔图〉考》,《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4年第1期。
②⑤(29)(40)林家钟:《道光〈福建通志〉纠纷始末》,《福建史志》1988年第1期。当时人关于通志纠纷的言论集于《鳌峰书院载笔图》。参见谢章铤:《鳌峰载笔图跋》,《赌棋山庄全集·文又续集》卷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679页。
③梁章钜(1775-1849),字闳中,又字林,晚号退庵,福建侯官人。他曾刊刻郑光策的文集使其经世思想传于后世。
④(16)(19)(26)(34)高澍然:《与郑方伯、王观察论通志兼辞总纂书》,《抑块轩文抄》上卷,陈氏沧趣楼选本1948年校印,第89,89,89,89,90页。
⑥参见史革新:《陈寿祺与清嘉道年间闽省学风的演变》,《福建论坛》2002年第6期。另见,陈忠纯:《嘉道间螯峰书院的学术特征及其影响》,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⑦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史学杂稿订存》,齐鲁出版社1980年版。曹江红:《黄宗羲与〈明史·道学传〉的废置》,《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⑧史革新:《陈寿祺与清嘉道年间闽省学风的演变》,《福建论坛》2002年第6期。
⑨⑩(15)(25)陈寿祺:《答陈石士阁学书》,《左海全集·文集》卷五,清道光年间陈氏刻本,第76-77,77,76-77,76页。
(11)(12)梁章钜:《退庵随笔》,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846-847页。
(13)陈用光(1768-1835),字硕士,一字实思,清新城(今黎川)钟贤人。出身桐城派。
(14)陈寿祺:《与陈石士书》,《左海全集·文集》卷四,第32页。关于陈寿棋与陈用光的古文之争,另参见陈忠纯:《清嘉道间鳌峰书院的学术特征及其影响》,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17)(32)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三,清咸丰元年(1851)刻本,第14,15页。
(18)刘存仁:《上督学李铁梅阁学书》,《屺云楼文钞》卷三,光绪四年福州刻本,第1-2页。
(20)郑光策(?-1804),字琼河,又宇苏年,闽县人。掌教鳌峰书院三年(1802-1804年)。
(21)梁章钜:《郑苏年师》,《归田琐记》卷四,第75页。
(22)张际亮:《题鳌峰载笔图》,自谢章铤辑:《陈卿贤鳌峰载笔图纪事辑录一卷》(缩微胶卷),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4年。
(23)(38)谢章铤:《鳌峰载笔图跋》,《赌棋山庄全集·文又续集》卷二,第679页。
(24)陈寿祺:《与方彦闻令君书》,《左海全集·文集》卷五,第75页。
(27)参见郑光策:《答谢生鹏南书》,《西霞文钞》卷上,清刻本,第67页。
(28)陈寿祺:《上仪征公阮夫子书》,《左海全集·文集》卷五,第29页。
(30)陈寿祺:《谢震传》,《左海全集·文集》卷九,第1页。
(31)陈寿祺:《檄福建郡邑采访通志事实(代)》,《左海全集·文集》卷三,第64页。
(33)王捷南:《序》,《闽中沿革表》,清道光刻本,第1页。
(35)掷贞文:《福建通志修纂沿革史》,自陈衍撰:《福建通志》第一册,1938年8月刊,第6-7页。按:郑文言:以上各书“或不愿被删削,或密匿不出,多自行刊刻布于市。”(郑贞文:《福建通志修纂沿革史》,第6页。)另参见林家钟:《道光(福建通志)纠纷始末》,《福建史志》1988年第1期。
(36)林则徐:《鳌峰载笔图题辞》,引自《林则徐年谱新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86页。
(37)谢章铤:《评诗课卷答伯潜同年》,《赌棋山庄全集·余集》卷一,第1448页。
(39)陈忠纯:《鳌峰书院与近代前夜的闽省学风——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变迁及其影响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