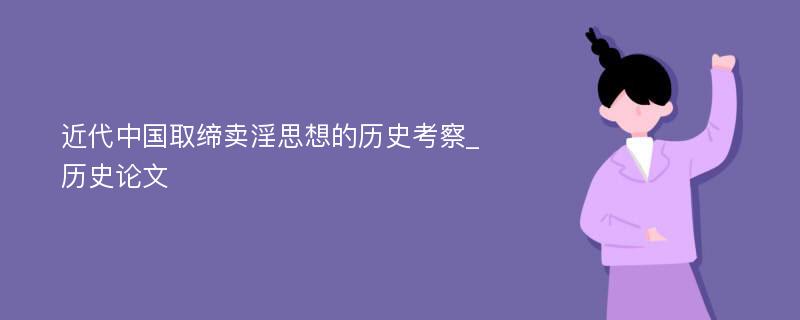
近代中国废娼思想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中国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4)05-0659-05
娼妓在中国由来已久,相传春秋时期齐国管仲“设女闾三百”,自此中国就有了公娼制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男性一直以娼妓为消魂荡魄怡情适性的工具,留下了许多倚翠偎红怜香惜玉的诗资文料。娼妓的痛楚生涯直至明清之际才为进步人士所关注。明末文人张岱在《陶庵梦艺》、清代学者俞正燮在《癸巳类稿》中均以不同形式对被凌辱的娼妓深表同情。但当时中国还没有什么新的力量足以瓦解中国封建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什么新型的理论武器足以摧毁封建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平之鸣只能是唏嘘的叹息而已。进入近代社会,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晚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资产阶级人权学说为思想武器,开始对娼妓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批判与讨伐,发出禁娼废娼的呼吁。到五四时期,废娼思想更加系统、全面而又深刻,酿成了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本文所要探讨的,是近代废娼思想的演变过程及其特色,力求从中得出某些启示。
一、太平天国朴素的废娼思想
近代废娼始于太平天国时期。为了防止男女混杂,破坏军风,败坏社会风气,太平天国严禁嫖娼。韦、石两王曾发布告示:“娼妓最宜禁绝也,男有男行,女有女行……倘有习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当娼者,合家剿洗,邻右擒送者有赏,知情故纵者一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1](225)为了禁娼,太平天国还规定:“凡我兄弟俱要各归各衙,不准私人过馆及在别馆寄宿等弊,违者斩。”[1](225)正是由于太平天国法律十分严厉以至实行株连法,其结果,在其管辖区娼妓大大减小,一些地区基本绝迹。这得到当时的目击者英国人呤利的高度评价:“在太平天国所有城市中,娼妓是完全绝迹的。”[2](241)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洪秀全等人毕竟是农民小生产者,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处于萌芽、广大农村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其一切活动仍摆脱不了传统几千年封建意识的束缚,更不太可能创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因此,其废娼思想也正如其男女平等思想一样,均不具有近代资产阶级人权意义上的思想内涵。相反,它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军事色彩:
其一,它是禁欲主义式的废娼。在洪秀全等人看来,男女两性关系是邪恶之源,只要男女之间相近一下,交谈片刻,相助一次,就有男女授受不清之嫌,就会淫荡奸邪,败坏民风,触怒天父上主皇上帝。为此,太平天国制定一些不近人性的严禁奸邪淫乱的法令,设立了分别男女的“男营女营制度”,将男女完全隔离开来,甚至达到“男与女不得交谈,母子不得并言”的地步[3](799)。这种禁欲性观念上进行的禁娼,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二,它是“上下迥异式”的废娼。太平天国禁娼是上下有别的,这集中体现在天朝领袖的极端的纵欲与一般军民的极端的禁欲。太平天国领袖们对“天朝”男女军士严行隔离,而自己却广选女色,妃嫔成群,淫奢无度,“各伪王俱有妇女十数人,传话出入者均十余岁女童,伪侯伪丞相以下,俱有妇女数人,以外皆不准私藏妇女”[4](377)。这种封建等级制下的禁娼恰恰说明,宗教教义上的抽象平等所掩盖的是天国首领们轻视妇女、禁锢妇女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
其三,它是“男女有别式”的废娼。“当娼者,合家剿洗”,“私行宿娼”者如何处置却没有下文、不了了之。这与一味指责、重罚卖淫妇的男女两重性道德标准没什么两样。
其四,它是“军事战争式”的废娼。太平天国禁娼妓,如同其禁缠足一样,其要旨是出于军事战斗需要。诚如著名太平天国史学家简又文评论:“在他们军事行动期间,凡占领一地,必定以城邑为军事根据地,几乎完全变为一座大军营,除官兵及军眷之外是不许老百姓居住,以防止宵小和间谍的混入,在这种实际情形之下,也不容许娼妓的活动。至于市郊乡间,如在交战或驻兵的情况下,兵荒马乱之中,也不容许娼妓的存在,所以就是不禁也会自禁的。”[5](1198)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并非近代人权意义上的禁娼,它只是太平天国政权控制臣民将士、提高战斗力的一种权宜之策。浓厚的封建色彩和军事色彩,决定了其禁娼不可能是彻底的、长久的,它也不可能会给妇女带来身心解放、主体意识的觉醒。当然,太平天国的禁娼之举,对数千年来娼妓制度进行了猛烈地冲击。这种冲击,是近代废娼思想产生的必要前提。
二、辛亥革命时期:近代人权意义上禁娼思想的产生
近代人权意义上的废娼思想萌生于辛亥革命时期。20世纪初,伴随西方女权思想的广泛流播和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日渐高涨,愈来愈严重的娼妓问题也开始为不少爱国志士所关注。他们在反帝反封建、提倡妇女解放的同时,发出了禁娼废娼的呼吁。《新女界杂志》《妇女时报》《女子世界》《天义报》等刊物,为受凌辱最甚的妓女鸣冤、呼救,认为妓女大抵出自寒门,不幸被人卖为娼妓,“父母得钱而鬻女,奸贩渔利而领家。于是逼其卖淫,教之婪索”,“辱骂出其前,鞭笞随其后,盐浸酒渍,痛彻心髓,炮烙囊抓,暗无天日。甚或至体无完肤,泣不成声,犹迫令强作欢颜,趋承游客”[6](443)。娼妓制度受到了舆论的指责。韶懿的《论娼妓之有害而无一利》一文,观点更进一步。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呜呼!人道之蟊贼,社会之大蠹,孰有如娼妓者哉。”接着从政治、经济、道德、卫生、法律等五方面对“既乖天理又悖人道”的娼妓制度的社会危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揭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废除娼妓的主张,即“广兴女学”厉行法律”筹画生机”,其中后者是“祛除娼妓”的“根本立论”“唯一要务”[7](286)。这些认识,显然比单纯的道德谴责要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天义报》派在娼妓问题的认识,比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独到之处。他们不仅把“废尽天下娼寮,去尽天下娼女”男女并重”视为“男女革命”的重要部分,还探讨了娼妓产生的社会根源。畏公在《女子劳动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上产生娼妓、妾御的原因是由于“生计”问题造成的。由于社会财富集中于资本家手中,“富者益富,妨夺平民之利,使之趋于贫,因家贫而鬻女之故,而娼妓妾御日益多,则娼妓妾御之制,谓之造因于贫民之家,不若谓其造因于富民之家也。……是则富民之心,不啻促贫民之家造设娼妓妾御养成所,以供一己逞欲之预备也”。揭示了残酷的阶级剥削是造成劳动人民贫困化、卖女为娼、卖女为妾的根本原因。由此文章进一步认为:“公产之制不行,于生计不能大加改革,而徒欲改良风俗,虽废娼废妾之论宣传于全国,而为妾为娼之贫妇女,宿娼蓄妾之富民,决非舆论及法律所能禁。”[8](933)这些主张无疑向彻底揭示妇女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接近了一步。
民国初年,不少女权团体或社会风俗改良团体把铲除娼妓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中华女子参政同盟会”在成立宣言中就把“公娼制度之改良”与“男女平权”“妇女政治地位之确立”并列为自己行动的政治纲领[9](57);“中华民国家庭改良会”也把“不得为狎游赌博”作为其“改良家庭习惯”、“实行男女平等”等十项条件之一[9](75)。把废娼同女权紧密联系起来,深化了对娼妓的认识。
从以上不难发现,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废娼禁娼的认识,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思想新颖性。与封建士大夫们,20世纪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废娼已不再完全停留在道德评论层面上,他们已开始从尊重女权、社会文明、经济发展等高度进行审视与评判。这种废娼意识和呼声已接近资产阶级人权意识上的废娼思想。这一特点,与资产阶级男女平等思想、天赋人权说等西学在中国传播息息相关。它们为晚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思娼妓制度提供了新型的思想武器,使他们有可能超越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站在新的高度对娼妓制度进行审视,从而超越前人。尤为注意的是,《天义报》派无政府主义者从对马克思主义主义妇女理论的理解出发,得出了娼妓现象是源于“生计”问题的正确结论。这些认识,令人耳目一新,颇为深刻。
其二,思想广度和深度的有限性。就思想的广度而言,当时参与抨击娼妓制度的知识分子人数甚少,他们主要集中于遁公、何震、畏公、韶懿等几位先进知识分子身上,而且他们也没有很好利用自己的团体和自己的舆论阵地来进行宣传,其思想散见其他文章之中,除了韶懿的《论娼妓之有害而无一利》一文外,尚无专门论述娼妓问题的作品,所以,他们的呼声十分微弱,其思想影响也十分有限,更未能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潮。正如五四废娼论者王会悟所指出的,辛亥时期女界发行的出版物中,就“有几种曾略论到关于娼妓问题的话”,但这些出版物的寿命都很短,并不曾产生什么反响[10]。就理论的深度而言,除了天义报派外,大多数先进分子对废娼问题的认识尚停滞在零散、肤浅的阶段。他们虽已从人权的高度来审视废娼问题,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但他们的思想仍缺乏系统性、全面性,也没有从社会制度上探索卖淫现象存在的原因,寻找废除娼的根本途径。
上述这些特点,展示了它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展示了这股新兴社会势力具有的朝气和活力。但这些特点又十足地反映出正在形成的中国资产阶级,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娘胎中,带出的先天性软骨病和畸形症。
三、五四时期:禁娼思想的成熟
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关妇女诸种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妇女解放思潮出现了一个空前活跃的局面。娼妓问题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废娼的舆论遂起,并逐渐形成一种群众运动。
五四废娼论者对娼妓问题的讨论,涉及的内容很多,诸如娼妓的历史和现状,娼妓存在与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的关系等。其中,最令人关心的是“为什么要废娼”和“怎样废娼”的问题,这也是当时宣传和讨论最多的两大主题。
关于废娼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五四先进分子在这一方面的论述很多,其中,李大钊《废娼问题》一文很有代表性,他提出五大废娼理由:“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为保持妇女地位不可不废娼”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11](347,348)。除了上述理由外,还有持正国体、淳正社会风俗、维护妓女自身的健康,保持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提高民族人种的质量等等作用。无疑,当时所鼓吹的废娼理由中,首要的是妇女的平等自由和人格解放。这同五四妇女解放思潮的总旋律是一致的。
关于废娼的具体办法与根本途径。废娼论者认为,废娼“其事至困难,断难期朝夕间也”,因此,要铲除娼妓,应有“治标方法”和“治本方法”[12](90),即要“标本兼治”。当时先进分子对“治标方法”的论述最多,其中浙江省议员惠民等所提议案和胡怀琛的《废娼问题》一文最为详细,颇有代表性。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分期取缔娼妓机构;分析娼妓来源、断绝娼妓的来源;分析嫖客的来源及原因,提出断绝嫖客嫖源的措施;大力提倡正当的娱乐,提高全民的文化教育素质;禁止淫秽书刊画报和影戏等。这些“治标方法”是属于改良性质,但在当时仍不失其进步意义。而且难能可贵的是,王会悟、李三无等废娼论者还看到了娼妓最终的社会根源是私有制,明确地提出了“治本之法”:“要想铲除娼妓阶级,非先从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着手实行改造不可”[13](352)。将铲除娼妓制度与废除私有制联系起来,其认识是深刻的,显然是他们主动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现。
由此可见,五四时期废娼的议论,已不再简单地停留在对买卖春行为的指责和批判上,从社会制度上加深对废娼问题的认识,探索卖淫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寻找废娼的具体办法和根本途径。这种认识,适应了妇女解放的时代潮流,把握了人的近代化的内在要求,对推动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五四时期废娼思想,无疑是辛亥时期这一思想的延续与发展,但与后者相比较,却有着诸多方面的差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一,社会基础更为广泛。如果说辛亥时期呼吁废娼仅是少数几人呐喊,那么到五四时期这支队伍已经扩展到一大批知识分子群体身上。他们当中既包括名闻遐迩的鸿儒硕学,也包括一些其名不扬的进步青年。他们在《新月》《晨报》《民国日报》《益世报》《华北新报》《妇女杂志》《新妇女》《解放画报》《妇女声》《女星》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对废娼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李大钊《废娼问题》,王会悟的《中国娼妓问题》《废娼运动我见》,王无为的《文化运动与废娼运动》,李三无的《废除娼运动管见》,胡怀琛的《废娼问题》,周建人的《废娼的根本问题》,邵力子的《娼妓与亲权》等均是专门论述废娼问题的力作,它们对于开拓人们的视野,深化人们对娼妓问题的认识,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其二,政治实践性。与20世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五四先进分子没有停留在废娼的理论探讨上,还于1920年至1924年在上海、南京、苏州、广州、浙江、天津等地先后开展轰轰烈烈的废娼运动。其中,广州废娼运动的规模、影响较大。1921年9月,广东青年会发起旨在废娼的贞洁运动,并成立了领导机构“贞洁大运动会”,一时,“四方风闻响应,各县议员也纷纷提议废娼,差不多成了全省有力的舆论”[14]。次年4月1日,广东“贞洁大运动会”发动近2万群众举有了公民废娼大游行,向当局提出了废娼议案。这些活动虽因得不到支持均无实际的效果,但在扩大废娼思想影响、深化人们认识、开通社会风气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其三,思想更为深刻。如果说辛亥前后废娼思想没有做到系统、全面而深刻,那么,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应该说做到了这一点。这种深刻性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把废娼问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主题——人的解放联系起来。这对开启人们觉醒,理解废娼本质,无疑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如前所述,辛亥时期,“中华女子参政同盟会”等女权组织就把“公娼制度之改良”列入各自的政治纲领;何震等无政府主义者也将“废尽天下娼寮,去尽天下娼女”视为“男女革命”的重要部分。然而,这些思想在当时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影响甚微。就思想界的主流,废娼问题与妇女解放一样,并没有纳入到人的解放的轨道。而五四先进分子一开始就将废除娼妓上升到妇女解放、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前提之一这样一个高度。他们认为,娼妓制度的存在无异于将女子视为玩物,“大失妇女在社会上人格的尊严,启男子轻侮妇女、玩弄妇女的心”,所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第一应该把这妇女界最大的耻辱革除,不使他再留一点痕迹”[11](347);所以“对于娼妓,是应该行二重解放的,先解放他使他变普通女子,再解放他使变‘人’”[15](46)。将废娼问题与妇女解放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既有说服力、号召力,同时又深化了对五四妇女问题的认识,有利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
(2)五四废娼思想与当时改造社会的探索结合得异常紧密。五四前后的进步青年面对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新潮,他们的视野逐渐转向民众的解放与社会的改造,这就使得废除娼妓就逐渐成为改造社会的探索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诚如时人所指出的:“解放与改造,要从社会不平处做起,更要从不平中间最不平处做起,眼前劳动者和普通的女子,所受待遇,固然是不平之至;但比起操皮肉生涯的娼妓,却好得多;不讲解放与改造则已,倘讲解放与改造,我敢说第一种要解放的人,就是娼妓;第一个要改造的环境,就是娼妓的环境,再也不能有什么异议。”[16]总之,“五四”之后,废娼逐渐与改造社会的探索合流。
(3)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使五四废娼思想跃进到一个新境界和新层次。“五四”之后,以王会悟、李三无等代表的进步人士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来分析废娼问题。他们认为,娼妓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的存在,如果不从根本上废除私有制,推翻代表这种制度的现政权,要想彻底根绝娼妓制度是不可能的。李三无、王会悟等明确指出:“社会上所以有娼妓这种阶级,完全是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下面必然的结果”,所以,“要想铲除娼妓阶级,非先从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着手实行改造不可。如果不想方法谋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只是诉诸个人的道德,拿外部的压力做绝灭娼妓阶级的唯一手段,这才是其愚不可及呢”[13](354)。这些表明了五四时期废娼思想已经跃上了一个新的境界。
与20世纪初年相比较,五四废除娼思想,不论其思想的广度,抑或其深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反映了人们对时代主题的新思考、新选择,以及人们在对历史的反思中和在世界新思潮的影响下,价值取向的新确定。显然,这些对当时及其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4-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