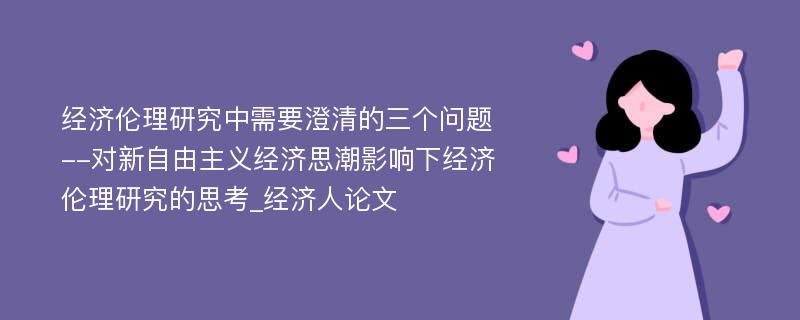
经济伦理研究有待澄清的三个问题——反思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影响下的经济伦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伦理论文,自由主义论文,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3-0121-06
经济伦理研究在中国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市场体制的改革之前中国很少有人研究经济伦理。1992年之后,尤其是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规划了市场经济转型的方略之后,经济伦理的研究日渐兴起。其初衷是,面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狂热的逐利冲动、市场成为道德无政府状态的场所、道德虚无主义的蔓延,以及市场中出现的信用缺失、钱权交易,伦理学界的一些同仁把目光转向市场与道德的关系,探索市场关系带来的伦理变革,揭示市场关系的伦理机制及其与非市场关系之间的界限、企业经营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等问题,并试图通过这种研究呼吁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界和企业界重视道德建设,寻求解决市场经济下道德建设诸多难题的途径。随着经济的繁荣、市场的兴旺,经济伦理学也成为伦理学诸分支学科中的显学,吸引了很多学界同仁的关注。除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之外,也涉及到历史上的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等学理问题。同时也开始面向世界,从广泛的介绍引进国际上的研究成果,与国际上的经济伦理学界开展交流和沟通,一直到走向世界,把中国的研究成果向国外介绍。
近两年,对金融危机的反思,成为经济伦理研究的焦点。学界对危机本身做了许多分析。尤其是对于导致危机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国际上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做了许多分析,并提出了如何从中汲取教训的各种见解。但是,这种经济思潮对经济伦理学本身有什么影响?是不是需要作出清理和反思?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就是要不要用“反求诸己”的精神,来反思这场危机?即不仅要把“危机”作为我们的一个研究对象,而且要把我们以往所做的经济伦理的研究本身作为一个反思的对象,去思考我们以前的研究。这个学科该向何处去?笔者曾经在《如何对金融危机进行伦理反思》一文中提出:对金融危机的伦理反思不能停留于华尔街高管个人的贪婪和美国公众的消费主义的层面,而需要深入到19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政治潮流推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蕴含的政治哲学以及与其相应的伦理观念。其中与新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不可小视。中国学界要正视由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对各个学科的影响①。本文拟就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及其背后的哲学观念给经济伦理研究带来的三个问题作一讨论。
一、如何看待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经济伦理学能不能囿于纯经济的视阈?
自马歇尔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特点是,一反以往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现象仅仅做一种抽象式的研究,把其他的因素尤其是政治和社会等因素都抽象掉了。这种抽象式的研究固然有其价值,促进了经济学的数学化,推进了计量经济学等方面的实证研究。但是,其天然的不足式的研究是就经济论经济。而且把功利主义的效率论,作为基本的出发点,衍生出当今的GDP主义,或者可以称之为只求效率的“增长主义”。然而,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经济生活、尤其是市场其实不是自足的,它是镶嵌在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之中的。
金融危机的爆发,自然有市场运行自身所产生的问题,但是政府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的经济政策显然不仅仅是从经济的角度制定的,还受整个国家战略的支配。就一国范围来看,有学者已经指出,美国的金融危机与国家干预的失败和政府政治伦理的错位有关。泡沫往往是政府的作为所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之后,主持美联署的格林斯潘是有意地制造房产的泡沫。他感到地产的收益对于消费的作用大于股票,于是刻意吹大泡沫。次级贷款这种金融的新形式就是为此服务的。美国的“两房”就是一个政府支持的机构,而其泡沫的积累也是在政府的政策下形成的。危机治理的过程,也与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有密切关系。在摆脱危机的过程中,有些国家出现了主权基金的信用危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强政府的国家,能迅速地摆脱国际危机的冲击,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但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包括了伦理问题都不仅仅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的品德所致,而是与政府的政策导向、激励机制等有密切关系。经济生活中的钱权结合,它所导致的剥夺性积累的现象大量发生,以及相当普遍的分配不公等,这些都是经济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至少与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缺失息息相关。而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伦理问题是这种情况在观念上的反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经济问题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而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问题,也不能单纯地就经济伦理谈经济伦理。
如果从国际范围来看,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包括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单单从经济视角是说不清楚也搞不明白的。因为,现在的世界不仅有一个全球市场而且是由为数众多的主权国家组成的。冷战之后的全球经济体系,是由依托其军事政治霸权的美国经济霸权为主导的。许多运行的规则和架构都是在美国主导下,以自己的霸权、国家利益以及为此服务的一些经济观念为前提制定出来的。以全球自由贸易为例,如意大利学者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所指出,1990年代在克林顿时期美国是积极追求和提倡全球化的,强调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多边贸易。但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帝国计划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自我监管学说“仅部分相符”②。一旦自由市场的运作对美国的中心地位构成威胁情况就不一样了。到小布什的时候就觉得“全球化”“听上去就像要制定诸多可能会限制总统的选择并淡化美国的影响力的规则”③。许多西方国家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大力推进自由贸易,一旦经济上遇到困境就把本国的利益、本国的难题放到首位。自由贸易的旗帜大家还都是想要举的,但是贸易保护是舍不得丢掉的。只是想把保护主义这顶帽子加给他人,以取得自己更大的利益。而其中所说的利益不仅仅是经济的利益,还有许多,包括军事地缘政治等等的国家利益。
至于对于金融危机的伦理反思,起初相当一部分的分析都集中于下面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华尔街的高管们的贪婪去寻求原因,从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角度寻求出路;另一个方面是从美国公众的消费主义的伦理观念去寻求原因,将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美国人的超前消费和大量透支;这种分析认为金融精英正是利用这种现象将债务捆绑成有毒资产,形成泡沫,一旦泡沫被刺破,危机就接踵而来。然而这类分析,除了表达公众对华尔街金融精英的贪婪无度和不负责任的愤慨之情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公众对于美国人的消费无度与享乐主义的不满之外,在某种强度上,还是显得苍白无力。此后一段时间里,中国学界又转向对财富观念的分析,试图从财富观念上寻求根源,并提出种种新的财富观念、财富伦理。然而“财富”如当年斯密所说,不是金银,而是劳动的产物,这就自然会涉及生产关系以及维系各种生产关系的政治等上层建筑,不同的财富观念就是被这些社会关系所决定的。
经济伦理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自然离不开经济学,但是它能不能建立在马歇尔以后的抽象的经济学说的基础上,就成了一个问题。看来,起码需要重返政治经济学。离开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基础的经济伦理,也就无法直面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难题。危机之后在中国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就是,经济学界有一些学者更加重视政治经济学了,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李斯特等人的国民经济学。从事经济伦理的学者中也有一些同仁开始从政治经济学中汲取智慧,并探寻新的视角。
这是很有益处的。以亚当·斯密为例,只要读读这位“被引用最多但是被阅读最少的”的学者的著作,就可以看到,他在《国富论》中明确地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是一门政治家、立法家的学问而不是企业家的学问。这就意味着经济包括经济伦理,是离不开社会、政治的。此外,如阿里吉所说,他有一个历史社会学或者经济社会学视野,以一个“大分流”考察框架,具体地考察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演进。对资本主义的中心如何从意大利到荷兰到英国,并对北美半殖民地(也就是今天的美国)前景作出分析。这个视角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非常重要。没有这个历史的大分流的视角,我们就无法理解美国何以会从最大的债权国演化为最大的债务国,并深陷信用危机;无法理解那些金融寡头和跨国公司的作为;无法理解今天的危机下各国的不同处境。个别企业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各种伦理问题,也需要在这样一个大视野中理解和解读。
许多经济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是经济之外的但对经济具有重大作用的东西,如政府的财政、货币、社会以至于军事外交等政策或者是政府对市场、企业的监管出了问题。研究经济伦理不能囿于经济领域,否则只能是隔靴搔痒,击不中要害。当然,经济伦理研究并不是要取代政治学、社会学,但是它可以从伦理的角度为市场良法、政府政策提供价值维度和伦理支持。这本来就是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功能。经济伦理包含了企业伦理但是不能归结为企业伦理。
二、如何看待个体的经济活动及其伦理观念与社会的各种制度因素、包括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经济伦理学要不要摆脱“原子主义”的思维模式?
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不仅要研究经济如何运行还要研究各种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明确地把生产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下的雇佣劳动制度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在哲学上突出地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至于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则鲜明地反对原子主义,强调国家才是“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个人都是他的国家的一个成员”⑤。“个人从国家那里获得文明、教育、进步、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带来的利益。如果国家衰落,个人就得承担起衰落的灾难性后果”⑥。总之“个人的祸福系于国家的独立和进步”⑦。即便是亚当·斯密,也如美国学者沃哈恩所说:他确实是个人经济自由的倡导者,但不是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者。也没有说过,所有人都是“社会原子”。他说过人只能在社会中生活,他不是把人看做反社会的⑧。斯密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之后,明确地把地主、资本的占有者和雇佣劳动者加以区分,而不是泛泛地谈论个人,也不去泛泛地谈论富人。近来有学者把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公民”解读为“非个体的个体”⑨,这也许可以用来解读斯密的个体观。
但是新自由主义,无论在社会哲学上还是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特点都是以原子主义的个体主义作为出发点。把人当作社会原子,把个体当做是自足的,而且把所有的社会现象包括经济现象解析为个人的行为,理解为个体之间的博弈。这样就把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因素,尤其是生产关系,包括了企业内部的雇佣与被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生活中的分配关系以及国际经济秩序中占有霸权地位国家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的权力的不平等等重要的环节都抽象掉了。这种抽象如果作为一种理论的假设,由此作出推论以展示经济生活中的某种现象演化的趋势或可能性,自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把这种抽象当作可以普遍适用的公式,甚至当做事实本身,那就失之谬误了。这也正是新自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纠结之处。因为离开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自然也就会把市场竞争视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生存竞争。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在中国也颇为流行。一时间,离开了制度因素,离开了生产关系来谈论经济动机、谈论财富观念、穷人与富人、输者和赢者、强势和弱势,等等,到处可见。
这种情况对经济伦理学也颇有影响。我们引进的经济伦理学的著作其中大部分是把康德的道义论或者是穆勒的功利主义作为其伦理学的前提,而这两者无不以原子主义的社会理论为方法论的基础。对于经济伦理的许多问题的讨论,如信任、企业责任等等往往也都是从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契约关系为基本的概念框架。但是,这并不足以解释现实生活中企业和企业家的全部行为。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学界引进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把员工和企业主看做是一个利益相关者,这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企业中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就被遮盖了。雇佣劳动者能不能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被排除在视野之外。利益关系如恩格斯所说是生产关系的体现。所谓“利益相关者”是值得分析的一个提法,它实际上是把复杂的生产关系简单化和抽象化了。此外,现实生活中有的企业家在抗震救灾中自觉自愿地作出了很多奉献,其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意识到每个人如李斯特所说:作为国家的成员,与其他的成员一起“拥有共同的政府、共同的法律、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荣誉、共同的防御和保护他们的权利、财富、生命的共同的制度”。这些具有重大的伦理意义的行为,在原子主义的概念框架下,也难以得到解释。此外还有许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离开了制度因素,包括生产关系,是看不清楚也说不清楚的。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是国际上的贸易战、货币战,还是国际金融体系的权力之争等等,都与制度的因素有关。伦理生活的社会基础不是生产力、不是GDP,而是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社会结构(职业分布、阶层结构等)以至于政治制度等等制度性的东西。离开了这些制度性的东西,经济伦理就难以面向现实,也难以发挥作用。看来经济伦理的研究必须拓宽视野,纳入制度性的各种因素,跳出原子主义的窠臼。
三、如何对待“经济人假设”?经济伦理学要不要超越“经济人”概念?
在原子主义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经济人”概念。也就是认定:“人永远是一个功利最大化者”;“我们在一般情况下都仅仅受自利的驱动”,是“不管别人的人”,或者在经济交换的时候是“不关心别人的利益”的人,并把这一概念作为推论所有的经济问题的出发点。
人们往往把这一概念归诸于亚当·斯密。但是正如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所指出,真正作出“经济人”假设并加以严格界定的却是约翰·穆勒⑩。1836年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一文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不同于技艺的“科学”,目的是要寻求一般的法则,那么它所需要采用的方法就是“归纳推理综合法”或者可以直接称为“演绎法”。其特点在于,“这门科学必然是从假设而不是从事实中进行推论的”。而政治经济学预设的对人的定义,就是“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11)。这一段文字就是“经济人”假设的经典表述。另一种表述就是,“只把人看作是渴望占有财富,并能对达到目的的各种手段的有效性进行比较”(12)。他“宁可要较大份额的财富而不要较小的财富”。简言之,就是把人看作是理性的、自利的、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这也就是后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人”的界说的基本内涵。
当年约翰·穆勒强调这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一种假设,这种假设仅仅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具体地说就是在市场交易中,人们既不像从事慈善活动那样,出于对弱者的同情,从利他的动机出发;也不像给亲友馈赠那样出于亲情、友情或对家族成员的义务。对市场中人们的经济动机的这种假设,比较确切地揭示了人们在市场中的经济行为,就这一意义而言,确实是“最接近真理的假说。”但是,穆勒还认为,即使在经济生活中,这一假设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还可以有另外的一些假设,或者可以把人视为与他人联系的,因而会产生诸如爱慕、良心、义务感;或者把人视为生活在社会中人,即是构成人类整体的一份子,因而会关注整个社会、以至全体人类的福利。所以“经济人”这一假设不意味着,人事实上就是如此。他一再发出警示:“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会如此荒谬地认为人类事实上如此”(13)。可是当代的新自由主义早已将穆勒的警示置之度外。他们不仅把“经济人”假说当作“事实上的人”,把“自利”视为人不变的唯一的本性,并推行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把这种假设推广到伦理、社会、政治等诸多领域和学科,将集体行为、利他主义等等都视为出自利己的动机。可见把“经济人”视为“事实上的人”的一个后果就是剥去了人类本来具有的“良心、义务感以及对人类福利的关心”等等道德情感,结果是对利益的追求、逐利的市场竞争,就变成了赤裸裸的动物般的生存竞争。经济自由主义就这样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合流。要旨就是把整个社会生活看作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这就是所谓的适者生存,或者说不适者淘汰(也就是不得生存)。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把这种观点形象地描述如下:把人生就看作是一场输赢的赌博。“生活的目标成为不断啮取树叶,直到能够得着的最高树干,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可能方式是,让脖子最长的长颈鹿活下来而饿死那些脖子较短的”。至于这种竞争性的斗争的代价则根本不予考虑。于是那些饿死的长颈鹿所遭受的痛苦,那些在争斗中落到地上并被践踏掉的甜嫩树叶,脖子较长的长颈鹿由于过量摄食而引起的不适,在这种原本温和的动物脸上所浮现出来的贪婪、焦虑等种种不愉快的表情等等,都统统被略去了(14)。
这类观念,近年来在中国十分流行。一方面“经济人”不仅用于解释当今的经济行为而且还用于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甚至解释古代的历史。连一本关于明朝历史的畅销书也说:“斯密同志告诉我们,人永远是自私的。”讲三国的名人的名言“诸葛亮选了刘备这支绩优股”,传递的也是这样的观念——古今中外的人都是一个利己的动物。另一方面,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本来是在西方也为众多思想家和社会人士所不齿的观念,反而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人们谈论的都是胜者、败者、或强势者、弱势者(也就是被边缘化者)。就把人生看作是一场赌博,赌的不仅仅是金钱、股票,还是生命本身。“赢”成为人生的目标。给“赢者”奉上的一顶最为冠冕堂皇的帽子,就是“成功人士”。“成功人士的标志”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广告词。铺天盖地的广告所定下的成功人士的“标准”,就是香车、豪宅和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于是大款、大腕、大官、大牌,就成为全社会仰慕或者妒忌的对象。至于那些辛勤劳作,为国家默默耕耘但却囊中羞涩买不起那些奢侈品的众多普通的体力和智力劳动者,自然就变成了“非成功人士”、“弱势群体”。在一定意义上也就属于“失败者”、“输家”的行列,更不用说那些默默地承受着改革代价的困难人群了。更有甚者,“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赢在起点”,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早教广告词,铺天盖地,大有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当做婴儿的乳汁的架势。
面对这样一种态势,经济伦理却显得软弱无力。究其原因之一,就是有些论者,仿效一些西方学者,把“自利的经济人”作为基本的出发点。以对信任问题的讨论为例。有些论者一味地强调,信任只能由“自利的经济人”在竞争中反复博弈才能产生。把信任和诚信的缺失归之于市场的不成熟。好像只要假以时日,等待市场成熟起来,这类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要么认为依托胡萝卜加大棒的外在的制约和激励机制,经济伦理才可能有一定的约束力。还有的论者则力图证明,以利润的无限追求为目的的资本,本身就会在自身的演进中产生道德,因为道德也可以成为一种能够带来利润的资源,出于利润的追求就可以滋生出道德来。但是,当今的危机以严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非常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经过几百年的反复博弈建立起来的信用体系,也是靠不住的。而外在的各种约束和激励机制,真正能够发生作用的也只有严格的法制。然而如果只有依靠外在的法律的强制,那么,伦理也就被归结为法律了,其自身的独特功能也就被隐去了。伦理学自身的价值又何以显示?把“自利的经济人”作为伦理学或经济伦理学的基本出发点,其结果必然会使伦理学或经济伦理学丧失自身的主体性而被边缘化,甚至沦为资本的工具。
看来,“经济人”能不能成为经济伦理的基本出发点,就成了问题。而这恰恰是关乎经济伦理何以可能的根本性问题。固然在市场经济下,“经济人”这一假设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是具有解释力的。因为事实上在市场的经济活动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确实是企业和个体的经济动机。如何对这种动机进行导引是经济伦理学需要直面的一大问题。但是,如果不把穆勒所说的“经济人”假设所抽象掉的“人类本来具有的”“良心、义务感以及对人类福利的关心”等等道德情感,恢复到人性的基本假定之中,不把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一个归属于一定的国家民族和其他共同体的成员所具有的社会感情(包括道德的传承)和认同感纳入到推论的前提之中,那么,我们还有可能找到约束无止境的利欲追求的内在的约束力,发挥经济伦理本该具有的伦理功能吗?当然,这里的问题相当复杂,但现实的人或企业家本来就是复杂的社会存在,绝不仅仅就是单一的纯粹的“经济人”,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许多德行感人的企业家的范例,其实已经给出了回答。
总之,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那么20世纪90年代,我们从事经济伦理研究的初衷,就难以实现。搞得不好,就成了学者圈子里自弹自唱的卡拉OK。甚至会被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所侵蚀,成为他们的附庸,失去自己存在的根据。
注释:
①赵修义:《如何对金融危机进行伦理反思》,《道德与文明》2010年第2期。
②③[意]乔万尼·阿瑞基:《亚当·斯密在北京》,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188-189页。
④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⑤⑥⑦[德]李斯特:《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载《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8、28、31页。
⑧[美]沃哈恩:《亚当·斯密及其留给现代资本主义的遗产》,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
⑨参见黄显中《公正德性论——亚里士多德公正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⑩[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11)(12)(13)[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中译文刊载于《海派经济学》第六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137、138页。
(14)[英]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载凯恩斯《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译本,第296页。
标签:经济人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财富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伦理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