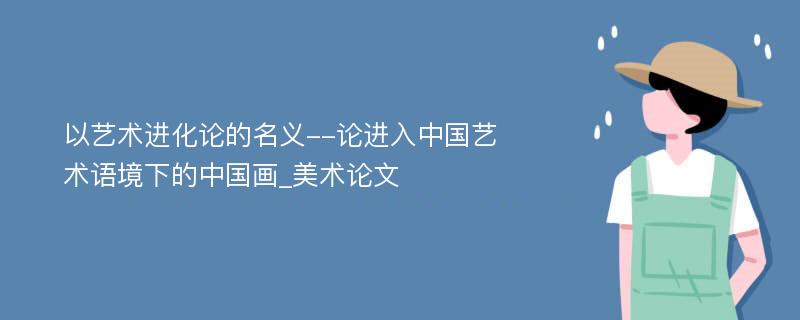
以艺术进化论为名:美术入华语境中的中国画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画论论文,华语论文,进化论论文,中国论文,美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2年,陈衡恪、陈寅恪兄弟二人游学东瀛,经上海,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①此时,陈氏兄弟的祖父、因戊戌政变而被革职的陈宝箴已辞世二年,而经李提摩太协助逃至海外的康有为继续流亡,两年后将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登岸,身临其境地观摩西方古典文明。
十五年后,康有为发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感叹,提出“以形神为主,而不取写意;以着色界画为正,而以墨笔粗简者为别派”②。再过数年,陈衡恪撰写著名画论《文人画之价值》,似乎针锋相对地写道:“所贵乎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③看起来,图真与写意,这两个曾经完全可能融合无间而南北宗论者经过精心策划方才勉强区分的范畴,终于在西学东渐的巨大阴影下,前所未有地凸显为非此即彼的民族复兴的美学。
然而,李提摩太也许会说,康、陈二人艺术思想差距远没有他们肤色区别那么巨大。作为维新派主事者,或是其支持者的直接后裔,他们必定都仔细读过李提摩太所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熟悉那种充斥于晚清民国思想界的进化史观。当他们以不同旨趣谈论绘画的时候,只不过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为本土文化寻求出路的普遍焦虑。考虑到康、陈及其同时代人都自觉把中国绘画划入了“美术”这样一个外来范畴,倘若我们果真打算对其艺术理论作出合理评价,至少应追问一下,“美术”对他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近人多有指出,“美术”(fine art)乃近代自东瀛舶来的西洋货。据大村西崖之说,日本“因参与奥国维也那博览会之报告书而有‘美术’二字之新译语。每回内国劝业博览会亦设美术部,绘画遂视为重要”④。易言之,日本“美术”这一概念的出现,与明治政府维新兴国之策密不可分。然而,无论是最早接触“美术”这一概念的东方人⑤,还是讨论“美术”入华的艺术史研究者,似乎都易于忽视隐藏于这一事实背后的意义。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次年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大清举国震动。数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拉开序幕。同年,上海的英美传教士机构广学会记录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知识风气:
去年我们为中国人翻译的一本最重要的书,就是李提摩太先生译的马恳西的《泰西新史揽要》。……最近碰巧李提摩太先生为了教会工作到北京去,他发现士人们都在谈论这本书,把它叫作新学问。他们开始认识到过去不知道这种新学问,他们需要对它关心。⑥
《泰西新史揽要》即英国史家罗伯特·麦肯齐的《十九世纪史》。北京的士人们从中发现的“新学问”,即进化论的历史观。按照柯林武德的意见,《十九世纪史》“把那个世纪描绘成一个进步的时代,一个从一种几乎无法再加以夸张的野蛮、无知和兽性的状态进步到科学、启蒙和民主统治的时代”。它属于“第三流历史学著作中最乏味的一些残余”⑦。但这么一本在西方不受好评的著作,却在晚清成为最流行的历史读物,洋务改革之李鸿章、张之洞,维新变法之康有为、梁启超,均甚推重之。约两年后,不妨认为是在此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严复翻译了著名的《天演论》。此后数十年,甚至可能直至今日,整整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刻上社会进化论的烙印。
1896年,康有为两次向光绪进呈关于明治维新的编年史著《日本变政考》,其序开篇完全是“新学问”的简要演示⑧。直到此时,直到中国人接受“新学问”,正视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以前所未有的焦虑和谦卑去看待东洋邻国之崛起的时候,明治政府所引入的“美术”才真正地进入他们的视野。《日本变政考》详述明治六年日本变法而于其国中所立会若干,“其会之有关工艺者,曰书画会,曰名磁会,曰雕刻会,曰七宝会,曰女红会,曰锦器会,曰古钱会,曰博览会”。叙述中尽管尚未出现“美术”二字,却比此前任何中国人的记载都更准确地把握住明治政府引入“美术”这一概念的初衷。康有为按语:“一理一事,莫不有学以教导之,有会以讲求之,是故人人而教之,则人人皆可为国家之用矣。”⑨这种从纯粹功利角度看待艺术的观念,是借鉴明治维新推行政治改革的康有为在讨论艺术时的立足点。在后来多年海外流亡生涯中,康氏每至一处,始终不忘考察当地工业与艺术产品,并时常设身处地考虑如何通过商业输出国内艺术品。在数年后所撰《官制议》中,他构想了一系列政要部门,其中赫然有“美术部”:
美术兼音乐,吾国有乐部,则已设专部也。今各国工艺进化日上,皆由讲求美术之故。吾国古乐已绝,而画则名士乃为之,至雕刻、织绣等事,士人不为,又无振兴之,以此绝艺沦胥。故工业、商情皆大败,由美术不振之故也。今宜改乐部为美术部,或以文部兼之,或即因乐部之名为之可也。其属分音乐、图画、织绣、雕刻、建筑五司。……如此则中国工艺必大兴矣。不设专官主之,则未有能刮起气象者也。⑩
今人也许会嘲讽说,康有为错误地把“美术”当成了实用艺术。但不要忘了,从一开始,东方人便是为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进步,为了强国富民这种功利目的创造和引入“美术”这一概念。从康德开始的那种以美为美的艺术思想,除非经必要的偷梁换柱,在1903年以前之中国尚无生根的土壤。
即使是最早真正研读了康德哲学的王国维,首先接触到的“美术”仍然很可能从属于进化论这种“新学问”。1902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发表日人元良勇次郎著《伦理学》中译本。是书原作于1893年,为启蒙类读物,著者自序称“自欧洲之文明转入以来,科学之进步一日盛一日……惟于伦理主义……不务进步”,宜“参考欧洲之科学的及社会的思想,以考究道德之原理”,进化论色彩昭然可见(11)。该书所附术语表中有“fine art,美术”一条,这不仅是现存观堂著述中最早出现该概念的材料,并且因《教育世界》这种刊物阅读面远胜此前各种东游日记而可被视为“美术”入华之标志性事件。易言之,在中国,“美术”从一开始便是进化论输入的副产品。
但比康有为更熟悉德国哲学的王国维很快就捕获了“美术”的原义。邵宏曾指出,王氏首先在20世纪初将日语译词“美术”引入中国(12)。此说若指“美术”二字首次进入华人著述,固未然,若指未打折扣的“fine art”观念最早在中国得到解释和传播,则极是。译出《伦理学》后数年,王国维对“美术”、“美学”这两个日译词表现出极大兴趣。1904年,《教育世界》所刊王文《孔子之美育主义》、《红楼梦评论》不仅明确宣示“fine art”之非功利性,并且以“美学”、“美术”为中国文学批评之核心概念。次年五月,《教育世界》又刊其《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论曰: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及实业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求诸哲学及美术不可。(13)
至此,西来的“fine art”终于名副其实地在汉语世界找到了对应物。
然而,强调“美术”的非功利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砍断其与进化论的联系。王国维使用“美术”以前,“fine art”的概念已通过传教士作为进化论有机组成部分被引入中国。1879年起,德人花之安所著《自西徂东》在《万国公报》连载,其中有《上艺之华美》一章。1882年,华人牧师颜永京译《肄业要览》由上海格致书室出版,谈到“闲时玩物适情之举”(14)。但无论“雅艺”、“闲时玩物适情之举”如何切合于自古君子“游于艺”的思想,人们更需要的是容纳“fine art”的新学科分类体系所代表的“进步的”新学问,而非“fine art”本身。
1900至1901年,蔡元培《学堂教科论》将学术分而为三:“曰有形理学,曰无形理学,曰哲学……彼云哲学,即吾国所谓道学也。”无形理学之下分名学、群学及文学。其中,“文学者,亦谓之美术学。《春秋》所谓文致太平,而《肄业要览》称为玩物适情之学者,以音乐为最显,移风易俗,言者详矣”(15)。这一界定保留着艺术可“成教化,助人伦”的传统观念。可以说,1901年在《肄业要览》这类读物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蔡元培对“fine art”的理解还远远不如数年后写下《孔子之美育主义》的王国维。
十一年后,中华民国成立,留德四年归来的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旋即援康德哲学立论推行美育。其《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曰:“美感者……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起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16)但从根本上说,蔡元培的美育是通过艺术作用于现象世界的策略。1917年,他依据同一套理论提出,美术通过作用于国民道德而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日耳曼民族美术偏于高,故德军攻战勇猛,拉丁民族美术偏于美,故法人防守沉稳,“战争持久之能力,源于美术之作用者,亦必非浅鲜矣”(17)。即使这种德国哲学、美学在政治军事学中之演绎多少有点庸俗化的嫌疑,我们亦不必过于苛责。因为,蔡元培的美育与《肄业要览》的“闲时玩物适情之举”并没有本质不同,仍是救国存亡大计中之一部分。无论是蔡元培,还是在接下来二十余年里被延揽至其美育计划之内的各种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恐怕都从不曾构想过一种与进化论断绝联系的艺术教育体系。在1917年所作《以美育代宗教说》中,蔡元培的论证基本上是置于康德哲学框架的“天演论”:
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知识;二曰意志;三曰感情。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而有之。……天演之例,由浑而昼。……知识、意志两作用,既皆脱离宗教以外,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然而美术之进化史,实亦有脱离宗教之趋势。……于是以美育论,已有与宗教分合之两派。以此两派相较,美育之附丽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18)
当蔡元培滔滔雄辩地说明美育代宗教之合理性的时候,其心目中论敌乃是推崇孔教的康有为。但蔡氏并不知道,早在十多年前,康氏已根据社会循序渐进的理论构想了一个边境和社会等级彻底消失的大同世界,在那里,从人们尚在母胎直至弱冠,美育俱占有重要地位。康氏几乎是以当年孔子叙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口吻写道:
假有家富能学,父兄为都士,知所教,教学能至弱冠,然其间濡染家庭市井都邑之恶习,费去家事、事病、送死、吉凶、祭祀之闲日,多有贫贱、死丧、困苦、哀伤之感情,而无公家院舍、园囿之精洁广大,无歌乐、图画、书器、雏形之美备,无万千齐驱并进之策励,无学级学类、良师益友之教导观摩,其间相去,何啻天渊?故必行大同之道,而后人人为有用之美才,人人为有德之成人也。(19)
关于这个乌托邦的书可能在1902年已经基本写定,但迟至1935年康有为逝世八年后方得以较完整面貌刊布,此前其对美育的讨论从不曾面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蔡元培的美育说曾经受到其论敌的影响。此种异辙同辕的情形令人相信二者立论时有共享的知识背景。入华的“美术”可能促生各种面目迥异的艺术观,但这无妨其内在必然的亲缘性。
对于最早接受“美术”这一概念的那几代知识分子来说,需要考虑的可能并不是美术是否符合某种很可能是线性发展的进化规律,而是如何把中国艺术从过去到今天到未来的发展脉络安置于一套自西徂东的艺术进化论框架中。
至少,人们很可能会首先探究“进步的”西方文化里最伟大的艺术是何等模样,然后以之观照本土。不言而喻,物色的结果必然是与古典文明和文艺复兴相当的唐宋传统,尤其是“写实”的宋画。最典型的例子是康有为。游历欧洲时,他发现“今欧洲以罗马为正统”,“罗马画为全欧第一,凡欧人学画有名者,必来罗马学焉”。在罗马,有代表着进步方向的拉斐尔:
基多利腻、拉飞尔,与明之文征明、董其昌同时,皆为变画大家。但基、拉则变为油画,加以精深华妙;文、董则变为意笔,以清微淡远胜,而宋、元写真之画反失。彼则求真,我求不真;以此相反,而我遂退化。……以画论,在四五百年前,吾中国几占第一位矣,惜后不长进耳!(20)
可以说,正是1904年面对拉斐尔艺术时,康有为才确立了1917年时“中国之画……至宋而后变化至极”、“宋人画为十五纪前大地万国之最”的观点(21)。既然中国绘画史中只有宋画和部分延续宋画趣味的元画最接近文艺复兴的审美标准,那么自宋以降的中国绘画便必然是一个衰落过程:
试问近数百年画人名家,能作此画不?以举中国画人数百年不能作此画,而惟模山范水、梅兰竹菊萧条之数笔,则大号曰名家,以此而与欧美画人竞,不有如持抬枪以与五十三生的之大炮战乎?盖中国画学之衰,至今为极矣!则不能不追源作俑,以归罪于元四家也。……吾于四家……但以为逸品,不夺唐宋之正宗云尔。惟国人陷溺甚深,则不得不大呼以救正之。(22)
以枪炮高下喻绘画优劣的修辞充满启发意味。这绝非美术本体内的讨论,而是牵涉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之宏图的进化论美学。在康有为看来,衰落的中国艺术就像衰落的中国一样,必须通过变革寻求进步。他写道:“士气故可贵,而以院体为画正法,庶救五百年来偏谬之画论,而中国之画可医而有进取也。”“若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23)。
康有为提出拯救中国画的要求尚不足两月,吕澂和陈独秀在《新青年》举起著名的“美术革命”大旗。观吕、陈二文,其心目中“进步的”中国美术基本是接近西方古典的唐宋传统。尤其是陈独秀,论调与保皇党康有为如出一辙:“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24)毋庸明言,陈独秀的美术观与其对“德先生”、“赛先生”的推举密不可分,而这使他与国粹主义者势同水火。但除了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精神发展的产物,这两位“洋先生”还能是什么?这种理性精神体现于艺术,难道在东不是宋画传统、在西不是古典文明吗?就像康有为那样,陈独秀已经陷进西方文明的圈套。
陈独秀拥护的赛先生,其实康有为素来重视。在1904年所作《物质救国论》中,他认为“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其所谓物质,实即列强兴盛所由之工业文明,与科学精神相联系。从明治日本那边借来的“美术”这种学问,当然不容置疑地从属于物质学(25)。从此出发,写实艺术得到推崇自是毫不稀奇。在陈独秀按赛先生要求提出“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以前,康有为早就撰写了《画学、乐学、雕刻宜学于意》,其论有云:
绘画之学,为各学之本,中国人视为无用,亦知一切工商之品、文明之具,皆赖画以发明之。……若画不精,则工品拙劣,难于销流,而理财无从治矣,文明之具亦立国所同竞,而不可以质野立于新世互争之时者也,故画学不可不致精也。(26)
而在陈独秀号召“美术革命”的那一年,康有为的弟子、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的徐悲鸿发表了著名论文《美与艺》和《中国画改良之方法》,力倡写实主义画风。如果再读一下次年蔡元培在北大画法研究会的演讲:
……西人之重视自然科学如此,故美术亦从描写实物入手。……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27)
我们便会发现,与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相比,康有为才是美术革命的真正首倡者与核心人物。
但1898年借先进西学以维新的康有为何尝料到,二十年后,在其学说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将其斥之为旧文化之代表,而立论乃基于更“先进”、更“新”之西学!就在陈独秀号召“美术革命”不久,李大钊在另一卷《新青年》中写道:
最近又在本志上看见独秀先生与南海圣人争论……以新的为本位论,南海圣人及投书某君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前。以旧的为本位论,独秀……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后。……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的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有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这就是新的气力太薄,不能努力创造新生活,以征服旧的过处了。(28)
横的空间接触之紧迫固然是不容置疑的,纵的时间性质之差异却难免是主观人为。在“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背后,隐藏着进化论线性逻辑的激进版本——为了先进的文明,旧有的一切,只要不符合先进的洋标准,就应当统统被摧毁。目睹如洪水猛兽般之新文化运动,倘思当年维新之前因,推及他朝除旧之后果,1918年的康南海能不心寒?此时此境,他在艺术思想上的真正同道者,不是跟他一样支持写实画风的陈独秀,而是提倡艺术陶写性灵的陈衡恪。
尽管以维护传统文人画闻名于近代画坛,陈衡恪并不属于冥顽不灵的保守派。不过,当新文化运动之呼声越来越狂热时,他却冷静地与之保持距离。1920年,他提出:
研究之法,宜以本国之画为主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其法大略如此。例如我国山水画,光线远近,多不若西人之讲求,此处宜采西法以补救之。风景雨景,我国画之特长,宜保守其法,而更加以深心之研究,使臻于极佳境界而后可。他如树法、云法,亦不若西法之真确竟似,故观察方面当更须留意。(29)
固然可算对此前蔡元培“以科学方法入美术”说之响应,但细玩“以本国之画为主体”,曲折可见其文心与时流崇尚之赛先生貌合神离。作为维新派后裔,他愿意接纳代表科学精神的物质学,但作为书香世家出身的传统文人,他一定深刻地察觉到以进步为名之全盘西化的幼稚和危险。因此,在艺术上原本极具革新精神的他转变为传统艺术的维护者,这与政治、文化上维新变法在前、推崇孔教在后的康有为如出一辙。汪荣祖在研究康有为、章太炎时指出,“康、章何尝反对新文化?他俩反对的只是五四式的新文化而已。换言之,他俩在追求新文化的过程中,忽然半途杀出五四这一程咬金,使他们二人不得不弃车保帅耳”(30)。此语完全适用于艺术领域的陈衡恪。
迫使传统文化遭受颠覆危机的,归根到底是自晚清以来不断输入中国的进化论逻辑,对于像陈衡恪这样一些被划入国粹主义阵营的画家来说,如果试图证明传统艺术尚且值得保留,便必须在理论上处理这套当年由李提摩太者流带来之“新学问”——别忘了,“美术”自入华以来一直从属于这种“新学问”。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不久,陈衡恪在《东方杂志》发表《中国人物画之变迁》,文末曰:
现在有人说西洋画是进步的,中国画不是进步的,我却说中国画是进步的。……不过自宋朝至近代,没甚进步可言罢了。然而不能以宋朝到现今几百年间的暂告停顿,便说中国画不是进步的。……安知中国绘画不能于最近的将来又进步起来呢?所以我说中国画是进步的;但眼下的中国画进步与否,尚难为切实的解答罢了。(31)
其论与康有为把中国艺术的黄金时代置于宋代并没有太大区别,但已流露出担心传统文化失声于西方冲击之下的失落感与矛盾心态。此时陈衡恪必在苦苦思索,在“美术革命”之外是否可能存在另一种中国美术的出路,它将符合艺术进化论,同时不至于使作为精英文化的文人传统骤然发生断裂。
1921年,陈衡恪必定找到了新的解决方案。那年秋天,在撰写《文人画之价值》等重要论文后,他在《绘学杂志》发表未完稿《中国画是进步的》。该文可注意处有二:其一,尽管全文中并未提到宋元以来的文人画,但已抛弃“自宋朝至近代,没甚进步可言”的观点;其二,在追溯中国绘画起源时,陈氏特地重申一年前发表的文章《绘画源于实用说》(32)。既然物质学和赛先生是根据功利性标准断定文人画为衰颓、落后,那么,为了把自古至今中国绘画的发展视为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就非常有必要质疑、替换这套标准。声称美术起源于实用艺术,并非像康有为或陈独秀那样强调艺术的实用意义,而是试图指出从实用到非实用乃是进步。在线性逻辑的一端,从实用艺术中脱离出绘画,在另一端,符合物质学与赛先生标准的宋画当然也可进化成文人画。根据《文人画之价值》中的著名定义,这种更“进步的”艺术是物质至上主义的对立面:“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33)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美术”,即1905年王国维所谈到的“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
因此,“美术革命”者出于功利目的倡导的写实主义,在非写实的文人画面前就绝非“进步的”,这成为陈衡恪于1921年所作白话文《文人画的价值》与文言文《文人画之价值》的核心论点。如后一文所说:
文人画之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何以言之?……六朝进于汉魏,隋唐进于六朝,人意之求工,亦自然之趋势。而求工之一转,则必有草草数笔而摄全神者。……宋人工丽,可谓极矣。……而东坡、文与可,极不以形似立论。人心之思想,无不求进;进于实质,而无可回旋,无宁求于空虚,以提揭乎实质之为愈也。(34)
然而,由于在衡量艺术时丝毫不打算舍弃西来之艺术进化论,崇尚文人画之陈衡恪与崇尚宋画之康有为其实相去不远。康有为在“进步的”西方找到与宋画相当的古典艺术,陈衡恪同样在西方艺术史中发现比古典艺术更“进步的”现代艺术,就论证文人画之价值而言,后者将比任何修辞都更具说服力。因此,陈衡恪不失时机地对西方艺术的发展方向进行分析:
西洋画可谓形似极矣!自十九世纪以来,以科学之理研究光色,其于物象体验人微。而近来之后印象派,乃反其道而行之,不重客体,专任主观。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联翩演出,其思想之转变,亦足见形似之不是尽艺术之长,而不能不别有所求矣。(35)
于是,他成功说明,那种符合物质学和赛先生之标准的图写真实之画风,无论于东于西,都处于艺术进化历程中的过渡阶段,其后还有更“进步的”、“不求形似”的艺术。
由是观之,同样是通过东西方艺术之比较,康有为标举“十五纪前大地万国之最”的伟大宋画,陈衡恪则维护先西方数百年而脱离物质进入性灵的文人艺术。在此在彼,都不能不说源于一种文化政治策略。然而,这是深受本土精英文化熏陶之知识分子在面对异质文明入侵时不得不然之举措,无论其言论存在多少谬误,后人绝无权利吹毛求疵。在康、陈所生活的时代,一种世界美术的格局正以艺术进化论为名逐步形成,没有任何民族有资格宣称自己的“美术”是封闭系统中之独立存在体。康有为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登陆前不久(1903),日本学者冈仓天心《东方的理想》在伦敦出版,首次告诉西方人,中国人认为“在关于图绘艺术的六法中,描绘自然的理想退居第三位”(36)。陈衡恪成为中国画学研究会重要成员的那一年(1920),罗杰·弗莱的论文集《视觉与设计》面世,该书通过大量对非西方艺术的评论促使西方古典霸权之解体与各种前卫艺术之兴起。1926年,即康有为辞世一年前、陈衡恪病逝三年后,黄宾虹筹备的《艺观》画刊在上海发刊,第一集载美国收藏家、画家白鲁斯《纽约中华古画展览宣言》,其文颇可借为本文结语:
19世纪之后半期,西方之物质与科学进化,既已在本土得胜,渐伸其势力于全地球,最后乃及于远东。因此,机械上、智识上之发明与产物之刺激,即西方之所谓进步,中国乃不得已而开放其门户矣。……美术乃人类进化之反照,易言之,美术实人类进化之明镜也。……中国富于美术及哲学思想,足以自成一派,其在未来效用,盖可断言也。欧美经东方及已国先哲之影响,盖已在美术及精神上得有觉悟矣。……研究中国之美术,可以使吾辈得生命之新观察与理会,盖可断言。(37)
注释:
①《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5页。
②(21)(22)(23)康有为:《万木草堂所藏中国画目》,《康有为全集》第十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1页,第442—443页,第446页,第441、451页。
③(33)(34)(35)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李运亨等编《陈师曾画论》,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167页,第167页,第171页,第171页。
④大村西崖:《文人画之复兴》,陈衡恪译,见《陈师曾画论》,第192页。
⑤1880年私费游历日本的士人沪商李筱圃,1887年奉召外出日本考察的大清官员傅云龙,均曾在日记留下关于“美术”的记载。
⑥参见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点校说明,李提摩太、蔡尔康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⑦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1—214页。
⑧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103—104页。
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五,《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168—169页。
⑩康有为:《官制议》卷一一,《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312页。
(11)佛雏:《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6页。
(12)邵宏:《衍义的“气韵”:中国画论的观念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3)《王国维遗书》册五,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100—101页。
(14)参见林晓照《晚清“美术”概念的早期输入》,载《学术研究》2009年第12期。
(15)蔡元培:《学堂教科论》,《蔡元培全集》卷一,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4—336页。
(16)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卷二,第13—14页。
(17)蔡元培:《我之欧战观》,《蔡元培全集》卷三,第4页。
(18)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元培全集》卷三,第58—60页。
(19)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108—109页。
(20)康有为:《意大利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366、376—378页。
(24)陈独秀:《美术革命——答吕澂》,载《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
(25)(26)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79—80页,第93—94页。
(27)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第二次始业式演说词》,《蔡元培全集》卷三,第417—418页。
(28)李大钊:《新的!旧的!》,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15日。
(29)陈师曾:《对于普通教授图画科意见》,《陈师曾画论》,第148页。
(30)汪荣祖:《康章合论》,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2页。
(31)陈师曾:《中国人物画之变迁》,《陈师曾画论》,第159页。
(32)陈师曾:《中国画是进步的》,《陈师曾画论》,第178页。
(36)Okakura-Kakuzo,Ideals of the East,New York:E.P.Dutton and Company,1905,p.52.
(37)洪再新:《从罗振玉到黄宾虹》,见范景中、曹意强编《美术史与观念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8—2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