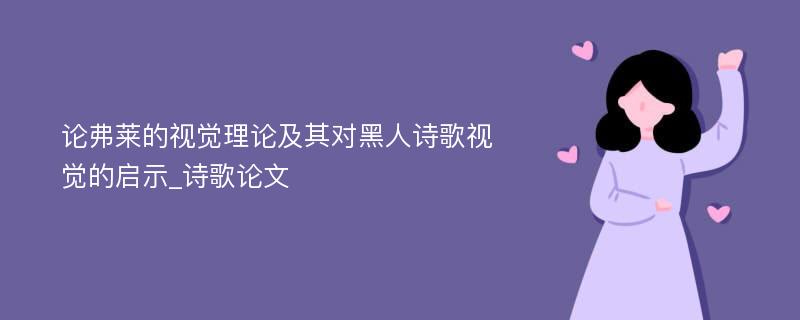
论弗莱的视像理论与布莱克诗歌视像之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像论文,布莱克论文,诗歌论文,启示论文,弗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核心是想象,而神话想象中的视像(vision)则是其想象理论的核心。弗莱批评理论中的想象与视像问题源自他对威廉·布莱克的研究。弗莱的第一部著作——《可怕的对称》研究的是布莱克的诗歌,奠定了其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基础。 布莱克是一个被批评界从多角度阐释的诗人。他被作为视像诗人、神话诗人、神秘诗人,同时他还有魔鬼诗人的称号。学者曾从以下角度研究布莱克:布莱克与神秘主义,布莱克与浪漫主义,布莱克与象征主义,布莱克与现代主义,布莱克与《圣经》元素等;布莱克与科学的关系,与牛顿的关系,与哲学的关系,与洛克的关系,与宗教的关系,与埃及文化的关系,甚至与印度文化的关系;还有布莱克与艺术的关系,与心理学的关系,与精神分析的关系,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等,从此可以看出布莱克的复杂性。作为一位视像诗人,比利海默(Rachel V.Billigheimer)认为,他上被联系到之前的《圣经》,下被联系到之后的W.B.叶芝等。拉里西(Edward Larrissy)的《布莱克与现代文学》(Blake and Modern Literature)一书的导论用的标题“布莱克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也表明布莱克意义的广泛性。该书第二章以“在神话与心灵方面比较布莱克与叶芝”为题,第三章标题是“在布莱克与叶芝之间的艾略特”,第四章则是“布莱克与叶芝、奥登与狄兰·托马斯中的相反的同一”,第五章是“布莱克与乔伊斯”。当然,将布莱克置于浪漫主义中的研究更是常见,布鲁姆所编的《视像指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导读》一书所列的视像诗人,第一章就是“威廉·布莱克”。 布莱克被认为没有人影响了他,他也没有影响任何人,这是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的。实际上,布莱克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文学创作上,他影响了叶芝、狄兰·托马斯、艾略特、乔伊斯等神话作家,而理论上,毫无疑问,他成就了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而布莱克的这两种影响都与其想象,特别是与其诗歌中的神话视像有关。 视像是西方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论题。西方很多研究者都涉及对“视像”的研究,如亚当斯(Hazard Adams)的《布莱克与叶芝:相反的视像》(Blake and Yeats:The Contrary Vision)和哈罗德·布鲁姆《视像指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读本》等。布鲁姆专用一章分析了布莱克诗歌中的个体视像(The Individual Vision),描绘了布莱克诗歌中的比尤拉(Beulah)等神话王国或自然的阶段的视像。他比较了布莱克诗歌中的四个王国中的比尤拉与伊甸园,比尤拉是女性化的、静态的,不同于伊甸园,后者是能量的;比尤拉是春,伊甸园是秋;在视觉上,伊甸是火焰而比尤拉是一朵花。(Bloom 24—26)此外,“巨人形式”的视像是布莱克神话诗歌中突出的个体视像。布鲁姆同时还解读了其他浪漫主义诗人,如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等的诗作,他认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存在普罗米修斯的视像,具体存在于布莱克的《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华兹华斯的《序曲》与雪莱的《解放的普罗米修斯》等作品中。布莱克生活的时期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为暴政与黑暗的时期,诗歌因此走向内部的想象性。布鲁姆谈到布莱克诗歌的视像时说:“浪漫主义断言不只是一种断言,它本身就是一种玄学体系,一种历史理论,比其中任何一种更重要得多,它是所有浪漫主义——特别是布莱克——所称的一种视像,一种看的方式,存在的方式,更人性的生活。”(Harold Bloom xxiii — xxiv)可见,“视像”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重要传统视域之一。 布莱克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视像诗人;西方形成了对浪漫主义诗歌的视像研究。布鲁姆就是对浪漫主义诗歌的视像颇有影响的研究者,而弗莱则是将诗歌中的视像理论化的理论家。 所谓视像,也就是强调能看见,使之能看见,它与神话相连。布莱克诗歌的视像是神话视像或仿神话视像,布莱克被称为神话诗人与视像诗人。《圣经》的创世纪中有“光”与“声音”的意象,上帝使所有事物可见与不可见,后来的整个有秩序也就分为可见与不可见的。如用布莱克的视像化,文学就是要使不可见的变成可见。上帝就是不可见的,如同空气不可见,但你知道它存在。在弗莱的想象论的原型批评理论体系中,视像不是一种实在的形象,而是一种象征的隐喻关联,它生成可视性、可感性、可听性,具有神话与口头文学全面感官的原型性。 视像虽然具有形象性,但它不能等同于人物形象,它往往是一种形象在作家、读者或观众的主观关联外部的一种呈现。它可以是不同的事物、概念、故事、形象,它具有高于作品中的形象、高于具象的超越性。它还可以是历史的呈像、哲学的呈像,或事物与故事的呈像。视像具有很强的呈现力,其呈像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文学想象或文化想象的过程。 视像最能激发人的想象力,因而成为弗莱想象理论中的重要范畴。弗莱在其第一部研究布莱克的著作《可怕的对称》中,提到了“想象创造了现实”,他还指出“欲望是想象的部分”(27),也有“视像的想象”(visionary imagination)的提法。弗莱注意到原初视像,也就是神话中的视像,具有强大的投射功能,因为它们代表的各类原初关怀或基本的人性关怀会不断投射到人类的想象中,神话视像也就一直在被呈现而始终活在当下。 弗莱认为神话具有视像性,文学具有视像性,文化具有视像性,甚至各种学说与理论同样也具有视像性,而文学则直接继承了神话的视像性,文学想象中包含了神话的原型视像。 在弗莱的理论中,视像与《圣经》神话有联系,比如说伊甸园是视像化的,它是宇宙空间的第二个空间层次。而现实的自然世界作为第三级空间层次,也像地图一样覆盖了整个自然现实的生活,成为自然现实世界的摹本。而文学与文化所建构的想象世界和理想世界中包含有伊甸园的摹本,它转化成为城市花园意象。弗莱的视像多少接近于鲍德里亚的拟像,有时转化为城市花园出现。而弗莱的自然现实世界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模拟,但它又是图示化的,是非真实的。弗莱的理论不直接指向实在的现实,但指向的是自然的现实对高级的、人类堕落前的伊甸园自然世界的模仿。 伊甸园等神话视像是图画般的、有细节的、全面的、可视的,这是文学所要真正表现的。《圣经》神话的四个层次的宇宙空间视像,一直是后世西方文学的想象的摹本,隐含于后世的文学中。文学的视像性越强越被认为是好的文学。在弗莱看来,实在的社会现实低于上帝创造的那个人类自然的世界。或者说,神话中想象的伊甸园,即亚当、夏娃堕落前的自然层面,优于堕落之后的自然现实层面。而当今的现实生活,也只是亚当堕落后的自然现实的一种新的图示化。因此,人类堕落后进入的自然现实层面始终带有对伊甸园,这一人类堕落之前的高级的自然层面的模仿或戏仿。这就是弗莱的文学批评,不直接建立在现实层面上,而建立在《圣经》神话之上的立足点。而且对神话视像的模仿与戏仿的不同带来不同的叙述文类,传奇、浪漫主义都属于高模仿,它们是对神圣的模仿,被视为世俗经典;而对堕落后的自然现实或现实世界的模仿则是低模仿,也就是现实主义,它与反讽相连,包含了对神圣的反讽、戏仿,呈现的便是魔怪世界。这种魔怪世界的范围与表现形式极为丰富,比如,同性恋就被认为是对神圣的或正常的性恋的戏仿,而妓女是对婚姻关系的戏仿,它属于对神圣婚姻的反讽,因而属于魔怪世界。 弗莱的理论构设与神话宇宙空间的想象关联,它与历史进程或现代进步的历史意识对立,其视像建立在《圣经》宇宙空间之上。但丁、T.S.艾略特、W.B.叶芝与乔伊斯的作品中,都有宇宙之轴或神话宇宙空间的意象。虽然在当今的科学观中,垂直的宇宙观已经过时,但这种想象空间依然为文学所表现,就如同日落日出作为想象与景观,施加影响于诗人一样。弗莱的理论视像带有神话视像的特性,神话视像被定位为高于现实,就如同鲍德里亚的拟像,是一种“超真实”一样。也就是如同博尔赫斯的皇帝的故事中,皇帝详细的地图成为帝国本身的摹本,而使地图优先于领土,也就是“超真实”优先于真实。这是因为真实的实在没有起源,而伊甸园以及亚当走出伊甸园,进入自然现实的层次,都带有起源的印记,因此,神话视像高于现实。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建立在神话是超真实性的原型与范型的逻辑之上的。神话中的原型视像版图在文学想象中永远优先于现实的真实生活,它是一种高级的摹本,框定了文学的想象,高于现实实在。因此,文学模仿的对象,就不只有现实主义强调的模仿现实,弗莱强调的文学是模仿神话的想象空间与伊甸园等神话视像。在文学系统中,则体现为文学模仿文学。如果套用鲍德里亚的话,在弗莱看来,神话也是比实在更权威的一种超实在,是现实世界中人们建构文学、文化、文明的理想过程中试图模仿的一个范本,它融入文学、文化、文明创造的想象的过程中,使神话、文学、文化、文明在想象与创造中连为一体。在想象论与创造论中,现实不是很重要的因素,因为现实是文化与文明建构的现实,没有纯粹自然的现实,而文化与文明的建构必然包含了神话的伊甸园的意象,文化与文明都是对神话摹本的模仿。因此,不带有起源性的现实是次等的。就神话而言,就诸神的形象而言,神所造的世界成为先在与被模拟的世界,它框定了后来西方文学与文化中的想象与创造。而文学是对神话,包括神话视像的模仿,不是对现实的模仿,这种模仿包括象征、意象等结构。因此,与视像相连的想象,而不是现实,在弗莱的理论中成为前景问题。而在现实主义文论中,现实是前景问题。这体现了弗莱理论与现实主义文论的某种对立。 弗莱指出,在批评家那里,“《圣经》不仅是文件、文献资源,而且是故事的视像资源”(Double Vision:3)。弗莱研究了布莱克诗歌的神话想象,并将之作为整个诗歌创作的原则。弗莱的视像话题与布莱克诗歌中的视像是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文论中的“视像”概念也通常与布莱克联系在一起,布莱克被誉为视像诗人。 布莱克的诗歌中存在着大量神话启示视像,包括“辩证”的视像、“循环”的视像、“心灵”的视像、“身体”的视像、“个体”的视像等等,是一个神话视像的资源库。 布莱克1789年出版了诗与画的合集《天真之歌》,写天真的、为神灵充溢的欢愉状态的人们;而1794年出版的《经验之歌》,写现实经验处境中的人们。后来合成一个集子《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副标题为“人类灵魂的两种对立状态”,包含有辩证意象。布莱克的诗歌中的神话是希伯来预言传统而非希腊传统,自成神话体系,其中存在伊甸园、比尤拉、生生世和乌尔罗(Eden、Beulah、Generation and Ulro)四个想象性的层次,也是四个王国,也代表自然的四个阶段。布莱克的循环体现为四者关联,最终的愿望是重返伊甸(不同于《圣经》的伊甸园)。这种循环被描述为“奥克(Orc)循环圈”。Orc被认为有“恶魔”之意,也有Cor(心灵)的字母重组。 《天真与经验之歌》和《地狱与天堂的婚姻》等诗歌题目就体现了布莱克的辩证视像。布莱克的“天真之歌”所写的“天真”状态,是神灵同在的视像化。人受到上帝的保护,是孩子气的未完全成人化的天真视像,也是福音书上看到世界在天真的状态的光中的视像化。它与经验世界、与人类现实世界是对立的。但天真又必须进入经验,就像儿童必须进入成人,辩证对立一定会进入阶段循环之中。 在《威廉·布莱克的诗与设计》一文中,弗莱认为,《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直接根植于象征书的体系中,它们是英语文学中迄今为止最好的象征书。(Black:121)“诗歌的单位是意象而不是观念,因此一首诗的整体意义是一个整体的意象,一个单一的视像化的画面。”(Black:125) 弗莱吸取布莱克诗中对立相反的因素彼此作用与连接的辩证意象,并指出其中语境化的复杂性,这应该也是弗莱在《双重视像》中指出的“视像真正拥有他所宣称拥有的强力”(19)之一种体现。他说:“大多数布莱克的最著名的抒情诗是对他所称的天真或对他所称的经验的表达,并存在两个相反的心灵状态的时候,人们应该知道任何既定的诗中所呈现的是这些矛盾的哪一种。”(Black:2)如布莱克的“《弥尔顿》中对人类的摈弃与救赎,被称为相反”(Black:31)。也就是说,一种视角中的上帝是慈爱的、怜悯的;另一种视角则视上帝为任性的、非理性的、残暴的。同理,上帝是爱世人的,也有憎恨人类的。在弗莱编的《布莱克:批评论文集》中,“小女孩的迷失;浪漫主义原型问题”("Little Girl's Lost:Problems of a Romantic Archetype")与“布莱克的向日葵的复杂:一种原型的思考”("The Complexities of Blake's Sunflower:An Archetypal Speculation")等论文都是讨论布莱克诗歌中的原型视像或原型意象的。前者认为布莱克处于“视像文学的传统中”(Black 68),后者探讨了向日葵的意象的隐喻。(Black 56—64)弗莱在该书的导论中也指出,布莱克的抒情诗是处在“从基督教与古典资源中选用大量神话与寓言材料的象征书的传统之中”。(Black 3)而这种视像化正是布莱克与《圣经》作为象征书的传统,《圣经》中的视像也是与基督教史诗中的传统一致的,即“现实的视像分离进入到天堂与地狱的永恒的构成中”。(Poetry and Design 126)在布莱克的诗中存在将现实天堂化与地狱化的同时存在,因而也构成相反的、两极化的辩证意象。还有著名的“羊羔”与“老虎”(The Lamb and the Tiger)。布莱克的诗的含义远比这种对立丰富,老虎明亮的眼睛与黑暗的丛林的对照,已经不是简单的对立。布鲁姆认为,在《老虎》中,看到可怕对称的人,可能也看到上帝的爱作为光出现,上帝的愤怒作为火出现,也可以说上帝既造了老虎也造了羔羊,从而实现了同一。(36) 布莱克的辩证视像,来源于《圣经》。在《圣经》“创世纪”中存在着“生命之水与死亡之水的对照,这是《圣经》意象中最重要的对照之一”。(Frye & Macpherson 35)弗莱将《圣经》中大量相反或对照的意象与现象归类为两个种类,而且它们又不是固定的,呈现出与语境的联系。弗莱说,“我讲到《圣经》的想象结构,想象倾向于分裂为两个相反的种类:一个是启示的或理想的,与伊甸园应许之地耶路撒冷、与耶稣相联系,与耶稣的精神国度在一起;另一个我称之为魔怪的,它与暴政的异教王国,与埃及、巴比伦联系在一起,在《新约》中,与罗马联系在一起。”(Frye & Macpherson 41) 弗莱列举了《圣经》中有四条河流,有生命之水,它们中戏仿魔怪意象的则是尼罗河。最明显的戏剧化的死水的意象是死海,红海是死海的意象。可见,水本身就有两种辩证对立的意象:生命之水与死亡之水。“海有死亡的一层象征与重生的一层象征。依赖于从埃及人还是从以色列人的视点来看它。”(Frye & Macpherson 46) 视像也随语境而转换。弗莱说,“是否一个意象属于一个种类或另一个种类,完全依赖于语境,而这个语境不难决定。”(Frye & Macpherson 41)在《圣经》中没有意象必须总是魔怪的或总是理想的。在其他神话与宗教世界中,蛇总是智慧的真正象征。可见,理想的或魔怪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弗莱针对这种转换与对照,提出“戏仿式对照”的概括,将魔怪世界纳入进来。弗莱指出天堂有绿洲:生命之树与生命之水两个意象,而这些天堂意象也有它们的魔怪的对立面:异教王国(heathen kingdom),形成了我们称为戏仿魔怪的想象种类。(Frye & Macpherson 42) 布莱克诗歌的辩证视像与循环视像是连为一体的。布莱克的辩证不同于黑格尔式的强调否定对方。《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的副标题虽然为“人类灵魂的两种对立状态”,但两者具有递进关系。布鲁姆认为布莱克的题旨在于,“没有两种状态的同时存在,人类的存在将停止。两种状态是对立的,因为它们不能在一种人类存在的有限范围内和谐,但它们是同时的。现实证明,不仅是一种否定另一种的关系,而且是它们显露出如同存在本身的多样性一样的彼此的相互作用。”(33)在布莱克的诗歌中,天真是布莱克所称的比尤拉,经验是严厉而又充满活力的生生世(Generation),代表天真的比尤拉要循环行进到代表经验的生生世,也就是,天真是要进入到经验状态的,而经验要到乌尔罗,再回到伊甸,回到天真。布鲁姆认为在“天真”与“经验”之间存在这样双重的反讽。这种循环移动是自然发展的,也是想象的。(33) 布莱克诗歌中循环的最高点是伊甸,但它不是《圣经》中的伊甸,而是指艺术家创造的他所称的伊甸,而最低点则是乌尔罗或唯我的自我反映。布莱克的“经验暴露出天真的不稳定的非现实性;而天真则谴责经验现实的表里不一”(Bloom 34)。这就是天真与经验的对立,但天真又必然循环到经验,这就是相互作用的辩证视像,它以比尤拉形式进入生生世的视像性表达。《耶路撒冷》的结尾宣称“地狱对天堂开放”,也表达了两种对立视像的辩证关联性。 布莱克对历史循环的视像有一个比喻的说明。他用橡树和橡果的关系说明部分与整体的循环视像。历史的橡果可以看做是人类的原初的橡树,也可以理解为从原初的橡树落下又返回橡树,这便是布莱克的历史循环的视像,即结合与分裂是同一个存在的交互方面。布莱克的循环意象建立在伊甸园、比尤拉、生生世、与乌尔罗四个王国中。布莱克注重它们之间的关联与斗争,其轨迹是核心意象“奥克循环”,它包含“童年、成年、老年”的循环意象,还包括女性、男性的性别关系以及肉体与心灵的合一等。在四个王国中,生命采取循环的形式,从堕落的世界出发,又返回到堕落的世界;理想最终是返回伊甸园,循环到理想。 此外,布莱克诗歌中存在身体精神合一以及男人女人合一等神话视像。布鲁姆指出:“布莱克既不是自然主义者,也不是超自然主义者,他拒绝接受既定的人类身体作为现实。对于布莱克,心灵是真正的或没有堕落的身体”(32)。布莱克重视的是心灵与身体的结合,“奥克”(Orc)是没有具体的身体。身体与精神的结合的布莱克式的神话视像,对弗莱的神话的“首要关怀”,这一根植于生命本体的神话关怀的关怀理论是有启示的。 生命来自女性的身体,因而就有大地母亲的意象。弗莱在所编的关于布莱克的论文集中指出,“大地自然的身体是所有生命的子宫与坟墓。生命的母亲是与死亡回归的母亲”。(Black:138)在《批评的解剖》中弗莱也用到“子宫”一词。而性的意象:新娘与新郎的意象,在《圣经》神话中与男人、女人的实际关系无关。它是宗教信仰的隐喻。基督是新郎,而新娘是信基督的人。它意味着基督象征性地是唯一的男性,唯一的个体,唯一能说“我是”的人。这体现的是隐喻思维。《圣经》是一个隐喻的文本,所有关系是隐喻的关系。弗莱说:“《圣经》依靠隐喻的同一。隐喻在《圣经》中不是语言的装饰,它是思想控制的模式,隐喻是一个语法的阅读。这是‘那’的宣称,而两个事物是非逻辑的,或进一步说是反逻辑的。”(Black:31)布莱克的《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也体现了对《圣经》的隐喻。性别只是一种隐喻,是将神圣肉体化或视像化的一种途径。布莱克说:“一个城市,也是一个妇女”,这指的是指耶路撒冷。所以,女性不是性别意义上的女性,它“包括了大地。基督的新娘,也包括了男人,甚至也喻指对教会的惯例象征”。(Black:30)《圣经》中的三位一体,三是一,一是三。身体与血、面包与酒是同一的,都指耶稣的身体。这些都是一种隐喻思维。弗莱将《圣经》整体化,建立在两个结构因素上,其一是叙述,其二是意象结构,其中包括视像。 弗莱说:“性爱使我们中大多数人进入想象世界之门”。(Fearful Symmetry:78)在伊甸,没有女性上帝,但上帝与人的隐喻关系,也采取了新郎与新娘的隐喻。天堂与地狱的婚姻是隐喻,也是视像。布莱克是视像的建构者,但其热衷插入宗教比喻并进入自动想象的自由中,这对自动的想象有损害。 布莱克的诗歌中存在个体的视像,在神话中是巨人个体。在《耶路撒冷》中,“Erin是神话制造的精灵与个体视像”(Bloom 116),而且每一个Albion,每一个视像的个体组成,被强化进了“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的自然之中。对世界的每一沙砾、每一花朵的个别性的强调本身就是对人的特殊性的意象建构的强调。 布莱克的个体视像定下了浪漫主义想象的神话框架,而且也开启了浪漫主义对个体的强调与尊重,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现代意识。浪漫主义思潮所表达的是,社会的进展只有通过个体化自身实现。因此,要允许个体找到自己同一他的领域范围,因而个体也就拒绝接受社会惯例;相应地,浪漫主义文学也表现出最大的反叛性。在布莱克诗歌中,关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描写都体现出反叛的革命视像。个体被作为巨人的个体对待。普罗米修斯在雪莱诗歌中的重现就是这种浪漫主义类型的个体化的体现。布莱克除了写有诗歌《法国大革命》,其反叛还表现在其诗歌中的主要的天真视像被驱使到潜意识的下面,成为一种颠覆性的革命力量,布莱克以奥克(Orc)形象来表现它。 布莱克的诗歌中也有社会视像。厄德曼(David V.Erdman)的《布莱克的奴隶视像》一文(Blake:88—103)体现了一种类型的视像,因而也就是社会视像。而厄德曼的《阿尔比女儿的视像》一文则写了布莱克对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的向往,描写了“朝向美国”的愿望。布莱克蚀刻的诗中也有处女奴隶和儿童奴隶的形象:“在太阳下的奴隶的声音,用钱买的儿童等,表现欧洲被它的黑人姐妹支撑,前者戴着珍珠链,后者则戴着奴隶的镯子”。(Blake:92)而弗莱则在同一论文集中他本人所写的《威廉·布莱克的诗歌与设计》一文中指出“布莱克的政治热情是无政府主义的与革命的”。(Blake:119)维尼弗莱德·邓博(Winnifred Dumbaugh)的《威廉·布莱克的美国视像》一书指出:“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布莱克走进了伦敦的街道,头戴自由的帽子,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男孩’,而他最强有力的话是《法国革命》”。(120)丹尼斯·索拉特(Denis Saurat)在《布莱克与弥尔顿》一书中比较了两位诗人的革命性,认为“两者都有对现实的需要,弥尔顿的理智驱使他进入政治,朝着实践的现实与其他人一起努力,而布莱克的欲望将他推向神秘主义,朝向视像的现实,分离于他的同时代人”。(75) 关于布莱克的一部有影响的专著是费舍尔的《视像的山谷》(The Valley of Vision:Blake as Prophet and Revolutionary),作者认为“作为革命者与预言者,布莱克分离于他的同时代人,但同时,他的预言的源泉不是理性主义的理论,而是先知的视像,他与感知和沉思的联系多于与概念、判断的联系”。(4)费舍尔指出:“布莱克拒斥希腊人,而自认为是希伯来预言家的继承人,他明显地从他的同时代人与他们的欲求那里迈出了一大步。他的同时代人欲求按照理智与依赖于教条所揭示的或经验调查的自然系统来理解人、社会与世界。”(4)这就是布莱克分离于当时欧洲出现的科学的自然与理性思潮,他对世界的认识对立于当时的牛顿、洛克等的自然科学与哲学理念。 布莱克接受的是希伯来传统,而不是希腊传统。但在希腊传统中,无论如何,“柏拉图是希腊智慧的最高教授”。(Fisher 48)而西方学者认为,“柏拉图的目的也是布莱克的目的,即永恒存在的视像,但两者的路径不同。前者贬低想象,而后者强调想象的路径”(Fisher 48)。希腊哲学强调本质推理,它们在逻辑推理的追求中遗失了自然世界。柏拉图拒斥荷马,诉求道德和理性,这是布莱克的感知立场所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布莱克也对立于牛顿与培根,后者抽象化地进入自然力量的描绘。”(Fisher 15)当然,布莱克更不同于下一个时代的实证主义与后来的经济决定论等理性范式。“对于理性主义者,他的封闭系统要求看待生活整体的观点,对立面之一总是拥有否定的品质,它们中之一必须是假的。而主观化通过建构一个学说系统使一切对立面无效。”(Fisher 6)“传统的形式逻辑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中,对立面被按照肯定与否定的语汇表达——论题与反论题”。(Fisher 6)而对于布莱克,他认识的世界是非逻辑的,是想象的。布莱克强调“真正的观念是以视像的形式存在”。(Fisher 15)布莱克的预言的源泉不是理性主义,不是经验,而是感知与视像。他认为个体认识他的存在不是靠经验、理智,也不是被动接受他的自然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靠一个对立面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但这种对立面不是黑格尔式的肯定与否定的对立面,他对抗于黑格尔的概念导向的否定。布莱克的对立面包括三个阶段,是布莱克的“视像辩证法”(Fisher 7)。三个阶段的视像即“拣选、救赎、责罚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历史运动所组成,对应于想象、情感与多数人面对新的、不寻常的与不可预料的时候所运用的那种理智,任何两种的相互作用将第三种置于对立的位置,或是中立的,或是转换的力量。通过辩证斗争,人可以上升或堕落,但没有它就停止了存在。”(Fisher 7)而“三种之间的相互作用则产生了历史的运动”。(Fisher 7)而这其中“上帝的礼物是人类通过他的艺术创造的能力”。(Fisher 7)布莱克将艺术的创造力与上帝、与神圣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布莱克的“视像辩证法”是开放的,其核心是创造,其辩证不会导向黑格尔式否定的、单一的结果。布莱克三个阶段也是个体生活的三个方面,救赎与拣选之间存在矛盾,以责罚的视像带入第三方面,而责罚与救赎又构成视像辩证法的两个对立面,它们之间又带入第三个透视的方面,即拣选——一种理性的否定。没有矛盾就没有过程,也就没有人类的进程,进程中则包含有创造。 弗莱也看到了布莱克诗歌中的辩证的视像与循环的视像的关系,并将布莱克的循环视像与整个艺术结合起来,认为循环视像是整个艺术的视像。在《可怕的对称》中,弗莱指出:“艺术的最完整的形式是一种循环视像,就如同《圣经》,看到的是堕落与拯救两极之间的世界。”(113—114)因为辩证意象一定会进入阶段循环,而循环构成重复,而弗莱视循环的重复视像为艺术的整体。“诗人的想象通过制造具体与可见的暗含的创造的力量,重复了肉身化。布莱克的《弥尔顿》的开头,说到自己的神经是作为伊甸园的一部分,他的艺术试图意识在当下这个世界中。”(Blake:26) 弗莱同样也将布莱克的这种循环扩展到整个文学中,建构了文学叙述模式的循环的文学史体系;同时也将之扩展到文化中,因而,循环就有了变体,也有复杂的情形。如《圣经》中,游牧阶段、农业阶段、城市阶段各个阶段都有丰富的视像,游牧阶段羊羔是理想的动物的启示,而农耕阶段,以牛作牺牲,是对羊羔作牺牲的变异重复。 布莱克的视像还展现了一般化的对称的倾向,生活形式的艺术,像哥特式建筑,保持了对称的适当附属。这也形成了布莱克对弗莱的艺术是一种设计的对称的诗学思想的启示。弗莱研究布莱克的《可怕的对称》,指向的是艺术想象与构思。自然需要转换,转换成文明世界,想象、构思与设计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弗莱从布莱克的视像推演出了其理论的神话关联思维,它不同于理性逻辑的论证性,不强调对立,而强调关联与同一。布莱克在《耶路撒冷》中的诗句表达了关联并存的思想,即否定不是对立,对立是共同存在。布莱克在这种对立的共同存在的辩证运动中,植入了创造的核心理念。艺术的创造,人类的创造,不是寻求矛盾对立的否定,而是寻求同一的关联。预言家的任务就是将自己同一于灵感与神圣的上帝言辞的视像。世界最初诞生是上帝以视像的形式创造的,世界的呈现也是一种视像的呈现,文学艺术对世界的呈现也是同一于上帝“神圣语词”的视像呈现。这说明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本质,形象带有人的规定性,而视像则体现的是与上帝相连的一种宇宙论。布莱克在《法国革命》中将历史作为一种视像来看,文学艺术不止是对人的形象描写,更是对世界的视像描绘,艺术是世界的视像化。这种视像化是诗人的想象。视像与想象是布莱克诗歌的核心,也是弗莱理论的核心。视像与想象接通于创造。弗莱建构了“创造与再创造”的文学体系,甚至整个文明都运行在“创造与再创造”的轨迹中,文化与文明形成人类与自然分离的封套(envelope)。弗莱说:“日常的世界不是人要居住的世界,人要居住的是要经过创造的世界,城市与花园,但又不是《圣经》中的伊甸园或新耶路撒冷。艺术家试图使世界对其他人是可见的。”(Blake:26)而“诗与预言是上帝语词的声音呼召”(Blake:26)。这样,创造便与视像相连,与语词图景相连,但又不是《圣经》图景本身,也不是回到《圣经》中的伊甸。艺术的创造与视像和现在相连,所谓视像化也包含了肉身化。布莱克诗中,耶路撒冷是一个城市,也是一个妇女。这是视像化,但也可以说,视像化是一种化身的呈现,这也符合弗莱说的“诗歌的单位是意象而不是理念”(Blake:124)。布鲁姆也说过:“眼睛看到的多于心灵所知道的。”(53) 视像与现实的关系中,弗莱是重视视像的,但视像并不与现实完全割裂,两者的联系,弗莱在《可怕的对称》中表达为,“如果现实被证明将是无限的,感知必须也是无限的。视像化因而是认识。”(32—33)所以,视像理论也就包含有弗莱的认识观。这种文学的视像认识完全不同于文学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对现实的认识是通过对文化与文明的认识来实现的。而文学的想象视像根植于宗教,根植于神话,它在文学、文化与文明的建构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