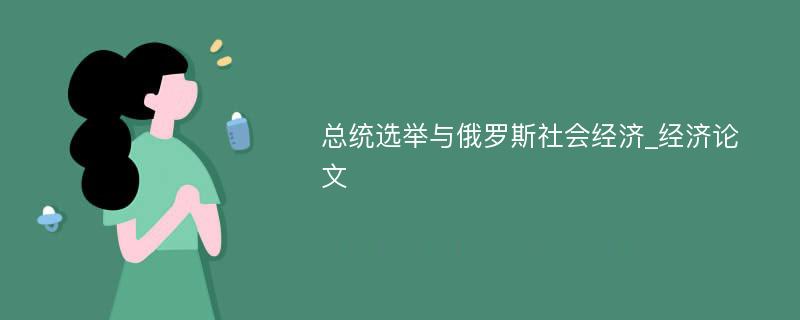
总统选举与俄罗斯社会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社会经济论文,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7月3日,俄罗斯各种政治力量经过激烈的角逐,终于在第二轮投票中选出新一任总统。正如大选前各界预料的那样,在任总统叶利钦战胜强劲对手——共产党人久加诺夫,蝉连俄罗斯联邦总统。这次选举是在一个非同一般的时期进行的,选举结果对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进程将产生很大影响。
其实,就俄罗斯目前的社会经济形势而言,叶利钦并不比对手占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处于不利地位。
1991年12月8日,一纸“别洛韦日协定”宣告了苏联的解体。从1992年1月2日起,俄罗斯开始进行以私有化和放开价格为中心的激进改革,俗称“休克疗法”改革。这场改革彻底改变了俄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取消了原有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实现了向商品货币关系的转变,通过私有化改变了原有的所有制结构,目前俄罗斯国内总产值中的三分之二是由非国有成分生产的。国家已不再垄断生产资料。俄罗斯全国有2.8万多家股份制企业。根据国有资产委员会的资料,到1996年1月1日,有12.2万家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占俄国企业总数的53.3%[①a]。尤其是商业、公共饮食业和服务几乎全部实行了私有化。俄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已经初步形成了以非国有制为主的多种成分经济。
但是这些变化并未活跃俄罗斯的社会经济,恰恰相反,过去的5年是俄罗斯经济大滑波的时期。5年中国内总产值下降近一半。[②a]这个下降幅度远远大于美国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状况,也大于同样处于转轨之中的任何一个东欧国家。经济危机触及到所有生产部门。比如,农业生产在1991—1995年间下降近30%,工业生产下降50%以上,投资下降近70%。1995年经济下滑的势头有所减弱并出现稳定迹象,但是同前几年的大滑坡相比,这种稳定的意义是有水分的。按照俄罗斯有关部门预测,1996年经济有可能在下滑3—4%到增长2—3%之间徘徊。但是第一季度的发展结果表明,生产又下降4%[③a]。整个上半年经济没有摆脱下滑的局面。
对于俄国经济这种大滑坡通常有两种解释,但是均缺乏说服力,比如,有人把俄国经济下滑的原因归结为进行结构改革。克服苏联经济结构不合理性所付出的代价。但是5年来俄罗斯经济结构并未发生积极变化。这一时期采掘工业下降30%,而加工工业则下降50%以上,机器制造业下降60%以上,民用消费品生产下降的幅度更大。还有人把俄国经济下滑的原因归结为克服俄国经济超军事化所付出的代价,不错,近几年俄罗斯军工综合体生产下降三分之二,其中1995年下降21.1%。但是许多生产民用耐用消费品的军工企业,生产下降更严重。仅1995年,军工综合体中军品生产下降16%,而民品生产下降30%以上。[④a]此外,消费品生产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1990年为47%,1994年下降到20%。1990年工业生产总值中轻工业占12.1%,机器制造业、机器加工工业占30.8%,而1995年分别为2.2%和17.7%[①b]。相应地,原料和初加工产品的比重大幅度上升。更重要的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生产大幅度下降。1990—1994年,轻工业生产下降75%。1995年轻工业生产总值只相当于1990年的18%,其中缝纫制品只相当于1990年的9%,皮鞋只相当于12.5%。[②b]因此不得不通过进口大量日用消费品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1994年市场上三分之一以上的商品是进口货。轻纺商品有60—70%依靠进口。食品的市场供应情况亦是如此,全国有50%的食品,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有70%的食品是依靠进口来保证供应。
经济滑坡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90年俄罗斯人均国内总产值8285美元,1994年下降到4230美元。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都受到很大影响。改革开始后首先放开的是消费品价格,而工业部门的工资都还维持前苏联时期的水平。1996年2月,俄罗斯国内价格水平已经达到世界价格水平的63%,但是工业企业的每小时工资报酬只相当于西方国家水平的十五分之一至二十分之一。5年来工薪阶层的购买力下降60%左右。[③b]放开价格后,居民几十年积蓄起来的银行存款一下子变得一文不值,而证券私有化的实施又使大多数人失去了成为切实的所有者的机会。于是社会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1995年12月,10%富裕的居民掌握了近27%的全部货币收入,而10%最贫穷的居民的收入只占有所有居民收入2.5%[④b]。1991年,10%最富裕的居民和10%的最贫穷的居民收入差距是4∶1,1995年他们之间的差距达到13.5∶1,如果加上非法收入,则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达25∶1。[⑤b]
这样一来,俄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们物质生活状况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现政权的不同态度。按照左翼学者阿尔巴托夫的分析,支持现政权的人占总人口的30%。他们均属于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包括(1)新兴买办资产阶级;(2)当权者阶层(阿尔巴托夫称其为“管理机关中的贪污受贿分子”);(3)知识分子精英;(4)采掘工业部门的工作者。此外还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约占居民的60%,他们是贫困的阶层。[⑥b]他们对现政权的态度并非一致,其中相当一部分持反对态度,还有一部分人持犹豫不决的态度。
在社会心理方面,最富有的阶层无疑希望目前的改革方针能够继续下去。而最贫穷的阶层则坚决反对现行的政治和经济方针,希望能通过选出新的领导人来改变他们目前的尴尬处境。这一部分人有强烈的怀旧情绪,他们是共产党候选人的坚决支持者。从整个社会看,不满现状的人占多数。根据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的调查分析报告,1995年俄罗斯人最普遍的情绪和感觉是(1)对国家目前的状况感到耻辱(占被调查人数的64.5%);(2)周围的一切太不公平(58.3%);(3)不能再这样下去了(55.1%);(4)恐惧国内犯罪率的上升(54.1%)。这种社会心理状态不仅反映俄罗斯目前各阶层的社会情绪,而且在1995年12月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已经发挥了作用。
俄罗斯总统选举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展开的。叶利钦是在对自己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开始竞选的。2月份,他的支持率只有10%,而久加诺夫的支持率为16.4%,3月份叶利钦的支持率为17%,而久加诺夫为25.8%,到4月份叶利钦的支持率仍低于久加诺夫23.8%∶28%。共产党候选人之所以能获得较高的支持率,除现政权经济政策的失误造成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并导致人们怀旧以外,共产党人在思想、组织和竞选纲领方面的调整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从5月份开始,随着叶利钦竞选活动的全面展开,他的支持率开始迅速上升,以领先久加诺夫的得票率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叶利钦立刻与得票率居第三位的列别德(获15%的选票)结盟,赢得了关键的一部分选民,最终得以连任俄罗斯联邦总统。
其实,这个结果并未出乎各界在大选前的预料。那么叶利钦取胜的原因何在呢?首先,叶利钦的竞选战略是成功的,他利用自己作为现任总统的优势地位,充分利用舆论工具,向主要竞选对手展开了强大的攻势,向选民施加影响。第二,同列别德的结盟对赢得第二轮选举的胜利几乎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三,西方的支持也起了一定作用。
但是,仅仅依靠这些是不足以取得胜利的。众所周知,俄罗斯虽然进行了5年之久的激进改革,但毕竟还是一个过渡社会。所谓过渡社会,就是说这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尚处于形成阶段,尚未最后定形,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政治上,俄国现在虽然建立了总统制国家,但是势均力敌的反对派明确表示最终要恢复苏维埃政权、取消总统制。在经济上,俄国目前形式上已经建立起以非国有成分为主体的多种成分经济,而以俄共为首的反对派的目标是建立以国有成分为主体的多种成分经济,反对目前实行的全面私有化政策。除现政权的坚决反对者和拥护者(他们占居民的少数)外,大多数居民思想大都处于混乱和矛盾状态。他们怀念过去的物质生活,又惧怕回到“铁幕”时代;既欣赏选举、议会、出版自由这些民主形式,又感到这些在俄国行不通,决定不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叶利钦在竞选中充分利用了过渡社会中居民的这种心理特点。他到处宣传,如果久加诺夫上台,社会就会回到“铁幕”时代,社会就将再次发生动荡。这些宣传对那些犹豫不决的选民显然产生了影响。此外,总统选举不同于国家杜马选举,如果说国家杜马选举是党派之间竞争的话,那么总统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个人之间的竞争。于是俄罗斯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表现上(抽象地)大多数人都拥护“民主”,而实际上(具体地)却都希望出现一个“铁腕人物”来整顿国家秩序。根据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上述分析报告显示,近70%的被调查者希望俄国能出现“铁腕人物”来整顿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叶利钦无疑比久加诺夫更有优势。利用这种社会心理情绪是叶利钦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次选举的如期举行对于俄罗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它表明按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的准则进行政治斗争已经为各派政治力量所接受。选举结束后,共产党人冷静地接受了选举结果。久加诺夫在得知选票统计结果后还给叶利钦发了贺电。左翼力量在这次选举中实现了联合,这也是一大收获。虽然他们的候选人落选,但是他们显然并未停止努力和斗争。8月7日,左翼力量成立了“人民爱国力量联盟”,久加诺夫仍为该联盟的领导人。这表明左翼力量并没有因为在总统选举中受挫而气馁。他们在总结经验,调整战略,等待历史给他们提供新的机会。1996年年底俄罗斯进行地方选举运动。共产党人和左翼力量全力以赴争取在地方选举中争夺更多的地盘。这次选举将直接影响到议会上院的力量对比。
总统选举已经结束,新政府已经成立,但是执政集团和反对派的力量对比并未发生大的变化。新政府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和效果如何将直接影响力量对比。政府政策上的任何失误都会加强反对派的力量。这无疑给政府提出了严峻的课题。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局势始终相互影响。经济改革方针上的分歧和政府政策的失误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不稳反过来又加重经济危机。大选后新政府要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首先,选举刚刚结束,车臣境内战事又起。这场持续了20个月之久的战争不仅是新政权沉重的政治包袱,也是沉重的经济包袱。新政府面临的最困难问题是如何使国家摆脱危机、使生产停止下降并开始增长,使经济结构得到切实改善。但是投资匮乏给这一问题的解决蒙上了厚厚的阴影。预计1996年国家投资计划只能完成15—20%。[①c]政府希望今年国内总产值和工业增长3%的打算肯定会落空。目前国家支持本国机器制造业结构改革的资金只相当于1991年水平的三十六分之一。每年仅用于10个联邦级机器制造业结构改革项目的资金就需要9万亿卢布,但是1996年各种集资渠道加起来才筹集到7.5万亿卢布,而且其中6.2万亿卢布的资金来自企业。[②c]在目前严重的支付危机和混乱的金融市场条件下,企业不愿将钱投到生产领域,连一些国家银行也不愿向生产部门投资,而是在金融领域进行投机,因此要完成这个数字也是相当难的。虽然经过4年的艰苦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终于在1996年3月同意向俄罗斯提供102亿美元的贷款,但是国际金融机构的各种贷款是附加各种苛刻条件的。俄罗斯多半是利用这些钱来堵预算赤字的漏洞。这些钱并不会对俄罗斯经济增长起到多大作用。看来,要使国家摆脱危机和解决堆积如山的经济问题,仅靠“看不见的手”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应该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控制力度。而现在由于国家软弱无力,社会上有组织的犯罪和黑色经济猖獗,企业和居民看到国家无力保护他们的利益和安全,也不履行对国家的义务,不依法纳税。
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俄国目前面临三条发展道路。第一条道路:继续保持目前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1996年生产下降也许会停止,但是将出现一个滞胀时期,经济和政治不稳定将会持续许多年。第二条道路:放弃市场改革并回到用行政命令方式管理经济,借助国家强制手段动员国内资源。但是这种方法将伴随大镇压、强制对私有经济实行再国有化,这在俄国目前形势下必然会导致内战,甚至可能会使俄罗斯解体。第三条道路:一方面要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再次复发,另一方面又要制定出合理的社会政策,保护国防综合体,逐渐地实行能够保证投资积极性和进行必要的结构改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预算和税收政策。这就要求新政府有一个深思熟虑的经济发展战略。大选的结果客观上给新政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但是还需要新政府及其各权威机关领导人在国家发展方针上克服分歧,达成共识,抓住时机。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现政权的反对派也是一支很有影响的力量,也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他们的社会经济利益应该受到重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稳定,也才能保证经济健康发展。
尽管有些科研单位和学者认为,俄罗斯国内总产值要达到改革前1990年的水平至少需要15—20年时间,但是俄罗斯有广博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科技潜力、一批熟练的劳动生力军,具有再展宏图的一切条件。
(1996年7月)
注释:
①a 见《1996年的俄罗斯经济》1996年莫斯科国际商业学校版,第43页。
②a 《俄罗斯统计年鉴》1995年版,第244、471页。
③a 1996年5月31日至6月7日《真理报》。
④a 1996年1月25日《金融消息报》;1996年2月17日《红星报》。
①b 《1996年的俄罗斯经济》,第13页。
②b 1996年4月16日《金融消息报》。
③b 《1996年的俄罗斯经济》,第34页。
④b 1996年2月14日《消息报》。
⑤b 1996年2月14日《消息报》;〈俄〉《权力》杂志1995年第11期第42页。
⑥b 〈俄〉《对话》杂志1995年第2期阿尔巴托夫的文章。
①c 1996年4月30日《金融消息报》。
②c 1996年3月5日《今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