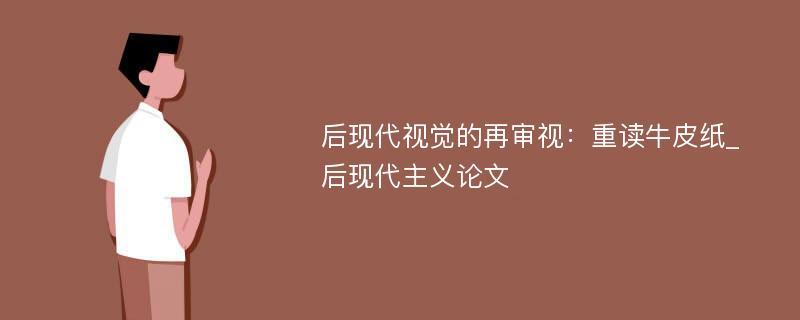
后现代视域再审视——重读卡夫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后现代论文,卡夫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卡夫卡,这个四十一岁时就去世的短命鬼,这个一辈子没结婚的光棍汉,向来被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三大师”(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之一来看待。他作为小说领域中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与后现代主义能有什么关系?
国内学术界有不少人认为,按照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点来说,它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的达达主义运动。如此说来,既然后现代不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象,既然“历史是可以抹去旧迹另写新字的羊皮纸,而文化渗透着过去、现在和未来”[①],那么,卡夫卡为什么不可能与后现代主义有关系?也有人把后现代主义总结为美学意义上的四个原则:不确定性、虚无、抽象和荒诞[②],那么,哪一点又与卡夫卡的小说对不上号?当然,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并不是什么公认的东西,更何况那些表面特点随时都可以发生变化。然而,认识与理解后现代主义思潮,应该——至少是可以——从其核心的精神入手,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卡夫卡不算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不也可以作为它的观照对象吗?
要知道,就连卡夫卡的身世,也给人一种后现代式的滑稽/荒诞之感。例如考察他的国籍,就很难断定他是哪国人:你若说他是奥地利人,那么他事实上生在捷克,不仅当时的捷克与奥地利是两码事,即使今天也是如此;你若说他是捷克人,那么,不仅如今的捷克已经分裂,而且,当时的捷克归奥匈帝国所“领导”,也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你若说他是奥匈帝国人,那么现如今,这个“国家”又因被分成捷克和奥地利两个具体国家,所以已经不存在了。这种现象过去只在文学作品中,比如海勒的那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见过,现在,卡夫卡却给我们一个生活的实例。一个分明存在,又没有象马克思那样被祖国“开除”国籍的人,我们却不知将他如何归类才好,这不滑稽、荒诞吗?我们确实掌握的依据,只剩下他是犹太人这一条了。可是,犹太人当时是个仅仅在世界上流浪的民族,以此为他的出身依据,就同以“死亡”为人定性差不多;总不能按照现在的情况,说卡夫卡的国籍是以色列吧?这不就同《第二十二条军规》中,那位丹尼卡医生只因在生存的名单上被人划掉,就到处都不承认他还活着,甚至是当面不承认他还活着一样吗?
在从特定性格角度来理解“卡夫卡文学现象”方面;德国学者龚特尔·安德尔有过很好的概括,他认为卡夫卡的身世证明了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决定他只能写出“卡夫卡式”的作品。安德尔指出,“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最初确是如此),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他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家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语)。[③]就这样,卡夫卡的身份到处没有着落,卡夫卡什么都不是。然而他存在着,这是事实,可这存在却是一种透着滑稽可笑,透着荒诞的事实。这种人不管处于什么时代,他若在思想上不接近后现代主义的思路,那才叫奇怪呢。如果不是这样,还能是一本正经地去沉思人类的命运,或去探索什么人类灵魂中的无意识吗?
此外,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想基础是存在主义,卡夫卡早在1909年,就开始了对它的研究。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是丹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克尔凯郭尔,他的《忧郁观念》一书,为宗教领域的存在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命运是反复无常的,人类对命运完全无能为力,因此,人生就是一种悲剧性的孤独存在。想要脱离这种存在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却可以生活得比较有内容。谁追求这种有内容的人生,谁就应该皈依上帝。对于这种存在主义思想,卡夫卡接受了它的前半截,而对“皈依上帝”的后半截却态度暧昧。卡夫卡心中的上帝是个什么样子,他心中究竟有没有上帝,都只能划上问号。
卡夫卡的这种研究和接受,都不是学究式的,他追求对世界和生活环境的感悟。因此,在非常热衷克尔凯郭尔的同时,他还对中国的老庄哲学发生兴趣。也许很少有人指出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喜欢争辩的姿态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老庄式的辩才,甚至也能看到他们思路相通的诡辩逻辑,看到他们最终相同的虚无和消解倾向。卡夫卡的创作在多大程度上得力于老庄哲学(比如《老子》中“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思维,《庄子·外篇·知北游》中“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耶,皆有所一体”思维,在卡夫卡小说中如何具体表现着),这是一个深奥且复杂的问题,然而进行东西方两种哲学“主义”并轨的尝试,卡夫卡却是较早的西方人士之一。早期存在主义给予卡夫卡创作上什么影响,人们谈得也许太多了,中国老庄哲学对他的影响,由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倾向,人们却谈得很少。其实,在老庄哲学中,尽管富于智慧的论述不成思想体系——这也正是后现代理论的特点——但总起来说,老庄的思想却体现出弱者的生存观念,体现出纯知识分子“物外神游”、冷峻却超然的意识形态。这些思想对卡夫卡的影响,恐怕在创作中还是体现比较明显的。
M·怀特在其哲学著作《分析的时代》中,是以提及黑格尔的方式,来这样展开自己的叙述的:“几乎二十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显赫的十九世纪的德国教授(黑格尔)开始的”[④]不知历史为什么那样相象,因为在小说界似乎也可以说,二十世纪的几乎每一种重要的小说流派,也都是以攻击十九世纪那位著作众多而思想复杂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开始的。无论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小说,还是后现代主义的“新小说”,都没有忘记通过攻击以往的文学大师,来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他们那么自信和自傲,相信从自己这里出发,巴尔扎克的时代就算翻过去了,历史在自己这里,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因此,他们潜在的口号是,打倒巴尔扎克!
相形之下,卡夫卡则显得那样软弱,那样渺小。他十分胆怯地说,“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⑤]按照习惯的理解,我们很难相信,这样一种性格的人,能够写出什么优秀的小说。这是一个窝囊废,一个可怜虫,最多会引起我们的同情,根本不会引起我们的敬意,更不会引起我们的佩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的作品却赢得了世界性荣誉,尽管这荣誉在他死后才姗姗来迟。
卡夫卡的成功,首先在于他对弱者哲学的看重,在于他不象同时代其他小说家那样,去进行所谓宏伟的叙事,而是转过身去,以弱者的观点看世界,却创作在当时不合时宜的“弱者的史诗”。他曾经这样来概括自己的创作特点:“我从生活的需求方面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带来,就我所知,和我与生俱来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从这一点上说,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的时代的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收了进来;这个时代与我可贴近呢,我从未与之斗争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倒有资格代表它。对于这个时代的那微不足道的积极东西,以及对于那成为另一极端、反而变成积极的消极事物,我一份遗产也没有”[⑥]。于是,在短篇小说中,无论是格里高尔(《变形记》)还是格奥尔格(《判决》),在长篇小说中,无论是约瑟夫(《诉讼》)还是K(《城堡》),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明显的弱点,都那么软弱可欺,他们面临的外部世界并没有对他们专门用心,只是个“例行公事”的正常运转,就把他们全打败了:父亲可以往格里高尔身上扔苹果,不管儿子如何想要表示自己对父亲的感情;父亲也可以“判决”格奥尔格去投河自尽,不管儿子如何真心地爱他;法院可以让约瑟夫永远摸不着头脑,不管他如何四处奔走竭尽努力;城堡更可以让K永远找不到憩身之处,不管他如何机关算尽。在小说提供的世界里,主人公总是越抗争就越显得软弱,越抗争就显得越无奈,越抗争就显得越渺小下去……
卡夫卡笔下的“弱者”,不是其他现代主义小说中的所谓“普通人”。尽管他们也普通,但比普通人弱小得多。在作品中,这些弱小者不仅不象意识流小说的主人公那样,承担着小说叙事人的艺术角色,而且也不象意识流小说里的“普通人”那样,往往有自己的思想逻辑和行为准则。他们具有再正常不过的理性思维逻辑和再正常不过的行为方式,根本用不着以现代理论来解释他们,只能说他们的一切都来自莫名其妙的“命运”。他们总是碰上外部世界与自己过不去,于是,他们经常处于“被告”的地位,让那无法言说的外部世界对自己进行莫名其妙的审判。
他们不是不想为自己的命运做主,然而事实是他们做不了这个主;他们不是没有进行过抗争,然而事实是越抗争越被命运扼住生存的喉咙。正如《诉讼》中那位胡尔德博士的经验之谈:
几乎每个被告,甚至是头脑极简单的人,都在诉讼的最初阶段抱有改革法院的强烈愿望,结果往往是浪费了时间和精力,这些时间和精力倒不如用到其他地方去更好。唯一的聪明办法就是使自己适应现行环境。即使有可能作一些局部的改进——不过这是毫无意义的痴心妄想——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对将来的被告有些好处,可是,由他冒犯了那些报复心理严重的法官们,却不免要使自己受到极大的损害。这种犯上的事情千万干不得!即使同自己的意愿完全违背,也必须委屈求全!
不管主人公是否听取了这种意见,他们的命运最终都在证明着这一规律:弱者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这也许是卡夫卡本人最真切的亲身体会,所谓他才说“每一个障碍粉碎了我”。他的本事不仅在于叙述出这些弱者一步一步被粉碎的过程,更为冷酷的在于,他还写出每到最后关头,弱者总是心甘情愿地走向死亡。格里高尔了解到自己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之后,默默地在一个夜晚悄悄死去,格奥尔格最终无法得到父亲的理解,转身便真去投河自尽,约瑟夫被处死时不仅不再抗争,而且还留下一句无比悲凉的人话,说自己的一生就“象一条狗”。
正如有人早已指出的那样,《城堡》里的K在作品中进行的是一场失败的较量。不过,如果说海明威作品中的人物在失败的较量中还能显出一种“硬汉”的英雄气度,是一种现代主义所推崇的“反英雄”(“反英雄”也毕竟是英雄,只不过是另一种英雄而已),那么在K身上,则带有更多的庸俗气,他是一种“非英雄”。他在小说中的欲望极为普通极为平常,即进入那个由城堡和依附于城堡的村子,进入由那些人所组成的集体,成为城堡的一个“顺民”。无论学者们对K没有进入城堡和村子做哪一种解释,有一个事实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对于K来说,根本谈不上什么斗争精神,更谈不上什么反抗行为。他是一个弱者,不管世界荒诞与否,弱者就是弱者,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
卡夫卡的心态不象同时代的其他小说家,他不象爱尔兰的乔伊斯,为出版一部小说,即使受到二十几个出版商的拒绝,也不失再尝试的勇气;也不象法国的普鲁斯特,在四个出版商拒绝出版之后,竟然坚持自费刊印自己的小说。卡夫卡不仅要求他的朋友在自己死后将作品统统烧掉,而且,即使他生前发表的那少数作品,也是经过朋友“巧施计谋和劝诱说服后才拿去的”。他没有现代主义作家的洒脱精神,没有现代主义作家的事业心,他写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写给自己的,是自己内心苦闷时的一种文字游戏,是一种排谴个人烦恼的心理治疗方式,是一种无意而为之的创造性艺术“日记”。
卡夫卡对父亲的恐惧是人人皆知的事,但这种恐惧不是一般性质的父子冲突。1919年11月,他曾给父亲写过一封没有发出的信,在这封著名的长信中,卡夫卡描述了自己对父亲的一种特殊恐惧感:
您几乎从来没有怎么认真打过我,这也是事实。可是那喊叫,那涨得通红的脸,那急忙解下吊裤带的动作,吊裤带放在椅背上的那情景,这几乎比真的打我还令人难受。就好比一个人该处绞刑。他要真处了绞刑,那他也就死了,倒也就没事了。倘若绞架上的一切准备工作他都得身历其境,只是当活套已吊在他面前的时候才获悉他受了赦免,那他可能就会受罪一辈子[⑦]。
从这里可以看出,对“强者姿态”(而不是对“强者”)的恐惧才是弱者的恐惧感受方式,这种感受由于“绞架上的一切准备工作他都得自身历其境”,因此,便再也不会因外在的解放而解除,它将永远都命定般跟随着当事人。卡夫卡正是从自己对父亲的这种感受出发,才写出那些被人们称为“卡夫卡式”的怪诞小说。也正因此,他小说中的那些人物才都只能算是弱者,而且都与作者拥有完全相同的经历或感受方式。
卡夫卡在第一次处在热恋中时,曾写过一个短篇故事献给自己的恋人,可是这篇题为《判决》的小说,竟然是这样一个故事: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准备结婚,为此他想写信,把喜事告诉远方的朋友。父亲得知后,却说他根本没有什么远方的朋友,而是想要背着自己作生意。突然父亲又改变了话题,说格奥尔格是个没有人性的人,倒是自己始终与那个朋友保持着联系,把格奥尔格的事情早告诉了他。于是,父亲判决格奥尔格去死,格奥尔格也就真的去投河了。
献给恋人这样一个故事,它将意味着什么?没有多久,卡夫卡果然与恋人解除了婚约。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象征,也可以说这仅仅是一种巧合,但你无法否认,小说中的感觉就是卡夫卡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感觉。你同样无法否认,主人公之所以急急忙忙投河自杀,就是为着尽快摆脱卡夫卡在上述给父亲信中所谈到的“绞刑前的恐惧”。
为什么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都那么胆小如鼠,胆战心惊?为什么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最痛苦的阶段,都是走向死亡的第一个阶段,越往后走越显得轻松?为什么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急急忙忙奔向死亡,而且在死亡真正到来时,又都那样平静?这些问题从卡夫卡的现实感受中,都能一一找出答案。正是这样的现实感受成就了卡夫卡,使他写出弱者所具有的命运,写出了弱者只配有的必然命运。
不分时间和地点,不分时代和历史条件,一律从抗争走向软弱,再从软弱奔向死亡,就是卡夫卡为他们谱写的弱者的“诗史”。从现实主义的视域来看,弱者是作家同情的对象,如果作家无处表达自己对人类的同情,就可以去描写弱者的命运;从现代主义的视域来看,弱者在内心世界上也是一个强者,他们的每一扇心灵之窗,都与强者一样,是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如果作家在强者身上难以挖掘人类的深层意识,就可以去描写弱者的心灵;然而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弱者就是弱者而已,既不需要以同情来显示作家自身的高贵,也不需要深入挖掘其心灵来弥补作家“创新”意识的枯竭。现实世界是强者的天堂,自然就是弱者的地狱,而且是弱者永远弄不明白的莫名其妙的地狱,卡夫卡不也是表达着这样的看法吗?
也许正由于从后现代的视域才能更清楚地看出卡夫卡的意义,所以在西方,首先意识到卡夫卡文学意义的,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然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股“卡夫卡热”才开始扩散开来[⑧]如果把他定位于现代主义创作思潮,这个超越时代精神的“业余作家”,其后现代主义的真正价值便会大逊其色。
注释:
①【美】伊哈布·哈桑:《后现代主义转折》,见王岳川等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1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②瞿世镜:《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第254—25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③龚特尔·安德尔:《卡夫卡:20世纪清醒的醉者》,第172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④《分析的时代》,第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⑤ ⑥卡夫卡遗作,见叶廷芳编《论卡夫卡》第7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
⑦卡夫卡:《诉讼》附录:《给父亲的信》见《诉讼》第268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
⑧【日】《三野大木》:《怪笔孤魂——卡夫卡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