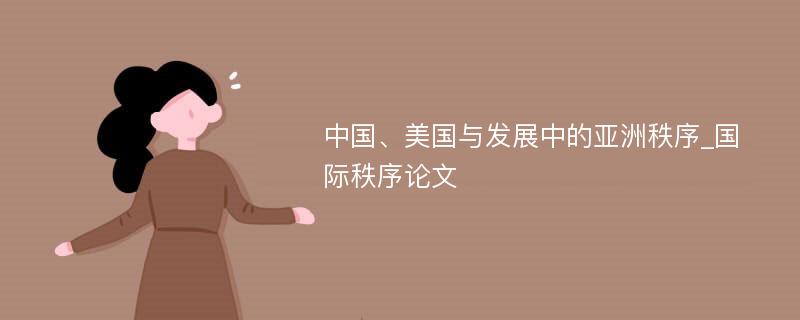
中国、美国与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中国正在日益崛起。这对亚洲地区的国际秩序来说是一个新的 变量,对这一地区的中美关系来说也必将带来深刻的影响。
一、中国崛起与亚洲秩序的改变
亚洲地区现存的国际秩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以出人意料 的方式突然结束,这给欧洲地区的国际秩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亚洲秩序似乎没 多大变动,冷战结构依然维持了下来。到了20世纪末,亚洲地区的国际秩序终于发生了 一些变化。导致变化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的崛起。亚洲 地区的国际关系原先并未能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而是一个包含了中亚、南亚、东南亚和 东北亚4个次区域的混合体系。各个次区域都有自己独立鲜明的内部特征,而彼此之间 却很少发生联系。现在这种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亚洲开始形成了一个从伊朗一直到 太平洋、从俄罗斯一直到澳大利亚的完整的国际体系。在最近这些年,这一秩序开始受 到中国崛起的巨大影响。
中国崛起是一个复合概念,包括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政治影响力以及国际事务 的参与度等多个层面,其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中国在最近几年大量地参与了国际组织并 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多边外交开始成为中国外交的新亮点。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 与以前相比,也显得更加温和与友好。这种政策调整始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在最近 几年变得更加突出。中国的周边邻国相应地也调整了对华政策,相继与中国改善了关系 ,并开始期待中国作为一个积极的、负责任大国出现在亚洲的国际体系中,于是,亚洲 地区的国际秩序开始发生变化。当然现在这种变化还只是处在进程当中,离最后定型还 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演变进程中,有一个特点似乎日益突出,那就是各国之间的相互依 赖在日益加深。在亚洲地区正在形成一张日益密集和扩大的联系网,而中国也在逐渐成 为这张网的核心。中国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安全维护、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正发挥日益 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了整个亚洲地区朝着更加和平与稳定的方向迈进。当然,我们也 不能忽视在这一地区还存在着一些十分危险的、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如在台湾海峡和朝 鲜半岛。在这两个地区都有可能引发冲突,甚至爆发大规模战争。
在东欧和苏联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中国领导层曾一度感到强烈的不安,对外部世界 持一种本能的警惕态度,对自己的内部体制和外交政策也变得不是很有信心。而现在这 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对外部世界采取了一种积极的态度,与周边各国、欧洲 国家、美国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在一些重要的多边国际舞台上,中国一改过去消极被 动的情况,开始提出自己的主张,积极参与到地区秩序的构建过程当中。其中突出的例 子就是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SCO)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国家内部,中国也历史性地实现 了最高领导层的和平交替,并提出了要加强执政党自身能力建设的新课题,使中国的发 展前景更加光明。
中国的崛起还体现在国际规范和高等教育等软权力方面。在国际规范领域,中国于199 7年提出并倡导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这对于预防和解决亚洲地 区的冲突问题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东盟合作论坛内部,通过实践这种新的安全观,推 动了各国安全合作的进程,有望把论坛变成一个类似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 的组织,这对于亚洲地区的稳定和中国影响力的增强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高等教育 领域,中国每年为周边国家培养了许多外交官、工程师、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这实际 上是扩大中国在这些国家影响力的一种重要途径。大约有85%的在华留学人员都来自周 边的亚洲国家,他们回国之后,自然就把中国的语言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带给了 本国人民,从而扩大了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
尽管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引起亚洲地区国际秩序发生变化的一个主要变量,但这并不 就意味着亚洲地区开始形成了一个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开始 成为亚洲地区新的霸主,历史上的东亚朝贡体系开始回归。这其实是一种夸大其辞的说 法,与现实是不相吻合的。我们可以从亚洲地区力量分布状况和中国自身的外交政策来 分析这个问题。
从亚洲地区力量分布的状况来分析,虽然中国的综合国力确实是在突飞猛进,影响力 也在日益上升,但中国仍然必须与美国以及亚洲地区其他的力量中心一起在政治、经济 、军事领域分享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无与伦比 的超强实力与影响力。虽然在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在亚洲的软实力开始下降,但这并不 妨碍美国在亚洲地区拥有超强的硬实力,这表现在美国不断强化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 的同盟与准同盟关系,维持在亚洲的驻军。因此,在分析亚洲地区国际秩序的运作上, 美国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影响 力。日本的GDP超过中国,日本在国际和地区中的经济影响力也明显比中国要大。从东 盟方面来看,东盟的经济实力也在逐渐增长,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东盟的规范性力量正变 得日益突出。东盟通过自身的发展历程和它创设的“10 + 1”、“10 + 3”体制以及可 能的“东亚共同体”的前景,在亚洲地区正发挥着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此外,亚洲地区 还存在着大量的各种领域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从中国自身的外交政策来分 析,中国在亚洲地区正变得日益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现状维护者的形象出现。这对中 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历史上,虽然中国早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就提出了“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而且大多数中国人也相信中国政府一直是这么做的,但实际上在过去 的岁月里,中国曾一度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输出到东南亚国家,与周边邻国发生过边界纠 纷、外交冲突甚至军事对抗。现在中国输出到这些国家的再也不是意识形态和军事武器 了,而是商品货物与劳务。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亚的很多国家相继建立和恢复了友 好的外交关系,虽然有的关系建立的时间并不长,基础还不很牢固,但相对于以前来说 ,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在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家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现在温和 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只是一种策略上的退让,中国长远的战略目标仍是追求霸权,这实际 上是一种误解。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即使当中国的实力远超过周边国家时,中国 也没有像德国那样谋求成为地区霸主,而是与周边各国形成一种经济上有共同利益、安 全上休戚与共的主从关系,即所谓“王道”而非“霸道”。
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及亚洲秩序的相应变化,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可以从两 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1)中国影响力的增长必然会导致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下降吗? (2)中美两国之间在亚洲地区事务上合作大于分歧,还是分歧大于合作?
现实主义者总是认为,国际政治是一种权力政治,各国都在追求自身的权力,而各国 之间则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一国权力的上升必然导致另一国权力的下降。约翰 ·米尔斯海默教授就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预言中国的 崛起必然会导致美国权力的下降,从而会引发中美之间的冲突。这是现实主义者悲观的 结论,实际上中美关系完全可以走上另外一条轨道,因为现在的国际体系与冷战时期有 了根本的区别。在美国与苏联两极对峙时期,“一方所得必为另一方所失”的理论可以 解释很多问题,但在冷战后的今天,亚洲地区有足够大的空间让中美两国追求各自的国 家利益,而不必然会走向冲突。有人说最近几年当中,中韩关系的改善就导致了美韩关 系的恶化,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美韩之间的一 些摩擦是由于美国自身的行为导致的,与中韩关系的发展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可以再 来看看最近几年当中美印与中印关系发展的情况就更清楚了。印度在保持与美国关系发 展势头强劲的情况下,与中国大幅度地改善了关系。在中亚,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并没 有降低美国在这一地区所发挥的影响力。所以,中美两国之间可以不按照现实主义所预 测的悲观逻辑进行互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6年中(克林顿总统的2年执政期与布什 总统的4年执政期)中美两国之间能保持良好合作状态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看在现实层面中,中美两国在亚洲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与分歧情况。我们可 以把中美两国在亚洲地区事务中的政策分为合作、分歧与不甚明朗三种,其中合作的部 分大致占到了60%~75%,分歧部分为10%,还有15%-30%的不甚明朗的部分。中美两国之 间,除了在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外,在反对恐怖主义、 防止核扩散、打击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等非传统领域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在 台湾问题、缅甸问题、朝鲜问题以及中俄关系等问题上,中美两国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
中美两国关于亚洲事务外交政策存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问题包括美国在亚洲的同盟体系 、朝核危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等。在1997年前后,中国的高层领导曾多次明确提出要 求美国放弃在亚洲的同盟体系,认为这些同盟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它 们本是冷战的产物,理应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而现在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变得 比较模糊,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出要把美国的力量驱逐出亚洲。在朝鲜核问题上,中美两 国都一致主张朝鲜半岛应该无核化,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中美两国却有不同的看 法。虽然美国基本上还是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通过对话的方式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但在 布什政府内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对朝鲜进行强硬遏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中国没有明确反对把日本和韩国纳入到防御系统当中去, 但对台湾,中国则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三、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
亚洲地区正在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新秩序?大国均势、大国协调抑或其他?我们先来看看4 种设想中的亚洲秩序的模式:第一种是轮毂模式。在亚洲事务中,尤其是在安全领域, 美国与其在亚洲的盟友构成了一个车轮的轴心和辐条,美国作为车轮的轴心,掌控着整 个亚洲地区的事务,但也离不开亚洲盟友的支持与配合。第二种是有限共治模式。有限 共治是与完全共治相对而言的。完全共治是指中美两国在亚洲地区进行完全的合作,共 同掌控亚洲秩序的主导权。这实际上不太可能,因为中美两国在亚洲事务中是不可能做 到完全合作的,比如在台湾问题上。但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在亚洲事物中的共同参与与 合作又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朝鲜问题在内的很多关键问题,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是 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的。所以把这种秩序称之为有限的共治。第三种是规范共同体模式 。轮毂模式与有限共治模式更多的是从硬实力的角度来分析的,规范共同体模式则是从 软实力的角度来看的。东盟各国与中国一起正在倡导一种就如何处理双边关系、预防和 解决地区冲突、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加强国际合作等问题的新的国际规范,以期在亚洲 地区形成有助于增强集体认同感的新的价值观念体系。东盟合作论坛与上海合作组织就 是这方面的事例。这对亚洲地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第四种是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各国 之间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国界已不再具 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了,各国的货物与观念在彼此之间自由流动。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 在逐步上升,开始从单纯的资本输入国变为输入与输出并存的国家。中国的大企业也开 始像韩国、日本的企业一样进行跨国经营了。传统的军事因素作用开始下降,美国在亚 洲的同盟体系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具备了上面4种秩序的某些特征,但又与其中的任何一种秩序不 完全吻合。所以,我们可以把现存的亚洲秩序看成是轮毂模式、有限共治模式、规范共 同体模式和复合相互依赖模式的一种复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