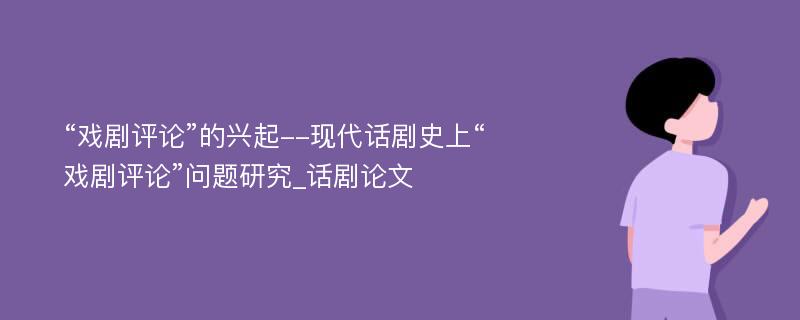
“剧评”的兴起——现代话剧史“剧评”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评论文,话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 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943X(2015)01-0021-11 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中,“新剧”作为一种舶来的艺术类型,从清末西人演剧到1928年“话剧”之最终定名,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演进过程。袁国兴将这一历史时期的戏剧活动称为“新潮演剧”,即各种各样的新剧“往往观念重叠、倾向接近、文类边界并不十分清晰,戏剧观念和戏剧意识游弋于古今中外之间”。[1] 这一思路可以这么理解:“新潮演剧”本来蕴藏了多种“可能性”,这个阶段既是一团乱麻,仿佛混沌未开,又好像提供了多种路径选择,而戏剧史的发展告诉我们这初始的丰富性最终走向了写实话剧观念的建构之路。那么,问题是:从观念重叠、文类边界不清的“新剧”演进成观念统一、边界清晰的“话剧”,是什么样的力量起了主导作用?当然原因有很多,但作为一种由“新的知识”与“新的审美意识”构成的“新的文体”——“剧评”,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从这一角度切入的思索与解读却被学界长期忽略了。 本文对“剧评”的兴起的解释分为四个方面。 首先需要界定:在本文的语境中,“剧评”主要是指对于“新剧”的评论与批评(这其中亦包含了当评论者需要言明新剧的文类特征时,将传统戏剧作为“对比方”而进行的论述)。其次,能够对新剧品头论足,必然意味着有掌握新剧“知识”的知识人,形成关于新剧的“知识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新剧的“审美原则”。再次,“剧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文体”,与传统戏剧的评点模式有很大区别,这使得考察“剧评”兴起的历史过程,也即是观察“话剧知识系统”的建构过程,并进一步研究此知识系统得以建构的深层文化机制。最后,具备了“知识范型”的转移与文化机制的建构等条件,李健吾对《雷雨》的评点体现了新剧人士对“话剧”从文体形式到内涵的全面掌握,代表了话剧剧评之成型。 一、文类的边界:从“评点”到“剧评” 在《新青年》杂志关于“戏剧改良”的讨论中,傅斯年和欧阳予倩都注意到了“评戏问题”。傅斯年总结了“中国戏评界”的四点陋习:第一是不批评、第二是不在大处批评、第三是评伶和评妓一样、第四是党见。[2](P.170-182)欧阳予倩在《予之戏剧改良观》里也指出所谓“旧的剧评”不过是“非以好恶为毁誉,则视交情为转移”。[3](P.295-298)当然,这些意见都是很严重的批判。不过,如若换一个角度视之:从这些批评中未尝不可以见出在近代传统戏曲范畴内(以京剧为代表)所固有的“戏评”之特点:以品赏色艺、玩味伶人为核心特征。 具体言之,在文体形式上,以诗词或兼有札记、笔记及诗话词话性质的短文为撰写形式。例如,名士易顺鼎诗咏歌郎贾璧云《贾郎曲》中有涉及梅兰芳语:“京师我见梅兰芳,娇嫩真如好女郎。珠喉宛转绕梁曲,玉貌娉婷绝世妆。”[4](P.1060)又如,张伯驹《红毹纪梦诗注》兼诗与补注,评色艺、录趣闻,可谓集传统“戏评”之特色。诗曰:“童伶两派各争强,丹桂天仙每出场。唱法桂芬难记忆,十三一是小余腔。”后有补注:“当时有两童伶,一小小余三胜(即余叔岩),谭派;一小桂芬,汪派……小小余三胜演《捉放宿店》,‘一轮明月’的‘一’字转十三腔,名十三一。叔岩成名后,不复作此唱法矣。”[5](P.3)而吴祖光的《广和楼的捧角家》更是把新闻记者之类的捧角之人描述得非常形象: 他们的捧角无非是在报屁股上弄一个戏剧专号,作些肉麻的捧角文字。捧角文章其实是不容易作的,作得多了,自然离不了那一套,如“娇艳动人”、“黄钟大吕”、“嗓音清超”、“武功精熟”、“深入化境”、“叹观止矣”、“予有厚望焉”,诸如此类,举不胜举。[6](P.259-264) 忽略其中讽刺调侃之意,吴祖光对于戏评文字的风格把握是大致不差的。客观地说,这种“戏评”风格与近代戏曲(尤其是京戏)对于演员色艺的特别强调是相适应的。从“艺”的角度言之:京剧进入鼎盛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是谭鑫培的出现。而谭鑫培最显著的美学风格恰恰是追求演唱的含蓄蕴藉和行腔中的韵味,形成了“沉郁顿挫”的美学风格。[7]从“色”的角度言之:文人墨客对于“男旦”的“鉴赏”更是清末流行的社会风尚。而对于古典戏曲的评点传统来说,戏剧评论的著作十分繁富,而且评论形式灵活多样,除了专著品评、作品选评外,还有剧本评点以及杂文、小品、日记、书简中的随评。[8](P.3)譬如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潘之恒《鸾啸小品》等等。它们基本立足于戏曲文本在绘情写景及叙事上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效果,也注意到了戏曲形式的探索。但“曲”的观念直到明末依旧占据戏剧观念的中心位置。 综上所述,当“新剧”作为异质性的戏剧形式上演于中国时,传统的“戏评”或“评点”模式从实质而言是基本无效的。“新剧”有“新剧”的表演方式和审美方式,布罗凯特对于“批评”的定义是“判断的行为”。[9](P.21)欲对新剧的好坏优劣进行判断,首先需要拥有新剧的知识。如何“认识”新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如何“评论”新剧。 查朱双云《新剧史》中有“评论”一节。所评均为关涉新剧整体发展的方针大计,偶尔兼及具体剧目。朱双云反对在联合演剧中以“抽签之法”分派角色: 盖新剧全恃乎配手得当者也。譬如恨海伯和棣华两角均抽得上选人才。而于鹤亭一角,适抽劣等之人。一着错,满盘都是输……此抽签法之不可行者一。同一悲旦角色,然恨海之张棣华与血泪碑之梁如珍,期间盖有不同。故往往善演恨海者,未必兼善血泪碑。凌怜影陆其美是其证也(凌善恨海陆工血泪碑)。使恨海与血泪碑两剧并演,所抽而各得其反,则联合演剧将永无完满之日矣。此抽签法之不可行者二。[10](P.1-2) “抽签法”不顾戏情戏理,将对演员的选择付之“运气”,朱双云反对这种做法,理由有二:第一,新剧的演出效果靠的是合适的演员并且搭配得当,这是对新剧特性的一种判断;第二,演员扮演角色不能兼善,所以要根据“角色”特性选择演员。不过,在朱双云的表述中,“角色”前尚有“悲旦”一词,说明对于新剧角色的认识尚没有与传统戏剧的“行当”划分相剥离。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行当意识”还笼罩在“角色意识”之上(从《新剧史》“派别”一节“生类”与“旦类”的分类方式亦可佐证此点)。《新剧史》出版于1914年,朱双云对新剧的判断颇能代表当时剧人的认知水准。虽然“行当意识”暂未消褪,但“角色意识”的“觉醒”还是通过以“剧中人”的特征为衡量演员的标准得到了表达。 涉及具体剧目,朱双云认为《祖国》一剧价值固高,但并不适合上演: 剧中人物,多系贵族。言语举止,在在异于常人。第是现今剧人,仅能描写中下社会,且纯以上海为归。若偶为上等之人,则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矣。故吾谓祖国一剧,万不可演于今日。若必演之,则必至唐突名著而贻讥大雅也。[10](P.3-4) 这段话透露了非常丰富的历史信息:朱双云对剧中人物的判断来源应是剧本(至少是来源之一),由此隐约显现的思维逻辑是:以剧本为旨归支配演员,从而认为目前演员的水准无法完成对“贵族人物”的塑造,所谓“唐突名著”即是此意。其次,“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透露出对于“写实”的极端重视:因为演员的条件对于扮演“贵族”尚不能“以假乱真”,所以“万不可演于今日”。 这段文字本意不是剧评,但客观上形成了“判断”,而且清晰地表达出了为何如此“判断”的理由,尤其是行文中浮现的理性之风,更能够使其区别于旧戏(京剧)的“评点”之文。另外,从朱双云对于不同剧目之间价值高低的判断中,亦可见出其秉持了何种“新剧观念”:“双云曰血泪碑一剧,罅漏颇多,殊无价值……恨海恩怨记二剧,虽为一时名著,然其价值,则远在梅花落祖国之下……祖国为世界四大悲剧之一,其价值可想而知。”[10](P.3)其中的价值序列颇能说明问题:《血泪碑》改编自时装京戏;《恨海》改编自吴研人小说;《恩怨记》为陆镜若编撰,受日本新派剧影响颇深;而《梅花落》与《祖国》均根据西方戏改编,尤其《祖国》一剧,是陈冷血翻译自法国戏剧家柴尔(萨尔杜)的代表作品。朱双云的“潜台词”其实是:愈接近西方戏剧的新剧,价值程度愈高。由此判断中显露的“边界意识”非常重要:它的意义其实就在于“用何种眼光、以何种标准”评估一部新剧的高下优劣。 1914年前后,是中国现代戏剧变革的一个转折时期,此前的笼统新剧概念开始发生分化。[11]与此相关,“文学”与戏剧的关系也被人重新进行探讨。譬如“新戏乃文学革新之一种”等等。[12]而就在这一时期,从史料上亦可观察到,出现了颇多以“剧评”或“剧谈”为题目的文章。这些文章多集中在《戏剧丛报》、《剧场月报》、《游戏杂志》、《繁华杂志》及《新剧杂志》等刊物上。虽然这些评论文章鱼龙混杂,但大量出现于这一阶段,可以视之为“批评的自觉”:此种现象乃是一种新的文艺形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对于“新剧”而言,发展已有十余年,问题肯定不会少。对于新剧从业人士而言,随着新剧知识的积累、视野的扩大、认识的深化,以“论说”的方式褒贬一剧之高低,其实是为了借此表达自身对于新剧的观念变化。反过来说,以观念统摄评说,表露出不再将“剧”当成“儿戏”,聊抒闲情。至少从当时的剧评上即可以看出,“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正在悄然地发生蜕变。 悼愚在《春柳之优点》(1915年)中说: 新剧虽无歌唱台步之必要,然注重剧本与服装则一也。且新剧除剧本服装外,更须兼重表情与布景,四者具备,始可与谈新剧。[13] 在此一观念之“观照”下,悼愚的评论聚焦于五点:第一,该社演剧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无不以剧本为之主任者,于未演之先数日,将剧本指令演员,悉心揣摩,不熟不止。故无临时指画,暨茫疏艰涩之弊。第二,表情非常周到,或嗔或喜或歌或泣,莫不宛然似真,能使观客恍如置身其间,不觉是伪,诚难得也。第三,布景绝佳,幕幕完备,唯布置微嫌濡延,致急性观客有不耐之诮。第四,演员程度高尚,如陆吴蒋欧阳等,均曾留学东瀛,于新剧研究有素,故演时各人有各人之精彩,固非率尔操觚者比也。第五,每演一戏,能不失当时之真。[13]对于“剧本”和“布景”的重视在这一阶段的评论中占据了主要位置,可以将此视为对于新剧“特性”的进一步认识。正如季子在《新剧与文明之关系》中说: 试观剧场布影无不以物质上之文明为竞争之粉本,而剧情表示则更利用社会心理无形感力,以期收引人入胜之奥妙。此新剧之所以擅长,而记者之认为文明关钥者此耳。[14] “新剧之所擅长”即是新剧“特性”之所在。所谓“剧评”之意义正于不经意间从这段话中显露出来:将真正之“新剧”从“似是而非之新剧”与“改头换面之旧剧”中拯救出来,并试图划出清晰的边界。 二、“剧评”的文体自觉 “剧评”反映了新剧人士对于“话剧”的认识水准和认知过程,在对新剧的不断学习与掌握过程中,马二先生(冯叔鸾)在当时剧人中最有“剧评意识”,其《啸虹轩剧话·叙言》如此表述: 曩刊剧谈三卷,颇多芜杂。盖新剧旧剧固截然两事,未可混同。自吾演艺于春柳,始能阐明兹义。故甲寅以来所为剧评,约有两要点。第一,严新剧旧剧之界限。旧者自旧,新者自新。一失本来便不足观矣。第二,严脚本结构与演员艺术之分别。脚本结构之美恶,是编戏者之责。演员艺术之优劣,是演戏者之责。不可并为一谈,遂张冠而李戴也……泛言剧理者,录为悬谈。就艺褒贬者,录为随评。颜曰剧话,用别于前此之剧谈。夫戏剧虽小道而与社会文化有密切之关系。文化愈盛,则其戏剧之组织亦愈益繁难。[15] 马二先生的这段叙言对于“剧评”而言意义重大:不仅包含对于“剧评”内涵与功能的明确认识,而且自觉到了作为“文体”的“剧评”之形式规定。“严新旧剧之界限”正说明要从“新旧不分”中辨识出新剧的面貌,确定“新剧之所擅长”,此为“剧评”在当时最大之意义;而“严脚本结构与演员艺术之分别”正说明“剧评”要有的放矢,对一剧之不同构成部分要建立不同的评价标准,以此评论具体剧目的水准,方能将“剧评”的指引匡正功能落到实处。 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对于“剧评”的“文体自觉”。马二先生首先区分了两种“剧评”:一为“泛言剧理”,一为“就艺褒贬”。前者名曰“悬谈”,其实相当于广义的“戏剧批评”,后者名曰“随评”,就是所谓“戏剧评论”了。马二先生的定义非常精准,对于“剧评”的文体界定是建设“剧评”的关键一步。 其次,以“剧话”区别于“剧谈”,盖有以表正式之意。何为正式?除文体区分与建立的考量外,就是对于“剧评”实际存在状况的反思。马二先生在《新剧不进步之原因》中谈到三点问题,其中第二条即“评剧者之盲于阿谀也”: 大报纸剧评每在可有可无之列,间有一二家,偶一载之。率为敷衍应酬之作。至于小报纸,则更足有令人失惊者。主笔先生强半受佣于新剧馆为缮写员。姑勿论其观剧之眼光如何,评剧之学力如何,第此辈在剧馆中之位置,尚在演员之下,而仰剧馆主人及一般管事者之鼻息以为生活……吾尝谓今之各报所作剧评,只可谓之剧颂。盖有褒无贬一意称赞,非颂而何然。[16] 也就是说,剧评水平之所以差,一是缺少发表场域,二是剧评者地位低下,没有独立性。故在马二先生看来,所谓“剧评”,无非是“剧颂”而已。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早期剧评者的身份及知识来源与“剧评”内涵之间的关系了。早期剧人多出身于新式学堂,其中有部分人曾留学日本。徐半梅说:“日本的剧场中,吸收了一部分中国学生,后来又造成了若干酷嗜日本新派剧的中国人。日后一般提倡中国话剧的人,大半出在这里头。”[17](P.11)那么,对于没有到过日本且有志于新剧的人士,他们的知识来源为何?徐半梅有亲身的体验: 我每月在虹口要买好几种关于戏剧的日本杂志,而文艺杂志中,凡载有剧本的,我也一定买回去,单行本的剧本,也搜罗的很多,世界著名的剧本,我也读过好几种,兰心大戏院每两三个月一次的A·D·C剧团演出,我必定去做三等看客,躲在三层楼上欣赏。我还发现一处日本的小型剧场……我便常常去看,成了一个老主顾了。[17](P.22) 虽然在早期剧人中,已经有人意识到了“严新旧剧之界限”,但由于在知识结构上对于西方戏剧的了解多是经过日本这一二手渠道,所以对于“新剧自新”之本源的了解始终隔膜难消。而且,“新派剧”与小说之间关系颇深,日本“新派剧”的名作除模仿欧洲浪漫派戏剧之外,多是根据家庭小说改编的“家庭悲剧”,诸如《金色夜叉》、《不如归》等等。特别提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在早期剧评中普遍存在的“批点小说”的行文与思维模式,与早期新剧人士的知识来源有很大关系,具体表现为按幕评点新剧。例如,在白蘋《评〈不如归〉》一文中,因该剧一共七幕,作者即按照幕之顺序逐段进行评说: 第三幕:送别一场,真妙到十二分,因现在之惨别,忆及从前之欢情,软语缠绵,销魂几许……噫,妾怨绘文之锦,君思出塞之歌,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痛矣痛矣。[18] 这种评论虽然态度堪称严肃,但显然不仅缺乏新剧的知识,更没有建立应该如何评论新剧的“新剧思维”,而仿佛是在品味小说。 在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中,还勾勒出一幅当时的“剧评”生产的生态图景: 那时,时报上新添了一个附刊,唤作“余兴”(其时尚无副刊这个名称,申、新两大报,有一个附张,专载省大吏的奏折的),这余兴中,什么诗词歌曲、笔记杂录、游戏文章、诙谐小品、以及剧话、戏考、都荟萃其中……徐卓呆却常在“余兴”中投稿。卓呆和我是同乡老友,为了要给春柳社揄扬宣传,所以偕同陆镜若来看我了……春柳社所演的新剧,我差不多都已看过。每一新剧的演出,必邀往观,不需买票,简直是看白戏。但享了权利,也要尽义务,至少是写一个剧评捧捧场,那是必要的.也是很有效力的。[19](P.41-402) “捧场”的心态恰恰是为马二先生所深恶痛绝的。但何以会有这种“捧场”的心态呢? “剧评”虽然不过是纸上世界,但与社会文化机制息息相关。马二先生已经认识到剧评的意义之重大,所以要“严新旧剧之界限”。换句话说,剧评不论是对于一剧水平之鉴别,还是对于整个新剧的发展,都有匡正指引之功。但剧评首先是一种“知识”,当时剧人关于新剧的知识素养、知识来源、理论水平、认识层次完全体现于其中。其次,“剧评”是一种“机制”,理想的状态应是整个新剧行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事剧评的人本身应该具备相对独立的社会身份、中等以上的社会地位,并拥有相对独立的发表剧评的媒介场域。而这一主一客两方面的构造在1914年左右这一历史时期,对于“新剧”这一社会新生事物而言,远未成型。 徐半梅将早期从事新剧的人分为三类: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从外埠慕名而来上海的献艺者;上海本地的热心戏剧者,他们的共同点是召集同志、成立剧团、四处演出,而他们的结果“都是失败的。又可以说,一出现就消灭,一个也没成功”。[17](P.28)新剧在此阶段整体意义上的失败,仅从“剧评”这一文体的意义上而言,其实象征着“知识范型”与“文化机制”的双重失败。也就是说,在以日本新派剧、本土传统戏剧及新旧小说为主要知识资源的新剧视野中,既无法完成剧评本身作为一种文体的建设,更无法通过剧评规范新剧本身;另一方面,缺乏能够令“剧评者”得以独立发言的“场域”与“机制”,使得剧评者不得不处于依附性生存状态之中,而造成一种捧场的游戏心态。因此,只有当“知识范型”发生转移与新的“文化机制”得以建立的条件下,剧评方能够真正“兴起”。 三、“知识范型”的转移 五四时期《新青年》关于新旧剧的论争,其实蕴藏着“知识范型”的转移。胡适提纲挈领,“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对新剧发展方向具有规定性意义。而“悲剧的观念,文学的经济,都不过是最浅近的例,用来证明研究西洋戏剧文学可以得到的益处”就从整体取向上预示着“知识范型”的转移。[20]欧阳予倩认为当时的剧评有三大弊端:第一条就是“缺乏社会心理学、伦理学、美学、剧本学之知识,剧评本身的技术手段和批评方法多不完全”。[3](P.295-298)文明戏出身的陈大悲在《爱美的戏剧》“编述底大意”中说: 我编这部书的材料,多半是从雪尔敦陈鼐底《剧场新运动》(Sheldon Cheney's The New Movement in the Theater),艾默生泰勒底《爱美的舞台实施法》(Emerson Taylor's Pratical Stage Directing for Amateurs),威廉兰恩佛尔泼底《二十世纪的剧场》(William Lyon Phelp's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ater)等几部书里取得来的,其余还有四五种参考的书。我起先原想专译《爱美的舞台实施法》,因为这部书专为美国人而作,与中国情形很多不合,不如拿人家先进国底戏剧书做基础,编一部专为中国人灌输常识而且可以眼前实用的书,比较的有些收获的希望。[21](P.10-11) 由此可明显发现新剧的“知识范型”从日本资源向欧美资源的转向。而知识范型转向“欧美资源”的优势主要体现于:一是直接从新剧的源头取法,通过留学西洋或阅读西文原著进入欧美戏剧的语境之中,减轻误读程度;二是就专业知识的系统性而言(譬如洪深在美国哈佛师从贝克学习戏剧),欧阳予倩所谓的各种知识的缺乏,特别是关涉剧评的“技术手段”与“批评方法”,在以欧美戏剧资源为取向的“知识范型”下,能够得到较大程度的弥补。这种弥补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肇始于《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形成了翻译(改译)西方戏剧剧本及戏剧理论的热潮。从1917-1924年,26种报刊、4家出版机构共发表、出版了翻译剧本170余部,涉及17个国家70多位剧作家。① 第二,从这一时期开始,主要大学的外文系逐步走向完善(譬如北大、清华、东南大学),且均以欧美语言及文学为主要专业规划。在课程设置上已开设系统的西方文学史(含戏剧)、某一时段的戏剧史及专人研究(如莎士比亚)等课程。② 第三,以胡适、宋春舫、洪深、熊佛西为代表的留学欧美之学人,在专业的系统学习与研究上,远远超过了留日学人。倡导者的知识素养与视野在专业上往往具备方向性的决定意义。这批人回国后又长期执教于国内高校,遂在专业知识领域形成“制度化传播”。另一方面,报纸的副刊逐渐为新文学人士所掌握。因为拥有相对自主的发言场域,所以马二先生对剧评“率为敷衍应酬之作”的批评,可以得到很大改观。由于早期新剧人士生存状况并不理想,往往呈现出一副混迹江湖的景象。而随着大学、报刊、出版机构等制度的逐步完善,相对独立的知识者阶层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成型,新文化人依托于此,职业身份与地位攀升于社会中上层,生活趋于稳定。③“仰剧馆主人及一般管事者之鼻息以为生活”的境况基本消失了。与此相呼应:新剧从整体走向上在这一时期从“市场”退回“校园”,目的也是为了重新寻找立足之基础。 余上沅在《晨报》创刊四周年纪念专号上说《晨报》“在促进‘新中华戏剧’的实现上,他确是一员猛将”。[22]重点不是“新中华戏剧”,而是余上沅把握到的这样一层关系,表现在本文的语境中即是:当知识者有了独立发言的场域,“剧评”文体、功能及意义的完善才能真正得到落实。陈大悲与熊佛西在《晨报副刊》上先后有两篇指涉剧评本身的文章。陈大悲论述的焦点在于“剧评家主体”的塑造: 戏剧是偏重感情的,而批评戏剧的人却不可偏重感情……换句话说,评剧家进了剧场,预备为舞台上演的那出戏作批评时,先应当把自己从听众所乐处的情网中解放出来,精确锐利的眼光透进剧本与演作底骨子去,探出他们底有力处与弱点来,然后很谨慎很忠实的下自以为最公正的批评。[23] 对于“剧评者”在戏剧整体中的位置,陈大悲亦有论述: 评剧家既与编剧家与演剧家在剧场中三权鼎立,同为剧场中不可少的分子,他为艺术经受的苦难当然与编剧家与演剧家相等……因为艺术的进步是有赖于艺术的批评家的……这个指路破迷的责任是要头脑清醒不为情感所困和具客观的眼光的评剧家去负的。[23] 而对于“剧评家”的“知识标准”,熊佛西侧重谈到: 戏剧批评家必须懂剧本,必须懂表演,懂背景,懂音乐,懂跳舞雕刻建筑以及其他一切与戏剧有关系的艺术……其次,他对于戏剧史亦应有系统的研究。末了最要紧的是他自己必须有他自己的主张。还有,他必须富有同情心和公正心。所以一个戏剧批评家不是一个无聊的捧角者或专事攻击他人的人。他是戏剧界的哲学家,理论家,历史学家。他与创作家与或其他的艺术家有同样的地位。[24] 合而观之:理想的“剧评家”应由两方面构成:第一是批评的德性:理性与公正。第二是批评的能力:知识和主张。也就是说,剧评家主体的塑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那么,能够塑造出理想的剧评家的社会文化机制是什么呢?从宏观角度言之:话剧进入现代专业教育体系的历史过程,即是提高与完善话剧从业者知识水准与人格素养的历史过程。从微观角度言之:作为“知识系统”的戏剧专业课程设置进入大学教育体系,使得剧评家主体的塑造具备了完成的可能。 四、话剧“剧评”之“成型” “评论”的专业与非专业的基本区分,就在于“批评的德性”和“批评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的系统性与发现知识的相关联性,往往决定了主张的高下。因此,本文将“剧评”在中国真正成型的标志定为李健吾评论《雷雨》文章的发表(文章名为:《〈雷雨〉——曹禺先生作》)。李健吾评论《雷雨》的文章初刊于《大公报》(1935年8月31日),后收在《咀华集》中(1936年)。[25](P.115)作为文体的“剧评”之所以在李健吾的笔下堪称“成型”,可从批评家主体塑造与社会文化机制两个方面分而言之。 许纪霖将1949年之前的知识分子划分为三代: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其中后五四一代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批:前一批出生于1895-1910年之间,后一批出生于1910-1930年之间。李健吾出生于1906年,恰恰属于后五四一代的前一批人。这一代人的特点是: 他们在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五四中的学生辈(五四知识分子属于师长辈),这代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如果说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很难用一个什么家加以界定的话,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五四一代开创了新知识范型之后,后五四一代作出了一系列成功的范例,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和学术的高峰主要是这代人的贡献。[26](P.81) 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随着“现代教育”在近代中国的逐步完善,李健吾这一代知识分子恰恰是“现代教育的典型产物”。观察李健吾的教育经历:受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热衷于校园戏剧活动、留学法国研究福楼拜与莫里哀,使得李健吾在现代大学这一体系内完成了“批评主体”的塑造。[27]在清华大学外文系的课程设置上,专门的戏剧类课程有《戏剧概要》、《莎士比亚集》、《近代戏剧》。还有《世界文学》一课,亦会涉及大量戏剧知识,更不用说清华图书馆以收藏大量西方戏剧原著而闻名学林。④在课程设置上将戏剧作为知识进行教授,不仅使戏剧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且推动了戏剧观念的更新,这一点对爱好戏剧的受教育者极为关键。另外,清华相对频繁的戏剧演出活动,令担任过清华戏剧社社长的李健吾有机会与戏剧实践保持接触,养成“专业感觉”。留法求学期间,李健吾更是受到了法国印象主义批评大家法郎士的较大影响,这一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渗透到了李健吾的批评风格之中。正如李健吾自己所言,倘若不是系主任王文显知道他热爱戏剧,留他做外文系的助教,留法的机会恐怕不会轻易降临。[28](P.215-217) 由此可见,新剧以“爱美”自居,水准固然难免幼稚粗率,但由市场退回校园,在学校(尤其是大学)这一社会文化机制中,凡有志于新剧的学子在知识结构和人格素养上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这一点至关重要。 从“批评的德性”而言,李健吾在《咀华二集·跋》中说: 一个批评者有他的自由。他不是一个清客,伺候东家的脸色;他的政治信仰加强他的认识和理解,因为真正的政治信仰并非一面哈哈镜,歪扭当前的现象……他明白人与社会的关联,他尊重人的社会背景;他知道个性是文学的独特所在,他尊重个性。他不诽谤,不攻讦;他不应征。属于社会,然而独立。[29](P.184) 这种“独立意识”的出现不仅能够显示出“批评主体”所受教育的类型和程度——即以欧美自由主义传统为宗旨的高等教育,更表明批评主体能够从该教育体系中获得客观的、较高的社会地位,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其个性的伸张。 从“知识和主张”而言,李健吾在评论《雷雨》一文中有两处最见知识含量:一为“作者运用两个东西,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新的是环境和遗传,一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新东西;旧的是命运,一个古已有之的旧东西”。另一为“作者隐隐中有没有受到两出戏的暗示?一个是希腊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Hippolytus,一个是法国拉辛Racine的phèdre,二者用的全是同一的故事:后母爱上前妻的儿子”。[25](P.116-121) 知识含量说明批评者对于戏剧的研究程度,这样就可以将对一部剧作的评论放置在整个戏剧史的背景下进行考量,从而有利于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从主张来看,“人性探索”与“艺术本位”是李健吾批评一以贯之的标准,欧美经典戏剧(亚里士多德式)是李健吾的衡量尺度。所以,李健吾不仅关注人物性格的塑造,“《雷雨》里最成功的性格,最深刻而完整的心理分析,不属于男子,而属于妇女”。[25](P.120)而且,李健吾对于戏剧整体结构的敏锐观察更是体现出了他对于“情节整一性”的自觉把握: 我引以为憾的是,这样一个充实的戏剧性人物,作者却不把戏全给她做……作者如若稍微借重一点经济律,把无用的枝叶加以删削,多集中力量在主干的发展,用人物来支配情节,则我们怕会更要感到《雷雨》的伟大。[25](P.123-125) 这种判断力只有以“知识与主张”为底蕴才能作出,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剧评”。陈大悲与熊佛西在《晨报副刊》上对于真正剧评家的“召唤”在李健吾这里实现了。可在李健吾专业的剧评背后,必须要看到在当时的北平,以大学建制为依托,以报纸副刊为场域,形成了一个批评家群体,而李健吾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有学者论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清华学派”,说明在1930年代前后,以叶公超编辑的后期《新月》、《学文》等刊物为发言场域,以清华大学外文系为核心群体(涵盖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师生),形成了一个批评流派,他们的特点是教养深厚、谙熟西学、强调作品的审美特性、注重批评的独立个性,并且实在地掌握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报纸副刊,通过评论、出版、评奖等活动体现自身的影响力。[30]所以,作为“个体”的李健吾的“剧评”之成熟,离不开作为“文化机制”的“学院力量”(即现代教育体系)之培育和依托。换句话说,“文体”背后有“制度”,作为“文体”的剧评与作为“机制”的剧评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前者是批评家的“个人制作”,后者是批评家的“运作场域”。唯有两者结合,才能使剧评产生效果。这种效果从表面观之,表现为对于具体作品的品评与指点;但究其实质,其实是“解释的权力”。而哪一种解释最终能成为“定评”,就要看哪一种文化机制最终成为“定制”了。 洪深说:“要晓得,在大学里学戏剧,所重的是理论与文学。”[31](P.241)“理论与文学”的功底正是撰写剧评的基础,而“在大学里学”恰恰体现文化机制的作用。倘若不是顶着“美国留学的戏剧专家”(明星广告部介绍洪深语)这一闪亮的头衔,洪深对于“新戏”“文明戏”“爱美剧”与“话剧”的区分,就不会有裁断的权威。在1928年一次戏剧人士聚会上,经田汉提议,由洪深定名“话剧”这一故事充分说明:现代教育制度使洪深获得了“象征资本”,而洪深则充分将此“象征资本”转化为一整套体系性的评论话语,建构了“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的、以西方近AI写作实剧为主流导向的理想秩序及价值标准。譬如,“剧本是戏剧的生命”、“现代话剧的重要,有价值,就是因为有主义。对于世故人情的了解与批评,对于人生的哲学,对于行为的攻击或赞成”等等。[32](P.176-177) 由此而言之:中国话剧“剧评”逐步建构的过程,即是“新剧”逐步划清自身与他者的文类边界、蜕变为“话剧”的历史过程。“戏剧”(包括“话剧”在内)作为“知识”进入现代教育体系,就必然意味着将被那些掌握“知识”的知识人重新定义与规划,而这一定义与规划的历史性表现形式之一正是:“剧评”文体之兴起与成型。 ①参见张文静:《略论“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周学普:《近代剧研究参考书》,《戏剧》1921年第1卷第6期,文中所列皆为欧美戏剧研究著作,共28种。田禽:《中国戏剧运动》,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据该书第八章“三十年来戏剧翻译之比较”中记载:从1908-1938年,总共出版了387册翻译的剧本。其中日本剧本84册,即翻译自欧美的剧本共303册。 ②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课程一览:《戏剧选读》,潘家洵主讲,学分六;《莎士比亚》,梁实秋主讲,学分六;《欧洲戏剧史》,赵诏熊主讲。国立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课程:《英文戏剧》,三年级必修;《莎士比亚》,四年级必修;《现代戏剧》,三四年级选修;《希腊悲剧》,三四年级选修。国立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课程:《戏剧入门》,袁昌英主讲;《莎士比亚》、《希腊悲剧》,方重主讲,此两门为选修课。私立光华大学文学院英文系三四年级必修课程:《莎士比亚》、《诗学》;选修课程:《欧美现代戏剧》。私立金陵大学外国文学系课程:《英文戏剧》、《莎士比亚戏剧》、《现代英文戏剧》,均为三学分。参见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文教·高等教育》,(第1063、1082、1095、1093、1085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③参见竹元规人:《1930年前后中国关于“学术自由”、“学术社会”的思想与制度》,《学术研究》2010年第3期。文中说:对于学术研究来说,1928年到1937年的近10年是近代以来比较稳定的发展期,所谓“胡适派”学人是1930年前后中国学术界的中坚,虽然有些对立的学人和学派,但他们能够吸引、提拔学生,动用国内外的种种学术资源,推动学术研究,影响力还是最大的。另参见章清:《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④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1924-1925年的课程表》,《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317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外国语文学系概况》,《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另参见龚元:《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清华传统”》,《戏剧艺术》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