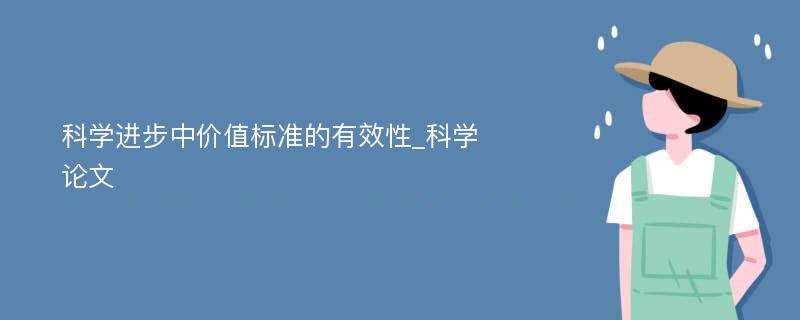
科学进步中价值标准的有效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效性论文,价值论文,科学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2)02-0103-06
一、科学进步中的价值因素
在历史社会学派之前的科学哲学中,科学的进步性不容质疑。在逻辑实证主义者和证伪主义者那里,科学的目的就是追求真理,科学的进步性就表现为新的理论不断积累(或新理论对旧理论不断否定)、并向真理不断逼近的过程。但是,Th·库恩(Thomas S·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和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科学方法多元论对科学的合理性和进步性提出了挑战,他们所提出的科学理论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限制了科学理论之间的比较,使科学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失去了意义。
L·劳丹(Larry Laudan)在《进步及其问题》中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重建科学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他在回避真理性的情况下把科学的合理性理解为科学的目的。他提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解题活动”,“科学唯一一个最一般的认识目的是解决问题”,“科学的进步就是解决越来越多的重大问题”(注:〔美〕L.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一种新的科学增长论》,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18~120页。)。即科学的进步性表现为旧的科学理论被功能更为优越的新的科学理论所代替上。之后,L·劳丹在《科学和价值》中进一步探讨科学理论的合理性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劳丹三角形”:科学的进步是科学理论、方法论规则、科学认知目的三者互动的结果。
就在《科学和价值》中,L·劳丹格外强调了科学的“认知价值”。他对价值(values)一词的使用给人们造成了一种不准确的印象:好像他把“价值因素”(特别是伦理价值因素)引入了科学进步问题,在我国甚至出现了深入探讨“科学进步中的价值因素”的研究方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提出了一种“科学→价值”进步模式。据称,这种模式“从根本上说就是指衡量科学是否进步的标准,在于科学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具体地说,就是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效应”(注:李建珊,贾向桐:《科学哲学的价值论转向——科学进步模式新探》,《南开学报》2000年第1期,第58页。重点处为原文所有。)。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科学哲学界就兴起了“科学价值论”研究,主要是从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文明、科学与道德的关系的角度分析科学对人类社会的价值(注:有关科学价值论的研究,可参见刘大椿,吴学金:《科学价值论》,《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第42~45页。)。“科学→价值”进步模式的提出无疑是科学价值论研究的一个延续。
显然,这种与人类利益相关的科学进步模式与科学进步合理性问题是大相径庭的。后者旨在研究新旧科学理论的关系,属于科学认识论问题;而前者则关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属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这种将主体价值直接嫁接到科学进步合理性问题中的研究是否符合科学进步问题的研究域是值得深究的——因为,如果不考虑概念之间的相关性、盲目地将认识论层面的问题转移到价值论领域,不仅会使该项研究本身缺乏有效性,而且将对科学进步合理性问题的进一步研究造成误导。因此,在科学进步问题上探讨以下两个问题是必要的:
1.这种关联是否具有有效性?
2.“价值”如何才与科学进步问题相关?
二、科学进步问题的认识论属性
显而易见,“科学→价值”进步模式中的“价值”指的是“伦理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也就是客体对主体的作用或效用”(注:我国的价值论(Axiology)研究者对价值大致持三种看法:1.价值存在于事物本身,是事物自身的属性;2.价值取决于人,是人的需要或欲望所指向的对象;3.价值存在于人(主体)与客体(事物)的关系之中,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的关系(可参见江畅:《论价值的基础、内涵和结构》,《江汉论坛》2000年第7期,第52~56页)。其中第三种“关系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同,本文采用的就是关系说,参见袁贵仁:《价值学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这一模式中的“科学价值”也就是“科学本身的社会价值,是科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属性对人的需要的有用性”(注:李醒民:《关于科学与价值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第44~45页。)。然而,科学的定义有三层含义(注:刘珺珺:《科学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
首先,科学是一种系统化、有条理、说明自然规律的理性知识(纯科学);(1)
其次,科学是一种包含更多内容的社会活动和驾驭自然的力量(应用科学);(2)
第三,科学是一种社会系统、社会建制,科学家在社会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起着其他社会角色所不能代替的作用。(3)
科学并不在这三个方面都涉及伦理价值,只有在物化过程(2)(科学理论转化成技术时)中才涉及伦理价值(注:当然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在实验的对象、手段、方式上也涉及伦理问题(受到关注的就是医学中的人体实验),但从本质上讲,仍属于技术问题,故本文不作专门论述。),在(1)中,纯粹的自然科学作为人类探索自然的知识体系属于K·波普尔的客观知识范围,它的表达方式是各个学科的基本理论,在这一层面上只有纯粹理论上的、或称认识论上的“认知价值”。“科学的伦理价值”和“科学的认知价值”具有不同的内涵,张华夏在《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中就明确了它们之间的区别,根据他的研究,科学共同体的价值目标是“追求真理达到知识增长最大化”,其行为规范表现为“知识公有、世界主义、无私利、独创性和科学自由”;而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目标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社会效用最大化)”,其行为规范表现为“功利原则、仁爱原则、公正原则、人类尊严原则”(注:张华夏:《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道德哲学的探索与反思》,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一般人在谈论科学价值时,通常是在说“科学的伦理价值”,而被认识论研究的科学价值则专指“科学的认知价值”。不注意区分这两种价值,就要造成观点的混淆和研究上的混乱。
例如,科学理论是否负荷价值(指伦理价值)、科学理论是否是价值无涉(value-free)或价值中立(value neutral)的,曾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争论。美国的格姆认为科学不是价值中立的,因为有些科学陈述蕴涵着价值判断,例如,“吸烟有害健康”或“使用高硫质煤炭是否会冒破坏生态环境的风险,这一点迄今仍未被充分确立”等陈述就涉及到了风险和安全概念(注:[美]格姆:《科学价值与其他价值》,王新力摘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年第4期,第16~17页。)。然而,格姆的观点是有缺陷的:他所列举的涉及价值的科学陈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实际上它只是事实判断,即“有科学根据的”陈述。严格说来,科学陈述只能是科学事实和科学定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的质能公式E=mc[2]、人类基因组图谱、化学公式等。格姆所列举的证据在原则上是无效的。张华夏已经指出:“……我们应该认识到科学作为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体系,它的基本定律,基本事实具有不依赖于人,不依人的价值观念为转移的客观内容。例如万有引力的定律的客观内容,即使在没有人类存在的情况下它们仍然起作用,而E=mc[2],这个客观规律本身,对于广岛的原子弹不负任何道义的责任”,“……科学规律本身,科学真理本身是价值中立的”(注:张华夏:《科学本身不是价值中立的吗?》,《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7期,第12页。)。他援引爱因斯坦的话说:“一切科学陈述和科学定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是‘真的或者假的’,粗略地说,我们对它的反应是‘是’或者‘否’。科学的思维方式还有另一个特征,它为建立它的贯彻一致的体系所用到的概念是不表达什么情感的。对于科学家,只有‘存在’而没有什么愿望,没有什么价值,没有善,没有恶,也没有什么目标”(注: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0页。)。在这一层面上,科学评价的标准只能来自科学内部。
从逻辑实证主义者到历史社会学派,科学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从来都是科学认识论问题。Th·库恩曾在《必要的张力》中提到过“价值”,他所指的也是科学理论的“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有效性”等内容,他尤其强调“……像精确性、广泛性、有效性等价值就是科学的永恒属性”(注:[美]〕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329页。)。由L·劳丹“引进”科学的“价值”指的仍然是科学的“认知价值”,仍然属于科学的理性范围。他在《科学与价值》的序中就明确指出:“这本书所要涉及的不是道德价值,而是认知价值;不是有关行为的伦理标准和规范,而是方法论的标准和规范。……我没有涉及上述与科学有关的那些伦理价值,因为它们显然没有在科学事业中占重要地位。”他对“认知价值”做了一个小注:“确切地说,人们如何把认知价值与其他非认识价值区分开来是十分复杂的。为了我在此分析的目的,我们可以采纳下面这种粗略和现成的特性描绘:如果某种特征描述了我们认为是‘好科学’的组成部分的理论特征,我们就可以把这种属性看成是一种认识的价值或目的”(注:[美]L·劳丹:《科学与价值——科学的目的及其在科学争论中的作用》,殷正坤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在劳丹那里,“认知价值”跟“认知目的”、“科学目的”是同义词,L·劳丹是在方法论层面提出了科学合理性的网状模型,他说,“如果某一系列理论使科学家们比以前要接近于实现或达到某种目标状态。那么(相关的那种目标状态的)进步就发生了。”
因此,科学在理论层面或者在认识论层面是价值无涉的,一般价值,特别是伦理价值,不能作为科学进步的标准。如果还有人认为“劳丹在科学进步的合理性问题上始终没能超出认识论领域是一种遗憾”,那就很可笑了。因为科学进步合理性本来就是认识论问题,如果超出了认识论,也就超出了该问题本身。
三、技术的负面效应与STS研究
“科学→价值”进步模式的目的是提醒人们关注科学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一模式所追求的是使科学的全部价值“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效应”,即“科学的每一次进步,每一种新理论、新学科的产生、发展及其应用,不仅能够是科学的认识价值增值(包括不断向绝对真理逼近,或者至少是能够部分地解决自身遇到的理论问题和事实问题),从而使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得到客观世界的‘认可’,而且应当是科学的认识价值、创造价值、物质价值、经济价值、人文价值、社会价值等彼此和谐不悖、共同发展(增值),从而使科学能够给人类以最大限度的终极关怀”(注:李建珊,贾向桐:《科学哲学的价值论转向——科学进步模式新探》,《南开学报》2000年第1期,第58页。)。这种提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这种模式所表述的毕竟是科学的应用问题而不是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它的研究内容已经超出了科学进步合理性问题的语境(context),进入了科学社会学的范围。
随着上个世纪核武器的使用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加剧,科学的道德问题被提了出来,诸如“核研究与核伦理”、“基因工程的社会责任”、“人体实验与医学伦理”、“环境保护与环境伦理”等(注:张华夏:《科学本身不是价值中立的吗?》,《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7期,第13~15页。),人们越来越关注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部门,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就是科学价值论(注:李建珊:《科学价值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重要课题》,《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第17~22页。)。科学价值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准确地阐明科学价值的含义、性质和特征,全面系统地分析考察科学的诸方面价值表现,深刻地揭示科学价值的发生、形成、实现、转移、增殖和再生产等运动规律,进一步探讨对科学的价值评价与计量的一般原则与方法等问题。”(注:李建珊,杨国勇:《科学价值论研究的背景、方法和意义》,《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第17页。)
那么,在科学价值论的研究域十分明朗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把科学价值论问题“嫁接”到科学进步的合理性问题上呢?
因为大多数人在指责科学家的工作时,却很少关注这样的问题:到底是科学还是技术负载价值?“科学”(science)是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以及一种活动或建制),它表明的是自然的规律,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科学本身也不能对人的价值观做出指导,爱因斯坦就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指出:“(科学)这个工具在人的手中究竟会产生出些什么,那完全取决于人类所向往的目标的性质。只要存在着这些目标,科学方法就提供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可是它不能提供这些目标本身。”(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范岱年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97页。)“技术”(technology)则是人们按照自身的需要对科学理论的应用——在人们的需求中必然包含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标准。显然,是技术而不是科学理论负载价值。正如H·莫尔在《科学伦理学》中所说的:“在考虑科学内在的价值体系——科学道德的时候,我一再说过,在伦理的意义上,真正的知识是善美的。在技术上,情况则完全不同。每项技术成就必须是有矛盾的,这就是说,它可能好,也可能坏,这取决于人们的观点或具体情况。技术必然是两面性的。……任何一项已知的技术分为道德上是好的或坏的,那要取决于人们所抱的目的,取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边缘条件。”(注:[西德]H·莫尔:《科学伦理学》,黄文摘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80年第4期,第97页。)因此,“科学的负面效应”这样的提法是不准确的,或许应该称之为“技术的负面应用”,或更确切地称为“人类对科学的滥用”。
在价值层面探究“科学的价值”实际上讨论的是技术的发明和应用问题。在技术负面效应的威胁下,判断“技术进步”的标准就是新技术是否能克服旧技术的负面效应、同时带来更高的正面效应。这也就是“科学→价值”进步模式所追求的“科学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科学在这种意义上的“进步”是以人类的价值观为标准的——毕竟对人类报以终极关怀的只能是人类自己,人类必须按照自身的利益去应用科学,但问题在于,这个“自身利益”是长远的还是暂时的,是针对人类社会的少数人的还是多数人的?
由此可见,“科学→价值”进步模式所表现的是科学的物化相对于人类利益的一种进步,这种进步的标准在STS研究中自有它特殊的意义,是有效的;但在科学进步合理性问题中,这个模式就显得勉强,实际上是无效的。
四、科学的进步在于知识的增长
科学进步合理性问题是科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L·劳丹的科学进步合理性模式的核心就是用“解决问题”代替“追求真理”,使科学进步表现为后继理论比原有理论解决更多的问题。L·劳丹在《科学与价值·跋》中曾再次申明:“人们可能会推测在这里概括出的方法论和价值论的批评模式能否适应于超科学的价值论,例如关于道的理论的价值论。就我个人而言,我抑制了想描述在关于认识价值的争论和关于道德或政治价值的争论之间显而易见的一些类似之处的企图。其理由很简单:进行科学论战不会同时又是政治或道德方面的论战,反之亦然。”(注:[美]L·劳丹:《科学与价值——科学的目的及其在科学争论中的作用》,殷正坤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179页。)这进一步表明了L·劳丹在Th·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之后对人类理性的恢复和强调。
科学的应用效应问题纵然引起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关注,但是,在纯粹科学理论层面,追求确定性、精确性、简单性、一贯性、充足理性(K·波普尔语)毕竟是从事具体研究工作的科学家的信念——即使道德层面,对科学的要求也是如R·K·默顿所提出的“科学的规范结构”(普遍性、公有性、无偏见性、有条理的怀疑精神等)。科学毕竟是一项理性的事业,科学的进步在于整个人类知识的增长,推动科学进步事业的只能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最后需要声明的是:本文并非刻意挑剔某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毕竟衡量科学进步的模式不是唯一的,进步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笔者只是就学术研究的方法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每一项研究都有其确定的问题语境和解答方式。有效的研究应该是有效的提出问题并在该问题的语境内做出合理的解释。科学哲学中所探讨的科学进步的合理性问题始终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是哲学家有意识地对人类知识增长和理智发展的反思,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思考不能脱离开认识论的语境,否则就要妨碍研究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