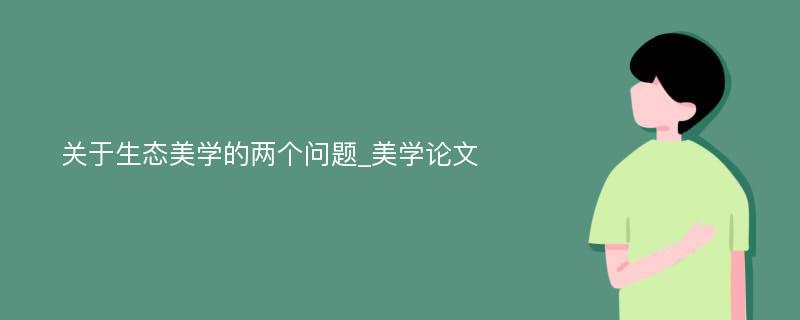
对生态美学的两点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两点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学界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继实践美学、生存美学、生命美学、体验美学、超越美学等之后,生态美学作为一种新的美学观念,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迄今为止已召开过四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发表了数量不菲的论文,美学界再度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正如一些学者所惊呼的:“美学的生态学时代已经来临”。生态美学的倡导者们都在满怀激情地为这一正在降临的崭新时代祝福。应该说,生态美学的登场确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人类思维长期被禁锢在主、客二分模式下而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在把自然当作人的对立面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人类的行为愈来愈变得毫无节制和缺乏理性,并且正在一点一点地毁掉自己赖以生存的物质根基: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物种数量逐年下降……在这种大背景下,生态学以及从生态学角度重新审视美学的“生态美学”的出现,正体现了学术对现世人生所给予的深切关怀。
但是,生态美学自身却存在着一些它本身无法克服的巨大缺陷,这些缺陷不仅将导致它很难把研究纵深地进行下去,更难以形成一门严谨、成熟的学科。所以,我们应该对它抱有审慎的乐观态度。
生态美学最重要的哲学——美学原则是“生态中心主义”。其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地球与人的关系,不是什么‘人类中心’,而是地球对于人类具有一种本原性的地位。也就是说,人类是由地球所构成的自然系统中产生出来的,地球是人类之母。”“其次,人对于地球和自然有一种依存性。这就是生态学中的生命链的客观规律。”“再次,人类与地球及自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一种有机的整体构成。这是生态中心主义哲学观最重要的理论观念,是其区别于主客二分的传统思维模式的最基本之点。”[1]
生态美学的倡导者们认为,当今人类正面临着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正是传统的、旧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观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这种哲学观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把自然和人对立起来看问题,因此总是把自然看作是人的对立物和认识的客体、支配征服的对象,人是宇宙的中心,是赋予自然事物以意义的主体,自然只是被动地供人进行研究的客体,只是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资料来源才有意义。生态美学因此号召进行所谓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重大“转向”,主张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观来代替“人类中心主义”哲学观,以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来代替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并加以解释说:“这种有机整体生态世界观的重要特点是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 tat)的观点引入整体论哲学观之中,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分裂的关系,而是我和你两个主体间平等对话的关系。”[1]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颇富创新性的美学观点。
第一,自然本身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按照传统,自然美是指自然界中自然物的美。这一定义,对生态学时代的自然美同样适用,但到底什么才是‘自然物的美’,新与旧的解释却大不相同。在传统意义上,由于自然内在生命的缺失,所谓‘自然物的美’就不在自然本身,而在人的观照和意义的赋予;它只涉及事物的感性形式,而不涉及内容。但在现代生态学的语境中,由于自然对象拥有独立自在的审美本质,所以它的美就首先是‘美者自美’,然后才是‘因人而彰’”。“当现代生态学将生命属性赋予自然,也就等于赋予了自然独立自在的审美本质。由此,自然美在传统美学背景下无法独立自存的难题,也就在生态美学语境中被有效破解了。”[2]
第二,为挽救人类日益失落、濒危的美感,把人从当前的非审美化生存境遇中解救出来,应该提倡对自然的部分“复魅”。“所谓‘自然的复魅’不是回到远古落后的神话时代,而是对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统治下迷信于人的理性能力无往而不胜的一种突破。主要针对科技时代工具理性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过度夸张,对大自然的伟大神奇魅力的完全抹杀,从而主张一定程度的恢复大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潜在的审美性。”“人类应该恢复对大自然的神圣的敬意”。[3]
生态美学的上述主张和认识有着明显的理论上的偏颇和不足,笔者逐一对此提出质疑和批评。
一、由“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切换,必然会导致美学中“人”的缺失
首先,用“生态中心主义”来替代“人类中心主义”并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彻底转型。事实上,“人类中心主义”也好,“生态中心主义”也罢,最终的旨归都还是要落实到人的身上去,假如生态哲学观真的有志于引领人类摆脱目前困境,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话。作为人类面对危机时的一种可能性的应急反应方案而被设计出来的生态哲学观,其最终目标仍然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人类自身的利益,人自身仍然是被优先考虑的对象,不管如何进行表述,这一根本目的是抹杀不了也掩盖不了的。“人们现在能够接受的只是用合理的人类中心主义取代不合理的、无限制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亲和态度是为了人自身的价值,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则是换位思考的习惯导致的。”“对于人类来说,彻底的思维转换是不可能的。”[4]所谓“生态中心主义”也无非是这种简单的换位思考的结果,而人类之所以要这样换位思考,正是因为人类开始意识到我们一贯对待自然的方式或许将会导致对自身的严重不利,威胁到人类整体的生存,因而有必要重新思考并加以调整和改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所谓“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而言,其实并非是一种真正的思维方式的转型,而不过是对同一个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一种便利的解决方式而已,是一种更加理性的选择,体现了人们试图用一种更合理的“人类中心主义”来取代那已经逐渐变得不合理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良好意愿,人还是被考虑的终极目的。这也正是当前倡导生态哲学和美学的人们一再为自己面临“反人类”的种种指责时所作辩护的主要理由。
其次,生态哲学观虽然以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为己任,主张“生态中心”,其实也仍然是这种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产物。它仍然明晰地意识到人与其赖以生存的周遭环境是有区别的,并且分别构成了问题的两极,只不过以往的哲学观凸显了人这一极的重要性,而它如今要强调的则是另一极——整体的生态系统(包括人在内)而已。在这种强调中刻意隐藏和消解了人所具有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单纯突出了人与外物的互相依赖性和起源上的无差别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中人的形象和地位的黯淡和模糊。生态哲学的这种企图其实是徒劳的。表面上看来,这种包括人在内的“整体生态系统”似乎弥合了人与自然的差别,而其实它仍然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那个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已,不管我们把它叫做“生态系统”也好,“生物环链”也罢,地球和自然对人的本原性、人对地球和自然的依存性其实早在“生态中心主义”哲学观出现之前就已经是人类不言自明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了。况且“生态中心主义”这种只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性而忽略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企图借此来克服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局限,也有掩耳盗铃之嫌。我们可以承认人与其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包括自然中的其他所有物种)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的生态系统,但在任何一个系统中、任何一种关系中、任何一个问题的论域中,都有层次之别,都有主次之分,纯粹的、绝对的、不分主次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否定人与自然的差异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与辩证法相矛盾的。人作为一种自为的存在,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显然有别于其他那些仅仅自在存在的物种,尽管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的物种都具有古老的、共同的起源,而且彼此之间相互依赖,但人毕竟已经不完全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了。“生态中心主义”所憧憬的通过“主体间性”观点的引入而将会建立起一种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对话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
再次,“生态中心主义”所提倡的这种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我和你两个主体间平等对话的关系”,把自然视为与人对等的、地位相同的主体,这种观念被引入美学领域后,类似“自然本身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之类的观点也频频出现,甚至宣称美是可以脱离人而存在的,所谓“美者自美”。言外之意即是“与人何干”?站在人的立场上,以人的身份,从人的角度来被探究的美学现象,最终却被断定为与人无关,这可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不禁要问:何谓“美者自美”?与人无干的所谓“自然独立自在的审美本质”又如何得以呈现?假如真是这样,美是与人无关的或者说美可以与人无关,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去研究它?如果这种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自然之美最终仍需要人来发现和彰明,那就证明它依然离不开人,对人仍然有依赖性。自然在与人发生审美关系之前它只是生命体的存在而已,不具有审美意义。至于各物种内部存在“审美活动”或不同物种之间可以相互审美的说法,我们想请教:它们这种审美是如何进行的?这种明显荒谬的主张将再次导致美学理论退回到诸如“美先于人类而产生”、“美在客观”等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遭到批驳的观点上去。
可见,作为生态美学重要的哲学——美学原则的“生态中心主义”不仅自身存在诸多缺陷,而且从生态学这种新的视角来研究美学问题,尤其是自然美的问题,往往过高地估计了自然与人关系中的自然的地位,并且因为刻意地消解人所具有的主动性和能动性,造成了理论中的人的形象和地位的黯淡和模糊,很容易得出所谓“美者自美”这种完全脱离人而谈美的新奇结论来。由此必然会导致美学研究中人的退位和缺失。而当人在进行不涉及人的审美言说时,这种言说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毫无理性也毫无意义的痴人呓语了。
二、“对自然的部分复魅”容易走向忽视理性的极端而且缺乏可操作性
自然的“复魅”是与“祛魅”相对而言的。“所谓‘魅’即是远古时代科技不发达之时,人们将自然现象看作‘神灵的凭附’,主张‘万物有灵’。远古的神话就同这种魅紧密相关。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现象有了更多的了解,不再有神秘之感,这就是‘自然的祛魅’。”[3]就目前情况而言,人的理性能力确实无法完全认识和掌握整个世界,科技时代的工具理性确实也正在一点一点地消灭着人对美的感受能力,人愈来愈习惯于对周围的事物进行物理的解剖、知识的验证和逻辑的推理了。理性认识的能力被当成了一把锋利无比的手术刀,无情地解剖着大自然这具千疮百孔的病体。是需要彻底改变这种现状的时候了。然而,在此过程中难免矫枉过正,势必会对理性在美的建构中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也一笔抹杀。
在西方,传统上的美学是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的,美学的研究也相应地被纳入到哲学的逻辑和思辨的轨道中来进行。如果承认美与人有关,美是人对外物的一种审美评价关系,就该承认,人对美的感受能力是一个历史地生成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和理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科学的进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使人终于有闲暇和有条件去专事不带来任何物质利益的“审美”了,人的头脑也因而日益变得敏锐和复杂了。其次,科学和理性帮我们逐步解除了蒙昧的束缚,我们的美感的发生一定程度上源于我们对外界自然的相关知识,自我保存的本能促使我们总是在确知这异己的东西不致威胁到我们的生存,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也就是只有在自然进入到我们的认知视野当中时,美感才有可能发生。尽管在具体的审美活动中并不总是需要知道这对象是什么(那是因为理性提供的知识早已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广阔的领域)。“尼科尔松指出,正是因为随着17世纪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发展,以及随后发展起来的地质学和地理学,人们对自然世界有了新的认识,自然的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才使得崇高的观念在对自然的欣赏中有了自己的位置。以前被认为只适用于对神的惊奇和敬畏,现在成了对似乎无限的自然世界的审美反应。而且随着自然科学的持续发展,所有的景观都将变成了审美欣赏的对象。”“科学知识和它对自然的重新描述,使我们在以前看不见美的地方看见了美,范式与和谐代替了无意义的杂乱。”[5]所以科学和理性在美的建构和生成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现实的审美过程中,理性也在发挥着作用。“美感虽是一种感性经验,却有理性基础,这个基本思想是首先由康德特别提出来的。”[6](P363)他以此来说明经验的、个别的审美判断为何会具有普遍性的道理。虽然旨在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而且方法和结论均是错的(他把这种普遍性完全归结为一种主观的假定),但这种思想本身却是正确的。正如蒋孔阳先生所言:“要知道,审美活动本身就是人类思维活动中的一种,对于美的认识常常是以思想上的认识作为根据。”[7](P76)也就是说,审美活动并不完全排斥概念的活动,理性认识确实常常在左右(或至少是干预)着我们的审美,他还为此特意举了一个通俗的救火的例子来作说明。
但是在生态美学的倡导者们看来,科学和理性似乎成了当今世界万恶的渊薮。科技和理性所带来的工业文明破坏了神话以及神话赖以产生的神话思维。“如今的孩子看到夜间的月亮不会再想到吴刚、嫦娥、玉兔、桂树,想到的只能是美国人制造的宇宙飞船。神话不再产生,神话的神秘性与感召力都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关于神话的科学研究。20世纪初,马克思·韦伯(Marx Weber)曾把近代思想的这一轨迹形象地概括为‘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8]不仅如此,技术理性的泛滥导致现代人变得越来越缺乏想象,越来越工于算计,越来越不讲操守、不讲信誉。日益膨胀的贪欲正引领着疯狂的人们肆意地糟践着原本宁静秀美的江河山川,“包括无节制的工业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农药对土壤的破坏与污染,工业烟尘和汽车尾气对大气的污染……等等。凡此种种都直接威胁并破坏人的存在状态,使人处于‘非审美化’。”[9](P16)于是人们开始呼唤“自然的复魅”(the enchantment of the world),试图重新恢复自然的神圣性和神秘性,以此激活人们那业已麻木、僵死的对美的感受能力。但由此可能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将是感性体验被过度拔擢,理性对美的构建作用不同程度地被忽视。
而尤为关键的一点是,这种对“自然的复魅”也仅仅只能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丝毫不具有审美上的可操作性。因为对自然的逐渐“祛魅”是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最初,人类的远祖与自然浑然一体,它还不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而仅仅只是一种自在的存在,不是自为的存在,慢慢地,劳动和直力行走促进了人脑的发育,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和周围世界是有区别的了,也正是从那一刻起,人类开始了对外在于自己的周围世界的思考和探究。随着这种思考和探究的逐渐深入,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和丰富,人类的知识就逐渐地积累起来了。凡是我们了解得多的事物,我们对它的敬畏就会少一些,待到人类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思维完全能够合理解释某种自然现象时,我们同时也就失去了对这种自然现象的神秘感,这就是所谓的“祛魅”。人类正是通过对自然的不断“祛魅”才逐渐地摆脱了蒙昧和迷信的困绕而一步步走向科学、理性和文明的。现在要对自然“复魅”,究竟该如何“复”?难道是要重新返回到远古洪荒的蒙昧和迷信中去吗?尽管有的学者对“复魅”作出了自己的理性的解释,表达了理想的意愿,但是对于如何“复魅”却难以给出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如果进一步再考虑到那些大力提倡对自然进行“复魅”的国外理论家们许多人都具有的宗教神学家身份(比如美国的大卫·格里芬等),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这种主张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另外,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涉及到如何对待当代科技进步的问题。虽然全球范围内自然环境的大规模破坏同科技理性的泛滥、工具主义的盛行和科学技术的滥用有直接联系,但更加毫无疑问的是科技还会持续不断地进步,而且从根本上说人类是需要这种进步的。只要科技不断地进步,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就会不断增加,也就必然会伴随着对自然的“祛魅”进程的同步发展。“自然的复魅”到底如何操作才能既不使人复归于蒙昧乃至重新被迷信所主宰,同时又能保证不断发展、进步的科技真正能为全人类造福,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见解是明显缺乏可操作性的。所以,如何做到“自然的部分复魅”从而有利于生态美的生成,这也是当前生态美学研究亟待作出回答的问题。
所以,在生态美学的建设中,一定要谨防将生态与科技对立,从而走到排斥科技、排斥现代化的极端这种趋向。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在一篇名为《我的信念》的文章中曾经这样写到:“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增加它崭新的远景。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美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其发展和完善始终离不开理性认识的支撑,具体的审美活动也并非全然与理性无关,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对自然的“复魅”这种主张,除了引诱人抛弃审美活动中的理性因素并使人重新拜伏在上帝的脚下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出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目前被人们所倡导的生态美学仍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缺陷,其具体主张也多半不具有可操作性,至少在目前尚不具备形成一门严谨、成熟的人文学科的条件,仅仅只能算是一种新的、视角独特的美学观念而已,在学科构建方面,还需假以时日,仍然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