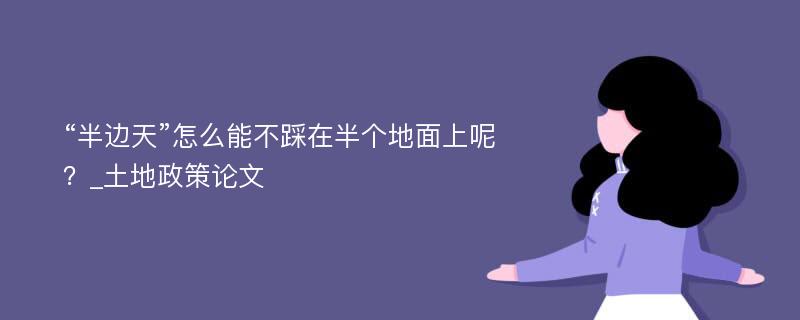
“半边天”如何踩不着半边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半边天论文,半边论文,不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象——为什么没有妇女的“立锥之地”?
徐小兰,四川省乐至县天池镇三里九村三队村民,1998年与本乡的公办教师张某结婚,婚后一直在女方的原籍居住,村里以她结婚为由,强制非法收回其责任田。
徐小兰两岁的孩子也没有土地,而且也没有权利享受国土局征用土地的生活安置补偿费。生活没有来源的徐小兰找过镇领导、县委、县政府等部门,但是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我们母女二人失去的不仅是土地,更失去了做人的人格与尊严,听说我们县城郊区几个村二十多年来像我这种情况的有上千人之多,这叫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以农户为单位的自主承包经营权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是,土地在承包期内不调整的政策在现实的操作中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在承包期内新增加的人口(包括新婚后到夫家落户的农村妇女、男到女家落户、新出生的婴儿)容易失去土地或者是无耕种土地,这部分人的权益没有办法得到充分保障,在这些人中尤以妇女的土地权利问题最为突出:
婚前——不分、少分。有些地方对未婚女性进行“测婚测嫁”,不分土地或者是少分土地;有的未出嫁女到一定的年纪虽未出嫁,但在土地调整中却不分给她们土地,甚至她们已有的土地也被强行收回。
婚后——失去土地。我国妇女目前主要是以“从夫居”为主,婚后妇女多是到男方家落户,许多妇女因婚姻流动而失去土地。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张林秀教授等最近完成的一项全国六省市1200户农户调查的结果反映出,50%以上的农户所在的村从分田到户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土地的小调整,而只有6%的农户认为媳妇嫁进来以后能分到土地。
对于“农嫁非”妇女,即是农村妇女与非农业户口的男性结婚,但男方父母是农业人口,女方失去在娘家的土地,在嫁入地即夫家不能够落户分田;另一种情况为,男方及其父母都是非农业人口,女方所在地又不予以落户、分田。有的地方女方所在地要求交纳一定的费用,否则就不允许落户,而且所生的孩子也应该交纳,孩子在14岁之前只享受半个村民的待遇。
离婚、丧偶——收回土地。男方村里将把女方户口迁回娘家并收回责任田,而女方娘家也不给分地;离婚后前夫再婚,对于前妻和后妻村里只给其中一人落户分地;丈夫死后,村里只保留其子女户口、田地,而要将女方户口取消,收回土地。
症结——法律和政策缺乏性别关照视角
法律和政策在涉及妇女土地权利方面不一致。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秀认为这是造成一些农村妇女无“立锥之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宪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各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婚姻法》和《继承法》又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突出强调了性别平等。《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妇女的地权在结婚、离婚后受到保障,然而规定并没有说明提供这种保障的办法。而根据《土地承包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的土地承包者之间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专家分析说,土地的分配和再分配都直接取决于村社的决策,而村社依然保留着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财产分配。这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怪圈: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在有关土地分配的决策中,往往以乡规民约为借口侵害弱势人群特别是妇女的权利,与国家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和其他法律政策相违背。
法律与政策往往缺少社会性别视角。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朱玲认为许多政策从表面上看是中性的,没有明显的歧视妇女权利的条款,但是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实的社会性别利益关系,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给妇女带来不利。现行的土地承包政策是以家庭为承包单位,虽然是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利,但是没有充分考虑不同性别利益上的差异,忽视了在承包期新增人口,特别是大量的由于婚姻而流动的农村妇女的权益。另一方面,没有明确家庭中个人的权利,而中国农村家庭长期普遍实行的是“从夫居”形式,一旦妇女的婚姻不同于传统的模式,如离婚、未婚以及男性到女性家落户等,而政策中又没有相关的明确规定,这部分的妇女就被置于法规政策的保护之外。
有关法律政策缺乏可操作性。有些专家们认为,我国现有的规定不明确,不能够及时有效地维护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土地权益。如对农用地使用权属性缺乏明确的界定,究竟是物权还是债权不清楚;现行法律允许有限制的土地调整,使得出嫁妇女有可能因为出嫁而失去土地;尽管倾向于把农用地使用权界定为家庭共有财产,但是没有进一步按民法通则的规定界定其为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
对策——将个人的权利从家庭和婚姻中剥离出来
立法原则上要实现两种革命:将个人权利从家庭中剥离出来,将个人权利从婚姻中剥离出来。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林志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经济法研究室研究员陈明侠等认为,以往中国人在家庭中个人的权利往往被埋没在家庭利益中而少有分离,女性的权利更是被埋没在婚姻关系中,这就使得女性在家庭中缺乏独立性,改变这样的观念将有利于我国的立法与执法工作。在土地权问题上,初始权男女不平等,女性少地或无地的状况加深了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对丈夫的依附性;忽视了个人的权利,也使得家庭成员在处分和使用土地权时受到限制,并影响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安全。在法律制定中,还要正视法律面对的是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现实,在制定具体的法律条文时应具有性别敏感性。如关注婚姻带给妇女土地权与利益的得失现状,关注女性婚姻与土地权实现程度与男性之间的差异问题。法律的制定应具有可操作性,如应当从立法上解决以“户”为单位承包和将土地权利保护到“个人”的统一与衔接。同时应建立相应的司法救济途径,以解决土地所有权与用益权之间的纠纷,使村民状告村民委员会的案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得以解决。
应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定为物权,以有利于保护土地权人。
土地承包关系以“户”为单位,以“个人”为基础,只有将土地权落实到每个家庭成员身上,才能真正保证权利的实现和效益的发挥,而将以“户”为单位的承包权利落实到家庭中的个人成员身上,是土地承包法与物权法的统一与衔接所遇到的问题。美国农村研究所北京代表处李平建议,在即将出台的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中明确规定属于家庭共有财产的农地使用权由家庭成员按份共有,明确规定家庭承包合同和经营权证上注明所有家庭成员的姓名,并由所有具有民事能力成员的签名或盖章,明确要求对农地使用权进行登记确权。此外,应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属于夫妻共有的农地使用权按份共有,以利于解决实际中的问题。
全国妇联的专家认为,妇女结婚的,在承包期限内发包方不应该收回土地,妇女离婚的,已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限内应该依法受到保护,可以作为家庭财产处理。承包期内不调整土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今后出现人地矛盾,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开发新的土地资源、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二、三产业等途径,用市场调节的方法解决,不宜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去调整承包土地。
专家还建议有关部门像婚姻法修改征求全民意见一样,全文公布《物权法》以及《土地承包法》的草案,听取与土地权利有直接关系的人群的意见,使法律的制定有更多的操作性,以利于更好地保护妇女的权益。
标签:土地政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