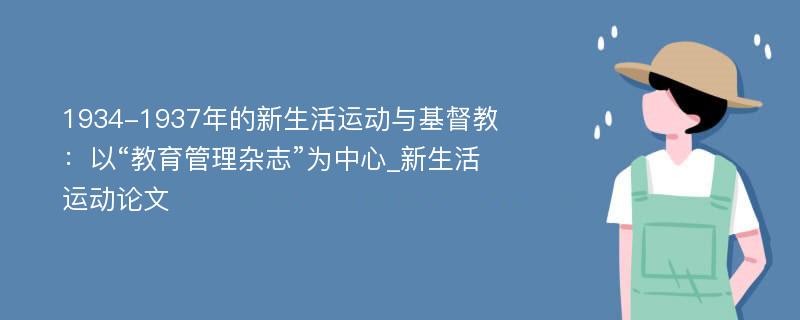
1934-1937年间的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以《教务杂志》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教务论文,新生活论文,年间论文,杂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7)04-0065-82
一、引言
在始于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中,政治权力的关心到达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这次运动将精神当作社会动员的根本力量,把日用常行细节的变化看成风俗移易、国家复兴的开端。参与运动和接受动员的不仅有政府官员和平民,还有基督徒这一特殊的群体。本文所关注的,正是基督教与新生活运动的距离、合作以及二者应对形势变化的方式和转变。随着1937年抗战的爆发,新生活运动转入了性质不同的新阶段。由于该阶段涉及的问题和材料很多,本文暂且将讨论的时期限于1934-1937年之间,希望能借有限的篇幅做些深入的思考。
关于本文讨论的主题,以中英文形式发表的研究都有不少,其中一些由于条件所限,暂时未能见到①。已见关于新生活运动的专著有关志钢的《新生活运动研究》②,书中对新生活运动缘起、发端、鼎盛、转轨、衰败的全过程都做了介绍,着重探讨了新生活运动的思想基础和官方对新生活运动的阐释与组织结构,在批评新生活运动的同时,肯定了运动在卫生等方面的成绩以及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并将新生活运动与后来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联系了起来。温波的《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5)》③对南昌的新生活运动做了专题研究,使用了当时江西的报刊与新生活运动参与者的记录,探讨了民间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使新生活运动得到了更具体细致的呈现,该书从哈贝马斯等学者关于合法性的讨论出发,认为由于缺乏民众的有效认同,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无法通过新生活运动建立。王晓华的《“模范”南昌》则以图像的方式呈现了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的情形④。C.W.H.Young的《江西新生活》⑤出版于1935年,由宋美龄作序,主要从在原苏区清除共产党影响的方面来看待新生活运动,并有一些采访和记录,可以看作当时国民党官方的声音之一。译著方面,易劳逸《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流产的革命》⑥中对新生活运动有所涉及,主要讨论了新生活运动与“蓝衣社”、法西斯主义的关联。柯伟林(W.C.Kirby)的《德国与中华民国》⑦也从中德关系和法西斯主义的角度研究了新生活运动。与新生活运动期间基督教团体活动有关的译作有邢军《革命之火的洗礼:美国社会福音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919-1937)》⑧,书中研究了社会福音在中国的一段历史,其中的第五章和第六章更对战争阴霾下的基督教国际主义、青年会与新生活运动以及社会福音转向革命福音的过程做了探讨。相关研究中常引用的一本英文著作是汤森(James C.Thomson,Jr.)的《当中国面对西方》⑨,该书研究了民国时期美国改革家的活动,涉及传教士牧恩波(George Shepherd)的生平以及基督教青年会面对新生活运动合作号召时的两难。书中对基督教与政治运动互动有详细的讨论,作者对新生活运动的看法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集中研究新生活运动的中文论文的数量不算少,在《重建合法性》一书的前言中,温波对中文论文的情况作过较详细的回顾⑩。从这些论文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如顾晓英的《评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1934-1949年)》(11)认为,新生活运动奴化人民,意在加强统治,有虚伪性、落后性和反动性,但对战时新生活运动做出了有保留的正面评价。而台湾学者邓元忠对运动评价甚高,他认为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为复兴民族而提出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掩护的抗日训练(12)。两种评价表现出两种叙述和理解的方式,也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影响(13)。后来的学者对此做了反思,如关志钢认为,通过具体细致分析,人们就会看到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确有值得肯定之处,而抗战期间的新生活运动则做出了相当的贡献,许多学者认同的“新生活运动失败论”是过于简单了(14)。除此之外,温波和李小萍还注意到了新生活运动研究中地域研究的重要性(15)。关于新生活运动与传教士这个问题,张庆军、孟国祥的《蒋介石与基督教》(16)一文,从蒋介石个人受洗、号召传教士配合新生活运动的行为出发,提出蒋介石倾向于基督教的背后有寻求英美支持的动机,亦涉及传教士对新生活运动的热情参与。另有汪进春的《浅议传教士与新生活运动》(17),可惜并不能算作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刘家峰关于黎川实验区的研究文章(18),尽管并未直接涉及新生活运动,但对看待政教关系这一问题是有帮助的,牧恩波牧师先在黎川实验区领导实验,后在新生活运动中担任职务,如果考虑到二者的关联,该文就更有参考价值了。
英文论文方面,陆培涌(亦名陆品清,Pichon Loh)于1970年发表的文章(19)研究了蒋介石的信念基础,也许是因为文化背景的关系,该文对蒋介石与基督教的讨论显得尤为突出。该文认为基督教对蒋介石来说,是宗教,是西方文明的代表,也是能够转化为工具性力量的社会组织,而且基督教整体上的改良主义手段也对蒋介石夫妇有着吸引力。文中也对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的关联进行了讨论。德里克(A.Dirlik)于1975年发表文章讨论了新生活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认为新生活运动将传统思想与现代化要求都当作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通过将“现代”限制在个人行为上、对道德进行工具化的阐释来避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吸收二者“好的”方面,但并没有考虑到或可以避免谈论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冲突的部分(20)。韦思谛(S.C.Averill)在《行动中的新生活》(21)一文里通过研究政府在江西的政策与机构,提出当时的国民政府是现代的改良主义政府,而运动的失败有政府行政不力的因素在起作用,除此之外还应归因于本地精英力图控制和扩大权力的行为。
1934-1937年间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22)是本文使用的主要一手史料,作者希望能借助这一重要的传教士刊物来讨论基督教(主要是新教)教内人士对新生活运动的评论和参与。《教务杂志》上的文章并不全是传教士或教内人士的作品,但由于该杂志由传教士编辑并在传教士中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们或能从杂志选择的文章及报导中看到一些具代表性的观点。《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23)是官方阐释新生活运动材料的主要来源。其他材料还包括这四年间的《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时人言论等等。本文将借这些材料来探讨政治与宗教的互动,以及二者在战乱背景中的变化。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这两种异质力量的结合,除了如蒋介石、宋美龄是基督徒这样的个人因素外,还有赖于两种力量对运动目标的理解。在对新生活运动目标有了部分认同的基础上,基督教力量经历了从旁观到参与的过程,并同运动一起在面对战争挑战时做出调整和变化。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描述起来似乎简单,但从历史材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内在和外在的斗争,可以想见历史上挣扎的痕迹。文章涉及的时段只是四年,但这四年里两种力量的合作、距离、挣扎、转变,以及这个过程中引发人们思考的政教关系、社会运动动力、宗教团体功能、战争与和平等问题,则未尝不具有普遍性。本文所希望的,正是从这一段特殊的历史中,看到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
二、理解目标:关系的基础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上作《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说,新生活运动正式开始。
关于新生活运动指向的说法颇多,这同运动目标不甚明确固然有关。对于新生活运动,那些或在官方文件中显而易见、或在实际过程中逐渐显露的目标,基督教方面有自己的理解,而理解这些目标的方式,则成为基督教与新生活运动关系的基石。
《新生活运动纲要》关于新生活运动主旨(目的)有(24):
新生活运动者,我全体国民之生活革命也。以最简易而最急切之方法,涤除我国民不合时代不适环境之习性,使趋向于适合时代与环境之生活。质言之,即求国民生活之合理化,而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为基准也。
又有:
若欲改善今日国民之生活,必自纠正其乱邪昏懦,陷溺沉迷之风始。此新生活运动之所以为今日立国救民之要道也。(25)
根据这种解释,新生活运动指向的是转移风气、立国救民,并以“礼义廉耻”这一中华固有德性为基准进行道德塑造。运动的进行,则“端赖国民人人自觉其需要,发乎人,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能修其身,所以立一家之风;能治其家,所以立一乡之风,与政教相辅”(26)。由此我们很难发现新生活运动与传教士的合作基础,而看到得最多的,还是传统文化、儒家修齐治平之道的词汇。《教务杂志》关于新生活运动的第一篇社论中,就有这种理解方式的痕迹:“看起来中国并不会完全西方化,但她会以现代的方式努力找到自我……中国自身的伦理意识正在复兴,有点吊诡的是,它叫做‘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表达了中国人的信念……中国人将按照自己的观念来使用他们从西方学到的东西。”(27)这种理解方式甚至会引发这样的困扰:“许多人强烈感到,唯一的内在困难,在于这一运动有意识地依靠中国传统智慧……从这点上看,中国教会在这场认真美好运动中的合作,就会是异教与基督教……的合作了。”(28)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复兴中国传统这一点上,基督教与新生活运动并没有太多的共同点。但如果把运动的目标解释为道德的复兴与人格的重塑,新生活运动对教内人士就有了更大的吸引力,基督教与新生活运动的可比较性也从而被发掘出来:“新生活运动的推行者已经正确地号召人民尽最大的努力来显著地改变生活了……基督徒相信,人们可以祈求神的帮助。我们需要神的引导与智慧来帮助我们努力实现目标”(29)。对于礼义廉耻,也有基督教的四原则与之对应:“新生活运动的礼义廉耻四原则在可理解性和可行性上都不如绝对诚实、绝对纯洁、绝对有用、绝对之爱这样的标准……我确信希望能过这样一种生活的基督徒都会尽力同新生活运动合作。”(30)这种说法虽然仍将基督教放在高于新生活运动的地位,但比较本身显示出确认二者相关的积极态度。
显然,新生活运动并不止于传统和道德的复兴。《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就包含着其他的理解方式。在这个标志新生活运动开始的演说里,蒋介石举了德国为国家复兴的最好先例,认为“虽然他们没有武力,但是还不到十五年功夫,居然就能够复兴起来,和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并驾齐驱”(31),而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国民有高尚的智识道德。他又举日本为例,认为他们生活中洗冷水脸、吃冷饭等习惯使得生活军事化了,所以兵强。以这种迅速复兴作为参照,蒋介石提出,新生活运动,“简单的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32)。这些言词常为关注新生活运动中法西斯成分的作者所引用(33),而在当时的基督徒中,也存在着对“军事化”说法的隐忧。《教务杂志》1937年5月所载的一次讨论会记录里,E·S.Yu表示:“想一想运动开始时的目标吧。它的目的在于让整个民族军事化。在我看来蒋介石将军定下这个理念是很不好的。我们需要以和平为目标的新生活,而不是以战争为目标的新生活。”(34)对于新生活运动的发起和领导者来说,动员人民不啻实现运动目标的根本途径甚至目标本身,而有了德日迅速复兴的先例,加上内忧外患的政局,新生活运动的“军事化”特征是难以避免的。但运动中法西斯、军事化的因素对于希望独立于政治控制、倾向于和平主义的基督徒而言,并不可能是合作的动力。
对新生活运动阶段目标的理解对基督教在新生活运动中的活动同样重要。自1935年4月始,新生活运动“渐由于‘规矩’、‘清洁’之初步时期,而入于生活之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进一步推行之时期”(35)。总的来说,战前新生活运动都注重礼义廉耻基础上的人格培养。在“规矩”、“清洁”一期,教内有这样的支持声音:“即使这场新生活运动并没有基督教的标签,但运动想在人们身上培养的正直、良知、公正、慈善这样的古老美德,从本质上说,与我们希望在基督徒生活中见到的美德是很相近的。中国基督教会的使命是尽一切可能向人们展示基督那样的基督教生活方式。这样人们也许就能经由对基督复活的信仰而拥有获得新生活的力量。”(36)文中还提到了蒋介石对传教士和牧师团体清洁、简朴、规矩生活的赞赏。教会对于社会的“规矩”、“清洁”,并没有排斥的理由,但似乎也难有深入的参与。教会并不满足于新生活运动浮于表面的工作,随着新生活运动的深入,传教士对新生活运动还有更多的理解和反思。
小詹姆斯·汤森以新生活运动为“儒家、法西斯、日本和基督教元素的混合体”(37)的说法不无道理。此外,传教士与新生活运动关系的前提还包括了对新生活运动指向的另一种理解,即应付共产主义运动对国民党政权造成的威胁。尽管这种指向并不明显表现在新生活运动文件上,但还是能从其他地方显现出来。
新生活运动的开始与蒋介石在江西指挥“围剿”不无关联。宋美龄在《江西新生活》的序中说:“从‘共匪’手中收复的地区道德沦丧败坏,这促使蒋介石大元帅发起了我们现在知道的新生活运动”(38)。而口气颇官方的《江西新生活》不仅时时将新生活运动开展后与共产党政权下的人民生活对比,还花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反共斗争(39)。新生活运动之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及采用改良手段,正与共产党之使用外来的共产主义思想与激进革命的手段相对照。教内人士对新生活运动的理解也不能忽视这一点。如1937年时K.S.Yu曾说:“除共产党活动的停止之外,国民党对传教士和推行宗教活动的温和理智的态度也是很振奋人心的……中央和省政府中‘基督教领导人的增多’也很好地说明了基督教事工的未来。”(40)后来成为新生活运动顾问的牧恩波牧师对共产党的态度虽然有些矛盾(41),但反感还是明显的。他曾做过关于“中国的苏维埃与江西的重建”的演讲,他表示,“我有七个同事被共产主义者杀死,在这种情况下,与我从事同样职业的人中,只有少数能够活到今天来谈论这些……现在应该由你们来证明,在暴力手段——革命之外,还有其他方法能够让中国人民得到幸福和安全,因为我很了解我的朋友们,这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42)
应该注意到,这些对共产主义的反感更多针对的是暴力革命的手段,而不是政权的性质。根据瓦格(Paul Varg)的研究,在牧恩波看来,如果共产党胜利,就会很麻烦。“但如果自由派胜利的话,牧恩波认为传教士将可以像往常一样继续自己的工作。”(43)在温和与激进的对比中,和平主义者倾向于温和手段似乎是很自然的,再加上“国民党是唯一一个可能对基督教宽容的政党”(44),牧恩波对新生活运动的如下的表示就可以理解了:“‘新生活运动’树立了新的社会目标,全新的生活秩序正在到来……人们得到了所有共产党承诺过的东西,而且是以一种对生长在中国文明中的人而言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在新生活运动开始的典礼上,蒋介石将军夫妇为将在历史上留名的伟大社会革命鸣了第一枪。东西南北终于联合起来了。孙中山博士的伟大梦想成真了。激进主义和共产主义死去了。”(45)陆培涌的研究认为,对政权的一方,蒋介石夫妇也深为“中国基督教团体和整个外国传教士群体总体上的改良主义方法”所吸引(46)。教会与政权在反共问题上有共同点,但这共同点的基础并不是共同的政治理念,而是共同的社会改造手段。
传教士和其他教内人士对新生活运动目标的理解,既是对基督教本身的体认,也是对自身境遇的思考。在此基础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参与到了新生活运动之中,但并不是被动地等待被政权使用,也不会对政权的要求一切照办。带着自己的认同、利益和反思,他们调适着与运动的距离,改变着他们所投身的运动。
三、从旁观到参与
(一)基督教在中国的新机会
1922-1927年间全国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47),对于基督教来说是很大的刺激。教会在反驳、回应批评的同时(48),也在调整着自身同民族主义、本地文化与中国建设的关系(49)。
非基督教运动让教会在处理社会关系上有了更多的经验,也使教内人士在非基督教运动后相对平静的时期里感到更多的欣喜和机会。1934年11月《教务杂志》的社论表达了这种情绪:“对于那些曾经历过几年前针对基督教和教会仇恨攻击的人来说,当前的形势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中国对基督教团体加强了支持……私立教会学校不再受到教育当局的歧视……基督教与非基督教机构为中国人民福祉这一共同的目标而扩大了合作,而所有这些都是合作的一部分”(50)。正是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新环境下,新生活运动成为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新机会。
蒋介石夫妇都是基督徒,这令个人色彩很强的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的关联变得理所当然(51)。关于蒋介石的教徒身份,公认他的皈依是受到宋美龄及其家庭的影响的。据说,蒋介石在1926年曾批评基督教“伪善”,但11月北伐开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接受《字林西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我与基督教并没有什么争执,我们将像以往一样欢迎传教士。”(52)对此有学者评论:“考虑到蒋介石之后不久与共产党的决裂,也许他作这样的陈述是为了争取中国基督教徒和外国力量的支持。”(53)但要说他的受洗只为了婚姻、争取支持等功利目的,也未必准确(54)。陆培涌分析基督教对蒋介石有三种意义,即“作为宗教,它能在精神上治疗蜕变的人格,也能为民族信仰提供心理支柱。作为一种西方的历史现象,可以将它有选择地介绍到中国,嫁接到儒家的母体上,从而使他将要构筑的二十世纪新儒教成为普适的经验。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基督教会又是建设新中国的有用工具。”(55)这种概括对我们看待新生活运动吸收基督教的动机是有助益的。
新生活运动对基督教表现出相当的热情,1934年底蒋介石夫妇即在中国北方巡视,号召教会抓住机会与新的社会运动合作。从材料看,我们可将基督教在运动中的功能归为三点:
首先是弥补新生活运动在精神方面的不足。虽然从相关言词上看,新生活运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精神支柱,但如果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官方阐释方式以及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行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新生活运动中的传统智慧是被高度外化和形式化的,它既不能像在传统社会里一样作为政权意识形态的基础,又缺乏深入人心的感召力。而宗教精神或能够为新生活运动增加活力和动力,有基督教信仰的知识分子也可能为新生活运动提供更多的帮助。
其次是通过基督教在社会服务上的事工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补充。新生活运动组织劳动服务团,表现出对动员民众和经济建设的双重需要。基督教在中国已有社会基础,让这样的团体参与到新生活运动中间,有助于扩大新生活运动的影响力。教会的社会服务包括了医疗、卫生、乡村建设、妇女工作等,这些事工与新生活运动的结合,则可以为新生活运动提供现代化方面的辅助,亦可为双方提供政治色彩较淡的合作。
第三是在运动中加入西方的色彩而争取外国关注和支持。由信基督教的领袖发起的带有基督教性质的运动,比较容易获得西方国家的关注。在国内外的斗争中,国民党也能以较良好的国际形象寻求西方的支持。传教士亦成为连接新生活运动与西方的纽带。
从基督教对新生活运动的实际参与中,我们看到,基督教能够为运动注入新的精神成分并提供组织机构上的支持。这既是合作开始的动力,又是合作深化的障碍。因为从教内人士的立场看,政治运动对宗教的工具性使用是应该谨慎对待的。
(二)热情的旁观者
在新生活运动的第一年,《教务杂志》对新生活运动的报导很有限,除五月份的社论外,仅有十二月份关于“陈济棠将军(General Chen Chi-tang)在辖下的广东省立法规范婚礼、服装式样、生日庆祝和礼物交换”的报导(56)。同期亦报导蒋介石对中国学生发表讲话,“确认宗教的价值及联合、依靠基督教的需要”(57),但并未提及新生活运动。数月后发表的一篇文章在回顾初期新生活运动时提到:“这场运动一开始,南昌的基督教会就都被邀请来一起努力推行新生活运动,教会借出传道室以供公开会议和演讲之用”(58)。所报导的参与固然有限,但基督教与新生活运动的联系已经开始。
1934年底,蒋介石夫妇在中国北方巡视并在太原会议上发言,邀请传教士与新生活运动合作。会上宋美龄表示,“今天基督教在中国的机会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里的都要好”(59)。一些教内人士的态度也颇乐观。董显光(Hollington.K.Tong)认为,这场在国内迅速流行开的运动“表明了中国国家领袖工作的方向”,文中还提到宋美龄“在与外国新闻记者的一次秘密非正式交谈中表示,她相信中国的最大希望在于此次改革,这次改革意在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将其与西方文化里中国需要的部分混合起来……在这次运动的刺激下,如果能有一个和平繁荣的环境,中国在十年内将就很有可能成为大国”(60)。Kimber Den的文章中提到,“1934年11月19日,在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执行委员会和工作人员的会议上,蒋介石将军公开指出,要推行新生活运动,中国基督教力量的合作是很关键和必要的。”(61)同景教入华以来的情况相比,人们感到“现在中国宗教宽容的自由氛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62)。艾迪(Sherwood Eddy)对新生活运动的工作印象很好,他看到“许多新造的公路和修建中的公交路线,比在俄国看到的都多。正直、高效的官员数量同三年前相比,有了更令人满意和注目的增长……新生活运动是一种承诺,尤其对蒋介石将军来说,这显然意味着官员和军官的崭新道德生活,他们应该服务和动员人民,而不是继续剥削他们。”(63)这些评论所表现的态度,更像是旁观者,虽然是乐观而热心的旁观者。
(三)参与运动的新力量
随着新生活运动的继续推行,教会变得越来越像是参与者;而当运动需要新的动力时,基督教在精神上的作用也越发显露了出来。
在“三化”(生活军事化、生活生产化、生活艺术化)正式推行之前,新生活运动的中心事项是“规矩”、“清洁”,是在衣食住行中体现礼义廉耻的原则。而运动的程序,则是“由自己作起,再求之他人。由公务人员作起,再推之民众。由简要之事作起,再及其次。由不费钱不费事不费力之事作起,再行其余。由机关团体,及公共场所……作起,再求之于全体之社会”(64)。因此,这一期的新生活运动关注的是“衣服要齐纽扣要扣好,帽子要戴正,鞋子要穿好,吃饭要规矩,座位要端正,饭屑不乱抛……脸要洗干净,手要洗干净,要漱口要洗头,要吃新鲜空气,头发要梳理,指甲要常剪,常常要洗澡……”(65)等等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以敦促民众改变生活方式。另有《新生活运动歌》、《新生活须知歌》等,把新生活运动的规条写入歌词,四字一断,以中国固有五声音阶谱曲,以向一般民众宣传(66)。在“三化”开始推行之后,对生活细节的关注仍然存在,但加入了公民训练、朝会运动、防空演习、提倡国货、节约储蓄、礼俗改良、捐衣救灾、民众识字等运动以对应“三化”(67)。
对于意在改变人们生活习惯的卫生运动来说,这样的措施可以收到成效。但对于新生活运动民众动员、人格塑造的目标来说,这些措施远远不够。《新生活运动须知》上那些细致的要求,如胡适所言,“不过是一个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识生活”(68),而且过于细致的条款在推行时很容易变得呆板和形式化,以至于受到人们的疏远(69)。即便人们都做到这些条款,也不过能改变生活的风貌,离军事化和战争动员仍有距离。在人格塑造方面,新生活运动希望借助传统智慧涤除陋习,转移风气。但传统智慧中自身修养、推己及人、修齐治平的过程,没有也不能通过外部力量敦促日常细节改变这一方法来实现。于是在新生活运动的进程中,传统智慧先是被化约为管子的“礼义廉耻”四字,然后被外化成了“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行为”、“清清白白的辨别”和“切切实实的觉悟”(70),并进而细化成规范人们生活细节的条款。与其说这是在复兴传统文化,不如说是将传统智慧的词句加上现代的解释,以进行现代生活方式的塑造。在这里,传统文化非但没有成为深入人心的精神信条,反而被外化和形式化为教条和口号了。以这种方式开展的新生活运动,一旦表面上的规矩与清洁状况有所改观,就很容易失去动力和更高的目标。结果是“随着运动的进行,手段代替了目的;应该是‘最初阶段’的工作被不停地重复,没有任何进展”(71)。
人们看到,新生活运动正逐渐失去最初的动力:“一开始,它强调很有必要注意的道德、举止和公共卫生。它也倾向于对这些强调加以军事化。可惜像反对化妆和时尚之类的努力过于肤浅……它一开始的热情已经过去。负责人的会议变得敷衍刻板。新生活运动的推动力已经减弱。简言之,这场运动表现得缺乏恰当目标。有人批评说,开展新生活运动主要是为了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中国紧迫的经济问题上转移开去。”(72)在1937年一个回顾前三年新生活运动的讨论会上,谢颂羔(Z.K.Zia)提出“新生活运动欠缺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它有太多的老生常谈;但却没有获得灵性的技巧”,这是一场缺乏核心人格的运动,“是基督徒宣扬耶稣基督和福音的时候了”(73)。1937年3月27日,经历了西安事变的蒋介石在美以美会东亚会议上致辞,“强调了坚定信仰的必要性,透露了平时以及在西安时圣经是怎样给将军以力量的……认可了富冒险精神的基督教信仰能够满足富冒险精神的人民的需要”(74),这对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同年5月6日,宋美龄在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双年会致词表示,人民精神的更新及性格的改善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在很大程度上这项工作主要应由教会来做,新生活运动和教会应该一起来完成这项工作,协进会则“对于蒋夫人在中华基督教会双年会上的演讲感到极大的兴趣和感激”(75)。教会表现出了参与者的姿态,并在参与的立场上对新生活运动加以批评,试图用基督教的精神力量来弥补新生活运动的不足,让新生活运动和教会都有更大的收获。
同精神力量相比,作为组织的基督教为新生活运动提供了更加具体有形的合作。1935年,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查各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及各地基督教会在使人生活向上,沐之以教义,范之以规律,与新生活运动,颇多吻合之处”(76),通告各地制定青年会及教会服务团组织简则。自1936年起,“领导权似乎转移到了蒋夫人和国民党中较美国化、较倾向于基督教的成员手中”(77)。1936年4月,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牧恩波牧师受邀到南京担任新生活运动顾问。7月1日,有青年会背景的黄仁霖被任命为新生活运动总干事(78)。“牧恩波的参与和励志社(OMEA,军官道德励进会)黄仁霖(J.L.Huang)中将担任新的新生活运动总干事这一事件,激发了人们新的信心。”(79)此前,牧恩波担任江西基督教乡村服务联合会(Kiangsi Christian Rural Service Union)的总干事,领导黎川试验区的工作。乡村建设从而成为基督教组织参与新生活运动的重要方式之一。教会一直在进行的健康计划和社会改造等事工也被纳入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在号召青年会及教会组织服务团时提出“1.由自身做起实行新生活。2.由家庭做起实行新生活。3.由本青年会或本教会做起实行新生活。4.劝导亲邻及服务机关实行新生活。5。利用讲道及其它集会宣传新生活运动”(80)。1937年5月6日宋美龄在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双年会的致词中回顾并提出了数种教会参与新生活运动的方式,包括乡村建设、同教会合作进行国民健康事业、成立祈祷会为国家命运和领袖祈祷、邀请传教士支持“轮上新生活”的宣传运动等,并希望他们为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做出努力(81)。汤森认为,“新生活运动的两项活动对教会有特殊的吸引力:推行禁毒运动和关注乡村生活”(82)。牧恩波对这两项活动也很热心,除了乡村的建设和官员的培训,他还“在危险的情形下数次勇敢地试图破坏上海与广州主要的贩毒帮会”(83)。他也提出了与新生活运动合作的方式,即“让所有的教会成员都实行新生活”和“服务”。针对“服务”,他号召基督徒加入当地社会服务团体,通过教会医院、学校和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来加入新生活运动,关注乡村,解决人们生活上的问题。他总结道:“新生活并不是要你们在行动中放弃基督教信仰,相反,是要你们在行动里放入基督教信仰。”(84)
尽管显出了热烈参与的情形,但教会总有着种种顾虑。新生活运动是一种社会改造和动员的运动而非基督教的运动。基督教的作用大部分是工具性的。教会方面处理政教关系时需要考虑的,是教会的生存、福音的传播和基督教的标准。对教会生存的考虑让教会倾向于国民党,对福音传播的考虑既使教会将新生活运动看作机会,也促使教会谨慎处理与政权的关系,对基督教标准的考虑则在教内人士中引起了对政教关系、民族主义、和平主义等问题的反思。这就是下面要讨论的主题。
四、政教关系:顾虑和思考
新生活运动的原则同基督教的精神有一些相合之处,新生活运动的社会工作也与基督教的社会服务事工有不少重合。宽松的宗教气氛和政权的邀请暗示着扩大传教工作的机会,但教会对于政教关系的顾虑和思考则持续存在着。
(一)政治还是服务:基督教团体的顾虑
新生活运动开始之初,面对邀请,青年会内部就出现了犹豫的声音。汤森认为,问题在于“同新生活运动合作不仅可能让青年会卷入一些更宏大且更不符合基督教的事情;而且还可能让公众把青年会与国民党不那么好的一部分联系起来”,问题是“他们要怎样参与一场由国民党赞助并安置人员的运动,同时又保持自己基督徒和民主主义者的认同呢?”(85)讨论的结果,是青年会在1934年5月做出决议,准备为乡村训练领导人和提供专家,并让城市会员更多地了解乡村的情况,但由于大萧条等因素的影响,“1934年的决议只是一种希望,而没有成为方案”(86)。根据邢军对鲍乃德(Eugene E.Barnett)通信档案的研究,当蒋介石认为青年会应为新生活运动提供更多干事时,总干事余日章“提出了相反的建议,让蒋介石派人到青年会以避免事情的公开化”(87)。青年会抱持着谨慎的态度,其他基督教团体也是如此。汤森曾讨论过到1935年秋天为止的意见分歧,有的基督徒认为“新生活运动激动人心、充满希望、在目标上高度基督教化”,另一些则认为它“肤浅、不合时代”,甚至“过于政治化而且是半法西斯主义的”(88)。牧恩波在南京与数百名受过德国顾问训练的年轻人共事,为此《教务杂志》的主编乐灵生(Frank Joseph Rawlinson)警告美部会的中国干事,军国主义基础“可能会是改组新生活运动的最大障碍”(89)。
新生活运动毕竟是由政治领袖直接发起的运动,同力行社、励志社的联系也让运动有明显的政治印记,对于基督教团体来说,如何与政治保持距离,从而避免卷入政治斗争成为政治的附庸,一直都会是一个问题。
1935年蒋介石号召在民间成立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在基督教青年会和教会中成立新生活服务团。《新生活劳动服务团组织大纲》(90)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及基督教各教会新生活服务团组织简则》(91)有不少相似之处。如服务团都以固有组织为单位,劳动服务团以地方团体机构为单位,青年会服务团和教会服务团则以会友和教友为团员,服务团和服务情况均应报当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备案等(92)。这是对基督教团体服务的认可和鼓励,但也带着政治权力向教会渗透的成分。政教合作意味着二者都要失去相对的独立性,而在政治主导的社会中,教会对独立性的担忧比政权要多得多。一些基督教徒认为,“这些规定可能会让一些地区的新生活运动联合会以为他们能控制教会生活。由于以前与党的官员有过不愉快的经验,他们自然会比较谨慎”(93)。为此,牧恩波牧师在1937年做过4点解释:“1、新生活运动不会变成任何党派控制的政治工具。它只属于人民。2、新生活运动总会和地方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没有官阶。他们也没有权力签发公文和法规,除非由主席下达。3、这场运动主要强调的是通过实行礼义廉耻的原则来发展人格……4、新生活运动是一场运动而非一个组织……新生活运动不是教会的对抗者,也没法做那些只有教会能做的精神工作……新生活运动并没有错以为教会只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而已。”(94)这些解释意在打消基督教团体内的疑虑,让基督教更多地参加到新生活运动中来,但也隐隐地透露出了教内人士的顾虑所在。
(二)宗教与国家:立案引起的思考
1934年以后,宗教政策比先前要来得宽松,而且部分地由于新生活运动的缘故,政权表现出对宗教的热情。从四年间的《教务杂志》里,我们看到“中国对基督教团体加强了支持”(95),人们也渐渐感到,“现在中国宗教宽容的自由氛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96)激烈的运动平息了,“现在中国对宗教宣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开放。虽然对未立案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会有一些歧视,但能够胜任职位的基督徒一样可以在重要的政府和商业机构担任职务。还有,重建计划显然需要基督教和教会的合作,这意味着人们认可宗教力量为中国重建的核心力量之一。”(97)基督团体所乐见的,是依靠社会力量、而不依赖政治力量或国家法律的新生活运动(98)。但政治和法律不仅是整个新生活运动的推动力,还是试图管理规范基督教团体的力量。宋美龄曾表示“新生活运动反对任何形式的严格控制(regimentation)”(99),但实际上政权对教会的控制却持续存在。政府要求教会学校向政府立案并进一步要求宗教团体立案,这在教内引发了更广泛的讨论。
江文汉(Kiang Wen-han)撰文讨论了中国教会大学的世俗化倾向。他提到,政府规定教会大学不仅要向政府立案,而且要遵循教育先于传道的原则。教会大学已经越来越倾向于世俗化,集中表现为信教学生比例下降、学生对宗教冷漠、为民族拯救的运动所吸引、精神上倾向于激进和社会主义、基督教目标模糊等等(100)。政治对教育的控制本来就不可避免,而从政治力量促进教会大学世俗化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新生活运动号召教会合作,似乎并未抬高基督教在国家生活中的政治地位。基督教也许是新生活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但并未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先前由不平等条约所保护的教会特权也在渐渐失去。
1937年6月的《教务杂志》上发表了由立案引发的关于政教关系的讨论。乐观者有葛德基(E.H.Cressy),他认为政府给了国内已立案的教会学校“公平甚至友好的待遇”,虽然“政府法规没有明确认可学校的宗教教育和礼拜活动,但法规中隐含着对这些活动的许可,只是不能在小学和中学里设置相关的课程”,“教会学校仍有机会为基督教事业做出贡献”(101)。鉴于当时只有中华基督教会(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和中国自立会(The Chinese Independent Church)向政府立案,P.Lindellsen认为其他教会“生存于外国差会的阴影中,而那些外国差会的地位又是通过所谓的‘不平等条约’确立的”(102),教会向政府立案,能够建立同政权的合法关系,得到官方的认可。W.Harvey Grant则表现出有保留的乐观:“虽然(政权和教会)作用的领域不同,但这两种组织是互补的,必须合作”,政府要求立案的意图“为教会造册,从而使双方都认可政府对教会的保护,并发现在宗教外衣下从事邪恶活动的团体”(103),但只有在“政府的法规仅限于提供信息和保护”(104)时,他才认可政府的立案法规。
Herman Maurer就远没有那么乐观了,他的顾虑是有代表性的,甚至可以看作对政教关系中问题的总结。首先的顾虑针对宗教气氛,这对于经历过反教运动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预言当前中国良好的状况会否持续……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君主会否让我们的希望成为空想,而让官员们站到与我们对立的一边”。政府在新生活运动里对教会表现出的热情,并没有坚实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基督教徒在中国仍然是少数群体。于是,他的第二重担心在于教会的独立性:“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领袖很强调我们为政府祈祷的义务,也很注重将属于凯撒之物交给凯撒,还以基督人格的一切力量参与到国家对社会重建的努力之中……但如何看待教会变成社会组织、耶稣基督的福音变为社会使命的倾向呢?”(105)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基督教对当时中国社会运动的参与,更多的在于社会服务的一方,如黎川试验区就曾被批评不仅过多卷入政治,还弱化了基督教性质,忽略了福音的传播(106)。新生活运动中基督教的活动也有同样的问题。第三重顾虑则关系到政权的非宗教性质。关于立案的政策,Maurer认为这还是政府的好意,关键问题在于教会“缺乏勇气,不敢向政府寻求对政教关系更深层次的根本理解”。“民主的非基督救国家并不太可能会在众多社会和宗教团体中,给占少数的基督教会以特殊关照”(107),所以教会应该承担处理好政教关系的责任,但是政府的政策“就像一把悬在我们头上的剑,它们是无害的,只要它们不掉下来”(108)。他悲观的结论则指出了政教关系的根本问题:“政府诚挚希望每个基督徒都成为模范公民,这没有什么,但政府很难承认,有时这些模范公民要服从上帝,而不服从政府。这一点令此世的教会无法最终解决“政教关系”的问题。”(109)
从逻辑上将政教关系划分为几种理想的模式或类型是轻松的,但站在具体历史过程的角度,我们会发现模式和概念对于处理当时的情境远远不够。在本文讨论的历史时段中,政治是社会的主导,教会在政权发起的运动中以社会服务的方式担任了工具性的作用,政权在控制教会活动的同时,也借基督教争取更多外部的支持。但宗教在政治主导的社会中并不只有被动的选择。教会有对自身命运的疑虑和担心,有对运动理想化一面的认同,也在反思和服务中改变着同运动合作的方式,为运动注入新的精神。更重要的是,面对当时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压力,政权和教会都不可能在真空中遵循像“命令—服从”、“控制—反抗”、“合作—分歧”之类简单的模式,而必须有所转变,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应对危机时,在宗教的一方,“模范公民”和“服从上帝”的选择重又展开,在政权的一方,运动的性质和目的则又一次被提上了日程。
五、面对战争
1934-1937年的这段时间,其实不过是动乱与战争中相对安定的间隙。这样的时局令新生活运动不能限于衣食住行的琐碎细节,教会也对周遭环境和迫近的战争有了更多的思考。在面对战争时,基督教与新生活运动仍然保持着关联。与之前有所不同,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在精神方面因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的问题有了较大的分歧,二者的共同点更多地体现到了具体的服务和事工上。
(一)责任和抉择:战争下的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
对于新生活运动来说,民族主义并未成为问题。新生活运动本来就有军事动员的成分,邓元忠认为新生活运动是掩护的抗日训练110,欧阳雪梅也从“三化”期间的经济建设和军事训练上看到新生活运动“明耻教战”的功能(111)。随着战争的发展,新生活运动的侧重点从日用常行转移到了民族命运上,从和平时期的衣食住行转移到了战争时期的服务中。蒋介石在1937年的纪念演讲时将形势描述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难严重,千钧一发的时候”(112),新生活运动应以两个方式做出回应:“第一就是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与他的精神;第二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与他的技能”(113)。为此,蒋介石提出应对紧迫形势的新生活运动应该“切实推行勿事铺张”、“集中力量贯彻到底”、“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简朴勤俭表里一致”和“精诚热烈自强不息”(114)。作为对新目标的延伸和确认,1939年的新生活运动五周年纪念训词中,礼、义、廉、耻更是得到了重新的解释,由“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行为、清清楚楚的辨别、切切实实的觉悟”变为了“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115)。像“明耻教战”这样的词汇也随着战争的进程而更多地出现在官方的言词中。
这一时期的教会则面临着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和平主义与战争抵抗之间的抉择。这两个问题对教会来说并不陌生,然而就同政教关系一样,很难有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但历史的摄人之处,正在于这些时时出现的矛盾和纠结。
1934-1937年这段时间里,随着日本侵华的展开,民族主义情绪扩展并高涨起来。基督教在中国并不是第一次面对民族主义。非基督教运动期间的民族主义气氛就曾让教会和青年会受到过很大的挫折(116)。教内也出现分歧和调整,瓦格发现“[南京]事件之后,传教士仍然继续签名请愿,差会也坚持向国务院表明它们对修改条约的支持……基督教在中国的未来有赖于将基督教的努力和中国民族主义志向结合在一起。”(117)教会中兴起的本色化运动则思考了中国文化的可能贡献,将基督教和民族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118)。然而,针对日本侵华而起的民族主义,对于教会来说有不同的意义,因为“日本人代替西方人成为了民族仇恨的主要对象”(119),反教运动平息,社会环境变得宽容,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矛盾在战争的阴影下更加凸显。与民族主义相合,像王明道这样的独立传道士以及新的教派出现了,“这些新的教派或运动与日益成长的民族主义相一致,吸引着民族主义者,因为它们基本上都完全中国化了,或是基本以中国资源支持的独立运动。它们也常常以狭隘的偏见攻击那些来自西方的分派。”(120)问题是,从“服从上帝”这一点看,基督徒应该是国际主义者,而民族主义的发展使得国家的界限越发清晰,战争的迫近也令“服从国家”成为中国基督徒不能不选的选项。于是,“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在战争的威胁下渐渐变为相对立的选择。
面对新的民族危机,1935年,谢颂羔提出,教会应当对时局有及时的、积极的言论,否则“如果战争到来……生活和宗教没有明显的联系。也就难怪年轻人会在教堂里感到不舒服了”(121)。1937年赵紫宸表示,“我们的民族危机是中国基督教的危机”(122)。1937年8月19日,《教务杂志》二十五年来的编辑乐灵生在上海租界的空袭中丧生(123),战争对传教士的威胁成为了现实的伤害。
从本文讨论的时段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在十多年前。但基督徒面临的矛盾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少,毕竟彻底的解决方式是没有的。从和平主义的角度,《教务杂志》上的文章体现了避免战争的希望。1936年2月社论表示,希望中日之间的问题“能够经由更有力的外交解决,而不要通过‘积极抵抗’可能导致的大屠杀解决”(124)。人们希望中日能有政治和外交上的妥协,进一步达成一致与合作,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对两国的进步是一种阻碍,对世界来说也是动乱的因素”(125)。中日基督徒也做出了合作的努力。1934年8月14-18日,一个规模很小的中日基督徒会议在徐宝谦和顾子仁的努力下在京召开,结果是“除了具有中日沟通的象征意义外,并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126)。1937年5月14日,十一名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代表和五名日本基督教协进会的代表会面讨论合作促进中日关系,但“这种互访并不能使基督教力量对两国的政治领袖或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两国基督教团体数量都很少,在日本,政策对基督教的压力比在中国更加明显(127)。基督教团体避免战争的努力毕竟微薄,教会不得不正视战争。
1937年夏,一些传教士在牯岭讨论基督徒面对战争的方式(128),选项有出于仇恨战斗、出于自卫战斗、绝对和平主义、帮助受苦者、传承中华文明与生活、寻求其他选择。他们认为,出于仇恨而战斗“不是基督教的解决方式,但许多中国基督徒是性情中人(humane enough),会与他的同胞们一样有这种感受”。至于出于自卫而战,“这种立场很可以理解,但也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立场”(129)。最后他们提出,“教会必须无私地为上帝之国的目标服务”(130)。面对这些选项,实际选择出于仇恨而战和绝对和平主义立场的教徒并不太多,而在选择自卫的人们身上,解决和平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也是最必要的。姚西伊在讨论“九一八”后中国基督徒的相关思考时描述了人数最多的“中间调和派”:“在两难的选择之中,他们采取了一种介于武力抵抗派与唯爱和平派之间的立场,试图在坚持基督教‘博爱’传统的同时,尽量为适当的武力反抗开拓一些空间,使其在基督教信仰框架之下获得一定的合法地位。”(131)这种描述部分地适用于认可自卫战斗的人们。
1937年10月《教务杂志》的社论提到,“教会也可以在战争危机中成为领导者。教会不投身于战争计划,但可以着手动员民族自卫的精神力量,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底线。”(132)同期杂志收入了曾参加一战的Ronald Rees的文章,他看到,“1914年,我们中在欧洲的一些人面临的形势在一些方面与今天的形势相当接近……他们无法坦白地说抵抗是错的,但他们感到作为一个基督徒,说战斗是对的要难上加难……在罪恶的纠结中,没有一种理想的道路;只能在两种恶中间做选择。”(133)和平主义者徐宝谦(P.C.Hsu)也认为民族主义和自卫战争是正当的,因为“一个民族的成员必须先有民族意识和民族团结,才能为世界作出真正的贡献”,所以“一个民族有权利为生存战斗,面对外国侵犯时,自卫战争是完全正当的”(134)。在战争中,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难以为继,因而徐宝谦将和平主义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而生活永远不会止于空谈或消极行动——比如反战”,他将“和平主义者”与“基督徒”当作可以互换的概念,因为“虽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反战,但所有的基督徒都应是和平与善意的使者”(135)。
面对战争,教内关于和平主义和抵抗主义的讨论,更多的作用在于精神上的安顿,对实际战争进程的影响同政治相比是很小的。战争来临时,新生活运动发生的转变不但隐含了政策上的变化,还为基督教在战争中的事工提供了支持。二者在战争阴影中的合作也更多地体现于此。
(二)战时服务:新合作的开端
瓦格发现,1937年战争再度开始时,传教士们的首要反应是“赞扬蒋介石将军”,有许多关于新生活运动的长文描述了这样的图景:“在蒋夫人的领导下,中国进入了一场伟大的运动,古老的恶将被清除,代之以爱国、自我牺牲的‘基督教’美德。”(136)战争的开始让基督教与新生活运动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训词》中提到,新生活运动中“有六十六个大学生……利用暑假机会,参加农村普遍的义务工作,改进农民生活,唤起农民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观念”(137)。新生活运动将这样的活动认可为拯救民族危亡的方式之一而加以鼓励,可见在抗战开始前新生活运动就已经包含了民族主义的内容。七七事变及八一三沪战之后,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新生活运动总会先设立驻渝办事处,而“总会及全部工作人员,乃留居武昌明月桥作各种战时之服务,至武汉撤退时,始全部西上重庆”(138)。在汉口工作时期,新生活运动的主要活动有战地服务、伤兵慰问、救济难民、保育童婴、捐款运动、空袭服务、发扬民族正气和征募物品运动(139)。1936年底1937年初傅作义部在绥远同日伪军对冲突期间,新生活运动总会曾组织战地服务团往绥远进行战地服务(140)。1937年后新生活运动转向战时运动。1937年9月25日,新生活运动伤兵慰问组在南京正式成立,由总干事黄仁霖兼任组长,分派各队队长,“出发于沪宁沪杭沿线各地医院,发放会长犒赏,慰问伤兵官员,视察医院设施,复以战事扩展,军医院分布全国,乃改编犒赏队为九队,分赴各地犒慰”(141)。1938年4月后,伤病慰问组又有了改编和扩大。
战时服务并不要求基督徒在和平主义与反抗之间做出抉择,且同社会福音派此前一直进行的服务并无性质上的不同。战争中教会和青年会社会服务的功能得到了更多的发挥。1937年12月的《教务杂志》报导了上海慕尔堂(Moore Memorial Church,后更名为沐恩堂)的战时服务工作(142)。慕尔堂收容了300名难民并照管其他两个难民中心,提供低价粥食,组织学生志愿者,开设诊所,并为难民子弟开办战时学校。1937年冬,青年会在上海成立“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委员会”并设五十余处支会。20世纪40年代青年会开展战时团契活动,教会方面也参与“伤兵之友社”的活动,成立“部队生活辅导团”等(143)。基督教运动与新生活运动都成为民族救亡这个更大运动的一部分。在新生活运动之初就被强调的军事化这时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而战前新生活运动和基督教的许多理想则在战争中进一步失掉了实现的可能。
教内人士对和平与战争的思考,以及新生活运动对目标及手段的调整,都是1937年后战争时期服务的前提。在危机和战争中,内在和外在的矛盾冲突都被迅速放大,新生活运动和基督教活动都被迫投入了一场更大的运动。
六、结论
本文关注的是1934-1937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里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团体的相互作用。这一时段中,新生活运动既象征着政治权力,又体现了某种社会理想,而基督教则以精神力量和社会团体的双重身份接受、反思、参与、改变着新生活运动。政权希望借宗教的精神力量来补充运动理论中形而上的部分,也号召基督教以服务的方式协助运动的推行。教内人士为运动的理想而振奋,也为运动的过度政治化而担忧。政权给基督教以有保留的支持,基督教也给政权以有保留的合作。1934-1937年是相对平静的四年。四年时间对于这样一场运动来说是太短了。在迫切的形势下,运动对琐碎细节的关注无法持续,基督教中绝对和平主义的声音也难有影响,民族危机和战争成为了改变新生活运动和基督教的重要力量。
在本文涉及的事件里,政教关系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包含了三个层次。
政教关系的第一个层次体现于新生活运动本身和基督教团体的活动。在这一层上,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的合作源于一些共同点。两种力量都有道德人格重塑的目标和改善社会生活的行动,都使用温和的改良方式,都强调精神的作用,这些令基督教团体与新生活运动的合作得以开始。两种力量的差异也是合作的动力。新生活运动有政治的支持,能够借国家机构的力量成为社会改造的主旋律,而基督教团体在社会中的影响有限,却因信仰和教义而在精神塑造上更有力量,因先前的乡村建设经历而在社会服务上更有经验。功能上的差异使新生活运动和基督教有了互补的可能,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则促使基督教团体认真对待新生活运动的号召。当然从另一角度看,基督教团体对新生活运动的政治化、军事化成分有所顾虑,并担心与政治过于接近,以致失去宗教性成为政治使用的工具,这些差异也是合作的障碍。
第二层次体现在国家政权和基督教的关系上。蒋介石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同时具有基督徒的身份,蒋介石夫妇时时提起这一点,亦获得基督教团体乃至国外民众的好感。但基督徒只是蒋介石的众多身份之一,同巩固政权、稳定内外局面相比,基督教在政治上的重要程度要低得多。蒋介石夫妇是基督徒并不意味着国家政策就会倾向于基督教。国民党政权对基督教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但不会放弃对基督教的控制。政府要求教会学校和基督教团体立案,可以解释为政府的善意,但其中控制的含义也是很明显的。政权号召青年会及教会成立新生活服务团,是吸收基督教成分进入新生活运动的标志,也是将基督教团体纳入政治体系的尝试。在这个层次上,由于宗教在政治生活中并不是重点,基督教团体改变政教关系的力量其实很小,“模范公民”和“基督徒”角色之间的冲突也难以避免。
第三层次与国际政治的影响有关。当政治的范围扩大到国际时,宗教面临的问题就不只是团体的独立性了。在1934-1937年的中国,国家政权和基督教共同面临的是外来的侵略和战争的阴影。于是,国家政策向应对战争的方向调整,宗教问题的重要性下降,民族主义、军事化在国家生活中兴起,政权发起的运动也相应地改变重点。基督教则要面对和平主义与自卫抵抗、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战争到来后,教会与青年会的事工集中到了政治性较少的社会服务上,新生活运动的重点也转移到至宗教性较少的“明耻教战”。战时服务成为基督教与新生活运动合作的新领域,二者的交集也越来越少。外部政治力量的影响促使国内政治和宗教活动发生转变,政教关系的性质也就更加复杂,问题已不在于合作的方式和控制的程度,而在于生存了。
本文希望能从材料中揭示更具体的历史,从而避免对社会运动与宗教活动简单化的叙述,并对政教关系这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获得更深的理解。
[收稿日期]2007-07-25
注释:
①暂时无法获得或未能见到的专著有:Walter Hanming Chen,The New Life Movement(Nanking: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es,1936).Jennifer Lee Oldstone-Moore,The New Life Movement of Nationalist China:Confucianism,State Authority and Moral Formation (Ann Abor,Mich.:UMI,2000).暂时无法获得的相关论文有:Christopher Tang,"Christianity and the New Life Movement in China",Doctor of Theology dissertation,San Francisco Theological Seminary,April 1941.Samuel C.Chu,"The New Life Movement,1934-1937",in J.E.Lane ed.,Research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on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East Asia Institute Series No.3,1957).
②关志钢:《新生活运动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③温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5)》,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④王晓华:《“模范”南昌:新生活运动策源地》,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7。
⑤C.W.H.Young,New Life for Kiangsi(Shanghai:The China Publishing Co.,1935).
⑥易劳逸:《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流产的革命》(陈红民、高华、洪邮生、申晓云、庞绍堂、汪利平、陈谦平、张益民译,钱乘旦校),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英文版:Lloyd 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Cambridge,Massachusetts & London,Engl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⑦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陈谦平、陈红民、武菁、申晓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英文版:William C.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⑧邢军:《革命之火的洗礼:美国社会福音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919-1937)》(赵晓阳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⑨James C.Thomson,Jr.,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⑩温波:《重建合法性》,前言第3-12页。
(11)顾晓英:《评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1934-1949年)》,载于《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3期,第50-58页。
(12)邓元忠:《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载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4,第29-41页。
(13)两种评价的分歧在英文资料里也同样存在,具体可参见注21韦思谛(Stephen C.Averill)的文章。
(14)关志钢:《新生活运动“失败论”析》,载于《深圳大学学报》第19卷第6期,2002年11月,第73-79页。
(15)温波、李小萍:《新生活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以南昌为中心的讨论》,载于《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总第137期,第32-36页。
(16)张庆军、孟国祥:《蒋介石与基督教》,载于《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第77-83页。
(17)汪进春:《浅议新生活运动与传教士》,载于《安徽文学》,2006年第九期,第85-96页。
(18)刘家峰:《徘徊于政治与宗教之间:基督教江西黎川实验区研究》,载于《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第86-92页。
(19)Pichon P.Y.Loh,"The Ideological Persuasion of Chiang Kai-shek",Modern Asian Studies,4,3 (1970),pp.211-238.
(20)Arif Dirlik,"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4,no.4 (Aug.,1975),pp.945-980.
(21)Stephen C.Averill,"The New Life in Action",China Quarterly,no.88 (Dec.1981),pp.594-628.
(22)The Chinese Recorder,vol.65-68(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Press,1934-1937).
(23)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5。
(24)应注意《新生活运动纲要》体现的运动主旨,很大程度上是在运动初期对整个运动的期望。随着局势的变化和运动的发展,新生活运动目标的重心发生了改变。新生活运动开展九周年时,蒋介石已经将新生活运动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物质力量相并列,将运动看作抗战中是“精神上无形的基本武器”,是“发动抗战的基本力量”、“实行三民主义的基本工作”了(《新生活运动九周年纪念广播词》,载于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95页)。并不是说新生活运动的目标发生了根本转变,而是说在形势的压力下,新生活运动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原先含有的一些因素被刻意强调了。
(25)《新生活运动纲要》,载于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1-2页。
(26)同上,第3页。
(27)"Editorial:The 'New Life Movement'",The Chinese Recorder,vol.65,no.5(May 1934),p.278.
(28)Joachim Muller,"Christians and New Life Movement",The Student World,First Quarter,1937,p.31.Cited in 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4 (April.1937),p.259.
(29)"A Symposium:What Can Christian Co-operation Add to the New Life Movement",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5(May 1937),p.295.
(30)Ibid.,p.296.
(31)《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载于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15页。
(32)同上,第21页。
(33)如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第205-208页。他认为德国的榜样力量在新生活运动中占有重要位置,而蒋介石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又与国外独裁主义国家引导个人道德的情形有关。又:易劳逸认为,法西斯主义的蓝衣社是新生活运动的领导力量(见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82-88页)。《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也有类似意见(见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206-1208页)。对此,蓝衣社活动曾经的参与者干国勋、宣介溪等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人们通常认为的蓝衣社实即三民主义力行社,而蓝衣社之说最早来自刘健群的一本小册子(参见干国勋等:《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84年)。邓元忠也认为易劳逸说法不当,认为力行社被误称为蓝衣社有七种原因可追迹,其中包括力行社的秘密性、德意黑衫褐衫党的风靡、励志社服务生常着蓝色制服的情形、日人误解并留下大量“蓝衣社”调查材料,而易劳逸等外国学者赴日收集中国近代史料未加鉴别的可能等等(参见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
(34)"A Symposium:What Can Christian Co-operation Add to the New Life Movement",p.295.
(35)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新生活运动手册》,[出版地不详],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5,第23页。
(36)Kimber H.K.Den,"New Life Movement and Christian Church",The Chinese Recorder,vol.66,no.2 (Feb.1935),pp.99-100.
(37)James C.Thomson,Jr.,While China Faced West,p.152.
(38)Mayling Soong Chiang,"Forword",in C.W.H.Young New Life for Kiangsi,p.iii.该书大部分内容都曾发表于《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上,有明显的反共指向,历史形势使然。引文中单引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39)See Section Two in C.W.H.Young,New Life for Kiangsi.
(40)E.S.Yu,"Church Unity:its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1(Jan.1937),p.31.
(41)牧恩波牧师反感共产主义,但仍认为共产主义有社会影响,他“将新生活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联系起来,把它们看作两种‘破坏旧中国’的力量”,见James C.Thomson,Jr.,While China Faced West,p.163.
(42)C.W.H.Young,New Life for Kiangsi,p.28.
(43)Paul Varg,"The Missionary Response to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in John K.Fairbank 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317.
(44)Ibid.,p.320.
(45)George W.Shepherd,"The Chinese Communists",in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34-1935,19th issue (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35),pp.89-96.
(46)Pichon P.Y.Loh,"The Ideological Persuasion of Chiang Kai-shek",p.237.
(47)可参考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
(48)可参考真光杂志社编:《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全编》,上海,中华浸会书局,1927。
(49)如1922年开始的本色化运动,可参见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29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50)Editorial,"Some Current Issues:China's Present Attitude to Christianity",The Chinese Recorder,vol.65,no.11(Nov.1934),p.674.
(51)有一种关于新生活运动开端的说法,是说宋美龄在牯岭避暑时,传教士提示宋美龄,如果蒋介石实行社会福利的“新政”,就可能给外国政府以好印象从而获得支持,新生活运动由此开始。这种说法,暂时未见证据,而且如果说这是新生活运动开展的唯一原因,似乎也过于简单。说新生活运动的目的仅在于争取外国支持改善国民政府的国际形象、新生活运动开展的主导方在传教士和宋美龄,恐怕也武断了些。毕竟新生活运动并不是一个社会福利计划,且具有很强的复兴传统的色彩。不过,蒋介石夫妇在牯岭时,受到传教士影响,还是有迹可寻的。牯岭是许多传教士的避暑之地,而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江西时,亦将牯岭作为夏季住所,且他们租住的房子属于南昌美以美会。(见Jonathan,D.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NY & London:W.W.Norton and Company,Inc.,1990),p.386.)另根据刘家峰的研究,同为美以美会教友的蒋介石夫妇与美以美会传教士长孙维廉(William Richard Johnson)甚为熟悉,宋美龄和长孙维廉的往来亦促成了后来与新生活运动颇有关联的黎川试验区的建立(见刘家峰:《徘徊于政治与宗教之间》,第86-86页)。当时南昌圣公会会长邓述堃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了传教士与新生活运动的密切关系。他回忆,在新生活运动的筹备阶段,宋美龄授意长孙维廉在北坛江西卫理公会江西布道使的住宅举行茶话会,邀请教内人土参加宣传新生活运动并受欢迎。此后基督教会以多种方式为运动宣传,并借此扩大教会的影响(见邓述堃:《宋美龄—基督教—新生活运动》,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三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第71-76页)。
(52)Pichon Loh,"The Ideological Persuasion of Chiang Kai-shek",note 96,p.235.
(53)Ka-che Yip,Religion,Nationalism,and Chinese Students: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2-1927 (Bellingham: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1980),p.66.
(54)参见张庆军、孟国祥:《蒋介石与基督教》,第78页。文中引美国《基督教世纪》对蒋介石受洗的评论,该评论也认为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过程中匆忙受洗,有争取外援的因素。
(55)Pichon Loh,"The Ideological Persuasion of Chiang Kai-shek",p.229.
(56)"The New Life Movement in Kwang-Tung",Fides Service,August 18,1934,cited in The Chinese Recorder,vol.65,no.12 (Dec.1934),p.796.
(57)"General Chiang and Religion",Letters From China,Nanking,October,1934,cited in The Chinese Recorder,vol.65,no.12(Dec.1934),p.800.
(58)Kimber H.K.Den,"New Life Movement and Christian Church",The Chinese Recorder,vol.66,no.2 (Feb.1935),p.99.
(59)"The Present Situation:Missionaries and New Life Movement",The Chinese Recorder,vol.66,no.1 (Jan.1935),p.61.
(60)Hollington K.Tong,"China's Modern National Leadership",The Chinese Recorder,vol.66,no.1(Jan.1935),p.10.
(61)Kimber H.K.Den,"New Life Movement and Christian Church",p.100.
(62)"Editorial:Will Modern Christian Survive 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66,no.6 (June 1935),p.392.
(63)Sherwood Eddy,"Impression of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66,no.6(June 1935),p.400.
(64)《新生活运动纲要》,载于萧继宗:《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11页。
(65)《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2月26日。转引自温波:《重建合法性》,第87-88页。
(66)参见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
(67)见温波:《重建合法性》,第92-93页。
(68)胡适:《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载于《独立评论》第95号,1934年4月8日。转引自温波:《重建合法性》,第273页。
(69)参见温波《重建合法性》,第212-218页。
(70)《新生活运动纲要》,载于萧继宗:《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6页。
(71)Arif Dirlik,"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p.946.
(72)"New Life Movement Revamped",The Chinese Recorder,vol.67,no.5(May 1936),p.311.
(73)"A Symposium,What Can Christian Co-operation Add to the New Life Movement",The Chinese Becorder,vol.68,no.5(May 1937),p.293.
(74)"Editorial:General Chiang's Christian Message",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5(May 1937),p.267.
(75)George W.Shepherd,"The New Life Movement",in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36-1937,20th issue (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37),p.70.
(76)《通告各地新运会制定青年会及教会服务团组织简则》,载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第233页。
(77)Arif Dirlik,"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p.948.
(78)黄仁霖:《黄仁霖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第55页。
(79)James C.Thomson,Jr.,While China Faced West,p.191.
(80)《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及基督教各教会新生活服务团组织简则》,载于《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263-264页。
(81)Madame Chiang,"Message to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6 (June 1937),pp.345-351.
(82)James C.Thomson,Jr.,While China Faced West,p.172.
(83)Ibid.,p.182.
(84)George W.Shepherd,"Co-operation with the New Life Movement",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5(May 1937),pp.286-290.
(85)James C.Thomson,While China Faced West,p.167.
(86)Ibid.,pp.168-169.
(87)邢军:《革命之火的洗礼》,第161页。
(88)James C.Thomson,While China Faced West,p.174.
(89)Ibid.,178.
(90)《新生活劳动服务团组织大纲》,载于《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260-263页。
(91)《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及基督教各教会新生活服务团组织简则》,第263-264页。
(92)参见《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260-264页。
(93)George W.Shepherd,"Church and New Life Movement",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5(May.1937),p.281.
(94)Ibid.,pp.281-282.
(95)"Editorial:China's Present Attitude to Christianity",p.674.
(96)"Editorial:Will Modern Christian Survive in China?",p.392.
(97)"Editorial:China's Attitude to Religi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5(May 1937),p.269.
(98)R.Y.Lo,"Christians! Support the New Life Movement!",translation of article in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5 (May.1937),p.284.
(99)Madame Chiang,"Message to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6 (June 1937),p.350.
(100)Kiang Wen-han,"Secularization of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5 (May 1937),p.302-305.
(101)Ibid.,p.572.
(102)Ibid.,p.573.
(103)Ibid.
(104)Ibid.,p.574.
(105)Ibid.,pp.574-575.
(106)见刘家峰:《徘徊于政治与宗教之间》,第90-92页。
(107)"What is the Rel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n China:A Symposium",p.575.
(108)Ibid.
(109)Ibid.,p.576.
(110)见邓元忠:《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
(111)见欧阳雪梅:《新生活运动与明耻教战》,载于《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2卷,1998年第3期,第75-79页。
(112)《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训词》,载于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55页。
(113)同上。
(114)同上书,第56-60页。
(115)《新生活运动五周年纪念训词》,载于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67页。
(116)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上海,1935,第101页。
(117)Paul Varg,"The Missionary Response to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p.311.
(118)参见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
(119)James C.Thomson,While China Faced West,p.159.
(120)C.Stanley Smith," Modern Religious Movement] In Christianity",in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34-1935,p.110.
(121)Z.K.Zia,"Should the Church Speak Out?",The Chinese Recorder,vol.66,no.9 (Sep.1935),p.543.
(122)T.C.Chao,"Christianity and the National Crisis",The Chinese Recorder,vol.67,no.1(Jan.1937),pp.5-9.
(123)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9(Sep.1937),pp.537-541.
(124)"Editorial:China's Intellectuals Break Out!",The Chinese Recorder,vol.67,no.2(Feb.1936),p.66.
(125)"Editorial:Signs for Political Co-operati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67,no.3(March 1936),p.131.
(126)刘家峰:《近代中日基督教和平主义的命运:以徐宝谦与贺川丰彦为个案的比较研究》,载于《浙江学刊》,2007年第2期,第100页。
(127)"Editorial:Sino-Japanese Christian Retreat",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8(August 1937),p.473.另:战争爆发后,日本基督教成为战争工具。日本牧师在上海组织“中国基督教会”,在杭州组织“东亚基督教会”,并在华北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表面上是华人基督教团,实际是日本人控制当地教会的机构。参见顾卫民:《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510-515页。
(128)Missionary Group in Kuling,Summer 1937,"What Can a Christian Do in Case of War?",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10(Oct.1937),pp.610-613.
(129)Ibid.,p.610.
(130)Ibid.,p.613.
(131)姚西伊:《“九一八”之后中国基督徒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与讨论》,载于刘家峰编:《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59页。
(132)R.Scott,"Editorial:The Church and the National Crisis",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10(Oct.1937),p.607.
(133)Ronald Rees,"The Witness of the Church in the Preset Crisis",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10 (Oct.1937),pp.613-614.
(134)P.C.Hsu,"Pacifism and Nationalism",(written for 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 in China).English News Letter,June,1937,cited in 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10(Oct.1937),p.617.
(135)Ibid.,p.618.
(136)Paul A.Varg,Missionaries,Chinese and Diplomats: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1890-1957(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p.255.
(137)《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训词》,第56页。
(138)《新运十年》,载于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202页。
(139)同上书,第202-204页。
(140)关志钢:《新生活运动研究》,第181页。
(141)《新运十年》,载于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260—262页。
(142)S.R.Anderson,"War-Time Service of Moore Memorial Church,Shanghai",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no.12(Dec.1937),pp.759-760.
(143)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372页。另:关于基督教新教人士参与救国运动的概况,可参见顾卫民:《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第524-5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