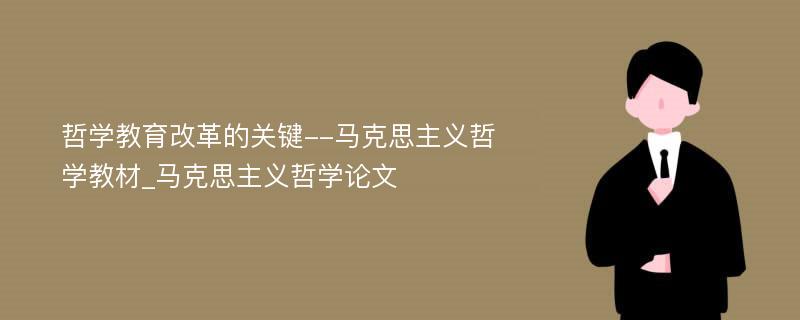
哲学教育改革之关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教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改革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教材论文,关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中国的哲学教育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这是学哲学、教哲学、研究哲学的人们的共识。
2.在文化多元和价值冲突显现的当代世界以及正在经历社会转型的中国,对精神与观念的寻觅建树,很大程度必须依靠哲学的功能。一个有着悠远文化传统、并有志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古老民族,决不会自甘沦为精神的侏儒与乞丐。中国的振兴需要精神,精神的建树需要哲学。但是,我们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实在不足以担当起这一历史赋予的重任!因此,哲学改革已是一份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和社会责任。
3.当代中国哲学状况是社会的映照与历史的积淀。极“左”思想对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伤害有多深,对哲学的伤害也就有多深。二十多年前,当中国挣脱极“左”思想影响、奋起走改革开放之路时,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即是哲学为之吹响的第一声进军号角。就这一点,中国的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愧于这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是无愧于12亿中国人对文明进步的热望和企盼的。然而,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作为一个古老而深邃的学术领域,其整体的转换和变化却是艰难而较缓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状况尤其如此。
4.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和哲学教育与研究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与地位之重要自不言而喻。因此,中国哲学改革的关键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的关键又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教材。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教材首先涉及的是一个影响“面”的问题,即这一改革有可能在很大范围和很基础的层面上产生社会效应。其次,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教材具有很强的急迫性。其三,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教材还具有拉动整个哲学学科群的作用。中国哲学要在整体上冲破现有困境并发生一场革命性“转换”,症结之处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教材,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5.在一般看法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教材的主要问题是:陈旧过时,空洞说教。这当然。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教学与教材问题(或称之为危机)还有更加深广的思想和社会原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其权威性毋庸置疑。然而,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成不变、没有发展创新的教条。因而,要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教材,必须首先把权威与丰富发展统一起来。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教材的陈旧过时,空洞说教,就是只讲权威性、忽视丰富发展、忽视理论性和学术性的结果。此外,多年来,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认识局限,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丰富涵义几乎被约化等同于斯大林式的“教科书”,并将它沿袭下来作为把握和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惟一的标准模式。中国哲学界一直受其束缚,至今尚未完全摆脱。
6.要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教材的“陈旧过时,空洞说教”,绝非仅仅作一些“修改、补充”即可收效。若要有根本改变,最重要的就是彻底清除斯大林“教科书”式的方式,以及将这一方式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和表达的惟一、正宗的模式的观念。只有这样,我们的教科书才能真正改变“千书一面”的情况。进而,哲学教学也才能不再受过去“教科书”的束缚制约,教员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就有可能被激发调动起来,“空洞说教”也就遁无踪影了。若要在教学、教员和教材三者之间选定一个突破口,教材显然更为关键。
7.沿袭斯大林“教科书”的模式构建“哲学体系”,是违背哲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这一方式也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把握和理解偏离了这一哲学的内在精髓。原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万事万物都是运动发展的,但是,哲学“教科书”本身的体系和理论构建方式,以及由它所体现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和表达的惟一性,却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发展及实现现代转换的一种制约。
8.一种“体系”就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表达方式即是一种把握和理解。无论是按唯物辩证法还是现代解释学,任何理解与表达都不具有惟一性和绝对性。固守某一种方式,并以其作为不可更改的“标准”模式,是毫无道理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和号召力就在于它自身的特色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难道还不应该从中感悟出什么来吗?
9.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肯定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教材。这种教材应是怎样的?首先,它肯定不是在现有的体系内“修改补充”就可得到的,也不是由谁来牵头“编写”就可解决的问题。其次,在教材类型上,一定要把应试性和非应试性区分开。此处因为主题和篇幅所限,应试性问题无法详论。但有一条不得不说:应试性教材或参考书籍绝不能粗制滥造。
10.非应试性教材的构架,似可循四条思路加以考虑:
11.思路一,以与对马克思、 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哲学思想发展历程研究相关联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诠释与表述。可以是关于他们全部的、整个的哲学思想历程的,也可以是关于某个人的某个阶段的哲学思想发展状况的,还可以是关于某个哲学理论部分形成发展过程的,等等。如青年时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就与其中年以及晚年的哲学思想侧重有所区别。而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所阐述的内容,往往都出之于中年时期,对青年和晚年时期的思想很少、甚至没有论及。这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把握是片面的,也抽掉了这一哲学本身的客观发展历程。而实际上,马克思和其他经典作家的思想也正如所有人的思想一样,都有它自身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都是逐渐走向完善、不断丰富充实的。而且,一个人的思想绝不可能一生都不变化。马克思在其晚年停止了《资本论》的写作,转而集中阅读人类学方面的著作,并写了一批有关人类学的笔记,这是马克思生前遗留的最后的手稿。这些笔记的内容、主题、甚至研究的层次与方法等等,都明显有别于他早期和中期的论著,其中所提出的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东方社会问题,等等(见《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都是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没有涉及到的。而马克思晚年之所以在其研究上发生这一转换,个中原因自然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这一教材的构架方式可称之为以“史”带“论”(即原理)。而有了“史”作为基础与背景,“论”就有可能成为生动的人的思想了,就不再是枯燥、呆板的教条了。
12.思路二, 以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研究相关联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诠释与表述。这一方式可称之为以“著”带“论”。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研究已出现了一些令人振奋的趋向,但从总体而言,研究还不尽人意,不仅数量少,且浮躁盛于平实的钻研,在审视与诠释的角度、方法上也有许多可探讨之处。解读、研究、讲授经典著作无疑仍然是一份学术苦差,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更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在目前高校盛行的“特聘”之风中,立志真正做这方面研究或教学的哲学人恐怕得打算“落聘”、甚至“待岗”。似乎是一个规律:“哲学的贫困”,往往只有靠哲学家的(物质)“贫困”来改变它。最终,哲学也许会感谢“贫困”的哲学家。有这一份自我慰藉算不错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异化是一个很基本的范畴,直接关系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建。而集中阐述这一范畴的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他一些早期哲学著作。如果我们能够把对这些著作的解读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发展联系起来写入教科书并讲授,再结合探求马克思在其较晚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著之中不用、或者很少用异化范畴的原由,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阐发无疑将因此而更深刻、更丰富。
13.思路三, 以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论著、思想、人物研究相关联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诠释和表述。显然,这一方式具有一定的对比研究的性质,故可称之为以“比”带“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无须怀疑。如果我们必须对此持一种“批判”的态度,那么这种“批判”的含义主要应当是“研究”。自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一百多年来,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历经了壮阔的起伏跌荡。离开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怎么可能具有国际性与现代性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闭关自守的研究,不仅是缺乏自信,而且也将把自己束缚在狭隘的囚笼中。目前,现有的教学与研究大都是两不相干,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块,“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又是一块。这一做法不仅割断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的连续性,也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其广阔的世界背景上“抠”了出来。当然,要改变这一状况是有相当难度的。不仅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观念要更开放、更明确,而且应当对它们做更全面、更详细的了解。改变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缺乏这方面必要训练的状况,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有关本体论、历史唯物论的教学中,能够联系对比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思想,辨析他提出“复活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口号,说明为什么在马克思的哲学著作之中虽然没有对本体论的专门论述,但却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没有、或者完全摒弃了本体论,以及卢卡奇关于“马克思从未放弃过用统一的历史辩证的方法去认识存在的本质”的论述,还有他提出的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方法问题,等等(参见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第1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这不仅对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至关重要,也是对深入探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这一有争议的、高难度学术问题的推进。可以想象,这样的教学必定是引人入胜的,也是有感召力和说服力的。
14.思路四, 以与对当代社会现实问题作哲学辨析与研究相关联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诠释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把对社会实际的关切作为自己的目的与责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也就在于它和社会实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研究社会、特别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社会理论。(见《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当代现实社会问题非常广泛,社会正义、生态环境、信仰信念、道德构建……,都是与社会最大多数人安身立命、生存发展紧密相关的。当人们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追寻解答时,他们必追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若能切实联系这些问题的研究,并把有关的哲学基本原理贯穿进去,空洞说教就有可能转变为紧贴实际的理论指导了。这一方式可称之以“实”带“论”。这里要明确的是,讲授哲学有关原理虽是教学的主要目的所在,但联系实际并不只是为原理寻找更多的注脚,而是要从对实际的哲学审视、辨析中,揭示哲学理论更深刻的内涵以及原理对现实的价值与意义。这不仅要求具备较高的哲学理论素养,还要求具备对社会生活的充分了解,以及恰如其分地运用逻辑分析、知识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哲学理论无疑有其抽象和思辨的一面。但任何哲学的产生及发展却决不可能没有实际的基础与源泉。不关心实际的哲学,终将为实际所离弃。
15.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教材的改革中, 能否冲破所谓“体系”的限制亦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受到其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曾一度把“体系”当成非常重要而必要的方面。但从近代到现代哲学的发展说明,对“体系”过分刻意的构建,将窒息真正有意义的哲学探索。而提出“问题”、探索“问题”则裹挟着强烈的现代气息。毫无疑问,在对“问题”的探索中也应包括了对自身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在矛盾的探索。一种哲学理论不可能没有“问题”或矛盾(逻辑的或非逻辑的),发现并将矛盾揭示出来就是哲学的一种“批判”功能,也是哲学发展前进的一个必要前提。如果时至今日,还把这种对哲学内在矛盾的揭示和研究当作是“现丑”或“给自己出难题”,真是大可不必。唯物史观是与历史决定论紧密相关的。而对于历史决定论,国内外哲学界颇多争论。波普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把历史命运之说称为“纯属迷信”,而对与之相关的历史决定论则被当作一种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拙劣方法。(见《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这自然使唯物史观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这一争论的深刻性是它关系到历史到底有没有客观规律可循,它带来的探讨无疑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特别是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发展是一个推动。对此,国内在这一问题上有较深入研究的学者提出:“我们过去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缺陷,至少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很少提到这方面的内容”;“面对非决定论的责难,我们也应该对历史决定论有一个新角度(如方法论和逻辑的角度)的辩护”。(李明华:《历史决定论的现代诠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16.在哲学的长河中,曾经产生过许多精采绝伦的哲学, 其中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却绝不意味着它们已经把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解决了,甚至给哲学发展盖帽、封顶了。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发展是生命漾溢的一道洪流,传统编结成了一条神圣的链子,将前代的创获保存下来并传递给我们。(见《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8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建立是哲学史上一次非同反响的革命,但它仍然处于哲学的历史长河之中,并通过那条链子秉承了由传统传递下来的林林总总。这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不能忽视的极重要的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