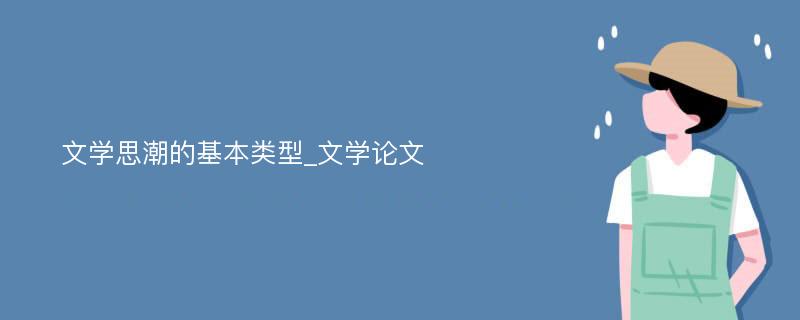
文学思潮的基本类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类型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类型研究是一种假定性很强的“特殊属性识别”,研究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论述需要而设定不同的标准将对象分类。文学思潮当然也可以按照不同的原则进行分类研究。不过,作为文学思潮理论体系建构需要的基本类型划分不是一般的分类研究,其任务是应该尽量找到与文学思潮本质特征相一致的逻辑分类原则,区分出具有“原型”意义的基本类型。
文学思潮的不同,主要决定于作为其支柱的文学规范体系的差异,而文学规范体系的核心则是文学观。一定的文学观就是对有关文学是什么(本质)、怎么样(结构、特征、发生、发展规律)、为什么(功能、价值)等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回答(或是通过范例获得的直觉感悟)。因此,我们可以从不同文学观的认识特征寻找文学思潮基本类型的划分原则。
任何认识都存在着客观的和主观的两个对立面,文学观的思考也存在着这两个对立面。歌德在谈到自己和席勒在创作方法上的对立时,所谈的是艺术原则层面的对立,他“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出发的原则”,而席勒却认为自己从“完全主观”出发的原则才是正确的。(注:《歌德谈话录》2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这里的艺术原则的对立,也就是文学观的对立,实质上这是从主观出发还是从客观出发去认识文学、从事文学活动的思维方式的对立。因此,我们可以把从客观出发还是从主观出发的艺术掌握方式作为文学思潮基本类型划分的原则。由于主客观的区别也是相对的,所以没有完全纯粹的主观或客观。事实上两者总是互相矛盾又互相渗透融合,两者之间的若即若离存在着无限的层次。不过两方面总有轻重主次之分,同时也存在着历时或共时向度的错杂而难分伯仲的情况。据此,我们把文学思潮分为客观型(从客观出发的原则为主体的)、主观型(从主观出发的原则为主体的)和复合型(主、客观原则难分主次的)三大类。
客观型文学思潮
从客观世界出发的艺术掌握方式占主导地位形成的文学观,把文学视为客观世界的摹仿或反映,文学的任务在于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真实性是衡量这类文学价值的美学准则。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艺术关注指向客体;在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中,要求文学倾斜于现实;对待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则要求让理智占上风。客观型文学思潮就是由这样的文学观念规范体系支配的文学活动系统的群体性观念整体。现实主义、自然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属于这类客观型文学思潮。现实主义要求以真实的细节、典型化的艺术形象、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社会生活,不仅要如实地再现社会生活的外在形态,更要通过这种形态提示出它的内在本质、价值及其必然性。由于认识到文学是社会的反映,所以巴尔扎克才立志要通过自己的小说写出十九世纪前期的法国历史。契诃夫清楚地知道按照生活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的现实主义必须做到“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注:《契诃夫论文学》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高尔基则把现实主义称为“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不加粉饰的描写”的艺术。(注:高尔基:《论文学》1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普希金、果戈里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在俄国刚出现不久,别林斯基就在对他们的创作进行的批评实践中,建构起俄国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促进了俄国现实主义思潮的形成和迅猛发展。现实主义要求冷静、精确地剖析现实,但并不排斥主观倾向和理想,只是要求这些主观倾向和理想在艺术形象的客观描写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无须直白。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一样要求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但更彻底,要求达到科学般精确,严格地再现,把观察到的事实按原样描写出来,不进行任何增、删,不作任何政治的道德的和美学的评价,让读者看来就像报道和记录一般。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所具有的“魔幻”一面的特征,似乎不符合“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客观型文学思潮标准。而且在人们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论评中,早就存在着种种异议,有人根据它与超现实主义的关系及其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技巧的借鉴而把它归入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还有人把魔幻现实主义纳入后现代主义的范畴;而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些文学大师却始终坚称自己的创作是现实主义。尽管从创作特征上看,魔幻现实主义表面上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面目也相去甚远,但是细细考察之下,会发现它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末同而本异,与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审美原则却是一脉相承,不过这种一脉相承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具有了新的发展。从文学观、审美原则而言,魔幻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样,坚持文学是现实的反映、再现。现实的真实性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活动的审美依托和价值准则。著名的魔幻现实主义大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伟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谈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时,就宣称在自己所“写作的任何一本书里,没有一处描述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在他看来,“现实是最高明的作家,我们自叹不如。我们的目的,也许可以说,我们的光荣职责是努力以谦虚的态度和尽可能完美的方法去反映现实”。他还说自己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总感到在自己所构思的和能够写出来的东西中,从未有一件事是比现实更令人吃惊的。我力所能及的只是用诗的手法移植现实。”(注: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谈文学与现实》,马尔克斯·罗德里克斯:《卡彭铁尔的神奇现实论》,转引自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156—157、20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有神话,有与现代主义相似的荒诞、幻想和夸张,形成了神奇的美学特征,但这一切都有客观的现实基础,都不是无端的主观虚构。因为拉丁美洲社会生活本身就是充满神奇色彩的现实,全部美洲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神奇现实的编年史”。(注:阿莱霍·卡彭铁尔:《〈这个世界的王国〉序》,《小说是一种需要》85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拉美文化是拉美本土的印第安文化和来自欧洲的基督教文化还有非洲的黑人文化的融合物,“美洲是不同时期共存的大陆。在这块大陆里,二十世纪的人可以向四世纪的人伸手,可以向如同没有报纸、没有通讯的居民伸手。”(注:见李德恩:《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5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印第安土著的无穷想象力、黑人的无穷想象力以及西班牙人的幻想和鬼神崇拜的混合,成为拉丁美洲现实神奇性的精神沃土。马尔克斯列举过拉丁美洲暴君的神奇暴政事实。他说:“海地的老杜瓦利埃曾下令把全国的黑狗宰尽杀绝,因为据说他的一个政敌,为了逃避这位独裁者的迫害,甘愿不再当人而变成一条黑狗。弗朗西亚博士享有哲学家的盛名,但他却把巴拉圭共和国封锁得像一所房子,只让打开一扇收取邮件的小窗,……路佩·德·阿吉雷(委内瑞拉)的一只断手在河里顺流而下,飘浮了多日,凡是看见断手飘过的人无不胆战心惊,生怕那只杀人的手在那样的情况下还会挥舞屠刀。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加西亚,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喂养动物。每只笼子都分成两格,中间只有铁栅间隔,一边放着猛兽,一边关着他的政敌。萨尔瓦多笃信鬼神的独裁者马丁尼斯,让人们把全国的路灯统统用红纸包裹起来,说是可以防止麻疹流行。他还发明了一种像锤子那样的东西,在进餐前先在食物上摆动两下,便知道食物中是否下过毒药……”。还有,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一夜之间,强盗变成了国王,逃犯变成了将军,妓女变成了总督”,或与此相反的情况都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现实。(注: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谈文学与现实》,马尔克斯·罗德里克斯:《卡彭铁尔的神奇现实论》,转引自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156—157、20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在印第安文化背景下运用印第安人原始思维来观照现实的,这也是其神奇性的重要根源。“印第安人以想象来思考问题,看不见发展过程中的事物,而是把事物带到另外的领域。在那些领域里,现实的东西消失了,出现了梦幻;在那些领域里,梦幻的事物又变成了可能触摸的和可见的事实。”(注:见李德恩:《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6—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印第安人的“现实”包含着物质世界的现实和幻想世界的现实,两种现实的统一组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两种现实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区别的,都是客观的、真实的。魔幻现实主义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现实”——拉美大陆独有的、无处不在的神奇现实,它生动、奇妙、原始。它或者如卡彭铁尔的《这个世界的王国》那样,“叙述的历史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的,不但历史事件真实,连人物(包括次要人物)、地点、街道以及一切细节都真实无误”(注:见李德恩:《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13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原封不动地予以再现,不需要任何加工;因为这一现实本身便是神奇的、现成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并且是伸手可及的。”(注: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谈文学与现实》,马尔克斯·罗德里克斯:《卡彭铁尔的神奇现实论》,转引自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156—157、20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或者如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无论怎样夸张、幻想,都“百分之百源于现实”——拉美“特有的现实”。
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和科技文明的空前进步,反而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普遍的日益严重的异化现象。如果说现代主义文艺表现的是人们在异化生活中内在的恐惧感、危机感和灾难感的话,后现代主义则关注人的自我的消失、人的物化、世界的无意义和不确定性。例如理论上的解构主义就“产生于一种特定的政治失败或幻灭感”,导致对真理、现实、意义、知识等传统概念的怀疑直至否定,在政治颠覆的尝试(1968年席卷欧洲的学生运动)失败后,“转入地下,进入语言领域”,通过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进行语言结构的颠覆。(注: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169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运用这一理论的批评实践就是从似乎清楚严密的原作中找出“一些弱点和缝隙,然后努力扩大已经露出的裂口,终于使原来似乎明确的结构消失在一片符号的游戏之中。”这种解构批评旨在指出作品本文的自我消解性质,论证不存在恒定的结构和明确的意义,否认语言有指称功能,否认作者有权威和本文有独创性,否认理性、真理等等学术研究的理想目标。(注: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164、165、16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观表现在创作上是对传统创作模式的全面颠覆,他们的小说没有传统小说那样完整的故事情节,主人公和人物也不再是作品的中心,作品的主要篇幅让位于大量物象的详细描写,主人公在小说中就像摄像机的镜头,所起的作用不过是将所有场面、人、事景物组接起来,他没有思想感情,没有性格特征,甚至连面貌、经历、家庭、社会关系、行为及其动机,在作品里都找不到明确交代。在叙述方式上,时空混乱、杂糅,任意切换,语句矛盾或模棱两可。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所要表明的就是不同于传统观念中的现实世界的真实,它不再是“充满心理的、社会的、功能的意义的世界。”(注:阿·罗伯—格里耶:《未来小说的道路》,《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上卷52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5。)真实的情况是:人不是世界的中心,客观世界是独立的存在,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世界充满了偶然性、不确定性。复杂多变,无规律可言。不仅客观世界而且主观世界也像迷宫一样,人们无法辨识。正由于世界是“不稳定的,是浮动的,令人捉摸不定,它有很多含义难以捉摸”,所以,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就应该“从各个角度去写,把现实的飘浮性,不可捉摸性表现出来。”(注:罗伯—格利耶语,转引自柳鸣九:《艺术中不确定性的魔力》,《嫉妒》134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给读者“制造出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注:阿·罗伯—格里耶:《未来小说的道路》,《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上卷,52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可见,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尽管对“现实”的理解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但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强调前者必需“真实”、“客观”地表现后者,这一“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还是一致的。
1987年在中国出现的“新写实”小说(或称“新写实主义”小说)标志着先锋态势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转向,它的主要特征是“写实”,但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写实”不同,它所要写的不是蕴含着崇高、理想等社会价值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之“实”,而是芸芸众生日常生活的原生态,流水账般记录普通人平庸琐碎的生活事实,他们也强调真实、客观,自称“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生活的本来面目”。(注:刘震云语,见《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池莉声称她的小说《烦恼人生》中的细节非常真实, 主人公印家厚的一天,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因为儿子从床上滚下地上,惊醒了全家,这时候是“凌晨四点缺十分”。八点上班之前,他得送孩子去幼儿园,乘公共汽车,为保证上班不迟到,得赶上六点五十分的那班轮渡。这一天赶到工厂时,还是迟到了一分半钟。然后是上午、中午、下午,在工厂工作、扯皮、发牢骚,晚上下班回到家里为家务杂事忙碌、争吵、烦恼;“上床时,时针指向十一点三十六分”。作者说这里记述的“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我不篡改客观现实”。(注:见《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作家为了在记述原生态生活时达到客观、真实,坚持以冷眼旁观的局外人态度——“零度的感情”进行叙述,不加任何评价,力求达到比较彻底的“无情观”——“用一种冷酷的态度把所见到的生活中的人和事娓娓道来。”(注:李书磊:《刘震云的勾当》,《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1期。)新写实小说“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 (注:《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钟山》1989年第3期。 )注重生活画面的逼真和细节的真实,不放弃人物故事,这与现实主义传统何其相似,但它却没有像现实主义一样致力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抛弃了典型化的艺术概括原则。新写实小说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历史、美学意识,采用了现代主义的一些艺术手法,但他的重视细节和人物故事又与现代主义作品相去甚远。它对“原生态”生活的还原追求与自然主义相通,可是它虽有生理、心理病态的描写却又没有完全强调生物学的决定论。它的平面化、“零度情感”与后现代主义的要求抛弃“深度”、意义,冷漠叙述、记录所见所感知的世界的零碎片断的主张一致,但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描写还没有超出现代主义的模式,没有跨进后现代主义把人物淡化为影子而以物象为描绘中心的境域。将新写实小说纳入上述任何一种文学思潮都可能引起异议,但从类型的意义上,把它归入“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客观型文学思潮范畴内,应该是合适的。
主观型文学思潮
以“从主观出发”为原则的文学观念规范体系是主观型文学思潮的核心,其审美依托与艺术指向是主体的主观愿望或幻想。对人性、主观情感、非理性的幻想世界、直觉、潜意识、生命冲动等等的表现被视为文学的本质。这类文学思潮的主体失去了与自然或其自身的统一性,在主客观的对立矛盾中,很容易取消二者的差别,混淆二者的界限,而用主观取代客观。因此,要求文学排斥客体、实体,以主观的理想、幻想、思辩的观念取代既存现实。即使作品中有指向外部世界的客观事物,也应该是与自身相对立的主观的象征。非理性主义倾向是主观型文学思潮的共同特征。但是,不同的主观型文学思潮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有强弱之分,艺术指向也有不同维度的差异。例如,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主观性非常强烈,然而它与现代主义的种种文学思潮、中世纪的宗教文学思潮的主观性就有所不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其他主观型文学思潮在与现实的关系上,都表现出强烈的拒斥和脱离现实的趋向,但浪漫主义对现实的排斥体现为对日常生活、艺术情感以至传统道德全部领域的习俗束缚的轻蔑,要求与过去的、现在的现实完全断绝关系,主张“以审美的标准代替功利的标准”,(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下)216 、217、2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所以,喜欢奇异的、遥远的、异域的和古代的事物,从宏伟的、渺远的、恐怖的事物中寻求刺激,赞赏破坏性极大的激情,凶猛的老虎因而得到布雷克的赞美。在浪漫主义的小说故事里,读者可以“见到汹涌的激流、可怕的悬崖、无路的森林、大雷雨、海上风暴和一般讲无益的、破坏性的、凶猛暴烈的东西”。或者是“幽灵鬼怪、凋零的古堡、昔日盛大的家族最末一批哀愁的后裔、催眠术士和异术法师、没落的暴君和东地中海的海盗”。拜伦笔下的“拜伦式英雄”不是反社会、无政府的叛逆者,就是好征服的暴君。(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下)216、217、221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6。)但是,浪漫主义追求的是个体人格的解放,尽管有着反理性的倾向,但其理想主义的主观愿望“还主要停留在社会理想、社会意愿的层面上,因此它并不全然抛弃现实生活,只是主张通过对现实生活进行想象和幻想性的加工处理而将理想展现出来。”(注:周来祥等:《西方历史上的五大文学思潮》,《文艺研究》1990年第2期。 )中世纪的宗教文学思潮呢,虽然也是要求与现实断绝关系,却比浪漫主义更彻底,文学完全是宗教教义的图解,世俗生活被描写为罪恶的悲哀的渊薮,而空想、梦幻、彼岸性的世界却是真实的、美的领域。现实的所有事物都只是象征、寓意的符号,任何能引起审美兴趣的东西,无非是指向彼岸的能使人们推测到比现实更美的世界的东西。女人的形象如果不是天使的象征,就是魔鬼的化身。文学的内容主要是对原罪、世俗生活的罪恶和死后世界的赏罚不同、以及种种宗教奇迹的描写,梦幻、象征和寓言是主要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但丁的《神曲》虽然透露着新世纪的人文主义的曙光,但从内容到形式,仍然保留着宗教文学思潮的许多特征。作品在宗教幻想中的地狱、炼狱和天堂三界的空间里展开了一个神秘的梦幻故事,全诗弥漫着浓厚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气氛,它所写的一切都是象征。诗人象征了人类精神,贝阿特丽采象征信仰,维吉尔象征理性,黑暗的森林象征意大利丑恶的现实,三头拦路的野兽象征着邪恶势力。诗人游历三界,象征着人类在理性和信仰的引导下,认识罪恶与错误而觉醒,获得新生,并达到理想的至善境界的历程。宗教文学思潮从主观出发,建造的是一个极端反理性的彼岸世界,既否定现实,也否定主体,可以说是主观的异化。而现代主义从主观出发的非理性主义并没有离开主体,只是深入发掘主体局部的非理性的精神因素,并将其夸大成世界的、人类的、文学的、艺术的本质,达到荒谬和神秘的地步。现代主义文学观可以说是强调自我表现的文学观,真实、真理都在于自我的主观感受,主观性就是真理,自我永远是惟一真实的存在。但这种“自我”已不同于浪漫主义的反抗现实要求通过文学改造世界的“自我”,现代主义者心目中的“自我”、“自我存在”、“主观”、“人”甚至现实“世界”都是非理性的个体的情绪体验。生活也只是这样一种情绪体验,是人们的头脑在日常中接受的“千千万万个印象”,“这些印象来自四面八方,宛然一阵阵不断坠落的无数微尘”,文学的任务就是真实地“记录”这些“微尘”般的印象,“不管表面上看来互无关系,全不连贯”。(注:伍尔芙语,见《外国文艺》1981年第3期, 209—211页。 )这种印象可以是由墙上的一个斑点而引起的漫无边际的自由联想,也可以是在世界的荒诞、人世的险恶、灾难临头之类恐惧感、危机感压迫下出现的人变甲虫、人变犀牛的梦境、幻觉。一切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体验、本能冲动、潜意识心理、瞬间情绪、梦境幻觉的表现,都植根于社会异化、理性危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彻底分裂的现实土壤。当自然、社会、客观世界、宗教、道德、理想、祖国、家庭、民族感情等等的真实感、神圣性和信念都破灭之后,“自我”就成为惟一可以抓住的现实,犹如在大海中抓住的一块救命的木板。现代主义者只能在“那由于孤独和难以表露的性欲和失去理性的心灵”——一个未知的非理性的领域里寻找“表达人类共同性的新语言”。(注:《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谈创作》1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复合型文学思潮
从文学观的认识特征来看,顾名思义,复合型文学思潮的文学观就是主观型和客观型的合成,即它既有“从主观出发”一面,又有“从客观出发”的一面。事实上,任何文学思潮都有程度不等的复合性,只不过复合的比例、程度有种种不同而已。因为,从主观出发还是从客观出发不可能绝对化。强调“从客观世界出发”,仍然离不开主观性,外界现实的再现,仍然是通过主观审美的投影,再现的客观世界即使是自然主义或新写实文学都做不到真正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无论如何隐蔽,主观性虽不直接露面,却又无处不在。同理,“从主观出发”也不可能丝毫不沾客观的边边,无论怎样的自我表现,都有其产生的现实基础;不管多么荒谬、怪诞、神秘的非理性主义抽象表现,都有其现实性的反映,都离不开客观时空、物象媒介的传达。我们这里说的复合型文学思潮是指这样的一种复合状态:这种状态的文学思潮若按“从主观出发”的原则去考察,它完全具备主观型文学思潮的特征;如果拿“从客观出发”的标准去衡量,它也符合客观型文学思潮的要求。然而,我们又不能把它划进任何一边,因为两者的特征都明显,划进任何一边似乎都有失公允。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就体现了这种复合型的特征。
过去,大多数观点都把古典主义视为现实主义,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有人指出了这一认识的不当,并分析了这种错觉的根源和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所具有的主客观复合的特征。人们为什么会把古典主义看作是再现主义或现实主义呢?主要原因在于布瓦洛提出的理论主张:“我们永远也不能与自然寸步相离”。这一主张表面看来是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再现主义审美原则。但实际上,布瓦洛所说的“自然”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继承的。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主张“艺术摹仿自然”,长期以来,人们也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是现实主义的艺术观,都没有注意到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人指责诗人所描写的事物不符合实际,也许他可以这样反驳:‘这些事物是按照它们应当有的样子描写的’。”(注:亚里士多德:《诗学》第25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论者认为,这段话可以证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艺术摹仿自然’并不是要求艺术作品‘符合实际’,而是要求艺术作品按照‘应当有的样子’去描写生活。”(注:周来祥等:《西方历史上的五大文学思潮》,《文艺研究》1990年第2期。)的确,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25章中谈到艺术有三种摹仿对象:“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注:亚里士多德:《诗学》第25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哪一种更好呢?《诗学》表明亚里士多德更赞成第三种,即象索福克勒斯那样“按照人应有的样子来描写”。为什么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艺术的目的即功能在于通过摹仿使人产生怜悯和恐惧并从这些情感的体验中得到陶冶(净化),因此,“即使诗人写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他固然犯了错误,但是,如果这样写,达到了艺术的目的,……能使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诗更为惊人,那末这个错误是有理由可以辩护的。”“为了获得新的效果,一桩不可能发生而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注:亚里士多德:《诗学》第25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应当有的事(样子)”既“可能”发生,也不排除“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应当有”的实质按亚里士多德对诗的本质的规定应指“普遍性”、“必然性”。十七世纪古典主义对亚里士多德“艺术摹仿自然”这一观点中“自然”这一概念的理解,强调的就是这种“普遍性”和“必然性”。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也正确地指出过古典主义理解的“自然”“并不是自然风景,也还不是一般感性现实世界,而是天生事物(‘自然’在西文中的本义,包括人在内)的常情常理,往往特别指‘人性’,自然就是真实,因为它就是‘情理之常’。新古典主义者都坚信‘艺术摹仿自然’的原则,而且把自然看作是与真理同一,有理性统辖着的,这就着重自然的普遍性与规律性。”(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18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请听布瓦洛的阐释:“谁能知道什么是风流浪子、守财奴,/什么是老实、荒唐,什么是糊涂、嫉妒,/那他就能成功地把他们搬上剧场,/使他们言、动、周旋,给我们妙呈色相。”(注:布瓦洛:《诗的艺术》,《西方文论选》上卷301—30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体现在创作中,就是“类型化典型”——人物都成了“普遍性”——某种观念或情致的化身:熙德——“荣誉”、贺拉斯——“义务”、安德洛玛克——“贞节”、阿巴贡——“吝啬”、答丢夫——“伪善”。“类型”是一种特殊属性的抽象结果,它排除了事物的个别性、偶然性,也就使得类型化的人物性格缺乏丰富性、生动性和发展的动态性。文学思潮的主体在进行文学活动之前,头脑里就预置了审美对象的固定模型:“每个年龄都有其好尚,精神与行径。/青年人经常总是浮动中见其躁急,/他接受坏的影响既迅速而又容易,/说话则海阔天空,欲望则瞬息万变,/听批评不肯低头,乐起来有似疯癫。/中年人比较成熟,精神比较平稳,/他经常想往上爬,好钻谋也能审慎,/他对于人世风波想法子居于不败,/把脚根抵住现实,远远地望着将来。/老年人经常抑郁,不断地贪财谋利;/他守住他的积蓄,却不时为着自己,/进行计划慢吞吞,脚步僵冷而连蹇;/老是抱怨着现在,一味夸说着当年;/青年沉迷的乐事,对于他已不相宜,/他不怪老迈无能,反而骂行乐无谓。”(注:布瓦洛:《诗的艺术》,《西方文论选》上卷301—30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这就是歌德指出的“为一般而找特殊”的“程序”。朱光潜先生认为“为一般而找特殊”的意思就是“从一般概念出发,诗人心里先有一种待表现的普遍性的概念,然后找个别具体形象来作为它的例证和说明”。(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4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例如莫里哀的《伪君子》,就是以答丢夫这个“特殊”表现“伪善”这个一般概念。所以答丢夫才成为“追求自家恩人的妻子时是伪善的,侵占财产时是伪善的,讨一杯水时也是伪善的”。(注:布罗茨基等编:《俄国文学史》上卷38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如此类型化扁平人物,或者说是“寓言式的抽象品”,可知古典主义文学观并不是完全从客观出发的,也有从主观——概念出发的一面。古典主义者既要再现客观生活,又要表现主观的观念,“因而只能将那些与观念相吻合的生活内容纳入自己的艺术作品,而将那些不符合认识范式的生活内容全部舍弃。”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中主客观的对立统一,“必然导致理想与现实的和解”、“情感与理智、天才与勤奋的结合”。古典主义文学创作中尽管展示了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和尖锐冲突,但冲突的结果“并没有象历史的本来面目一样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完成,而是在一种‘大团圆’式的艺术梦幻中被人为地化解和冲淡了。”(注:周来祥等:《西方历史上的五大文学思潮》,《文艺研究》1990年第2期。)悲剧《熙德》中的贵族青年罗狄克和施曼娜面对爱情和伦理的冲突,按现实的发展,他们只能选择爱情而抛弃伦理责任,或反之,只能顺从伦理而牺牲爱情。作者却从观念出发,借助于国王出面干预,年轻人既不悖于伦理,又实现了理想的爱情。《伪君子》中的资产者奥尔恭上了伪君子的当,本该难免被答丢夫篡夺财产和受到法律惩治的悲剧下场,但莫里哀也突然搬出国王,以国王的英明,洞察秋毫,使奥尔恭转危为安,害人的答丢夫则被逮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就这样贯穿于古典主义文学活动的所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