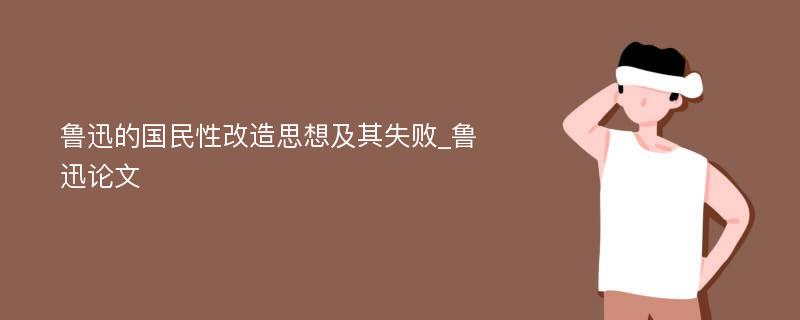
鲁迅改革国民性的思想及其失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国民性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12-0150-05
死后被尊为“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鲁迅,在青年时代就从提倡文艺运动的失败中反省 ,看见了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①他又感叹“中国一向就少有 失败的英雄”,而“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 亡。”②其实鲁迅自己就是这样一位少有的失败的英雄,失败于所为乃是他几乎命中注 定的莫大的悲剧。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一切真正的英雄”“其命运只能是悲剧 性的”,③而这种悲剧性本质上产生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 现”之间的冲突。④
一
国民性问题自20世纪初即受到中国第一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视。1902年梁启超创 立“新民”说,倡导“道德革命”,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敬告青年》等 文章,都系统阐述了改造国民性的理论主张。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就是在日本弘 文学院开始的,几乎与梁启超同时,但他思考的重点不是构建理想国民性的体系,而是 挖掘现实国民性的弱点和病根。否定性思维和韧性的战斗是他独具的特质。鲁迅对中国 国国民性的感情最热烈,认识最深刻,批判最彻底,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后期比前期有发 展,但执着于改革国民性的思维方式和奋斗目标始终没有改变。
鲁迅没有系统论述中国国民性的宏篇大著,他对国民性弱点或曰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主 要通过小说和杂文进行。写阿Q就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⑤其他 文学形象,包括“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⑥也莫不直接或间接地指向改 革国民性的总主题。杂文的形象性虽不如小说,但意旨比小说更明显,表达也较直接, 无论是文明批评还是社会批评,大都与国民性问题有关。他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 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⑦而“‘中国的大众的 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⑧粗略地罗列一下,鲁迅在杂文里明确指出过 的中国人国民性的弱点就有:卑怯、凶残,贪婪、自私,敷衍、守旧,昏乱、迷信,调 和、折中,麻木、健忘,无特操,信命运,要面子,眼光不远,善于做戏,自欺欺人, 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不敢正视人生的瞒和骗,不能平等待人的骄和诌,只求做稳奴 隶的苟且偷生,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等等。上述种种有的表面上似乎自相矛盾,它们也 并不一定同时都暴露出来,在不同条件和处境下表现即有所不同。对此,鲁迅在一篇讨 论国民性的“通讯”中有十分精辟的分析:
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 庸。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 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务,看见别人奈何他 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 ;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 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 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 下好看的假面具来。⑨
他以凶兽和羊为喻,认为“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 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但对于 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 去,一定要完结的。”⑩
中国人国民性的弱点决不是天生的、固有的。王瑶先生在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时发表 专文《谈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把鲁迅在杂文中多处讲到的国民性弱点产生的原因 大致准确地概括为三点:“首先是封建等级制度”,“其次是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 第三,“屡受外来侵略”,“这就说明,鲁迅对国民性弱点的分析既是从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现实出发,同时又是考察了它所形成的历史根源的。”不过,说“无论国 民性的积极面或消极面,鲁迅所注视的对象都是劳动人民”,(11)却并不尽然。至少, 鲁迅还密切注视着自己所属的中国的文人,即所谓知识分子,而后者当时尚未被视为劳 动人民一部分,事实上两者也不可能混为一谈。因此,说鲁迅关注的重点是劳动人民还 可以,说“都是”则有偏颇,这里关键是对国民性的解释。在鲁迅笔下,“国民性”是 与“国人的魂灵”、“民族根性”、“中国人的性情”等类词语同义的,用现在的话语 就是中国人——鲁迅所指实为中国的汉族人——的文化心理,即形成和表现为民族文化 的心理特质。鲁迅把儒家所谓的乱世治世“直截了当”即一针见血地称为“想做奴隶而 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12)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 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 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13)存在决定意识,所以,“中国的文化 ,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14)其中所显示的奴性心理(奴 隶性和奴才性)就是国民劣根性的核心。这种文化属于全民族,奴性心理更非劳动人民 所独有。它来源于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即所谓“圣人之徒”,依靠专制和“话语 霸权”得以普及,上行下效,逐渐深入人心,形成根深蒂固的国民性。“愚民的发生, 是愚民政策的结果。”(15)“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乱世时‘成则为王败则为贼’,平常 是一个照例做皇帝,许多个照例做平民;两者之间,思想本没有什么大差别。”(16)皇 帝统治时如此,“民国”以后呢?“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 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 表。”(17)鲁迅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 治地位的思想”(18)可谓“暗合”。
当年王瑶先生之所以强调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阶级性,是为了反驳“那种不加分析 地认为鲁迅这一思想属于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范畴”的错误观点。(19)正是由于那种庸俗 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的阶级论对人性论的简单粗暴的批判,鲁迅改革国民性的思想被尘 封了几十年。按照马克思的想法,“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 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20)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共同人性(即人的一般本性) 、性别之性、民族性或国民性、时代性、阶级性、地域性以及因家庭、婚姻、身体状况 、所受教育、社会关系、职业、经历等等形成的个性,极其复杂地构成矛盾统一的特殊 形态,因而“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其中,阶级性和国民性或民族性都是在特定时 代——还应加上特定民族、国家、地域等——“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而民 族、国家远比阶级的历史长久稳定,所以,鲁迅说得极是:“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 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21)然而一个国家的振兴,社会的改良,民族的进步,“根 柢在人”,“首在立人”,(22)必须抓住国民性的改革,才算是抓住了根本。“倘不将 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23)再难也要改。纵无灵 丹丹妙药,鲁迅还是开出了治本良方,一是科学,一是革命。鲁迅前期极重科学,致力 于思想革命,后期偏向革命,仍肯定科学救国。它们与改革国民性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这是一条漫长的不平的路,鲁迅艰苦求索,走完了一生。
二
鲁迅改革国民性的思想形成于留学日本时期,自然受西方和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他 很早就研读过美国传教士史密斯著的《支那人气质》(日译本)。他以“拿来主义”态度 ,对外国人的话语有鉴别,有分析,有取舍,决不照搬,更不盲从。他以和拜伦对奴隶 “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24)相同的且更为真诚博大深切热烈的爱心 ,对中国国民性之愚弱陋劣痛下针砭,目的在治病救人,使“民魂”得以发扬,人性趋 于健全,摆脱奴隶的地位和心理,“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25) 这和某些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时那种居高临下、冷眼旁观,甚至恶意欣赏或妄加指责 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但鲁迅对外国人的指责并“不很发生反感”,他由此而“博观和 内省”,分别情况予以弃取。例如,对史密斯《支那人气质》里“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 做戏味的民族”,“体面”是构成国民性的重要“关键”,鲁迅不仅坦然承认,而且进 一步开掘和批判。而对日本人安冈秀夫《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却显然有所保留 ,并嘲笑了作者对中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穿凿附会者多,例如说中国菜“将 肴馔和壮阳药并合”之类的臆断。(26)他认为日本新出的所谓“支那通”尚无真通,而 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虽然错误亦多”,但“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 中国人一看”。(27)鲁迅说:“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 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 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28)鲁迅决 不是从外国传教士那里,而是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亲身观察(阅读)、体验、研究中获 得国民性的真实而深刻的认知的。首先是现实:“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 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29)“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 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30)其次是历史:“我 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 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 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 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 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 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 ‘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31)同时把历史和现实联系比较:“历 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 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 无关。……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32)“二十多年前,都说 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 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 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 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33)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和批判在认识论和方 法论上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是真正科学的。
正如王瑶先生所言:“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一贯的,包括前期和后期。所谓改造 国民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揭露和批判国民性的弱点,一方面是肯定和发扬国 民性的某些优点,其目的都在促进一种新的向上的和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的诞生。 虽然他对国民性问题认识的深度和侧重点前后期有所不同,但这两方面的内容无论前期 或后期,都是存在的。”可是,说“如同鲁迅的思想经历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的发展过程一样,他的‘立人’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34)这 一论断却值得重新斟酌。鲁迅前期的“立人”思想虽有空想成分,主要表现为夸大文艺 改变人们精神的力量,但“致人性于全”(35)的美好理想则不应视为“空想”,否则共 产主义理想亦当以同类视之,而他对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运动”的质疑却无疑证 明了他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和科学精神。后期的“立人”思想虽在文艺宣传作用的估价上 较为实际,认识到文艺的无力,但仍坚持前期改革国民性的基本主张,肯定和发扬优点 的有所增加,揭露和批判弱点的力度不减,而自认为“觉醒了起来”的“阶级意识”(3 6)的科学性则还有待历史的验证。
值得一提的还有两点。
一是鲁迅在竭力攻打国民性弱点和病根的同时又常常以希望给人鼓舞,这也是一贯的 ,不过后期比较具体,前期显得抽象。但抽象的倒比具体的更有不朽的内在的哲理性和 生命力,不会因时过境迁而被淘洗。他号召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 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因为“ 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 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37)鲁迅离京南下前在女师大作最后一次讲演,结尾就 是一段情理兼备、境界高远的安慰和鼓励的话:
我们总是中国人,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是过 着受破坏了又修补,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我们所可以自慰 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 ,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 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 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 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38)
这种启示般的预言,比后期确信“苏联的存在和成功”、(39)“一个簇新的,真正空 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40) 是从空想到科学,还是从科学到空想,历史已经做出了新的回答。
另一点是鲁迅对中外国民性的比较,重点是中日比较,在一贯中且有发展。1925年在 《出了象牙之塔》(厨川白村)的译文《后记》里,鲁迅写道:“著者呵责他本国没有独 创的文明,没有卓绝的人物,这是的确的。……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 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着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 于生存。不象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 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 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他又说:“著者所指摘的微 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着中国。尤其是 凡事都做得不上不下,没有底力;一切都要从灵向肉,度着幽魂生活这些话。凡那些, 倘不是受了我们中国的传染,那便是游泳在东方文明里的人们都如此,……但我们也无 须讨论这些的渊源,著者既以为这是重病,诊断之后,开出一点药方来了,则在同病的 中国,正可借以供少年少女们的参考或服用,也如金鸡纳霜既能医日本人的疟疾,即也 能医治中国人的一般。”(41)而在1936年的一封通信中这样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 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 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 ,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42)鲁迅通过中日文化的比较诊治中国国民性的痼疾,昔 日的类似和后来的反差应使近代惨遭日本侵略的中国人警醒和深思。在他后期改革国民 性的思考中,不同民族和国度间的文化对比研究似乎比依据“阶级意识”的论说更具科 学性。他深刻地揭示了国民性源于人的本性的历史性变化及其复归的路,由此特别重视 教育儿童对改革国民性的意义。他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照相),透视中外儿童教育的 差异,分析两种文化的“动”“静”之别,深挖国民性的病根,并提出恢复健康的方法 。“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 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 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 ‘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 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下面这段文字最值得注意,包含了极其丰富而精深博 大的思想: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 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 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接着又补充一句:“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 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43)我以为,这篇《从孩子的照相说 起》,和写于同年稍后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样,都可以看作鲁迅改革国民 性思想重要发展的标志。
三
从鲁迅在日本与许寿裳讨论国民性问题至今,一个世纪已经过去。革命已使中国社会 几度沧桑,科学也在追赶西方缩小差距,然而国民性的改革步履维艰。只需想想文化大 革命中国民劣根性的恶性膨胀,民族道德水准的全面下降,看看近年愈演愈烈的集体腐 败,遍及各领域的“假冒伪劣”,我们就无法盲目乐观。鲁迅改革国民性的失败还不只 在国民性进步的缓慢,而且在他的这一思想并未被接受。精神上的讳疾忌医本是中国人 的通病。五四以来文化保守主义的国粹派、新儒家和政治激进主义的新老革命左派,不 谋而合地拒斥改革国民性。半个世纪统一国民鲁迅观的“三个伟大”的最高评语和把鲁 迅神圣化的宣传教育,恰恰割掉了鲁迅思想的这一精髓。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所谓知识 分子自我感觉太好,他们也许崇尊鲁迅,但或者不知国民性为何物,或者否定自身有劣 根性。更不消说从来不曾停止过的敌对党派的诬蔑和流氓文人的谩骂,近年来一方面是 笼罩在鲁迅研究上的传统的阶级论阴影尚未完全消散,另一方面则是国粹主义乘后殖民 主义思潮再度崛起,借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否定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从 根本上否定鲁迅的思想和成就。鲁迅却似乎早已预料到身后将向他泼来的污水,在《从 孩子的照相说起》最后写道:“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我相信自己的 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 ,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44)
其实,鲁迅并非不知道国民性的顽固和改革的困难,他是异常自觉地献身于这项生前 看不到胜利的工作,在《野草》里就曾描绘自我的形象,一个“失败的英雄”,在“无 物之阵”中老衰、寿终的“这样的战士”,“无物之物”——国民性——则是胜者。“ 但他举起了投枪”,(45)他的投枪就是一枝笔,“我明知道笔是无用的,可是现在只有 这个,只有这个而且还要为鬼魅所妨害。”(46)既然一切都在预料之中,那么预期的失 败就也许不算是失败,而只是必然的过程。而且,谁也不能说,在20世纪,国民性毫无 进步。鲁迅说过,“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 ,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47)在国民性进化的长路上,自觉为中间物的 鲁迅,决不向黑暗的过去倒退,要为子孙后代战取光明,拼死执着于现在,寄希望于将 来。他的反抗绝望、甘于失败的生命哲学,继承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正 是发扬了历史上国民性曾有的优点。今天以研究鲁迅为业的觉悟的知识者,是否也该想 想如何继承鲁迅的精神呢?
----------------------------------------
注释:
①②⑤⑥⑦⑧⑨⑩(12)(13)(14)(15)(16)(17)(21)(22)(23)(24)(25)(26)(29)(30)(31 )(32)(33)(35)(36)(37)(38)(39)(40)(43)(44)(47)《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 社1994年版,第129、174—175、928—929、974、634、644、140、150、68、759、960 、981、207、138、99、19、387、27、68、232—133、128、929、171、137、411、13 、709、103、242—243、709、455、727、906、727、89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58、30页。
(11)(19)(34)王瑶《谈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5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669页。
(27)(28)《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卷,第245、273页。
(41)《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卷,第243—245页。
(42)《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卷,第683页。
(45)《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卷,第215页。
(46)《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第7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