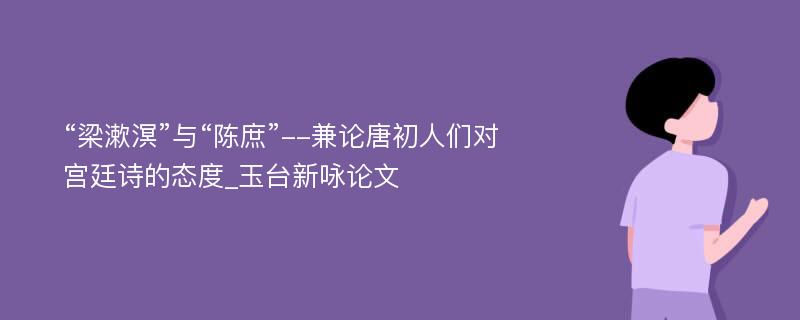
《梁书》、《陈书》不载《玉台新咏》考——兼论唐初人对待宫体诗的态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对论文,态度论文,梁书论文,陈书论文,兼论唐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856(2009)12-0076-04
关于《玉台新咏》的记载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作者署“徐陵”。但徐氏编书一事不见于《梁书》与《陈书》,使人颇感疑惑,对于此现象,刘跃进解释为“史书不可能对史传人物的所有著述记载无遗”,认为“似不足为奇”。[1]但从《梁书》与《陈书》的实际情况看,这种观点恐难成立。《梁》、《陈》二书均为“以人统事”的纪传体史书,与编年体史书侧重事件记载不同,纪传体更重视对人物生平经历的记述。如果所传之人属文人之列,那么其创作活动在其生平经历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对此类人物著述的记录历来较为重视,尤其是对作者的重要著述更是如此。《玉台新咏》之于徐陵,盖属此类。据《陈书》卷二十六《徐陵传》载,梁、陈时期徐陵的著述就已“逢丧乱,多散失,存者三十卷”,然则早在姚思廉撰《梁》、《陈》二书时,如果把《玉台新咏》看作是徐陵最主要的文学成就,殆不为过,所以,遗漏的可能性极小。从这个角度来看,《梁》、《陈》二书不载此事确实奇怪。而这一现象似乎只有联系初唐文学观念与修史背景来考查,可得到合理解释。
一
初唐文坛是一个文学观念与文学活动实际相抵牾的矛盾体,唐初,唐太宗及群臣出于统治的需要,认识到南朝绮靡文风对国家治理的负面影响,明确提出一系列文学主张,大力提倡一种新文风试图扭转这种局面。此种努力在当时所编史书中有显著体现,如《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的“论”,《北史》卷八十三《文苑传》之“序”与“论”均为太宗亲撰。如果说在《陆机传》中太宗对陆机、陆云的文学成就予以极高的评价,是对其文学主张的间接表达,那么在《文苑传》中则是鲜明而直接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与主张,对梁大同以前文学成就予以肯定的同时,对大同以后的文学创作活动进行了彻底否定,指出“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
作为最高统治者,太宗的观点及在诸史中的“制”,对修史群臣无疑具有方向性指导作用,所以,宰相魏征在《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中有与上文所引太宗语一字不爽的表叙,这绝不能单纯的看做是魏征的个人观点,而应当是以太宗为首的统治阶层意愿的表达,它是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文学概念的构建,由于修史者及其所修诸史的特殊地位和权威,此种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政令性质,而太宗的“御撰”称为“制”,更是与诏令无异。[2]唐初所修诸史《文学(苑)传》、各家传纪中涉及到对作家、作品以及文学大势变迁等问题的评介时,实际上也是以此为矩蠖,如: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
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手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
《梁书》卷六《〈敬帝纪〉论》曰:
太宗聪睿过人,神彩秀发,多闻博达,富赡词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以此而贞万国,异乎周诵、汉庄矣。
《陈书》卷二十七《〈江总传〉论》曰:
(江)总……好学,能属文,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
《周书》卷四十一《〈王褒庾信传〉论》曰:
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正是在这种官方思想的指引与约束下,虞世南以“上之所好,下必随之”[3]的理由制止太宗戏作艳诗的行为,认为一旦成风,对国家的治理非常不利;而陈子昂有“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4]的感慨,并有意识地在诗歌创作的实践中反对这种文风,与这种官方思想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初唐人在观念上虽有此种认识,太宗及群臣付诸正史的“制”与“论”带有法令性质,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但“法制似刚,而实脆薄,风俗似柔,而实坚韧,其蚀法制,如水啮堤,名虽具存,实必潜变,而并其名而不克保者,又不知凡几也”,[5]喜爱南朝绮靡文风习俗的改变,殆非一时之功。虽然唐初统治当局极力贬斥齐、梁绮靡文风,但时人对其持欣赏的态度还是主流,一时无法摆脱这种风气也是事实。此点在两方面得以体现:
(一)唐初所编两部类书——《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编撰类书主要是为了备查与学习之用,但其中可以更客观地窥见当时人们的实际文学喜好。太宗在《北史》卷八十三《文苑传》中说:“梁自大同以后,雅道沦缺”,其间作品属“亡国之音”,评价诗人则云“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但从两部类书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种表述并不能代表时人对宫体诗的态度。《艺文类聚》为唐初欧阳询所编,有学者以入选作品多少排列其中作家次序如下[6]:梁简文帝310篇,沈约228篇、曹植200篇、梁元帝175篇、庾信114篇、陆机113篇、郭璞101篇、庾肩吾96篇、江总83篇、曹丕80篇、傅玄80篇、谢灵运71篇、谢脁67篇、江淹66篇、潘岳60篇、、鲍照60篇、徐陵59篇、李尤58篇、刘孝绰56篇、刘孝威54篇、任防53篇、王粲51篇、傅咸51篇等。仅就笔者所列《艺文类聚》收诗情况来看,即使排除沈约、任昉二位梁初的诗人,活跃于梁大同以后的诗人就有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庾信①、庾肩吾、江总、徐陵、刘孝绰、刘孝威。可见初唐人对南朝诗歌、诗人的喜爱。而从《初学记》的编撰来看,这种风气直到玄宗朝仍没有扭转。
《初学记》编于玄宗初年,据《大唐新语》卷九“著述第十九”载:“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即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诏以初学记为名。”[7]可知《初学记》的编撰目的为指导皇子写作,选录的文章有范文作用。其中收诗较多的诗人很多亦见于《艺文类聚》,如沈约55篇、简文帝47篇、庾信36篇、曹植34篇、李尤32篇、江总30篇、张正见30篇、梁元帝27篇、傅玄26篇、庾肩吾24篇、郭璞19篇,鲍照18篇、谢灵运17篇、刘孝绰15篇。[6]宫体诗人及作品仍占有极大比重,作为给皇子练习写作的教材,其中所体现的统治者实际的文学取向便一览无遗了。
(二)唐初诗人的创作实践。非但从唐初所编书中可以看出时人的这种实际文学喜好,唐初人的创作实践更是清楚的反映了这一事实。检《全唐诗》初唐诗人作品,不脱六朝绮靡之气者占大多数。“初唐四杰”一般被认为是开启盛唐诗风的一派,他们的理论主张及创作实践为盛唐诗风先导,但“‘四杰’诗风亦属‘当时体’;并没有完全摆脱宫廷诗风的影响。他们的一些作品讲究对偶,声律追求词采的工丽和韵调的流转,不免有雕琢繁缛之病。”[8]而作为新文风的提倡者唐太宗,其文章更是被后人评价为“不能革五代之余习”、[9]“学徐、庾为文”、“所为文章,纤靡浮丽”。②太宗甚至有过“戏作艳诗”的经历,这种有意为之的行为,足以反映出他对六朝作品的喜爱。
综上,唐初虽然人们在观念上认清了齐梁文风的弊端,并在批判中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但在实际创作与欣赏中仍蹈袭旧文风不能自拔,在旧习俗与企图改变文学风气观念的冲突中,导致了初唐人对宫体诗及宫体诗人表里不一的态度。《玉台新咏》作为一部文学总集,流传至唐代,就无可避免要纳入当时的文学评判体系中,而时人在当时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对主要收录宫体诗的诗集——《玉台新咏》的态度当与对待宫体诗的态度具有一致性:一方面,因其中所收多为时人所喜闻乐见的宫体诗作,私下为人们所喜爱;另一方面,迫于舆论压力,公开谈论时应大力贬斥。
二
既然《梁书》、《陈书》为官修史书,其中所表达的是统治阶层所认可的观点,并非撰写者观念的自由表达,那么,假设姚思廉在撰写《梁书》或《陈书》时涉及到徐陵编《玉台新咏》一事,以当时官方对宫体诗的态度,对其作如何评价实际上已有定论,即对其进行批判。庾信因为文风浮艳被讥为“词赋之罪人”(《周书》卷四十一《〈王褒庾信传〉论》),而对于徐陵这种不仅写作艳诗,还专门收集传播的做法是尤其应该批判的,因为这无异于公开鼓励、提倡这种文风,其罪过更甚于庾信。姚思廉《梁》、《陈》二书之所以不提此事,当是出于这种观念的制约,不愿在传于后世的史书中对徐陵进行批评,从而采取回避的态度对待此问题,是为徐陵曲笔隐讳的结果。
中国古代撰史有避讳一说,是否避讳、如何避讳则视当时社会环境及撰史者自身的具体情况而定,大体遵循“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原则。《梁》、《陈》二书是初唐大修前代史的产物,对于唐初修史的利弊,稍后的史学家刘知几已有客观评价:“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史通》卷七“曲笔”条[10])这是其成书大环境。《梁》、《陈》二书虽然以洗练的语言为史评者称赏,但也没有摆脱刘知几所说弊端。姚氏所撰二史多隐讳,已为后世学者诟病,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指出:
(《梁书》)有美必书,有恶必为之讳。如昭明太子以其母丁贵嫔薨,武帝葬贵嫔地不利于长子,昭明听墓之言,埋蜡鹅以厌之,后事发,昭明以忧惧而死(原注:见《南史》及《通鉴》),而本传不载。临川王宏统军北伐,畏魏兵不敢进,军政不和,遂大溃,弃甲投戈,填满山谷,丧失十之八九。此为梁朝第一败衄之事。(原注:见《南史》及《通鉴》)而本传但云征役久,有诏班师,遂退还,绝无一字溃败之迹。他如郗皇后之妒,徐妃之失德,永兴公主之淫逆,一切不载。[11]
关于《陈书》,《廿二史札记》中则有“陈书多避讳”条专门讨论,如《陈书》卷二十八《始兴王伯茂传》记述宣帝兄始兴王伯茂死因时但云“路遇盗,殒于车中”,而实为宣帝派人所为(事见《南史》卷五十五《始兴王伯茂传》)。刘师知弑君一事《南史》卷六十八刘氏本传记述甚详,而《陈书》本传却只字未提,赵翼分析其原因谓“盖姚察父子与刘师知及寄兄茄同官于陈……遂多所瞻徇,而为之立佳传也”,[11]盖得其实。
《梁》、《陈》二书既有如此特点,以姚、徐两家有很深的家世渊源,姚思廉极可能在撰史时为徐陵隐恶。姚氏自称:“陈永定中,吏部尚书徐陵时领著作,陵引(察)为史佐,用陵让官致仕表等,并请察制焉。”“徐陵名高一代,每见察制述,尤所推重。尝谓子俭曰:‘姚学士德学无前,汝可师之也。’”(以上两条俱引自《陈书》卷二十七《姚察传》)在文学上二人也时有唱和,《陈书》卷二十七《姚察传》中又记载了江总在编自己诗集时,执意要把姚察与徐陵的唱和之作一并收入。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记述,明白的揭示了徐、姚两家的密切关系。
姚思廉作为晚辈,对父辈的徐陵定是尊敬有加的,在撰史时对他的一些不光彩行为隐而不书亦属自然。《陈书》的记载已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倾向性:其一,徐陵在梁代被刘孝仪弹劾免官一事,卷二十六《徐陵传》中一笔带过,对事件细节无所交待,其起因则说成“刘孝仪与陵先有隙”,明显偏向于徐陵。其二,据《南史》卷六十一《陈庆之传》附《陈暄传》:“陈天康中(566),徐陵为吏部尚书,精简人物,缙绅之土皆向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红丝布裹头,袍拂踝,靴至膝,不陈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识,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举止自若,竟无怍容。作书谤陵,陵甚病之。”此事《陈书》无载。其三,《南史》卷六十二《徐摛传》附《徐陵传》载:“后主为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辞句。’后主衔之,至是谥曰章伪侯。”此事《陈书》亦只字未提。其四,受初唐修史大环境的影响,姚思廉对宫体作品是持批评态度的,有伤于“轻艳”、“浮艳”的批评(分别见于《梁书》卷四《简文帝纪》、《陈书》卷二十七《江总传》)。但徐陵的诗文虽多可视为宫体作品,姚氏在其本传中却说其文章“颇变旧体,缉裁巧密”,无一字批评之语,与对待其他宫体诗人及作品的态度迥异。种种迹象均表明姚思廉确有因私人关系为徐陵隐讳之嫌。
姚氏对徐陵的文章可以笼统地给予好评,因为毕竟徐陵不是所有文章都是宫体之作,但《玉台新咏》作为宫体诗的结集,从唐初修史思想导向上看,其性质是不容改变的,纳入史书中对它及其编者要持批评的态度也是必然,故姚思廉出于为徐陵隐讳的目的,避而不提徐陵编撰《玉台新咏》一事。
[收稿日期]2009-04-21
注释:
①以今人观点,庾信入北后文风有一个明显的转变,不应完全归入宫体诗人之列,但唐初时视其为南朝绮靡文风的代表,《北史·文苑传》及《隋书·文学传》言“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周书·王褒庾信传》言“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是其证。
②[清]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史考”条载:“郑毅夫谓:‘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浮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神宗圣训亦云:‘唐大宗英主,乃学庾信为文。’(原注:《温泉铭》、《小山赋》之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