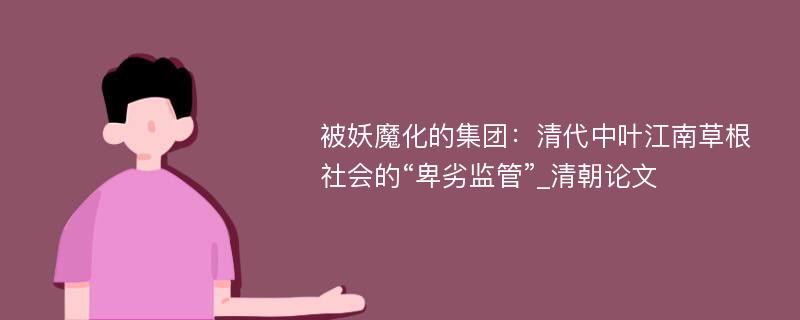
被妖魔化的群体——清中期江南基层社会中的“刁生劣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基层论文,群体论文,妖魔化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论在中国传统叙事,还是近代以来学者们的研究中,“刁生劣监”常被视为基层社会中各种罪恶的制造者。张仲礼引陈岱霖的奏折:“至若地方之刁生劣监,平时出入衙门,包揽词讼。一遇收漕届期,州县官广张筵席,邀请至署。面议粮价,分送漕规,多者数百两,少者数十两,谓之‘漕口’。又有不受漕规,但代各花户包揽完纳,一切帮费,任其入己。”①唐文权的解释比较客观,他认为清代候补官员和贡生以下的低级功名者越来越多,积压在等级森严的功名阶梯上。他们中不能出仕和做幕僚的群体,则退居乡里,凭借自己优越的社会地位成为包揽词讼或捐税者。“这些常常使官方感到头痛因而被称之为‘刁生劣监’的人,成为官与民之间在司法和赋税方面交涉的非合法中介,借以施展自己受挫的才能”。②《中国农民负担史》认为,刁生劣监,平日健讼者,包揽分肥,造成惊人数量的漕规。③此看法与早年孟森的看法非常相似。④孔飞力认为晚清城市知识精英对乡村刁生劣监有着习惯性的歧视。⑤吴琦的看法比较典型,认为绅衿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加大了其不法的力度,他们所交纳的漕粮大大减少,小民身上的负担极大加重。在漕粮征派中,绅衿成为获利丰厚的主要群体之一。当利益获取超出了朝廷的限度或触动官吏的利益时,会招致各种形式的限制和压制。⑥高翔的系列论文对清专制政治的本质、⑦清代前期的近代化趋势⑧作出了全新的阐释,并提出了影响清朝执政能力的诸多重要问题。⑨本文在很多方面,特别在清代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方面,受其启发极大。尽管明代就有“刁生劣监”的问题,但本文主要探讨清代中期的“刁生劣监”问题。
冯桂芬指出:“苏松重赋,沿官田租额为粮额,故常六七倍于同省,一二十倍于他省。”⑩道光九年,全国额征正、耗米合计4522283石,其中江南仅苏松道即征收1579462石,约占全国漕运总额的35%。(11)
在政权建立之初,清廷曾作过清除漕弊的举措,对加耗重收进行裁减。顺治二年(1645),清廷宣布江南等处人丁地亩钱粮等,“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官吏加耗重收或分外科敛者,治以重罪”。(12)清廷清醒地认识到:“官吏贪赃,最为民害……但有枉法受赃及逼取民财者,俱计赃论罪,重者处死。”(13)但利之所在,缺乏自下而上监督的官员进行贪腐,实为专制社会的普遍规律。清代的官员回避制度,被认为有利于中央政府和官员对地方的盘剥。(14)因此,尽管百姓负担本已极重,且朝廷立有禁令,官员却仍视漕弊为利薮,以种种名义进行浮收,中饱私囊。“最多者输钱直三四石当一石,稍少者输米二石有半当一石,更少者若元和之章练塘等二石当一石”。(15)
苏松地区征收漕粮,有淋尖、踢斛、捉猪等折扣,五花八门,“两次七折八折,即一石变为三四五斗”。水脚费定例每石52文,道咸年间增加了三四倍。另有花户费、验米费、灰印费、筛搧费、廒门费、廒差费。实际征收时,百姓名义承担的1石漕米,需征至2石五六斗。(16)漕运水手的帮丁贴费,早期每船为银百余两,至多二三百两;嘉道时代,递增至五六百两、甚至七八百两,以苏松为甚。(17)种种用费都转加到完漕的粮户身上,加上州县征漕的浮收勒折,粮户完1石漕粮要支付2—4石米。(18)
林则徐在道光十三年称: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和太仓4府1州之地,比浙江全省征粮多至1倍,比江西多3倍,比湖广地区多10余倍。在米价低贱之年,一百八九十万石米即合银五百数十万两;若米价较高,则又暗增一二百万银两。(19)林恳陈:“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20)
江南漕弊的主因在于国家的漕务体制及官员的监管制度。据两江总督蒋攸铦奏称:征漕时,民间常因浮勒,控告州县官,但州县则以刁抗为患。“究之各执一词,皆非虚捏。盖缘丁力久疲,所领行赠钱粮,本有扣款,而长途挽运,必须多雇人夫以及提溜打闸,并间有遇浅盘剥,人工倍繁,物价昂贵,用度实属不敷,势不能不向州县索费。州县既须贴费,势不能不向粮户浮收”。(21)更有甚者,各种体制内的官吏,无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贪腐,“州县朘削民膏,祇以供运丁之悉索;运丁之勒掯,仅以饱仓中蠹役之私囊。种种积弊相沿,实情事之所必有。且近日仓中吏役经纪,竟多至数百人,朋比为奸,坐享厚利”。(22)此外,州县办公费用紧张,官员便可随意浮收勒折。(23)
不言而喻,许多浮收钱粮极易成为官员们的黑色或灰色收入。1799年,嘉庆帝正确地指出,各种浮收弊端“总由地方官得受漕规,以为贿赂权要,逢迎上司之用……层层剥削,锱铢皆取于民,最为漕务之害”。(24)1809年,吴璥等在《会议漕务章程》折中认为:“江南漕赋,较他省为最多;而历年告漕者,不一而足。是皆由地方官于收漕时,弊端丛生。以致刁生劣监,挟制把持,告讦成风。”(25)嘉庆帝认为,“此固亏缺之一端,而其弊不止于此”;自总漕、巡抚、藩司、粮道、仓场、各衙门以及沿途文武各员并书吏经纪等处,向来存在陋规。(26)
江南漕负极重的次因在于清代的漕粮征收实行双轨制,不同类型的人群负担极其不公。漕粮征收一向有大、小户之分,“不惟绅民不一律,即绅与绅亦不一律,民与民亦不一律”,同一百亩之家,有的不完一文,有的完纳至百数十银两。(27)
不同职业的人群纳粮时的待遇极不相同。“缙绅之米,谓之衿米,举、贡、生、监之米谓之科米,素好兴讼之米谓之讼米”,这三种米,均是官府万不敢浮收的。(28)可见,双轨制维护了有权者的既得利益,损害了最广大民众的利益。
总之,清代的征漕体制是采用掠贫济富的方式,通过超负荷地剥夺平民的利益,在既保证中央政府核心利益的前提下,还要维护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两江总督蒋攸铦承认:“最苦者,良善乡愚,零星小户,虽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违。畏暴欺良,此赢彼绌。是欲清漕政,转为奸民牟利之薮,而良民之受困益深矣。”(29)在恶劣政体和无良官员的盘剥下,平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势必在交纳漕粮时要谋求自身损害的最小化,他们发现通过给予与地方基层官吏交好的生监们一定的利益,由生监们代交,可以减少许多盘剥。蒋攸铦指出:“乡僻愚民,始则忍受剥削,继亦渐生机械,伊等贿托包户代交,较之自往交漕加五六之数,所省实多,愚民何所乐而不为?是以迩年包户日多,乡户日少,不特刁民群相效尤,即良民渐趋于莠。吏治、民风、士习由此日坏。此漕弊之相因,而成积重无已之实在情形也。”(30)
可见,生监包揽漕粮,对平民和生监双方均属有利,而生监包揽,更是出于平民的“贿托”。冯桂芬指出:“且斗升小户,从来不知完米,不堪繁扰,势必假手包揽。”(31)苏松地区,“向来刁生劣监,包完仓粮,此古之道也。今则不但包完,而且包欠”。(32)
如果生监包揽漕粮是大弊的话,那么,其罪责完全在于清代的漕务政策和官员监察体制。令人惊讶的是,在清代的政治话语及后来的学术阐述中,替平民交纳漕粮,从而获取一定利益的生监被视为漕弊的万恶之源,他们似乎成了各阶层均予声讨的“刁生劣监”。有清一代,中央政府多次清厘漕弊;但每次中央政府除弊,均把自己的利益作为不可撼触的存量予以维持。自然,执行这些“除弊”政策的地方官吏,是不愿意剜肉般地牺牲自己的不当收入的;甚至不敢增加权贵集团避逃的税负。因此,掌握政治话语权的官僚们总是把漕负流量的增加归结为生监们的介入。
嘉庆十年(1805),清廷查处吴江县勒休知县王廷瑄亏缺仓库银米及生监王元九等勒索漕规一案。王廷瑄挪移库银达2万两以上,“皆因刁生劣监等,在仓吵闹,勒索陋规所致”。经审讯确定,从漕规中分享不当利益的生监有吴景修等314人。(33)每当开征漕粮时,生监们“挜交丑米,藉端滋事,动即以浮收漕粮列名上控,其实家无儋石,无非包揽交收,视为利薮”。嘉庆帝感叹:“今吴江一县,分得漕规生监已有三百余人,其余郡县,可想而知。”(34)1820年,嘉庆帝在批示山东巡抚钱臻所奏京控案件一折时,指出:“东省讼狱繁多,其弊源在于讼棍之把持……其势与南省包漕之刁生劣监,同一伎俩,大意专为从中牟利。”(35)道光初年,据御史孙贯一奏:各州县征收漕粮时,教官、典史以及武弁与刁劣生监,无不分食漕余。“甚有家居绅宦,腼然行之,绝不为怪”。(36)
由此看出,漕弊的主要责任被推诿给了刁生劣监。禁止生监们介入,实质是便于官员们肆意盘剥;清除生监包揽,显然是为了官府更好地浮收。清中期清除漕弊的核心目标已经异变为根除或减少生监们对官府的监督,排挤或消除生监们分润漕利,而非根除由政体和官僚们所造成的弊根。
有学者根据18世纪时清代官员和外国传教士的记载,认为当时清朝官员腐败问题极其严重,且无处不在。(37)清廷最高统治者尽管不承认、甚至不能看出各项漕弊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但每位君主几乎无需费力就能看出刁生劣监背后的官员腐败问题。
乾隆四十八年(1783),江苏巡抚闵鹗元参奏:上年收漕时,青浦县知县杨卓与该县生监倪溶等,揽收花户漕米,勾结漕书梅锦章等,包纳上仓,瓜分余利,“请旨革职究审”。乾隆虽然认为:“劣衿把持公事,串通蠹书,包漕渔利,最为地方之害。”但对与梅锦章勾结的知县进行了惩处,“着革职拏问”。(38)再如,嘉庆年间,在宜兴等地,百姓交纳漕粮,每石加至七八斗。百姓被逼以次充好,在开征之初则拖延不纳,待兑运在即,遂蜂拥而入,让官吏不暇验收。“且有刁生劣监,广为包揽,官吏因有浮收,被其挟制,不能不通融收纳。迨核计所收之米,已敷兑运,即以廒满为词,藉收折色,分肥入己”。(39)经嘉庆四、五年整顿,“从前加四、加五、加倍之弊,均已革除”。但嘉庆六年江苏征收漕米时,苏州知府任兆炯藉弥补亏空为名,将苏松等四府漕粮,尽数包揽承办,照旧加收浮粮,“以致该州县等竟敢公然仍复陋规,毫无忌惮。而劣监刁生,藉此挟制取利,故智复萌。旗丁等见地方官加收粮石,亦欲多索兑费,任意勒掯,百弊丛生。两年以来剔除漕弊、恤丁惠民之事,竟废于一日”。(40)
由于平民交纳漕米的总数减少,加之生监们参与分享浮收带来的额外利益,官吏们黑色和灰色收入势必极大地下降,因此,生监包揽漕粮的潜在受损者是官吏。在专制体制下,政治话语权向来被官僚集团所操纵,作为与官僚集团不断冲突的知识群体,被官府妖魔化应是必然之事。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地方官吏(包括清官)最痛恨刁生劣监了。一位江南地方大吏称:“其刁生劣监、好讼包揽之辈,非但不能多收,即升合不足、米色潮杂,亦不敢驳斥。并有无能州县,虚收给串,坐吃漕规,以图买静就安,遂致狡黠之徒,视为利薮,成群包揽,讦讼不休。州县受制于刁衿讼棍。”(41)更有地方官员发布告示称:“种种欺骗,般般诡诈,固由择术不慎,并非矢人之不仁,实则靠此为生,希冀渔人之得利,但知填己溪壑,不顾破人身家。此等忍心害理之为,多属劣监刁生之辈……罪实不可胜诛,言之殊堪痛恨。”(42)前述王廷瑄案发生时,江苏地方大吏甚至立碑直斥生员们“此直无赖棍徒之所谓,岂复尚成士类乎!”(43)
事实上,生监通晓国家法度,常常以法律为依据与地方官对簿公堂,甚至对其要挟。而清代官员向来奉行政治至上原则,真正依法行事者乃凤毛麟角,要找出官员们的违法犯罪证据,实易如反掌。因此,官员们往往看轻生监的真正违法行为,反而极其憎恨其对法律的较真,即便清官也不例外。江苏巡抚林则徐称:“生监之弊在于包揽,平居无事,惯写灾呈,一遇晴雨欠调,即约多人赴官呈报。若经有司驳斥,辄架民瘼大题,联名上控。及闻查赈,则各捏写户口总数,勒索赈票,自称力能弹压。只要遂伊所欲,便可无事。否则挟制官吏,讦告不休,京控之案,往往若辈为之。”(44)江南地方官对“讼师”、“讼棍”的憎恨远甚于盗匪,涉讼生监向来是地方官打击最力的群体之一。
嘉庆己未,王述庵在《与平恕书》中指出:“至近年州县所以鱼肉诸生,其意盖在立威,威立而诸生箝口结舌,则庶民何敢出而争控?是以狱讼之颠倒,征收之加耗,无所不至。”(45)王述庵指出,牵连甚广的吴中杖责诸生案实质是苏州地方官惧怕诸生检举而一手策划的冤案,“今冬定作清漕之局。但州县或有阳奉阴违,倍收多取,恐生监连名讦告,而州县指为哄堂闹事者甚多”。他直陈:“抑或如此案不科州县之失,而即科诸生之罪,若仍助其焰而长其气,则吏治之坏,不知伊于何底也。”(46)
1802年,嘉庆帝严旨要求江苏整顿漕弊,地方官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官场潜规则,“不清其源,而专欲惩治生监土豪”。嘉庆帝敏锐地看穿了官员们故意把经念歪的伎俩:“以为奉有谕旨,则地方官即不虑其挟制,生监等目睹浮收情弊,亦不敢与之计较。伊等之意,岂能逃朕洞鉴耶?”(47)
但清专制统治者的终极目标是维持政权稳定,而不是增加民生福祉和民众尊严;所谓清除漕弊、减轻平民些许负担不过是作为维护稳定的手段而已。而为了维稳这一大政方针,地方官员越出法度的残忍手段和暴力举措,多为最高统治者默许、甚至支持。这种事例俯拾即是。如乾隆初年,江苏官员听任商人购米出洋,引发苏州等地米价上昂,严重影响了百姓的生活。苏州市民顾尧年向官府建议平抑米价,“哭吁抚辕,从而和者,纷如聚蚁”。(48)署江苏巡抚安宁实际上是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苏州当时有“禄山不去地无皮”之谣。(49)仅安宁家奴李忠,违法所得达四五万两白银,因而人称“安宁,实不安宁”。(50)安宁在苏州拘捕39人置狱,乾隆帝在背后一直支持和鼓励安宁对苏州平民实施残酷暴行。他给安宁的上谕中称:“近年各省,屡有聚众抗官之案,几至效尤成习。而吴中民情素属浇漓浮动……若不严行惩创,何以示警?”(51)他亲自下令杖毙顾尧年、陆文谟、曹大混等人。(52)
作为清政权支柱的地方官员,又往往利用维稳这一大政为托词,反向挟制中央政府,以掩饰自己的不法之事,使中央政府惮于惩处其犯罪行为。
当由恶劣体制和无良官员造成的社会危机爆发时,清廷既不可能改革其体制,也不可能对官员进行更严厉的监察,而是把基层社会中具有动员能量的生监们视为政权的大敌,予以严厉的打击。
明末江南市民的群体性事件,曾予清廷以莫大的教训。(53)清帝对任何可能有损于稳定的事件,均作为政治大事。每位皇帝的硃批,对群体性事件无一例要求从宽的。1748年,江苏盛泽民众遏籴,乾隆指示两江总督:“重处以示警,毋稍姑息也。”(54)同时斥责署江苏巡抚安宁:“恐如此之宽,民益恨也。”(55)因此,地方官员往往夸大生监们的号召力,把他们说成群体性事件的祸首,塑造成专制政权的潜在危险。(56)两江总督陶澍称生监们“人繁势众,一经整顿,群然觖望,大则纠众闹漕,小则造谣兴谤”。(57)
江苏地方大员给道光帝的奏折称:“包漕衿棍,藉此横索陋规,不可不亟行革除。据奏富豪之家与稍有势力者,皆为大户,亦有本非大户而诡寄户下者。其刁生劣监,平日健讼者,则为讼米,完纳各有成规,而讼米尤甚。稍不遂意,非逞凶闹仓,即连名捏告,藉控为抗,包揽分肥,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至三四百名,漕规竟至二三万两。”(58)可想而知,如果每县具有相当号召力的刁生劣监真的达到三四百名,显然构成了对专制政体的莫大威胁,不能不引起清帝的警觉。
江苏巡抚陆建瀛奏称:“江南办赈,每有刁生劣监,希图染指,煽惑愚民滋闹。”(59)冯桂芬写道:“于是刁生劣监,挟制更多,小户愚氓,怨恨更甚。”(60)
不论生监是否真的有如此大的社会动员能量,均是统治者极为忌惮的。1748年,乾隆帝下达对青浦县朱家角镇、吴江县盛泽镇遏粜和吴江县咆哮县堂案的指示,要求督抚们,“凡事当绸缪于事先,豫为布置,勿令群情汹涌。倘有奸匪倡谋,即应早折其萌芽,勿令纵恣”。(61)
乾隆二十八年,据庄有恭等奏:访闻金山卫生员徐筠、南汇县生员徐周柄,跟从杨维中学习“邪教”,吃素诵经。并于各生员家中搜出《金刚弥陀经》及忏图册,经审讯得知系弥勒教支派。乾隆闻报后,谕军机大臣等:“徐筠等身列青衿,亦私藏经忏。受其蛊惑,则愚民之转相煽诱,流入邪匪,更不待言。该抚等自当严行查究,将传经设教之首犯,按律定拟,以示惩儆。”(62)
道光初年,御史孙贯一奏:“前数年之勒折,不过两倍市价,今则三倍市价。”对此,道光帝把打击重点转向了刁生劣监。如1822年,下令:“着通谕有漕省分各督抚,饬属严密稽查。如有刁生劣监等把持渔利,即行访拏。”(63)1826年,再次严令:“钱漕皆惟正之供,各州县如果实力征收,何至民欠累累?若刁生劣监任意抗延,动辄藉词控告,尤应随时惩办……毋稍宽纵,以儆刁风而清漕务。”(64)
可以看出,清廷对刁生劣监的打击,表面上是为了减少平民的负担,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清除具有社会号召力的人。在发生较大的生监动员事件时,政府对生监往往采取肉体消灭的方式;而在一些没有构成违法的事件中,当生监们显示了其动员潜力时,官员们则使用其他手段(如羞辱、恐吓等)加以惩罚。(65)嘉庆年间在苏州发生的吴中杖责诸生案,地方官员借诸生欠贷、聚集为名,对诸生“四出查拿,牵连数十,掌嘴销顶,凌辱不堪”。(66)
1825年,道光帝下令:“士为四民之首,欲正民风,先端士习。着各省学政严饬各学教官,随时稽查详报,毋使身列胶庠,恃符滋事。如有刁生劣监,即分别戒饬褫革。”(67)官员甚至为生员量身定做了“合法”的用刑步骤:“贡监生员每多包揽词讼,平空插入,扛帮讼事,如果到案,不可轻易责打。即或逞刁顶撞,亦不可认真发怒,即交号房看守,速将可恶之处及平日恶迹据实声叙,详请斥革功名,奉到批示,然后用刑惩办,始无后患。”(68)可想而知,在中国,官府欲寻生监“平日恶迹”,实如探囊取物。而通过塑造生监劣行并加以惩处,可从精神方面削弱生监们的社会影响力。
清王朝进入中期,各种社会弊病层出不穷。这些弊病多肇端于掌握权力的利益集团对平民的掠夺,漕弊仅是冰山之一角而已。生监包揽的根源是恶劣的体制和官员的腐败,但当时是官员、而非生监掌握社会的话语权,由刁生劣监来承担社会积弊的主要罪责,既合乎专制者的利益,也合乎官僚利益集团的逻辑。
大多数对法律或官员寻疵觅缺的刁生劣监,其动机是自利,他们不是平民的天然代言人,而是经常利用与官府的关系,欺压百姓。他们作为传统专制社会的产物,不可能超越时代的限制,本身有着数不清的缺点。1840年以前,生监们不可能是近代政治体制的倡导者,而是专制政体的拥护者。学者指出:“生监中有些人目睹中央和地方弊窦丛出却无以消除,如疼痛在身,骨梗在喉。”(69)至少,他们本可以成为法治的推动者和地方官员的有力督察者。但“更多的生监虽怀抱为皇帝、为国家尽忠之志,却常在专制制度下碰壁”。(70)
如果说生监能对基层政府进行挟制的话,除了生监掌握地方官员的违法把柄外,背后通常是对更有权势的官僚的依附。冯桂芬曾言:生监们“今日发串若干,惟其所取。明日收银若干,惟其所与。今日比某差,明日拘某户,今日具某禀,明日岀某示,惟其所使。州县俯首听命,虽上司有所不畏矣”。(71)这基本颠倒了生监与官员之间的关系。真正动用国家机器对平民行使暴力,惟有政府或官员才能做到,绝非一般生监所能为。冯桂芬的观念与魏源很相似,他们均鄙视乡村中的生监,“尽管晚清的城市化程度比一千年前的中国还要低,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理论中,天经地义地认为城市精英应该统治乡村愚民”。(72)
文学作品《九尾龟》的描述,真实地展示了刁生劣监不过是官员的附从而已:
这常熟县分,本来是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大绅士,祁彦文虽然是个侍郎,却向来不肯干预公事的。这位祁观察回到常熟,便干预起地方上的公事来。不但民间词讼争论的事情,他要插进去帮个忙儿,就是地方上的公款、常平仓里头的积谷,他也要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儿,出来混闹。地方上有了这般一个无耻的绅士,就有许多卑鄙龌龊的刁生劣监,挺身出来做他的走狗,在外面招揽词讼,把持衙门,无事生风,招摇撞骗,把常熟一县的人,弄得一个个叫苦连天,恨入骨髓。(73)
百姓宁愿相信“刁劣”的生监,不愿相信政府官员,本身恰恰说明政府官员公信力的缺失。冯桂芬称:“州县敛怨于民,深入骨髓,一旦有事,人人思逞。”(74)咸丰元年,嘉定等县发生“刁生劣监”“把持挟制”事件,起因是当年豁免道光三十年以前民欠银米,此时正征收道光三十年漕粮,“民间即哗然,以为圣恩宽大,而官吏屯膏,不无觖望。盖因江苏省赋额繁重,浮收勒折之弊亦甚”。(75)
林则徐奏称:“州县廉则人不敢啗以利,州县严则人不敢蹈于法,州县勤而且明,则人不得售其奸。”(76)他认为江苏地方官员不敢违法的原因就是担心生监们挟持:“刁生劣监虎视眈眈,如州县稍有营私,则讹诈分肥,人人得而挟制……是今日之州县,无从舞弊。”(77)官员无从舞弊之说,显然过于夸张;惮于生监们检举,应是实有之事。但在清代的政体下,生员们的监督效果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
清专制统治者热衷于构建个人威权,而蔑视制度权威。每当最高统治者更迭时,新统治者的个人威权和人格魅力多难与乃父乃祖相比,予人以一代不如一代之感。因此,在强势帝王之后的君主,多是现状的维持者,无法利用制度权威来消除社会弊病。道光帝曾言:“从前乾隆、嘉庆年间捏灾冒赈之案,无不尽法处治,今十数年来,各省督抚未有参劾及此者,岂今之州县胜于前人乎?”(78)从道光年间捏灾冒赈案无人查处,概可管窥当时社会积弊之重。即便生监们企图以法律为依据、以要挟为手段来监督官员,由于一些统治者的懦弱,也很难大面积奏效。
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教育的任务就是极力宣扬忠于王权的正面美德,生员—官员要随时为朝廷献身,君主即是朝廷的符号、也是朝廷的实体。(79)更为普遍的是,强势的专制统治者总是一方面极力矮化大众的智慧,另一方面自我膨胀地认为自己为千古一圣。百姓不但在其活着时要感戴其恩德,在其殁后也要学习其高尚情操、铭记其伟大思想。一部符合清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写道:“却说我大清圣祖康熙佛爷在位,临御六十一年,厚泽深仁,普被寰宇。”(80)乾隆帝称:“我朝自定鼎以来,深仁厚泽,浃洽人心……圣祖仁皇帝御宇六十一年,德政及民,恩周寰宇。曾免天下钱粮三次、漕粮二次。稽之史册,隆古未闻。我皇考爱养黎元,整肃纲纪,十三年中,惠民实政,不能殚述。朕诞膺景命,丕绍宏图,保赤诚求,无时不以爱民为念。”(81)乾隆的自我标榜应该是清帝们真实的自评:“朕自缵绪以来,益隆继述。凡泽民之事,敷锡愈多,恩施愈溥。此不特胜国所无,即上溯三代,下讫宋元,亦复罕有伦比。”(82)
生监们被认为是传播这些无量恩德和伟大思想的主力,清廷不惜耗费巨大的教育资源来提高生监们的思想觉悟。雍正二年(1724),御制《圣谕广训》万言,颁发直省督抚学臣,转行各地文武各官暨教职衙门,令军民、生员、学童等,通行讲读。乾隆时更把《圣谕广训》作为童子应试、初入学者等必须掌握的政治科目,学童们须正确背诵默写《圣谕广训》,方为合格。
在最高统治者看来,生监们的职责应是引导民众歌颂君主及其政体。正如嘉庆帝所云:“朕培养士子至优且渥,原望其束身自爱,键户读书,并当劝化闾里愚民,知所观法,方不愧四民之首。”(83)无论如何,生监们挟制地方官员、对其攻击讦告,事实上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政策法令、行政实践进行挑剔,这是最高统治者所无法接受的,只能视其为“刁顽”。
为了从思想源头减少各地“刁风”,雍、乾时代非常注重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二帝曾向浙江、广东、湖南、福建等省派出观风整俗使,(84)并向陕西、江苏、安徽等地派出宣谕化导使。(85)以让民人“深知感戴国家教养之恩”。(86)据1743年派往江苏的宣谕化导使所奏,“所至之地,传齐绅衿士庶,宣讲《圣谕广训》,反复开导”。(87)因此,专制政体本质上是反智的机制。当生监们发现体制、法律、官员督察体系的漏洞和缺陷时,清廷及各级官员不是弥补其不足,让体制在不断改良中完善起来,反而竭力打击看到真相的“顽劣”生监。
作为清廷上下共知之事,如果真有刁生劣监违法之处,背后必然存在更加严重的官员犯罪问题。曾国荃写道:“大凡劣监刁生控官,虽在临时,而其心之所不满于官者,亦未尝不在平日。平日苟无以服其心,遇事又被之执其短,则若辈挟其桀黠奸猾之伎俩,寻瘢索垢,列状上闻,比比有之。”(88)可见,刁生劣监的控案,多因官员违法在先。
两江总督陶澍慨叹:“凡包揽与白规最多之处,其收数自浮。如江北各属,此风甚少,故收数亦轻。”(89)诚然,淮北地区很少见到刁生劣监包揽之弊,但这并不表明淮北地区的社会治理好于江南。恰恰相反,这是淮北社会崩溃的结果。淮北基本不存在引经据典、事事依法援律与官府构讼之人,这里更多的是认为最高统治者“彼可取而代也”的项羽式人物,如刘邦、曹操、刘裕、黄巢、朱全忠、郭子兴、张士诚、朱元璋等。顾祖禹写道:“自秦以后,东南多故,起于淮泗间者,往往为天下雄。”(90)清中期以后,这里更是“盗贼渊薮”,仅捻军一厄,就让清廷耗费了无数行政、军事和财政资源。由此看来,不断兴讼、讲求法制的刁生劣监,未必不是清王朝之福,未必不可以成为法治社会的推动者,特别是成为清廷孜孜以求的社会稳定力量。
颇具讽刺的是,清廷上下对惩处刁生劣监一向不遗余力,但对查处更本质、更严重、影响更大的官员犯罪则要消极得多,这是因为最高专制者看待官员优劣向来以政治作为评判标准。康熙时代,两江总督噶礼贪名素著,多次被劾,却并未受惩。(91)甚至与“天下第一廉吏”江苏巡抚张伯行互劾,也能占据上风。但当噶母向康熙面陈:“噶礼极奸诈无恩”时,康熙敏锐地从其“不孝”中推出其“不忠”,而予诛杀。(92)通过这起案例,康熙明确儆示:清廷可以容忍官员一定程度的贪腐犯罪,但绝不能容忍其政治上的不忠。乾隆年间的巨贪和珅、王亶望、陈辉祖等官员,无一不曾是政治可靠的典型。
生监控诉官员,则以法律为标准。在生监们靳靳以官员违法犯法为大题时,朝廷往往视之为细枝末叶。在统治者看来,经济方面的违法犯罪远轻于政治问题。生监与朝廷在官员评价这个问题上,经常鸡同鸭讲,南辕北辙。这就是江南地区清廉如陈鹏年、张伯行之类的官员往往被朝廷罢黜;而贪暴如阿山、安宁者却能平安无事的原因。
一个专制王朝进入中期,各利益集团已然定型,其中以官僚集团最为关键。社会各种积弊或起或消,大部取决于统治者的执政能力;统治者执政能力的高下,主要取决于对法制的依恃程度,进而形成对官僚集团的约束和督察,而不是取决于对生监及其他民众的控制和打压。
作为乡村教育程度最高、国家培养最力、民众仰之、趋之的未来施政者,生监们在任何法治社会,都是国家的建设力量、政府的依恃对象,而非统治者竭力防范和打击的目标。有的学者从讼师的存在,推导出18—19世纪中国百姓已经明显地趋向于使用诉讼作为工具来解决冲突。(93)就犯罪率而言,生监无论如何也无法与官员相比。况且,任何一个群体、阶层和职业中的个体均会有违法犯罪行为,不论其比例多高,均不应否定整个人群,最应否定的是不良的政治体制。
清廷大力打击刁生劣监,是专制王朝进入中期后统治者的共性:宽于治吏,苛于罪民,枉法成习,欺诿成性;暴力和谎言成为政权的两大支柱。这不但丝毫不能展现统治者的仁德之心,反而暴露了统治者的颟顸、无能、短视和狭隘。
刁生劣监有时是贪官污吏的盟友,有时是其敌手。但不论为友为敌,刁生劣监均是贪墨官员的分利者,两者本质上处于利益冲突的地位。因此,刁生劣监受贪官憎恨是容易理解的。而像陶澍、林则徐之类的清官,同样痛恨刁生劣监,这并不表明后者真的罪恶昭彰,而是显示了专制社会中的清官同样无法越出政体的苑囿。其一,清官虽然比庸官有作为,但清官同样不能处处依照法度行事;其违法行为,同样忌恨生监们检举讦讼。其二,清官大多对专制政体充满信心,不可能从体制上找原因,不可能让自己和体制处于受监督、受约束的状况。其三,清官更看重自己的名声和前程,有些人的升迁欲望和升迁机会也更大,他们更不愿生监们对其为政吹毛求疵,而视之为抹黑其政绩。因此,在专制政体下,清官无法成为法治目标的建设者。
禁止生监包揽漕粮,并不是为了减少浮收,而是为了使官府的浮收更有保障。而禁止生监讦讼,也不是真的担心生监们捏词诬控,反而担心其控告大量被坐实,造成地方官员的施政事事受掣于民、听命于民,影响专制统治者的权威。在专制政体下,政府既无法解决漕弊,也无法解决官员其他腐败问题,只能对生监进行妖魔化,让其承担许多积弊的罪责,削弱其社会动员能量。这种头痛医臀式的问题解决方法,自然无益于清政权的稳定。
生监毕竟是潜在的科举成功者,亦即未来的施政者。通过打击刁生劣监,事实上对生监们进行了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施政实践教育,即忠于体制、听命君主、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是官场的硬道理;正义和法制从来都不是官场的信奉物,君临万姓的君主才是官场唯一图腾;依法行政、洁己奉公、爱民如子之类的政治话语不过是虚无缥缈的抚慰民众之宣传而已。就这一点而言,妖魔并打击刁生劣监,是由清代专制政治所命定的,是对清未来施政者进行现实教育的课堂。
注释:
①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②唐文权:《东方的觉醒——近代中印民族运动定位观照》,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00页。
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农民负担(1840—1949年)》,见《中国农民负担史》第2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134页。
④参见孟森:《孟森学术论著·清史讲义》,吴俊编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2页。
⑤参见Philip A.Kuhn,Ideas Behind China's Modern Stat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55,No.2,December 1995,p.331。
⑥参见吴琦主编:《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⑦参见高翔:《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高翔:《从“持盈保泰”到高压统治:论乾隆中期政治转变》,《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高翔:《也论军机处、内阁和专制皇权——对传统说法之质疑,兼析奏折制之源起》,《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⑧参见高翔:《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78—189页。
⑨高翔称之“政府统治能力”,参见高翔:《清帝国的盛衰之变》,《决策与信息》2005年第1—2期,第132页。
⑩(15)(16)冯桂芬:《与许抚部书》癸丑,见《显志堂稿》卷五,光绪二年校邠庐刻本,第31页下、31页下、36页上—下。
(11)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前言第3页。
(12)《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七,顺治二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4页上—下。
(13)《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七,顺治二年六月,第154页下。
(14)参见James H.Cole,The Shaoxing Connection:A Vertical Administrative Clique in Late Qing China,Modern China,Vol.6,No.3,July 1980,p.324。
(17)参见蒋攸铦:《拟更定漕政章程疏》,见魏源:《魏源全集》第15册《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六,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488—489页。
(18)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前言第3页。
(19)(20)参见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集》奏稿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1、152页。
(21)蒋攸铦:《拟更定漕政章程疏》,见魏源:《魏源全集》第15册《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六,第488页。
(22)《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一四八,道光八年十二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1页上。
(23)参见《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四一,道光二年九月,第744页上。
(24)《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四九,嘉庆四年七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05页下。
(25)(26)《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二〇,嘉庆十四年十一月上,第965页下、第966页上。
(27)参见冯桂芬:《均赋议》癸丑,见《校邠庐抗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9页。
(28)(29)(30)参见蒋攸铦:《拟更定漕政章程疏》,见魏源:《魏源全集》第15册《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六,第488页。
(31)冯桂芬:《均赋议》癸丑,见《校邠庐抗议》,第230页。
(32)冯桂芬:《与许抚部书》癸丑,见《显志堂稿》卷五,第31页下、36页下。
(33)(34)参见《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一四四,嘉庆十年五月下,第973页上。
(35)《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三七〇,嘉庆二十五年五月上,第896页上。
(36)《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四一,道光二年九月,第744页上。
(37)参见Nancy E.Park,Corrup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6,No.4,November 1997,p.968。
(38)《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八四,乾隆四十八年七月上,第849页上—下。
(39)《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四九,嘉庆四年七月下,第604页下。
(40)《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九五,嘉庆七年三月上,第272页上。
(41)蒋攸铦:《拟更定漕政章程疏》,见魏源:《魏源全集》第15册《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六,第488页。
(42)汤肇熙撰:《严禁讼师示》,见《出山草谱》卷三,光绪十一年刻本,第11页上。
(43)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0页。
(44)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44页。
(45)王述庵:《与平恕书》,见徐珂《清稗类钞》第8册“狱讼”上,第154页。
(46)徐珂:《清稗类钞》第8册“狱讼”上,第154页。
(47)《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九八,嘉庆七年五月,第315页上。
(48)冯桂芬撰:同治《苏州府志》卷一四九,光绪八年刻本,第6页上。
(49)张守常:《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
(50)蔡显撰:《闲渔闲闲录》卷五,民国嘉丛堂丛书本,第2页下。
(51)《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一四,乾隆十三年五月上,第161页下。
(52)参见冯桂芬撰:同治《苏州府志》卷一四九,第6页下。
(53)关于明末江南市民反税监等斗争,参见Richard von Glahn,Municipal Reform and Urban Social Conflict in Late Ming Jiangna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0,No.2,May 1991,pp.280-307。
(54)台北“故宫”与“中研院”藏明清折件:《尹继善奏朱家角盛泽镇刁民聚众遏籴》乾隆十三年五月,箱号2772,文献编号002343。
(55)台北“故宫”与“中研院”藏明清折件:《安宁奏报处理盛泽镇刁民聚众闹哄经过情形》乾隆十三年五月,箱号2772,文献编号002463。
(56)有学者指出,在基于亲属、地缘、职业或经济阶层各社会组织的大众之间的冲突司空见惯。由于民间当事人经常调解这些冲突,官方常常忽视了他们。参见Peter C.Perdue,Insiders and Outsiders:The Xiangtan Riot of 1819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Hunan,Modern China,Vol.12,No.2,April 1986,p.198。应该说,这些调解者不少是为官员们所憎恨的“刁生劣监”,官员们忽略他们在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有时并非无心之过,而是有意妖魔化的需要。
(57)陶澍:《陶澍全集》卷一七“陶云汀先生奏疏”,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418页。
(58)《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一一一,道光六年十二月上,第853页下。
(59)《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六二,咸丰二年五月下,第830页上。
(60)冯桂芬:《均赋议》癸丑,见《校邠庐抗议》,第230页。
(61)《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一四,乾隆十三年五月上,第167页上。
(62)《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九〇,乾隆二十八年七月上,第726页上。
(63)《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四一,道光二年九月,第744页上。
(64)《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一一一,道光六年十二月上,第852页上。
(65)清人笔记中载有地方官员对生员任意手戒的故事。参见曾七如:《小豆棚》,武汉:荆楚书社,1989年,第321页。
(66)徐珂:《清稗类钞》第8册“狱讼”上,第152页。
(67)李鸿章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三第5册,光绪二十五年刻本,第236页下。
(68)褚瑛:《州县初仕小补》卷下,见郭成伟主编:《官箴书点评与官箴文化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307页。
(69)(70)王跃生:《清代生监的社会功能初探》,《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4期,第95—96页。此处所引“骨梗在喉”原文如此,应为“骨在喉”。
(71)冯桂芬:《与许抚部书》癸丑,见《显志堂稿》卷五,第36页下。
(72)Philip A.Kuhn,Ideas Behind China's Modern Stat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i,Vol.55,No.2,December 1995,p.309.
(73)漱六山房:《九尾龟》第84回,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603页。
(74)冯桂芬:《上林督部师书》己酉,见《显志堂稿》卷五,第21页上。
(7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0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2页。
(76)(77)(78)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46、146、143页。
(79)参见C.T.Hu,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Examinations and Control in Pre-Modern China,Comparative Education,Vol.20,No.1,Special Anniversary,Number 8:Education in China,1984,p.23。
(80)文康:《儿女英雄传》第40回,台北: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第852页。
(81)(82)《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三六七,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下,第339页上、339页下。
(83)陶澍:《陶澍集》上册,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70页。
(84)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8—336页。
(85)参见《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七八,雍正七年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82页上;《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八五,乾隆八年二月,第381页下。
(86)《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一八,雍正十年五月,第563页下。
(87)《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八五,乾隆八年二月,第381页下。
(88)曾国荃:《阳高县程令禀遵札禀复办理地方情形由》,见《曾忠襄公批牍》卷三,光绪二十九年刻本,第4页上。
(89)陶澍:《陶澍全集》卷一九“陶云汀先生奏疏”,第14页。
(9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1册,上海:中华书局,1957年,第960页。
(91)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七八,第10104—10105页。
(92)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清代起居注》第28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b013891—b013892页。
(93)参见Nancy E.Park,Corrup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6,No.4,November1997,p.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