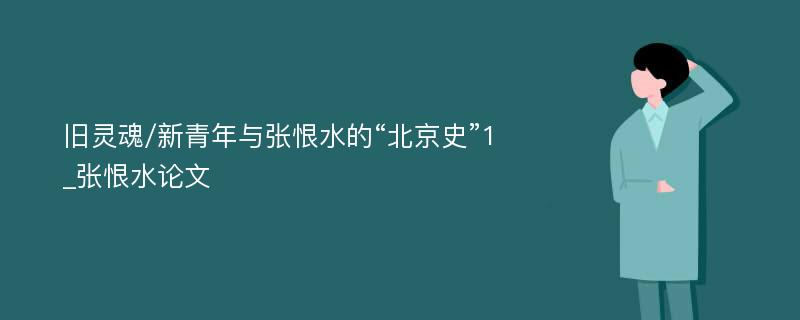
老灵魂/新青年,与张恨水的北京罗曼史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曼史论文,北京论文,新青年论文,灵魂论文,张恨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望1919年5月,时在芜湖《皖江报》任职的张恨水(1895-1967)虽未能亲身参与“五四”,但对新文化运动心向往之。仅数月之隔,时年24岁的张恨水便辞职北上,只身来到北京,造访而后栖居于这“首善之区”、文化古都以及五四运动的诞生地。我们不妨重温张恨水初到北京的震惊体验:走出北京火车站,闯入眼际并给他打下启蒙或启悟印象的是前门高耸的箭楼。一刹那间,这位浸润于才子佳人作品也阅读过新派文字的安徽“外省青年”,情不自禁为古都庄严雄伟、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与文化遗迹所震撼。②相形之下,自称“来自六千里以外小小山城里的乡巴佬” 的沈从文,初来乍到北京,流连忘返于“中国古代文化集中之地”的琉璃厂以及文化博物馆一般“分门别类的、包罗万象的古董店”,除此之外,这位湘西“外省青年”也被另一类事物所打动:“初初到这个大都市来,上街见到最多的就是骆驼,所得印象是充满风沙阅历而目光饱含忧戚,在道上却一步一步走得极稳”。③从20年代北京的独特一景——忧戚但也稳健的骆驼身上,沈从文观察、发现并解读着古都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底蕴。……在沈从文与张恨水等人的文学表述中,都市感受、历史意识、震惊体验既可以浮现在纪念碑式的文物古迹、帝都遗迹,也可以滋生于俯拾即是默默无语的日常物象。
在描摹20、30年代风云激荡、新旧杂陈的北京时,张恨水的代表作品包括章回体罗曼史《春明外史》(1924-1929)、《金粉世家》(1926-1932)与《啼笑因缘》(1929-1930)。这几部小说的情节安排、叙事策略、人物形象、空间场景,皆突现出张恨水本人混杂的观感与矛盾的姿态:在经受五四运动“人的文学”之洗礼以后,张恨水在北京现代文学的版图上既是旁观者,也是介入者,既是同路人,也是陌路人。他借《写作生涯回忆》曾自我忏悔,在五四时期的青年时代,他本人的双重人格表现在他既是一个受惠于五四新文化、剪掉辫子的“革命青年”,又是一个难脱“名士派”、“头巾气”的“才子崇拜者”。④实际上张恨水在此一时期渲染自己的北京想象时,作者的“两重人格”也显影于他笔下的一系列矛盾的人物形象上:他们是不完全的“新青年”,也是不彻底的“旧才子”/“老灵魂”。⑤他行销甚畅的章回体北京叙事在刻意经营现代北京的外史、稗史、野史、罗曼史之际,勾画出一系列徘徊在传统与现代、旧学与新知之间,具有双重人格、轻度精神分裂的“后五四”青年形象,如杨杏园、金燕西、樊家树等。值得申辩的是,五四本身并非铁板一块的同质话语,它牵涉到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等不同层面,而且新文化阵营本身的复杂性、歧异性与多元并存的状态,也应值得深细考辨。⑥另一方面,旧文学、通俗小说、市民文学等文学类型,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回旋”或“内爆”的踪迹。⑦具体到张恨水20、30年代的北京罗曼史,五四运动的核心命题之一“人的文学”,便迂回曲折地浮现在张恨水章回体“社会言情”小说中的个体形象、人物画廊、以及自由恋爱甚至多角恋爱等情节安排上:譬如杨杏园与梨云、李冬青,金燕西与冷清秋、白秀珠,樊家树与沈凤喜、关秀姑、何丽娜等缠绵悱恻的故事。虽然屡被新文学作家和批评家所诟病,张恨水在“新旧参合”的叙事安排中,还是引人注目地将“人”的问题以及作为新的主体/个体的“人之解放”的可能、尝试及其困境,转述到他一时“洛阳纸贵”的北京罗曼史当中,并有力凸显了五四新文学、新思潮与现代通俗文学、畅销小说之间的张力关系以及互动的格局。
一 好奇,幽闭,鬼屋啼笑:《春明外史》
是否因为过渡时代变动太剧烈,虚构的小说跟不上事实,大众对周围发生的事感到好奇?
——张爱玲⑧
好奇不仅仅是走马观花时的消闲娱乐,更是城市生存的一种模式。
——芭芭拉·本尼迪克特(Barbara M.Benedict)⑨
“好奇”不仅仅是无足轻重、即兴而来的小娱小乐。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处于变动剧烈的过渡时代,纷繁复杂的事实本身甚至比虚构的煽情悲喜剧还要精彩,而“好奇”正可以成为在新旧杂陈的城市环境中发现并整理都市观感、错乱印象与时空记忆的生存模式。就此意义而言,对于新闻、报纸、时事报道的“好奇”,正是捕捉时代问题的心理驱动力,诉诸文字则成为记载时代问题的有效形式。张恨水的《春明外史》正是以好奇姿态与新闻报道的风格,搜集京城的趣闻轶事与现代风情。于此同时,作者本人的才子佳人阅读经验,又驱使他开辟出主人公离群索居的“幽闭”式古典空间,编织缠绵悱恻的罗曼史叙事。
应成舍我之邀,张恨水为《世界晚报》的副刊“夜光”撰写了《春明外史》,从1924年4月12日起一直连载到1929年1月24日止。⑩小说的主人公杨杏园是皖中世家子弟,初到北京客居皖中会馆,他羁留之所的前任住户是科举考试三次落第的文官,“发疯病死于此,以后谁住这屋子,谁就倒霉”。(11)不信邪的“羁旅下士”杨杏园停留此地(后来移居一处假四合院子),白天是穿梭于北京大街小巷、“与时俱进”的现代记者,晚上则是幽居租赁而来的小四合院、“伤地闷透”(sentimental)的古典诗人,一生“无日不徘徊于避世入世之路”。(12)自封为“落伍青年”的杨杏园起初痴情于青楼雏妓梨云,但梨云因小肠炎而死;尔后他与才女李冬青(新式女学生与多愁多病旧式女子的合体)情投意合,(13)但李冬青身有隐疾,好事难成;最终杨杏园因肺病吐血身亡,魂断北京。造成杨杏园之死的肺痨,可谓一种现代疾病,罹病患者因过度疲乏、不堪生活/时代的重负而终至撒手人寰;而才女李冬青身有隐疾,正象征中国的古典传统在现代社会,无可奉告也无法言传的症候和隐痛。
笔者愿意用鬼屋啼笑的意象来解读张恨水的第一部章回体北京罗曼史。李欧梵在研究鲁迅的作品时,曾引用鲁迅本人描述现代中国精神状况的意象“铁屋”,而新文学写作与新文化运动不啻“铁屋中的呐喊”。(14)相形之下,与新文化运动若即若离的张恨水在他寓居北京的成名作《春明外史》中,提供的是鬼屋啼笑的主体位置与叙事策略。“鬼屋”中的幢幢鬼影,有因科举考试失败而疯狂至死的考生,有红颜薄命的青楼女子,也有在现代记者与古典诗人身份之间游移挣扎终致梦断北京的老灵魂/旧才子/新青年。“啼”,延续着“旧”小说才子佳人的眼泪,在五四前后联系着鸳鸯蝴蝶派踵事增华的叙事模式,是卿卿我我、涕泪飘零的言情传统,在《春明外史》,中,张恨水不断提及《红楼梦》与《花月痕》等前朝作品;(15)而“笑”,则是愤世嫉俗、心中块垒难平的讽刺与批判社会现状的“写实主义”传统,张恨水亦坦陈他如何受惠并改良《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小说。于是这鬼屋啼笑的叙事姿态,借助着与时俱进、却也与时代保持距离的“外史”文类,铺陈了张恨水所理解的1920年代北京城的社会史与心灵史。此处,“外史”一词意义丰富。所谓“外史”,就是不同于“正史”,或者是在“正史”阙如的情况下,书写的北京史。“外”,既是在“主流”、“正统”、“官方说法”之外,也是在新文学写作之外。所以张恨水谦称自己的《春明外史》是局外人的观察,是外行的说法。然而,此“外史”在“例外”之外,也不乏“例内”的含义,即,尝试书写原汁原味的北京形象,并提供内行说法。张恨水曾经与一些“老北京”如马芷庠、齐如山等通力合作,为出版社编撰北平指南、导游手册,就此意义而言,他也是“北京通”,是以资深作者(家)、权威人士的身份提供“真”北京的内行指南。
《春明外史》将公共话题转写成巷陌流言,其新闻体的城市快照凸显了可供索引的日用类书,其哀感顽艳的罗曼史感染过新、旧两派读者。请让我重申鬼屋啼笑的主人公杨杏园所具有的游离、分裂的主体形象。在白昼的工作时间里,他是职业记者、业余侦探、仿佛无所不知的旁观者,他的行动空间包括议会、豪门、剧场、公园、庙宇、名胜、公寓、旅馆、会馆、报社、青楼、学校、通衢、胡同、大杂院、小住户、陋巷、贫民窟、俱乐部、游艺场、茶楼、高级饭店等等。而在黑夜的“幽暗”时间里,他住在皖中会馆的鬼屋,或是后来租赁的小四合院,写作古典诗词(甚至偶撰武侠小说)、私人信函,与友人、恋人相会,在私密空间保留旧才子/老灵魂的书卷气,“词华藻丽,风流自赏”,却也黯然憔悴。(16)杨杏园的“两重人格”或“双重身份”在折射作者本人初居北京的精神世界之时,也将城市陌生人与北京专家、匆匆过客与都会导游的矛盾身份揉和一起。毋宁说,杨杏园的北京生涯从一开始就笼罩于层叠难散的城市魅影当中:有混沌动荡的都城现状,有挥之不去的古城旧影,有难以排遣的浪漫挫折与感伤,……京城十年屡睹“怪现状”的杨杏园,其生活的戏剧性或许不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九死一生”,但杨氏本人终于难逃厄运,心力交瘁而命断首善之都,这不仅仅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老套落魄才子叙事,更是五四之后的动荡时期在新旧文化之间一个不堪重负而终致崩溃的现代敏感者的浪漫写照。
二 家族谱系与城市魅影:《金粉世家》
罗曼史是走向最后审判的旅程,审判之后,
家是可能的,或者无家可归就够了。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7)
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称巴尔扎克的巴黎叙事“书写了巨型谱系”,而且“家是有机形式,个人在其中长大成人”。(18)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则提供了有关北京望族金家的“巨型谱系”,它最初于1926至1932年连载于《世界日报》的文学副刊“明珠”,后经张恨水修改而出版单行本。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说:《金粉世家》销路远在《春明外史》之上,是因为“书里的故事轻松、热闹、感伤,使社会的小市民层看了以后,颇感到亲近有味”。(19)在张恨水笔下,北京成为悲喜情节剧的场景,新旧杂陈的城市叙事被结构成“家庭罗曼史”(弗洛伊德语)。在弗洛伊德那里,“家庭罗曼史”是孩子(有时是神经官能症患者)讲述的美梦成真的童话故事,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为了躲避生身父母的权威或冷落,而构造的替代式的、理想化的父母形象,尽管他们的父母在现实生活中远非那样完美。这种幻想是对家庭成员、家庭生活以及家庭秩序的美化,也是对实际家庭生活的刻意扭曲、修改或“矫正”。(20)此处我借用“家庭罗曼史”一词,意义更为宽泛,关注的是金家两代的冲突、张力、欲望、爱恋、幻想与幻灭的叙事。从《春明外史》到《金粉世家》的文学旅程,是从“外史”与感伤罗曼史走向“正史”(“世家”)与多角恋爱的嬗变。张恨水北京叙事的主人公从“双重人格”者杨杏园改变成京城浪荡子金燕西,其空间场景也从租赁的鬼屋转移到金家的豪宅,甚至到投射到放映金燕西生活经历的电影院里面。
“世家”体在太史公的绝唱中,记载的是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的事迹。《金粉世家》不妨看做张恨水走出《春明外史》的“外史”叙事,经营“正史”的尝试。五四以降的新文学激进批判大家庭家长的权威,力倡背叛封建家族,离家出走,寻找真理与自由。《金粉世家》却“背道而驰”,刻画了理想父亲与一群不孝子女的形象。金铨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内阁总理,也是金氏家族开明的家长,理想的父亲,身体力行儒家伦理之余,也不排斥西方理念。其在古今、新旧、中西之间圆转灵活的折衷态度,体现在金家半旧半新的春节礼仪:“他们家里,说新又新,说旧又旧。既然过旧年,向祖宗辞岁,同时可又染了欧化的迷信”。(21)而金铨初见儿子金燕西的太太冷清秋,即很满意,因为冷清秋衣著“华丽之中,还带有一份庄重态度,自己最喜欢的是这样新旧参合的人”。(22)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折衷态度,还体现在金铨去世后丧葬礼仪的选择:是中国旧式的奢华气派,也是外国新式的简易风格。叙事者以全知视角揭示了金铨的长子凤举如何揣摩“新旧参合”的解决方案:
对于出殡的仪式,凤举本来不主张用旧式的。但是这里一有出殡的消息,一些亲戚朋友和有关系的人,都纷纷打听路线,预备好摆路祭。若是外国文明的葬法,只好用一辆车拖着灵柩,至多在步军统领衙门调两排兵走队子而已,一个国务总理,这样的殡礼,北京却苦于无前例。加上亲友们都已估计着,金家对于出殡,必有盛大的铺张。若是简单些,有几个文明人,知道是文明举动,十之八九,必一定要说金家花钱不起了,家主一死,穷得殡都不能大出。这件事与面子大有妨碍了。有了这一番考量,凤举就和金太太商量,除了迷信的纸糊冥器和前清那些封建思想的仪仗而外,关于喇嘛队,和尚队,中西音乐,武装军队都可以尽量地收容,免得人家说是省钱。金太太虽然很文明,对于要面子这件事也很同意,就依了凤举的话,由他创办起来。(23)
不过《金粉世家》的真正主角,是金家的不孝子金燕西,一位“时装贾宝玉”,一位现代颓废都市青年,一位显赫家族的纨绔子弟,以及他对出身寒微、才貌双全的女学生冷清秋始乱终弃的故事。本雅明曾经将游手好闲者界定为城市人群中英雄式的步行者。安科·格里博(Anke Gleber)在研究欧洲小说(尤其是魏玛时代早期的作品)时,也将游手好闲者联系到体现现代性的人物身上,如收藏家、旁观客、做梦人、艺术家、历史学者等,因为这些现代人物有能力将他们的观察转化成文本与图像。(24)张恨水笔下的金燕西一开始并非如此类型的现代人物,他也有别于上海新感觉派作品中的新式主人公,充其量他只是一个飘来荡去、摇摆不定、缺乏目的、不会判断与算计的城市多余人。他对旧学与新知都所知甚浅,他对异性的追求,也同样缺乏主见,三心二意。直到他遭遇冷清秋,才局部改变自己无根飘零的游荡状态。冷清秋是另一个李冬青,或者是女性版的杨杏园,她是现代世界的“老灵魂”,当步入金氏的豪门而倍感不适时,她与杨杏园类似,退入自己庭院的阁楼阅读古典诗词与佛教经书。冷清秋虽然不是“阁楼里的疯女人”,但她退守的姿态,仍旧无法持久地占据一个属于她本人的女性空间。突如其来的神秘火灾,令她与孩子离家出走,最后在北京偏僻街巷卖字为生。
诚如有论者指出的,“《金粉世家》帮助人们意识到,章回小说这个古老的形式并不一定局限于表现陈旧的内容,它是能够表现新思想新事物的”。(25)不过在新、旧之间,张恨水仍旧无法觅得或提供一个现代主体可以栖居的空间位置,他甚至只好求助于佛教信仰。金铨太太部分接受新式文明,但更笃信佛教,金氏家族因金铨的猝然去世而解体在即,金太太在夕阳西下的北京西山草亭,如是观照烟影里的现代北京:“你看,那乌烟瘴气的一圈黑影子,就是北京城,我们在那里混了几十年了。现时在山上看起来,那里和书上说的在蚂蚁国招驸马,有什么分别?哎!人生真是一场梦。”(26)这一旁观、不介入、幻灭之后的纯然客体化的视角,(27)位于北京城外,也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规划之外。在这一梦醒、警幻时刻,五四之后不久的北京城被解读成一个抽象的客体,一个佛经的隐喻,一个空虚的镜像。西山顶上的全景凝视,症候式地将纷繁的现代城市景观与漫长的人生阅历,指认并描摹成富于象征意味的“雾中风景”,凸显了老一代的女性俯瞰者带有宗教超越意味的另一种启悟。
有趣的是,张恨水在《金粉世家》的收束处,添加了一处叙事转折,从而开创了一处城市空间,并将金燕西变形为一个本雅明所阐述的现代人物。金燕西从欧洲游学归来,成为电影工业的明星。虽然在莫名火灾中失去妻、子、家庭,金燕西却有能力将自己的情史、痛史转换成荧屏之上的煽情悲喜剧,并大获成功。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曾经论到,“情节剧的核心表达了戏剧冲动本身:即戏剧化、凸显、表达、演出的冲动”。(28)毋庸置疑,金燕西在北京的电影院完满了自己的戏剧冲动,演出了《火遁》的悲喜剧,而且反转了“真相”:将妻子刻画成嫉妒成性的女子,报复心切,抱子跳入烈火,并将痛失妻、子的丈夫表演成狂癫之人,“临死的时候,口里还喊着,火里有个女人,有个孩子,救哇救哇!”(29)借助戏中戏、情节剧中的情节剧,张恨水将观看电影的现代体验与现实故事的叙事反转结合一处,冷清秋竟也是热泪盈眶的影院观众之一。鲁迅“救救孩子”的铁屋呐喊,被转换成“救救我的孩子”、“救救我的女人”的煽情悲喜剧情节。“西洋镜”里的世界重写了金燕西的都市体验与创伤记忆,拓展了生活空间,将私人情史翻拍成公共影像。于是张恨水章回体罗曼史里面那个游手好闲的多余人金燕西,竟出人意表地找到了将自己半新半旧的城市体验转化成文本与图像的新奇方式。
三 情史,恨史,痛史:《啼笑因缘》
展览通过直接宣示,或间接暗示,再现了身份认同。
——伊万·卡普(Ivan Karp)(30)
1929年,张恨水受严独鹤邀请,为上海《新闻报》撰写北京故事《啼笑因缘》,两年间连载于“快活林”,并成为张恨水的代表作品之一。《啼笑因缘》仍以章回体罗曼史的叙事模式,为上海乃至中国的读者详细展览了北京的市情风俗画(尤其是天桥风情),并造就了持久不衰的张恨水热,其跨文类流行遍及电影、电视剧、话剧、京剧、说书、粤剧、新剧、歌剧、滑稽戏、木头戏、绍兴戏、露天戏、连环画、小调歌曲等,至今盛行不衰。(31)张友鸾读罢《啼笑因缘》后大为激动,对张恨水说:“‘五四’新文学的主张是深化文学创作中的阶级意识,我认为你已自觉不自觉地在深化这种阶级意识,你已毫无愧色地走进新文学的队伍中了。”(32)
张恨水的“阶级意识”表现在他对北京不同类型空间及其涵义的“直接宣示”或者“间接暗示”的展览,也表现在他笔下的主人公樊家树与阶级背景不尽相同的三位女性之间错综复杂、难以割舍的浪漫情缘。与《春明外史》的杨杏园有所不同,《啼笑因缘》里的樊家树是现代新青年,离开南方的故园,求学北京。他是嗜读《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的“外省青年”,是被情史、恨史、痛史所困扰的新学堂大学生,也是最终黯然出关、离开北京的“平民化的大少爷”。樊家树遭遇到三位女性,天桥女子沈凤喜,是来自底层民间社会的天真、轻信、不幸的鼓书艺人;另一位天桥女子关秀姑则秉着儿女情长、却有英雄气概,是现代版的花木兰与侠女十三妹,并勇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为国效力的奇女子;何丽娜则是上层社会的摩登都市女郎,是财政部长的千金,相貌上与凤喜相似,清瘦之余,“有一种过分的时髦,反而失去了那处女之美与自然之美”,仿佛是“冒充的外国小姐”,(33)但是因喜欢樊家树而改变自己的仪表、性情与价值取向。张恨水借樊家树所呈现的北京罗曼史,并非简单的多角恋爱式滥情故事,而是“后五四”青年面对复杂的都市空间、阶级差异、社会现实、浪漫情感时,身处其间、难以取舍的精神境遇。
暂且不论五四运动是否可以用“文化启蒙”、“文艺复兴”来命名,(34)在张恨水那里,“后五四”青年樊家树的城市体验可以通过空间叙事来形塑。樊家树的平民主义倾向落实在他对不同类型空间与物象的适应与不适。他在舞厅受到声色的刺激,需要回到自己的“上房”翻看《红楼梦》等古典小说重获内心的安宁。他对天桥世界、平民生活的关注,远甚于他对奢华宅院的兴趣。天桥鼓书艺人凤喜经樊家树资助,进入现代学堂(女子职业学校)补习,与其说她受洗于新知,不如说她更钟情于新潮物质的诱惑:手表、两截式高跟皮鞋、白纺绸围巾、自来水笔、玳瑁边眼镜、金戒指等时髦物件。她的新青年学堂梦,体现在跟新文化启蒙与新式教育相关联的物质表象上面。(35)这是张恨水人情练达,深刻理解并刻画的某类底层女性的物质渴望,虽然在阶级意识上不够进步,但张氏的描写却表现出他对人性缺憾的洞见卓识。所以在他笔下,凤喜出入军阀刘将军的宅第,情不能已地目眩神迷于殿堂的饰物、高大的座钟、软绵绵的地毯、大铜床、无线电收音机、外国戏、瓷砖浴室、与电扇香水等等。(36)在张恨水看来,凤喜的悲剧源自她性格的弱点,她在受到逼迫之余,也半推半就地以身作妾,“想到这里,洋楼,汽车,珠宝,如花似锦的陈设,成群结队的佣人,都一幕一幕在眼面前过去”。(37)奢华摆设与西洋器物在张恨水的章回体罗曼史中,被赋予了道德评判的色彩。
樊家树与关秀姑的交往,关乎书籍的交流、启蒙知识的讲授,也触及文学本身的娱乐或教育功能。关秀姑的阅读书目,包括《红楼梦》(情窦初开际),《儿女英雄传》(儿女情长的猜测),以及《金刚经》、《心经》、《妙法莲花经》(克制情欲时)。侠女关秀姑的阅读史,关乎现代青年的情感教育,关乎新女性意识的启蒙(关秀姑置疑侠女十三妹对儒家伦理的服膺,不满文康书写的“女侠的雌伏”),也关乎在佛家禁欲经典与挺身报国的民族主义意识之间的取舍。张恨水所书写的五四之后的北京罗曼史,有戏剧化的万花筒展示,有情感与内心世界的丰富呈现。在逼仄的城市巨型空间与狭窄窘迫的大杂院之间,张恨水的文化价值观、情感圭臬、阶级意识、空间想象得以充分展开,呈现了经受传统章回体小说的浸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吹拂之下,新旧并存的现代城市景观。
佐思(王元化)在《“礼拜六派”新旧小说家的比较》一文中指出,“张先生在最近出版的小说《蜀道难》中借李小姐的口说:‘我们有力量,就赶上大时代的前面去站定,没有力量,只好安守本分,听候大自然的淘汰,伤感是没有用的’(四十三页)。这也是张先生自己的人生观:不伤感,不悲观,不失望,他只冷静的跟随着大时代走。自然,这还不是最正确的态度,但在礼拜六派的作者中,却要算出人头地的意见了”。他也指出,“时间会使某些新文学家衰败,也会使某些旧小说家新生”。(38)张恨水的北京外史、稗史、野史、通史,其核心要素是罗曼史,更确切地说,是失败的罗曼史,是既旧且新的感伤故事。在《春明外史》中,是古典诗人/现代记者杨杏园与艺妓梨云、才女李冬青失败的恋情,在《金粉世家》中是纨绔子弟金燕西与冰雪聪明的冷清秋之间的始乱终弃,在《啼笑因缘》中是新学堂的大学生樊家树与天坛鼓书艺人凤喜、富家女子何丽娜的有始无终。彼得·布鲁克斯在论述情节剧时曾指出这些悲喜剧中所展露的现实:在真实戏剧的面具背后所隐藏的现实,是神秘的,只能进行影射或加以置疑。(39)如果借用彼得·布鲁克斯所论述的情节剧来讨论张恨水的小说,我们不妨说,张恨水的章回体北京叙事是情节剧式的,但张恨水的罗曼史不是平面化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深广度,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表象下面新旧杂陈、丰富涌流、被影射也被质疑的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现实。张恨水的空间叙事与城市想象,既不同于(左翼)新文学,也有别于鸳鸯蝴蝶派。它在旧式章回体的长篇叙事当中,掺杂、渗透了新奇的写作技巧(如电影的“小动作”、日常生活琐屑繁冗但别有意味的“小叙事”与精彩细节等)与微妙的现代意识。张恨水城市快照的叙事策略,新、旧物像的有意参合,万花筒般的都市景观,集锦式的市情展览,经由作者有意为之的全知视角与全景演示,在空间的意义上,捕捉到上至金粉世家、下至杂院街角的城市罗曼史,从而凸显了新生事物、现代思潮与传统观念、历史遗绪之间掺杂并置的状况,并有力描述了夹缝中生存的老灵魂/新青年所体现出来的复杂深广、歧异多元的“五四问题”与时代症候。
注释:
①1928年6月20日到1949年9月26日之间,北京改称北平。为行文方便,笔者有时故意将北平与北京“混”为一谈。
②张伍:《我的父亲张恨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姜德明初到北京,也同样为箭楼、正阳门所震撼,并“惊愕地望着众多的城楼,长长的宫墙”。参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上),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页。
③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卷27,第13页。
④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载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7页。另参见范伯群:《张恨水的几部代表作》,载《礼拜六的蝴蝶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251页;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特别是“社会言情编”(范伯群、张元卿);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赵孝萱:《张恨水小说新论》,台北学生书局2002年版;T.M.McClellan,Zhang Henshui and Popular Chinese Fiction,1919-1949,Lewiston,N.Y.:Edwin Mellen Press,2005; Yingjin Zhang,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Fil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⑤夏志清早就指出有必要分析张恨水作品里面的“白日梦”与“幻想”,参见C.T.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Der-wei Wang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p.25。左翼“新青年”对张恨水作品的批评,可以参见杨沫《青春之歌》第26章,其中写到一位失业青年任玉桂《原是汉路火车上的司炉》,曾经中过张恨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的“毒”,在林道静的帮助下身心逐渐康复:“任玉桂渐渐变了。他不仅身体变得健康一些,而且精神也变得愉快了。从前,他躺在炕上无聊时,不是呻吟就是咒骂;要不,就看些《七侠五义》、《封神榜》或者《啼笑因缘》、《金粉世家》一类小说来解闷。现在在道静的启发下,他阅读起她偷偷拿给他的《大众生活》、《世界知识》等进步书刊来。”英文译本参见Yang Mo,The Song of Youth,trans.Nan Ying (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4),pp.455,457。
⑥参见陈平原:《何为/何谓“成功”的文化断裂——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14日。
⑦有关晚清狎邪、侠义公案、谴责、科幻等小说文类“回旋”或“内爆”的讨论,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台北:麦田,2003。另参见吴福辉,《消除对市民文学的漠视与贬斥——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二》,《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第62~64页。
⑧张爱玲:《谈看书》,载《张看》,台北:皇冠,1991,第188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⑨Barbara M.Benedict,Curiosity:A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Inquiry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p.94.
⑩王晓薇曾分析张恨水《春明外史》中的传统叙事模式,参见Hsiao-wei Wang Rupprecht,Departure and Return:Chang Hen-shui and the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Hong Kong:Joint Publishing Co.,1987),p.14.
(11)(12)(15)张恨水:《春明外史》,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第942、489页;第208、305页。
(13)李冬青自言,“我就是吃了旧文学的亏,什么词呀,诗呀,都是消磨人志气的,我偏爱它。越拿它解闷,越是闷,所以闹得总是寒酸的样子。自己虽知道这种毛病要不得,可是一时又改不掉”。杨杏园也有类似的偏好,气质,落魄和忧郁,见张恨水:《春明外史》,第337页。
(14)参见Lu Xun,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trans.William Lyell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以及Leo Ou-fan Lee,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
(16)在“鬼屋”之内壁挂佛像,地放蒲团,读佛诵经,是杨杏园在现代北平疗伤治病、化解内心痛苦的逃遁方式,第八十一回,这位“老少年”对新青年富家骏说,“你们年青的人,正是像一朵鲜艳的香花一般,开得十分茂盛,招蜂引蝶,惟恐不闹热。我们是忧患余生,把一切事情,看得极空虚,终究是等于零”。《春明外史》,第874页。
(17)Harold Bloom,The Ringers in the Tower Studies in Romantic Tradit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p.3.
(18)转引自Patrizia Lombardo,Cities,Words and Images:From Poe to Scorsese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64.
(19)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第41页。
(20)Sigmund Freud,"Family Romance," in Peter Guy ed.,The Freud Reader (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89),pp.297~300.
(21)(22)(23)(26)(29)张恨水:《金粉世家》,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06、464、761、1026、1049页。
(24)Anke Gleber.The Art of Taking a Walk:Flanerie,Literature,and Film in Weimar Cul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26.
(25)袁进:《小说奇才——张恨水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27)Joan Ramon Resina,"The Concept of After-Image and the Scopic Apprehension of the City," in After-Images of the City,edited by Joan Ramon Resina and Dieter Ingenschay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p.7.
(28)(39)Peter Brooks,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Balzac,Henry James,Melodrama,and the Mode of Excess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xi; p.2.
(30)Ivan Karp,"Culture and Representation," in Ivan Karp and Steven D.Lavine,eds.,Exhibiting Cultures: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and Lond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1),p.15.
(31)赵孝萱:《张恨水小说新论》,第92~95页。许子东指出,《啼笑因缘》因为是张恨水为上海读者而写,在上海连载发表,所以上海的编辑、评论家、读者的期待与意见,如要看武侠,要看噱头等等,也参与了这部章回体小说本身情节编织的过程。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假如《啼笑因缘》当初是在北京的报上连载,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见,许子东:《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重读〈日出〉、〈啼笑因缘〉和〈第一炉香〉》,载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497页。
(32)石楠:《张恨水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另参见第139页谈张恨水与晚清小说;第183页谈《金粉世家》的小说结构。
(33)(35)(36)(37)张恨水:《啼笑因缘》,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第53~54页;第109~110页;第123页。
(34)参见余英时(Yu Ying-shih),“Neither Renaissance nor Enlightenment:A Historian's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以及李欧梵(Leo Ou-fan Lee)."Incomplete Modernity:Rethinking the May Fourth Intellectual Project," in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ed.Milena Dole eov á-Velingerov á and Old ich Král (Cambridge,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99~324,31~65.
(38)佐思(王元化):《“礼拜六派”新旧小说家的比较》,载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第308~310页。有关新文学在“五四”时期、30年代初以及40年代前期对市民小说的批评态度,参见汤哲声:《新文学对市民小说的三次批判及其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4期,第118~132页。
标签:张恨水论文; 金燕西论文; 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读书论文; 啼笑因缘论文; 章回体论文; 杨杏论文; 春明外史论文; 金粉世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