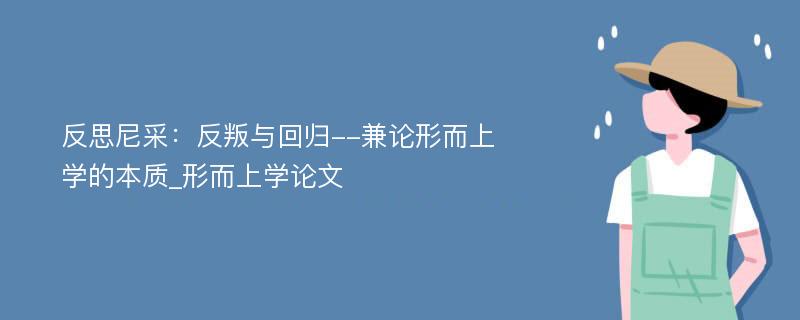
重思尼采:反叛与回归——兼谈形而上学的本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采论文,形而上学论文,本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定位
尼采为国人所知,大约始于鲁迅。七十多年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的尼采形象:他彻底摧毁了某种哲学传统,后尼采的哲学与前尼采的哲学完全不同了。似乎尼采给哲学造成的变化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本文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历史理解的“近视症”,它使人们惯于在牛顿、 爱因斯坦之后列上一个霍金(StephenHawking), 在马克思、列宁之后列上一个斯大林,等等。言下之义,现在的岁月,是真正新纪元的开端;我们,是新纪元的开拓者或参与者。谁不以为自己的时代真正轰轰烈烈呢?但这是历史眼光的真正缺乏;多少时髦、盲从与傲慢败坏了审慎的理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牛顿时代人们的狂热:“自然和自然规律隐没在黑暗中,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一切变为光明。”(注:引自E·卡西勒:《启蒙哲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而牛顿自己则甚有分寸,他写道:“我迄今为止还无能为力于从现象中找出引力的这些特性的原因,我也不构造假说。”(注: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第553页。)不幸象牛顿那样思想清明而坦率的人太少了。理解历史的近视症在解读尼采时更是时常发作,这一点尤其为尼采本人粗砺的文风和自负的口吻所加剧。
当然,这种理解上的近视症并非无药可医,比如在喧嚣过后,清醒回归,见识增长的时候。近些年来,胡塞尔、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哈贝马斯以及罩在“后现代”名下的很多人的思想占据着学界的热点,而尼采似乎终于沉寂了。但这正是好时节,可以脱却缭乱的眼睛、轰鸣的耳朵和懵懂的心智,平静地去探问尼采。或许,我们借此可以把尼采置于较为公允平实的位置上。
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尼采的批判与向往,缓解对其反叛性、终结性的过分推崇,并进而对形而上学的本性作出新的澄清。
尼采的反叛,笼统看来十分显著,但细究之下不禁要大打折扣。亚里士多德反叛了柏拉图,马克思反叛了黑格尔,可他们反叛的程度从“长时段”来看并不大,毋宁说他们是各自前辈卓有成效的变种。(注:相关议论可参阅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12页;以及《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 —427页。)他们都是伟大的继承者,一如他们都是伟大的革新者。 在类似的意义上,尼采也不是例外。
对于尼采的终结性,海德格尔有一种观点,认为他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注:参阅《海德格尔选集》,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63—820页。)这种观点只有一半是真确的,即尼采是形而上学家。但是形而上学并没有终结于尼采。也许让所有人都同意说凡是对生活的思想都会含有形而上学精髓的话会遭遇激烈的争辩,那么尼采自己的强力意志、透视观、轮回论、超人说等看法却表明尼采那里有形而上学。尤其关键的是,不能以为一个哲学家面目上拒斥形而上学惯常的辞令,形而上学就会从他那里消失了。形而上学仿佛谚语中的魔鬼,把它从门赶出去,它又从窗户跳回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形而上学有着从生活中无法割舍的人性价值。因此,断言某某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比断言某某不是一个形而上学家要冒更大的风险。即以海德格尔本人来说,形而上学依然是“阴魂不散”,他提醒人们勿忘笼罩着存在者的“存在”,并在《存在与时间》之后继续究诘“存在本身”问题,并将之称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注: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页。)。尽管海德格尔同尼采一样,瓦解了许多旧形而上学的东西,但就此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完结了。从来没有同一规格的形而上学语汇可以不变通地适用于柏拉图、尼采和海德格尔。而这一点恰恰要求我们要更加深入地把握住使形而上学成为其自身的意韵。本文倾向于将形而上学理解为一种对当下生活不满足与对未来更好生活寄托憧憬的特殊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 以消解的方式倡导哲学终结论的R·罗蒂的观点在此并不适用。按他的想法,比如说形而上学简言之是对好生活的憧憬,而追求好生活也可以是伦理学、政治学甚至文学的职能,并且形而上学的方式要么是推理的,要么是诗化的,经常是二者兼有,则方式又不能区别于物理学或诗,总之,形而上学既无独特的主题,又无独特的方法,因此形而上学想作学科“帝王”固然不行了,甚至作为学科活动也可以休矣,代以比如政治学或文学等等。(注:参见罗蒂:《后哲学文化》中“反本质主义和文学左派”,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 —161页。 )必须指出,罗蒂的论证会引伸到啼笑皆非的地步:依照消解策略,可以大大精简现有学术门类,剩下他比较钟情的几门(如自然科学或政治学)时,随后又会发现幸存者与日常生活谋划又不能严格区分。届时尴尬就逼上心头,要么甘于方法的任意中止,要么索性贯彻到底,那理论家的角色也就没了——奥康剃刀又站在哪里挥舞呢?!
如果说海德格尔在宣布尼采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时自己却矢志追求某种新的形而上学,如果说罗蒂的消解策略可以不必当真,那么,重新诠释尼采,并进一步澄清形而上学的本性,也就有其合宜性和必要性了。
二、生成与存在:反叛与回归
生成与存在的对峙,在一些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柏拉图、尼采那里是显见的主题。但又可以说它刺激着所有哲学家的情感和智力,它化身为多与一、意见与真理、事物与理念、尘世与天堂、经验与逻辑、感性与理性、沉沦与拯救、卑俗与神圣、庸碌与超脱等等看似不同实则相通的问题,为哲学家们反复琢磨。
通常,生成与存在并不等值,前者经常是虚幻的(巴门尼德)、次真实的(柏拉图)、罪性的(基督教)、有待升华的(康德)、有待规范的(卡尔纳普),后者经常是全真的、至善的、最终的、稳定的,因而是应当趋之若鹜的。这种类型的价值关系,几乎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传统特征。这些断定看似远离生活,却不仅仅是理论断定,它们包含着哲学家炽热的救世情怀。几百年来,在自然科学尺度的渗透下,哲学大有被“科学化”的趋势,少有人敢于张扬哲学对新生活憧憬的维度,因为憧憬隐含着褒贬,而褒贬似乎不属于科学。然而这却是哲学的命脉,哲学借此方能站稳自己的位置。哲学既平凡又独特。平凡在敏于现实的不足而憧憬未来,独特在竟以遥远的、漠不关心的、晦奥的理论方式副其使命。在哲学的平凡处,它和某总统的新政或某社区的发展规划属于同类;而其独特处却是人类迄今屈指可数的几种高举远慕的方式之一,它使一种理想长久为人求索玩味,在不同境遇中反复砥砺人于空忙、怠惰和厌倦。“哲学家乃是特殊职业:改恶,扬善,歌颂神圣”。(注:尼采:《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01页。)
就生成与存在来说,二者各自表征了一种生存境界,也都曾被发挥为哲学理想。但生成与存在总是作为两种必然的背景并置于思想的底蕴之中,而且没有一方曾被完全消解或超越。一般而言,生成作为一方每每是应被加工,被超越,被摆脱的,因此是作为理所当然的、由之出发的粗糙低级的境遇出现的。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总体倾向都是这样。但是,生成与存在,同为哲学思索的两极,原则上前者也可以作为理想得到发挥和渴慕,特别是当存在所表征的理想久追不获,耗尽了人们的才智、兴趣和耐心的时候,尤其是因反复强化而逐渐僵化使人有生机窒息的朕兆的时候。本来,任何理想的出发点都是对人的某一方面的强化或特化,同时也就是人性对其他方面的遏制或删削,反之亦然。约略而言,“人是什么?一半天使,一半野兽”,全部西方人性史都是在这两个极端间打转。神性可以凝结为存在方面,兽性则由生成认领;神性被认为是对人性的“提升”,也就是要除掉其中的兽性,而兽性则是人性的“堕落”,也就是使人永别于神性。可以说,无论什么理想,只要是理想,对人而言都并非可以甜蜜达到,倒是常有大痛苦伴行。什么时候理想的诱惑或许诺不敷痛苦的代价,该理想就要为人抛弃。在这种问题上,神性并不格外占着优势,可幸免于人类烦心的厌恶,也就是说,“兽性”的一方也可以对人成为理想。在这个意义上,单单打出“理想主义”的旗帜或“打倒理想主义”的旗帜,人们还是不知就里,必得追问理想是以神性为鹄的,抑或以兽性为鹄的?因此,当尼采指斥柏拉图主义的理想主义时(注:参阅尼采:《偶象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并不意味着理想主义本身该被反掉, 否则尼采自己的学说就无由提起了。况且,对某一种理想的反动必得也作为一种理想才能发挥效能,纵然是反对一切理想的理想在历史中也必得沦为理想。——理想之于人是宿命,理想之于哲学也是宿命。
若果如此,也就有了在学理上容纳尼采思想的合适理解框架。
从存在折向生成,于是便有许多诸如“最后”,“终结”,“死了”的惊赞,这实在是惑于辞令,缺乏根据的。与其说尼采一刀斩断了什么,不如说他突出了什么。并且既没有彻底消灭敌手,反之却在自己的学说里创造性地延续着对手的命脉。
那么尼采突出的是什么呢?生成。
按照存在的观点来看,生成是不须挖掘的,它似乎就是“出发点”,因而不用“达到”,倒是应该努力挣脱。但是人已然给世界和生活赋予了许多导源于“存在”路数的规定,它们已然拉开了人与生成的间距,这里不妨模仿海德格尔的修辞方式称之为“生成的疏远”,因而生成要求回复、达到、努力。它值得成为一种哲学理想和生活理想,其间必须消解导源于存在规定的蔽障。让我们来看尼采怎么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力的怪物,无始无终,一个坚实固定的努力,……它不消耗自身,而只是改变面目,……作为无处不在的力乃是忽而为一,忽而为众的力和力浪的嬉戏,此处聚集而彼处消减,象自身吞吐翻腾的大海,变幻不息,永恒地复归,以千万年为期的轮回;其形有潮有汐,由最简单到复杂,由静止不动,僵死一团、冷漠异常,一变而为炽热灼人、野性难驯、自相矛盾,……它就是我的‘善与恶的彼岸’。它没有目的,……没有意志……——这是权力意志的世界——此外一切皆无!”(注:尼采:《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00—701页。)在哲学家,世界就是世界观。尼采的世界,狰狞、雄壮、充满激情,脱却了目的、善恶、意志,冲碎了存在的规定之网。在这个世界,逻各斯也许在赫拉克利特的意义上还可以使用,但已决非沉思的理性所能捕捉,也决非刻板阴郁的德性所能皈依,感受它需要悲剧式的艺术跳跃。虽然从存在的观点看,不能配备理性—逻各斯的世界就是不可理喻、没有意义的,但尼采正要欢呼这种无意义,借此号召人们跃入嬉戏般的涨落、浮沉。超人也就将从中诞生。超人就是人的新生,人的理想。
生成既如此,它的理由何在?这特别要质问作为哲学家的尼采。尼采的确在学理上强有力地解说了生成与存在的关系。不过正是这一解说,泄露了尼采工作的陈旧性,尽管是伟大的陈旧性。
尼采对生成的理解,原则上可以完全追溯到赫拉克利特,因而没有根本的创新。尼采的独到之处,在于从生成的视野出发,澄清了“存在”之类生成的一种机制。“人们不应当把形成概念、类、形式、目的、法则(一个同等状况的世界)等的必需,理解为似乎这样我们就真能固定真实的世界;而应当认为这是一种必需,即为我们准备一个使我们的生存成为可能的世界。……在我们长期推行了同一化、粗糙简单化之后,我们就成了创造了‘物’、‘同一物’、主体、谓语、行为、客体、实体、形式的人了”。(注:尼采:《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40页。)这是在尼采那里罕见的同情了解的笔触。 他更经常是十分苛刻的:“从前,一般说来,人们把转化、变化、生成看作假象的证明,看作必定有某种引我们入迷途的东西存在的标记。今天,我们反过来看,恰好至于理性的偏见驱使我们设置统一、同一、持续、实体、始因、物性、存在的地步,在一定程度上把我们卷入错误,强制我们发生错误,……他到处看见行为者和行为,他相信意志是普遍的始因;他相信‘自我’,作为存在的‘自我’,作为实体的自我,并且把对‘自我—实体’的信仰投射于万物——他借此才创造了‘物’这个概念……存在到处被设想,假托为始因;从‘自我’概念之中方才引申、派生出了‘存在’概念……在开端就笼罩着错误的巨大厄运。”(注:尼采:《偶象的黄昏》,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由此看来,自我、物、主体、客体、实体、存在,这些赫赫有名的概念在尼采眼里都是使人的生存得以可能的手段、权宜之计。它们产生于人的虚构——一种有用的虚构;由它们勾织的“世界”也只是一个方便的工具性框架,是不能冒充为或误认为真实世界的。而令尼采大为不满的正是这种冒充或误认发生了,并且极有势力,成为传统。存在不再是对生成流变的权宜冷冻,却上升为最高的真实,生成反变为拙劣的赝品,假象的渊薮。完全的本末倒置。尼采针对这种“倒置”的动机和效果提出了四大命题:“第一命题。将‘此岸’世界说成假象世界的那些理由,毋宁说证明了‘此岸’世界的实在性——另一种实在性是绝对不可证明的。第二命题。被加诸事物之‘真正的存在’的特征,是不存在的特征,虚无的特征,——‘真正的世界’是通过同现实世界相对立而构成的:既然它纯属道德光学的幻觉,它事实上就是虚假的世界。第三命题。虚构一个‘彼岸’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倘若一种诽谤、蔑视、怀疑生命的本能在我们身上还不强烈的话。在后一场合,我们用一种‘彼岸的’、‘更好的’生活向生命复仇。第四命题。把世界分为‘真正的’世界和‘假象的’世界,无论按照基督教的方式,还是按照康德的方式,都是颓废的一个预兆,——是衰败的生命的表征。”(注:尼采:《偶象的黄昏》,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5页。)在此须要指明:无论存在之超越或虚构之被误为真实,理性无疑是其中熔铸的巨匠,换言之,理性是罪魁。
然而,存在占了生成的上风纯粹是一条迷途吗?按照理性的尺度规范人肯定是生命衰败的表征吗?尼采自己有一种晦涩的解说:“倘若一个人不得不把理性变成暴君,如苏格拉底所为,那么必是因为有不小的危险,别的什么东西已经成为暴君。这时,理性被设想为救星……整个希腊思想都狂热地诉诸理性,这表明了一种困境:人们已陷于危险,只有一个选择:或者毁灭,或者——成为荒谬的有理性的人。……制造一个永恒的白昼——理性的白昼——以对抗黑暗的欲望。无论如何必须明白、清醒、理智,向本能和无意识让步只会导致崩溃。”(注:尼采:《偶象的黄昏》,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0页。)这段话令人不禁生疑。没有什么哲学应该教人自毁,那么苏格拉底的抉择必定是十分可取的,因而不能把这一转变视为十足的迷失或衰颓,于是存在占了生成的上风也就有其历史的适宜性,而这是尼采自己也不否认的。虽然尼采对苏格拉底的严厉口吻无以复加,但并不排除他和苏格拉底的某种深刻的一致,他自己十分清楚:“苏格拉底与我难解难分,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与他战斗。”(注:尼采:《哲学与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支持着这种“战斗”的是革故鼎新的伟大冲动:“当价值的来龙去脉业已澄清之际,宇宙在我们眼里也就失去了价值,变成‘无意义的’了,——不过,这只是一种过渡状态罢了。”(注:尼采:《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第427页。)过渡期后的宇宙意义,尼采勾划出一整套,如超人和强力、永恒轮回和热爱命运等。显然,一个“候补”的哲学之王大现其身了。不仅如此,尼采还强调:“给生成打上存在性的烙印——这是最高的权力意志。”(注:尼采:《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74 页。)这句话实际上等于为他曾激烈批评的所有哲学家翻了案,而他自己也就俨然那伟大哲学庙宇中的又一尊新神。这新神乃是恺撒和耶稣的混血儿,伟大的理想家,传统的嫡子。
三、形而上学的本性:虚化现实与筹划未来
形而上学是什么?
这个问题不知被提出多少回了。在时间之流的冲刷之下,不禁使人为给形而上学确定普适的规范而踌躇再三。就对象或内容来说,理念、上帝、自我、单子、绝对、意志、存在,不一而足。就方法来说,知性推证、辩证显现、神秘感悟、诗意宣示,莫衷一是。既缺乏确切的内容,又没有一定的方法,那么形而上学也就几乎不成其为“学”了。其实,不是“学”的却可以是智慧,本来,“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 )未必就肯定又是“什么学”。历代哲学大师对形而上学都爱不释手,孜孜以求,津津乐道;同时,形而上学自身位置的合理性却又无时不处于被拷问之中。形而上学的这种境况康德描绘得很漂亮:“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而且由于缺少一个公认的标准,每个人随心所欲地塑造他自己类型的形而上学。至今被叫做形而上学的东西并不能满足任何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的要求;然而完全放弃它又办不到。”(注: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63页。)那么, 居然古老常新的形而上学竟不能为自己的存在一劳永逸地确立理由吗?本世纪以来,人们见仁见智,越发对这个问题没有把握了。既然没有定论,下面的意见也许就并非不值得考虑:既非界定其内容或对象,也非拟定其方法,而是从考虑形而上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的角度出发,我们会看到,形而上学的运筹方式是虚化当下现实世界,对照以一个尚待达到的新的世界,为生活提供一个异于当下的可能维度,——形而上学的事业不多不少就是这些。
就方法而言,虚化不是方法,毋宁是一种取向。就对象而言,形而上学既不沉迷于彼岸,也不拘泥于此岸,毋宁说它撑持、联络于两个世界之间。
形而上学呼应于人的生存状况:人有明天有未来,尤其作为一个整体,更是这样。形而上学正是人指向未来的谋划方式。凡形而上学对现实世界有所评论,都不是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将其视为假象,而是在如何能生活得更好、更有力度的价值论意义上视之为不足取。对形而上学探讨来说,真假之分在本质上是理想与现实之分。并不是先认清了真假之后,再将前者当作应当追求的理想,将后者当作应当萃取或唾弃的对象,恰恰相反,理想或对未来的积极谋划,先于真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说:“真实的世界和表面的世界——我把这种对立的来源追溯到价值关系。”(注:尼采:《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9页。)说到底, “哲学思索的本质就是忽视眼前的和暂时的东西”,“哲学家希望用新的世界描述代替现有的世界描述”。(注:尼采:《哲学与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2页。)
人而不求价值,这是不可能的。人不能拒绝未来的降临。形而上学的人性根据也就在于这里。何时人在,形而上学就在。M ·舍勒卓越地指出:“人唯有作为由此一王国到彼一王国的‘跃迁’、作为这两王国之间的‘桥梁’和运动,才有自己的存在。他不能放弃决定自己属于哪一王国的权利,因为放弃决定也是一种肯定的决定——动物——如果是动物的话,一种蜕化了的动物。超越本身的热情烈焰——无论其鹄的是‘超人’抑或‘上帝’,这便是人唯一真实的‘人性’。”(注:舍勒:《爱的秩序》,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1页。)
正由于形而上学基于人性的未来谋划功能,它有着诡谲奇妙的历史:它往往以自毁的形式真正延续自身,事情仿佛总是重新开始,另起炉灶。理念论把价值锚定在理性可能通达但却疏远于感官、欲望的存在之上,尼采则以对生成之颂扬和对存在的解剖几乎瓦解了作为理念论的形而上学,但尼采又恰恰是作为一样的形而上学的权力意志的哲学家而出现的。形而上学如同火凤凰涅槃一样反复再生,理想、未来的尺度一次次以不同的面目重新攫住了最富天才的思想家。只是由于眼界促狭,才会出现把形而上学再生性的自毁等同于它的真正消亡的误解。
进一步,我们须澄清两个疑惑:
首先,鉴于已有形而上学的艰深以及随之而来的不稳定性甚至混乱,它给理知的把握造成极大的困难,有否可能改善它,拟定一类顺乎理知习惯的形而上学?其次,形而上学是否是人的超越性理想性的唯一模式?
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艰深对形而上学来说也许是根本的,理由在于未来、理想作为尚不存在的东西只能甘为一种设定,它与现实的联络并非逻辑推证能够框定,在这类问题上诉诸臣服于现实的实证主义,属于文不对题。海德格尔在论及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时说:“哲学的一切根本性问题必定都是不合时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哲学或者远远超出它的当下现今,或者反过头来把这一现今与其先前以及起初的曾在联结起来。哲学活动始终是这样一种知:这种知非但不能被弄得合乎时宜,倒要把时代置于自己的准绳之下。”而且,“就其本质而言,哲学决不会使事情变得浅易,而只会使之愈加艰深。这样说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日常理性不熟悉哲学的表述方式,或者认为它近乎梦呓。”(注: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13页。)对于实证的日常理性来说,形而上学的确总是不合规范的。尼采也曾阐发形而上学运作的非推证性,他名之为“形而上学的心理学”:“——这个世界是表面的,因此,一定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条件的,因此,一定有一个绝对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矛盾重重的,因此,一定有一个无矛盾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变易的,因此,一定有一个存在的世界。——这些都是十分错误的推论。这种结论是痛苦激发的结果。根本说来,这些推论都是愿望,它们要这样的世界;同样,对一个制造痛苦世界的仇恨也表现在对另一个世界的幻想上,一个更可贵的世界。”(注:尼采:《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59页。)确实,假如完全拘泥于知性逻辑要求, 理想的翅膀也就根本无法高翔。
后一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否定的。人之高举远慕超越现实并不限于形而上学一途。在既存的文化样式中,神话和宗教与形而上学一样比肩矗立在人类当下境遇的极限处,透露着明天的消息。它们都比形而上学古老,但它们与形而上学一样是对未来的筹划,功能是一致的。这三者中形而上学之所以能保有自己的独立性,是因为形而上学较强的反思性和世俗性。反思性使它区别于主要诉诸灌输和习惯的神话,世俗性使它区别于主要通过情感和信念来指涉超然世界的宗教。
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权力意志论文; 尼采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哲学史论文; 商务印书馆论文; 人性论文; 现象学论文; 终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