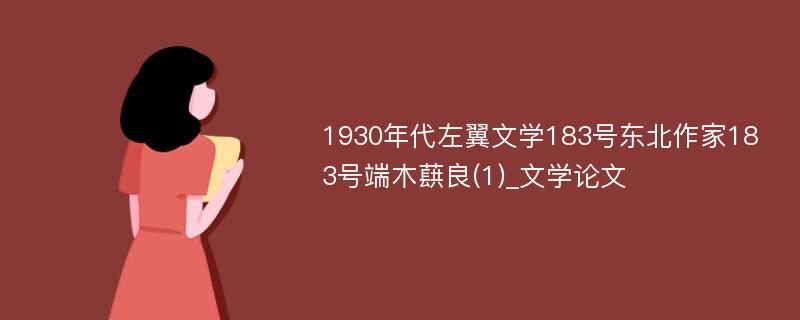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183;东北作家群#183;端木蕻良(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三十年论文,端木论文,作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现代文学研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新时期里,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以重新发露它的意义和价值开始的:我们重新解读了鲁迅,从鲁迅的著作中发现了与政治家、革命家的思想学说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发现了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和对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追求,发现了他的孤独和绝望,发现了他对孤独的和绝望的抗争,并从他对孤独和绝望中发现了他的哲学;我们重新解读了茅盾和郭沫若的作品,不但在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了与外国文学影响的联系,也从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了种种难惬人意的弱点和不足;我们重新发现了徐志摩、李金发、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冯至、《九叶集》派的诗、《七月》《希望》派的诗,重新发现了胡适、梁实秋,重新发现了周作人、林语堂、废名,我们把他们的作品从尘封的“资产阶级文人”、“反革命分子”的档案馆里解放出来,使他们的作品重新焕发了昔日的光彩;西方的研究者、港台的研究者帮助我们发现了张爱玲、苏青、徐訏、无名氏,我们自己则发现了沈从文的小说、新感觉派的小说,新武侠小说、新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也进入了我们研究的视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曾对东北作家群的作品投射过关注的目光。新时期最早以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大概是我的师弟王培元,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写东北作家群的,他后来编辑出版了《东北作家群小说选》;在东北作家群研究中卓有成效的是东北师范大学的逄增玉先生和河南大学的沈卫威先生,他们都有东北作家群研究的专著出版,对东北作家群各个作家的分别研究也在东北作家群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地区自己也曾出版过东北作家研究集刊类的刊物,出版过大型的东北作家的丛书。但所有这一切,在众声喧哗的当代文学研究的论坛上,都没有发生更大的影响。在当今的社会上,人们热衷的是周作人、林语堂的散文,穆时英、施蛰存、张爱玲的小说。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并且是我们新时期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但假若我们从整体上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研究进行一次扫描,我们会发现,在我们每一步都似乎朝着一个理所当然的正确方和向前进的时候,当我们每个人都真诚地、认真地进行着自己的探索和研究,都在发露着我们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我们却也在不自觉中遮蔽了很多东西。“十七年”被奉为主流的左翼文学受到了自那时以来最严重的冷淡,甚至鲁迅因与左翼更亲密的关系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怀疑乃至轻视,似乎左翼文学已经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似乎它原本来就是一次历史的失误。在“十七年”,“左”是坠在它胸前的一块荣誉奖章,而现在,“左”则成了打在它脸上的一块耻辱的印记,而“十七年”被贬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文学的作品则拥有最大量的读者,似乎他们才是当时最最正确的文艺方向的坚持者,其作品也体现了那个时期最高的艺术成就,不“左”在“十七年”是一块耻辱的印记,而现在则成了一个“光荣”的符号。左翼文学被遮蔽了,“东北作家群”自然也就被遮蔽了,因为东北作家群是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旗帜下陆续走向文坛的,他们的基本倾向从来都是“左”的。虽然上述那些研究者还在不断地阐释他们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但他们的作品却已经没有多少读者。假若我们现在问林语堂是谁?施蛰存是谁?只要有点文学常识的人都会给我们作出正面的回答,但假若我们问端木蕻良是谁?骆宾基是谁?恐怕就没有多少人能够回答出来了。但是,只要真的读过端木蕻良、骆宾基作品的读者,只要不是以他们的政治态度而是依其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感受和衡量他们的作品,他们就一定是较之林语堂、施蛰存低一个等级或几个等级的作家吗?我认为,情况远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对萧军和萧红是熟悉的,但我们熟悉萧军并不是熟悉他的作品,而是熟悉他与萧红的关系,而对于萧红,我们常常一反过去的态度,不是把她视为一个左翼作家,而是将之视为一个非左翼作家而得到我们的肯定的。我们没有以她为标记拒绝张爱玲,但却常常以她为标记拒绝丁玲。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在无形中被我们遮蔽了,我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的作品,而是我们自觉不自觉地离开了他们,离开了他们作品的思想意义和审美风格。我们告别了豪放和粗野,走向了细腻和缜密。
这个变化不是不可理解的。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和动荡中走出来的,是在从“革命文学”、“左翼文化”、“解放区文学”发展出来的“十七年”的文学中走出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的旗帜下“横扫”了学院派知识分子,“横扫”了所有被视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包括当时“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阵营中的大多数人。我们厌恶了豪放和粗野,我们尝到了“左”的苦涩,我们希望一个稳定的社会,一个和睦的人际关系,一个充满了爱和同情的世界。任何带尖刺的东西,任何富有震撼力的激情,任何与我们平静生活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东西,都会在我们的心灵中引起一种恐怖的回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们需要周作人,不需要鲁迅,周作人即使批评我们,也带着温和的性质,而鲁迅的攻击则令人感到一种无可逃遁的紧张;我们喜欢徐志摩,不喜欢闻一多。徐志摩的潇洒和从容是我们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一种人生态度,而闻一多则令我们感到一点憋不住的激烈,一种与我们希望平静的心背道而驰的情绪;我们喜欢戴望舒而不喜欢艾青,因为艾青的诗中有一种承担的沉重,一颗动荡的反叛灵魂;我们喜欢张爱玲而不喜欢丁玲,因为即使张爱玲感到荒凉和寂寞的那个世界,也是我们愿意进入的世界,而丁玲的世界却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进入的。那是一个太危险的世界,一个令我们自身难保的世界……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然而然的倾向,也是无可厚非的倾向。我们就这样进入了文化界,成了我们时代的文化“精英”。我们还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不满,但我们已经能够在我们的文化中居住下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按照我们自己给自己制定的作息时间表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文化的“建设”,按照我们给自己制定的质量标准检验我们的学术“成就”。我们不承认任何外在的权威,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权威;我们不承认任何的圣人,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圣人。在我们自己的意识中,我们就是真理、正义、公道、进步、社会文明的象征,我们以反主流文化的姿态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
但是,我们是怎样成了我们时代的“精英”,我们时代的“圣人”的呢?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进入中国当代文化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制造了半生的苦难,但也为我们清扫了中国当代文化的空间。旧的主流文化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没有了自愈的能力,我们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般地大踏步进占了新时期的文坛。在开始,我们还能听到从远方传来的零星的枪声,到了后来,到了比我们更年轻一代的作者那里,则连这枪声也听不到了。这是我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的人生观和文化观。我们喜谈建设而厌恶破坏,因为我们已经不需要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我们需要破坏和不需要破坏的所有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莽莽苍苍的文化空间。我们不必破坏什么就能建设起“自己的园地”,这个园地的“建设”有西方文化的现成图纸。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封闭为我们保留下了这些图纸的“新颖性”和“创造性”,使我们在中国大陆文化的疆域内获得了“创造者”和“探索者”的美誉;我们喜谈温和而反对激烈,因为文化大革命压制了反对我们和不反对我们的所有人的“气焰”,我们已经没有多少严峻的文化敌人,我们不需要激烈也不会激烈;我们喜谈爱情而诅咒憎恨,因为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在变成弱者的强者身上发泄了所有的憎恨,只有把文化大革命那段应当让毛泽东负责的经历丢到九天云外,我们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就是没有憎恨也不会憎恨的人。我们好说“告别革命”,实际上不是我们告别“革命”,而是“革命”告别了我们。我们根本就没有革过命,也从来没有打算去革命,我们向谁告别?……总之,我们是戴着白手套而采摘了我们的文化成果的。但一当我们成了文化的“精英”,一当我们在被文化大革命清扫出来的文化空间中安了营,扎了寨,并且占领了这个领域的角角落落,其他的人就很少有可能挤进我们的文坛了。他们开始向经济的领域、政治的领域进行战略转移。但一当转入经济的领域、政治的领域,我们这一套文化却行不通了。在经济的领域里,金钱就是皇帝,经营手段就是将军,我们的人道主义只能当老板们的擦脚布,谁要真把我们的文化当成金科玉律,谁就会被拔光吃净;在政治的领域里,权力就是生命,策略就是骨骼,我们的幽默和冲淡只能当政治家会议桌上的一种点缀品,谁要是真把我们的文化当成自己的指导思想,谁就会永久地被踩在别人的脚下,成为各种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们在“文化”上胜利了,但我们在“社会”上却失败了。在“文化”上,我们讲的是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是理解和同情,是幽默和冲淡,是达观和超脱,是中庸和和平,而在“社会”上,行动着的却不是我们的文化原则。金钱和权力以及金钱和权力的联合力量起于草末,聚于原野,奔流在长江大河,我们的精英文化微笑着迎接了这阵给世界带来清爽和活力的狂风,但当它像龙卷风一样在世界上汇聚成了一股其大无比的力量,我们的文化的宫殿却也开始发生着精神的坍塌。它把我们的文化连根拔起,抛到空中,旋到天上,而后又撒落在大地。我们的文化实际早已成了文化的碎片,收拾不到一起来了。我们高谈着个性主义,但我们的个性主义却不能不是在现实规范约束下的个性主义;我们高谈着人道主义,我们要求别人对我们实行人道主义,但我们却未必对比我们更弱小的人实行人道主义;我们高谈着自由,但真正得到自由的仍然是金钱和权力,而不是社会上的人;我们高谈着同情和理解,但我们同情和理解的永远是那些根本不需要我们理解和同情的国家和个人,是比我们更强大、更富有的国家和个人。他们没有我们的同情照样能够强大和富有,而需要我们同情和理解的却未必能得到我们的理解和同情……我们自以为成了我们时代的孔子,但是实际上,我们却成了我们时代的杨朱。我们与杨朱不同的是,杨朱为我,杨朱的文化也是为我的文化,而我们讲的却是人类、国家和社会,是人类的文明、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文学的发展。在开始,我们是用现实的感受看待文化的,是用对中国的体验看待西方的,是用人的需要看待科学和理性的,现在却颠倒了过来。我们开始用文化规范现实的感受,用西方的标准要求对中国的体验,用所谓科学和理性的标准来衡量人、要求人。我们开始是被别人的思想标准和文学标准所衡量的,而现在我们开始用自己的思想标准和文学标准衡量别人、要求别人。但这也恰恰证明了,我们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正统的文化、高雅的文化、主流的文化,我们以反正统、反高雅、反主流的姿态体现的却是我们时代的正统的、高雅的、主流的文化。这正像朱元璋,反了皇帝,成了皇帝,我们则是反了主流文化,成了主流文化。我们用我们的主体性扫荡着一切不同于我们的人的主体性,似乎所有的人都必须匍匐在我们的文化价值标准面前惴惴不安地等待我们的审判。在我们的文化价值标准面前,连鲁迅也成了不值一哂的心理变态狂、不可救药的激进主义分子、横躺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块僵硬的石头。但据说,这都是为了反对主流文化的需要。
二
在我们谈论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时候,提出来的常常是谁是主流文化、谁不是主流文化的问题。我认为,这种提问题的方式就是值得商榷的。谁是主流文化?谁是非主流文化?这个问题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层面上才能进行确定的指认,而一当脱离开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层面,主流文化可能成为非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也可能成为主流文化,想在不断流动的历史上指认一种文化是不是主流文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谁是官?谁是民?今天我当了官,我就是官,明天我不当官了,我就不是官了。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问题也是这样。所以,这里的问题首先是什么是主流文化、什么是非主流文化的问题,而不是谁是主流文化、谁不是主流文化的问题。什么是主流文化?主流文化是一个社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被普遍视为合理性、合法性的文化。正因为它是被普遍视为合理性、合法性的文化,所以它的生产和传播是不会受到政治、经济法权的抑制、压迫和摧残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受到政治、经济法权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保护;什么是非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是一个社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被普遍视为非合理性、非合法性的文化。正因为它是被普遍视为非合理性、非合法性的文化,所以它的生产和传播是不会受到政治、经济法权的保护的,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受到政治、经济法权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抑制、压迫或摧残。实际上,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就其本身是没有正确和谬误之分的,主流文化既不是绝对正确的文化,也不是绝对谬误的文化。它像任何一种文化一样,都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本能需要但又不是所有本能需要的体现,是现实社会一部分人的本能需要但又不是现实社会所有人的本能需要的体现。它之成为主流文化永远是现实社会一种本能需要压倒其他所有其它本能需要、一部分人的本能需要压倒其它所有人的本能需要的结果,因而它也自然地具有一种社会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性质。社会霸权是说整个社会都会强制地让每一个人都简单地、无条件地服从它的文化原则,违背它的原则就是违背整个社会的原则,并且会受到社会各种形式的惩罚;所谓文化霸权就是在文化上它的原则和结论已经被确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所有其它的文化则必须为自己作出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证明,并且是以主流文化的原则作为论证的公理、定理系统的。这样,主流文化实际已经是一种失去文化本质的文化。文化本身就是在人类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人类不断求知的过程。它既然已经被社会公众承认为绝对的真理,既然已经不需要对自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作出新的证明,它就失去了人类相互交流的功能,也退出了人类求知的过程,其文化的性质就退化甚或消失了。非主流文化也不是绝对正确的文化或绝对谬误的文化,但自然主流文化已经在社会上具有了社会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性质,它就一定会对每个个体的人的另一些本能需要构成抑制、压迫和摧残,并且这种抑制、压迫和摧残在社会的少部分人那里则成为不可忍受的。法家的文化对于秦王朝的统治是一种合性、合法性的文化,秦朝的法律对于推行秦王朝统一的政策和法令是一种需要,但到了陈胜、吴广那里,则成了无法忍受的压迫和摧残。当受到抑制、压迫和摧残的人的本能要求还仅仅是一种内心的体验,还仅仅是一种无可名状的痛苦,它还不是一种文化,但当这种内心体验找到了一种语言形式,使之在社会上有了公开表达的可能的时候,它就成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在反抗主流文化的抑制、压迫和摧残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对主流文化进行证伪的过程中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的,所以非主流文化的总体特征就是其批判性,“破坏”性,它是对主流文化的批判中逐渐建构自己的。但也正是由于非主流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激活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其中也包括它所反对的主流文化。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主流文化才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公理,而成了必须接受挑战、必须重新论证自己的东西。假若它已经不能论证自己的合理性,它就无法继续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的认可和信奉,它的权威地位就会逐渐地丧失,甚至最终让位给反对它的非主流文化。必须指出,非主流文化也是一种群体性的文化,因为文化不能不是群体的。文化是一种语言形式,是交流的手段,它至少还有一个发话者和一个听话者,并且在二者之间能够起到彼此沟通的作用。但主流文化体现的是社会整体,非主流文化体现的则是社会整体之内的更小的社会群体,并且这个社会群体也像它的文化一样,是在社会整体中不被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的社会群体。非主流文化在其内部也是被普遍视为合理性、合法性的文化,也是对不同的本能需要和少部分的现实需要具有抑制、压迫、摧残的作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整个社会上已经成为主流文化。当它还是非主流文化的时候,即使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是建立在反对主流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在不断建构自己的过程中发生的。这并不说明它在整体上已经是一种主流的文化。主流文化因其社会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性质可以建立在一个抽象的理念的基础之上,人们在不理解其合理性的基础上也必须遵从它、信奉它,其理念是与自己的生活体验、精神体验相脱离的,而非主流文化则没有这种社会霸权和文化霸权,人们是在自己的生活体验的推动下离开主流文化而趋向于非主流文化的,即使这种文化理念自身具有抽象的性质,其中也曲折地指涉着这些人的实际的生活体验和精神体验,不是纯粹的做戏,不是完全骗人的东西。由于这种原因,主流文化往往表现出一种胖大而无力的特征,而非主流文化则表现着一种瘦小而有力的特征。主流文化的无力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绝对谬误的语言形式和理论形式,而是因为这种语言形式和理论形式已经与现实人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失去了更直接、更紧密的联系;非主流文化的有力也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绝对正确的语言形式和理论形式,而是因为它与现实人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存在和发展有着更直接、更紧密的联系。非主流文化并不总是能够上升为主流文化,恰恰相反,大量的非主流文化是不可能上升为主流文化的。中国古代的道家文化从来没有上升到主流文化的地位,因为它自身并不具有社会政治的性质,不具有成为主流文化的基本条件,但它却一直作为儒家文化的解构力量存在着,满足着社会联系之外寻求个人心灵平静的知识分子的愿望和要求。但那些具有社会政治性质的文化是有可能上升为主流文化的,社会文化的整体演化往往具体表现为一种新的主流文化代替了另一种主流文化,这种新的主流文化仍然将会遇到新的非主流文化的挑战,但它也给社会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一个新的基础。西方18世纪的启蒙主义文化、中国20世纪初的三民主义文化,中国20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都经历了由非主流文化向主流文化转变的过程。但在3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却不能视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也不是当时的主流文学。我们在反主流文化的旗帜下对鲁迅、对左翼文学运动的批判,并不具有真正反主流文化的性质,而是对现实主流文化的一种曲折的肯定形式。
三
我们对鲁迅、对30年代左翼文学的批判是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旗帜下进行的,但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往往只讲少数知识分子理念上的现代化,而不讲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化、文明化。实际上,中国文化的落后性不仅仅是由少数知识分子理念上的落后造成的,更是由整个社会经济上的落后造成的。中国古代书面文化向来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文化,其中多数又是官僚知识分子。中国大多数的社会群众无法参与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他们的感受和体验得不到直接的表现,更无法发展出独立的文化。少数具有反叛心理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是一个更强大的官僚知识分子集团。他们的文化是通过官僚知识分子的消化和吸收才得以在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一定的影响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但却永远无法构成一个相对统一的非主流文化,更没有力量上升到主流文化的地位上去。这样一个文化发展状况,是不可能带来整个文化性质的变化的,是不可能导致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整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推动下发生的,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却并不等同于中国文化的西方化,仅仅由少数留学生把西方文化的理念介绍到中国是无法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文化生活、利用书面文化载体表达自己现实的生活感受和精神感受、表达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只有表达,才有对话,才有心灵之间的切实的碰撞和交流;只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进入到这种对话关系当中来,中国文化的社会化的程度才会不断提高,中国文化才不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卖弄嘴皮子、卖弄笔杆子的杂场,各种不同的文化理念才会在切实的生活感受和精神感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形成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文化,形成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文学艺术。它没有一个确定的终点,也不是一次一劳永逸的革命,而是一个曲折变化的历程。任何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带着自己独立的生活感受和精神感染进入中国的文化界、参与到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活中来,都会给中国的文化带来新的变化,都会给整个社会文化的格局带来一次新的调整。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变化、不断的调整中逐渐实现的。任何一个阶层都没有垄断中国现代文化的权力,也没有永久地占据主流文化位置的力量。“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少数知识分子进入了中国文化的舞台。在当时,它是一种非主流的文化,是在反叛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带来了中国文化根本性质的变化,也给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胜利并没有把新文化整个地提升到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地位上去,只是增强了中国社会对新文化的容受力。中国文化的格局原本是极其狭小的,新文化的格局则更加狭小,它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加入。1927年的中国事变重新把大量青年知识分子排斥到了政治、经济法权的保护圈外。他们仍然不是中国社会的普通群众,不是工人和农民,但他们的社会处境却与底层的社会群众有着更多的联系,他们的生活感受和精神感受与那些已经有了稳定社会地位的学院派教授和学者有了更明显的距离。他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它处在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之间的联系通道上,是上下两个阶层的通风管道。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社会感受,有他们自己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社会感受和精神体验无法代替其他所有社会成员的感受体验,不是惟一正确的,但却也是中国社会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感受和体验。他们的文化无法代替整个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但其他社会阶层的文化也无法代替他们的文化。他们起到的是把整个中国社会挂到国家政治统治的战车上的作用,是把穷人挂到富人的经济现代化的战车上的作用,是把社会群众挂到上层知识分子文化的战车上的作用,使中国的现代化不致只成为国家政治统治者统治手段的现代化,只成为少数富人的消费生活的现代化,只成为少数学者和教授的话语形式和理论形式的现代化。中国社会要发展,中国文化要发展,但这种发展却不能造成整个下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更严重的脱钩现象。假若上层社会被西方文化的拖车拖到“超现代化”的高度,而整个中国社会群众却被现代化的反作用力抛到更加原始的茹毛饮血的生活之中去,这种现代化的也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我认为,这就是30年代左翼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戴望舒、穆时英、施蛰存、沈人文等人所体现的非左翼文化也不是当时的主流文化。当时的主流文化是三民主义文化、是被当时政治、经济法权化了的三民主义文化,这些非左翼的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当时主流文化的束缚和抑制,但当时的主流文化对这种文化已经有一定的容受力,这种文化也已经适应了在当时主流文化的束缚和抑制下曲曲折折表达自己内心意愿的社会条件和文化环境,已经失去了“五四”时期直接向当时的主流文化挑战的能力。左翼文化则是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非主流文化,不论在它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多少不应有的波折和挫折,有着多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作为一个整体,它关注的是那些被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也包括中国现代文化所遗弃了的人们。正是它,给当时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个新的生机,也带来了一种新的话语形式和理论形式,一种新的审美倾向和审美形态。在30年代,它起到的不是消灭了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戴望舒、穆时英、施蛰存、沈从文所体现的非左翼文化的作用,它的非主流文化的地位使它根本不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而是通过挣扎和努力在中国文化界存在下去,发展起来的作用。它在当时的发展是有限的,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最惨重的,但这恰恰证明了它的非主流文化的地位。
通讯地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邮编:100875
标签: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端木蕻良论文; 作家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