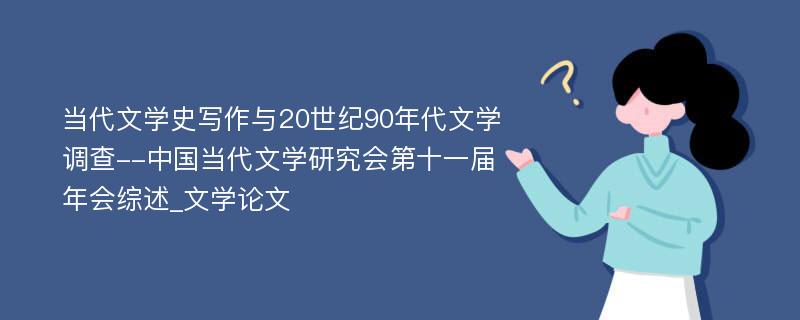
当代文学史写作与90年代文学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1届学术年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文学史论文,研究会论文,年会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7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9-8445(2000)04-0041-09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肇庆学院承办的第11届学术年会于2000年11月5日至9日在广东肇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20余人出席会议,人数多,规格高,时间长,信息广,气氛热烈,思想丰富。年会围绕“当代文学史写作与学科建设”和“90年代文学考察”这两个中心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各抒已见,求同辨异,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交流,集中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动向。
一、当代文学史写作与学科建设
1999年出版了两部很有分量、很有影响的著作,即洪子诚独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和学科建设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与会者(包括作者本人)对这两部著作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评论,在高度肯定其学术成果的同时也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
洪子诚(北京大学)在《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写作问题》中指出:80年代许多优秀学者多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我也曾打算从事文学批评工作,但自己能力不够,于是退而求其“次”,作文学史研究。到了90年代,文学史研究忽然重要起来,而现状批评却有衰落的趋势。我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学史有那么重要吗?”我认为文学史工作不能取代文学批评,文学史当然也对现实发言,但无法取代对现实直接发言的文学批评。其次,是关于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贯通问题。“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观念,是对“现当代文学”划分的一种反思,但它实际上也构成对“当代文学”的挤压,“20世纪文学史”写作中已体现了这种挤压。这很正常。我们应尽可能发现可以贯通的内部问题、内在线索,这种工作,既可以从现代文学向后延伸,也可以从当代文学的基点向上溯源。“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存留,因为它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第三,“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这是借用的一种说法。外部研究侧重以确立的观念,评价体系,对对象进行评价。“内部研究”关注对象的内部逻辑,深入到对象内部,发现概念、范畴、形态的内在依据和演化逻辑。它可能更有效“解构”对象。但是,问题在于从事内部研究很有可能被对象所“同化”,而失去对文学现象的判断力和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力。第四,“当代史能否当代修”的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之所以有问题是时间距离所产生的压力。这种近距离,处理亲身经历的现象,既可以增加我们的判断自信心,也可以使我们犹豫不决,而回避了必须的决断。
陈思和(复旦大学)结合《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编修和他本人的学术研究谈了他的几点体会。首先,他认为“当代文学史”在空间上有缺陷,它实际上仅指1949年以来大陆社会主义文学,台港文学并未包括进来,这样,当代文学与台港文学无形中产生了隔离,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是不全面的。其次,是语言的局限。我们说的当代文学史实际上是汉文学史,与少数民族文学非常隔膜。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底层的文学我们并不了解。第三,是文体问题。近期上海评出的“90年代主要作品”大部分是小说,无一诗歌。90年代,诗歌多发在同仁刊物上。那么,正式发表的作品与同仁刊物上的作品有何关系?后者是否应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呢?第四,是文学史的层次研究问题,从对文艺理论、文艺运动、文学作品等诸种层次划分看,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很不完备。它只是一本“初级教程”,是面对大学专科和一般本科生的。
与会者从不同角度评价了这两部著作所取得的学科建设的实绩,认为它们各有特点,可以互补。毕光明(海南师院)在《当代文学史:新写作的可能性》中认为:陈著偏重于文本阐释,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五十年》论中见史,洪著则最有史的品格,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它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展现了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如强化问题意识,贯注历史批判精神,从“功能”(毛泽东文艺思想确定的文学新方向)入手寻找“结构”(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进程),回到历史深处的方法,重构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体系等。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能用确定不移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和建立在文体研究基础上的文学本体观,去照亮晦暗的历史材料和文学事实,使新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得到实现。黄伟林(广西师大)认为两部著作在理论体系上均有重大突破,其学科意义主要在于此。陈著以“民间”、“战争文化”、“潜在写作”、“共名”、“无名”系列关键词结构文学史,显示一个完整的文学史理论体系,充满内在的学理逻辑力量,文学史不再是作家作品的罗列或时间坐标的历时推移,而成为一个纵横有序的立体结构。洪著虽然不象陈著直接标明关键词,但全书贯通着严谨的学理思路,若辅以洪先生在《南方文坛》主持的“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栏目进行观照,更可看出洪著内在的文学史理论体系。洪著对史料的爬梳不仅体现了史家“信”的原则,而且也暗藏了思想家“识”的才能。陈剑晖(华南师大)、宋炳辉(上海外国语大学)、王光东(上海大学)都对陈著所建构的文学史理论新概念表示赞赏,并作了阐发,特别强调了“潜在写作”和“民间”的重要意义。
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两部史著提出了某些异议或意见。金汉(浙江师大)认为,有不同的文学观、文学史观有就不同的文学史,各种各样的文学史的出现正是文学史学繁荣的体现。我赞赏席扬提出的新历史主义。我与洪子诚不同,他掌握大量史料而我则面对大量作品。而文学史主要应是作品,是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的揭示,文学史应该是文学艺术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黄伟林认为,洪、陈两部文学史在经典作家作品的层面上似乎都脱离了惯例。洪著有意淡化了作家作品,陈著则淡化了“经典性”。虽然当代文学史的特殊性质决定了“经典”认同的困难,但既然是一门学科,又是这门学科的教材,在我看来,“经典作家作品”的认同虽然“知其不可为”,也应勉力“为之”。学科教材与学术专著不是一回事,它可以“存异”,更要“求同”,在这一点上,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姿态更审慎。王春荣(辽宁大学)发言的题目是《文学史编写的“创新”与“规范”》,认为“文学史”或“文学史教材”作为一种特定的知识型构,它在创新与规范上应该是辩证统一的,而不应该是对立的。1999年出版的四部文学史(洪、陈、杨外,还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修订本)在创新性上最具个性的是陈思和主编的《教程》,将创新与规范统一得较好的是洪子诚的个人史著。他把学术个性与当代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统一起来,这正是“史著”科学性和质的规定性所要求的。而《教程》虽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却有以“隐形”替代“显性”、“无名”替代“共名”、“民间”替代“精品”的嫌疑。这是对“史著”、“教科书”这种特定知识型构的“信史”的伤害。王春荣还就《教程》中所渗透的文学史观在操作时所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批评意见。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认为,文学史应是评论家和作家共同写就的,把文学史看成是作家作品史,有片面性,周扬、胡风、冯雪峰的文艺理论无专章专节,这样的文学史必然跛脚,没有台港文学也欠全面。洪、陈著均应在书名后面加上:(50年代—90年代,大陆部分),才准确、科学。王敏(河南师范大学)的发言纵论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历史和现状,认为在40余年的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点,即研究具有“意识形态化”,时代特色影响、制约着文学的研究;同时也存在研究的局限性,即在客观历史事实与个人化著述方面往往忽视前者,同时在文学史写作中女性是缺度或是失语的,到了90年代仍未冲破男性话语霸权,揭示出女性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更多的发言者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学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经验、思考、建议和构想。晓雪(云南省文联)提出两点建议:应更加重视和充分评价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划时代的发展与成就;给中华诗词(指现当代人用古典诗词的形式创作的各种诗词作品)以一定的地位。王万森(山东师大)结合编写《新时期文学》谈了三个问题:“新时期文学”能不能成史?怎样概括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文学的变化?运用什么样的理论模式操作?他认为,用单一的意识形态与文学史对接显然行不通,把文学史作为创作成绩的排行榜也不适宜。我们注重了与人文科学和更为开阔的社会科学的融合,并关注文学的内部结构变化,力求把新时期文学放到大文化语境中去考察,并在判断和评价中强化对文学的反思意识。周晓风(重庆师院)的发言涉及当代文学学科整合的问题,他认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第一,研究对象范围的整合。这主要是指大陆文学与台湾和香港、澳门文学的整合问题。这涉及到深刻的中华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决不可等闲视之。第二,研究对象性质的确认。这中间又涉及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问题,汉语写作与少数民族文学融合的问题,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问题,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语境问题,文学的技术条件和传播方式问题,这些问题目前还没得到深入研究。第三,史料与基础理论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意识形态痕迹甚重,史料的可靠性存在较大问题,应加以特别重视。所谓基础理论既包括文学的一般理论,更涉及文学史的理论和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特殊理论应对。王卫平(辽宁师大)在题为“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创新与突破”的发言中,就如何重写文学史提出以下构想:建构自己的阅读体验;建构自己的价值体系;建构自己的语体形式;树立文学的精品意识。他认为,虽然我们已经有了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水准较高、突破较大、探索性质较明显的文学史著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就不需要继续,不需要创新与突破了。因为,没有一种完美无缺的文学史,只有不同角度、不同类型的文学史,与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比较而言,当代文学“史”的建构仍然是薄弱的。黄伟林认为,文学史的写作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经典作家作品,二是理论体系,三是历史品格与文化背景。历史品格应该成为文学史的品格。文学是在文化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文学史的写作必须深入到文学的文化根基。当代文学史前30年的文化背景是社会主义文化,新时期文学的文化背景多元化了,但仍可看出诸如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全球文化等因素,文学史的写作在这样的背景展开,才可能既有开阔度,又有深度,作为一个学科才能真正站立起来,在众多学者的参与中茁壮成长。席扬(福建师大)对文学史理念及“可信性”提出质疑,认为,所谓的“信史”,都只是策略或花招而已。我企盼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应当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异化环境中自我权力资源不断外化的一种描述,成为知识分子的文学为生命展开方式而不断认证自我、实施关怀的过程。任何文学史的写作,只有在为他人的阐释可能提供启迪下获得意义。“信史”不应该是文学史的境界,“史”的本质属于思维方式或方法论。王耀文(太原师院)从文学史家自身素养的角度,阐述了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史家意识,认为由这样几种因素构成:人格精神(由写家独立自由的精神所培植的人格魅力在文学史文本中的发散);学养(包涵思想与学术能力的整合)、艺术感悟(建立于鉴赏基础上的阐释)。由于思想资源的匮乏等诸种原因,我们缺少伟大的阐释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多是曲学哗世的炒作,少有到位的诛心之论。阎纯德(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就20世纪中国文学史编写提出如下思考:文学史的撰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政治的荫护下发生、发展和繁荣的;文学史写作,一是要历史主义地描述,二是要科学地论述;文学史的写作是一种创造,但又不能随着历史亦步亦趋。潘旭澜(复旦大学)回顾自己几十年来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关联,评析了当代文学史写作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下所面临的问题。1993年他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辞典》出版。他构想自己写作的一本“当代文学史”是给专家们看的。他认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确实与以前不同。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国家意识,《讲话》所提出的文学实践才开始普及。另一方面,从中国大陆看,1949年开始,文学发生了变化,这使整个华文文学格局也有了明显不同。如果以1949年为上线,当代文学史的下线也可随不同写作者的观念而定。他认为,我们的文学史思考还应在外延和内涵方面拓展,构架也应超越以前,因为当代文学史构架曾深受高尔基、季莫维耶夫文学史构架的影响。当代文学史的形态也应是多种多样的,应将文学接受外来影响,读者接受等视角体现出来。当代文学史不仅要写出历程,也要写出流变、规律。文学史不必写得很厚,只要写出自己的观点就够了。杨匡汉(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题为《当代文学史:观念与策略》的发言中,认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工作有三:批评,文学史,史论。批评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文学史是通过不同作品的联系与区别对文学发展的演进脉络的叙述;史论是以发生过的重要问题与现象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探讨。三者互为补充却又有其独立性。因此而出现了“教材型文学史”与“研究型文学史”的两种可能性。他认为,“当代”有过程性、复杂性和分离性的特征,需要有对应的策略。“史论”的研究需要理念支撑,如把握“历史还原”、“底限共识”、“和而不同”等等。当代文学研究是充满活力、期待创造的工作,我们扮演的身份和承担的职责,是问题的发现者、意义的澄清者、隐患的批判者、创新的激活者和价值的守望者。於可训(武汉大学)在发言中谈到当代文学史观念的几个问题,认为:文学史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经典化是相对的,是通过对作品的不断阐释和评价完成的,在经典的作品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建立起一种文学秩序,就是文学史。这样,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就必须回到作品本身,回到文学本身,而对于文学作品的选择,就必须坚持效果史的尺度,即该作品是否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和艺术效果,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效果和艺术效果;不能把对作家的自然史的研究尺度,即对作家的生平事迹、创作历程和人格成长等方面的研究史料,如日记、书信等,代替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否则,文学史写作就失去了边界。基于这种理解,所以他主张回到作品上来,回到对作品的阐释和评价上来,还把文学史写作作为一种“文学”史写作,而不是思想史、文化史或作家的心灵史的注脚,正如我们曾经反对把文学史变成政治思想史的注脚一样。鲁原(青岛大学)在题为《文学史的历史阐释》的书面发言中,对20多年来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和出版从结构、观念和方法三个层面进行了历史的观照。他认为,文学史编写的突破在于文学史观念的突破,新的文学史观念提供新的文学认识。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文学理论话语的更新,这为文学史观念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使多种文学史的产生成为可能。新的世纪将是思想观念更加丰富活跃的年代,多元的批评观念必将带来多样的当代文学史。
还有一些发言就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其他问题提出了有学术个性的见解。古远清呼吁要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学的研究,他以余秋雨在文革中的经历为例指出,当代文学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匿名写作给后来的研究带来很多困难:当事人有意隐瞒;特殊材料不能公开;很多回忆录不可靠。上述问题直接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因此治学的人必须要有辩识材料的能力才可能尽量接近事实。曾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一种题材的文学史演变》中,考察了抗美援朝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演进,认为这是一个难以磨灭的文学记忆的宝库,可以得到丰富的历史启示和文学启示。周政保(八一电影制片厂)在《当代文学研究的范畴问题》中,结合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评析并讨论了有关当代文学研究的范畴、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孟繁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传媒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中,对“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作了简要的界定,并结合当代文学史的演变,分析了“传媒”在当代文化史上的功能与性质。
唐韧(广西大学)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了当代文学课教学的改革:一,明确教材在教学中的地位;二,教师示范自己的“筛法”;三,养成学生的“绝对辨音力”;四,考试改革探索。
二、90年代文学考察
在世纪之交召开的这次年会上,对90年代文学的考察自然是中心议题。与会者就许多文坛热门话题展开学术争鸣,表现了历史转型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特点与趋势。
发言者对90年代文学的走向作了整体评说。王干(江苏省作协)在《走出90年代》中,认为90年代确实是一个论争频繁的年代,上半叶围绕“新写实”、围绕“后现代”、围绕《废都》展开了争论,争论本身都跨越文学界,下半叶“人文精神”之争、“马桥”之争、“断裂”之争,还有意犹未尽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火药味很浓,但论争都是双刃剑,既伤了对方,又伤了自己。而90年代文坛是一个口号林立、旗帜飘舞的年代,本人参与策划并鼓吹的就有“新写实”和“新状态”两面“酷旗”,类似的还有“新体验”、“新市民”、“人文关怀小说”、“60年代出生的作家”等等,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90年代文学特定条件下,这种特定条件实际离不开这三个条件:一、文学的个体化和个人化与文学的集团化并存,一大批自由撰稿人的出现,为多种口号和旗子的树立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二、民间策划与政府号召井水不犯河水,由于文学的个性化出现,写作者不必唯政府的马首是瞻,但是他们对政府的号召并不反感。三、文学载体由原来的刊物的一枝独秀到多头进展,出版社的畅销书、报纸副刊上的随笔、网络文学都对文学期刊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文学期刊策划一些“旗帜”出来也是为了招徕作家和读者,这实际上是期刊市场意识的觉醒。整个90年代的文学几乎是80年代的剩余和分裂。90年代文学中出现了许多的困境,也出现了许多的闪亮的碎片,都是主导文学的“异己”和否定,事实上,文学本身也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过剩部分。刘敏(《文学自由谈》)将90年代文学划分为四个时代:90年代初期是诗的时代,作家的创作还保有80年代的浪漫诗情、理想、幻想和精神,作家创作的意识中有集体主义和群体意识。90年代中期是散文时代,现代感性欲望在时代意识中,丧失了聚焦的可能。时代生活变得破碎,生活越变越碎,越变越小,观点多变,特别是报纸副刊泛滥,使作家创作进入前所未有的焦虑时期。90年代中后期是小说时代,时代生活像小说一样变得大起大落,跌宕起伏,作家再也坐不下来写作。下海、经商、炒股,生活中偶然事件的增多,作家有一种炫富心态,向媚俗倾斜。90年代末期是传记时代,作家由群体走向个体,追求个人主义至上,个人品味的写作。吴培显(湖南师大)在题为《文学多元化与文学基本问题》的发言中,谈了三个问题:一,文学观念的多元化与价值差别。二,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与文学的基本问题。三,文学基本问题与文学的终极性价值目标。金汉和金岱(华南师大)都使用“逃亡”一词描述90年代文学走向,但所指意义和评价并不相同。金汉在《逼近:“人本”与“文本”——中国新文学的当下走向》中认为,自80年代末开始,突然文学变了,从逃离“现实”到对文学的自觉,中国作家出现集体大逃亡,仿佛事先约定。疏离现实之后文学的走向:一、走向历史,出现了再现型历史小说,目的是对历史重新叙说。二、创造型历史小说,目的是实现特定历史文化中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三、从传统的社会学主题走向关注生命、文化、人本的现代哲学主题。四、走向文本。金岱在《世纪之交文学:“逃亡”与“精神规则的重建”》中认为:自80年代中期以来,新时期文学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走向:逃亡。最早是先锋文学对形式的关注,后来新写实小说转而写生活的琐屑与无聊,90年代以后的痞子文学、女性的和私人化写作,以及迎合市场与大众需要的通俗文学等等,都是对传统的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文学的一种逃亡。首先我们必须肯定文学的这种逃亡走向对于消解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文学,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型,实现文学的非神圣化、世俗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只是一味地向无立场、无意义的虚无处逃亡,就会威胁到人的生存状态,因为人的生存不能没有精神规则,由此建设精神规则的问题凸显出来。90年代,这种建设的努力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热、宗教热和人文精神热。但这些试图建设的努力尚未能摆脱独断论的传统思维模式。于是,重建精神规则的任务在当前非常重要。郭宝亮(河北师大)和赵栩(汉中教育学院)都在发言中对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提出了批评。沈泽宜(湖州师院)认为,目前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有一种不恰当的非政治化倾向,这是不好的。真正能使人感动并且异常真实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脱离政治。当然现在所说的政治并不是过去那种僵化的阶级斗争模式的政治,而是指处处透露出关注现实、勇于批判的良知。
对于市场经济所造成的90年代文学消费倾向,学者们带着批判的意识作了冷静的分析。陈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无根的苦难:欲望表达与反本质主义叙事》中认为,在进入21世纪之际,有部分中国作家热衷于书写“苦难”主题。苦难主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性,但它打上的特殊的时代烙印却是值得仔细辨析的。由于苦难的展开被性的场所遮蔽,对性的反复叙述成为苦难深化的必由之路,苦难转化为当代性史。苦难的动机让位于对当代消费社会主导趣味的叙述。这反映了当代作家所处的矛盾状况,当文学成为一种弱势文化,文学写作者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时,他们试图批判当代社会现实。但他们的批判性写作的根基何在呢?如何把现时代的理论批判转化为审美批判?一种与当代商业主义审美霸权妥协的审美批判?这必然又是一次自我颠覆。考察当代文学的发展,我们发现怨恨与狂欢这二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和审美态度,总是被当代作家混淆在一起,成为互相制约缠绕、补充和颠倒的反现代性表意策略。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在《90年代文学写作中的消费主义倾向》中认为,90年代,在多种矛盾冲突甚至彼此交锋的观念中,消费主义倾向呈愈烈之势。首先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消费主义是作为文化变迁的符号而出现的,它表征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事实是不容怀疑的。其次,不应该以一种道德主义的简单姿态去面对消费主义,而且应该去分析导致消费主义倾向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消费主义的伦理信念是建立在“导致更大平等和自由”的乐观基础上的,然而这个基础被抽空了社会结构和消费主体差异的内容。作为消费的后果,文学写作面临着文化产品过剩和文化符码的不断复制、自我循环,语言或其他符码也蜕化为消费品。许文郁(北京政法学院)的发言题为《大众文化性质略论》,她说90年代文学向大众文化靠拢,她不认为性和暴力就是大众文化,关键是是否媚俗。大众文化批评具有精神建设性,改变它的物质大于精神的缺点。大众文化批评应成为精神的守望者,在迷幻的大众文化的旷野中树起标志。它还必须具有兼容性。郎伟(宁夏大学)在题为《迷乱的星空》的发言中分析了70年代以后的作家成长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认为“70年代以后”作家的创作缺陷在于:过于超前市场金钱的操作,与传媒的浅薄宣传合谋,创作当中的心灵内容逐渐被消费、享乐主义时尚压迫和消解。他们的创作又一次向当代创作界提出一个问题,市场因素进入创作界是否一定意味着要颠覆传统话语,描写人类生活和文学的神圣感、庄严感?石兴泽(聊城师院)的发言题为《趋俗:当下文学的风景线》,他说:我来自齐鲁之乡,也许过于传统保守,但是文学上粗俗、趋俗倾向泛滥是不争的事实。我最突出的感觉是作爱把人物联系起来。我感到困惑,作爱是个人的事,写作是公共的事,为何要把二者联系起来?我用微弱的声音提醒人们警惕文学的堕落。同是来自齐鲁之乡的张学军(山东大学)则在《90年代文学:生存现实主义》中,用“生存现实主义”概括90年代潮流。他认为:90年代席卷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强制性的改变着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80年代对理想的憧憬和浪漫的激情已悄然消退,现实场景中的世俗性物质需求逐渐凸现。生存现状的改变,使人们对终极价值敬而远之,而在现有目的和眼前利益的得失中沉湎不已。趋利务实的社会心态,迫使人们踏上了应付自我生存的旅程。这种消解理想主义、关注物质实利的世俗化倾向反映在文学上,就形成了一股生存现实主义的潮流,贯穿于90年代的始终。他列举并评析了新写实小说、先锋小说转型后的创作、“现实主义冲击波”、“女性小说”、“晚生代”作家的小说创作在“生存现实主义潮流”中的特征,认为它们的主题都是一种关注现代人当下生存困境的现实主义创作。这种现实主义以琐屑的生活碎片消解了理性深度,以对现实的无奈认同取代了批判精神,以对欲望满足的追逐与主流话语拉开了距离。创作主体不再是一个文化启蒙者,而成为一个生命体验的叙述者。从中只能倾听无可奈何的唉声叹气和本能欲望的喧嚣。张学军也通过评述90年代末的几部长篇小说的出版,预示现实主义在告别了浅层次的欲望写作之后,将在新世纪赢得再度辉煌。
发言者也对90年代的文学批评进行了批评。谢有顺(《南方都市报》在《小说写作的紧张感及其缓解方式》中谈到:前不久在上海作协和华东师大召开的一个会上,评出了百位批评家眼中的“90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及10位作家”,从这份排行榜可以看出,批评家与普遍的读者之间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两套评价标准和选择系统,因为就“影响”二字而言,这份排行榜中没有王朔、贾平凹、王小波和卫慧等人,是不健全的。批评家的审美标准还停留在80年代,集体主义、道德主义、理想主义以及某种语言幻觉的美学趣味还统治着批评界,它与过去的意识形态批评在话语路径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漠视当下的日常生活以及这种生活中的趣味性,漠视个人的、内部的、与宏大主题无关的话语努力。在当下的语境中,文学应该回到具体,回到细节,回到个人的内部的事物中,也就是说,回到对现在的生活和人群的具体感受上。那种对过去失去了记忆,对现在失去了愤怒,对未来失去了想象的作家和批评家是非常可疑的。蒋原伦(北京师大)认为90年代的文学批评显得很弱,成为像创作那样的个人化行为,评价体系出现分裂,对于作品的评价有专业评价和市场评价,没有统一的批评体系,所以没能产生震聋发聩的效应。真正优秀的作家是不会与批评家共谋的。我认为分裂的局面无法改变,我感到困惑。张慧敏(香港中文大学)在发言中将90年代作为我们无以避开的生存环境来理解,论说了在电子时代网络公共空间中文学与批评的互动。针对批评现状,陈剑晖呼吁一种贵族式批评或绅士式批评,即一种批评的气质、风度和精神境界,它包含人文的理想和开阔的文化视野,回到常识,尊重传统,宽容心态,对作家和作品的爱。刘俐俐(南开大学)则在《请批评放作家一马》的发言中呼吁一种感性的、审美的批评,真正以艺术感悟为根据,同情地进入作品,保持文学创作新颖鲜活的个性。
与会者还对90年代诗歌表示关注。吴思敬(首都师大)以《先锋诗坛的裂变与分化》为题,认为目前诗坛上存在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或曰口语写作)的论争虽有争夺话语权的成分,但它确实反映了90年代以来不同的诗人的艺术观念和艺术主张的分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圣化写作与世俗化写作这两种诗歌创作历来有的运动形态,它们互相矛盾,互相作用,互相渗透补充,并非绝对对立。沈泽宜在《90年代诗歌和南北对话》中基本赞同吴思敬的发言,也有不同意之点。他认为“知识分子写作”的提法不妥,“民间写作”者也是知识分子。两派各有特点、优点,也各有弱点。还有不属于这两类的诗人默默耕耘。真正的艺术大师将在中间地带产生,包含了中西诗歌的优秀传统。周亚琴(中国社会科学院)、彭金山(西北师大)、徐伟锋(中国现代文学馆)都对时下诗坛和诗评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此外,还有关于某种特殊题材、特殊地域和其他文体的研究成果在会上发表,如王震亚(首都师大)的《近二十年留学生文学的回顾与前瞻》,章罗生(岳阳师院)的《关于报告文学研究的三个理论问题》,陈敢(广西师院)的《略论散文题材的现代性》。王新民(无锡教育学院)在《文体失衡余论》中呼吁当代文学研究应有所关注当代戏剧文学的研究。古远清的一次发言题为《台湾文学正在蜕化为“台独文学”》,认为这一动向值得我们每一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高度关注和警惕。也有一些发言通过对有代表性作家的个案分析思考作家的文化立场,探讨中国文化的走向,如姚新勇(暨南大学)的张承志研究,吴周文(扬州大学)的残雪研究,刘川谔(湖北大学)的池莉研究,都在文化层面提出了问题。全球化、高科技和网络文学也是热门话题,张荣翼(重庆师院)、乔美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顾骧(中国作家协会)、包明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朱水涌(厦门大学)等,都在发言中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关于网络文学,葛红兵(上海大学)认为,网络文学是新世纪文学的生长点,它具有自由传播、表现方式丰富、创作方式多样、多态参与等特点,是一种继口头文学、纸面文学之后的新的文学形态,尤其是其在网络科技支持下的超文本形式,更是令纸面文学无法比拟的。徐伟锋和宋炳辉不同意葛的观点。徐伟锋反对网络文学的革命性说法,认为葛混淆媒体与媒介的区别。文字是媒介,只是放的地方不同,网上写作还是用文字写作,与纸上写作没有本质区别。宋炳辉在《网络文化对文学的冲击》的发言中,对网络将使文学形成新质的乐观主义的、神话化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互联网的发展普及所带来的文学信息的繁多、及时,文学写作的自由性质,其实有它的两面性,它可能会形成新的霸权和大量的文学垃圾。精英文学毕竟是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人人参与写作只能导致文学的平面化、平庸化。从艺术交往的深度而言,数量、速度反而会导致交往的浮浅化。在阅读方式上,纸面文学的便利是网络阅读不能替代的。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前任会长朱寨(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本次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整个会议既有很好的学术质量,又始终保持着平等的民主的讨论气氛,是一次成功的会议。
收稿日期:2000-11-20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当代文学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当代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当代文学作品论文; 艺术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