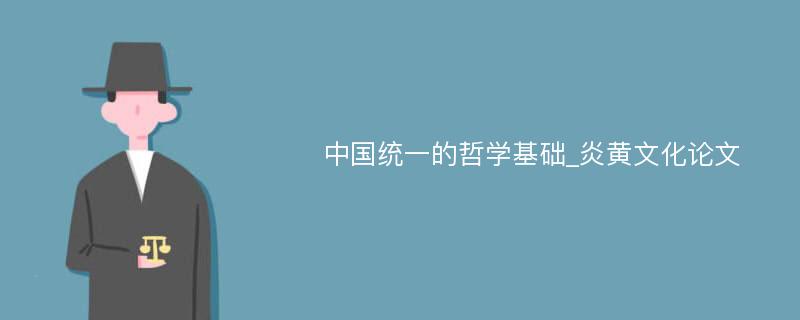
中国统一的哲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哲学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思想与文化息息相关,主导着一个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它不仅形成民族文化中共同的结构及思维模式,且决定其价值理想和实用性。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哲学具有主导的作用。纵观中国哲学,儒、道、墨、法等兼而有之,而作为中心之中心的最高范畴,就是那各家皆欲言而未能尽言的“道”。
“道”,就其本意来说,是“规律”的意思。
万事万物,无不有“道”,社会历史也不例外。“道”在社会历史中的表现就是民意。民意为历史之“道”,民心所向预示着历史的趋势。孙中山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为基,当发端于心理。”此话极为准确地抓住了历史之“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现时代的“民意”,又究竟是怎样的呢?如果明白了民心所向,那么我们对那个历史之“道”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清楚明白了。
要分析民意,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文化传统在民族心理中的沉淀,从而影响了民心之所向;二是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客观情况,对民心的影响。我们先来看前者:文化传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民族心理结构。而在文化传统中,哲学的中坚思想尤其起着核心的作用。在中国,这种核心作用是由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来承担的。“中国”与“四海之内”常常是一个意思:中国乃中央之国,暗示了一种向心情结,“四海之内”则有一个“内敛”的象征。加上中国是个农耕之国。依土地而生,同一块土地,往往“吾祖死于斯,吾父死于斯”,而子子孙孙生活的还是这块土地,这样逐渐发展了一种祖先崇拜、依血缘关系而结成团结一体的独特文化。概括起来说,中国文化以祖先崇拜、血缘关系作基础,呈现出一种向心、内敛、凝聚的特色。这种文化特色同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是融贯一致的,交互影响的,如儒家的“亲亲”思想,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的人道主义思想。中国的这种哲学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已经广泛地渗透到了民族的情感、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当中,构成了民族共同的心理结构。这种民族心理结构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对人们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尤其对价值观和道德情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中,家庭观念、乡土观念、爱国精神等带有向心、内敛色彩的道德情感特别重,中华民族有极强的凝聚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中华民族及其灿烂文化历数千年而不灭,也恰好是这一凝聚力的有力证明。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饱受军阀混战、列强蹂躏的苦难史,中国人民在长期的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没有一个强大的、安定的、团结统一的中国,是难免遭欺凌、受压迫的命运的。历史的纷乱结束之后,人民殷切期盼着一个安定、团结、统一的中国。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提高,也不能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统一的中国。因此,团结统一正是人民的愿望,历史的趋势,谁置人民的意愿于不顾,谁就是逆“道”而行。在历史强大的力量面前,我们只能遵循历史规律,依“道”而行,才会“缘道理以事者无不能成”。
诚然,包括台湾、港、澳在内的中国领土和主权还没有完全统一,但从“道”的立场来看,最终的统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道”包含两个方面:“实”与“势”。“实”是已经实现的事物,“势”是指虽一时未能实现但终究趋向于实现的现实性。中国之统一港、澳、台湾,既是民心所向,又是历史的大趋势,那么这种统一最终要成为事实,乃是必然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无视这种必然的历史趋势,要用分裂取代统一,他们违背“道”,以自己的意志代替民意,背“道”而驰,一意孤行,宣扬“台独”。他们采取的方式就是先造舆论,以名乱实,惑乱民心,因此一些奇怪的论调纷纷出现。荀子有言:“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荀子·正名》)可见,这种以名不符实,以名乱实的论调和混淆是非的行为,早已为我国古代先哲所唾弃。
提及台湾,吾人首应以地缘关系观之,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地质学家认为,在中生代时期,台湾属于大陆东部的前陆盆地;在新生代时,台湾海峡成为陆地,台湾与大陆曾连成一片。其次,从历史上看,早在旧石器时代,台湾与大陆的古人类文化就已有了渊源关系;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台湾番族考》中指出:“台湾的番族是百越的支裔,这种番族之占领台湾,不在宋元之际,而在遥远的上古时代。”这说明台湾土族与大陆古越族有浓厚的血缘关系;宋元时期汉族人民大量移居台湾,历史文献已有明确记载。大陆与台湾的民间贸易往来,始于宋代。宋元时,已派兵驻守台湾。明朝时荷兰人入侵,台湾曾一度易手。但在1662年,明将郑成功又光复台湾。明亡后,中国统一于清,台湾仍作为清朝领土的一个部分。直至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其三,从文化现象上看,“中国”一词,系指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治下的人民,都只属于一个民族:中华民族。这一说法,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不相矛盾。诚然,中国有50多个民族,但到了近代,在近百年的与西方列强相抗争的斗争过程中,这50多个民族结成了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体,各个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这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地理生存空间。这个地理生存空间就是中国的疆域。在这一片国土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结成了共同的民族精神,并孕育了民族独特的文化结构。与世界上的其它文明不同,世界上其它的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或转移,或泯灭,只有中华文明,千百年在这一片相对固定的疆域内繁衍发展。因此,中国之统一就有了特殊的含义,它是国家、民族、国土、文化四者的统一,而在这四者当中,尤以文化的统一为最为深刻的基质:共同的文化所形成的具有强烈的凝聚力的民族精神,为其它统一提供了一种向心力量。
要完成中国统一,合乎“道”的方式有两条:一曰德,一曰力。古代圣哲先贤以为治国平天下,“德”、“力”皆不可废。王充在《论衡·非韩》中有过论述:“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一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强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治国之道中“德”与“力”的关系。引伸至中国统一理论中来说:统一是“道”,“德”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达到统一。“力”则是发义兵以谋统一。“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表明了“德”与“力”的互补关系。因此。可以说主张和平统一中国是“道”,发义兵统一中国也是“道”。当今之势,和平之声日益高涨,人民呼吁和平,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是最为光明的前途。若发义兵,亦迫不得已而为之也。义兵之要,在“义”而不在“兵”。“义”就是“为天下兴利”。也可以说,合乎“义”必合乎“道”。与此相反者是不义,不义就是为了个人私利、为了一己私欲而作的行为。譬如:为了满足某些个人的权欲或小集团的利益,便企图分裂中国,大搞台独的行为,就是“不义”的行为。“义”与“不义”,势同水火,水火必不相容。因此,自古以来,仁人君子都高扬天下之大义,民族之大义,而鄙视不义之行。
孟子有语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因此,企图制造“台独”,逆道而行者,必“寡助之至”,众叛亲离,诚如老子所说:“不知常,妄作,凶。”最后的下场必然是“祸莫大矣”。
自古以来,顺“道”则昌,逆“道”则亡。台湾某位自谓具农业经济博士之能,而“喻于利者”,宜深自省之,以免沦为民族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