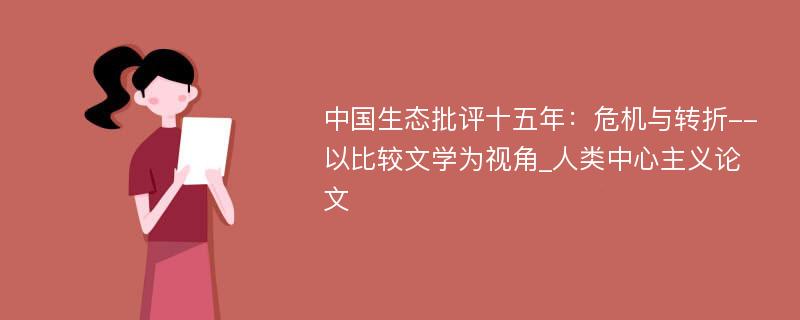
中国生态批评十五年:危机与转机——比较文学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转机论文,中国论文,十五年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批评是当代生态思潮与文学研究的结合,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是对生态危机的综合回应,其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发轫于美国,成熟于90年代中期,后迅速发展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学、文化绿色批评潮流,其内容庞杂丰富,学理探究深沉,学术视野宽广。其兴起的主要原因是日益恶化的现实生态危机的催逼和生态哲学的发展与成熟,中国生态批评的兴起也不例外。在中国(主要指中国内地)生态批评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呈现两种理论形态,即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主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属于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
总体上看,中国生态批评依然处于草创时期,与西方生态批评相比尚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缺乏自觉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即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意识;所运用的理论比较单一;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阐释存在简单化的倾向;对女性压迫与环境退化(或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对性别压迫与环境退化)之间的纠葛还远未深入展开;理论明显滞后,等等。以上不足严重制约了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与深化,徘徊于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困境中,一直处于学术的边缘。如果这种状况不尽快得到改善,中国生态批评将会被淹没在生态文明的“洪流”之中,而失去其独特的学术批判锋芒与文化建构力量,进而不能为生态文明的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由此引发严峻的生态焦虑之后的生态学术生存危机。在此,笔者试图透过比较文学的视野简要地分析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状况,既肯定其成绩,也指出其困境,并展望其未来。
一 荒野中的呐喊:中国生态批评
1.中国生态批评的兴起
在中国文学艺术领域(包括生态文学创作领域),生态意识的觉醒虽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有所发展,但是,作为生态批评的文学理论应该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最早以生态美学为题发表的专文是1994年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与佘正荣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①。15年来我国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概况如下:1999年1月由海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办与海南大学精神生态研究所创办了我国唯一的生态批评刊物《精神生态通讯》,该刊现由苏州大学文学院生态文艺学研究室主办,已发行了60多期,旨在推动生态批评与生态文艺学建设。中国生态批评学者如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张皓以及王晓华等教授都曾在该刊或其他刊物上多次撰文,他们的文章或阐明自己的生态立场,或探讨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扩大了生态批评的影响;从2001年至今,中国生态批评学者先后分别在华中师范大学、西安、苏州大学、贵阳、南宁、青岛、海南、兰州及北京等地市举行了十多次较大规模的生态批评学术研讨会②。2007年党的十七大鲜明地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构想后,使得多年以来一直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流社会边缘的环境问题进入了主流,随之而来的是,多年以来一直处于边缘的绿色文化研究也进入主流文化的视域。这是我们对现有发展模式深刻反思后得出的新认识,环境问题既是现实问题,也是文化问题,因此,解决环境问题的对策理应包括技术策略和文化策略,其中,文化策略是更具持久性、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策略。因此,生态文明的提出为生态批评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创生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迄今为止,国内已出版的代表性生态批评专著有: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2000年),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2006)、《生态批评的空间》(2006)和《走进大林莽:四十位人文学者的生态话语》(2008),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年)和《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蒙培元的《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2004年)以及盖光的《生态文艺与中国文艺思想的现代转换》(2007年),等等。另外,对西方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的引介与研究也构成了中国生态批评的重要内容,已出版的专著有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2003年)和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2006年)。其次,还有一些博士论文题目也选定在生态批评及生态文学研究领域。其余则大多是对西方生态批评简略的介绍,泛泛而谈的多,深入研究的少③。总的来看,以上这些学术活动较为广泛深入地探讨了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文学艺术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等议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生态批评学术的发展,扩大了生态批评在中国学界的影响。
2.中国生态批评面临的主要理论困境
生态危机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导下的西方文化的危机,是现代西方文明引领下的世界性危机,这几乎是绝大多数东西方生态批评学者的共识。因此,可以这样说,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是全球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这既是东西方生态批评产生的现实原因,也是东西方生态批评学者面对的共同的历史语境,但是东西方学者回应生态危机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
西方生态批评学者具有强烈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即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意识,这种“跨”的特性是西方生态批评的显著特征。具体来说,无论在建构生态批评理论还是从事生态批评学术实践,西方生态批评学者都表现出较强的跨学科、跨文化意识,并且认为这种“跨”的特质是基于生态整体主义(或曰生态中心主义)哲学的整体观、生态学相互联系的观点,其跨学科性是与基于机械论、二元论和还原论的传统文艺研究模式之间的重大区别。一方面西方生态批评跨越学科界限对自己的文化中的反自然因素进行痛苦、彻底的反思与清理,涤除自己文化中的反生态因素,同时也从跨学科的角度阐发人与自然的亲缘关系④。另一方面,西方生态批评学者还大胆冲破自己的文化圈,走向曾被“他者化”、边缘化的文化,比如,他们走向东方的道家、儒家、佛家等,旨在吸取别样的生态智慧,改造他们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绿化他们的文化生态,实现文化自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西方生态批评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在人类文化中的种种表现形式,这种批评传统是林恩·怀特(Lynn White)在其影响深远且极富挑战性与煽动性的文章《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一文中所开创的。在该文中怀特将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归咎于浸透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犹太—基督教,尽管如此,他也将解决生态危机的文化使命寄托于基督教,主张通过复兴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St.Francis of Assisi)所开创的具有生态中心主义等思想的基督教少数派传统来绿化基督教,进而绿化西方文化⑤。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生态批评已开始突破基督教文化圈,走跨文明生态对话之路,美国神学学者托马斯·贝利(Thomas Berry)、塔克(Mary Evelyn Tucker)及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等都是倡导跨文明生态对话与协商的主要倡导者。杜维明的《超越启蒙心态》(Beyond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成了跨文明宗教与生态学对话的重要文献。在他看来,解决全球生态问题、建构全球共同体的根本出路在于:一方面要超越启蒙心态,另一方面要深挖三种传统精神文化的生态资源,即:第一种是以希腊哲学、犹太教和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伦理宗教传统;第二种来自非西方的轴心时代的文明,包括印度教、耆那教、南亚和东南亚佛教、东亚儒学和道教以及伊斯兰教;第三种包括一些原初传统:美国土著人的、夏威夷人的、毛利人的,以及大量的部落本土宗教⑥。美国环境哲学家J.B.科里考特(J.Baird.Callicott)主张建构一种全球共享的国际环境伦理与植根本土传统文化的多种环境伦理相互激荡的生态型人类文化,以便能“立足本地,放眼全球”,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全球生态危机⑦。9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1993-1996三年间以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宗教研究团体组织西方生态批评学者、环境学者、宗教界人士及科学家召开了多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就宗教与生态问题广泛地开展文明对话,并陆续出版了多部探讨世界诸宗教或土著文化与生态学关系的专著或文集⑧。
生态批评学者与宗教界人士大多赞成这样的观点,“没有一种宗教传统或哲学视野可以提供一种解决环境危机的理想办法,生态批评强调观点的多元性,这与生态的多元和宇宙观的多元是一致的”⑨。中国学术界对生态危机的反应主要呈现这样一番景象: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是生态型文化,因此,这一次中国生态批评界并没有唯西方生态批评理论马首是瞻,而是积极主动参与生态话语建构,努力建构自己独特的生态批评话语模式、学科理论,希望以平等的姿态与西方学者开展生态对话。在建构生态批评话语理论过程中,他们大多回到古代文化寻求生态资源,尤其是求教于老子、庄子,部分学者也向儒家求教,探寻道家、儒家思想中蕴涵的生态智慧,这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自己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与珍视,这与西方生态批评家不谋而合,因为西方早已将老庄列入世界上最初的伟大生态哲学家⑩。
然而,总体上看,与西方生态批评相比,中国生态批评存在严重的不足,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学者所撰写的生态批评作品大多缺乏自觉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缺乏西方生态批评所具有的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广阔视野,存在一定的简单化倾向。往往是以中释西,“单向阐发”(11)。主要是以中国古代文化生态思想,尤其是以道家思想阐发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阐发以挪威生态哲学家阿伦·奈斯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环境哲学(12);少数学者也着手发掘儒家生态文化资源,蒙培元先生在其著作中较为深入地阐发了儒、道两家的生态智慧(13)。还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探寻生态智慧,或者说绿化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在解决生态问题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对此,曾繁仁教授在《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一著中有所论及,曾永成教授在其《文艺的绿色之思》(2000年)和《回归实践论人类学》(2005年)中对马克思生态精神的当代阐发也给予了较为深入的论述。而西方生态批评跨越现代生态学、生态哲学、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心理学、法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生态问题,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洛夫甚至认为跨学科性是西方生态批评最显著的特征(14)。
此外,即使在探讨儒家和道家生态思想时,中国生态批评学者的阐发明显也不够深入,往往将二者分开来讨论,没有从整体上探讨道家与儒家在解决当今环境危机上的作用。可是西方生态批评学者在探讨道家与儒家的生态学主题时,却能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道家与儒家尽管具体教义相去甚远,但二者都具有相同的有机整体世界观,总体上看,道家是深层生态学取向,而儒家是社会生态学和政治生态学取向;道家可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儒家可更好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实现社会公正。所以,儒家和道家分别给我们提供了动/静平衡的生态理论与实践模式,二者的结合可更有效地解决当今紧迫的生态问题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在当今这种个人主义泛滥、文化趋向多元、社会利益分层加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国际政治角逐日趋惨烈的大背景下,儒家这种整合社会力量、协调社会利益、发动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解决环境问题的功能显得更加重要,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方可重拾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解与和谐(15)。
除了缺乏自觉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以外,中国生态批评对女性、自然、文化及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研究明显不足。中国生态批评的奠基者之一鲁枢元教授在其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生态文艺学》(2000年)一书中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所涉及,对女性、文学艺术、女性压迫及自然退化之间的关系有精湛的分析(16),但很遗憾其篇幅太短,在其以后的作品中鲁教授也很少论及此议题。其他学者更少谈此议题,有关女性、文学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论述只是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之中,远远未给予应有的关注。近年来有少数作者将博士论文题目选定在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范围之内。而在西方,有多位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学者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透过女性的视野深入探讨父权制与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譬如: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学者麦钱特(Carolyn Merchant)撰写了多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专著,甚至著名的男性生态批评学者默菲(Patrick.D.Murphy)也撰写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专著。站在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多视角深入剖析环境退化与性别压迫的关系,甚至有生态批评学者透过环境公正的视域透析社会性别、生理性别与环境行动主义之间的关系,主张拓展生态女性主义范围,建构怪异生态女性主义(Queer Ecofeminism)文学批评(17)。
此外,与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相比,中国生态批评运用的理论不仅很不成熟,而且非常单一,有平面化的倾向。西方生态批评不仅以生态的尺度进行文学、文化批评,而且还积极地借用其他批评理论,或者说,与其他批评理论交叉整合,深化生态批评的内容,拓展生态批评的空间。西方生态批评与后殖民理论结合,对反生态的经典名著进行重审、颠覆,甚至重写,将殖民者对殖民地的占有、对殖民地人民的统治与对大地的征服、掠夺结合起来,这就大大丰富了生态批评的内容,揭示了生态问题的复杂性。西方生态批评学者也充分利用其他文学理论,将其绿化,成为生态批评理论。比如绿化巴赫金的交往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让巴赫金理论成为生态批评理论的一部分等(18)。
最后,中国生态批评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生态资源的阐释与利用存在简单化的倾向。也就是说,在对中国文化进行生态解读,发掘其生态资源时,忽视了清理中国文化中反生态的因素。坦率地讲,催生中国生态批评的直接动因是日益恶化的现实生态危机,二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已经导致环境状况急剧恶化,中国也为此付出了难以扭转的生态代价。如果生态危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在可预见的将来,全国1.5亿人口将会沦为生态难民(19)。西方现代化国家中曾经出现过的生态困境在中国被复制,甚至更严峻,难怪有人说:“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受到污染的环境已经开始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过去20年至25年,中国基本上走的是一条‘污染’繁荣的道路。”(20)中国生态批评学者是否也应该将中国的生态灾难完全归于西方文化?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一下,中国发生的生态危机与中国文化传统是否也有关系?如果有关系,是否也应该对中国文化中的反生态因素进行文化清理?
中国生态批评除了存在以上方法论上的单一及视野狭窄等不足以外,在发展进程上与西方生态批评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那就是其理论明显滞后,依然徘徊在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模式中,没有依据历史和现实的需要不断推动理论的发展,深挖生态危机的历史与现实根源,拓展生态批评的视野和学术空间。
二 理论滞后:深陷荒野的中国生态批评
迄今为止,中国生态批评主要是站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从形而上层面探讨文学、文化与环境的关系,锁定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此处的“环境”主要指“纯自然”或“荒野”,“生态”实际上也大体等于排除了人的存在、被抽象化了的自然存在,而人类参与的环境或城市基本上没有纳入生态批评学者的视野,种族、阶级以及性别等范畴与自然及环境危机的纠葛还远未给予综合的考量,对与现实环境问题紧密相关的生态政治、生态教育等议题的讨论显得更加稀缺。由此可见,中国生态批评依然深陷荒野之中,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然而,西方生态批评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作为有影响的学派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但西方生态批评学者也意识到,从历史与现实层面来看,这一时期的生态批评对生态危机文化根源的诊断也并非完全击中要害,所开出的文化处方也未必十全十美,“药到病除”,而是受到了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初的美国草根环境公正运动的质疑与挑战。随着环境公正运动的深入发展,作为生态批评思想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尤其是其激进的一支深层生态学,受到了以有色族人民、穷人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第三世界以及环境哲学内部的严厉批判,生态批评似乎也因此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美国著名的公民权利领导人、基督教联合教会争取种族公正委员会执行负责人本雅明·夏维斯(Rev.Benjamin Chavis Jr)于1987发表了环境公正运动史上里程碑式的研究报告《在美国有毒废物和种族》,在该报告中他直言不讳地宣称:“种族是全美居民社群与有害物质压力相关的主要因素”,并首次提出了“环境种族主义”(Environmental Racism)这个术语,以凸显环境压迫与种族的关系(21)。1991年,300多名来自美国、加拿大、中美、南美洲以及马绍尔群岛等国家和地区的少数民族领导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首届有色族人民环境保护领导人峰会”,会议旨在协调全球有色人种社群的环境立场,坚决反对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殖民主义,尊重多元文化,确保环境公正,重续人之精神与大地母亲神圣性相互依存的关系,表达了重建人与大地母亲和谐关系的强烈愿望,议定并通过了17条“环境公正原则”(22)。这“17条原则”实际上就是有色族人民的环境公正宣言,指导环境公正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也正式宣布了“环境公正”人士与主流环境主义者不同的环境立场。
从国际层面来看,深层生态学遭到了第三世界学者的严厉的批判,其中最有名的批评者是印度生态学家罗摩占陀罗·古哈(Ramachandra Guha)。在其影响广泛且极富争议性的《美国激进环境主义与荒野保护:来自第三世界的批评》一文中,古哈首先总结了深层生态学的主要特征,并逐一予以批判(23)。在他看来,如果将深层生态学的生态实践用于世界范围,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尤其对不发达国家贫穷的农业人口更是如此。古哈认为,深层生态学所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二分并将其作为理解当前面临的全球环境退化机制是没用的。实际上,生态问题是两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所引起的:一个是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城市精英过度消费的问题;另一个是不断增长的军事化,包括短期的(如不间断的区域战争)和长远的(如军备竞赛和可能的核毁灭)。而这类问题是相当世俗的,与人类中心/生态中心的界限没有明显的关系,因此,无论在哪个分析层次,生态危机的根源都不能还原成为“对待自然所采取的更深层次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
如果这种界限的区分与基本问题无关的话,那么,强调荒野保护的主张用于第三世界肯定是有害的,它实质上是把资源从穷人手里直接转移给富人。在古哈看来,非西方环境运动首先要考虑的是弱势群体——贫穷的无地农民、妇女和部落——的绝对的生存问题,而不是提高生活质量;其次,环境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公平、经济和政治的再分配问题。把专注于荒野保护的深层生态学应用于第三世界带有浓厚的西方帝国主义色彩。
古哈还指责深层生态学肆意曲解东方宗教哲学——印度教、佛教和道教——与文化传统,它透过生态中心主义来阐释这些东方传统文化的做法“相当粗暴地歪曲了历史”,是对东方的“生态他者化”,将东方文化纳入西方思想轨道,其目的是为了论证深层生态学的“普适性”,这种歪曲明显带有浓厚的生态东方主义色彩。
笔者认为,古哈的分析等于是说,人类中心主义成了在近现代以来靠大规模地掠夺、征服自然而发展起来的西方强国推卸、转嫁环境责任的形而上的借口,美丽的托词。专注于荒野保护的深层生态学在理论上充满了赤裸裸的生态帝国主义话语,文化上带有浓烈的东方主义色彩,实践上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生态剥削的基础之上的。从历史与现实视角来看,第一世界既能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享有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也能保持持续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对少数族群、有色人种以及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生态剥削、生态殖民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全球环境的恶化与不公正的经济秩序密切相关。
另外,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也受到社会生态学家和生态女权主义思想家的批判。他们都反对说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生态破坏的深层原因,而认为具体的人类体制、制度及实践——不公正的制度和实践——才更为重要(24)。
由于受到了环境公正运动的猛烈批判,生态批评圈中产生了普遍的学术焦虑。为应对危机,生态批评学者不得不严肃慎重地重新审视自己的学术立场,评估来自多方的批评,总结生态批评学术的得失,进行重大的学术调整。于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部分生态批评学者顺应环境公正的诉求,将环境公正引入生态批评学术活动之中,促使了生态批评的转向。1997年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学者T.V.里德(R.V.Reed)也首次提出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术语(25)。具体来说,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主张站在环境公正的立场上,透过种族的视野研究文学与环境的关系,呼吁生态批评从荒野回家,回到人与自然交汇的中间地带,这样使得生态批评不仅具有崇高的生态理想,而且也立足牢固的现实(26)。有鉴于此,美国生态批评学者布伊尔(Lawrence Buell)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已经历了两次“生态风波”,第一波可大体归为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第二波可称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27)。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不是对其前一阶段批评理论的简单抛弃,而是推陈出新,对它予以修正、深化与拓展,其主要目的是透过环境公正的视野考察文学、文化甚至艺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生态批评不仅要憧憬生态中心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更要关注现实世界的环境公正问题,这不仅拓展了生态批评的空间,开辟了新的学术路径,而且大大地深化、丰富了其内容。这样看来,西方生态批评不仅要深层追问生态危机产生及其日益恶化的历史文化根源,抨击人类中心主义这个毒瘤,还必须深入探寻生态危机产生的更直接的现实根源,那就是现实人类世界广泛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环境剥削与压迫,必须探寻通向生态可持续和社会普遍公正的绿色路径。
与第一阶段相比,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呈现了以下一些新的特点:(1)因为种族是环境不公的核心问题,因此,种族视野显然成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基本观察点;(2)环境公正批评大力拓展了主流环境主义关于“环境”的定义,“环境”是“我们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地方,也是我们祷告的地方”(28)。因此,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人工环境,甚至城市生态也纳入生态批评研究的视野,生态批评也由此“回归”了人类社会;(3)批评手段的多样化,也就是,生态批评学者积极地借用其他批评理论或与它们交叉整合,深化、拓展其学术领域;(4)倡导大力修正第一阶段环境经典的尺度,拓展环境文类的范围,甚至认为任何文本都具有“环境特性”,即便是传统生态经典,也可以透过生态公正的视野重新阐释;(5)强化文学与环境关系的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研究,这是对第一阶段区域主义文本中心的超越;(6)第二阶段特别强调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重视学术研究与生态政治、生态教育以及社会公正等之间的纠葛,以便更好地协调城市与乡村、环境公正与自然保护之间的关系(29)。其中,美国生态批评学者亚当森(Joni Adamson)的《美国印第安文学、环境公正和生态批评》(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Environmental Justice,and Eco-criticism:The Middle Place,2001.)及其与他人共同主编的《环境公正读本:政治、诗学和教育》(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ader:Politics,Poetics and Pedagogy.)(11)被公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作品,后者确立了环境公正批评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基本批评范式,它倡导环境诗学与环境政治及环境教育的结合,在环境危机这样一个复杂、严峻、庞大的问题面前,既需要学理上的探究,更需要现实的考量,否则,我们的一切理论都只是乌托邦式的空谈。
根据以上分析可见,无论从生态批评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上看,还是从生态批评理论的建构与现实生态批评维度的推进上看,与西方生态批评相比,中国生态批评的确存在较大差距。当然,中国生态批评学者也在不断探索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并立足中国的生态现实大胆地进行生态批评实践,鲁枢元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不仅是中国生态批评的开拓者之一,而且还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理论探索者,生态理论的践行者,其学术路径引领中国生态批评走出了象牙塔,从某种意义上说,开辟了新的学术维度——环境公正维度,从而有可能真正缩短中西生态批评之间的差距。
三 一次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实践:2006年海南生态批评会议
鲁枢元先生曾经感叹说:“当中国人在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上意气风发、奋起直追的时候,西方人却已开始反省自己”;当西方的人文世界逐渐恢复“自然”的崇高地位时,中国现代思想界对自然的思考反而冷落下来,等等。(30)这些都说明至少就对生态问题的思考来看,我们中国人无论在思想界还是学术界都慢了许多。这话听起来很刺耳,然而回顾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史,就知道鲁先生所说的都是大实话。生态批评在中国本土的萌发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平等地参与全球生态对话的契机,更是一次建构独特的中国生态批评话语的机会。正如曾繁仁教授认为,“生态美学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美学研究的资源由西方话语中心到东西方平等对话的转变”(31)。
笔者认为,中国的批评界不盲目地追随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一开始就关注自己的位置,认识到自身文化蕴藏着丰富的生态资源,积极参与生态文化的建构,其意义还远不止于患生态“失语症”,更在于拒斥西方学者的“生态东方主义”倾向,让中国学者透过比较文化的视野来阐释自己文化所蕴藏的生态智慧,建构富有中国文化精神的生态批评理论。也就是说,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者们的初衷并不是那么“单纯无私”,除了怀有“白色共产主义”理想以外,还承载了不少民族文化的期许。伴随以上中国学者的生态省悟,他们在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方面做了大胆探索。
2006年12月12日,持续了4天的“‘人类纪与文学艺术’田野考察及学术交流会”圆满结束。从这次参会人员的组成来看,规模并不算“大”,规格也不算“高”,因为参会的五十多人中,“知名”学者不算多,吃的不是生猛海鲜,住的不是星级宾馆,完全没有许多学术会的气派与豪华,采取流动开会的方式,将会场搬到了田野、山川、旷野,坐下来开学术研讨会的时间也不多,更多的是与会者之间的交流。可这种开会方式与生态批评所倡导的简朴、多元、和谐是吻合的,除了会议期间观点的针锋相对,争辩时的唇枪舌剑,它的温馨与和谐不亚于任何一家“超”星级宾馆标准化的微笑,笔者甚至认为这次海南会议是一次真正的生态批评学术之旅,是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一次实践,会议展示的成果标志着中国生态批评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会议理念代表其发展的新动向。这也许是会议策划者鲁枢元先生对中国生态批评状况深思熟虑后的新构想,反映了我们生态批评理念与西方的理念之间的差距的确正在缩小。
在此笔者想谈谈海南会议的生态政治属性。我们都知道文化的生产、流通、消费是个权力运作的复杂过程,只有当作者生产的文本被出版商、杂志社认可,出版发行以后,文本才有可能对受众施加影响,作者的目的才有可能达到,因此在文化的生产消费过程中,出版商、杂志社编辑、传媒人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生态批评的重要目的是试图通过文化变革,改变人们的世界观,从而改变世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如果没有文化领域各阶层的广泛参与、交流与合作,如果他们不了解什么是“生态批评”,仅靠几个呆在书斋里的生态批评学者、专家教授在学术会上猛烈抨击人类中心主义,为自然的权利而呐喊,能行吗?海南会议就是社会各界人士的聚会,其中包括:生态哲学学者、生态批评学者、文艺理论学者;关心生态问题的诗人、作家;关心生态问题的社会贤达;有关出版社、报刊杂志的编辑及传媒界的记者;环保人士以及热爱环保事业的“绿色义工”;还有法籍学者万德化(Artur Wardega)先生。让来自社会各界不同职业的人士聚在一起谈论生态问题,了解社会各个层面所处的生态状况,从而知晓他们的环境需求,凸显生态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与艰巨性,有益于探索最大限度地协调社会公正与环境保护互动共存切实可行的可持续战略。
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会议。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不少兄弟民族至今依然与自然保持着一种神圣的、灵性的、和谐的关系。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是少有的,灯火辉煌的不夜城是罕见的。他们的生产方式是粗放的,住的是简陋的房屋,吃的多是粗茶淡饭,房屋的建筑材料和食物大多取自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真是“靠山吃山”。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少刻意改变自然,他们的自然充满了生命,会说话,能与人交流,真可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乾卦·文言》)。当然,用发展、进步、现代化等流行的字眼来看,他们的文化也许是“落后的”、“原始的”,应该予以“开发”,然而,从生态的视角来看,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绿色的、可持续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隐藏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多种可能性,也是人类的希望之所在。可是就是这些蕴藏丰富的、多姿多彩的生态智慧的文化由于不追求经济的无限发展,成为发展的“障碍”,正遭受现代化的“推土机”的威胁,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不少可被列入“濒危文化”的行列。由此可见,作为生态批评学者,无论是从生态的视野挖掘少数民族文化的生态内涵,还是站在环境公正的立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
在中国,生态不公问题日益严峻,穷人和富人享受自然提供的福祉差距很大,遭受环境侵害的程度也迥异,城市和乡村环境反差同样如此。鸟语花香、淳朴丰饶、悠然自得的田园美景正在消逝,而高消费、高耗能而又缺乏再生能力的人造“生态”城市正在构建。另外,幸存的为数不多的自然风景区被现代“技术座架”(海德格尔语)框定为“旅游商品”,成了商人争相投资开发的产品和当地政府快速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当地政府或管理不善或竭泽而渔,不少“胜地”已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更有甚者,由于旅游开发,使得自然风景区的“土著居民”失去了传统的生存方式,成了无家可归的、生活无着落的游民,风景区成了商人、有钱人的天堂,当地政府的财源,“土著人”的地狱。(32)
这次“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实践”的成果已经汇聚在鲁枢元先生最近主编出版的《走进大林莽:四十位人文学者的生态话语》文集中。与以往学术会议论文集大不一样的是,该文集收录了不少非“职业学者”的文章,让来自不同层面、不同职业的绿色人士来谈论生态问题,打破了专家教授们对生态话语权的垄断,消解了国内学界中长期存在的学术等级制,这恰好与生态多元、生态平等的原则是一致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避免了仅从形而上讨论生态问题的做法,大有与我国前一阶段学院派生态批评(生态美学或文艺学)展开对话并对之进行修正的态势,真正做到了“重启人与自然的诗意对话”。比如,环境主义者颜家安在其《海南的生态美学经济》一文中与“生态美学”展开对话,针对三亚旅游胜地的特殊情况,他指出既要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也要重视当地人之生存权问题,为此,他提出了集生态、美学和经济于一体的“生态美学经济”的新设想。在该文中作者也提出将自然引入城市,关注城市生态,让“生态”成为人们生活的环境,这是环境公正关注的重要议题,很有启发性。欧阳洁和孙绍先在《海南黎族的生态智慧》一文中引入了种族维度,开始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解读少数民族文化,发掘其生态智慧,这是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显著特征。(33)总之,该文集代表了生态多元的声音,体现了中国生态批评开始从“形而上”转向对“形而下”问题的关注,反映了中国学者对生态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依我看,该文集可算是中国版的“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读本”。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看出,海南生态会议标志着中国生态批评已开始从生态中心主义型走向环境公正型,显示出中国生态批评发展的新动向。深信中国生态批评的未来是光明的,因为其既有乌托邦的理想,又立足当下严峻的环境现实。
概而言之,近年来尽管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势头迅猛,成绩喜人,但与西方生态批评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学术实践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其发展也因此受到严重的制约。当然,对比分析绝非是将西方摆到“是”的位置,而把我们摆到“非”的境地,恰好相反,对比是为了凸显我们在生态批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了解我们的不足,避免在多元的全球生态语境中患“生态失语症”。
生态文化多元性要求生态批评必须向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趋势发展。为此,中国生态批评的当务之急是:一方面要警惕西方学者就生态问题可能表现出的“东方主义”思维惯性,以防生态问题蜕变成“白人的生态负担”。另一方面,要立足本土生态文化资源,彰显其独特的生态智慧,同时还必须放弃盲目的抵触情绪,积极主动地借鉴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在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中推动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致力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让其成为推动中西生态对话与交流的重要文化实力,进而为建设永续和谐的全球生态文化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②③⑩(18)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354、335、353-354、368、366-372、173-192页。
④胡志红:《生态批评与跨学科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58-62页。
⑤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eds.The Ecocriticism Reade: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p.3-14.
⑥⑦⑨(15)Mary Evelyn Tucker and John A.Grim.eds.Worldviews and Ecology:Religion,Philosophy,and the Environment.New York:Orbis Books,1994.pp.19-28,30-38,11,150-160.
⑧Mary Evelyn Tucker and John Berthrong.Confucianism and Ecology:the Interrelation of Heaven,Earth,and Huma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xviii-xxxiii.
(11)参见曹顺庆《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343页。
(12)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144页。
(13)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4)Glen A.Love.Practical Eco-criticism:Literature,Biology and Environment.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3.p.9.
(16)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5页。
(17)Rachel Stein,ed.New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al Justice:Gender,Sexuality,and Activism.New Brunswick:Rutgers UP,2004.
(19)陈中:《中国1.5亿人将沦为生态难民》,《文摘周报》2005年3月1日。
(20)《松花江污染敲响中国环保警钟》,《参考消息》2005年11月25日第1版。
(21)Edwardo Lao Rhodes.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America:A New Paradig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3,P.14.
(22)Mark Dowie.Losing Ground: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at the Clo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Mass:the MIT Press,1995.pp.284-285.
(23)Ramachandra Guha,"Radical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and Wilderness Preservation:A Third World Critique",In Contemporary Moral Problem.7[th].ed.edited by James E.White.Wadsworth/Thomas Learning,2003,pp.553-559.
(24)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林官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266页。
(25)(26)(28)Joni Adamson,Mei Mei Evans and Rachel Stein,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ader:Politics,Poetics and Pedagogy.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2002,pp.160,4-5,20.
(27)(29)Lawrence Buell.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MA:BlackWell ublishing,2005.pp.138,1-133.
(30)鲁枢元:《自然与人文》“绪论”,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31)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32)陈统奎:《天堂岛怎样成为幸福岛?》,《文摘周报》2009年2月13日第1版。
(33)鲁枢元:《走进大林莽:四十位人文学者的生态话语》,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标签:人类中心主义论文; 生态危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生态文化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比较文学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美国宗教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