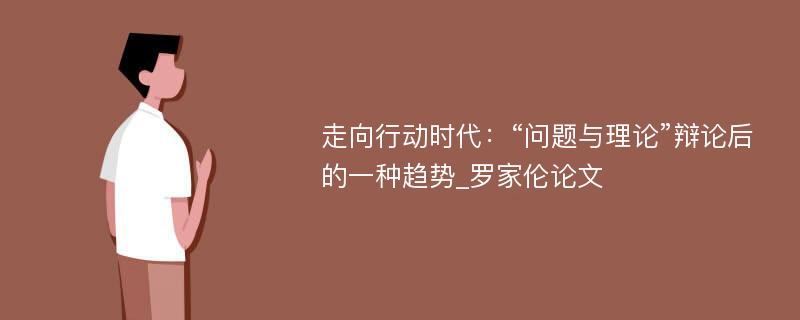
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倾向论文,走向论文,主义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曾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进行再考察,颇感觉那次论争虽然为 时不长,却触及到一些时代关注的焦点,反映出“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异常丰富而活 跃的动态。以前较早的论述常把这次论争视为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等)与马克 思主义的一次重要斗争,从20世纪80年代起,相关论述逐渐显得更为缓和,持论也更加 平正,当然迄今也还有基本坚持原来看法者。(注:关于这一论争的既存研究和研究现 状,参见罗志田:《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待刊),下面两 三段的看法也多本该文,具体论证将不重复。)不过,这一重要争论也还有不少需要进 一步考察的必要。
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几年后的反应看,在最初的争论后,双方都曾向对方表示善意 ,而马克思主义者一方似更明显;胡适的主张不但当时有人赞同,后仍得到呼应,其中 也包括一些共产党人。所以,对争论是否体现了两种意识形态的交锋这一点,至少不宜 过分强调。有些后来认为是冲突的观念,对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而言,未必就那样对立, 反可能有相通之处。
当时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阵线混淆、各种流派混杂难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 意味着某种共性。不仅知识界,包括在国会中占优的安福俱乐部在内的朝野各方都以为 中国“社会”的革命或改良不可避免。这样的朝野相似性,特别是那时掌权或接近掌权 的一方颇有仿效民间言说以“攀附”清流的倾向,致使胡适等以“新舆论界”自居的一 边希望有所“区分”,以确立自身的特性。对胡适等人而言,想要区别于“政客”是那 一争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若祛除我们的后见之明,回归时人当下的认知,类似那些试图兼顾“问题”和“主义 ”的观念和行为,过去常被研究者视为“调和”,对当事人而言可能并无此意,因为他 们未必看到(或至少并不看重)两种取向之间的对立。仔细观察,可见胡适和李大钊关于 “问题和主义”的言论在一段时间里共同成为从罗家伦、傅斯年到毛泽东等青年一辈的 思想资源,则这一争论可能根本不像后来认知的那样意味着新文化人的“分裂”,或即 使“分裂”也不到既存研究所强调的程度。
在关于中国社会改造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这一问题上,当时倾向于整体或根本解 决中国问题的人相当普遍,其中不少人甚至不那么激进;而在主张根本解决的人中间, 也有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整体或局部解决 两种取向未必势不两立,反可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毛泽东、王光祈和张东荪等都曾一 度提出从改造局部走向整体“根本解决”的主张,而包括恽代英在内的一些人甚至将暴 力革命视为走向根本改造的第一步。(注:说详罗志田:《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 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待刊。)
通过中国改造与世界改造(或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联,整体或局部解决的类似思 路也被一些人运用于思考和处理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后者是“问题与主义 ”之争引发的又一关键问题。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共产党人至少到20年代中期仍在呼应 胡适的主张。(注:参见罗志田:《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 之三》,待刊。)这样看来,时人思想观念那兼容的一面的确不应忽视。
前述朝野间体现出的某些“一致”既导致趋新一方试图“区分”的努力,可能也是相 当一些读书人态度偏于温和的潜在因素。另一方面,当时也确实有不少人看到根本改造 和点滴改革之间的对立(例如胡适)。且不可否认的是,从1920年后期开始,在随后的一 两年间,陈独秀、毛泽东以及新民学会和少年中国学会中许多原本态度偏向温和的读书 人突然转向激进,以前那种试图兼顾根本改造和渐进改良的取向逐渐显得较难自圆其说 ,反倒是两者间的对立日渐明朗。(注:金观涛先生关于《新青年》杂志对“革命”一 词的使用频度进行的统计表明,自1920年后期起的几年间可见“革命”一词使用频度的 急剧攀升,可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一时期读书人突然转向激进的趋势。参见金观涛:《观 念起源的猜想与证明——兼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2003年12月),125-140页,特别是136页的图表。)
这是为什么?那时中国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特别是哪些因素导致数量不少的读书人如 此失望?或许“五四”后几年那段时间见证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非常值 得进一步认真考察研讨。苏俄的介入中国政治和中共成立后表述出对中国历史和现状明 显不同的认识,应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个相对次要的可能因素则是像工读互助团、新村 和菜园一类自食其力的“互助”尝试的失败,这些偏于理想甚至空想的做法和想法曾经 一度风靡,但在实际社会中居然“行不通”,似乎导致读书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 识。(注:参见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919-1923,伟大的开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226-245页。)
另一个未必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却与“问题与主义”之争直接相关的因素,或许是“空 谈”成风导致“实行”的凸显。(注:侧重“行动”当然是五四学生运动后中国社会一 个相对普遍的倾向,罗家伦当时就反复说,“这次‘五四’‘六三’的结果,只是把全 国的人弄‘动’了”(罗家伦致张东荪,1919年9月30日,《时事新报》,1919年10月4 日,3张4版);“‘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 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2卷4号,1920年5月)。但与“空谈”对 的“实行”得到凸显,却与“问题与主义”之争有更多的关联。)郑伯奇在讨论少年中 国学会的分歧时,就指出关键“不在主义而在实现主义之手段”。(注:《少年中国学 会问题·郑伯奇意见》,《少年中国》3卷2期(1921年9月)。)安徽青年韦丛芜等人的感 觉或更有代表性,他们发现,全国普遍的现象是“高谈阔论现在大有人在,实地做事却 未必有人”。然而,“智识阶级唱得再热闹,不把这种少数人的信念,脚踏实地去宣传 到普通一般人的心里,使他变成一般人的普通信念,于社会改造上没有多大动力”。所 以他要“像教徒们的传教一样”去实地宣传,以促成平民思想的转变,实现全社会“真 正的革新”。(注:韦丛芜、李寄野致胡适,1922年,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 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30册,649-650页。)
这其间还有一个“汉宋之争”的传统延续,即学问是否当有益于世,读书人是否该出 而“澄清天下”。胡适在1923年曾打算以整理国故为“他一身的大业”,张彭春就感觉 当时“中国有才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作‘活事’的机会,所以要他们才力放在不被现 时人生能迁移的古学古理上”。所谓“活事”,是指“经营现时人与人发生关系的事业 ,如政治、学校事业、民族生活等”。(注:张彭春:《日程草案》(即日记),1923年2 月20日。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微缩胶卷。) 张是一个倾向文言而不喜白话的留学生,他也把整理国故视为疏离于时代需要的“死事 ”,可知当年不少新型读书人还是继承了传统士人那种对天下的关怀。
其实胡适此前也很强调面向社会的实行,他在1919年为《孙文学说》写的书评中说, “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是 不尚空谈的’”。其实,那些“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的政客,自己没有计 划,混一天算一天,“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真正的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 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孙中山就是一个实行家,其“一生所受 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正因“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 空谈”,致使其“《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胡适强调,“现在的大危险,在于有 理想的实行家太少了;现在的更大危险,在于认胡混为实行,认计划为无用”。(注: 胡适:《评<孙文学说>》,《每周评论》31号(1919年7月20日),《胡适文集》(以下径 引书名),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册,28-30页。)
王光祈也注意到“现在一切富于惰性的政客,终日奔忙”于“解决零碎的问题”。这 样一种“头痛医头、足痛医足的办法”,虽“美其名曰研究问题”,然其流弊正在于“ 终日埋头在局部具体的事实里头,而不能高瞻远瞩为根本的计划”;甚至使人类“没有 一个共同最高的理想,限于一种极狭隘极无味的事实上面”。故他也主张“建立一个根 本计划”,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注:若愚(王光祈):《总解决与零碎解决》, 《晨报》1919年9月30日。)
罗家伦则针对学生自身指出,如果没有“一定的目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摸一 下,西碰一下,没有计划,只谋应付,仿佛一个船在大海,失了指南针一样,其结果必 致全舟尽覆、根本破产而后已”!故今后“不能不有一个具体的大计划”,就像造大房 子一样,“必须由工程师先把全体的图样打好,然后一步一步的造去,才能成一个预定 的房子”;若“东拚一块,西凑一块,和斗‘七巧板’一样”,则房子很难造成功。( 注: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2卷4号 ,第855-856页。)
若对比一下三人的看法,他们皆倾向于有“理想”或目标明确的“计划”,胡适和王 光祈都看到当时政客之所为正与之相反,而王光祈和罗家伦则同样试图区分“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和有计划的“一步一步的”行动。但在王光祈眼里,政客之忙于“解决零 碎的问题”恰与胡适提倡的“研究问题”有些关联。这样,由胡适来辨析有理想有计划 的“实行”并非“空谈”(时孙中山以空谈著称,有“孙大炮”之名),多少也体现出他 自身倾向的某种调适。
以胡适当年的影响,他所提倡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很快风靡,但社会风尚的无形力 量却使其实际的走向有所转移。张闻天观察到,当时“青年普遍的心理”是“自己没有 对于各种学问做根本的研究,人家要研究问题,他也加入研究”,但实际并未研究什么 问题,不过“拿他的直觉写出来”。而青年之所以有点直觉就要写,是因为“心目中另 抱出风头的目的”。(注:张闻天致张东荪,《时事新报》1919年12月12日发表,收入 《张闻天早期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2页。)换言之,那时就“研 究问题”发表言论已经可以“出风头”,故不少青年愿意追随。
在这样的世风下,张申府发现,随着“问题”本身的流行,主张研究问题一方自身也 渐出现“空谈”的风气。“一个人出来说”不能瞎谈主义不研究问题,“于是许多人也 渐渐的口说问题,笔写问题。可是问题从何而来?问题发生于事实。有了事实的不相容 ,有了事实的搁浅,于是成立问题。解决问题只是求去掉事实的不相容,使其归于和谐 ,进行遂顺。所以解决问题必须明白事实,必须按切事实”。然而那时“讨论问题”者 却“不察事实,不管事实之有无,捕风捉影,设立问题”。这样设立出的问题,其解决 自不能“与事实有涉”。且如此“清谈问题”,与空谈主义也是一丘之貉。(注:赤(张 申府):《随感录·研究问题》,《新青年》9卷6号(1922年7月),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 印本,第84-85页。)
张氏因而从哲学角度提出,“把杜威、罗素、柏格森三家之说合在一炉”,其实也就 是“切实试行”这四个字。故“吾们不论主张什么东西,都要实地试试看”。做“一件 事,不能总说要预备。预备与实行不能划为截然的两件事”。他认为:“不论什么好思 想,都是生活迫出来的。不与实际接近,如何能说实话?不与社会奋斗,能把社会怎着? ”且“一个主张,一个方法,不行,怎能知其可行不可行”?只有“越切实的试行,才 越觉着有活趣”。故“不知则已,知则必行!不思则已,思则必行!不主张则已,主张则 必行!”(注:赤(张申府):《随感录·切实试行!》,《新青年》9卷6号(1922年7月) ,第79-81页。)
胡适重实行的观念也引起张申府的注意,他曾问陈独秀:“适之现在上海么?‘干!干! 干!’现在怎么干法?”(注:张崧年致陈独秀,《新青年》9卷6号,第89页。)这里说的 是胡适在1921年5月的一首诗,其中反复说:“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到那年10月,胡适在另一首题为《双十节的鬼歌》的诗中,更提出纪念双 十节的一种方法即“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 好政府”。这些诗在朋友中反映不一,老辈的范静生认为其方法太简单,而曾怂恿胡适 革命的朱谦之见了则大喜。(注: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 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254页。)一向被视为温和的胡适也曾表现出这样激进的一 面,当年世风的走向可见一斑。
问题在于,一旦“干!干!干!”成为主导的倾向,思想和知识都可能退居二线,甚至连 “知识”本身的含义都可能转变。这样一种双重的转变可能意味着读书人在整个社会中 地位的下降,而那些欲追赶时代的读书人或许不得不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约束,甚至自 我否定。
章太炎在清末提出“目下言论渐已成熟,以后是实行的时代”(注:章炳麟:《<民报> 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1906年12月),《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 77年版,上册,第328页。)之后不久,便自然产生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 约二十年后,太炎的弟子鲁迅在北伐时即观察到“知识阶级不可免避的运命”,即“革 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注:鲁迅: 《关于知识阶级》(1927年10月25日),《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8),人民 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若读书人不能自觉意识到自己处于思想让位于实行 的时代,其他阶层可能会起而提醒,沈雁冰又十多年后说,当小市民中的知识分子不断 述说着各种“理论”之时,“旁观者却先不耐烦起来,会大声喝道:‘这是行动的时代 ,不是空论的时代!’”(注:茅盾:《又一种看法》(1938年7月),《茅盾全集》,第1 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页。)
“行动的时代”的确是一句有力的棒喝,而“行动”与“空论”的疏离甚至对立则可 能使一些读书人在“行动”中发现自己原有的知识“不合用、不够用”。《学生杂志》 的一篇文章说,“五四运动以前的学生,以为‘知是现在的事,行是将来的事’,只知 而不行。因为不行,所以他们的知,合不合用,够不够用,他们自己绝对没有觉得”。 到五四运动学生出来参与种种事业,“一实行,可不对了。因为自己的知识不合用、不 够用而发生的种种困难,他们都觉到了。于是,学生界的知识饥荒起来了,求知心非常 急切了”。(注:文叔:《五四运动史》,《学生杂志》10卷5号(1923年5月),13页(文 页)。)
实际上,这一新感知的“知识饥荒”更多可能是因为“知识”本身的内容改变了。中 共党员张国焘在1922年说,“我们很知道‘知识便是权力’,我们并不看轻知识(马克 思派还特别看重知识)”;不过,若“要得到知识,便要是得到一种与民众有利的知识 。要得到与民众有利的知识,只有在民众中间去活动才能得到这部分最重要的知识,在 书本子上是得不到什么的”。而讲教育也“不能专讲学校教育,组织群众,率领群众运 动,向群众宣传,便是一种最重要的群众教育”。(注: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 地位及其责任》,《向导》12期(1922年12月6日),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汇刊本,第9 9页。)
既然知识和教育都在民众那里,学校正在传播的“知识”便显得“无用”,至少“不 够用”,结果导致杨荫杭所说的“教育破产”,即“学生自视极尊,谓可以不必学;且 谓处此时世,亦无暇言学。于是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而学生流为政客”,学校也“改 为政社”。(注:《申报》,1923年2月3日,收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 出版社,1993年版,第711页。)在“读书不忘救国”的年代,这一现象或不少见。沈昌 在“五四”几年后回忆说:“我自参加‘五四运动’,一天一天的浮嚣起来,昧然以天 下为己任,而把自己的切实基本学识弃去了。”(注:沈昌:《我十年来的学生生活》 ,《学生杂志》10卷1号(1923年1月),第5页(文页)。)
也并非青年学生如此,在当年那种日益激进的语境中,如果“知识”的含义真像张国 焘所界定的那样产生于“在民众中间去活动”,而不是“在书本子上”或“在研究室里 ”,投身于整理国故的胡适等于是选择了一条违背世风甚至疏离于“知识”的路径,这 或者是他自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几部古书的整理,于人生有何益处?于国家的治乱安 危有何裨补”?更不能不转而提倡青年学生先在实验室里做出成绩,再来“一拳打倒顾 亭林”。(注: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 联书店,2003年版,第342-349页。)
顺着这一思路延续下去,胡适在1930年对知识青年说:“谈主义的书报真不在少数了! 结果呢,还只是和汤尔和先生说的,‘不过纸张倒霉,书坊店走运’!于老百姓的实际 苦痛有什么救济?于老百姓的实际问题有什么裨补?”有些“我们国内的少年,见了麦子 说是韭菜,却要高谈‘改良农村、提高农民生活’,真是痴人说梦”!胡适再次建议: “少谈主义,多研究一点有用的科学。带了科学知识作工具,然后回到田间去,睁开眼 睛看看民众的真痛苦、真问题。然后放出你的本事来,帮他们减除痛苦,解决问题。” (注:胡适:《汤尔和译<到田间去>的序》,《胡适文集》,第8册,第400-403页。)胡 适所提倡的当然与政治革命的实践有较大距离,但在注重“实行”方面则是一致的。
当然,重实行的风气兴起之时,也有一些人转向学理方面的努力。罗家伦在“五四” 之后几个月即发现“现在全国青年——也有壮年在内——都觉得起了知识的饥荒”;他 也感觉到自身的责任,即“我们要赶快接济他们知识的粮草(intellectul food)才是” 。这一“知识饥荒”的产生仍与群众运动相关,但罗家伦并不以为当往群众那里去补充 知识。相反,他注意到全国各地提供知识粮草的“我们”同样“感受知识的空虚,不够 应用”。故提出“现在是大家分工的时候”了,即一部分人去从事社会工作,而另一部 分人则在学术方面努力:“要知道现在中国没有一样学问,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位置的 ;无基本文化的民族,在将来的世界上不能存在的!”因此,“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 今刻不容缓之图”。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都不要 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局愈乱,愈要求学问”!(注:罗家伦致张东荪 ,1919年9月30日,《时事新报》,1919年10月4日,3张4版;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 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1920年5月1日),《新潮》2卷4号(1920年5月) ,第852页,第860-861页。)
罗家伦给他自己的“分工”便是从事落实在学术之上的“文化运动”。他的北大同学 傅斯年亦然,傅氏在1920年春颇感近来“考虑的心思周密,施行的强度减少”,这使他 “心志上觉得很懒怠”,想要“寻个救济的法子”;但经过反思,对自己求学的经历有 一个“恍然大悟”:他在北大预科时处于所谓“‘国故时代’,念书只为爱他”。后来 “旧信仰心根本坠落”,所学开始注意切合今世;“因为切今世,于是渐在用上着想” 。最近则顿悟“这个求合实际、求有成功的心思”使他“很难和学问生深切的交情;不 能‘神游’。所以读书总觉不透彻”。于是“下决心”不考虑学问的“收获”,准备“ 至少以三年的功夫去研究”作为“心理的、社会的科学之根源”的“心理学”。(注: 傅斯年:《留英纪行》(1920年5月),《晨报》1920年8月6、7日,均7版。并参见Wang Fan-shen,Fu Ssu-nien: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53-54.)
这样一种有意识的“分工”恐怕比“问题与主义”争论时不同的观点立场更反映出新 文化人的“分化”,即相当一部分读书人,尤其是北大“新潮社”中人,认识到应致力 于从学问上提高个人以及整个中国人的层次,外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位置”,内则能 够给全国青年和部分壮年提供“知识的粮草”。但这更多是一种主动的“分工”,而不 是过去许多人认知的那样一种被动的“分裂”。也就是说,“五四”后一两年间,在一 些态度温和的读书人突然转向激进并更加注重“实行”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人选择了更 偏于学理也更加“迂远”的路径,即出国留学。(注:关于“新潮社”诸人的出国深造 ,参见Vera Schwarcz,The Chinese Enlight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PP.133-133.)但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变动是那样急剧,以致许多人在外国游学数年之 后,会看到一个已经相当不同的祖国。(注:还有一些人后来因其他原因走到更偏学理 的取向,如张东荪就在北伐时感到报纸不能自由说话而退出报界转入学界(参见张东荪 :《思想与社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4页)。而胡适也长期徘徊在“思想” 和“行动”之间,他一生有好几次“干政治”的冲动,与“问题与主义”之争最近的一 次是在1926年访问苏俄之时(参见罗志田:《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近代 史研究》2003年4期)。)
傅斯年在“五四”当年曾说:“现在的时代,恰和光绪末年的时代有几分近似;彼时 是政治革命的萌芽期,现在是思想革命的萌芽期。”(注: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 的改革》,《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918页。)在一 定程度上,20世纪20年代的“整体与局部”之争也是清末最后十余年关于“立宪或革命 ”争论(注:参见亓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66年 。按,将清季之争以“立宪或革命”来概括可能较多反映了后之研究者的认识,至少在 争议的早期,也曾有人用“革政”或“革命”来界定类似的取向,参见桑兵:《庚子勤 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 局,1989年版(该书第6章即名以《“革政”和革命》,然似未多申论)。)的再现,两次 都出现了学理到实行的转折,两次都以“实行”方面的结果实际否定了学理方面的努力 ,或为此争论下了“结论”。所谓争论,本意味着思想的探索。既然已有“结论”,则 一些人的探索或许仍在继续,相互的辩论却实际被终止了。
其实,正如少年中国学会巴黎同人在“五四”当年所说,当时的中国“处处皆是问题 ,方方皆宜着手”。针对那样的现状,既有主张围绕具体问题步步着手者,也有试图以 一种主义为宗旨以避免东扶西倒之病者。巴黎同人即倾向于后者,他们认为,中国处此 “近代空气之中,实有万不能不改善之势。而邦人积重难反”,故非“为根本的改造不 可”。对这样的大事业,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只有“集成团体,内而互助,外而协力, 庶几改造之业,能底于成”。若“从事于其间者,无一定之宗旨,自难收连贯主从之功 ,而有东扶西倒之病。故严格论之,即无主义不能作事”。(注:《巴黎同人致京沪同 志》(1919年9月27日),《少年中国》1卷7期(1920年1月),第57-62页。)
这类无形中想要“定于一尊”的主张实有悖于新文化运动时的基本精神,却因有利于 “实行”的需要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基本上,“五四”后较受欢迎的西方“主义” 似乎都带有明显的排他性,而试图定于一尊的主观努力更强化了各类“主义”的排他性 ,使得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原具包容性的团体纷纷解体,逐渐走向尊奉单一“主 义”的组织。
胡适当时曾有所警觉,他认为“单有一致的团体主张,未必就是好的。安福俱乐部何 尝没有一贯的团体主张呢?所以我们所希望的团体主张必须是仔细研究的结果”。(注: 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胡适文集》,第11册,第12-13页。)但这基 本是以派别划线(即安福系先已“政治不正确”),并未排除在“仔细研究”基础上的单 一团体主张;且胡适对“有计划的政治”始终青睐,这恐怕是后来他对国民党的新型组 织形式大唱赞歌的“内在思想理路”。(注:说详罗志田:《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 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
或可以说,尊奉单一“主义”的中共之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恰顺应了许多知识青年的 突然走向激进,而苏俄此时介入中国政治,提供了新型动员整合的组织模式和行动模式 ,无疑起了相当大的助推作用。但包括思想资源在内的外力介入既可能凸显某些既存的 问题,也可能导致新问题的产生——中共党人后来长期应对的“教条主义”就是这些新 问题中的一个。由此更可见“问题与主义”之争确实触及和揭示了不少后来得到持续关 注的问题。
标签:罗家伦论文; 胡适论文; 胡适文集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新青年论文; 时事新报论文; 新潮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