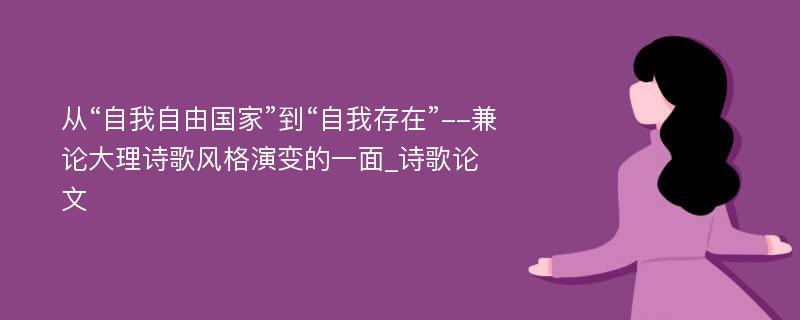
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兼探大历诗风演进的一个侧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风论文,之境论文,大历论文,有我论文,侧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11-0164-13
“大历”,在中国诗歌史上属于长时期受人冷落的时段,从盛唐到大历,一般被认作唐诗之中衰。尽管明人高棅在按“四唐”、“九品”的框架给唐诗序目时,将大历诗人群定位在“接武”一栏,表示这个阶段的诗歌创作仍能多少接续盛唐之余韵①,但若其作用仅在于延续旧观,且在保守中还丢失了若干重要的精神(如所谓“气骨顿衰”之类②),则其意义就极为有限了,也许这正是评论家们多忽略大历诗坛的原因。其实大历诗风的意义主要不在守旧,而在于有所更新,即为唐诗艺术的新变探索路径。大历的新变可能成就不高,而开创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自应肯定。可喜的是,当今学者中已有人发现这个问题,提出古典诗歌传统中的情景交融艺术至大历方得以实现的观点,很值得我们关注③。当然,将情景交融的发端断自大历,不免有割裂传统的危险(尤其是将盛唐诗排除于情景交融之外,似叫人难以接受),亦容易导致对“情景交融”内涵的狭隘化理解,故未能得到学界普遍认可。而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大历诗风的新变,把它理解为诗歌艺术构建从侧重“无我之境”朝偏向“有我之境”的置换转移,或许更切合实情。这一新变不仅显示出大历诗歌自身的存在价值,更重要的,是为一部分晚唐诗乃至两宋曲子词的艺术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而于中唐至北宋之交,当诗歌意象艺术的主流由主情的“唐音”向主意的“宋调”转型过渡之际,更在主情诗潮内部开启了由“无我”向“有我”演变的另一条通道。这将是我们探讨本课题的用意所在。
一、“有我”与“无我”之概念辨析
为了确切地把握古典诗歌艺术从“无我之境”向“有我之境”转换的实质,我们还得自概念的辨析入手。
众所周知,“有我”与“无我”这对范畴是由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一书中首加标举的,提出后,引起广泛重视,议论甚多,分歧亦大,迄今未有定论。一部分人士对这一划分持根本否定态度,认为诗歌作品乃诗人心灵之结晶,其中必含有其自我情意体验在,不可能“无我”,因亦不存在两种境界的区别。此说虽振振有词,实出于对王氏原说的误解,可不予置辩。另一些人则以为“有我”与“无我”只是相对而言,实即诗人情意姿态体现于作品中的隐显强弱程度的差异,这个说法接近常识,得到不少人首肯,但终觉不够明晰,难能揭示其中精义。此外,更有用“移情”、“自失”、“虚静”、“解脱”等各种理论来评析两种境界的,品类实繁,不遑列举。
且来看王氏自身的解说。在其《人间词话》的手稿里,有这样一段集中的表述: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此即主观诗与客观诗之所由分也。④这段话的意思并不特别费解。“有我”与“无我”作为诗歌境界的两种基本类型,出自诗人艺术表现方法的不同:侧重于客观写实者,诗中情思与物象均显得合乎自然,故常处在相互调协与融和的状态中;而若倾向于主观写意,则诗人的情意必然要凌驾于物象之上,遂使物象皆染有“我”之情意色彩。论者以“客观诗”与“主观诗”来作概括,正为了表明二者分野之所由来。
不过这段表述于《词话》正式发表时有了变化。在引用诗词作例句后,王氏对两种境界给以这样的诠解: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⑤改动主要是两点:一是在两种境界提出后,分别加上“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的字样,对其内涵给予新的界定;再一是删却了后文“此即主观诗与客观诗之所由分也”的归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删除后一句话,据我的推测,怕是为避免混淆。我们看《人间词话》第十七则有这样的说法:“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⑥且不考虑这段话语所表达的见解是否合适,仅就其中“客观之诗人”与“主观之诗人”的提法而言,即很容易和手稿里的“主观诗”与“客观诗”混为一谈,而实际上,这里的“客观”与“主观”专指作者表现的对象属外在人生世相抑或仅限于一己情思(故举《水浒传》、《红楼梦》与“李煜词”作比较),跟手稿用客观写实与主观写意的表现作风来说明两种境界的生成是不相干的,删去当可免除误会。至于添加上“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的新界定,则又体现了论者对问题的深一步思考。我们知道,一种艺术的表现方法往往并不停留于单纯表现技巧的层面,却常要同艺术家对世界的审美观照及其整个艺术思维方式紧相关联,甚至会涉及其人生态度与人生理念。王氏对两种境界的新界定,正是为了将“有我”与“无我”的区别界限,从表现领域转移到观照世界和感受人生的层面上来(可能也是他放弃“主观诗”与“客观诗”提法的一个理由),这自然大有利于提升两种境界之说所含带的美学与哲学思想内蕴,却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按“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之说,源出于北宋理学家邵雍。邵雍从张扬“性理”出发,在人如何看待世界的问题上,提出了“反观”的主张。他以为:“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⑦那么,怎样才算“以物观物”呢?照他的说法:“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⑧也就是说,要凭借自身内在的“性理”去烛照万物,方始有可能透过纷扰的现象世界来体认万物的本真,即所谓“天理流行”的境界,这在只顾满足个人情欲追求的人来说,是万万做不到的。所以他又宣称:“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⑨,“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⑩。由以上叙说看来,邵雍是将“以物观物”与“以我观物”作为两种根本对立的思维方式乃至人生态度提出来的,前者显扬“性理”,后者任从“情欲”,而提倡“反观”式的“以物观物”以反对任情徇私的“以我观物”,实即理学家们一力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其间尚有佛老思想的影响,兹不细论),这跟王国维用“有我”与“无我”来标示诗歌艺术的两种境界,显然风马牛不相及。不过邵雍的提法中亦含有某种启示,便是主体的人在面对客观事象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姿态:一是从个人情意出发去应接对象,于是必然在物我关系上打下主体的鲜明印记,这叫做“以我观物”;再一种则是要努力泯灭物我之间的界限,使主体以“物化”(与物同化)的状态去应对事物,也就是所谓的“以物观物”。“以物观物”并非指依照事物的原貌去观看事物,乃意谓以“物化”的“我”来对待世界,“我”既然与世界万物同属一体,万物与“我”的本真亦便在相互观照之中同时得到开显。这正是王氏接过邵雍的话头所要阐发的一点意思,也正是这点意思使其两种境界说又跟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思想挂上了钩。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对青年时期的王国维有过重大影响,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叔本华倡“意志哲学”,以“意志”(意欲)为世界的本体,也代表人的本性。但他又认为,恰是意欲的难以满足,造成人生诸般烦恼的根源,而审美之所以能帮助人们祛除烦恼,即在于它让人沉浸于不起欲求的艺术观照之中,从而暂时解脱了意欲的束缚(11)。这个说法跟邵雍之倡导“以物观物”以反对“以我观物”,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王氏早年深深服膺叔本华的这套理论,他把处身于日常功利关系中的主体称作“欲之我”,又以从事审美观照的主体为“纯粹无欲之我”(12),审美与艺术活动的功能乃是将“欲之我”转换为“纯粹无欲之我”,虽无益于当世之用,却有其大用,能使人从生活实用之欲的领域提升到精神层面的追求上来,以遂其知识与感情心理的慰藉和满足(13)。看来王氏的这一见解也构成了他划分诗歌艺术中两种境界的原初出发点。所谓“有我”或“以我观物”之“我”,都是指有具体情意指向的“我”,以既定的情意指向去同外物打交道,不免使“物皆著我之色彩”。而“无我”或“以物观物”中“物化”了的“我”,既然排除了个人的主观情欲,则大体相当于“纯粹无欲之我”,在其不起思虑的宁静观照之下,“物”与“我”之间的自然和谐得以充分展现,“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两种境界的区分,根底上出自两个不同的“自我”。不同类型的主体与对象世界建立起不同的心物关系,有着不同的审美感受方式与艺术表现方法,而不同诗歌境界的生成也就不可避免。像这样从叔本华思想影响的角度来把握王氏两种境界说的,论者甚多,似已成为学界之主流。
但我以为问题还须作深一层的发掘。两种境界之说如果仅仅是叔本华“意志哲学”的翻版和引用,它又如何能适应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实际?且当叔本华的哲学理念已被世人扬弃之后,此说何以能继续流行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和研讨呢?这就关联到王国维对叔本华思想的改造了。
改造的第一步,是调整两个“自我”之间以及两个“自我”与两种境界之间的关系,这需要从哲学家的立场转向艺术家的立场。叔本华作为哲学家,是以否定意欲、寻求解脱充当指引人生之路的。哲学家可以这样做,艺术家则不能,因为艺术活动必须有情意体验为根底,而情意体验又必须来自人的生活实践;脱离人间烟火,一味寻求解脱,便不会有诗歌艺术产生。这就是为什么王氏不能像叔本华那样将“欲之我”与“纯粹无欲之我”截然对立起来,拿后者来否定前者,却要在艺术殿堂里给两者各自安排位置,让它们分领“有我”与“无我”两种境界的缘由。不过这样一来,难免会产生新的矛盾,即:审美与艺术活动的功能本是要让人在凝神观照之际实现精神上的超越,如果始终执定有具体情意指向的“我”,不能与实际生活中的功利性欲求相剥离,那只能算个人情意的宣泄,谈不上美的创造。王国维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他在《人间词话》第六十则里讲到:“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4)这一由“入”而“出”的过程,将艺术家如何使其生活实感提升为艺术境界的奥秘揭示出来了,其中对既有感受(“入乎其内”所得)的重加审美观照(“出乎其外”之“观”),自是决定性的一环。这在他的两种境界说里也有反映,如《词话》第四则所云:“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15)这里以两种境界类比西方美学中的“优美”与“宏壮”,且不去评说,值得注意的是,他将两种境界的生成皆归之于“静”(即审美静观),区别仅在于:“无我”时的主体本身处在不设情意指向的宁静自然状态,他的情意体验是与审美观照同时发动的,审美的“我”与情意的“我”遂合二为一了;而“有我”中的“我”则是预设了情意指向且或正起着某种情意活动的主体,他要将内心积淀的情意体验按审美的方式宣示出来,需要借助相应的物象作表达,这一将情意转化为物象(审美意象)的过程,也就是他通过审美观照将实际生活体验转变为审美体验的过程,所谓“由动之静”正标示着这一转变。由此可见,王氏对审美观照的理解,并不全同于叔本华那样一味寻求意欲的解脱,却更重视审美对情意体验的升华作用,于此达成两个“自我”及其与两种境界之间关系的协调,成为两种境界说得以成立的关键。
不单如此,更有进一步的改造,乃是将叔本华的“意志”本体转换为中国哲学的自然境界,这可说是由外来文化基点移向了本土文化基点。叔本华“意志哲学”的产生本有其西方精神文化的土壤,而其鼓吹意欲的解脱,又染有印度思想的色彩,这跟中国固有理念之持守“天人合一”,以“物我同化”为自然境界的趣尚很不一样。在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虽也含带接受佛教“空观”教义的一面,毕竟不占主流,主流的倾向仍是复归自然。因此,王国维在叔本华哲学思想的直接影响之下,固然要以“纯粹无欲之我”为追求目标(其《红楼梦评论》即以此为主调),但当他转向古典诗歌艺术研究之时,则不能不从实际出发修改他的理念。在发表稍早于《人间词话》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他郑重指出:“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象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16)约略同时写成的《文学小言》里,也有“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之说(17)。《人间词话》广泛涉及诗词艺术,以“境界”为立论之本,而其界定则为“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18)。慎莫将王氏之“真景物”、“真感情”误认作诗词中常见的写景抒情,他强调:“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由此盛赞李后主之词“以血书”、“性情愈真”,有别于宋徽宗被虏囚北之作“不过自道身世之戚”,而“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19),还特别推许清初词人纳兰性德能“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20)。据此而言,他所讲的“情真”、“景真”,实乃是一种自然本真的境界,不仅要以“肫挚之感情”、“高尚伟大之人格”为基底,且要以自然之心态来接纳万象、传递情愫,使物我之间的天然和谐得以呈现。这只要看《词话》中举以为“无我之境”例证的诗句,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与其说显示了“意志”的寂灭与解脱,毋宁说展现的是人与世界的自然本真关系,是人对世界的自然本真的感受。即使像“有我之境”的例句,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固然折射出主观情意活动的强烈色调,而经过词人的审美观照,情意化入物象,物象承载情意,亦自有一种心物交融的和谐感。王国维之所以要采用邵雍的“以物观物”说来界定其“境界”的内涵,可能正是因为“物化”的主体中隐含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主旨,较之于叔本华的“纯粹无欲之我”更接近于古典诗歌艺术的精神取向。
绕了这么一个圈子,现在可以对王氏的两种境界说下一按断了。在我看来,两种境界说是王国维借用新的审美理念对既有艺术传统进行阐释的结晶。据他所言,古典诗歌艺术中存在着“有我”与“无我”两种不同的境界,根子来自不同的人生理念与审美态度。以自然本真之“我”去应对世界、感受生活,其审美观照的方式通常也是自然兴发式的,所摄取到的物象多贴近事物原貌,引发的情意体验易于与物象相亲附,让人感觉“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就叫“无我之境”。而若从有特定情意指向的“我”出发,由刻意宣示情意的需要去寻找和构建其情感对应物,必然会将既有的情意心理转移到对象身上,使“物皆著我之色彩”,成为“我”的情意载体,则谓之“有我之境”。“有我之境”亦须经审美观照而使实生活中的体验升华为审美体验,但其心物交融的关系终不如“无我之境”来得自然本真,所以王国维要说:“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21)不过我们今天来评说这两种境界,着眼点并不在于等次高下,乃是要借取王氏的这一概括,来考察古典诗歌艺术演化的历史轨迹,下面就来进入这个话题。
二、古典诗歌艺术从“无我”向“有我”之推移
情思与物象的关系,或曰情景关系,实乃古典诗歌艺术中的一个核心命题(22),而其追求实现的目标便是情景交融(23)。情景交融的理论依据即中国文化思想传统中的“天人合一”理念,对这一理念支配下所形成的物我同化关系的体认,恰构成诗歌艺术情景交融的源头。情景交融也是诗歌艺术两种境界的共同基础,无论是“无我之境”的“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抑或是“有我之境”的“物皆著我之色彩”,实际上均体现着情景在某种程度上的融通交会,只不过一属于自然天成的交会,一属于人工作意下的交会罢了。正因为如此,古代诗人在追求情思与物象结合的过程中,“有我”与“无我”经常是同时并举的,总的说来,从侧重“无我”朝偏向“有我”的转变,是一个基本的趋势,而在这一推移演进之中经历交替反复与互为消长的格局,亦自难免。让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这一基本的进程。
大体上说,我国早期诗歌创作在情思与物象的结合关系上,呈现出天然状态占据优势和人工意识的开始萌芽。其间也有各个阶段发展状况的不同。
从流传至今的篇目看来,原始的歌谣常系直述情事之作,物象多为配合情事而设,其独立的艺术功能尚不显著,这自是跟“诗言志”的古训相切合的。原始歌谣里的物象亦常带有巫术和宗教的痕迹,如《礼记·郊特牲》所录《蜡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宅。”这实是一篇祷词,是先民意图通过其巫术或宗教的行为来直接影响外在自然界,使自然物听从人的意志安排。这一呼告显示着情思对物象的驱动作用,但在先民的观念中却是原始“天人合一”状态下的一种自然行为,或可称之为超自然信仰下物我同化关系的自然展现,并不类同于后人诗歌作品里用主观情意来渲染和改造物象。
这类巫术与宗教的痕迹在《诗经》里还多少有所保留,不过《诗经》诸篇用作比兴的物象,已经同诗人所要表达的情事建立起某种联想心理的关联(习俗的或偶发的),物象多用于引发情思或比况、衬托情事,表明古典诗歌艺术中物我同构的原则已初步形成,“天人合一”的理念正式落实到艺术构思的层面上来。《诗经》的物我同构虽出自诗人的联想和想象,但大都不离乎人们朴素的感受与表现,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以及“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之类,写情状物均出于自然天成,物态人情亦皆符合其实际象貌,在诗歌境界上自应归属于“无我”。当然,其物象的铺陈尚多处于简略、零散而构不成景观的局面,情思与物象之间联系也时或流于表面化,除《秦风·蒹葭》之类极少数篇章能达到神韵、氛围俱足的境地外,恐怕都还够不上后世诗歌情景交融的标准,只能算是物我同构,而物我同构恰是情景交融的出发点。
早期诗歌物我关系中天然状态占优势的情形,到《楚辞》里开始发生变化。《楚辞》作为作家文学的发端,诗人的主观情意有了明显加强。屈原自述其创作的动因乃“发愤以抒情”(24),其遭谗被逐、忧国思君的愤怨郁结于心,需要有所宣示,待到用诗歌形式进行抒述时,又常借助瑰丽的想象和各种虚拟的物象来作表达,这就使他的艺术创造初步转向于“有我”式的人工营运。在屈赋中,物象的铺陈描绘进一步展开了,物象对情思的烘托、暗示作用有所加强,尤其是以虚拟与象征性的物象来寄托情思的艺术方法(所谓“美人香草”式的寓意作风)得到广泛应用,不仅大大提升了原有的比兴手法,更为后世诗人的托物寄情开启了重要的法门,在“因物兴感”的传统艺术思维方式之外,提供了“缘情写物”、“假象见意”的创作新路子。不过屈赋虽凭借虚拟、想象的活动来构造物象,其采用的手法仍然偏于写实,并不企图以主观情意来改变物态。至宋玉《九辩》,诗人的情意始凸显于物象之上。《九辩》的主旨据作者自述,应是“贫士失职而志不平”,但诗篇开首“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一句领起,即将诗人自己的情意涂染到眼下的秋景之上,成为“移情入景”的最早范例。以下抒述情怀时又不断插入物象描绘,如“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以及“叶菸邑而无色兮,枝烦挐而交横”、“梢櫹槮之可哀兮,形销铄而瘀伤”,放眼四周,动植物界尽是一片哀怨衰飒的气象,正应合了“物皆著我之色彩”的界说,故可认定宋玉正是古典诗歌“有我之境”的奠基人,《九辩》即属开山之作。
先秦之后,以汉魏六朝为代表的中古诗歌史进一步推进了情景交融的诗歌艺术,也具体展示了“有我”与“无我”两种境界之间的交替消长。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大致可划为两汉、魏晋和南北朝三个段落。
两汉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多向探索和广泛实践的阶段。其作者队伍包括王公贵族、官僚士大夫、失意文人乃至民间歌手,其诗歌性能有庙堂祭祀、贵主宴乐、家族垂训、文士述怀、政治讽刺以及风俗纪事,而其采用的体式亦不限于原有的四言与骚体,更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等各种创新试验。不过它给予后世以深远影响的,除乐府民歌和一部分文人仿作中建立起来的诗歌叙事的范例外,仍以文人五言古诗所代表的抒情篇章为主,而其抒情艺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古诗的一大特点,是情事的相对集中和情景的比较展开。这些作品所要表达的无非游子思妇离别、失意的情怀,事实背景不多,情思与物象的表现便有了更宽阔的空间。其中抒情自是主干,而物象的描绘上亦明显突破了以往比兴手法的简略形态,时或有成片成块的景观出现;一些物象还同诗中情事合为一体,构成完整的场景,在此前诗歌作品里并不显见。可以说,古典诗歌艺术中“景”的观念的成立,是以汉人诗作为初始表征的。古诗的另一重大创获,便是情景交融的初步实现。《诗经》与《楚辞》里的物象虽也表达情思,但经常用的是比兴手法,用为比兴的物象自身往往游离于情事之外,单凭联想心理的缀合作用与情事发生关联,情景的交会不免隔了一层。而古诗中的景物有不少处于现场,本身就构成情事活动的场景或背景,景与情之间有着天然的契合关系,其相互照应当更为密切。故我们认为,古典诗歌艺术中的情景交融并不需要等待唐人方始出现,作为诗歌抒情的艺术传统,早在汉魏之际即已崭露头角,只是汉魏古诗多直抒胸臆之作,景物的铺陈烘托尚欠发达,其成熟则有待后来。
两汉诗歌抒情的路线在魏晋得到了延伸,且因魏晋文人较为自觉地从事景物的观照与表现,诗中写景的成分不断增强,情景交融亦逐步提升。不过魏晋诗歌创作的主导观念仍是抒情。诗人们一方面大力推扬“感物兴情”,要在自然兴发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另一方面又很重视主体情意的宣示,时或表露出“缘情写物”的新动向。自后一方面需求来看,他们着重吸取了楚骚的经验并加以拓展。我们知道,楚骚在屈原手里,是以比兴寄托为特色的。屈原的比兴寄托并不同于《诗经》里朴素的比兴手法,它不仅仅是借物象以引发情思或比况人事的一种修辞手段,而是寓有深意的一整套象征体系,所谓以物喻人、以古喻今、以仙喻凡、以男女喻君臣四大象喻系列的建立(25),正体现出屈赋以“兴寄”达意的艺术传统。魏晋诗人中没有完全追步屈原风格的,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积极采纳了屈赋的象喻艺术,不光如阮籍《咏怀》八十二首中多见到这类带比喻、象征色彩的物象范型,即使在左思《咏史》、郭璞《游仙》以及曹植《美女》《白马》诸篇里,亦常打上比兴寄托的印记,成为诗人借他人他事以自陈怀抱的一种形式,不免带有从主观情意出发以寻求其情感对应物的痕迹。与此同时,宋玉式的移情入景的艺术手段也得到了广泛应用,突出的表现便是各种情感性的字眼大量加诸自然物象。《古诗十九首》里已有“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这样的用法,到魏晋诗人手里就更加普遍。像曹操《苦寒行》中的“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苦雨诗》的“苦雨滋玄冬,引日弥且长”,曹丕《善哉行》(其二)的“离鸟夕宿,在彼中洲,延颈鼓翼,悲鸣相求”,以及曹植《赠白马王彪》诗第四章所云“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总之是将“悲”、“苦”、“孤”、“寒”、“惨栗”、“忧伤”之类专属于人的感情或感觉心理转移到物象身上,以形成一种主观化了的情景交融。这些都表明“有我”的意识在中古诗歌史上一度抬头,尽管它还没有从根底上摆脱自然兴发式创作思维方式的制约。
但是,这一朝向“有我之境”发展的趋势,在晋宋之交开始受到阻遏。南朝山水、咏物、宫体诸诗潮的兴起,将诗歌创作的主流由“缘情”引向了“体物”。景物在诗中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一方面改变了诗歌传统重情思、轻物象的风气,大有助于状物绘形及其构图经营技巧的精工锻造,另一方面也造成诗人情意体验的稀释与淡化,致使物象的繁密布置掩抑了情思的空虚贫弱。所谓“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26),大体指明了这阶段诗歌艺术之得失。而在这一“尚形似”风气的笼罩之下,不单加诸物象身上的情感化词语纷纷消解,原先景物描写中已然发展起来的烘托、暗示、象征、移情诸手法,也一律转化为形容铺排,方刚抬头的“有我”意识重新返归于“无我”,不过不是那种在自然兴发基础上达致情景交融的“无我”,却是“性情渐隐,声色大开”(27)的“景以代情”式的“无我”。这是情景交融的诗歌艺术在演进过程中的一段曲折,而又是借助景物地位提升以通向更高水平的情景交融的必由路径。
现在可以进入盛唐。盛唐作为古典诗歌抒情艺术的高峰,似已成为共识,而高峰的一个显要标志便在于情景交融境界的成熟。能做到这一点,跟盛唐诗人对汉魏古诗善于抒情和六朝诗歌偏长写景的经验给予全面地综合、吸取分不开,也是六朝后期开始,经初盛唐一百多年来诗人们精心探索的结果,在他们共同努力之下,单纯的“体物为妙”转变为唐人的“化景物为情思”(28),于是有了“情景交融”。盛唐诗坛对于构建情景交融的诗歌境界,是有观念上的自觉的。选家殷璠在其为当代诗人传影的诗歌选本《河岳英灵集》里,以“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来批评此前的不良诗风,又以“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充当其衡诗的赞语(29),这“兴象”自是指的饱含情兴之“象”或具足情味之“象”,不管怎样理解,都意味着情思与物象的内在统一。另一位诗家王昌龄在其《诗格》一书中更具体论及诗歌作品中的情景关系,其云:“凡诗,物色兼意兴为好。若有物色,无意兴,虽巧亦无处用之。”又云:“诗贵销题目中意尽。然看所见景物与意惬者当相兼道。若一向言意,诗中不妙及无味。景语若多,与意相兼不紧,虽理通亦无味。”(30)这里所说的“物色”与“意”相兼且相惬的关系,亦便是诗中情景的两相结合了。《诗格》还就诗歌作品里“情语”和“景语”(他称之为“意句”和“景句”)的搭配方式作了细致探讨,而其着眼点仍在于二者的融通会合,可见盛唐人对于情景交融的诗歌艺术确有足够的体认,断言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尚未能实现情景交融,不免过于匆遽。
盛唐诗歌的情景交融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举凡诗歌艺术上卓有成效,确能将诗人的情意体验转化为诗歌意象,以达致情思与物象相互照应、相互渗透者,皆谓之“交融”,并不以某种格局为限。在具体形态上,情景的结合方式自是多样的。可以“寓情于景”,将诗人情意含藏于景物画面之中不予表露,如王维《辋川集》里的写景小诗《鹿砦》、《辛夷坞》、《鸟鸣涧》等,仅从画面传送出自然界宁静、自在乃至活跃的生命气息,而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即寓于其中。也有“系景于情”,乃在抒情中缀合物象或借助物象以表达情思,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杜甫《江汉》),本是抒述思乡之情或不甘迟暮的心态,却借白露、明月、落日、秋风等物象衬托出来,备见情味。更有情景并出、自相交会者,如杜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江汉》),一句诗里情景俱到,分不清究竟是在写景还是抒情。当然,较常见的仍属情景分列对举,即上下联或一联中的上下句分别用以写情和写景,可以先情后景,也可以先景后情。这类格局有人不以之为“情景交融”,其实交融与否要视其情物之间有无密切的内在联系而定,不在于形式上的分列或交会。清人王夫之曾举孟浩然与杜甫题咏洞庭湖的诗作加以比较,认为孟诗《临洞庭》之颔联“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虽写出湖水的壮观,但颈联转向“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的干谒之请,不免“钩锁合题,却自全无干涉”,而杜甫《登岳阳楼》诗在“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之下,接以“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身世浮沉之感,则“凭轩远望”之情“居然出现”(31)。由这个例子当亦可加深我们对情景交融的领会。
然则,盛唐诗歌的情景交融究竟属于“有我”还是“无我”的性质呢?这个问题也不可一概而论。整个地看,盛唐人写诗重视自然兴发,且其兴发之情意和感受到的物象通常直接地表现出来,致使其诗作多呈现自然浑成的风貌,比较接近“无我之境”。这不单指王孟诗派的田园山水诗篇,李、杜、高、岑诸人亦皆有此类作品。像王夫之举到的李白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他以之为“景中情”的范例(32),实际上也是“景生情”,由“月下捣衣”引发对远征亲人的思念,联想天成,情味宛然,确系“无我之境”的代表作。这样的诗歌李白写得甚多,其“清新”、“飘逸”风格的形成当与此相关,而盛唐各家的诗风尽管因各人个性及所写题材各别显出差异,追求自然清新、气势浑全则是共同的趋势,亦意味着其艺术境界之多倾向“无我”。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主体精神的高扬也是盛唐文人的一大特点,由此触发主客之间的激烈冲突,主观情意凌驾于客观世界之上,亦时会产生“快心露骨”的诗歌作风,从而在对象身上录下“我”的影迹。李白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像他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箇长”(《秋浦歌》其十五)、“黄河之水天上来”(《将进酒》)、“燕山雪花大如席”(《北风行》)以及《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诸篇,多以夸张变形的物象甚或虚拟想象之景观来表达个人情意,就容易导入“有我之境”。不过盛唐人的“有我”,多属屈赋式的“假象见意”,少有宋玉式的“移情入景”,且其借物象张扬自己的情意,基本仍未脱离自然真率地表达个人实际感受的出发点,跟后世诗人一味沉潜于主观心灵世界,借物象以曲写“我”之心态的做法仍有差距,只能算在“无我”前提下孕育着的“有我”苗子,或由“无我”朝向“有我”转变的先兆而已。
三、大历诗人对“有我之境”的刻意营造与功过得失
以上简略地回顾了古典诗歌艺术中的情景关系自先秦以至唐中叶的演变历程,不仅看到其情景交融艺术的日趋成熟,且涉及情景交融的方式从“无我”向“有我”的推移。比较而言,以自然兴发为基础的物我同构更能体现诗歌艺术的本然状态,故而在前期诗歌创作中拥有绝对优势,而随着诗人自觉意识的抬头,主观情意体验能动作用的增强,“自我”在诗中的显影也就日益明朗化。但直至盛唐时期,自然天成的“无我之境”仍占据诗歌作品的主导地位,“以物观物”的艺术思维方式亦常支配着诗人们的创作活动,这一基本形势要到大历诗坛方始发生变化。大历诗风演进的一个重要侧面,便是将“因物兴感”、“触景生情”式的创作路线转变为“缘情写物”和“移情入景”,从而正式开启了通向“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的门户(33)。这是诗歌意象艺术发展中的一大变局,其深远的影响要到后世诗词里才得以充分显现。
为什么大历诗坛在艺术作风上会出现这样一种变化呢?根底上自离不开社会的驱动。我们知道,以“大历”为标识的代、德之交,在唐王朝历史上是一个历经动乱之后的苟安时期。一方面,席卷全国的“安史大变乱”暂告平息;而另一方面,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财政拮据、外患频仍等一系列社会矛盾亟待解决。这样的时代所需要的人才是干吏而非文士,故才子式的大历诗人们在此环境下常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已失去盛唐文人固有的理想抱负,既无信心也无能力来面对实际社会问题。正是这种对外在世界的疏离感,使他们形成清冷萧条的心理感受,并将这类感受收敛、沉潜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细加品味,更进以寻求合适的释放时机,这应是从主观情意出发的“缘情写物”创作路线产生的深层背景。换一个角度看,自“因物兴感”转向“缘情写物”,又显示出艺术思维活动方式的重要变革。“因物兴感”的特点是感受与表现合一,诗人在接受外物触动时,自然地感受物象并兴发情意,若将这种感受直接表现出来,其所含物象与情意必然是自相契合的,这就构成了“无我之境”。而“缘情写物”的要害恰在于感受与表现分离,感受所得并未即时付诸表现,乃是聚敛并积淀于人的内心世界,形成主体自身某种特定的情意指向(或称“情意结”),待到需要宣示时,另寻觅其情感对应物作载体,于是不可避免地走向“物皆著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34)。大历作者未能像盛唐诗人那样敞开胸怀去迎接外在世界的直接感发,却更多地沉潜于内心体验,另外,大历诗坛上盛行的酬赠、唱和、送别、寄远等作风,亦加深了诗人们按预设情意去布置景物的习气,这些均促成了“缘情写物”思维机制的发达,而使“有我之境”得以广泛生成。
然则,大历诗人又当如何来营造其诗歌艺术的“有我之境”呢?那便是在“缘情写物”的总方略下,抓住选景、写景与构景几个环节作精心安排。
首先,在选景上,其所持原则为“因情设景”,即根据既定的情意指向来挑选和设置景物,以传达其内心的情愫。处身苟安状态下的大历诗人们,其生活接触面是不广的,多从个体生存的现实环境里去寻找情感对应物,故诗歌题材不离乎宦游、迁谪、送别、酬赠及日常生活、自然风景等,表现相对单一。即便少量涉及战乱情事的诗篇,亦往往限于行役途中的见闻(如刘长卿《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戴叔伦《过申州》等),反映仍属浅表。且其所选景物更常带有特定情感色调,便于与他们自身清冷萧疏的意趣相适应。如刘长卿《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一诗云:“荒村带返照,落叶乱纷纷。古路无行客,寒山独见君。野桥经雨断,涧水向田分。不为怜同病,何人到白云?”题意为喜客见访,而选用的物象如“荒村”、“返照”、“落叶”、“古路”、“寒山”、“野桥”等,全属一派寒荒景观,恰足以写照其心绪。他那首著名的绝句《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也是以“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的孤清景象来营造氛围,由此引向“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旅人投宿场景,方显得格外真切动人。这都是善于从周边生活环境来提取适用物象的好例子。但有时候,周边的物象不足以传情,诗人们便也常借用传统的情景模式作填补,如以“竹”、“鹤”表清高,以“雁”、“燕”表归思,以“浮云”、“夕阳”寓送别,以“明月”、“芳草”寄相思,等等。这类表述仍然符合大历诗歌“因情设景”的创作原则,而用得过多,亦会给诗歌作品带来模式化的缺陷。
其次,进入写景,这是大历诗人用力最勤的方面,主要的原则便是“移情入景”。按“移情入景”的作风兆自宋玉,到汉魏古诗里得到广泛应用,算是开了“以我观物”之先声。不过当时作者采用的移情手法还很粗略,多停留于将“悲”、“愁”、“哀”、“怨”之类情感性词语加诸物象身上,缺少精细、深入的刻画,其情景交融便有相当的缺陷。大历诗人对“移情入景”有了更充分的体认。戎昱《秋月》一诗里写得很明白,其云:“江干入夜杵声秋,百尺疏桐挂斗牛。思苦自看明月苦,人愁不是月华愁。”他已经懂得,景物的情感色彩完全是人的主观情意渲染上去的,人将自己的情感心理转移给了物象,情景之间便达成了一体融合。这里明显表现出大历诗人对于“移情入景”的自觉性,尤其是“思苦自看明月苦”一句,典型地概括了“以我观物”的思维方式,可说是“有我之境”原理的初步阐释。而有了这样的认识,大历诗人们对于移情手法的运用自要灵活、充实得多,我们姑且将其分解为几种不同的类型来谈。
第一种形态可称之为物象的知觉化,指物象经过诗人感知官能的作用给予呈现,其间刻有人的感知心理的印记。例句如钱起诗“牛羊上山小,烟火隔林疏”(《题玉山村叟屋壁》)、“鹊惊随叶散,萤远入烟流”(《裴迪南门秋夜对月》),其写牛羊因上山远行而形体变小,烟火由林木遮隔而气焰消疏,以及鹊随叶而惊飞,萤入烟而流动,均非事物原貌,乃是人对物象的一种感知;将这一感知状态录写下来,在反映物象的同时连带反映出人的心理感受,遂使物象的呈现带有某种情趣。这类写法在大历诗人中用得很普遍也很有特色,像郎士元诗“蝉声静空馆,雨色隔秋原”(《送钱拾遗归兼寄刘校书》)、司空曙诗“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云阳馆与韩绅宿别》),皆属于此类名句。有时候,诗人在表达自己的感知时,还暗示出特定的情感意向,更耐人把玩。钱起诗“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赠阙下裴舍人》),表面写听觉和视觉,实际在颂美和企羡裴舍人之应召入宫、承受恩遇,论者所谓“‘花外尽’者,不闻于外也;‘雨中深’者,独蒙其泽也”(35),恰切地点明了诗句含蓄之意,这也是物象知觉化的一种功能。
与物象知觉化稍有差别,第二种形态可谓为物象的情绪化,指诗人将自己的情感活动直接注入所表现的对象之中,使物象显示人的情思。比较简单的例子如刘长卿诗“离人正惆怅,新月愁婵娟”(《宿怀仁县南湖寄东海荀处士》)、“莺识春深恨,猿知去日愁”(《湖南使还留辞辛大夫》),以及钱起诗“风急翻霜冷,云开见月惊”(《送征雁》),李嘉祐诗“无人花色惨,多雨鸟声寒”(《自常州还江阴途中作》),多是将情感性词语如“愁”、“恨”“惆怅”或具有浓重情感色彩的感觉性词语如“冷”、“惊”、“寒”、“惨”等加诸物象之上,于是物象成了人的主观情意的载体,这正是汉魏古诗应用移情的固有手法。不过大历诗人毕竟有所创新,那就是不直接使用情感性字眼,通过其他途径,依然实现景物情绪化的功能。李嘉祐《自苏台至望亭驿人家尽空春物增思怅然有作因寄从弟纾》一诗,纪吴地战乱后乡村败残的景象,用了“野棠自发空临水,江燕初归不见人”作描绘,其“野棠”和“江燕”两个物象上面并未附加情感性词语,但凭借“空临水”、“不见人”这两个细节,就把物自有情、人事实非的强烈感受传达出来了,也是一种人情化的表现方法。又如其《送王牧往吉州谒王使君叔》诗中的“野渡花争发,春塘水乱流”,钱起《忆山中寄旧友》诗中“树深烟不散,溪静鹭忘飞”,以及皇甫冉《秋日东郊作》里的名句“燕知社日辞巢去,菊为重阳冒雨开”,均有将物象情意化的倾向,却避免了较为生硬的情感性字眼插入,而让情意色彩在物自身所采取的行为、姿态中表露出来,虽仍有人工作意的迹象,较之简单化的移情则见得更为生动也更为自然。
大历诗中的移情还可能有第三种形态,姑名之曰物象的联想功能化,指诗人将自己的联想心理加诸物象,让物象经过联想作用后能获得更丰富的意蕴,且更能体现诗人的情意指向。这一联想活动可以是由物及物,即通过物象的叠加以拓展诗人的情思。如郎士元《听邻家吹笙》诗云:“风吹声如隔彩霞,不知墙外是谁家。重门深锁无寻处,疑有碧桃千树花。”诗所要描写的对象是邻家的笙乐,但诗人的感受不限于声音之美,他从风里传送的乐音联想到空中的彩霞,更将音乐的发源地想象成碧桃盛开的仙家。经过这样几道转折,笙乐获得了听觉与视觉、地面与天空、人家与仙境多重叠合,诗人对笙乐的情意感受也就层层累积上去了。联想活动亦可由己及人,将自己感受到的物象传递给他人,以便在共同的感受中构建新的情意空间。李端诗“日落众山昏,萧萧暮雨繁。那堪两处宿,共听一声猿。”(《溪行逢雨与柳中庸》)其实听见猿声的仅限于他自己,他却将猿猴的哀鸣连同周遭山昏雨繁的景观一起推向友人,设想两处分宿而能共听共感,个人体验便因相思之情更增添了厚度。他的另一首诗“暮雨萧条过凤城,霏霏飒飒重还轻。闻君此夜东林宿,听得荷池几番声”(《听夜雨寄卢纶》),也是将夜雨景象外射给对方,只是在自己感受的“萧条”与设想友人荷池听雨的清韵之间构筑起一定的张力,情思显得稍为复杂。移情的联想心理还可以体现为自然物象与社会人事之间的交流,这在古代诗歌传统中谓之“比兴”,大历诗人亦加沿用,而在多数情况下则又打破传统“比兴”的简单套式,使联想心理开展得更为活跃,物象与人事也有可能更紧密地融成一体。如钱起诗“生事萍无定,愁心云不开”(《对雨》),又“客心湖上雁,归想日边花”(《登复州南楼》),皆为一句诗里情事与物象并举,情事的内涵即由物象予以暗示和展开,物象烘托情思,情思渗入物象,较之传统“比兴”手法之借物象作引子或作比况,在感受上自有区别。这方面最为著名的例子,乃是司空曙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一联(《喜外弟卢纶见宿》诗),它把本不相干的两个意象合到一起,让垂暮之人与将枯之树形成叠影,而“白头”与“黄叶”自相交会,连同“雨中”萧条之感与“灯下”暗淡之光亦取得氛围上的同感共振,由此产生出极大的撼动人心的力量,则人所共知。这些都应视以为大历诗歌“移情入景”的重要创获。
选景与写景之余,还当考虑构景,也就是如何将分散的物象总合成具有整体效应的艺术图景。大历诗人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并不突出,而亦有他们自身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们习惯于用静态化的方法来处理时空关系,常爱将摄取到的物象作平列式空间并置,这样构造出来的图景必然呈现为静态的展示,有远近高下的比照,却缺少先后流动的时序。有时候,诗的内容必须包含时间上的转换,但他们也尽量将过程简化为孤立、静止的几个点,任其作平面式推移,不取腾挪跌宕式的起伏。最典型的莫若当时诗坛常用的饯别诗体,习惯写法是从送别场景领起,叙情事,点染物象,而后移向行旅途中可能遇见的景观,结以到达目的地后有待实现的期望,全篇似乎写了一个过程,给人的感觉依然是静态的缀接。大历诗人构景的另一个特点是画面的精细化,他们喜欢对物象作细致的刻画,形态生动,却往往显得大气不足。刘长卿诗“高树潮光上,空城秋气归”(《步登夏口古城作》),将潮水泛光映现于树梢以及空城中易于聚集寒气的细节表达得相当熨帖,而诗篇的生命容涵则未必相称。钱起《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一力学步王维《辋川绝句》,其中有不少精彩的特写镜头,但终不如王诗来得自然浑成。这是因为盛唐人写景常取大景与小景相结合,整个画面见得生态灵动而又气势浑沦,大历诗人一味在物象精细上用工夫,气度就不免有所缺损。这个时期的作品在取境上还有追求深远的倾向,诗人们不单爱好营构幽深的境界,如前引钱起诗“树深烟不散,溪静鹭忘飞”,以及司空曙诗“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更常使用一些特殊字眼来制造深远的感觉。如用“隔”字将画面空间分割成前景与后景两个层次,将所要表现的对象隐藏于被隔开的后端,利用前后景观之间自然形成的张力,便可加大对于所关注对象的距离感,并使整个画面增添了纵深感,钱起诗“烟火隔林疏”、郎士元诗“雨色隔秋原”均属这类例子。又如使用“出”、“入”等字样提示物象的向外延伸或持续运行,从而促使观景者的目光及其想象活动随物象外移,不断趋远,也会加强画面给人的深远感受,如刘长卿诗“相思晚望西林寺,唯有钟声出白云”(《舟中送李十八》)、郎士元诗“荒城背流水,远雁入寒云”(《盩屋县郑礒宅送钱大》)以至前引钱起诗“萤远入烟流”等,实际上都具有这样的效果。以上特点虽属新巧,却并不一定能显示大历诗歌在艺术上的成功,要注意的是,此类构景技巧的应用,跟大历诗人们偏向内敛的心境及其萧疏落寞的情怀有密切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不妨将其构景的原则归结为“含情布景”,它和“因情设景”、“移情入景”同样体现着“缘情写物”的基本方略。
我们已经对大历诗风演进的一个重要侧面,即如何从“因物兴感”式的“以物观物”转向“缘情写物”式的“以我观物”作了考察,并就选景、写景与构景三个方面之促成“有我之境”在大历诗坛的广泛传播给予具体说明。应当怎样来看待古典诗歌意象艺术上的这一新变呢?总体上讲,艺术是要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出新的,古典诗歌创作由侧重自然兴发的“无我之境”移向更讲求人工作意的“有我之境”,实有其受历史推动之不得不然。这一转变在盛唐后期诗人如杜甫、岑参等人的一些诗作中即有所呈现。杜甫得后人盛赞的“碧瓦初寒外”、“晨钟云外湿”之类诗句(36),正是物象知觉化的绝好样板;其“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秋兴八首》之七),更带有鲜明的移情烙印。而岑诗“孤灯燃客梦,寒杵捣乡愁”(《宿关西客舍》),用“燃”和“捣”两个动词,将“孤灯”、“寒杵”与本不相干的“客梦”、“乡愁”挂接到一起,其新奇可喜的意趣不正来自物象的联想功能吗?可见诗歌写意的作风在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已然冒尖,大历诗人们的努力不过是将其推广放大而已。用写意取AI写作实,人工取代天然,诗歌艺术的原初美质或有所损伤,但有失必有得,大历对“有我之境”的追求不仅丰富了诗歌创作的表现技巧,亦且更新了其思维方式,为其日后的发展开出了新的生机,功绩不容抹杀。当然,也不能对这一新变估价过高。不光因为大历诗人们的生命体验相对贫弱,致使其诗中生命力度明显下降,也不光是他们经常追随前人甚至重复自己,造成艺术表现上套式化倾向的严重存在,还要看到,“有我之境”作为一整套艺术格局的开发,在他们手里尚处在起步阶段,远不足以穷尽这一新境界的巨大魅力。比如说,他们选景的对象多限于眼下手头的现成物料,视野相对狭窄,未能打开心胸,博思广益,乃至发挥想象和幻想,去精心拟构新的意象,以便从“因情设景”过渡到“因情造景”。又比如,其表现手法上一味倚仗移情,虽亦能使“物皆著我之色彩”,终嫌色泽单调,若能进一步调动其心体变造之机能,则物象的变异与物态的出新当大有改观,而“我”之情意也会更见复杂多样且含蕴深沉。至于景观画面布局上的工巧、平板而缺少生气,前已述及,无庸多议。大历诗风新变上的这些不足,要等经历了元和诗体大变的冲击,进入晚唐诗以及曲子词的阶段,才会转出新的局面,将“缘情写物”的诗歌艺术逐渐推向成熟,这或许便是大历新变开创意义之所在了。
收稿日期:2013-06-25
注释:
①参见高棅《唐诗品汇》卷首《五言古诗叙目·接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参见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③参见蒋寅《大历诗风》第六章《感受与表现》中的论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按:此书迄今仍属大历诗风最有深度的研究著作,本文的立意即在接过其话头而重加阐释。
④参见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第7页附注1所引王氏原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⑤⑥参见《人间词话》刊稿第三则、第十七则,《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1、198页。
⑦⑧参见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十二《观物篇六十二》,《四库全书》本。
⑨参见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十四《观物外篇下》。
⑩参见邵雍《击壤集·自序》,《四库全书》本。
(11)参见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第三篇《世界作为表象再论》中有关艺术与审美问题的讨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2)提法分见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与《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转引自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出版社1987年版。
(13)参见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人间嗜好之研究》诸文,载《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
(14)(15)参见《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第220、192页。
(16)(17)参见《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33、27页。
(18)《人间词话》第六则,参见《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第193页。
(19)《人间词话》第十六、十七、十八则,参见《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第197—198页。
(20)《人间词话》第五十二则,参见《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第217页。
(21)《人间词话》第三则,参见《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第191页。
(22)按:这里所说的“物象”,不限于自然景物,举凡感官意识所能把握的对象,包括人的形态与动作在内,皆可谓之物象,故“情”与“景”便组合成诗歌艺术的基础。情、景之外,作品中还当有“事”存在,但在一般抒情诗里,“事”往往同情思结合为情事,且情事的展开亦常关联到物象,故“事”与情、景难以分割。有的诗歌里还会有“理”的成分出现,它可能容涵在情、景之中,也有可能独立显示。总之,情、景、事、理作为诗歌作品构成的四大元素,其中情、景实为主干,这正是古典诗歌艺术特别注目于情景关系的缘由。
(23)“情景交融”一语在古代诗学里也有不同解说,有的论者将其视以为诗中情语与景语交互呈现的一种配置方式,属表现形式问题,本文意指诗人情意体验渗透于诗中物象所达致的融通会合的境界,它标志着古典诗歌抒情艺术的成熟。
(24)参见《楚辞·九章·惜诵》,《四部丛刊》本洪兴祖补注《楚辞》卷四。
(25)参见朱自清《诗言志辨·比兴》第三节《赋比兴通释》所论,载《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6)参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载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7)参见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载丁福保编《清诗话》下册第532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28)借用范晞文释周弼《三体诗法》语,参见《对床夜语》卷二,载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42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9)参见殷璠《河岳英灵集叙》及卷上陶翰评语,载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第107、142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0)参见《诗格·论文意》,载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65、16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1)参见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所言,载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第74—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2)参见《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同上书第72页。
(33)按:大历诗坛上浮在着不同流派,其主流人物通常指钱起、郎士元为首的京城才子集团和刘长卿、李嘉祐等江南地方官诗人,本文所论及“缘情写物”、“移情入景”的艺术方法,即以他们的一部分代表性诗作为依据。
(34)“感受与表现分离”作为大历诗歌创作活动的特点,蒋寅《大历诗风》第六章里有具体说明,本文得以借鉴,不过他以之为诗歌艺术情景交融的生成条件,本文则解作“有我之境”得以产生的思维机制,可供讨论。
(35)参见朱之荆《增订唐诗摘抄》卷三所录诗下评语,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36)参见叶燮《原诗·内篇下》所论,载《清诗话》下册,第585—586页。
标签:诗歌论文; 情景交融论文; 有我之境论文; 文化论文; 诗经论文; 人间词话论文; 读书论文; 叔本华论文; 王国维论文; 楚辞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