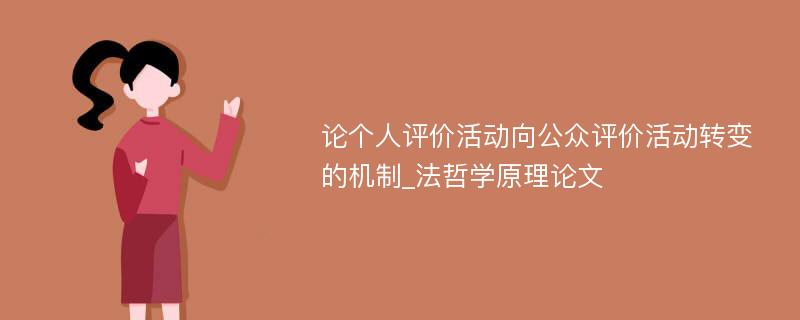
论个体评价活动向民众评价活动转化的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价论文,民众论文,个体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在研究社会评价活动中群体主体作用的根据时曾指出,群体的主体作用既可以通过处于群体内组织结构金字塔尖式的权威机构所进行的评价活动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群体内众多个体所进行的评价活动之间的互动体现出来(注:参见陈新汉:《论社会评价活动的主体》,《学术月刊》1997年第7期。)。前者为权威机构评价活动,后者为民众评价活动。所谓民众评价活动,就是众多个体针对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评价并通过传播中双向或多向互动显现出群体主体作用的评价活动。民众评价活动不是个体评价活动,但与权威机构评价活动不具有超个体评价活动的形式不同,个体评价活动是民众评价 活动的细胞。本文着重研究民众评价活动在个体评价活动基础上形成的机制。
一、黑格尔对群体以“无机方式”表达意见的思考
《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晚年在柏林大学任教期间唯一正式出版的著作。对于这本著作,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深刻之处也正是于他处处都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出发,并把这种对立加以强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2页。)在这本著作中,黑格尔对群体表达意见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尤其是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出发,对民众表达意见的两重性进行了分析。
黑格尔认为,动物不能意识到自己是具有特定的对象、内容和目的的特殊物,而人则 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特殊物,这种意识就是意志。因此,意志是“经过自身中反思而返 回的”特殊性,是“自我的自我规定”(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332、323、201、332、259、255、331、323、333、331—332、332、332—333、333、332页。)。他常常把“意见”和“意志”并列在一起予以理解,如:“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332、323、201、332、259、255、331、323、333、331—332、332、332—333、333、332页。)。在他看来,意见体现着意志,而意志总要通过意见表达出来。
黑格尔认为,不仅个体具有意志,而且群体也具有意志。他研究了个体意志和群体意 志之间的关系。个体意见是自我私有的,它本身不是一个普遍性的自在自为的思想。而 与个人意见相对立的群体意见则表达着群体的“普遍”意志,体现着众多个体意志的普遍性。因此,这两者的关系体现着特殊和普遍之间的关系,并互为中介。他还分析了 作为市民的个体与作为市民社会的普遍物之间的关系,认为“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 身就是目的”,但“单个的人只有作为某种普遍物的成员才能表现自己。”(注:黑格 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332、323、201、332、259、255、 331、323、333、331—332、332、332—333、333、332页。)由此,“特殊的东西必然 要把自己提高到普遍性的形式,并在这种形式中寻找而获得它的生存”(注: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332、323、201、332、259、255、331 、323、333、331—332、332、332—333、333、332页。)。在黑格尔看来,这是市民社 会的一个原则。
这种上升的过程通过群体表达意见的两种现实形式——“有机方式”和“无机方式” 体现出来。“有机”和“无机”作为活动方式的特征,原本是与自然界中有生命的物质 即“有机体”和无生命的物质即“无机体”相对应的。“有机方式”就是由此引申而来,即其活动特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内在性、自洽性和自组织性。“无机方式”的特征则与此相反。
黑格尔把“有机方式”与国家相联系,把“无机方式”与民众相联系。黑格尔说:“在国家中现实地肯定自己的东西当然须用有机的方式表现出来,国家制度中的各个部分就是这样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332、323、201、332、259、255、331、323、333、331—332、332、332—333、333、332页。)他认为,国家以“有机方式”所表达的群体意志体现着“作为意志而实现自己的理性的力量”(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332、323、201、332、259、255、331、323、333、331—332、332、332—333、333、332页。),即它总能自觉地、理性地代表(至少在形式上)群体的意志,而把个别人的意志“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从而是片面的环节”(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332、323、201、332、259、255、331、323、333、331—332、332、332—333、333、332页。)包括在内。他把一个群体内的成员“没有经过某一种程序的组织”而表达意见的方式,称为“无机方式”(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332、323、201、332、259、255、331、323、333、331—332、332、332—333、333、332页。)。他说:“单个人的多数人(人们往往喜欢称之为“人民”)的确是一种总体,但只是一种群体,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332、323、201、332、259、255、331、323、333、331—332、332、332—333、333、332页。),因而“不论人们在表示意见时是多么地慷慨激昂,也不论在提出主张时或攻击和争辩时是如何地严肃认真,这些都不是关于实际问题的标准”(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332、323、201、332、259、255、331、323、333、331—332、332、332—333、333、332页。)。
黑格尔对民众通过“无机方式”表达意见的两重性作了深刻的分析:在一个群体内“个人所享受的形式的主观自由在于,对普遍事务具有他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332、323、201、332、259、255、331、323、333、331—332、332、332—333、333、332页。),因而表面上是混乱的;而“绝对的普遍物、实体性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跟它们的对立物即多数人独特的和特殊的意见相联系”,因而内在的东西却是“绝对的、普遍的、实体性的和真实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332、323、201、332、259、255、331、323、333、331—332、332、332—333、333、332页。)。对于这种两重性,黑格尔还引用了一句民谚:一方面是“Vox populi,dox aei[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332、323、201、332、259、255、331、323、333、331—332、332、332—333、333、332页。),但另一方面,“Chel Volgare ignorante ong un riprenda,E parli p iu di quel ehe meno intenda。[无知庶民责斥每一个人,他对所了解得最少的东西却谈得最多。”(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332、323、201、332、259、255、331、323、333、331—332、332、332—333、333、332页。)这“两种说法不应看作是出于不同的主观观点”(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332、323、201、332、259、255、331、323、333、331—332、332、332—333、333、332页。),而是民众表达意见两重性的具体表现。
在这里,黑格尔实际上以个体意志与群体意志的关系来分析“无机方式”的两重性的 。一个群体内的众多个体总是从各自的需要、利益出发,对众多个体共同感兴趣的“普 遍事务”发表意见,由于处在同一个群体内,因而总与群体主体的需要、利益发生一定 程度的联系,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着群体主体的意志。从表面上看,各种意见林 林总总,有很大的杂乱性,但群体主体的意志作为“绝对的普遍性、实体性的东西和真 实的东西”也就实现了。群体意志不是个体意志,但群体不具有超个体的形式,即群体 意志必须通过个体意志表达出来。这就是普遍寓于特殊之中,并通过特殊体现出来。以 民众表达为代表的“无机方式”,正是群体主体表达自己意志的一种现实形式。这就给 我们的论题以深刻的启示。
尽管黑格尔深刻分析了群体以“无机方式”表达意志的两重性,并且认为“无论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尤其在我们的时代”(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32、332页。),但他对“多数人独特的和特殊的意见”的蔑视是显而易见的。他说:“由于这里所考虑的是独特观点和独特认识的意识,所以愈是独特,它的内容就愈是恶劣;因为凡是其内容完全是特殊的和独特的那些东西都是恶劣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32、332页。)这不能不说是他唯心史观局限性的体现。
二、对社会事件的个体评价是人际传播的主要内容
主体以利益为标准,来衡量客体属性对于满足自己需要所具有的意义,因此评价活动 总是与体现需要和利益的意志相联系。黑格尔所分析的群体表达意志的“无机方式”, 实际上指出了众多个体评价活动以“无机方式”转化为体现群体主体的民众评价活动的 途径。这种转化是与个体之间交流(即传播各自的评价内容的信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
群体是人类存在的普遍形式。作为社会的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这就意味着,个体 总是要与群体中的其他个体发生各种人际关系,群体之间也总是要发生各种关系。群体 间关系归根到底是人际关系。人们之间所发生的各种关系是“基于有意义的符号之上的 一种行动过程”(注: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 18页。),是以信息交流作为必要前提和基本内容的。这在远古时代是如此,在现代的 信息时代更是如此。人际之间的信息交流可概括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人 际传播是最基本的,它为民众评价活动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中介。人际传播中最原始和 最基本的形式是面对面的交谈,这可以是两人之间的交谈,也可以是多人之间的座谈。 以后有了书信之间的往来,有了电话对话和电视会议,在信息时代更有了互联网电子邮 件的交流和聊天室里的漫谈,等等。
人周围的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构成了主体认识活动的客体,这些客体构成了人生活于 其中的客体世界。人周围的客体与主体之间总是构成一种价值关系,这些价值关系构成 了人生活于其中的价值世界。价值世界离不开客体世界,但价值世界不等同于客体世界 ,它体现着客体世界与主体之间的意义关系。人生活在双重世界之中,不仅要对客体进 行认知活动,而且要对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评价活动。由此,个体在与他人进行 的交流中,不仅要传递和接受关于客体世界的信息,而且要传递和接受关于价值世界的 信息。
学术界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客体信息比价值信息更重要。其实不然。趋利 避害是生物体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则,人作为高级形态的生物体也必须遵循这一根本原 则。为了要趋利避害,就要把握“利”和“害”,而要把握“利”和“害”,就要重视 价值信息。这在人类的初始阶段体现得尤其突出。现代西方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说, 对于现代人思维所关注的客体的固有属性和客观因果性,原始人是不大感兴趣的,“他们所追求的往往是某种实际效果”(注: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3页。)。而“效果”正是对人而言的价值。在艰苦的自然环境面前,原始初民必须始终把与趋利避害直接相联的“利”、“害”的价值信息的获得看成是最重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环境对人类来说已经不像原初时代那样残酷了,但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价值信息从根本上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现代西方哲学家舍勒尔明确指出:“实际上,通常对价值的认识甚至于发生在更为精确的专门知识之前”,因为“对价值的认识比所有一切纯理论上的理解都更为在先,更为根本”(注:引自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5页。)。这仍然是源于趋利 避害的根本原则。
人们必须与他人交流信息。尽管有时以交流客体信息为主,有时以交流价值信息为主,但由于在总体上获取价值信息比客体信息更为重要,因此在总体上更趋向于交流价值信息。传播总是有目的的,即使在交流纯粹的关于客体世界的信息中,也体现着传出者和接受者对于客体世界信息的意图,从而在关于客体世界的信息中融入了评价内容。可以说,在信息传播中,价值信息总是占据着重要的或主要的地位。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价值信息都能够得到传播。一般说来,只有对其他主体有意义的 信息,才能被其他主体接受和再次传出。因此,传播的信息一定是与人们共同感兴趣的 话题相联系。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把大家的利害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有关社会事件(包 括能把大家的利害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自然事件,这类自然事件也就成为社会事件)的话 题。这种利害关系对于各个体而言,可能方向相同但程度不同,也可能方向根本不同。 利害关系的方向相同,意味着个体之间的评价观点相同,因此彼此间有共同语言,大家 都有交流自己评价内容的欲望,以便引起“共鸣”。利害关系的方向不同,意味着个体之间观点不同,大家也都有传递自己评价内容的欲望,以便通过讨论、争辩,说服、 压倒对方。个体之间相互交流关于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目的在于壮大赞同自己观点的人 数,减少反对自己观点的人数,以形成声势。从根本上说,其目的就在于维持或改变共 同感兴趣话题中有关社会事件目前存在的状况,以便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使自己的 利益得到维护。民众评价活动正是在这种人际传播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三、个体评价内容在传播中的客观化和主观化
民众评价活动在人际传播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与个体评价内容在其中经历着客 观化和主观化的机制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个体评价活动的内容在传播过程中必然客观化。所谓客观化,是指个体主体的 评价内容通过符号编码形式凝结在媒介上。媒介是与编码联系在一起的“传播活动中承 载、传递信息的中介物”(注: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999年版,第576页。),它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地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如面对面 交谈的声音、由电话联系的电磁波、互联网中的电子邮件等。这样,个体主体的评价内 容就由观念形态转化为物质形态,离开个体主体的意识而存在。尽管在人际传播过程中 ,这一以符号编码形式凝结在媒介上的评价内容存在的时间较为短暂,但这一客观化的 形态是存在着的。
这种以符号编码形式凝结在媒介上的评价内容,形成了客观认识成果。在哲学史上, 柏拉图首次对客观认识成果作过认真思考,认为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有一个由理念组 成的世界,这个理念世界就是客观化的认识成果。波普对客观认识成果做过认真研究, 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关于作为客观化认识成果的世界3,波普明确指出:“思 想内容的世界实际上是人类精神产物的世界”(注:波普:《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 书店1987年版,第409—410、367—368、367—368页。)。他强调了“世界3的实在性” ,即它既具有相对于“主观意义和个人意义”(注:波普:《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 书店1987年版,第409—410、367—368、367—368页。)而言的客观性,又具有自主性( 注:波普:《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09—410、367—368、367—3 68页。)——它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他们的研究对我们的论题很有启示。
这一以符号编码形式凝结在媒介上、作为客观认识成果的评价内容,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它是精神形态的客观存在。一般说来,有两种涵义的客观:一种是物质的客观实在性——“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客观实在性”(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6页。)。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来理解,这种客观实在与物质同义。另一种是精神的客观存在性,即指它离开人脑而独立存在。客观实在是客观存在的,但客观存在不一定是客观实在。客观化的评价内容以符号编码形式凝结在物质载体上,离开人脑而存在于社会之中,是一种精神的客观存在。精神的客观存在作为一种具有一定内容的意识信息,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观念化的存在,因而不是客观实在。其二,它是社会化的存在。客观化了的评价内容以符号编码形式体现出来,符号是由人们在社会中约定俗成的关于对象的指称物(注:Morris,Signification and Significance,Cambridge,Mass.MIT Press,1964,p.22.),因而客观化的个体评价内容就能为其他个体所理解和接受,从而也就成为社会的存在物。个体评价活动的内容客观化,是传播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次,在传播过程中还必须使以符号编码形式凝结在媒介上的评价内容主观化。凝结在媒介上的社会化了的个体评价内容,只有被其他个体主体把握,即再次转化为个体的主观形态,才能使它的社会化形态现实地发生作用。这个过程就是评价内容的主观化,它是传播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环节。
以符号编码形式凝结在媒介上的个体评价内容主观化的过程,首先表现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符号体系以其感性形式作用于主体的感觉器官,引起一定的神经脉冲,从而在大脑中形成关于物质符号体系的感性映像。这个感性映像并不直接就是它所标志的意义信息本身。在第二个阶段中,主体抓住这个感性映像中抽象性的一面,把它转化为组织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中的意义信息,即把物质符号体系所携带的意义信息以观念形式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对于语言使用者和书本阅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无意识的过程”(注:波普:《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5页。),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阶段的区分是不存在的。我国魏晋时期的王弼把这两个阶段概括为“得象”和“得意”。他认为,“得象”才能“得意”;而要真正地“得意”,又必须“忘象”(注: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他看到了“象”和“意”之间的辩证关系。
经过上述两个阶段,物质符号体系所携带的个体评价内容就以观念形式呈现在接受者的意识中。但评价内容主观化的过程还没有完结,这就是接受者必须对传递而来的评价内容予以理解。这个过程就是个体主体以他人评价内容为对象的评价活动过程。释义学家对这个过程作了分析。狄尔泰认为,接受者“决不是心灵一片空白,因而不可能是可 以真实地反映向他呈现的任何东西的超然的研究者”(注:转引自张汝伦:《意义的探 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189页。)。他正确地看到了接受者总要从他的 角度来理解传递而来的信息。贝蒂对这个过程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应该坚持对象的 释义学自主性原则,即“根据(原)作者的情况来理解知识的意义”;同时也要坚持理解 的现实性原则,即“解释者应该消化他的解释对象,使它所体现的精神成为他自身精神 的一部分”(注:转引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1 89页。)。这种见解十分有见地:只有理解,才有再理解;没有再理解,也不可能有简 单的理解。客观评价内容主观化的过程主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的。
传播学家把上述哲学语言转化为传播学专门语言。埃利斯·劳纳·伍曼(Elisabegh Noelle-Neumann)概括出传播的一条原理就是:“交流者总要将相互作用融入有意义的 模式之中”(注:Elisabegh Noelle-Neumann,The spiral of Silence:Public Opinion-Our Ski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238.)。埃弗雷特·罗杰斯( Everett Rogers)说得更是直截了当:“相互作用是重要的,因为与其说信息传播是信 息简单地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还不如说是授受关系的产物。传播能使意义逐渐趋向 一致,即意义并合。新思想的产生,正是意义并合过程的产物。”(注:Everett Rogers,Communication Yearbook 3,New York Free Press,1981,p.67.)唐纳德·弗赖 伊(Donald Fry)和弗吉尼亚·弗赖伊(Virginia Fry)则认为:“观众通过联想赋予媒介 信息以意义”(注:Donald Fry and Virginia Fry,A Semiotic Model for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in Communication Yearbook 9,ed.M.L.1991.)。这就是传播 学中经常谈到的“积极观众”说。
接受者接受评价活动的信息,更是要对这种评价内容根据自己的情况予以再理解(即再 评价)。或者赞成,并以自己的评价观点予以补充和丰富;或者反对,并以自己的评价 观点予以驳斥和修正。只要接受者接收传递而来的评价信息,这个再理解即再评价过程 就必然发生,不管接受者意识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四、个体评价活动在人际传播中向民众评价活动转化
通过传播过程中的客观化中介,个体评价活动的内容以符号编码形式凝结在具有物质 形态的媒介上。这就使得个体评价内容能够离开个体主体而存在,能够为社会其他成员 接受和理解。个体主体的评价内容没有客观化以前,仅仅是个体自己的,不能为其他社 会成员接受和理解,不能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影响。因此,传播过程中的客观化中介, 为个体评价活动向体现群体主体的民众评价活动的转化提供了可能。
通过传播过程中的主观化中介,客观化了的评价内容必然被理解和再理解。这种已经被理解和再理解的评价内容,可以再一次作为个体评价内容而客观化,再次在传播中作为对象而被理解和再理解。在传播过程中,这种社会化了的评价内容的主观化可以不断地进行下去。通过传播过程中的主观化中介,即通过接受者对评价内容的理解和再理解,个体评价活动向体现群体主体的民众评价活动的转化,就有可能转化为现实。
在人际传播的客观化和主观化过程中,参与其中的每个主体都发挥了作用。群体的主 体作用体现在众多个体的作用之中,形成“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 个总的结果”,“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 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78页。),于是评价活动的主体就由个体主体转化为群体主体, 参与其中的每个主体都发挥了作用。也就是说,个体主体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即通过 理解和再理解的方式,参与了评价内容的形成,从而使评价内容由个体内容转化为群体 内容。于是,评价活动的主体就由个体主体转化为群体主体,评价活动的内容就由个体 内容转化为群体内容。
在人际传播过程中,传出和接收作为原因和结果相互过渡,相互转化,互为因果,并且往往是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等,从而在一个复杂的传播网络中实现了个体评价活动之间双向和多向的互动。正是这种互动,使得评价活动呈现为多层次的客观化和主观化的过程。由此,体现群体主体的民众评价活动就在众多个体主体的评价活动及其传播的互动基础上形成。
在个体评价活动向民众评价活动的转化过程中,从表面上看,个体所享受的形式的主观自由在于他对普遍事务具有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因而众多个体评 价活动的意见总是林林总总,有很大的偶然性,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但 是偶然性中隐藏着的必然和现象背后存在着的本质即群体主体的意见,“作为绝对的普 遍性、实体性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也必然通过偶然性和现象呈现出来。于是,体现 群体主体的民众评价活动也就形成了。在这里,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因此偶然性 是必然的;本质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因此现象是本质的。
传播是个体评价活动向民众评价活动转化的中介。传播的发展与媒介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从发展的顺序看,媒介主要有形体和器具媒介、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互联网的产生是印刷术发明以来最伟大的媒介革命。互联网开创了数字化时代,为达到全球信息资源的共享提供了强有力的媒介工具和途径。民众评价活动总是与大量信息的获得联系在一起。互联网的最大特点是开放性,在信息传播中的传出者和接受者之间建立了即时互逆式的联系。人们通过这种即时互逆式的联系,建立网友组织,倡导并组织召开网络会议,形成意见集团。民众评价活动随着意见集团的形成而形成。互联网突破了以往传播中的时空限制,能使数量巨大的人群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信息的双向互动。互联网超越时空的信息传播对于民众评价活动的快速和大规模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是其他媒介传播信息所无法比拟的。
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评价活动的现实形式有、并且只有两个,这就是权威机构评价活动和民众评价活动(注:参见陈新汉:《社会评价活动论纲》,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众多个体评价活动通过群体内组织机构的“有机”中介,与权威机构评价活动联系起来,从而成为权威机构评价活动的基础(注:参见陈新汉:《论权威机构评价活动机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在群体内通过传播中双向和多向互动的“无机”中介,即通 过传播过程中多层次的客观化和主观化的中介,评价活动的主体由个体主体转化为群体 主体,评价活动的内容由个体内容转化为群体内容,但这不是与权威机构评价活动相联 系,而是与民众评价活动相联系。民众评价活动就在众多个体评价活动的双向和多向互 动的基础上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