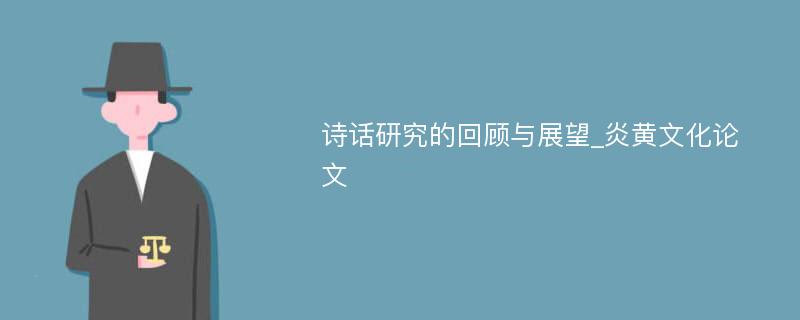
诗话研究之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诗话与东方诗话圈
中国诗话,在北宋欧阳修时代崛起之后,经历了宋、元、明数代的
繁衍和发展,至清代而鼎盛,成为中国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最主要的著
千年诗话,卷帙浩繁,汗牛充栋,表现出特别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且早已跨出国门,衍生出了古代的朝鲜诗话与日本诗话,越南文论亦深
受其影响。据本人《中国历代诗话书目》考查,中国历代诗话之知见书目,数以千计。流传至今的中国诗话之作,尚存有一千三百九十余部,加之朝鲜诗话、日本诗话之存世者,中、韩、日三国诗话的传世之作,总计尚有一千六百二十余部之富。如此繁富的东方诗话之作,形成了东方文学批评史乃至东方文化史上一种不容忽略的文化现象,这就是“东方诗话圈”。
东方诗话圈,是古代儒家文化圈的产物。世界古代文化,因民族与
地域而异,但是论其发祥地,大要不出其二:一是东方之中国,二是西
方之罗马。西方文化源于埃及,而兴盛于罗马,波及于整个欧洲;东方文化,以中国为宗主,以儒家文化为纽带,凡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如朝鲜、日本、东南亚地区,很早就进入了儒家文化圈之内。中国诗话则凭借着儒家文化的翅膀翱翔于周边各国和地区,走向世界。而且,由于印度佛教文化传播于中土,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禅宗思想及其思维方法,极大地影响于中国历代诗话,乃至古代朝鲜、日本诗话。于是,在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孕育之下,从印度→中国→朝鲜→日本→东南亚,在世界的东方,便形成了一个跨越时空的东方诗话圈。
中国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论诗著作,是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而以钟嵘《诗品》为“百代诗话之祖”;日本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论诗著作,是释师练的《济北诗话》,而日本学者多以空海大师辑录的《文镜秘府论》为日本诗话之宗;朝鲜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论诗著作,是徐居正的《东人诗话》,韩国学者则以李仁老的《破闲集》为“韩国诗话之冠”。中、韩、日三国诗话之中的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论诗著作,其问世时间虽然有先后之分,但其论诗体例、结构形式、论诗宗旨,乃至基本概念、范畴、范畴群、理论体系与方法论,如出一辙。可以说,中韩日三国诗话是出于同一个母体的孪生兄弟,只是中国诗话为其长兄而已。这个母体,就是中国儒家文化。盛极一时的中韩日三国诗话,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交融混一的产物,既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还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朝鲜民族、日本民族各自的文化性格、文人心态、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
比较而言,以中国诗话为代表的东方诗话以及越南文论,具有与西
方诗学完全不同的特色:其一,就名称而论,东方诗话自欧阳修首创“
诗话”以降,中韩日三国历代论诗之作,多沿袭“诗话”之名,据不完
全统计,现存一千六七百部历代论诗之作,以“诗话”名书者多达近千部。“诗话”之名,陈陈相因,相续相禅,历久不变,正是儒家注重祖宗崇拜的宗法文化观念的一种反映。而西方诗学自从亚里斯多德《诗学》问世以来,则很少有人继续沿用“诗学”之名。名为“诗学”,实为文艺理论之通称也。
其二,就论诗体制而言,东方诗话大多采用语录体式,由一条一则
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长短随宜,
灵活多样。这一体制特点,初期诗话显得尤为突出;北宋以后的诗话论
诗体制,或有按内容分卷编排者,论诗条目亦有扩充而为段落者,但其基本体制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内容更丰富,体制更完美而已。
其三,就论诗内容而言,东方诗话以诗为主,属于狭义的诗学。故
其内容不出“论诗及辞”与“论诗及事”两种类型,前者源于钟嵘《诗
品》,我称之为“钟派”;后者始于欧公《六一诗话》,我谓之为“欧
派”。比较而言,古代朝鲜诗话多以“论诗及事”为主,属于欧派诗话
之列;日本诗话多以“论诗及辞”为主,属于钟派诗话之列。
其四,就论诗风格而言,东方诗话大多属于“以资闲谈”的随笔之
类,行文运笔,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拘束,有如学术散文,形散而神不散,始终以论诗为中心。特别是其语言风格,平易浅近,多运用宋元兴起的白话文,完全摈弃刘勰《文心雕龙》式的骈俪风格,很少有学究气、书卷气,也与逻辑严密、体制完备的西方诗学大相径庭。以其使作者能够“挟人尽可能之笔,著唯意所欲之言”,故赢得了古今中外广大的作者群;以其能“使人心开目明,玩味不能去手”,故又赢得了古今中外广大的读者群。这正是东方诗话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五,就论诗宗旨而言,东方诗话多遵循儒家“温柔敦厚”与“兴
观群怨”诗教之旨,以《诗三百》为圭臬。清人徐世溥《榆溪诗话》云:“《三百篇》者,诗之昆仑,亦诗之海也。”日本久保善教《木石诗话》谓“诗之渊源,在《三百篇》”;长山樗园《诗格集成》说:“《三百篇》,诗之祖也。”韩人崔滋《补闲集》亦谓《三百篇》“发其性情之真,而感动之切,入人骨髓之深耶”。因之而尊杜,称颂杜甫为“诗圣”,《补闲集》云:“言诗不及杜,如言儒不及夫子。”日本古贺侗庵《侗庵非诗话》云:“诗至老杜,是谓集大成之孔子。”清人袁枚《随园诗话》云:“文尊韩,诗尊杜,犹登山者必上泰山,泛水者必朝东海也。”与西方诗学不同,东方诗话论诗倡言“诗品出于人品”之说,特别注重诗人的诗品与人品,追求诗人的理想完美人格和诗歌的蕴藉朦胧含蓄,而以“意境美”为最高审美境界和批评标准。
二 诗话整理与诗话研究
中国的诗话研究,始发于诗话之整理。诗话之整理,是诗话研究的
基础。郭绍虞先生说“整理也是批评”(《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
。中国诗话的整理和研究,肇于宋盛于清。
宋人之于诗话文献资料的整理,主要力量集中在诗话之裒辑汇编。
如北宋佚名的《唐宋分门名贤诗话》,阮阅的《诗话总龟》,南宋胡仔
的《苕溪渔隐丛话》,蔡正孙的《诗林广记》,任舟的《古今类总诗话》,何汶的《竹庄诗话》。其中,佚名《唐宋分门名贤诗话》久佚,今在韩国大田发现其残本,经考证成书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是中国第一部诗话类编。最具研究价值的,当推南宋魏庆之的《诗人玉屑》21卷,辑录两宋诗话论诗的短札谈片,以资料丰富、理论色彩突出而见称于世。
元人之于诗话的研究,主要在于考证方面,较有成就者是方回。他
是第一位对宋代诗话予以认真考辨的学者,撰有《诗话总龟考》、《渔
隐丛话考》、《诗人玉屑考》、《竹庄备全诗话考》、《古今类总诗话考》《瑶池集考》、《可言集考》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分别对宋代各家诗话之卷数、作者、内容、版本与文字传播中的正误等,进行考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方回是中国诗话史上具有现代意义的诗话研究的真正开创者。
元明人之于诗话之整理,有王恕所辑《南溪笔录群贤诗话》3卷,
王昌会所辑《诗话类编》32卷,黄省曾所辑《名家诗法》8卷, 俞允文
编《名贤诗评》20卷等。陶宗仪所编大型丛书《说郛》亦辑录唐宋诗话
之传世者,杨成玉编辑宋人诗话十种而为《诗话》10卷,比前人之诗话
类编,其文献资料更为完整,为清人致力于诗话丛书的编辑打下了基础。
清人之于诗话之整理和研究,具有集大成之功。 主要表现在:(1
)诗话丛书的编辑,有何文焕的《历代诗话》57卷,收编宋元明历代诗
话之作27种,附《历代诗话考索》1卷。 其次有顾龙振的《诗学指南》
8卷,辑录唐宋元人诗评、诗格、诗式、诗法之类凡41种。 朱琰《诗触
》5卷,收编钟嵘《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等16种。 继何文焕之后
,有清末民初丁福保的《历代诗话续编》76卷,《清诗话》51卷。这三
套诗话丛书,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2)纪事体诗话的系列化。 清人继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之后,大力编撰纪事体诗话,如厉鹗《宋诗纪事》100卷,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100卷,陈衍《辽诗纪事》12卷,《金诗纪事》16卷,《元诗纪事》45卷, 陈田《明诗纪事》187卷,后人邓之诚又撰《清诗纪事》8卷, 与旧题尤袤《全唐诗话》等相辅相成,使历代纪事体诗话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3 )诗话著作提要:著作提要,本身就是一种文学批评。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以内容提要形式,于“诗文评”之中对49部历代诗话和73部诗话存目予以简明扼要的评价,自成一家之言,富有学术权威性,于当初与后代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4)诗话研究专门论著之崛起。 清人关于单篇诗话的研究,有三种形式:一是注释,有胡鉴《沧浪诗话注》,王玮庆《沧浪诗话补注》。二是批评:对于《沧浪诗话》的批评,清人有三派:誉之者如王士祯、潘德舆承宋、明之说,把严羽“比之达摩西来,独辟禅宗”;攻之者如冯班撰《沧浪诗话纠谬》1卷,承钱谦益之论, 指斥严羽“禅悟”说为“热病”和“呓语”;折衷者为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严羽《沧浪诗话》自成“一家之言”,能“救一时之弊”,持论较为公正。三是诗话之宏观研究,有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一篇专论,于诗话之源流、性质、特征、分类、演变过程、文学地位和清代诗话的门户之风等,全面地进行批评,是中国古代第一篇专门化的诗话研究论文,颇多精到之见。
“五四”以降,诗话之整理和研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郭绍虞
先生即是中国诗话之整理和研究的一面旗帜,开创了诗话研究的一代风
尚。其主要贡献有三:(1)钩沉集腋, 编辑《宋诗话辑佚》《清诗话
续编》;(2)勤于考证,撰写《宋诗话考》;(3)中国诗话研究的重
大突破:他以《诗话丛话》、《沧浪诗话校释》、《宋诗话辑佚序》、《清诗话前言》、《浅谈清代诗话的学术性》等学术论著,使中国诗话研究趋于系统化、专门化,把中国诗话之整理和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与此同时,台湾地区影印出版了《古今诗话丛编》、《古今诗话续编》、《清代诗话访佚初编》三套诗话丛书;日本于大政八年(1919)整理出版了一套《日本诗话丛书》;韩国于近期也出版了《韩国诗话丛编》和《日本诗话丛编》。如此繁富的大型诗话丛书的整理出版,无疑将有力地推动诗话研究的蓬勃发展,一大批诗话研究的专门著作应运而生。其主要代表作:日本有船津富彦的《中国诗话的研究》;韩国有赵钟业的《中韩日三国诗话比较研究》和《韩国诗话研究》《东方诗话论丛》;中国有蔡镇楚的《中国诗话史》、《诗话学》、《石竹山房诗话论稿》,刘德重、张寅彭的《诗话概说》,张葆全的《诗话与词话》及其与人合编的《中国古代诗话词话辞典》等。
三 诗话与诗话学
从“诗话”到“诗话学”,是历史之必然,是诗话研究趋于系统化
、专门化的重要标志。
“诗话”之名,始创于北宋之欧阳修;“诗话学”之名,始创于民
国之徐英先生:都是诗话研究史上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1936年的《安徽大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诗话
学发凡》的论文,作者是原中央大学、安徽大学教授徐英。徐文以文言
体式纵论中国诗话之源流、派别、体制、演变、流弊等,文末又仿效旧
题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形式,阐述诗话学之内容和学术价值,在于“
述原始”,“述体派”,“述诗学”,“述诗品”,“述本事”,“述
说部”,“述杂体”,“述标榜”等八个方面,以此构成诗话学的理论
体系。我以为,徐文的最大学术价值在于鲜明地标举“诗话学”,高扬
起“诗话学”这一面新的学术旗帜,在中国学术史、文学批评史上尚属第一次。与欧阳修首创“诗话”一样,徐英先生对于“诗话学”的首创之功,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然而,徐英先生的《诗话学发凡》,还仅仅只是一种“发凡”而已
,给人一种言犹未尽之感。也许徐老先生有其撰写《诗话学》之计划,
也许已经成书而尚未付梓,我们皆不得而知。但是《诗话学发凡》一文
的字里行间,已经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代表了前辈学者对“诗话学”
的呼唤。正是如此,为继承前辈学者的未竟之业,亦考虑到除了中国诗
话之外尚有古代朝鲜诗话与日本诗话的客观事实,我在八十年代中期撰写《中国诗话史》之时,便在序言中率先提出创建“东方诗话学”的主张,且将这种主张变为现实,九十年代伊始,一部曾为徐英先生命名的著作《诗话学》问世。从《诗话学发凡》到《诗话学》问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凝聚着无数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滴滴心血,也算是我们递交给前辈学者的一份并不以为满足的答卷。
在诗话研究中,我之所以要为徐英先生标举的“诗话学”张目,主
张替诗话立“学”,而不沿用大家熟悉的“诗学”之名,主要是出于以
下较深层的理性思考:
其一,西方有“诗学”,自亚里斯多德《诗学》问世以来,“诗学”之名便成为西方文艺理论之通称。人们说“西方诗学”,就是称西方文艺理论,而西方文艺理论又主要是以戏剧学与叙事学为其中心的,是一种广义的“诗学”,与中国人所理解的狭义的“诗学”,其概念的内涵是颇不相同的。我们认为,中国人没有必要跟随于“西方诗学”之后亦步亦趋,削足适履,勉强去建立一门与“西方诗学”完全不同的狭义的“诗学”。倘若以“中国诗学”命名,可能会在概念之内涵与外延上与“西方诗学”造成混乱。
其二,中国虽然亦早有“诗学”之名,但其概念内涵大凡有二:一是“《诗》学”,即“《诗经》之学”,以《诗三百》为研究对象,是研究《诗经》的专门学问,属于经学范畴,与现代意义上的“诗学”大相径庭。中国早在西汉时代出现的“诗学”,乃指“诗经学”,是一个特定的“诗学”概念。二是诗格之类诗学入门著作,如元人杨载《诗学正源》1卷,范梈《诗学正脔》1卷;明人黄溥《诗学权舆》22卷,溥南金《诗学正宗》16卷,周鸣《诗学梯航》1卷,等等。 这些名为“诗学”者,实皆为诗格之类诗学入门著作,与唐人诗格、诗式、诗法之类无异,与现代意义上的“诗学”有别。我们没有必要重复使用“诗学”这个概念,《诗经》之“诗学”耶?诗格之“诗学”耶?抑或现代意义之“中国诗学”耶?人们习称之“西方诗学”耶?半个多世纪以前,徐英之所以标举“诗话学”,而非“诗学”,也许正是出于这种逻辑思考。
其三,“诗话学”之名较之于“诗学”,其概念之内涵、外延的规
定性,更符合中国人谈诗论诗的文化传统和审美特性。一般认为,所谓
现代诗学,指的是研究诗歌艺术原理的专门学问。如本世纪之初出现的
一批以“诗学”命名的著作,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1929)、谢无
量《诗学指南》(1930)、傅东华《诗歌原理ABC》(1928)、 胡怀琛《诗歌学ABC》(1929)、范况《中国诗学通论》(1935)之类, 都是西风东渐的产物。此类“诗学”著作,只注重“论”,如同“诗论”一样。然而,中国人谈诗论诗,往往并不限于诗歌理论,还包括诗情、诗趣、诗本事、诗人生活方式等等,是诗的生活化与生活的诗化,是诗文化的升华。这种谈诗论诗的著作形式,就是诗话。诗话是中国、朝鲜、日本等流行的一种论诗之体,是“论诗”而非“诗论”,是东方诗文化的产物。有人建议我把“论诗之体”改为“诗论之体”,我以为不妥。因为诗话之述不仅仅是“诗论”,更多的是“论诗”,其实际功能要比“诗论”广泛得多。诗话之述,一般包含着诗谈、诗评、诗论、诗事、诗说、诗证、诗史、诗范、诗格、诗解、诗则、诗训、诗谱、诗句图之类,或各自有所侧重而已。“诗学”之旨,以“诗论”为归。其内容的单一性与诗话所呈现出的诗文化特色,是大异其趣的,因而并不符合中国人长期形成的谈诗论诗的文化传统和审美特性。当今学术界,把诗话等同于“诗论”,甚至把诗话纳入“诗学”范畴之中,实在是一大误会。
其四,诗话的学术价值所致。当今之诗话研究者,多从诗论的角度入手,注重从中发掘其“诗学”概念、范畴、范畴群乃至理论体系。这当然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从总体而言,如果诗话研究仅仅只限于这一个方面,即远远不够。诗话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诚如《蔡宽夫诗话》所云:“古今沿革不同,事之琐末者,皆史氏所不记,唯时时于名辈诗话见之。”诗话所表现的不仅是作家们的诗学观念,而且更多的是其史学意识、文化意识、审美意识;诗话的创作,是理性的自觉,但更多的是感性的体悟。诗话是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心态、审美情趣的真实记录和生动体现。中国文人以“余事作诗人”的态度作诗,又以“以资闲谈”的宗旨写作诗话,但始终体现了作家们所崇尚的文化观念。诗话所开创的这种论诗传统,深深打上了民族文化性格和审美情趣的烙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地域文化,形形色色的文化色彩给历代诗话涂饰了一层层亮丽的光泽。天地人合一,儒道释互补,真善美和谐统一,深邃的人生哲理,闪光的诗思感悟,优美的风流雅韵,真切的生命体验,复杂的文人心态,多彩的生活情调,无尽的闺思低吟,诗化的青楼红尘,浓郁的民俗风情,奇谲的道风仙骨,清妙的禅月诗魂,生动的语言艺术,文人之兴会,名士之风雅,诗家之逸趣,智者之顿悟,乃至名物典章,历史沿革,奇闻轶事,饮食起居,书画棋弈,声律音乐,茶道酒令,舞马斗鸡,花木虫鱼,都在诗话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述,诗话的字里行间,散发着非常浓郁的文化气息,充满着历代文人的诗外人生之思。从儒家文化、宗教文化到地域文化、民俗文化,从女性文化、青楼文化到音乐文化、饮食文化,乃至诗的文化传播,一切文化现象中凡涉于诗者,历代诗话都有生动的反映。许多诗话之作注重文化的阐述和诗人对社会人生的感悟体验,因而今天的读者仍然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与古代作家们心灵沟通,相知相缘,从中获得审美享受,把握诗外的人生真谛。诗话中连结古人与今人的情感纽带,正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正是这种种文化基因,才使中国诗话相续相禅,生生不息;亦使历代诗话的文化品味始终不失其民族面目。所以,我认为研究诗话的角度和方法,应该是呈现多元化的格局,不应该只是单一化的诗学研究。应该注重其文化学研究,或者作美学的研究,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审美语言学的研究,比较诗学的研究,民俗学的研究,宗教学的研究,等等。如果拘于一端,以西方诗学的尺度去衡量东方诗话,就可能挂一漏万,拾羽失鹏,甚至因为不与西方诗学相侔而形成某种偏见。我们提倡对诗话进行文化学的研究,注重诗话的文化阐释,是以诗话本身的文化价值体系为依据的。它不仅有利于诗话研究的思维空间的拓展,也有益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其五,关于诗话之“文体”。所谓“文体”,是指文章之体裁、体
制或风格。明徐师曾《文体明辨》云:“夫文章之有文体,犹宫室之有
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文各有体,此种“体”,是其内在结构与外
部形式的规则之表现。诗话是一种论诗著作形式,不同于一般的文学、文章之类,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笔记”。“笔记”以随笔杂录为特色,而诗话虽采用随笔体式,但始终围绕着“论诗”这个中心。从整体而言,诗话是文学批评之一种,不存在“文体”问题。非要言其“文体”,也就只能如章学诚、郭绍虞所说的“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两种随笔体式。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说“从文体上说,诗话几乎没有自己的文体”,而“缺乏内在结构与外部形式规则的东西不能成为学,诗话正是如此”。诗话确实没有“文体”,一般的文学批评著作,都只有郭绍虞先生所谓的“韵散二途”,岂能以“文体”论之?实在是混淆了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两种不同体制形态的根本区别。“诗话学”作为以诗话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门学问,与历代文人所标举的“诗经学”、“楚辞学”、“文选学”、“杜诗学”、“敦煌学”、“红学”一样,其建立之基础本不在于“文体”;即使是所谓“诗学”、“赋学”、“词学”、“曲学”、“戏剧学”之类,亦非以其“文体”为唯一标准。以学科面而论,当今之所谓“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比较文学”、“文艺学”乃至“经济学”、“生物学”、“化学”、“法学”等等,没有哪一个学科是以“文体”为依据的,主要依据就是其研究对象,任何一门学科或学问的创建,以其本身而言都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二是有自己的学科基地和专门人才,三是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以文体为依据,“文选学”等就会被扼杀;以文体为唯一标准,“诗话学”等同于狭义的“诗学”,实际上是不理解诗话而又苛求于诗话。事实上,中国古代没有一部符合西方诗学标准的诗学著作,以正统文学的诗文为研究对象的《文心雕龙》出现之后,所谓“诗学批评”则多以诗话这种论诗著作形式出之。因此,中国“诗学”的理论体系,亦只能通过诗话研究这一基本途径才能建立。其他选本、评点、笔记、序跋中的诗学内容,比诗话更为散乱无序,以它们为基点是不可能建立什么中国诗学体系的。否定诗话,无异于否定“中国诗学”。以单篇诗话而言,受传统文化和民族思维方式之影响,除《沧浪诗话》等等少数诗话之外,多数诗话于“诗论”或“诗学”的阐释不成系统,这也是事实。正因为如此,欲以建立中国诗学体系为己任者,则必须对数以千计的中国诗话(兼顾选本、评点、笔记、序跋中的诗学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总体研究,以宏观审视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的学术态势,通过对其概念、范畴、范畴群乃至系列的研究,才可能建立中国诗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特别是清代诗话的四大学说,即王士祯《渔洋诗话》的“神韵说”,沈德潜《说诗晬语》的“格调说”,袁枚《随园诗话》的“性灵说”,翁方纲《石洲诗话》的“肌理说”,都是中国诗学理论批评的集大成者。这样一来,“诗话学”的创立,不仅不会妨碍所谓“诗学”,而且更有益于“诗学体系”的创建。何乐而不为哉?
四 诗话呼唤新一代之崛起
“五四”以降,中国文论界受“欧洲文化中心论”之影响,推崇西方诗学而漠视中国诗话,卷帙浩繁的中国诗话被人们斥之为“鸡零狗碎”而备受冷落。徐英先生反其道而行之,率先标举“诗话学”;郭绍虞、钱钟书等前辈学者独具慧眼,为诗话之正名而据理力争。直至八十年代之初,郭绍虞在弥留之际,仍撰写了一篇题为《浅谈清代诗话的学术性》的论文,认为“清人诗话,也不必像章学诚这样说得‘可忧’‘可危’”。对于鄙薄诗话之论,钱钟书先生曾予以严厉批驳。《中国文学史·宋代的诗话》指出:“在各种体裁的文评里,最饶有趣味、最有影响的是诗话”,“后人瞧不起宋代的诗歌,因而把宋代的诗话也牵连坐罪。元初就有人慨叹说:‘诗话盛而诗愈不如古’;明人更常发‘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那一类议论。这种话只能表明那些人对唐人讲诗法的书无所知晓,至少是视而不见。”在《读拉奥孔》中又说:
一般“名为”文艺评论史而“实则”是《历代文艺界名人发言录》,
人物个个有名气,言谈常常无实质。倒是诗、词、笔记里,小说、戏曲
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
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值不得搜采和表彰,充其量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再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更不妨回顾一下思想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用而未失去时效。……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这是对那些崇拜名牌理论著作
而轻视中国诗话的浅薄之见的莫大讽刺!
千年诗话,饱经沧桑,而历久不衰,且早就走出了国门,这个客观
事实充分说明诗话之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总体而言,在中国古代文
学理论批评的各种样式之中,诗话之体还是幸运的。然而,诗话未来发
展的命运如何,不仅系之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系之于诗话本身
的文体优势,更系之于中国学界的新一代。
诗话呼唤新一代之崛起!这种“呼唤”主要包含三个基本层面:一是人才,二是创作,三是研究。以人才而论,在中韩日三国诗话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大批著名的诗话作家应运而生。日本有释空海、虎关师炼、石川丈山、依藤东涯、祗园南海、山本北山、西岛长孙、释六如、津阪孝绰、菊池桐孙、久保善教、古贺侗庵、市川世宁、田能村孝宪、大洼行、广濑淡窗、川路柳虹、三木露风、吉川幸次郎等;古代朝鲜有李仁老、崔滋、李齐贤、徐居正、李济臣、许筠、梁庆遇、洪万宗、南龙翼、南羲采、朴永铺、金渐、李家源等;而中国更数以千计,大凡历代文学臣匠、学术大家,从欧阳修、司马光、陈师道、叶梦得、姜夔、严羽到王夫之、王士祯、叶燮、沈德潜、袁枚、赵翼、翁方纲、纪昀、章学诚,从陈衍、梁启超、林昌彝到郭绍虞、罗根泽、钱钟书、钱仲联、台静农等,无不与诗话结下不解之缘。其中钱钟书先生更以《谈艺录》这部里程碑式的诗话之作为自己的学术起点,成就了一座巍然屹立的“学术昆仑”。我们说,诗话呼唤新一代之崛起,就是期望新的一代诗话大家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主张运用“诗话”这种传统形式来谈论新诗或旧诗,以指导新旧两种诗体的创作实践,记录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心灵感悟。诗人流沙河的《流沙河诗话》,就是现代新诗话的一个突出的范例。如冒景璠督钱钟书先生撰诗话时所言:“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谈艺录》卷首)。广大诗人、文艺家以及一切爱好诗话的学者们,若能集其谈诗论诗之语而为诗话,传统诗话之宏扬,新诗话之崛起,也就指日可待了。这是中国诗话的根本出路之所在。
学问者,乃天下之公器也。诗话研究,是中外学者共同的学术事业
,绝非是一种个人的或派别的行为。中国诗话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一
种广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因此,诗话研究也应该注重本身所具备的开
放性特点,以中韩日三国诗话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学术坐标,以东方诗话圈为时空范围,以西方诗学和印度梵语诗学为参照系,运用多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旨在建立能够与西方诗学并驾齐驱的“东方诗话学”。其学术前景是相当广阔的,然而,作为一门新的跨国性的学问,“东方诗话学”的创建与完善,远非一人之力、朝夕之功可以奏效的,而是需要一代或几代人为之长期努力,特别是中、韩、日三国诗话研究专家的共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