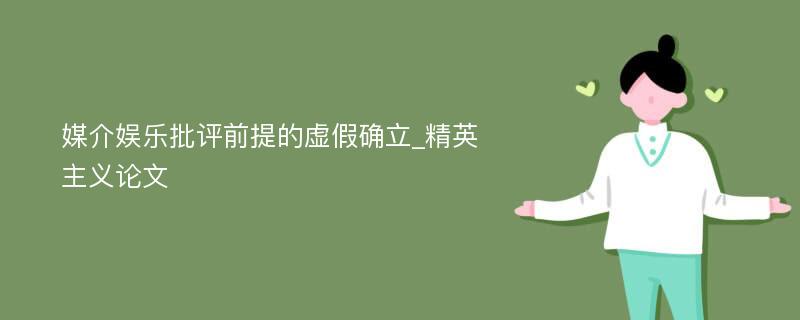
媒体娱乐化批判中的前提误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提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和《玫瑰之约》为滥觞,国内媒体迅速掀起娱乐浪潮。央视也相继推出《幸运52》、《开心词典》、《非常6+1》等大型娱乐档节目。当下,随着“超级女声”、“梦想中国”等大众参与性娱乐节目收视率的一路攀升,娱乐化电视节目以其平民化、生活化和轻松化的姿态,把普罗大众引向一个高昂的狂欢年代,媒体也进入一个“娱乐新时空”。
伴随于此,学界对媒体娱乐化的批判声音也日益凸现。
然而,在这些批判声音中,存在四大前提误设:一是受众的误设;二是传播者的误设;三是媒介本身的误设;四是传播效果的误设。这种“自己立个菩萨自己拜”导致的后果是,当前不少媒介批评者对娱乐化和其影响作了无谓的夸大。所谓误设,就是进行错误设置。前提误设,即指错误地设置了所讨论话题的前提,从而导致问题的讨论失去逻辑起点和现实意义,所得结论也漏洞百出,不堪推敲。
一、对媒体受众误设的批评
有学者认为“快乐的媒介培养了受众的顺从心理,削弱了他们的辨别力和对社会的批判精神”[1],尤其是面对新闻的娱乐化倾向,认为是“对新闻的意淫”[2],他们看来,中国受众在娱乐化的“拟态环境”中,在娱乐化的轮番轰炸下,很容易盲目跟风,全盘接受,沉迷于简单的快乐中不能自拔,从而丧失思考和批判的能力。
这种批判显然缘于如下推理:媒介娱乐化容易使受众顺从和堕落——现今的媒体是娱乐化的——所以,现今的受众容易顺从和堕落。在这个逻辑链环中,可以看出媒介批评者分明给自己设置两个错误的前提:一是娱乐化必然使受众走向顺从和堕落,受众都是缺乏批判能力的、是被动而非能动的;二是用笼统的受众概念代替有差别的受众。
1.受众在娱乐面前走向顺从和堕落——受众能力的误设
认为受众缺乏批判力,会在娱乐化的浪潮面前变得庸俗或沉迷,并必然走向顺从和堕落,这实际上是一种单向传播观念,是早先“魔弹论”的翻版。
“魔弹论”(也称“皮下注射论”)认为,大众传媒所面对的受众就像整齐划一的靶子,被媒体发射的新闻信息“魔弹”击中后应声倒地,毫无反抗。实际上,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经历不同,个人的天赋、心理结构、素质、价值观等均不尽相同,根本不存在完全等同的受众。“个人差异论”、“社会分类论”、“社会关系论”以及克拉帕的“有限效果论”、拉扎斯菲尔德的“二级传播效果论”,均已发现并指出“传播者将讯息传向受众的过程中,传播不是注射式和直接的,必须通过中介因素”[3],这就宣告了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魔弹论”的破产。
对受众能力的误设重蹈了魔弹论之覆辙,无视受众作为主体的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也就无形中夸大了娱乐化的影响和威力。
2.受众是无差别的群体——受众结构的误设
泛娱乐化的倾向的确会导致一部分人麻木和庸俗,但是这部分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受众。受众是一个多层次存在的社会群体。因此,要讨论娱乐化对受众所产生的影响,必须针对具体的对象和群体进行讨论,空泛地、抽象地说娱乐化所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不科学的。这种笼统地讨论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影响,其模糊认识有:
一是没有弄清楚受众的内涵层次。受众按照规模具有三个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特定国家或地区内能够接触到媒介信息的总人口,这是最大规模的受众;第二个层次是对特定媒介或特定信息内容保持着定期接触的人;第三层次是不但接触了媒介内容而且也在态度或行动上实际接受了媒介影响的人”[4]。
由此可见,并非所有受众都会对娱乐进行定期接触,都会在态度和行为上受到娱乐化的影响,更不是任何受众都产生负面效应。
二是把受众混同于一般的大众。现代意义上的“受众”,是报纸读者、广播听众、电视观众和上网者的统称,是随着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而产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过去那种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失去了统一的行为参照系,变成了孤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即所谓‘大众’”[5]。我们所说的精英人群、普罗大众同属于受众行列,精英人群分为“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传媒精英”[5],普罗大众也是有三六九等之分的。可以看出,受众并不等同于大众,且大众当中的部分受众是具有智慧的群体。
因此,受众是具体而非抽象、有层次而非笼统的群体,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娱乐化对不同受众所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拉扎斯菲尔德在“舆论领袖”理论中认为:大众传播的流程为“大众传播——舆论领袖——普通受传者”。这就告诉我们,受众里面不乏有智慧的群体。
3.普罗大众和精英人群要看同样的节目——受众需求的误设
这种误设认为,受众都应该是高雅的,受众也应该过着跟精英阶层一样的精神生活,研读四书五经、欣赏高雅艺术……批评家们用精英人群的生活习惯、审美观念、行为方式来框套普通大众,企图让受众远离娱乐,实在是一种“位置迷误”。
文艺学的新批评理论中,称“过分偏重作家创作意图的文学批评为意图迷误,过分偏重读者心理反应的文学批评为感受迷误”[6]。借用此,“位置迷误”就是把受众放到了其本不该处的位置进行批判和审视。
这样看来,用少数精英群体的生活标准和要求,来衡量普罗大众的生活标准和要求,把其放到精英位置进行批判,显然是方枘圆凿,标准混乱。这就如同,要求普通大众整天抱着《红楼梦》、读着《尤利西斯》,整天关注国计民生、眼盯股市行情,整天思索国家命运,社会前途,是不合理也是不可能的。鲁迅曾言,“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里会知道北京捡煤渣的老婆子的辛酸,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中的焦大也不会爱上林妹妹”[7]。
二、对传播者误设的批评
有媒介批评家认为:“新闻娱乐化也会导致媒介放弃其社会责任,因为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对于娱乐化的追求必然要导致庸俗化的倾向,媒介在维护正义、劝人为善的名义下,利用人们猎奇的心理,大肆将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公之于众,只是在结尾处象征性地加上评论,还美其名曰以此为鉴,以防后效。在这一过程中,以防后效的目的没有达到,受众的猎奇心理倒是得到了满足,媒介的利润也大幅飙升”[1]。
此观点很有代表性,有意无意地认为媒介控制者是不及格的把关人,在经济利益的刺激和驱动下,媒介成为赚钱机器,媒介控制者成为纯粹的商人,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另一方面,由于娱乐的冲击,媒介控制者正在偏离社会主流观念。这实在是对占有并使用媒体的新闻传播者一种极大的认识偏差:
1.传播者仅仅是赚钱的商人——传播者传播动机的误设
前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现任清华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院长的范敬宜,在谈到社会责任时说:“我们新闻工作者更应该自觉地时时刻刻把维护社会稳定当作自己的生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像爱护自己的婴儿那样来爱护它,不使它因为自己的些微不慎而受到损伤”[8]。
现代都市报的鼻祖、华西都市报的创始人席文举,在其整合型媒体理论中提到,“一个市场化的强势媒体,能够给读者提供丰富的信息,拥有巨大的发行量和受众群,可以吸引大量广告来获取丰厚的收入……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媒体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根本立足点在于媒体不仅创造经济价值,更要创造社会价值。社会价值是媒体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9]
体制内的媒体领导者如此,体制外的如何呢?凤凰卫视的“角色定位是‘拉近全球华人距离’,媒体理想是‘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10]。这是缔造凤凰奇迹的凤凰总裁刘长乐一贯提倡的媒体责任意识。再看阳光卫视,其定位就是要以历史、地理、人文和科学的传播为宗旨,致力于提升文化传播。
可见,大众传播媒介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使命,自觉承担着文化传承、舆论监督、沟通交流的作用。娱乐,仅仅是传播者所传播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远非全部。
2.媒介传播者缺乏主流观念——传播者文化结构的误设
媒体批评者认为,传播者在娱乐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各行其是,偏离了社会主流观念。
维护主流文化、尽量避免冲突、保护权力精英被认为是当今社会的三种主流观念。在中国,偏离以上三原则的大众媒体是无法生存的。
主流文化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一是意识形态层次,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当今社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大众传播,都是国家和政府所不容许的;二是传统文化层次,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潜移默化地指导着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违背传统文化的大众传媒是不可能得到大众认同的。
避免冲突从行业内外进行分析:行业外部,若大众传媒不能很好地同政府和其他行业进行有效的合作和沟通,则很难有效利用新闻资源,即“新闻环境资源、新闻信息资源和新闻受众资源”[11],甚至会遇到对抗;行业内部,若冲突不断,则很难找到合作媒体,很难共享信息资源。
保护权力精英的分析:权力精英们掌握着国家资源,牢牢控制着国家机器,若不能很好地维护他们的利益,甚至背道而驰,则很可能得不到政策的扶持,甚至直接被行政权力所取缔。因此,我们的大众传播媒体,无一不具备当今社会的主流观念,否则,就意味着不可能有很好的市场发行量以及市场潜力,也就意味着市场空间的萎缩和前途的堵塞。尽管媒介在娱乐传播中大张旗鼓,但仍然保持着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遵循。
三、对媒体自身误设的批评
媒体误设是媒体批评对媒体本身的错误判断,媒介误设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即认为媒介把娱乐当作核心、媒介中只存在新闻媒介和新闻媒介只有通俗的大众媒介。这三个误设的原因对在内容、新闻媒介和大众媒介的概念认知失误。下面我们对三个误设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
1.媒介把娱乐作为核心,除了娱乐还是娱乐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误解。实际上除了纯粹的娱乐报刊外,其他的很多媒介往往都是把娱乐资讯放在版面的次要位置,而将重要版面让给主流新闻。我们从报道领域的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正是市场的抉择。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今后传媒竞争的焦点,将在于经济报道,而不在于一般报道,特别是娱乐报道”,原因是“市场力量已经成为今天左右社会前进、左右人们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力量之一,或者说基本力量之一”[12]。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媒介为娱乐新闻或报道提供一定的版面和时间,也有它的合理性。美国学者C.R.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中,围绕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问题提出了“四功能说”,即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5]。赖特认为大众传播的一项重要功能是提供娱乐,尤其是在电视媒体中,娱乐性内容占其传播的信息总量的一半以上。
还有的学者指出,从个体和狭义的概念看,中国传媒应分成两大类:一类为公共性传媒,而其中又可分为重要新闻传媒、一般新闻传媒、具有显著思想文化特性的传媒;一类为经营性或市场性传媒,主要为实用性、服务性和纯娱乐性的传媒[13]。新闻娱乐化的领地主要在第二类经营性和市场性传媒。并且即使这类媒体,娱乐化内容也不是一统江山,还有服务性和实用性等更为重要的内容存在,占着不小的比重,那些认为新闻娱乐化已经泛滥成灾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实际。
2.所有的媒介只是新闻媒介
事实上,媒介不仅仅只是新闻媒介,还有非新闻媒介,如出版印刷、学术期刊、文学期刊、科学期刊等表达精英文化的出版物。很多学者都有类似的看法:大众传播媒介是在传播过程中用来传递讯息的居间工具,包括报纸、杂志、书籍等印刷媒介和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14]。在这个地方,媒介批评者们所犯的错误是将媒介的概念理解得过于狭隘了。
有的学者指出:“对于商业性或具有商业化倾向的媒介,市场逻辑成为主宰,发行量、收视率等标志着受众群的量的指标,已成为生命线”,“在这样消费逻辑引导之下的媒介自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娱乐化倾向”[15]。所以,在当今的社会现实条件下,大众传媒的娱乐化,包括新闻娱乐化有一定的合理成因在里面。
3.新闻媒介只是通俗的大众媒介
其实新闻媒介有很多种类,如党报党刊等,还有很多面向精英阶层的报刊,它们不大可能走向娱乐化。有的研究者在自己的媒介批评著述中说:“论文题目中的‘媒介’,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16] 这就将媒介的概念内涵限制得过于狭隘。前面已经分析过,都市报之类的报刊由于市场取向的原因,娱乐化成为其立足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但作为党报党刊来讲,由于其肩负的重要的宣传功能和导向作用,它就不可能像其他报刊那样随随便便地进行娱乐化的运作。
在很多学者看来,都市报之类的传媒被看作不入流的,是边缘化的。法国思想家鲍德利亚指出:大众文化与其说是将艺术降格为商品世界的符号的再生产,不如说它是一个转折点,终结旧的文化形式,并将符号和消费引入自身地位的界定之中。所以,传统批判理论指责大众文化被框定在极度的消费主义之中,风格千篇一律的刻板单调和平庸陈腐,是无的放矢。
新闻娱乐化同样可以看成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对新闻娱乐化的指责也可以说是有失偏颇的。大众传媒将新闻娱乐化就是将大众的符号引入自身地位的界定中,以此同精英文化区别开来。从某种程度上说,大众传媒将新闻娱乐化是在履行自身应有的职责。
四、对传播效果误设的批评
传播效果误设是媒介批评前提误设的最后一个方面。传播效果问题是与实践结合最密切的研究领域。传播效果研究的实践性和实用性决定对其的错误研究必然导致对实践的错误指导。很多媒介批评者有这样的认识,即接受主体会对新闻娱乐化内容全盘接受,接受之后接受主体会愈加堕落。有的学者所说新闻娱乐化会使“人们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逐渐对社会现实产生麻木的心理,进而丧失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批判。快乐的媒介培养了受众的顺从心理,削弱了他们的辨别力和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将接受主体作为一种单一的媒介接受方看待了,没有看到接受主体其他行为角色。
传播学上有很著名的由卡茨提出的“使用—满足”学说认为,接受主体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要求和兴趣来决定的,人们使用媒介是为了满足个人愿望和需求。换言之,效果的衡量和确立应围绕着受传者。从复旦大学教授张国良的一项受众调查研究来看,受众关注的信息类型主要是与工作、生活相关的信息。地区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样看来,就算大众媒介登载大量的娱乐化新闻,受众如果不需要,还是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现在学界对媒介的属性的认识一般是这样,作为具有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生产者,新闻媒介从属于上层建筑,又属于信息(娱乐)产业……既然新闻媒介有产业的属性,那么新闻媒介的产品必然面临要获取经济效益的问题。市场经济对媒介而言的最大变化是在消费领域确立了新闻产品的“消费者”——受众的主体地位,在生产领域确立了媒体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者的地位,新成立的都市报市场化程度尤其高。于是媒介从原来绝对意义上的“引导”受众转到“引导”与“迎合”并存,市场理念开始与新闻理念并重甚至超出。
那么什么样的媒介产品才能赢得受众的欢心呢?大众传媒要赢利,必须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以换取广告融资。作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现代媒体,它的产品生产和销售同样执行着经济学中的“大数法则”(law of large number)和通用法则,即什么商品最好销,消费群最大,就生产什么;哪些商品投入小产出大,就着力经营哪些商品(新闻)。新闻虽然不是商品,但它具有商品性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大众传媒究竟以什么样的新闻吸引大数的受众,让“产品”易于销售从而提升广告经营呢?“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假设受众的智能有限,喜欢娱乐,而对深入探讨任何课题不感兴趣”。
五、结论
无论是从受众本身还是从传播者本身,从媒介本身还是媒介传播的效果来看,都应当在正确的前提下讨论媒体娱乐化,不能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同时也要看到,娱乐属性是新闻媒介的内在追求,娱乐化的倾向是具有合理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