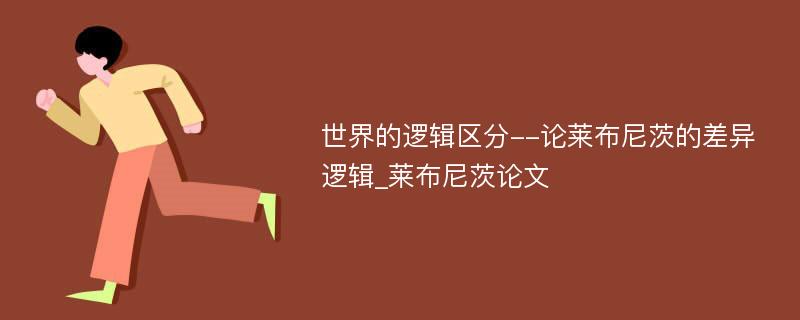
世界的逻辑区分——--论莱布尼茨的差异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差异论文,世界论文,论莱布尼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3)03-0318-05
逻辑学是莱布尼茨哲学体系的基础。然而,人们对莱布尼茨逻辑学的研究多是突出它与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关联,以及对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意义,至于它自身的特征却疏于研究。我们认为,莱布尼茨的逻辑学实即一种差异的逻辑学,其特征就是从观念本身出发,对事物进行了先验的逻辑区分。
一、对事物的逻辑区分
在莱布尼茨看来,真理就表达在主谓命题中,而凡主谓命题又都是蕴涵着的,即任何谓项都是内含于主项之中的。但无论是主项还是谓项,从逻辑上看,它们又都是由观念或概念构成的,主谓命题所表达的是观念之间的某种蕴涵关系。
但何谓观念呢?他认为,所谓观念就是一种指向事物,并把事物思维着的带到近前的能力,同时它本身还是对事物的一种表达,从中能推论出对应于外部事物的真理。不惟如此,观念还具有区分和辨别事物的功能,而根据其分辨程度的不同,它就被划分为明白的和模糊的,清楚的和混乱的。例如,“一个观念,当它对于认识事物和区别事物是足够的时,就是明白的;好比当我对一种颜色有一个很明白约观念时,我就不会把另一种颜色当做我们所要的颜色,而如果我对一棵植物有一个明白的观念,我就能把它从邻近的其它植物中辨别出来;否则观念就是模糊的”[1](第266页)。而一个观念要是清楚的,则仅仅能“使一个对象和另一个对象区别”开来就不够了,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把那些被很好地区别开的、也就是本身是清楚的、并且区别着对象中那些由分析或定义给与它的、使它得以认识的标志的观念叫做清楚的;否则我们就把它们叫做混乱的”[1](第267-8页)。莱布尼茨认为,清楚的观念与金匠所具有的金子的观念相似,而他的这种观念就是“建立在区别开来的特征和化验员试验结果基础上的,它足以把金子从其它相似的物体中区分出来”[2](P.284)。
清楚明白的观念这种区分事物的功能,在逻辑上,主要是通过对观念下定义来实现的。对观念的定义可以沿两个方向进行。一是向上从较低的种出发,不断追溯它所在的属,并对这些属进行区分、归并,直至最后把它归于一个最高、最普遍的属为止。这个最高、最普遍的属,在莱布尼茨那里,就是上帝观念。二是向下从属出发,对该属下面的种不断进行划分,直至最后,达到一个不可再划分的“最低的种”。当然,对于这一过程,“只要还存在着某个种的至少有一个成员自身具有而别的成员不具有的特征,那么继续再分下去就是可能的”[3](第73页)。这样,从最高的属到最低的种,一个作为整体的观念“树”、观念网络便形成了;而在这棵“树”上,在这个网络中,任何一个具体的观念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在它与其它观念的关系中显示出自己的清楚明白程度,展示出自身区分事物的逻辑功能水平。
在这个观念网络中都是连续的、充实的。莱布尼茨指出,有两个不同的类,它们的种差的划分是有区别的。在第一个是数学的或逻辑学的类中,种差是以量来确定的。如根据“单纯的差”,“最小的一点不相似”,“使两个东西根本不相似的一点最少的区别,就使它们有了种的区别”了[4](第338页),例如椭圆和曲线,就由于数量大小而“有无穷数量的类或种,而每一个种之中又有无穷数量”[4](第339页)。在第二个是物理学的或实在的类中,种差不是以量而是以本质来确定的,种差是根据为一定的个体所共同具有的固有属性来划分的。而且,一旦种差确定了以后,就不必再去进一步去寻求个体之间的差异了。例如人这个类,我们只要以理性这种本质属性作为区分人与动物的种差就够了,而不必再在人这个类之中,去寻求其他的属性的划分了,因为无论人们如何变化和人体差异有多大,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来判断,在人们之间,照内部的真实情况,有一种本质的种的差别”[4](第363页)。
二、可能世界和个体的区分
在所有的观念中,实体的观念十分突出,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与其他观念的差异。实体观念的这种突出特征就是,它只能做谓项的主项,而不能再做其他主项的谓项。也就是说,实体是单纯的、独立自存的,它的观念就包含着它的全部谓项或属性,而它本身并不被包含在其他实体的观念之中。
在莱布尼茨看来,这样的实体观念就是上帝观念和个体实体的观念。上帝,作为最完满的存在,是包容一切的,一切也都只不过他的谓词而已;而个体实体,作为创造物,虽然其实在性不如上帝那么大,但却也是完全的,以至于其一切属性都是内在于它的观念本身,就“足以完全理解这个实体和推论出这个实体是其所是或可能成其所是的所有谓项”[2](P.300)。从逻辑上看,上帝作为最完满的存在,是自身一致、不自相矛盾的,并且是最大的可能的;上帝还是惟一的,不可能有多个上帝的观念,上帝作为最大的可能性,也不允许再设想有比他的可能性还要大或还要小的上帝,否则就自相矛盾了。上帝作为上帝,只有一个。和上帝观念不同,个体实体的观念则可被设想为是无限多的;相应的,由个体实体组成的世界也是无限多的,至少在上帝的理智中,是可能存有无限多个可能的世界和个体的。然而,在无限多的可能世界和个体的差异,上帝又是根据什么而把它们区分开来的呢?
在莱布尼茨看来,上帝是根据一定的目标、计划,按一定的秩序来设想世界的,世界即他的这些设计、规划的产物:这“恰如一个建筑物的观念源自于建筑者的目的或设计一样,这个世界的观念或概念就源自于被上帝视为可能的设计。因为任何事物都应当用它的原因来解释,而对于世界的原因,则可以在上帝的目的中找得到”[5](P.108)。另一方面,上帝不仅依据于一定的目的、计划而构思世界,他还根据无数种法则来设想世界,其中“一些法则适用于这个世界,另外一些法则适用于另一个世界”[5](P.108)。由此可知,根据不同的目的、计划和法则,无限多的可能世界便能够区分开了。
随着不同的可能世界的形成,无限多的可能个体也就随之区别开了。在莱布尼茨看来,世界即是可能个体的集合,但它不是杂乱无序和任意的,否则任何一种集合都是可能的,都是无差别的。相反,这种集合必定是符合一定的原则,即符合和遵从上帝对于世界的规划和律令的。另一方面,那些能够遵从相同的原则和规律的个体还不能是相互矛盾、彼此排斥的,而必定是相互一致、彼此融合即可共存的。因为惟有这样,它们才可能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可能世界,那些不能够适应这些规律或法则,且与这个世界的个体相互排斥、不可共存的个体,肯定是被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的,虽然它们也可能由于能够适应其他的原则和规律,而集结、共存在一起组成其他的可能世界。这样,根据这种逻辑上的可共存还是不可共存,是相互一致还是彼此排斥,我们就可以把隶属于不同世界集合体的个体区别开了。
可共存性虽然能把不同世界的个体区分开来,但却不能把同一世界的个体区别开来,因为可共存性对于同一世界的个体而言,只标明了其同一性而根本就无法显示出其差异性。但诸个体肯定不会是毫无区别的,世界也决不会是铁板一块。问题是如何区分开诸个体,或如何确定诸个体之间的差异?
对于同一世界的个体,我们可以按其所属的不同的类将它们区别开来,因为,类概念作为一般的本质概念,借助于它,至少能够把属于它的诸个体与不属于它的诸个体辨别开来。如借助理性动物这个类概念,就能把个体的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但借助于类概念对诸个体的区分是有限的,因为它不能将同类的个体区别开来,例如对于我和他人而言,“为了理解我是什么,仅仅意识到我是一个思维的主体是不够的,我还必须清楚地想到所有那些把我与任何其他的可能的精神区别开来的东西”[5](P.126)。
如何能比较彻底地确定个体间的差异呢?首先,上帝是从世界整体出发,从一切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联系,而非从某个孤立的个体出发,来设想并创造每个个体的。例如,对于亚当,上帝就是在考虑好了整个世界系列之后,才形成了关于他的判断的,他关于亚当的判断,只不过是“他就整个世界和原则上的规划而做出的决断的结果,那些原则上的规划规定了世界的原初概念”[5](P.109-110)。另一方面,按照上帝的设计,世界又是通过每个个体来表现的,即通过处在每个具体位置上的、每个特定视点上的个体来表现的,而凭着它在世界整体中的这个位置、视点,每个个体就把它和其他个体区分开了,因为正是这些不同的位置和视点决定了不是那个而恰恰就是这个,不是某个不确定的而恰恰就是这个确定的个体才真正适宜于此表现、展示世界整体。换言之,世界整体的表现是绝对不一样的。
其次,就个体本身而言,它的概念“包含着和整个事物系列的关系”[5](P.104),包含有它在实际存在中的各种状态,以致凡在世界中发生的一切,凡它自身所经历的任何事情,都作为它的谓项从属于它,都能在它的概念中被发现。另一方面,个体的概念也是特殊的。它不过是整个事物系列上的一个环节、整个世界网络中的一个纽结,或者说,是一面从自身所处的特殊位置和视点出发去表现整个世界的镜子。这样,个体作为特殊的事物,它实际上已经从世界系列中被分辨出来,已经从事物的关系中被区分出来,已经在特定的位置上与其他的个体区别开来了。莱布尼茨看来,每个个体的这种特殊性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于它、包含于它的完全的概念之中的,是作为它的属性、谓项隶属于它,能为它本身所表现的。我们只须对个体的概念进行分析,只要分析到一定的程度就能够发现它的特殊性,找到它与其他个体的差别,从而也就能在逻辑上将它与其他个体区分开来。然而他认为,对个体概念的分析是不可能像分析三角形那样被穷尽,从而能够达到对它的清楚明白的意识的;严格说来,只有上帝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他才有关于个体的清楚明白的观念,从而也只有他才能把它们区别开来。而个体作为有限的个体,是永远达不到上帝那样的清楚明白程度的,它对于自身与其他个体的差异性往往“只有混乱的经验”[5](P.116),而这也就决定了,它是无法完全清楚明白地把自己和其他个体区别开来的。
在莱布尼茨看来,不仅可以设想无数个不同的世界和个体,而且还可以设想无限多个各不相同的同一个体:例如亚当,如果我们只一般地设想他的一部分谓项,例如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人,他被放进了伊甸园,上帝用他的一根肋骨创造了一个女人等,并且“如果我们把这些谓项归属于他的这个人就叫做亚当的话,那么,所有这些并不足以就确定这个个体,因为,可能存在有无数个亚当,也就是说,适用于这些属性的可能的人有无限多个,而这些人相互之间是不同的”[5](P.110)。这是因为,在所给定的只是关于个体的一般性条件的情况下,在逻辑上是可以设想出无数个可能个体的。例如,对应于不同的世界系列,相关于千差万别的关系网络,鉴于各异的位置关系,是可以相应地把这个一般的、不确定的个体分别予以定位和加以特殊化的,而随着这种特殊化,无数个不同的个体如亚当便产生了,并且只要与之相关的具体条件有任何一点细微的差别,都将使被特殊化出来的是一个不同的个体。但同时,这个被特殊化了的个体与这个世界系列的可共存性,它与这个世界关系网络的契合性,它在某个位置上的恰当性,都能把它与另一个可共存于另一个世界的、和另一个关系网络相适合,和另一个位置相适宜的与其相似的个体区别开来。当然,能够完成这一区分的就只有上帝了。
三、事物的可辨别性
从包含了其所有谓项的完全的个体实体概念出发,莱布尼茨还论证了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则,亦即世界事物的可辨别性原则:“存有两个完全相似的或仅在号数上不同的个体是不可能的”[5](第128页),所谓完全的无差别状态只是一个幻想,因为,“如果两个个体是完全相似和相等的,并且是凭本身不能区别的,那就不会有什么个体性原则;我甚至敢说在这种条件下,就不会有什么个体的区别或不同的个体”[1](第234-5页),相反,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叶子”一样[6](第39页),一切事物和其他任何事物都是有区别的,从而都是能够予以辨别的。
从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则出发,莱布尼茨认为,仅仅用时间和空间来辨别事物是不够的,还必须诉诸于事物本身。他说,“虽然在我们就事物不能对它们很好区别时,时间和地点(也就是外在关系)可为我们用来区别事物,但事物仍然是本身可区别的”[1](第233-4页)。也就是说,“除了时间和地点的区别之外,永远还必须有一种内在的区别原则”[1](第233页)。另一方面,在莱布尼茨那里,空间和时间不是某种绝对的、实在的东西,而是某种相对的、观念性的东西,它们不过就是事物共存与连续性的秩序和关系。因此,与其说事物可以借时间和空间来加以辨别,毋宁说是“通过事物来对一个地点或时间和另一个地点或时间加以区别的”[1](第234页),时间和空间的区别以事物的区别为前提,我们只有在先行辨别开了不同的事物之后,对事物的秩序和关系即时间和空间的辨别才是可能的,而不是相反。
事物是不同的,从而是可辨别的,这一点从个体实体概念本身可以得出来。一方面,个体实体概念作为完全的概念,就包含着它和其他个体实体的关系,整个世界就能在它的属性中得到表现。另一方面,作为特殊的概念,它又是从特定的视点、特殊的位置关系上对整个世界加以表现的,且世界在这个视点、这个位置上的恰当表现,也只有这个特殊的个体是真正适合的。同样,在其他视点、其他位置上恰当表现这个世界的其他个体,也都肯定是惟一的,是被上帝一次性安排好、定位好了的。所以说,个体之间就是可区分和可辨别的了,因为不可能有相同的两个个体在同一视点、同一位置上去表现这个世界,在这个视点、位置上去表现这个世界的惟一性,决定了只可能有一个个体适宜表现它:也不可能有相同的两个个体在不同的视点、位置上去表现这个世界,视点、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适宜在不同视点、位置上表现的世界只能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除了由个体实体概念而来的论证之外,莱布尼茨还应用充足理由原则,论证了事物的可辨别性。从他关于充足理由原则本身的表述来看,则它显然是一条关于事物存在和发生的原则而非关于其一般本质的原则:而它与矛盾原则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针对只有一种可能性,其反面蕴涵矛盾、必然要发生的事情的,而是针对具有多种或至少有两种可能性,其反面并不包含矛盾、偶然发生的事情的。根据充足理由原则本身,在这诸多存在的可能性中,只有一种可能性能够成为现实,而这种可能性所以能够成为现实的理由,只有通过对这些可能性进行比较和辨别,在它们的差异中才能找得到。否则,如果这些可能性毫无差别、无可辨别,它们有同等的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则也就没有事情能够发生了。因为,那样一来,就没有理由决定,是这种可能性而不是那种可能性能够成为现实的了。正如一架天平,假如“两边完全一样,如在这天平的两端再挂上相等的重物,则整个天平仍然静止不动。这是因为没有一边下降而另一边不下降的理由”[6](第18页)。或者,即使有一种可能性成为了现实,而由于无论哪种可能性的现实发生都是一样的,漠然无差别的,则这种发生就只能归于一种盲目的必然性的支配作用了,只能归于一种宿命了。但所有这些显然是荒谬的和悖理的,因而事情决不会是如此发生的。
在莱布尼茨看来,关于两个无法分辨的东西的设想,抽象的说并非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是“和上帝的智慧不相容”,“因而是不存在的”。“因为选择总得有某种理由或原则”[6](第38页),但在事物毫无分别、在事情无论如何发生都没什么差别的情况下,是无法找到理由的,因而上帝就将是毫无选择、无所取舍的。这样,他就要么无所作为,要么就只有毫无根据地盲目行事了。但无论怎样,这肯定已经不是凭智慧行事的上帝的所作所为了。例如,设三个相等或完全一样的事物A、B、C。对于它们,共有六种不同的安排即ABC、ACB、BAC、BCA、CAB、CBA可供上帝选择,但既然它们都是一样的,则就可以用A或B或C而把这六种安排替换为AAA或BBB或CCC,而又由于AAA=BBB=CCC,则这六种安排最后就都可以替换为AAA。在这种情形下,上帝就无法在这六种安排中进行区分、辨别,从而无论他做出哪种安排就都是一样的。如果他于其中选择了一种安排,那么他的这种安排就是无理由的,如果他无从选择,则他就将是无所事事的,而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都将不是智慧的,他就不再是上帝了,因此,“把三个相等的和全部一样的物体安排成不论怎样的次序都是没有区别的,因此,它们决不会是只凭智慧行事者所安排的。但他作为造物主,也不会产生这样的东西,因此自然中也不会有这样的东西”[6](第38页)。这样,莱布尼茨就借助上帝,既论证了也确保了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事物的可辨别性。
收稿日期:2002-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