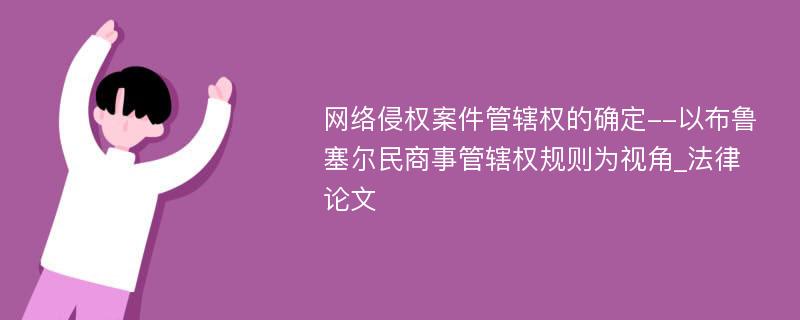
涉网侵权案件管辖权的确定——以《布鲁塞尔民商事管辖权规则》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辖权论文,布鲁塞尔论文,视角论文,规则论文,民商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涉网侵权案件管辖权的确定,因为争议案件所涉相关当事人和相应行为地点的认定,较之于传统侵权案件更为复杂的原因,不可避免地使传统管辖规则的适用面临着新的冲击与挑战,但是与合同争议案件管辖规则不同,欧盟在实现《布鲁塞尔民商事管辖权公约》向《布鲁塞尔民商事管辖权规则》演变的过程中,并未就相应侵权管辖条款加以变革,而是基本保留了原公约相关内容之规定。《布鲁塞尔民商事管辖权规则》第5条第3款规定,损害行为发生地或将可能发生地法院,就侵权行为、非法行为或准非法行为事项享有管辖权。与以前公约规定所不同的是,新规则明确认可损害行为可能发生地法院就侵权或类似行为的管辖权。① 显然此种可能行为地点的管辖根据,不仅具有确定临时或保全措施管辖权的意义,而且对保护争议案件受害人特殊利益,有着确定实质管辖权的重要意义。② 问题是规则本身与以前的管辖公约一样,并未就损害行为发生地或可能发生地加以界定,由此如何就损害行为发生地或可能发生地加以认定便成为问题的关键。③ 在涉网侵权案件之争中,有关行为地点的确定或识别这一确定侵权案件管辖权所需明确的问题核心之所在,较之于传统侵权争议案件而言,无疑会更为复杂而棘手。
一、侵权行为地管辖规则的继受与发展
尽管《布鲁塞尔民商事管辖权规则》是在网络技术手段对传统管辖规则形成冲击与挑战的背景下修订而成的,但是,规则本身并未就涉网侵权行为所引起的管辖权确定问题特别加以规定。由此,成员国法院在确定涉网侵权行为管辖权时,《规则》第5条第3款所规定的侵权行为地管辖规则,无疑将是有关受案法院据以确立管辖权的当然选择。
欧盟立法委员会在制定《布鲁塞尔民商事管辖权公约》时,并不觉得存在就侵权行为地到底指的是加害行为地抑或是损害结果发生地,这一适用该项管辖规则的核心问题予以明确规定的必要,相反,委员会选择在该问题的规定上,与法德等成员国所采取的规则保持一致,并不就此明确加以规定。④ 由此,公约有关侵权行为特殊管辖规则的规定,给缔约国受案法院留下了相当的自由,相应地也给公约的具体适用带来某种程度上的不确定性,这一做法在修订后的管辖规则中仍得到了延续。
(一)侵权行为管辖规则的适用范围
新管辖规则如以前的公约规定一样,未就构成适用该款内容之前提的侵权或类似行为的诉因或争议事实的识别问题予以明确。由此,特别是在关涉合同或不当得利等类似争议事项时,难免会出现到底是以合同争议为由援引规则第5条第1款的规定确定管辖权,还是以规则第5条第3款的规定为据而确立损害行为地法院对争讼案件的管辖权的问题。与此相关,还会提出对规则所规定的侵权行为应自动地赋予其以独立的含义,抑或依受案法院地国的国际私法规则加以认定的问题。⑤
对上述两个有可能成为援引管辖规则第5条第3款之规定前提的问题,从欧洲法院有关原管辖权公约判案实践分析,欧洲法院秉承应赋予侵权行为地以独立于成员国国际私法规则的自主含义之立场,认为不应将有关侵权事项的管辖规则扩展适用于与合同争议事项有关的管辖权确定之中,从而避免限制管辖规则第5条第1款之适用范围。欧洲法院在Kalfelis v.Bankhaus案中,应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请求判决指出,欧洲法院曾经在有关合同争议事项管辖规则的解释中主张,为确保公约的统一实施和对相关当事人的公平救济,不应简单地仅依据某一有关国家的国际私法规则而就公约有关内容加以解释。由此,对公约所规定的侵权、非法行为或准非法行为,应主要在顾及公约结构和宗旨的基础上赋予其以自主性的含义。而为确保公约的统一实施,必须认可公约所规定的侵权、非法行为及准非法行为,涵盖所有旨在寻求被告当事人承担责任,但又与公约第5条第1款所称合同争议不存在联系的诉讼请求的概念。⑥ 尽管法院在该案中强调如关涉合同争议事项时,应就公约第5条第3款有关侵权管辖条款的适用范围严格加以解释,而不致限制公约第5条第1款有关合同管辖条款的适用范围。然而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在涉及不当得利诉讼请求时,仍可能提出可否依公约第5条第3款之规定而确立损害行为地法院管辖权的问题。因为不当得利争议事实既有可能起因于当事人之间既存的合同关系,也有可能起因于某种单一的事实或加害行为。
有关不当得利管辖权确定所存在的疑问,最终在欧洲法院所审理的Tacconi v.Wagner一案中得以澄清。⑦ 在该案中,欧洲法院指出,公约第5条第3款所称侵权行为涵盖所有非起因于公约第5条第1款所规定合同意义上的责任类型。由此,只要不存在当事人相互间所自由议定的债务协议,违反善意缔约责任和不当得利的权利请求,都属于公约第5条第3款所规定的有关侵权行为的管辖范畴。此种以当事人相互间是否存在自由协议为依据,而就公约有关侵权行为管辖规则的适用范围加以解释的做法,在欧洲法院于稍后所审理的VKI v.Henkel一案中得到了延续。⑧
从上述欧洲法院的判案实践考察,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认为,欧洲法院有关侵权行为管辖事项的解释规则仍在发展演变之中,其适用范围似乎有扩大适用的趋势。只要争议事项并非起因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协议,无论是不当得利、人身伤害、诽谤,抑或是不当地使用他人商标等知识产权侵权事项,都在规则所确立侵权缘由管辖规则的支配之下。
(二)侵权行为地的确定
关于侵权行为地的确定,在原《布鲁塞尔民商事管辖权公约》和新的《布鲁塞尔民商事管辖权规则》中,都没有明确加以规定。考察起来,尽管欧洲法院在其判案实践中一贯强调管辖法院与争议案件之间的紧密关联性,欧洲法院就侵权行为地的认定,还是秉承了既可以是加害行为地电可以是损害结果发生地这一颇具灵活性的广义解释标准。
欧洲法院在1976年所判决的Bier v.Mines de Potasse d'Alsace一案,是一起对侵权行为地管辖规则所谓侵权行为地,较早加以解释的著名案例。在该案中,欧洲法院判决指出,加害行为发生地和损害结果发生地,在具体案件中都可以成其为确定管辖权意义上的重要联系点,公约第5条第3款所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必须被理解为既包括损害结果发生地,也包括引致损害的加害行为发生地。⑨
尽管相对于环境损害赔偿而言,在涉及诽谤、不当陈述等无形损害赔偿之诉时,因为加害行为地和损害结果发生地的多元性和认定上的困难,往往使相关管辖权的确定问题更为复杂而棘手,同时也更容易使确立特殊管辖权所要求的行为地与争议案件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分析的合理性受到怀疑。不过,从欧洲法院的判案实践分析,欧洲法院似乎并无意于区分侵权行为的不同类型而确立不同的解释规则。也许这种做法因在某种程度上减损了管辖规则的可预见性,并易于引致挑选法院而可能受到批评,⑩ 但是在相当程度上无疑维护了公约所确立管辖规则的一致性。
欧洲法院在前述Bier案有关实物损害赔偿权利请求之诉中所确立的,损害行为地既可以是加害行为地也可以是结果发生地的解释规则,在涉及非金钱之诉的Shevill v.Presse Alliance一案中同样得到了适用。(11) 欧洲法院在其判决中,将英国枢密院向欧洲法院所提出的七个问题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加以阐释:首先,当权利请求起因于在数个缔约国境内发行的报纸所载的诽谤文章之时,损害行为地点该如何加以确定?其次,受案法院在确定其是否可依公约第5条第3款之规定,以损害行为发生在域内而行使管辖权时,是以其内国法标准来确定侵权行为的存在,抑或是以独立于内国法律体系的特殊规则来确定损害行为的存在及其给受害人所造成的损害程度?简言之,该案所涉及的两个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损害行为地,以及如何确定损害行为的存在。
1.损害行为地的确定
关于损害行为地的确定问题,欧洲法院秉承其在Bier案中所确立的侵权行为地同时涵盖加害行为地和结果发生地的解释规则,在Shevill一案中强调指出,该种规则同样适用于非人身或金钱之诉,特别是因诽谤而造成的自然人或法人名誉毁损的管辖权确定之中。该案咨议官Darmon在其所发表的咨询意见中坦言,在诽谤案件中采用有别于。Bier案所确立的规则也许可避免复合管辖问题,但这将是以牺牲欧洲法院判案实践的一致性为代价的。(12)
欧洲法院进一步指出,在诽谤案件中加害行为地只能是所控报刊出版人营业机构所在地,因为该地是损害行为的起源地,也是在该地出现了诽谤言论并付诸出版发行。这一解释确实与普通法国家法院所奉行的将诽谤言论传播于第三人时才引致损害的实践有所不同,不过与欧洲法院向之所秉承的应对公约第5条第3款之规定,赋予独立于缔约国内国法律含义的一贯立场保持了一致。至于如何确定诽谤案件损害结果地的问题,受案法院认为该地应该是因不当行为而给受害人造成不利影响的地点。受案法院并没有将损害结果发生地,等同于受害人自身因诽谤言行而蒙羞或自卑的地点,因为这样将可能等同于授权权利请求人所在地法院享有管辖权。相反,诽谤出版物在所有知悉受害人的出版物发行各国造成损害后果。(13)
须强调指出的是,欧洲法院所认定的上述两类法院所享有的管辖权的权利范围有所不同,作为加害行为地的报刊出版人所在地法院,就所控诽谤言论所造成的一切损害享有管辖权,而无论受害人是在该国抑或是在他国遭受侵害。受案法院所确认的这一由被告人报业机构所在地法院行使管辖权的管辖根据,通常将与被告住所地法院相一致。由此,除非原告当事人选择在损害结果地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公约第5条第3款有别于公约第2条的管辖规定将无甚意义。与所控报业机构所在地法院享有类似于一般管辖的权利不同,后果发生地法院仅可就原告当事人在其境内所受损害的赔偿请求行使管辖权。不过,从理论上言之,只要在报刊发行地知晓权利请求人的存在,该权利请求人即可在每一个报刊发行国分别提起诉讼请求。的确,就裁判的公正性而言,每一个损害结果发生地法院都是最适于就其境内所发生的诽谤行为的构成及其相应损害程度加以认定的法院,但就其境外所受损害而言,则因该法院与损害后果间不存在紧密的联系而并非是最适宜的裁判法院。(14)
2.损害行为的认定
Shevill案所涉及的第二个问题集中在,受案法院是否需依有别于其内国法的特殊规则来判定争议行为是否有损害性,以及所控诽谤行为是否存在及其损害程度等问题的分析之中。该案被告抗辩指出,原告并未遭受构成损害行为的任何损害后果,事实上也不存在原告声誉确已受到侵害,以及那些知悉原告的人接触到该所控侵权晚报的任何证据。被告主张应该摈弃英国法上所认可的一旦存在诽谤行为,即可推定当事人承受损害结果的内国法规则,相反,为确保公约解释上的一致性,应该要求存在事实损害的证据。欧洲法院判决指出,该公约的目标并非统一不同缔约国间的实体法规则及程序规则,公约的核心目的在于确定哪一缔约国法院就所涉民商事争议享有管辖权,以及方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就程序规则,欧洲法院强调了一个一贯的理念,即假使适用受案法院所属国的内国法规则并不至于减损公约的有效性,则受案法院必须适用其内国法。(15)
从欧洲法院的上述判决我们不难注意到,尽管法院倾向于应就公约所规定损害行为发生地赋予欧洲意义上的独立解释,并拒绝在该解释过程中援引英国法,但是受案法院的此种立场在有关损害结果发生地这个次一级的问题上有所倒退,法院非但拒绝就损害结果发生地发表统一的欧洲解释规则,而且还认为这一直接关乎管辖后果的条约解释问题,可因援引受案法院所属国的冲突法规则而依内国法加以确定。(16) 须强调指出,从欧洲法院的判词分析,受案法院地国冲突规则的适用,在确定侵权行为是否存在问题上,似乎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意义。受案法院判决指出,只要不致减损布鲁塞尔管辖体系的有效性,则必须仅由受案法院依其冲突法所确定的实体法,对被告所从事的行为是否构成损害行为予以认定。(17)
最后有必要强调指出,为了增进了公约相关条款适用上的确定性,欧洲法院在Dumez France SA v.Hessische Landesbank及Marinari v.Lloyds Bank plc等案进一步明确指出,(18) 受案法院以损害结果之发生为基础所赖以确定管辖权的根据,应限于侵权行为给受害人所直接造成的损害,而不包括间接损失在内。然而问题似乎并没有完全解决,何谓直接损失,何谓间接损失并非往往一目了然并易于得到认定。(19)
二、涉网侵权案件管辖权的确定
在《布鲁塞尔民商事管辖权规则》制定过程中,欧盟范围内曾有过就涉网案件管辖争议,应否确立来源国标准、接受国标准、抑或针对性标准等特别管辖规则的争论。不过,在最终修订的《布鲁塞尔民商事管辖权规则》中,就侵权行为管辖权的确定问题,除了明确认可受案法院可就即将发生的加害行为行使管辖权外,并无其他新的发展变化。由此,就涉网侵权案件管辖权的确定而言,无疑将继续援引规则第5条第3款有关侵权行为管辖权确定问题的规定,前文所述欧洲法院向之有关该款规定先后所作的管辖权解释规则,也将扩展适用干涉网争议案件管辖权的确定之中。(20) 这一做法在维护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和必要的灵活性价值方面无疑有其值得称道之处,否则,每一种新的技术出现以后,都将引起新的责任类型及其新的法律规则。(21)
为了使我们对涉网侵权案件管辖权确定问题能有进一步的认识,下文将首先就来源国标准、接受国标准等涉网侵权案件管辖权确定中所可能遇到的理论问题简要加以评析。来源国标准倾向于依据行为人所在国的冲突法和管辖权规则解决有关跨国争议,在涉网案件中所谓来源国通常将是某网站经营人所属国、网络信息发表者所属国或在线商品及服务提供者所属国。而所谓接受国标准,则倾向于依据受害人所属国的法律及管辖规则确定跨国争议的解决,在涉网案件中,接受国通常将是所涉网站信息阅读者所属国,其声誉或其所拥有知识产权等权益因某网站所载不当内容而受损的受害人所属国,或购买接受商品与服务的买受人所属国。分析起来,来源国标准因为容易助长涉网行为人挑选相关法律规定较为宽松的国家从事商务或侵权行为,而容易受到消费者保护组织的质疑,就诽谤及损及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件而言,其合理性则更容易受到批评。来源国标准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成员国政府的合作及欧盟相关统一私法制度的形成。事实上,就目前阶段而言,认可来源国标准的《电子商务指令》也仅在法律适用领域确立了相关规则。在管辖权确定领域,尽管因为欧洲法院自Bier案以来即确认损害行为地既可以是加害行为地,也可以是损害结果发生地的原因,信息来源国亦可就相关侵权行为享有管辖权,但据此并不能得出欧盟在侵权领域已接受来源国标准的结论,显然这只是对侵权行为地规则进一步加以认定所带来的当然后果。
将接受国或所谓目的国标准应用于涉网案件管辖权的确定之中,同样也受到批评。批评者担心,认可该标准,有可能使一些国家将其过于严苛的法律适用或管辖规则,仅因在其域内可以浏览相关网页内容的原因而将其内国法律片面地适用于外国网站。接受国标准将可能导致任何可登录某网站的受案法院,将其冲突规则及管辖标准适用于该有关网站,从而加重网站经营人的责任,并有可能限制互联网技术手段及电子商务的应用与发展。不过,在当今网络技术手段日渐成熟,网站经营人对其市场范围已可有所选择的背景下,似乎并没有就此过于担心的必要。从《布鲁塞尔民商事管辖权规则》和欧盟判案实践分析,除了B2B合同类型外,欧盟的国际私法规则事实上倾向于认可接受国标准。(22) 如果说在消费合同领域,《布鲁塞尔民商事管辖权规则》在某种程度上言之,并未排除针对性标准可适用性的话,在侵权领域,则基本上可归因于以效果规则为核心的接受国标准了。
尽管《布鲁塞尔民商事管辖权规则》未就涉网侵权管辖权确定问题特别加以规定,只要受案法院的管辖实践符合公约规定和欧洲法院对公约相关条款所作的解释规则,即可以就相关涉网侵权之争行使管辖权。然而网络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的确给欧盟成员国如何合理而有效地行使管辖权问题带来新的冲击与挑战。首先是因为欧洲法院在Shevill一案中,明确承认可由受案法院依其内国冲突法规则所确定的实体法来认定侵权行为的存在,由此受案法院即无须顾忌域外网站持有人,是否存在针对该国为商务行为或侵权行为的主观努力,只要在该国境内可登录该所控网站并获悉有关内容,即可以侵权行为发生地在该国为由而就域外网站持有人行使管辖权。德国汉堡地区法院在有关丹麦网站商标侵权之诉的Re the MARITIM Trade Mark案中即认为,在涉网商标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地是任何可以使用该网站的地方,既然所涉网站及其内容在技术上并未局限于特定的国家,由此通常也可在德国登录该网站,此即达到了德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要求。受案法院指出,任何涉网行为人都明白可在世界各地获取其所提供的在线内容,由此必须预见得到依公约第5条第3款之规定在外国法院被诉的可能。(23) 相反,英格兰法院因为在依公约第5条第3款之规定行使管辖权时,要求权利请求人提出强有力的诉讼缘由及实体主张,因而可能会考虑到所涉网站的针对性,所以其行使管辖权的条件也许会严格一些。不过这并非是藉以批评一国管辖实践的充分理由,只是某些国家受案法院在确定是否行使管辖权时,更加倾向于不就实体问题给予过多的关注。事实上,前述德国法院在就丹麦网站所涉商标侵权取得管辖权后,从构成侵权所要求的联系因素考察分析,最终判定丹麦当事人的行为并未构成侵权。(24)
具体到涉网诽谤案件,如何援引Shevill案所确立规则以确定损害结果发生地也不无疑问。欧洲法院在该案中指出,诽谤侵权损害行为发生地是知悉受害人之存在的报刊发行地。然而在涉网诽谤案件之中,何以确定诽谤言论的发表及散布地点往往颇为棘手,这无疑给《布鲁塞尔民商事管辖权规则》相关条款的适用带来新的考验,也许在必要时尚有待欧洲法院对此进一步予以澄清。
尽管欧洲法院在Shevill案中明确指出,该所控报业经营人所在地即是加害行为发生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该地是所控信息的来源地,而且该报经营人就其所拥有报刊内容享有较高程度的支配控制权。然而在涉网诽谤案件中,该标准的适用无疑有其现实困难,首先是涉网诽谤案件的相关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而且相互间的联系往往较为松散,网络持有人或其运营商就相关网站所承载的内容,往往缺乏一定的控制甚或并不知晓相关内容的存在,相应地真正信息发表人的身份往往不易得到确定,而其行为通常也与网络服务商所在地国无甚联系或联系甚微。由此,如果权利请求人的诉讼请求仅限于删除所控不良信息内容或终止加害行为的进一步发生,尚可依循Shevill案所确立的规则,在网站持有人或网络运营商所在地法院,有效提起实质或临时保全措施之诉。而如果受害人还欲就其所承受的人身或经济损失寻求救济,网络服务商所在地法院则未必是适宜就该项争议加以裁判的受案法院了,因为依欧洲法院就公约第5条第3款所确立的解释规则,尽管网络服务商所在地法院可就任何起因于该所控侵权行为的权利请求行使管辖权,受案法院也有义务就侵权行为地赋予欧盟意义上的统一解释,然而并不排除受案法院以其内国国际私法规则所确定的某内国实体法规则,确定侵权行为是否存在及其损害程度的可能性。由此,在网络服务商通常可就其所承载内容,因缺乏必要的控制或知晓程度的原因而可予免责的情形下,受害人似乎很难选择在该相应国家就其在各成员国所遭受的所有损失提起诉讼权利主张。此种类似于单一发表规则的公约解释规则,即使权利请求人可以就此有所主张,有时也难以在实践中得到适用。相反,损害结果发生地法院则较易就其境内所发生涉网诽谤行为取得管辖权,惟一让人有所困惑的是,关于诽谤言论的发表散布地在涉网背景下该如何加以认定,是否凡可登录该网站的国家都可初步推定为诽谤言论的发表地或散布流传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将不可避免地使受害人可以选择在任何其所属各国,或知晓该人之存在的欧盟各成员国法院提起涉网诽谤之诉。最后有必要强调指出,在涉网诽谤案件中,虽然所涉网络服务商和信息发布人及其散布人就所控不良信息的参与程度不同,但依《布鲁塞尔民商事管辖权规则》第6条有关多个被告当事人管辖权问题的规定,受害当事人有在各有关被告当事人住所地法院之中,选择某一受诉法院就其所受损害提起诉讼请求的可能,只是此类受诉法院的管辖范围也许还将是个个案分析的问题。
与涉网诽谤案件管辖权的确定相比较而言,有关涉网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管辖权的确定问题更加复杂,首先是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权利请求中,如果所控侵权人以相关权利的存在及其有效性提出抗辩,则受案法院必然面临着该以管辖规则第22条第4款的规定为由,确认相关权利注册登记国法院的专属管辖权,还是以规则第5条第3款的规定认可侵权行为地法院的特殊管辖权的问题;其次,如果在欧盟各成员国为侵权行为的各当事人之间有紧密联系,能否由某一国法院就包括在他国境内为侵权行为的所有被告,依规则第6条第1款的规定行使管辖权;再次,知识产权的属地性特征,必然带来能否由对被告享有管辖权的某一国法院,就他国境内所为侵权行为发布禁令等临时措施的问题。由此,有关涉网知识产权管辖权的确定问题,有必要另以专文加以讨论。
三、小结
综合前文所述,我们不难注意到,在网络技术背景下,因为就网络争议案件所涉当事人身份地位及行为地点加以认定所存在的困难,使布鲁塞尔管辖规则体系下久已确立的传统侵权行为地管辖规则,在不同类型侵权案件中存在不同的挑战,但是侵权行为地管辖规则,并未因网络架构的虚拟性和网络行为后果在某种程度上的普及性,而从根本上被予以否定。为确保管辖权行使的确定性和维护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存在就侵权行为地适当加以严格解释的必要,但是在有关网络识别技术已日渐成熟的背景下,这不应成其为轻易否定侵权行为地这一传统管辖规则可适用性的充分理由,在传统管辖规则被证明具有足够可塑性的情形下,承继传统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行为发生地国所存在的维护本地居民及社会利益的特殊需求,使行为发生地管辖规则的适用往往有其天然的合理性。也许就场所化逻辑推理分析而言,涉网侵权行为地的认定往往有其现实困难,但是并不因此而完全否定侵权行为地管辖规则本身之存在的合理性。由此,尽管《布鲁塞尔民商事管辖权规则》是在网络技术背景下,应欧盟成员国跨国民商事交往的发展,和增进欧盟成员国间司法合作的需要而重新厘定的,侵权行为地仍被作为受案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主要依据而予以确认。(25) 事实上,即使是美国受案法院,在经历了否定传统管辖规则的初期尝试之后,也重又回到了注重传统管辖规则可适应性的分析轨迹上来。
分析起来,受案法院就涉网侵权案件行使管辖权时,所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传统管辖规则能否继续适用,而是该如何适用的问题,特别是该如何将涉网侵权案件与特定法域有效而合理地结合起来。简言之,涉网案件管辖权确定中所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侵权行为地等传统管辖规则能否继续适用,而是该如何有效而合理地实现涉网争议案件的场所化。也即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应否变革传统管辖规则自身,而是如何在场所化分析这一逻辑推理过程中有所进步。此种认识,无疑对确立和完善我国涉网案件国际民商事管辖规则体系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注释:
① See Wendy Kennett,Current Developments: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50 ICLQ 725 (2001).
② Peter Schlosser,Report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Association of the Kingdom of Denmark,Ire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to the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and to the Protocol on Its Interpretation by the Court of Justice,para.134 (1978).
③ See Ulrich Magnus & Peter'Mankowski,(eds.) ,Brussels I Regulation,Sellier & European Law Publishers,2007,pp.214-215.
④ P.Jenard,Council Report on the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OJ C595.3,p.26 (1968).
⑤ See Youseph Farah,Jurisdiction Aspects of Electronic Torts,in the Footsteps of Shevill v.Presse Alliance SA,11 C.T.L.R.196,197 (2005).
⑥ Case 189/87,Athanasios Kalfelis v.Bankhaus Schroder Munchmeyer Hengst & Co [1988] E.C.R.5565 at 15 - 18 ; See Astrid Stadler,From the Brussels Convention to Regulation 44/2001 :Cornerstone of EU,CML Rev.1637,1649 (2005).
⑦ Case C-334/00,Fonderie Officine Meccaniche Tacconi SPA v.Heinrich Wagner Sinto Maschinenfabrik GmbH (HWS) ,September 17,2002.
⑧ Case C-167/00,Verein fur Konsumenteninformtion v.Karl Heinz Henkel [2003] All E.R.(E.C.) 311 at [50].
⑨ Case 21/76,Handelskwekerij G.J.Bier B.V v.Mines de Potasse d' Alsace S.A.,[1976] ECR 1735,1746 (para.15).
⑩ See Douglas W.Vick and Linda Macpherson,Anglicizing Defamation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36 Va.J.Intl L.933,973 - 74,985 (996).
(11) Case 68/93,Shevill v.Presse Alliance,[1995] ECR 415 ; [1995] 2 WLR 499.
(12) Shevill,[1995] 2 W.L.R.at 521,540.
(13) Id.at 533,540.
(14) Id.at 522,540.
(15) See Abla Mayss and Alan Reed,European Business Litigation,Ashgate,1998,pp.132 -33.
(16) See Douglas W.Vick and Linda Macpherson,Anglicizing Defamation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36 Va.J.Intl L.933,984 (1996); Adrian Briggs & Peter Rees,Civil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s,3rd ed.,LLP,2002,pp.162-64.
(17) Case 68/93 [1995] ECR I - 415,464 (para.39) ; See Jonathan Hill,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s in the English Courts,Hart Publishing,2005,pp.148-49.
(18) Case 220/88,Dumez France SAv.Hessische Landesbank ,[1995] ECR I-49; Case C -364/93,Marinari v.Lloyds Bank plc [19951 ECR I -2719.
(19) See Adrian Briggs & Peter Rees,Civil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s,3rd ed.,LLP,2002,pp.159 -60.
(20) See Peter Stone,The Treatment of Electronic Contracts and Tort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under European Community Legislation,11 lift.Comun.Tech.L.121,133 (2002) ; Oren Bigos,Jurisdiction over Cross-border Wrong on the Internet,54 ICLQ 585,601 -02 (2005).
(21) See Youseph Farah,Jurisdiction Aspects of Electronic Torts,in the Footsteps of Shevill v.Presse Alliance SA,11 C.T.L.R.196,198 (2005).
(22) See Graham Smith,Here,There or Everywhere? Cross-border Liability on the Internet,13 C.T.L.R.41,42 (2007).
(23) [2003] I.L.Pr.17.
(24) See Graham Smith,Here,There or Everywhere? Cross-border Liability on the Internet,13 C.T.L.R.41,44-45 (2007).
(25) See Ulrich Magnus & Peter Mankowski,(eds.) ,Brussels I Regulation,Sellier &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2007,pp.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