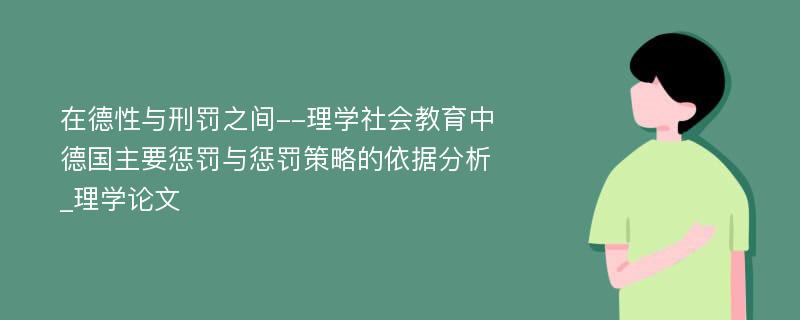
德化与刑罚之间——理学社会教育中德主刑辅策略的基础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化论文,主刑论文,探析论文,刑罚论文,社会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3)06-0006-05
对于理学家而言,如何促进并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并进而达于一个理想的伦理化的社会是其始终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主要是以教育(或教化)的方式通过促进每一个体道德化的发展来完成,这种对于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中教育优先性地位的提倡也是儒学的文化特性所决定了的。社会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保持社会秩序稳定、促进社会关系和谐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被理学家广泛重视。在社会教育中,理学家普遍坚持德主刑辅的策略,对这一社会教育策略的强调,既是对先秦以来儒家思想的继承,又是其对现实治国策略的反思及理学思想特性的反映,因而具有新的内涵。
一、理学社会教育中德主刑辅策略的提出
在理学社会教育思想与实践中,道德教化与刑罚惩戒是两种最基本的手段。在这里,如果说道德教化是一种积极的教育,偏重于形成个体内在的向善的自觉并进而外化为良好的行为习惯的话;那么,刑罚惩戒则是一种消极的教育,更倾向于以可能施加的外部刑罚处置而使个体形成一种戒惧之心,从而避免对既有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的破坏,而不仅仅是以刑罚处置本身为其目的。德、刑在社会教育中的地位与关系正如程颐所讲:“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罚,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渐至于化也。或疑发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逐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盖后之论刑者,不复知教化在其中矣”(注:《周易程氏传》卷第一。);朱熹也讲:“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但于根本上少有欠阙也”(注:《朱熹集》卷五十八《答邓卫老》。)。
在理学社会教育的思想与实践体系中,不同社会教育的主体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围绕着道德教育与刑罚惩戒来组织种种教育资源,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来实施具体的社会教育行为。而就这两种基本的社会教育手段在理学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与关系而言,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以道德教化为主,以刑罚惩戒为辅,即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的观念并非理学所始创,也并非儒家所独有,不过最为儒家所力主。对于德主刑辅问题,先秦儒家也有较为充分的论述,如孔子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又讲:“圣人之设防也,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治也”。(注:《孔子家语·五刑解》。)孟子也讲:“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注:《孟子·公孙丑上》。)。对这一问题,后来儒家人物多有论述,基本上都主张以刑辅德、期于无刑,提倡先德后刑,反对不教而杀,坚持重德轻刑,主张慎刑戒杀等。
理学社会教育对德刑关系的处理,是基于学派的传承而对先前儒家德刑观念的继承,但并非对先秦以来儒家德刑关系论点的简单沿袭,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及理论基础。换言之,它是理学家在对当时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依据其天理人性的思辨理论,对先秦以来儒家德主刑辅观点的创造性阐述。这种阐述虽然由于每个理学家对问题的思考角度及理论体系的不尽相同而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但共同点是主要的,这种共同点表现为德主刑辅的阐述有着共同的现实与理论基础。
二、理学社会教育中德主刑辅策略提出的现实基础
在理学教育家的言论中,普遍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对国家治理状况的不满及对社会秩序无序的批判,一种对当时帝王失德、民心不归的失望,对纲纪不振、吏治不明的揭露,对学校不昌、士风薄恶的痛心,对教化不明、民心竞奔的批判,认为这些社会弊端导致的结果便是社会秩序的混乱及人伦关系的恶化,最直接的表现便是社会风气的恶劣。如陆九渊便称,“王泽之竭,利欲日炽,先觉不作,民心横奔,浮文异端,转相荧惑,往圣话语,徒为藩饰。而为机变之巧者,又复魑魅虺蜴其间,耻其非耻,而耻心亡矣。”(注:《陆九渊集》卷一《与邵叔谊》。)德主刑辅的社会教育策略正是理学教育家在洞察当时社会流弊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其现实社会基础。
(一)出于对最高统治者德性修养的缺失而不能以德率民的批判,提倡修君德而化万民,为德主刑辅社会教育策略提供根本性的支持。
不管是与古代圣王(尧、舜、禹、商汤、文、武、周公等)相比,还是仅对其修养品性的现状而言,对于由宋至明最高统治者的德性修养,理学教育家存有一种普遍的失望感,如王守仁在《自劾不职以明圣治事疏》中对明武宗朱厚照的批评:“每月视朝,朔望之外,不过一二”、“劳力于掣肘,耗气于驰逐,群臣惶恐,两宫忧危,宗社大本,无急于是”、“即位以来,经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悦心于骑射疲劳之事”等。在理学教育家看来,君心为治之大本,君心之正邪,决定着民心之善恶、社会之治乱,而现实中帝王德性之不修正是社会不治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君主来说,首先应“正心诚意”以立其大本,这样才能以德率民,刑罚的作用才能得以正常地发挥。
对于帝王修德以治天下,理学教育家是一致的,如周敦颐主张修圣德而化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其多乎哉?”(注:《通书·圣化》。)程颢主张定君志而趋正道:“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学,明善恶之归,辨忠邪之分,晓然趋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事成矣。所谓志定者,一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注:《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一《上殿札子》。)。朱熹主张正君心而正万事:“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注:《朱熹集》卷十一《戊申封事》。)。王守仁则主张养君心而别善恶:“人君之心,顾其所以养之者何如耳?养之以善,则进于高明,而心日以智;养之以恶,则流于污下,而心日以愚”(注:《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人君之心惟在所养》。)等。张载、陆九渊等其他理学家也持相同的观点。理学教育家普遍认为帝王为社会教化之源,修德不仅对官吏做出了榜样,同时也为万民所效法,是实行德主刑辅策略的根本所在。
(二)出于对君主治国策略的批判,提倡儒家道德教化的重要性与优先性,而以刑辅之。
对于君主的统治策略,理学教育家普遍持一种怀疑与批判的态度,认为统治者未能以德化为先,而钟情于财利兵刑功利之术、佛老二氏虚无之教,也是国家之所以不治、世风之所以日下的重要原因。在张载看来,不以德化为本而尚功利之术,是将道学与政术别作二事,君相应以父母天下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怎能谓之王道,而所谓父母之心是视四海之民如己之子,如此,治国之术必不为秦汉之少恩,必不为五伯之假名。朱熹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也体现了其倡导王道仁政教化、反对霸道功利之术的主张:“若真有意于古,则格君之本,亲贤之务,养民之方,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谓当先而宜急者,曷为不少留意,而独于财利兵刑为汲汲耶?”(注:《朱熹集》卷七十《读两陈谏议遗墨》。)又在上孝宗皇帝书中论佛老之非,认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讲乎大学之道,而溺心于浅近虚无之过也”(注:《朱熹集》卷十三《癸未垂拱奏札》。)。
理学教育家对治国策略的批判不仅仅基于对现实的考察,同时也出于对传说中上古三代之治的向往,认为三代以教化为先,虽有刑罚而不用,人人比屋可封;后世不以教化为本,徒有刑罚而民不治。如程颐讲:“窃以生民之道,以教为本。故古者自家党遂至于国,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则入于小学,是天下无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民莫不从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贤能群聚于朝,良善成风于下,礼义大行,习俗纯美,刑罚虽设而不犯。……后世不知为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驱之以力,法令严于上,而教不明于下,民放僻而入于罪,然后从而刑之。噫!是可以美俗而成善治乎?”(注:《河南程氏文集》卷九《为家君请宇文中允典汉州学书》。)
君主治国策略的失误直接影响到国家吏治与地方政府的作为。由于君主崇尚功利之术、虚无之教,不能选贤使能、以德化民,因而纲纪的紊乱、官吏的腐败与社会风气的恶化便是必然的结果,各级官吏或者钻营于官场之间,以苛刑待民而中饱私囊,如陆九渊所称:“大抵吏胥献科敛之计者,其名为官,其实为私。官未得一二,而私获八九矣”(注:《陆九渊集》卷四《与赵宰》。)。或者崇尚虚无之教、耽于淫佚之事而不知以德率民,如朱熹称:“盖有国家所以昭示明神,祈以降祥赐福于下,其勤如此。顾今之为吏者,所知不过簿书期会之间,否则觞豆歌舞,相与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饰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释氏之祠,则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与先王之制、国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尝有概于其心哉?呜呼!人心之不正,风俗之不厚,年谷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欤?”(注:《朱熹集》卷七十九《鄂州社稷坛记》。)
在理学教育家看来,君主对功利之术、虚无之教的提倡最终结果是纲纪紊乱,学校废弛,民风竞奔,盗贼四起,上不能以德率民、教化百姓,下不能各务其业,劝善戒恶,君主不以修德为事,日日耽于宴游享乐之间,谏臣冷落、佞臣伴行,各级官吏不能勤政守职、化民成俗,日以钻营交结为事,以苛政扰民为能,士人则或沉溺于章句、训诂与辞章之学,以应科举、逐功名为务,或迷恋于佛道虚无之说,而于正己修身之事漠不关心,而百姓或不知和睦忍让而日陷于狱讼,或为生计而流为盗寇,父老不知教化其子弟,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失序的状态,这是理学教育家所不愿看到的。
三、理学教育家对德主刑辅社会教育策略的本体论证明
对于德主刑辅的提倡,除了基于对当时国家治理的考察外,也有理学教育家基于本体论与人性论的证明。而本体论与人性论的证明也是理学教育思想抽象化、思辨化的具体体现,这是理学教育的特色。德主刑辅命题的本体论证明由于理学思想体系特征的不同可分为强调“理”的客观唯心论的证明(如张载和朱熹等人)和偏重于“心”的主观唯心论的证明(如陆九渊和王守仁等人),这与理学思想体系强调本体论研究的思维趋向是一致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策略也由于理学本体论的证明成为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唯一合理的治国策略。
(一)周敦颐:法天为治,仁育刑肃。在周敦颐看来,圣人法天治民,仁育万物,刑肃万民,因而以德刑治民是效法天的结果,是法天的表现。他讲:“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物”;(注:《通书·圣化》。)“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则过焉,故得秋以成。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注:《通书·诚》。)正由于德刑同为法天的结果,因而具有本源上的一体性。
(二)张载:理为礼本,刑自礼出。张载希望用礼来节制社会秩序,实现礼治的社会。在他看来,“礼”出自“理”,“理”决定“礼”,是“礼”的根本,“盖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理,礼则所以行其义,知礼则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之后”。(注:《张载集》,《张子语录下》。)礼有出于自然的,也有出于人为的,而教化刑罚都是礼治的具体体现,从根本上讲,都是合理的:“礼者圣人之成法也,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欲养民当自井田始,治民则教化刑罚俱不出于礼外”。(注:《张载集》,《经学理窟·礼乐》。)
(三)二程:法天明刑,道体刑用。在刑的来源上,二程认为,“先王观雷电之象,法其明于威,以明其刑罚,饬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为之防者也”(注:《周易程氏传》卷第二。)。而就德与刑的关系而言,道为体,刑为用,“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纲纪,分正百职,顺天揆事,创立制度,以尽天下之务,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注:《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
(四)朱熹:德体刑用,刑在德中。朱熹将“理”作为德、刑的根据,认为礼字、法字实为理字,“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者也。故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注:《朱熹集》卷十四《戊申延和奏札一》。)而就德刑二者关系而言,德又是刑的根本,“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注:《论语集注》卷一《为政》。)而德礼又包括刑政于其中,德与刑并非二事,道德性命之与刑名度数,虽有精粗本末之分,然其相为表里,如影随形,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有德礼则刑政在其中者,意则其善”。(注:《论语或问》卷二。)
(五)陆九渊:以心为本,德刑一体。陆九渊是一个心本体论者,在他看来,理不在物而在心,“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穷之变。诚得其理,则变之不穷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注:《陆九渊集》卷三十二《拾遗》。)而治国之根本,本于君主之一心,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将德刑并列起来以为政有宽猛,认为德、刑出自君主之二心是犯了二本的错误。既无二本,便无先后,便不可交替使用。陆九渊认为,君主以仁心化治天下,而“五刑之用,谓之天讨,以其罪在所当讨,而不可以免于刑,而非圣人之刑之也。”(注:《陆九渊集》卷三十《政之宽猛孰先论》。)何况圣人在用刑之际也体现了其宽仁之心。
(六)王守仁:以心为本,刑自心出。王守仁对陆九渊的“心即理”的命题做了充分的发挥,认为“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注:《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此心具有天理,天理的具体化就是“礼”,而刑法作为“文”的一种,是礼的外显之一,“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浑然全体之中,而条理节目森然毕具,是故谓之天理。天理之条理谓之礼,是礼也,其发见于外则有五常百行,酬酢变化,语默动静,升降周旋,隆杀厚薄之属”(注:《王阳明全集》卷七《博约说》。)。它宣之于言而成章,措之于为而成行,书之于册而成训,炳然蔚然,虽其条理节目繁杂而不可穷诘,但从根源上讲无不是心的外显,而圣人之心作为为政之本,是一切礼乐刑政教化之本源,“仁君之心,天地民物之主也,礼乐刑政教化之所自出也”。(注:《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人君之心惟在所养》。)
四、理学教育家对德主刑辅社会教育策略的人性论的证明
理学的人性论是对先秦儒家人性论的继承与明晰。理学关于人性论的一个总的趋向是以孟子先验的人性善说为本,改造荀子的性恶论,抛弃了董仲舒、韩愈等人的性三品论,坚持人性善的先验性与普适性,但同时也对人性恶的因素或人的恶行的出现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理学的这种人性论使得理学教育家对教育作用与范围的认识更为彻底,对人的发展、变化的可能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同时并未走向极端,而是给刑罚的震慑与惩治留有余地。
(一)以教化为本的根据:人性善的先验性与普适性。在理学家看来,人性是天之所予人者,是不学而能的、不虑而知的,且为圣凡所共有。朱熹讲:“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仁义礼智之性矣”(注:朱熹《大学章句序》。)。陆九渊讲:“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注:《陆九渊集》卷十五《与唐司法》。)。王守仁也讲:“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达道也”。(注:《王阳明全集》卷七《重修山阴县学记》。)同时,人性具有永恒性、虚灵性及主宰性等特点。(注:参阅拙著《拒斥与吸收:教育视域中的理学与佛学关系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203-219页。)一方面,正是由于人性善的先验性与普适性,使得身为教育家的理学家对教化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对教化的乐观态度弥漫于理学家的言论之间,如张载称:“‘人皆可以为尧舜’,若是言且要设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则圣人之语虚设耳。”(注:《张载集》,《经学理窟·学大原下》。)程颐讲:“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自己者,皆自弃也”(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另一方面,由于气禀、私欲、邪说等因素的影响而使人不能为善,因而必须对其加以教化,如陆九渊讲:“此心本灵,此理本明,至其气禀所蒙,习尚所梏,俗说邪说所蔽,则非加剖剥磨切,则灵且明者曾无验矣。”(注:《陆九渊集》卷十《与刘志甫》。)理学人性论的变化及其对引导人们向善的积极、乐观态度是理学教育的一个特色。
(二)以刑罚为辅的根据:对教化作用有限性的认识。虽然理学教育家希望通过教育达成一个理想的社会,但他们并非理想主义者,对于教化作用的有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们并非一味地强调通过教化使每个个体向善,而是给刑罚的震慑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具体而言,之所以采取刑罚,张载、程颐和朱熹等人将其原因更多地集中在人性中先天的恶的因素的存在,这种先天的恶具体表现为气禀的偏浊,这也是贤愚分途之始,如朱熹讲:“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长久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夭”;(注:《朱子语类》卷四。)而陆九渊和王守仁等人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后天恶的因素上,认为是后天的恶遮蔽了先天的善性。对于人性中恶的因素的根治,理学家将重点放在了教育与自我修养上,提出了很多的道德教育原则与自我修养的方法。但对于极少数人而言,教育并不能使其克去人欲,复尽天理,自觉向善,如程颐认为,人性本善,然亦有不向善者,原因就在于虽然人性皆善,但才则有不移之下愚,主要表现为自暴与自弃,对自暴自弃之人,教化是不起作用的,“人苟以善自治,则无不可移者,虽昏愚之至,皆可渐磨而进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注:《周易程氏传》卷第四。)。因而只有通过刑罚的震慑使其不肆于恶。甚至对于向善之人刑罚同样也有其警诫的意味,如朱熹讲:“‘君子怀刑’,言思刑法而不必犯之,如惧法之云耳”,“无慕乎外而自为善,无畏于外而自不为非,此圣人之事也。若自圣人以降,亦岂不假于外以自修饬。所以能‘见不善如探汤’,‘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为其知有所畏也。”(注:《朱子语类》卷二十六。)从根本上讲,与主动的施教相比,刑罚的使用是不得已而为之,陆九渊讲:“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无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无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则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夫五刑五用,古人岂乐施此于人哉?天讨有罪,不得不然耳。”(注:《陆九渊集》卷五《与辛幼安》。)
结语:理学德主刑辅社会教育策略新的内涵
由于论证基础的变化,理学的德主刑辅的社会教育策略与以前包括先秦儒家的相关思想相比,有了新的内涵:首先,对德主刑辅社会教化策略的强调有其鲜明的针对性,它是儒家在西汉取得独尊地位后,在封建社会经历了自西汉以来一千多年的社会变迁后,对儒家德化政治的重新提倡,其目的是为了减少以至消除各种功利之术与宗教思想在政治统治中的地位,提高君主和各级政府官吏的道德素质,坚持以德治国,使得国家的统治真正走上儒家一直倡导的“修德治人”的德化政治的道路;其次,通过本体论论证将德与刑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坚持德刑同源、德刑一体、德体刑用,强调严刑、慎刑,反对滥刑、宽刑,在坚持道德教化的基础上,强化刑罚的震慑作用,为德刑一体的政治统治与社会教化提供基础;最后,通过人性论证明对道德教化与刑罚惩戒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的论述,一方面使人们对于道德教化的作用有了更加积极的态度,但同时对其局限性的说明又强调了刑罚作为教化必要补充的地位。
标签:理学论文; 儒家论文; 王阳明全集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古代刑罚论文; 陆九渊集论文; 朱熹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人性论文; 王守仁论文; 张载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