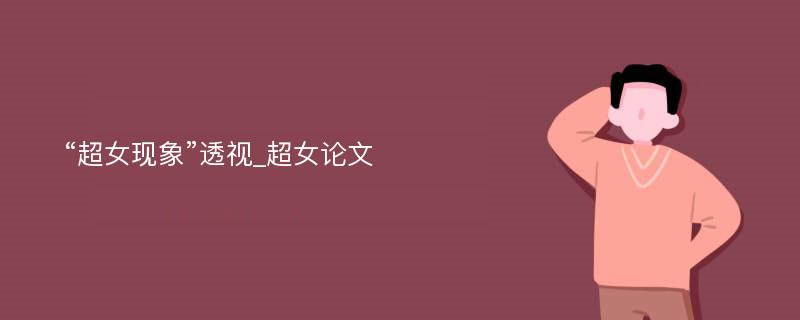
“超级女声现象”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视论文,女声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超级女声——青春的亮相
“超级女声”在中国已有二年的历史。2004年,湖南卫视首次推出“超级女声”节目,这一电视歌唱比赛节目,类似于德国的“德国寻找超级明星”和美国的“美国偶像”,作为大众通俗文化活动一面世,立刻成为新的青年流行文化热点。“超级女声”选拔分为海选、淘汰、决赛三个阶段。喜欢唱歌的女性,不讲条件、不分唱法、不限年龄、不论容貌、不问地域,总之,不设门槛,均可免费报名参加。2004年,虽然是第一次举办,全国四个赛区就有6万余人参加。
2005年,“超级女声”红透全国。年初一开赛,报名者络绎不绝,在广州、杭州、郑州、长沙、成都五个分赛区,前来报名的队列长达数千米,全国共有15万人报名参与。参赛者中年龄最大的89岁,最小的只有6岁,但绝大多数是十几到二十几岁的青春少女。由于电视媒体的全程播放、众多媒体的广泛宣传和观众之间的短信互动,很快形成了“超级女声”狂潮,从南到北,由东至西,“超女”热浪席卷全国。央视索福瑞7月份的调查统计显示,“超级女声”白天时段收视份额最高突破10%,居31个城市同时段播出节目收视份额第一,收视率首次超过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8月份,2005年“超级女声”总决赛的广告报价为15秒插播价11.25万元,超过了央视一套最贵的19点45分时段的15秒11万元的报价,这是央视在电视行业老大的地位第一次受到挑战。再从类似栏目的比较来看,“非常6+1”和“梦想中国”几乎同时举办,但其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中的影响力仍然远不如“超级女声”。前者在四川赛区报名人数为3672人,资格赛的6人总得票数是25万多,而“超级女声”成都赛区报名人数近4万人,赛区总决赛仅前三名的选票便超过30万。
“超级女声”是一次众多妙龄少女美丽青春的集体亮相。历时半年多的激烈比拼,8月26日,3名青春少女从15万参与者中,最终闯入了2005年“超级女声”的总决赛。最终名次由观众短信投票产生,李宇春以3528308票夺得本年度“超级女声”冠军,另外两名选手周笔畅和张靓影分别以3270840票和1353906票获得亚军和季军。三人所得短信投票相加,超过了。800万张。外电报道,同期收看电视和网络互动的超过了5亿观众。这是何等的壮观场景,又是何等的风光无限。她们把自己美丽、帅气、自信、活泼、可爱的青春风采,前所未有地层现在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观众面前。
二、想唱就唱——青春的宣言
“超级女声”海选阶段,吸引了海量的报名者。有媒体这样描述:参赛选手中什么样的都有,有瘦得像根筷子,站都站不稳的;有胖得一动就“水波荡漾的”;有形象气质俱佳的,也有普通平凡得不会多看一眼的;有年龄小得要大人领着抱着的,也有老得嘴里没牙的。选手们的穿着打扮也是五花八门,有穿礼服的,有穿旗袍的,有穿工装的,也有穿校服的,还有穿着露脐露背装的,甚至还有人穿着睡衣,大大咧咧站在评委眼前的。选手们唱起歌来更是千奇百怪,有唱一半就没声的,有跑调十万八千里还在摇头晃脑的,还有的手舞足蹈连唱带跳,动情之处乱打滚的。
“超级女声”参加者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是想借此锻炼自己,一位选手在报名之前就给组委会发短信:“得知今年又要举办‘超级女声’大赛,我梦里都笑醒了,虽然我不一定会被选上,但我想挑战一下自己。”还有的人则直接说:“就是为了出名,当超级明星,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成都赛区报名期间,媒体调查反映,在前来报名的女生中,在校大中学校学生占了80%,其中不乏高三女生拿着复习资料来排队的,不少学生还坦言,她们是逃课来报名的。因此还引发了讨论,认为是“超级女声”的负面影响。
与批评的声音形成强烈对照的,却是越来越多的青春少女对“超级女声”乐此不疲。喧闹的人潮,万人汇成的几百米长龙,十几个小时的等待,全国各大赛区相似的场景如期出现。从凌晨开始,就陆续有数千人到万人涌入“超级女声”报名现场,走廊、过道、洗手间,只要是视力所及的范围,到处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女孩。正如一位大赛评委描述的那样:几万张女孩的脸孔,她们充满梦想和期待的神情,她们的笑脸和泪水,她们的花衣服、白衬衫、七分裤、小圆帽子……潮水似的从他们的眼前和脑海中流过。
“超级女声”的一首主题歌准确地诠释了万千青春少女们的狂热行为。歌名叫《想唱就唱》,歌词是这样的:“推开夜的天窗,对流星说愿望。给我一双翅膀,能够接近太阳。我学着一个人成长,爱给我力量,梦想是神奇的营养,催促我开放。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地自我欣赏。想唱就唱,要唱得漂亮。就算这舞台多空旷,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
海选阶段,选手们不仅唱歌,还拿出各自的绝活儿充分地展示自己,在比赛中奇招迭出。载歌载舞只是常规武器,炫彩出场甚至自己编词者也不少。当然大多数都是传统的中式说唱,有的动作超级难看,有的歌声超级难听。穿各类古怪服装者更是层出不穷,前卫的裸露装和老土的红纱裙都不算什么,有人甚至把婚纱穿到了海选现场。有趣的是,一位评委问一位17岁的参赛“超女”,“你知道自己走音吗?你身边的人知道你走音吗?”这位选手很爽快大方地回答:“我爸我妈都说我走音走得厉害。”评委又问:“那你为什么还来参赛?”这位“超女”选手没有正面回答问话,而是反问这位评委:“走音与参加‘超级女声’有什么关系吗?”这句话听来令人啼笑皆非,但却掷地有声。
“想唱就唱”,这是青春的权利。“想唱就唱”,谁也不能阻挡。唱的准不准,是否走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表达了我的青春愿望,我喊出了我青春的声音。这也恰恰说明,海选给每个选手30秒的时间,已远远超出了节目选拔者初衷的本意。大多数青春少女要的是这个过程、这个体验,而不是“超级女声”的本身。所以,选手提出“走音与‘超级女声’有什么关系吗”的诘问,非但不奇怪,而恰恰道出了这一代青年的个性特质。
三、粉丝选秀——青春的狂欢
“超级女声”红透大江南北,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离不开喜爱和追逐“超女”们的全国“粉丝”(歌迷)们的推波助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超级女声”,不仅有15万人直接参加海选,更有数以百万计的“粉丝”参与。荧屏内外、网上网下、全国各地、海外及世界不少地方,狂热的“粉丝”们追逐各自喜爱的“超女”。随着竞赛进程的推进,“粉丝”们热度不断升温,“超女”们形成了各自的铁杆“粉丝”团队。
“粉丝”与媒体、“粉丝”与“超女”之间的互动造势,共同演绎了“超级女声”的神话,制造了“超级女声”的奇迹。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超女”和“粉丝”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每当周末,飞往长沙的班机成为各地“粉丝”和记者的包机。比赛前后的报道更是铺天盖地,北方报纸做8个版“超女”不过是小儿科,南方报纸一天可以拿出32个版、40个版报道“超女”。每次走近湖南电视台所在的广电大厦,还有几百米距离,就已经看见成千上万的“粉丝”们围在道路两旁,那景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正像前文所述的“走音”与“超级女声”有什么关系那样,其实,“粉丝”们是不关心歌曲的,她们只要看到自己的偶像上台就可以了。偶像往那一站,不管她唱得怎么样,都是沸腾和欢呼,声音大到连主持人和评委的话都听不到了,这种狂热已无法用正常逻辑去解释。“粉丝”们不能接受偶像短信落后,不能接受偶像上PK台,不能接受偶像没能直接晋级,即使评委的批评意见也不允许。
现场热度还远不及网上和短信的火爆。同期报道的媒体超过百家,相关的网页100多万项,因比赛规定每部手机在一场比赛中只能为一名选手投15票,很多“粉丝”用自己的手机投完了票还不甘心,不惜重金买新手机卡,跟身边的人借手机投票。女儿缠着并不喜欢看“超女”的爸爸、妈妈为自己的偶像投票的“粉丝”也比比皆是。有的“粉丝”把“超女”的笑脸制作成耳环,挂在自己的耳朵上,以表达对“超女”的坚定不移的支持和喜爱。
在比赛的关键阶段,“超女”的命运由观众短信决定。因此,还涌现出不少“超级粉丝”。广州一白领“粉丝”出资10万元为广州赛区的“超女”在网站上做拉票广告。在长沙某移动电话营业厅,一位男“粉丝”一口气买下一万张神州行,花费50万元,为的就是给自己的偶像投票。还有一群20多岁的女孩子则花6000元买下了12部小灵通,临走时还叮嘱卖手机的老板“不要忘了给某某投票哟”。还有不少大中学生“粉丝”,很有秩序很有规模地组织起来,走到大城市的街头宣传鼓动,进行广泛拉票。有的甚至是把仅有的一点点零花钱也毫不心疼地拿出来投上一票。
一位男士上街遇到一乞丐,纠缠不休,便想掏钱打发了事,不料乞丐一番话令他瞠目结舌。乞丐说:“谢了,你把那点钱留着给某某‘超女’投票吧。”这不是笑话,而是发生在“超级女声”决赛阶段的真事。更有甚者,不少“粉丝”每天为自己的“超女”写一篇日记,每天上网发帖子,每天为“超女”做祷告,每天看见报刊亭有报道“超女”的报刊就统统买下。
这是青春的狂欢,狂欢的青春,青春就应该是张张扬扬的。中国青年没有自己的狂欢节,中国的女青年更难得狂欢一次,而“超级女声”却引发了她们的狂热。“粉丝”们在享受“超级女声”带来的文化大餐、娱乐盛宴的同时,也正在制造着中国青年特别是中国女青年自己的狂欢节。
四、超女现象——青春的律动
回眸这个热闹的夏天,红火的2005,“超级女声”引发的激情、热辣、火爆与疯狂,如同大自然的“热岛现象”,其热度并没有因为进入秋冬季节而降温。“超级女声”留给我们的是,凡有“超女”的音像制品与出版物和饰物热卖,凡有“超女”参加的演出与活动热看,凡与“超女”有关的生意热涨。加上街头巷尾人们对“超女”的热议,专家学者对“超女”的热评,主流非主流以及海外媒体对“超女”的热报,广大“粉丝”及青少年对“超女”歌曲的热唱。超乎寻常的“超女”,产生的“超女”效应,进而引发蝴蝶效应,这一切,不只是“超女”动人,“超声”动听,“超迷”动心,也不只是“超女”造梦,而是在青年中、在文化娱乐界、在全社会,实实在在形成了一个不能不正视、不能不关注的“超级女声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它带给人们几多亮色,几多思考。
其一,“超级女声”开辟了青年娱乐文化的新天地。有人这样概述中国电视的现状。一张豪华的桌子,上面摆满了数百只盘子,但每只盘子里都是饺子。在观众对传统电视节目的长期审美疲劳之下,“超级女声”出现了。特别是在长期推崇含蓄、内敛、隐忍的文化氛围里,短短二十几年,中国经历了社会现代化的转型,青年感到诸多不适,狂欢的需求产生了。而“超级女声”电视节目的出现正是满足了青年大众的这种狂欢的需求。无论选手还是观众,从“超女”节目中获得了新奇的感官经验,也获得了临时性的自我解放。观众与选手,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青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有了共同的话题,又做着各自不同的梦。“超级女声”首先带来了中国娱乐节目彻底的平民化和娱乐青春化,让每个有梦想的青年都获得一个自由展现的电视平台,满足了许多青年心中埋藏已久、急需释放的欲望。这种娱乐文化彻底平民化的趋势说明,在今天已经不能关门办文化,那种自己拍自己播的时代已经过去,特别是“超级女声”把节目做成了一场社会时尚、社会风潮,产生了累积的效应。累积“粉丝”,累积人们的忠诚度,通过短信互动来培养观众,培养收视率,培养青年的兴趣,引起社会的关注。这无疑对传统娱乐文化是一种冲击,一个挑战,一次超越。
其二,“超级女声”提供了青年民主参与实践的新平台。“超级女声”一跃成为娱乐圈当之无愧的头号风暴,有人认为是一次青春与民主的有机结合,有人认为是新一代青年一次文化民主意识的觉醒,海外舆论甚至认为,“超级女声”为中国民主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议论风起,见仁见智。的确,“超级女声”为所有参加者提供了平等参与的机会。“超级女声”从海选一路走来,是以“人人都有机会”,人人都可参与的民主机制展开的,机会均等与优胜者的秘密在于“起点公平”。不管老幼、职位、美丑、贫富等等,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体现了对普通人的最大尊重,也最有效地动员了青年。同时,“超级女声”设立了一套尽量能够体现民意的评审规则。选手的去留由三类人决定。任何想参与评选的观众、通过挑选出来的大众评审团和专业评委。每一类评委都有权利通过投票方式对参赛者进行评判,但又都无法独占决定某位选手去留的权利。“超级女声”的“粉丝”们不分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她们关于“超女”的话题和讨论五花八门、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成千上万的超级“粉丝”们,因为参与这场规模盛大的超级狂欢,度过了这个热辣火爆的夏天,感受了“超女”带来的欢乐悲伤,付出了为“超女”们投入的罕见热情。“超级女声”的做法无疑是一次民主选举的演练,如何将公平公正深入人心,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里颇具示范意义。特别是决赛阶段的大众评委与观众投票的决定性作用,其做法无疑在潜意识里引发了广大青年的共鸣。按照民主、竞争的程序选拔“超级女声”,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崭露头角的舞台,创造了更多公平透明的竞争机会。让大众化民主选举真正成为可能,这应当成为我们社会努力的方向。
其三,“超级女声”彰显了青年“中性化”审美的新趋势。首届“超级女声”前三名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今年“超级女声”全国十强中受欢迎的李宇春、周笔畅、黄雅莉等与中国传统美女标准相去甚远,让电视机前无数男观众心如刀绞。特别是在8进6比赛中,“超女”中的美女叶一茜跟黄雅莉PK,唱功前者要好于后者,但大众评委却无视众多男性观众的捶胸顿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黄、PK掉了叶,被认为是裤子女生战胜了裙子妹妹。今年“超级女声”冠军李宇春,这个男孩子长相的四川音乐学院大三女生,从成都唱区里脱颖而出,她的个性、她的魅力、她的独特的台风,一下子就打动了无数青年女性和无数的“粉丝”们,她们普遍惊叹,原来女孩子也可以这么美好地帅气与利落。李宇春身上具备了许多看来只属于男性的美好品质,像豪爽、帅气、潇洒、绅士、干净、自然大方等,被同样是女性的无数观众与“粉丝”们大加赞扬。“中性化”的魅力是超越性别的。李宇春的出现,让中性之美重获评价,她所具有的震撼性撼动了男性社会关于女性美的传统定义,同时也让更多男性观众发现她的美丽与价值,并在女友的鼓励下为她投下一票。从《我的野蛮女友》走红,到“中性气质”称霸“超级女声”,跨性别气质的得宠,似乎成为一种时尚流行趋势。无论是李宇春的帅气,周笔畅的爽朗,还是黄雅莉的阳光,“中性美”这个2005“超级女声”创造的新流行词,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青年、特别是女青年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的新变化。对于“中性美”的出现,《中国青年报》的一次调查反映,60.8%的人认为这是社会文化多元化的正常表现,只有10.1%的人认为是性别混乱的另类行为,无法理解。而大多数人认为,促进男女平等,最有效的在于改变人们的社会观念。
其四,“超级女声”反映了青年与社会互动的新特点。“超级女声”落幕了,它既好评如潮,又议论争论不少。“超级女声”的参与者以大学生为主,从青年人的角度来考量,笔者认为对待“超女”、对待青年,应多一些冷静,多些客观,多一些关爱。“超级女声现象”,不仅受到了国人的关注,新加坡《南华早报》、美国《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等海外媒体都在研究。应该说,“超级女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狂潮无疑是大众文化兴起的表现。大众文化的特征就是城市化、消费化、娱乐化。人的文化消费是多层次的,我们需要对“超级女声”宽容一点,对青年文化消费群体宽容一点。过去是文化训导大众,现在是明星娱乐大众,而“超级女声”是大众娱乐大众。更重要的是,“超级女声”的消费群体都是以青少年为主。这也说明大众文化消费正在日益青少年化,青少年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消费的主体。当代中国青少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代,接受教育最多的一代,也是最有能力消费的一代。未来他们将支配文化走向,支配大众兴趣。他们的兴趣将日益主宰社会,而“超级女声”则预示着这种支配与主宰的力量。同时也显示着青年与社会互动的力量。只有青年文化与社会文化、青年与社会的和谐互动,才是健康有益的,才能成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推动力。
基于这样的认识,秉持科学的态度,我们对待“超女”对待青年,唯一正确的选择是:用心倾听她们的心声,用心感受她们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