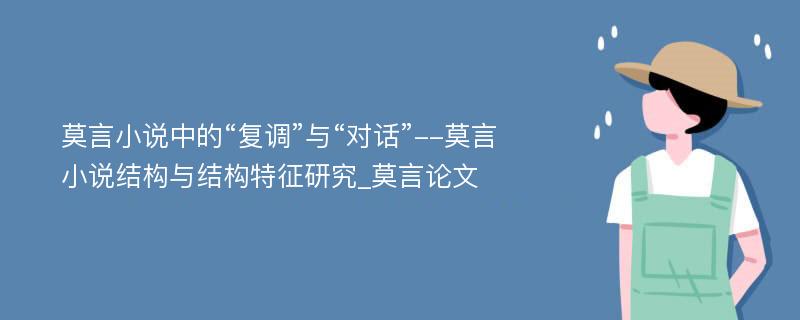
莫言小说中的“复调”与“对话”——莫言小说的肌理与结构特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肌理论文,小说论文,特征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 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0)03-0035-07
文体是作家作品自觉的和不自觉的艺术动机、话语蕴涵的表现形式、存在之家。巴赫金指出:“在艺术中,意义完全不能脱离体现它的物体的一切细节。文艺作品毫无例外都具有意义。物质、符号创造的本身,在这里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因此,作家对生活的发现、对人生的体验以及艺术上的创新往往“物化”在作品的肌理、结构等文体方面,或者说流溢在形式结构上或通过独创的组织结构形式表现、呈示出来。而美国文论家马克肖莱尔更直截了当地指出:“现代批评已经证明,只谈内容就根本不是谈艺术,而是谈经验;只有当我们谈完成了的内容,即形式,即作为艺术品的艺术品时,我们才是作为批评家在说话。”[2]43不言而喻,我们除了从内容层面来理解莫言文学的意义外,还必须从文体的角度来观察和发现莫言文学的独特之处,如此才能达到对莫言文学的透彻把握。
莫言作品的普遍肌理和整体形式结构或体裁性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复调”“对话”如同肉体的肌理普遍分布在作品中,组织结构上也采取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对话”格局。
一、“复调”与“对话”
何为“复调”?它与“对话”是何关系?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梳理的一个问题。
复调是音乐的概念,源于希腊语,指由几个各自独立的音调或声部组成的乐曲。巴赫金借用这个概念来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特点,并强调这只是一种比喻。
巴赫金认为欧洲的小说有两种体裁类型:一种是传统的独白小说,小说的人物是受作者支配的;一种是复调小说,复调小说展示多声部的世界,小说的作者不支配一切,作品中的人物与作者都作为具有同等价值的一方参加对话。[3]
显然,复调是个比喻,既然是复调,则至少有两种调子,也许是多种、无数种,这取决于作品中人物的多少,即主体的多少。而复调的根本则在于对话,在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对话以及主体自我内部的对话。换句话说,复调、对话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是一回事。那么,既然有了对话,何以再生出一个复调概念?这就在于,通过另一种话语方式(这里是音乐)的比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的用意。更重要的是:一、对话突出的是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间的特殊关系状态,而复调可以用来描述多个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情状;二、对话突出话语性、直观性、语言性——尽管对话也可以是比喻的,隐蔽的,间接的,而复调则往往较为隐蔽,不够直观,并且是非语言(狭义)性的;三、如果说对话、话语突出语义指陈和不同对话主体间观点、意图的差异、分歧的话,复调突出音调的感染、风格的差异。可以说没有什么对话不是复调的,也没有什么复调不是一种对话。巴赫金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说:
在每一种声音里,他能听出两个相互争论的声音,在每一个表情里,他能看出消沉的神情,并立刻准备变为另一种相反的表情。在每一个手势里,他同时能觉察到十足的信心和疑虑不决;在每一个现象上,他能感知存在着双重性和多种含义。[4]40-41
因此,当对话是直接的语言叙述、陈述的时候,复调往往以隐蔽的、侧面的位置和方式在显露、传达对话中的主体的存在性感受和体验,如同诗有韵、歌有调。换句话说,虽然复调与对话这两个概念的语义侧重点不同,但在根源上是一致的,也即都发源或指向生命主体的存在、生命主体的精神。因此,有时作品的有些内容是直观的对话,我们可以说,这些是对话;有些部分外观上不是对话,它们更像是复调,如:
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红高粱》)
但这种复调何尝不是主体对话的一种隐蔽的投射、表达?因此在下文的讨论中,为了方便,我们将不再严格区分这两个术语,并且它们会交叉出现。重要的是要面向它们的源头,面向生命主体的存在,面向生命主体的心灵,面向生命主体的精神。
二、“复调”与“对话”之源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这部著作中,巴赫金充分肯定了理论家B.基尔波京的看法:许许多多研究者在所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只看到唯一的一颗心灵——作者本人的心灵。基尔波京则相反。他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殊才能恰恰是善于看到他人的心灵。[4]50基尔波京是这样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一种才能,似乎能直接观察他人的心灵。他仿佛戴着光学镜在窥视他人的心灵,能够把握住最隐秘的思想,观察到人的内心生活中最不起眼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越过了外部的屏障,直接看到人的心理过程,并形诸文字……”巴赫金还指出:陀思妥斯夫斯基能够在一切地方,在自觉而有意义的人类生活的种种表现中,倾听到对话的关系。哪里一有人的意识出现,哪里在他听来就开始了对话。[4]56
阅读莫言的作品,我们会发现莫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具有突出的能“看到他人心灵”的才能。应该说,这种才能每个人多少都有一些,尤其是小说作家们都会具有,然而,相比起来,少数最一流的作家在这方面的才能会显得特别地甚至不可思议地突出。莫言即在此列。他似乎不是从外观察到人物的内心,也不是用自己的想象去推测人物,那些呈现出的东西好像就是人物自己“说”出来、表露出来的,而他只不过是记录了一下而已。但小说不是人物采访、人物“自述”“自传”,它是作家虚构的产物。因此,莫言是必然要借助观察和内省,设身处地的“将心比心”的理解才能做到的。而要达到他作品中的境地,这观察力、记忆力无疑是要非同寻常的,这内省力,这人生体验是需要极其地丰富与深刻的。特别是它需要作家不是发出自己一个人的声音,只以自己的眼光和观点来看待人物、事物,而必须依靠个人才能的同时超越个人“视界”。如果只以自己的声音、以启蒙的独白来看待人物和世界,作家就不能理解生命和世界的“对话”本质。对这一点有些论者也作了很好的描述,如葛红兵在《直来直去》中写道:
“五四”作家的启蒙语言是从西方借鉴的,这从他们语式的欧化上可以看出来,这种语言上的欧化与精神上的欧化即启蒙化完全一致。比如说鲁迅对阿Q的批评,在启蒙话语中,阿Q是没有地位的,我们从阿Q身上看到的是愚昧、自欺、受骗等国民性的缺点。这种遮蔽的东西在莫言的《檀香刑》里被颠覆了过来。比如赵甲这个人物,变成了一个充满了敬业精神的,无论怎样都要活下去的,充满仪式感的人物。他身上这种韧性是来自民间的力量。我认为这一点与莫言对语言体式的选择有关。[5]
葛红兵的这段描述可以用来说明莫言作品中人物之间潜在的对话性关系。但将之归因为语言体式的选择则有本末倒置之嫌,因为莫言登上文坛从事创作之初没有选择明显的民间语言体式之前就如此构筑作品了,或者说即使选择了民间语言体式,也不见得就能避免“启蒙式独白”的思想意识和构筑作品的方式。这一点与语言体式的选择没有直接的关系,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与民间语言体式没有直接关系一样。但这里关于作品中人物地位、评价等的描述的确可以旁证莫言作品基于内在的复调思维、体认方式而对作品形态产生的影响和导致的结果。
那么,作家要超越个人视界则必须有充分的主体意识和生命主体精神,即以生命或生命主体的意识和态度出发去观察和想象、理解和尊重每个人物而不仅仅是主要人物的生命存在的境况和他的肉体与心灵一体的、真实生存的体验、感受、话语、表情及行为,从而让每个人物展现出他的真实存在中的自我,发出自己的声音,使所有的人物不论其在知识、权利、地位、金钱等等方面拥有的多少而都显露出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尊严、愿望等等谱成的声音,使主体和主体以生存、生命的权利与名义发出话语,使主体和主体之间形成生命的对话,从而使作品进入复调的艺术境地。
读莫言的作品,我们常会对于作者对人物的内心,对人物细微深刻而又往往极其隐蔽、并且稍纵即逝的主体性生存体验准确捕捉的才能感到惊讶。有时即使读一两句描写,我们也能感受到莫言作品渗透到细胞、基因的对话的喧声,甚至在对场景、景物、植物的描绘中这种对话的喧声也无处不在。如《红高粱》一开始,父亲与奶奶告别:
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吭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奶奶夹袄里散出的热哄哄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
就这不经意的一句中,父亲其实感受到了多重“对话”:奶奶的,这是热哄哄的香味。其实即使在奶奶这里发出的也并非单一的话语。另一重可以说是一种未出场的存在发出的话语。因此,父亲感到凉气逼人。
莫言常常好像孙悟空钻入了人物的内心,是一撮毫毛吹出了千万个孙悟空而潜入了人物的每一器官和部位,而且在一部作品中他不是潜入某个主要人物内心、内部,而是潜入所有人物内部,谁出场就钻入谁的内心,因此,我们读他的作品,我们也就能“披文以入情”地进入每个人物的内心和身体,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人物生命存在的真实的、切身的境况,被它的主体性、生命主体精神所感染、触动,从而心生理解、同情与尊重,产生相互间的对话。但莫言不是在依照对话理论来构思作品的。这里的根本恰在莫言始终尊重了每个人物的生命主体性,意识到并尊重到每个人物灵与肉统一中存在的那个永不止息的自我源泉,倾听到了这些生命泉流的自己的声音,体会到这些生命的感受、体验与反应,从而活脱脱地将之形诸了文字。因此,发现并尊重生命、尊重每一个生命主体,必然会达到真正的对话、复调的艺术境地。
三、笔触中的“复调”
如果说在总体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和莫言的复调有什么不同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是显著形态的,经常是以言论的方式长篇大论地出场,而莫言的复调是隐微的、隐蔽的。一个是大树之间的对话,一个是幼苗之间的对话,然而对揭示生命主体的存在境况和精神境况的深刻性来说,他们殊途同归,不分大小,而且就诗学的意义来说也不分伯仲。
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是显著的而莫言的是隐蔽的呢?这是因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常常是知识分子型的人物,他们是好言语、好谈论的,因此,对话在时空中的展现是明摆着的、唇枪舌剑般的,而莫言的人物大多是处于生存底线的体力劳动者或非知识型人物,他们大多讷于言语,或者他们即使不讷于言语,也不喜欢“快意空谈”,坐而论道。他们往往是直接用身体和行为说话,而非滔滔不绝的言词。因此,要尽精尽微地捕捉、理解和表现、书写出他们内心的、身体的、表情的、言语行为的意图感受,传达出他们的声音,描绘出他们之间共同形成的众声喧哗、多音齐鸣的对话景观是艰难的,就像将作曲家的作品搬上舞台是容易的,而将自然的天籁、变化细微丰富的天籁尽显舞台是艰难的一样。因此莫言写出了忍辱负重的沉默的大地的内心的丰富的体验和心声,但莫言不“言”,他常常采取的是显示,是将每个人物的存在,生命的主体的存在呈现出来的方式。这种隐形的由人物在同一话语空间或生命场景中出场而相互构成的哑剧般对话结构是莫言作品中天然分布着的一种隐微对话,它没有外在形态表现,它是以人物主体自身的显现而自然形成的,即每个人物都充分地表征出了自己的主体性,从而向读者显示出他们之间的无言的对话性。如前所述,莫言总是好像潜入人物的内心,发现人物内心体验到的每一点细微的变动并捕捉到这些变动,通过对人物“心理”的提示、刻画,特别是表情、行为的描写、交代而展示出来。因此,即使像《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始终沉默不言,但他的生命感受、体验,他的主体性在作品中也始终被表现、描绘、提示了出来,而不管它们多么隐微。《枯河》中的男孩、女孩一样,不管是否是主角,他们出场的时刻,其主体性存在即表露无遗。这些大多是以近似绘画艺术的“笔触”般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的双耳共鸣着,模模糊糊地看到父亲的手臂在空中挥动时留下的轨迹像两块灼热的马蹄铁一样,凝固地悬在我与父亲之间的墙壁上。其实没有墙。阳光射到父亲身上,反射出一圈褐色的短促光线,父亲像一件古老的磁器灿烂辉煌。他脸上有一千条皱纹,每条皱纹里都夹着汗水与泥土,如纵横的河流,滋润着古老的大地。家乡的土地是黄褐色的,深厚的土层下边是古老的沧海,它淤积了多少不平,我爷爷的爷爷也许知道。父亲用古老的犁铧耕耘着黄土地,在地上同时在脸上留下深刻悲壮的痕迹。父亲用脸来证明着我的该打。
父亲面对着我站着,站得那么遥远寒冷,他的脸一团黑,疲乏地垂着两条长臂,长臂好像经不起大手的重量才被坠得这般长,血液好像流进了大手才使手这样大。父亲的手上凝集着令世界悲痛而起敬的表情,这表情唤起我酸涩的感情,我的舌头在嘴里熟了。
父亲挥手打我时,我的心里酝酿着毁灭一切的愤怒。新帐旧帐一起算!我看到我们父子三十年的空间里,飞动着铁锈色的灰尘,没有温情,没有爱,没有欢乐,没有鲜花。但是我知道我的感觉是偏颇的。父亲伛偻的腰背和遍身的泥土抗议我的偏颇。他的骨头上刻着劳动的深痕,他的眼睛里结着愁苦的车轮轧出的血红的辙印。他站在疲乏的椿树下,好像一个犯人,在我面前,垂下了灰白的头。我听到从他的喉咙里发出一阵“喀啦喀啦”的声音,随着这声音,父亲耸着肩,慢慢地慢慢地蹲下去。父亲被我打败了。我站在火热的太阳下,表皮流汗、内里冰凉,我的空壳里,结着多姿多彩的霜花,还有一排冰挂,状如狼牙……
我是匆匆赶回来的,穿着都市里通俗的衣裤。面对父亲,这衣裤顿时生辉,显出高贵和奢侈,它有多余的口袋和纽扣,还有不必要的干净。打败了父亲,我感到深刻的罪疚:一个几乎赤身裸体的老头子,七十岁,蹲在他的衣冠整洁面孔白胖的儿子面前,阳光照着他的近乎赤裸的身体,照着夏天的打麦场。
这是《爆炸》中摘出的几个片断。莫言一开始就懂得,作家是以作品本身而非外加的言论来发言、说话。如果把所有的记忆、感受、观点、愿望一缕缕撕扯出来总是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然而肉体和心灵一体的身体、生命体却将这些都深藏不露地融汇一起,而承载着生命主体的存在记忆和真实境况的一个动作、一个姿态、一个表情就包含着生命的千言万语。因此,《爆炸》的一开始,“父亲”给“我”的一巴掌就蕴藏着阐释不尽的丰富内容。而只有设身处地地理解才能领会出它们的意义,仅用理性的思维来推测的东西总是苍白的,失血的。因此,就得从认知和理性的天空降临生命存在的大地。
没有对人物的生存状况的切身的理解,是凭空想象不出这样的描写的,而这样的描写在莫言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这些描写,没有静止的物的色彩,每一笔都包含了对生活的力透纸背的叙事,只是这种叙事是以笔触的形式表现出来,是隐藏的,而不是展开的、语义陈述的,而是非语义的,它们像凡·高的笔触、色彩一样浓重凝炼地诉说着生存的“故事”,发出着主人公的生命存在的声音,内心的感受和愿望,因此它们蕴藏的意义就像海德格尔对凡·高的《鞋》所做的阐释一样,如果抽丝剥茧一样把这里蕴藏的意义用记叙的语言陈述出来将需下笔千言,滔滔不尽。
四、微型的和不完整的“对话”
我们看到,在莫言的笔下,即使对话,也往往是只言片语不成其“对话”的,然而这对话,这外表——词语的外表——非常独特的滞涩凝重、欲言又止,答与问外表错位、答非所问的对话,却沉淀、蕴藏、凝结、传递出主体内心多少的存在话语:
我迎着娘走去,我看到娘兴奋的枯脸,一阵热风把她灰白的乱发吹动,吹得更乱。女儿在娘的身后,提着一个绿色的长方形小收音机,畏畏缩缩地看着我。
母亲说:艳艳,叫爸爸呀。
我说:娘……
母亲说:你回来了?有什么事?
我说:没事。
母亲的眼泪流出眼眶。
……我说艳艳,我是谁?她轻轻地说:你是爸爸。我说:你怕我?她说:爸爸。
我答应了一声。
面对从远方城市突然回家的“我”,“娘”的感情书写在脸上——“我看到娘兴奋的枯脸”。但“娘”没有直接与“我”对话,她只是对“我”的女儿说:“艳艳,叫爸爸呀。”而“我”没有同女儿对话,“我”却回答的是“母亲”,但“我”其实什么也没有回答,因为“我”只是发出了一个字的声音:“娘……”。娘也没有涉及情感,“娘”只是“公事公办”“就事论事”地说:“你回来了?有什么事?”“娘”说“你回来了”没有叙事的意义,这是明摆的事实。“我”回答“没事”,“我”也就事论事——“没事”,所以,我的回答简短至极。然而“母亲”与“我”的情感的对话在这语义叙述——空洞简短的“无意义”的语义叙述的背后显露出来。“我”的感情在“语义”语言的陈述之外,在语境和语义陈述的语言的字里行间、空白处溢满了。我与女儿的对话同样是错位的、不完整的,但现场的亲情对话却溢出纸面。不深入人物的生命主体的内心世界,这样的描写和对话是不可能写出的。
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因为具有同时立刻听出并理解所有声音这一特殊才能(堪与他这才能媲美的,只有但丁),才能够创作出复调型小说。”[8]莫言的作品也让我们看到了这“同时立刻听出并理解所有声音这一特殊才能”。这是他的艺术的卓越之处。我们还举一段《爆炸》的例子:
……姑骂一声,又问我:你信不信,我真的见过狐狸炼丹。妻子说:姑,你别说,俺害怕。姑说怕什么!妻子说:您说吧,俺不怕。姑说,也不过是十几年前的事……
“妻”与“姑”的对话表面上看与叙事毫无意义,全无一点“来头”,妻的瞬间前后的话语变化莫名其妙,互相矛盾。但恰在这看似无意义的“闲言碎语”中,莫言“同时立刻听出并理解”到了妻子作为一个生命主体发出的隐微的主体之声:姑要讲“狐狸炼丹”,妻要作出“反应”,作出“配合”,作出“参与”,以显示自己主体存在的同时,表明对姑的主体性的一种积极回应,她说:“姑,你别说,俺害怕”。让姑“别说”,自是发出了自己主体的“不同”声音,“俺害怕”又向姑亲近地“撒娇”的同时,向姑“示媚”,对自己的主体性作出“谦抑”“自抑”的姿态。这种主体显示自身又轻轻自抑、压低自身的姿态,发出的是一种特殊的“话语”“声音”,试图与姑产生对话。当然作为一个生命主体,她是体察到自己与姑的现实“身份”地位的差异的。姑的回应即是证明:姑回答了她,甚至是带点喝斥,满足或“应付”了她的对话邀约,但姑给她的“对话”空间是有限的,“怕什么!”——既作出了“对话”回应,又及时结束了这个对话,拒绝了延续,没有“多余”。因为在姑的心目中可以和她对话的对象是城里归来的有知识有地位的“我”。而“妻子”也识相地对“姑”的这一点“对话”回应作出了“知趣”“知足”的回应:“您说吧,俺不怕。”——看来怕与不怕的真实性及提出,毫无意义,它们只是主体姿态显示、表现的一种特殊符号行为。整个对话的变化隐微精妙,传达出了几个不同的生命主体同时在场的一种微妙的话语交锋、交往,虽只一瞬,但传达的信息“惟妙惟肖”。没有特殊的才能和视界是察觉不到这些微末的生命主体内心的幽微的生命态度的悸动的。
五、“对话”主体的泛化
如果说莫言的作品处处捕捉、显示了微妙的“双声语”现象、笔触中的复调、微型的和不完整的对话现象,它们全息式地分布在作品的肌理中,鲜明地表现了他对生命主体间的对话关系、意识的确认的话,在莫言笔下,这种意识、这种复调和对话,还不仅展现在人物——人类生命主体——之间,也不仅展开在动物之间,而且还展开在人与动物之间,甚至展开在人与植物之间:
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悒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它们。父亲恍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八月深秋,天高气爽,遍野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它们是真正的本色的英雄。如果秋水泛滥,高粱地成了一片汪洋,暗红色的高粱头颅擎在浑浊的黄水里,顽强地向苍天呼吁……(《红高粱》)
除了动植物,无生命的事物在存在的特殊语境也具有了生命:
水红衫子!你越来越醒目,越来越美丽……你不要后退呀!你后退我前进……(《球状闪电》)
从生命主体的对话的角度来说,人与动物的相依相赖、平等对话的意识非常分明,这是莫言视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可以说,术业有专攻,莫言不以人类学为目标,也不以对学问、专门系统的知识的追求为己任,但莫言看待世界、生命的眼光是与人类学相通的。莫言具有人类学家一般的广阔的心胸视野。这在他创作的初期就表现出来了。如《白狗秋千架》对在艰苦年代父亲从舅爷家抱回白狗一事是如此叙述并阐释的:
舅爷是以养狗谋利的人,父亲抱回来它,引起众人的羡慕,也有出三十块钱高价来买的,当然被婉言回绝了。即使是那时的农村,在我们高密东北乡这种荒僻的地方,还是有不少乐趣,养狗当如是解。只要不逢大天灾,一般都能足食,所以狗类得以繁衍。
这样的对于生命世界景观的描述,让人感到一种人类学胸怀般的大气。其实人与动物之间的平等对话式态度已经成为莫言组织构造作品的一个基本原则或特征。《白狗秋千架》如此,《红高粱家族》更是如此,狗及其他的动物与人类一样是作品的主要角色,它们的故事以及它们与人的故事构成作品的基本内容,动物的生命故事参与到人的生命故事之中,成为人的生命生存的一部分,同时,动物的故事与人的故事构成一种复调式结构,形成一种映照对话结构。如果说,《红高粱家族》与《白狗秋千架》中,“狗”等的生活与故事如此凸现在人的故事中,是基于生存中的自然机缘的话,《球状闪电》中,动物与人的故事的共同书写,完全是一种鲜明自觉的创造式发现与设计了。如作者把远离人的生活世界、几乎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故事毫不搭界的刺猬,请进作品成为作品中一个贯穿前后的显著“角色”,成为一个“观察者”,刺猬甚至成为“说话者”“叙述者”“表达者”:
沟外雾蒙蒙的原野上,潮气像流水一样波动着。几只青蛙追扑着翅膀被打湿的蚂蚱和飞蛾。野草梢上挂着水珠,叶子背面沾满泥土。下吧,你娘的!它恨恨地骂着,顶多淹了我的窝,淹了我的窝,我就到蝈蝈家的牛饲料储藏室里住几天。
《牛》这篇作品中,“牛”自然是一大主角,这不仅是因为故事是围绕着牛展开的,还因为牛的命运、牛的生命遭遇也在与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故事形成一种双线互文照映关系。牛与人的对话也是形成作品的一个潜在的结构因素,牛自然始终以一个生命主体的身份出现。
六、作为结构方式的“对话”
莫言作品组织结构上的一个大的特点是多角度、多层面的对话性,即除了处处密布的隐形的、微型的对话以外,莫言的很多作品在整体和局部组织、组成以至于细节安排方面均表现出鲜明的、突出的“对话”结构、构造特点。
长期以来,人们对莫言的总体印象是感性、感觉的爆炸、激情的恣肆、放纵,甚至担心他的艺术创作在一任生命自由流淌、感觉自由舒展的情况下,一旦进入失控状态,会造成艺术的随意、紊乱、泛滥,然而莫言的创作,几乎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博大、冷静、清晰、坚定的眼光在统领、关照着作品中的每个具体情节的进展,并且他将自己的这种超出人类学之上的视野和观察以“对话”的方式呈现出来,无声地体现在作品的总体建构上时,我们会对莫言决断的冷静、眼界的开阔和胸怀的博大感到震惊。如《欢乐》这部杰作,我们都确认它是一部主体情感的宣泄之作,甚至有的人会认为它有些泛滥,缺乏节制,然而这部作品在整体构成上就是以多重对话的冷静方式构筑的。张志忠在《莫言论》中如此评价这部作品:
《欢乐》在莫言的创作中,是一篇大容量、多方面的揭示当代农村生活中的丑秽、长河大浪般的宣泄其心灵痛苦的主要作品,那构成作品的万余言的长段落,以及一气呵成的气势,正是作家长歌当哭、回旋不绝的情绪使之然,他原先分散在各个作品中的悲凉和愤懑都萃集于此,而又天衣无缝般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悲秋的挽歌”“献给死亡的歌声。”[6]
这段文字很出色地描述、概括了这部作品的整体风貌和具体内容、审美特征及风格,但这段概括还没有涉及《欢乐》整体上的对话结构安排。
其实,《欢乐》这部作品具有突出的对话特征,它至少存在以下几重对话:第一、作品的主人公与读者。这是不言而喻的,以“你”的人称叙述就意味着阅读是一种对话,读者与人物的对话、对视。这重对话在作品中也是无形的,因为出场的只是齐文栋,读者不存在于文本中。但齐文栋是在以倾诉的方式叙述,那么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自然就是“对话”的另一方,在阅读中出场,即对话在阅读中实现。因此,这是一个主人公与读者直面对话的作品,只是读者这一方是隐在的。美国精神分析批评家诺曼·霍兰认为,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是能动的,在这过程中读者的自我能与别人即作者的自我同一,“我的感觉活动也是一种创造活动,我通过它得以分享艺术家的才能。我在自己身上找到弗洛伊德所谓作家‘内心深处的秘密,那种根本的诗艺’,即突破‘每个自我与别的自我之间的障碍’的能力……”[2]28。霍兰这里虽然说的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一种心灵关系,但与任何一种对话关系中主体双方心灵关系展开的机理和效应一致,在这里正可说明读者在阅读时与“你”——齐文栋的精神对话关系。第二、人物之间的多重对话。这不是由外部结构形成的,而是由叙述内容完成。作品突出了不同人物,不同生命主体之间的内在碰撞与冲突。第三、文本内部不同文体、文本之间构成“对话”式修辞结构。这也是这部作品的两大板块的合拢之处,真个作品的博大境界的隐秘所在——整部《欢乐》的主体部分,百分之九十九的主体部分是由主人公齐文栋的倾诉构成的,但作者又“别有用心”地安排了一个“篇外篇:中学生作文选《我的母亲和她的小鸡》”。这就使作品的意义、容量和境界在这两个文本的对话式结构下达到新的广度、深度和高度。如果说前面的倾诉之声表达的是主人公个体生命主体遭遇的苦难的话,正像《白狗秋千架》里说的——“即使是那时的农村,在我的高密东北乡这种偏僻的地方,还是有不少乐趣”——那样,主人公的世界、母亲的世界虽然充满了丑陋、污秽和苦难,生命主体在经受着蹂躏与践踏,但民间社会依然有生命主体平等相处、亲切对话的一面或者说一种卑微虚弱的“世外桃源”的一面。这篇作文描绘出了民间社会的生命主体,贫困但有憧憬,贫困艰难但有信任有交流,贫困艰难但有智慧有乐趣,有自由平等亲切相处的一面。这个“篇外篇”既与“正文”形成齐文栋的生命主体内心的“微型对话”,又是作品整体性的、结构性的不同文本间的对话,也寄寓了齐文栋和作者莫言对民间生命主体、对母亲、母亲的生命世界的景观的另一面的发现、尊重与认同。从风格上来说,在泥沙俱下般的污秽、痛苦一泻千里、波涛汹涌的宣泄之后,是质朴清浅的民间平静生活的一幅素描。这就使作品的格局和境界绝然不一样了。由此也不动声色地体现出了作者的沉着、理性、宽容、博大的一面。其实《欢乐》中作者让齐文栋与母亲在“冬妮亚”家遭遇这一情节按一般阅读习惯会让人感到有些突兀、蹊跷,甚至有“落入俗套”之嫌。但这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了作者追求“戏剧”式对话的意图信息。作者不避落入俗套之嫌,强力让人物在此遭遇,也是作者对生命主体的遭遇和实情的打破物质时空而刻意显示其强烈对比差异所产生的结果。其实这是打破传统小说的审美习惯,强烈地要表达出这种“戏剧对话”般的生命景观的胆识、意志使然。是对话意识要求小说艺术牺牲让步或超越艺术习惯的结果。也许这种遭遇在那样的时空中发生的机遇不多,但打破物质之墙的阻隔,从人物生命主体的现实处境上来说,这种遭遇在主人公与母亲那里始终在背靠背地几乎每天发生着、展开着。因此,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说,这个“对话”安排不光是不得已的,也是令人回味,颇见深意、用心和艺术胆识的。
《酒国》这部以侦探小说为外形的作品,荒怪、辉煌而又神奇,它在总体结构上也是以对话的方式构成的。“肉孩”是一个待确证的客体,侦察员的任务是通过自己的侦探手段、本领来摸清“肉孩”事件的真相,由此侦破的一方与反侦破的一方之间展开了一连串的特殊对话,这是作品的主线。最终不同主体之间的“叙述”使“肉孩”这一客体的确证成为不可完成,主体的差异使这个“客体”存在的真实实在性被解构。除了这一线索引起的对话以外,小说在外部结构上就由几重主体和文本的对话构成:小说的每章由三部分三元组合而成——以第三人称对省人民检察院特级侦察员丁钩儿进行特别调查时的各种遭遇的叙述,酒国市酿造学院勾兑专业博士生李一斗与作家莫言之间围绕李一斗的习作所写的往来书信,李一斗的工作。如果再加上作品之外实际进行创作的莫言,那么,这种主体与主体,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往来就是很多重的了。
莫言的许多作品,《红高粱家族》《笼中叙事》《檀香刑》等等,无不在整体上隐藏着一种贯彻始终的对话结构安排,从莫言的整个创作来看,他的这种以对话的形式结构作品的方式的出现绝非偶然。
收稿日期:2010-01-10
标签:莫言论文;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文; 小说论文; 复调论文; 文学论文; 红高粱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欢乐论文; 父亲论文; 爆炸论文; 肌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