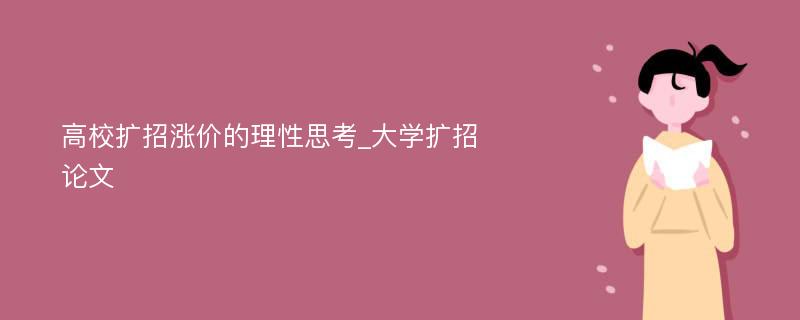
高校“扩招涨价”的理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00)04-0118-04
建国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基本上呈现出外延式增长的态势。这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的确具有现实的意义,但是由此而带来的质量、效益等问题也确乎值得忧虑。1999年2月我国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然而这一旨在对外延式发展进行调适的决策尚未完全启动,我国的高等教育似乎又偏向了外延式增长的一面。这或许恰恰体现了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所面临的窘惑。
1999年,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同时,扩招生的学费也大幅度提高(对此,我们姑且称之为“扩招涨价”)。高校扩招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教育自身发展的合乎规律性的需要;涨价既符合我国经济的增长趋势,也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表面看来,“扩招涨价”似无异议。然而,如此跃进式“扩招涨价”,其合理性则值得质疑。
一、两难的选择: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窘惑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从形态上来讲是“后发外生”型的,它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有着很大的差异,或者可以直接地说,我国现代化进程“是在面临外部现代性挑战的情况下强行启动的。(注: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第213页。)”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发展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国情。建国50年来,我们始终没有摆脱“穷国办大教育”的艰难探索,一个“穷”字已成为我们许多浪漫幻想的桎梏。然而,已现代化的国家在诸多方面(当然也包括教育,进而高等教育)对我们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示范效应。于是,我国的各项事业几乎全面启动,这对于一个原本贫困的后发展的人口大国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我国的高等教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探索。因此,这种示范效应与其说是一种发展的参照,勿宁说是一种强大的外部压力。于是我们的步履决不可能从容,于是我们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赶超”的主题。发展高等教育,成为我们赶超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抉择。然而,我国的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数量和质量的两难选择,相应地高等教育也便存在着内涵式与外延式两条发展道路的窘惑。或许是由于对大量高科技人才的需求,我国的高等教育主要选择了外延式发展道路,这突出地表现在1958~1960年、1983~1986年两次高等学校的超高速发展(注:房剑森:《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与
中国的实践》[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页。)。外延式发展道路对于我国在短时期内实现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校入学人口和毕业生数量的提高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此而导致的“学历饥渴驱动下的‘历’假与无‘力’及相应的高等教育孱弱之躯的浮肿”也日渐凸现(注:李燕:《当代中国教育的“后发外生”问题论析》
[J],《海南师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第8页。)。于是我们又不得不转向内涵式的发展以求调适。然而遗憾的是,外部世界的发展并没有给我们预定下自我调适的时间。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不仅要追赶上先行者已达到的教育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同时还要适应先行者当下的发展趋向,这正是作为后发展国家在教育上必须面对的迟发展的负效应。(注:褚宏启:《论教育的迟发展效应》[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第29页。)
已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对后发展国家的示范效应大大刺激了后发展国家公众享受高等教育的普遍期望,而且这种期望本身的增长比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所能满足期望的能力要快得多(注:褚宏启:《论教育的迟发展效应》[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第29页。)。当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正在由大众化迈向普及化(有的已实现了普及化)之际,我们的高等教育却面临窘境:强行赶超势必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平稳发展则难以满足公众的期望。这种窘境表现在发展方式上,就注定了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上的两难选择。其实,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究竟应当选择哪条发展道路,应视其国情而定,二者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在经过了50年的外延发展之后,应自然地转向内涵式发展,以求调适。倘若忽视了这一点仍追求超高速发展,必然导致一系列难解的尴尬。
二、难解的尴尬:跃进式“扩招涨价”导致的忧虑
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目标虽基本实现,但由此而产生的冲击波并未平息,它所导致的一系列忧虑也并未解决。
(一)跃进式扩招导致的尴尬
第一,大规模跃进式扩招非但没有减轻国家负担,相反,可能会给国家财政带来更大负担。按照教育部关于普通高校的设置标准计算,增加一个大学生需新增基本建设投资3.8万元(注:《北京大学课题组一项专题报告 结合常识与知识 直言高校大幅扩招涨价弊大于利》[N],《南方周末》,1999年9月17日。)。按照1999年的扩招幅度,每年按扩招48万人计算(注:焦新:《今年高考将于明天开始》[N],《中国教育报》,1999年4月6日。),4年内国家财政需增拨基本建设投资729.6亿元。倘若这笔款项如期到位,将会给本已紧张的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否则,便只有以牺牲教学质量为代价。
第二,据调查表明,目前我国普通高校的教师中,教学专任教师与教职工总数的比例严重失调。据《一九九八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普通高校有教职工102.96万人,其中专任教师只有40.72万人(注:教育部:《一九九八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N],《中国教育报》,1999年5月22日。)。专任教师紧缺一度造成教学质量方面的危机。如此48万学生大军一拥而入,无疑对师资配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增加专任教师势在必行。然而,这批教师从何而来?倘若这一点无法保证,那么牺牲教学质量又将成为必然。
第三,我国近几年来几乎每年都有部分高校毕业生未及上岗,便即失业,究其原因,并不是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已经过剩,而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及教育质量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高校培养的人才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这一方面表现为毕业生分配时往往出现专业不对口,许多专业的学生在择业时无人问津,造成结构性失业;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目前的高校毕业生普遍存在能力欠缺现象,无法适应社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改变这一现状的措施在于高等教育自身的改革,尤其是要优化专业结构,提高教育质量。也就是说,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应重点在内涵发展,而不是外延增长。倘若忽视内涵发展盲目跃进式扩大招生规模,无异于饮鸩止渴,雪上加霜。
第四,跃进式大规模扩招势必带来学历的迅速贬值。这一点印度等许多国家已成前车之鉴。我国目前尚有近两亿文盲,文盲总数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二。我们的“双基”目标尚未完全实现,却又将造成学历贬值,这一矛盾如何解决?这将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第五,我国普通高校实行的是严进宽出政策,这一点与我们的国情相一致,我们尚无法达到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水平。但是今年的“扩招涨价”使得分数线一降再降,事实上造成入学的门槛也大大降低。倘若我们不相应地改变高校教育管理体制,严把出口关,那么,这种“宽进宽出”的放羊式教育势必影响到高等教育的质量。
(二)大幅度涨价引发的忧虑
我国的高等教育在1985年以前是完全免费的。1985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可以在计划外招收少量自费生,学生应缴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自此,高等教育由国家和个人分担费用的改革探索便开始了。1993年,我国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东南大学开始了高校并轨收费制度的试点,1997年,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并轨收费制度开始实行(注:鄢波:《中国高教收费制度的历程》[N],《南方周末》,1999年9月17日。)。高等教育缴纳一定量的培养费,有其客观原因。从国家的角度讲,由于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且很少有企业和财团投资,高等教育确实给国家财政造成极大负担,从而相应地挤占了初、中等教育投资。这种教育投资的分配方式势必影响教育的长远发展,因此高等教育阶段有必要让学生个人承担一定量的学费。从家庭和个人的角度讲,随着我国年人均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大部分家庭有能力负担一定量的学费,而高等教育投资对于家庭和个人都会带来一定的预期经济收益,因此家庭和个人有理由、也有可能负担一定的费用。然而,无论如何,高校收费应考虑中国的国情,并进而考虑到现实的民情。因为,保障有潜力、有才能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毕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出发点。但是,高校扩招中的大幅度涨价却似乎偏离了这一基本出发点,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忧虑:
第一,我国自恢复高考制度的20多年来,高等教育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尽管目前教育界对高考指责颇多,但那只是高考自身的改革和完善的问题,我们历来坚持的择优录取原则不能丢弃。倘若真的如有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将大学生平均收费提到与其平均开支持平(1997年我国大学生平均开支为10666元(注:张孝文:《“教育产业化”的思考》[N],《光明日报》,1999年9月22日。)),那么,择优录取的原则势必受到冲击,就此,学生的社会成分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进而未来的人才质量将呈现怎样的趋势,我们对此表示忧虑。
第二,据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农民1997年人均总收入2999.2元,纯收入2090.13元,年均消费支出2536.79元,仅剩462.41元(注: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8)[Z],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345页。)。按照今年的扩招自费标准,每个学生近一万元的学费(有的学校对有些扩招生的收费已达几万元)竟然相当于一个农民近5年的纯收入!因此,是否会有一大批家境贫寒的优秀学生因昂贵的学费而失学,这是我们的忧虑之二。
第三,“扩招涨价”无疑是一种“分不够,用钱凑”的做法。可是,实际情况却是,有钱人不必“凑”,没钱的人没法“凑”。虽有人认为学费上涨可以缓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矛盾,但这种缓解却是剥夺了一部分优秀而又贫寒的学生的受教育权,而把分数较低但交得起钱的学生送进了大学校门。我国的贫富差距本已够大,如果又因此而造成受教育机会的极端不平等,这将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们深感忧虑。
第四,学生(尤其是家境贫寒的学生)即便能够交费入学,但心理上已经背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加之目前虽“金榜题名”,但日后就业仍前途未卜,倘若毕业后失业或收入过低,如此高额投入与经济收益之间的严重失调,极易造成某些学生的反社会心理,从而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对此我们有理由表示忧虑。
第五,1997年后,随着高校并轨收费制度的全面展开,高校中贫困生比例急剧上升。尽管从国家教育部到各学校都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力求保障贫困生的基本受教育权利,但随着收费标准的提高,相对于日渐庞大的贫困生队伍,政府和校方的努力无异于杯水车薪。于是贫困生勤工俭学将成必然。勤工俭学充分体现了这部分学生自强自立的可贵精神,但是有的学生却因此而冲淡了学业,这不能不令人担忧。更为可虑的是,有的学生虽未必贫困,但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在打工赚钱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这一点已有多方报道。那么,随着学费的大幅度提高,这种现象是否会进一步恶化,我们对此表示忧虑。
三、沉重的负载:拉动经济增长似难以奏效
有一种看法认为,“扩招涨价”会刺激相关消费,从而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我们认为:这一看法值得商榷。
第一,“扩招涨价”无法启动预期的银行储蓄
按预计,以每个扩招自费生交纳1万元计算,48万扩招自费生4年将缴纳192亿元,加上学费外的其它消费,将启动约200亿元的银行储蓄。即便果真如此,这200亿元在我国的5万多亿银行储蓄中,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况且,这200亿元也未必全部动用银行储蓄。事实上,许多家庭是把准备买房、购物的正常消费挪作了学费。如果真的“倾家荡产”为子女缴纳高额学费,就更没有能力消费了,在高学费条件下跃进式扩招是刺激消费还是限制消费,尚难下结论(注:杨帆:《发展教育要降低学费》[N],《南方周末》,1999年7月16日。)。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我国目前银行中的个人储蓄大部分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注:张孝文:《“教育产业化”的思考》[N],《光明日报》,1999年9月22日。)。而且据1996年统计,占全国人口70.63%的农村人口的总储蓄额7670.7亿元(注: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7)[Z],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页。),农民平均储蓄额并不高,这应当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因此,启动200亿元银行储蓄似难以实现。
第二,“扩招涨价”将导致更高的银行储蓄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中国父母的普遍心态。当普通高校收费标准大幅度提高之后,实际上恰恰触动了最敏感的消费神经。一个学生的学费几乎相当于一个农民五年的纯收入,这一残酷的现实将促使中国父母更加勤俭节约。实际上,“扩招涨价”动用的银行储蓄极为有限,但影响的将是全国学生家长的消费观念,并有可能导致新的储蓄热潮。这一出一进,孰轻孰重,实在难以预料。
第三,“扩招涨价”拉动经济增长一说似无充分依据
教育部门对国民经济总产出的拉动作用是有限的。1997年,高教部 门和其它教育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分别为0.85和0.83,在119个部门中排序分别为第100名和103名。(注:《北京大学课题组一项专题报告 结合常识与知识 直言高校大幅扩招涨价弊大于利》[N],《南方周末》,1999年9月17日。)有人依据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增长有必然的正比例关系。因为人力资本理论假定,教育与生产率存在正相关,教育的发展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然而“那些为教育做过最大努力的国家,都没有取得最高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的高额教育投资不仅没能达到经济增长和改变落后面貌的目的,反而造成本国的文凭膨胀与过度教育,辛辛苦苦培养的人才不断外流。(注:雷鸣强:《教育功效观——一个教育原理的新视角》[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5~6页。)”这已经成为我们发展高等教育的前车之鉴。教育之于经济的确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知识和人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得以凸显,从而“教育成为知识经济的支撑点和现实经济的生长点”,这乃是教育经济功能的正常体现。然而教育的经济功能不是万能的,企图通过高校“扩招涨价”拉动经济增长,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
结语
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也必然地要走向大众化进而普及化,这一点,我们笃信不移。但这只是明天的理想,而非今天的必然。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考虑中国国情,办教育同样需要考虑中国国情。倘若不考虑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不注重教育结构的协调配合,盲目地大规模扩招,极易导致人才过剩和人才奇缺的双重浪费现象。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前提下,侧重于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招生规模可以在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适度扩展。这一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曾注重外延式发展的后发展国家来说尤其重要。
收稿日期:1999-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