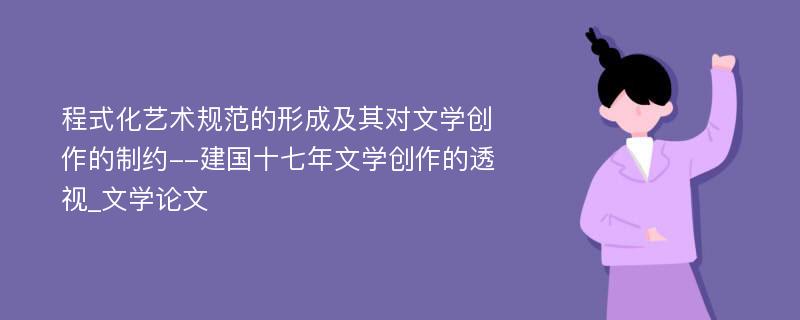
模式化艺术规范的形成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制约——对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创作的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创作论文,其对论文,透视论文,模式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一定程度上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衡量无产阶级文艺的标准,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和阶段,标志着中国文学走向了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也就是说,中国新文学的总体风貌诚如毛泽东所概括的那样:“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然而,我们也不能讳言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尺度等对文艺创作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理论命题,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审美发展和生成的严格制约和苛刻要求。既然无产阶级的理论要求文学艺术家们为人民大众而创作,那么这就要求作家们必须认真面对人民大众文化层次较为低级的严酷事实,这就要求作家们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到充满泥土芳香的场景之中。在这种文化氛围和时代背景之下,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审美文化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而审美视角的改变必须依赖于创作主体内在的自觉皈依才能得以实现,但是当代众多的文艺工作者由于自身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在这种特定的时8刻对这种政治环境的适应就远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然而激进的政治体制、硬性的文化政策以及落后的文化环境,却促使那些自觉或不自觉的作家艺术家们必须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恪守这时代的统一要求和集体的共同意愿。我们已经说过,在毛泽东《讲话》的指引下,中国文学无疑已步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作家们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同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文艺实践纳入到了一个时代需要的大众化的轨道。也就是说,在鲜明的政治立场的统摄下,作家的文学创作不仅要“镜子”式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具有革命性倾向的社会和人生,而且要表现出一种对革命理想积极追求的昂扬向上的情绪。然而不必否认,这是对于政治的甘愿认同。这种认同,扼杀了作家艺术家们在艺术审美上的独特选择,因此在政治指导下的审美形式和功利色彩便成为了作家艺术家们内在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艺术意识,他们纷纷在对时代、政治之于艺术、审美的苛刻要求和认同前提下进行着艺术实践。
建国以来,当代中国文坛向所谓的“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发起了一连串的攻击和声讨,文学创作也频频受到了诸如“难道我们的工农兵就是这样吗?”的疑问和责难。因此,中国的当代文学创作便逐渐走入到了一种只能描写“新人新事”、只能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机械的模式之中。通观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创作,在思想观念上陷入了一个只能表现通体光明事物和描绘“高、大、全”形象的窠臼,在形式技巧手法上坠入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深渊。一些极左的文艺理论家们在一场又一场的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中,又善意地曲解着文艺思想的有关内容,把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一步一步地引入到了单纯地充满着政治功利性色彩的“工具论”范畴。在这种歪曲的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的世界观的指导作用放置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作家艺术家们的具体文学创作实践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被“阶级斗争支配一切”的因果命题和理论模式所支配。也就是说,文学创作一旦离开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作家艺术家们就写不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一种整体的文化规范和时代要求,新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几乎没有人敢打破和冲撞这种理论模式和创作规范。因此,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从局部上讲陷入了一种对现实进行“京剧化妆式”的粉饰阶段。作家们不敢贴近现实,亦害怕走向人生,总是与现实、人生保持着一段若即若离的距离,以致整个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没有直接、真实地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缭绕文坛的是历史的尘埃和烟云。文学不能“干预生活”,文学不能针砭时弊,文学不能逼近现实生活中的灰色和人的心魄灵魂。若越雷池一步,立即就会被各种各样的社会的浪潮所吞噬乃至所扼杀。路翎的《在洼地上的“战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李国文的《改造》、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李威仑的《爱情》、宗璞的《红豆》、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海默的《洞箫横吹》、郭小川的《望星空》、吴雁(王昌定)的《创作,需要才能》、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巴人的《论人情》、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等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几乎都成为历次文艺思想斗争中攻击的目标,它就是对所有文学艺术家们的一种威胁和警告。
总之,由于当代作家那股强烈而又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化审美艺术观,由于当代作家不是以艺术家的身分来观照现实,而是以革命家或政治家的眼光来判决是非,并把这一是非价值的判断过程和判决结论,直观地套入文学艺术的营构之中,这就形成了对当代中国作家文艺创作的种种限制或制约,也就决定了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创作一种模式化艺术规范的形成。
二
首先,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创作选择的文学背景几乎形成了惊人的同一性。
毫无疑问,新中国的诞生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进程。刚从苦难和战争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大众,虽然还面临着种种思想上的矛盾、困惑和物质上的贫穷、困难,但却走入了一个开天辟地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大都从革命要求出发,深刻反思过去,力求脱胎换骨,设法跟上新时代,带着蓬勃的青春朝气和为理想而献身的斗争精神,以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改变了历来那股弥漫在文学艺术天地里的为摆脱物质或精神苦难而斗争的阴凉气氛,从而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一种充满着希望、洋溢着光明的欢乐情绪。勿庸置疑,这种新的精神状态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历程的新的起步和开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规范了新中国文学创作的社会主义方向,指定了文学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方针,从而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这都推动或限制着文学创作切合或迎合着政治或时代的要求。作家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所写的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实际革命斗争中发生在中国人民身边的事情,如火如荼的农民斗争,你死我活的战争场面,热火朝天的建设情景,这些事情本身的价值又与时代提出的政治要求紧密地粘合在一起。因此,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创作无一不是在政治意义和时代命题规范的事件上取材,也无一不是摄取这些特殊题材或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斗争意味,而很少去发掘政治题材蕴藏的人情或人性色彩,从而造就当时或后来的接受主体由此获取的感慨或启悟是几乎清一色的政治式的说法和教化。
我们以取材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文学艺术作品为个案,对于上述观点就会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和认识。美国侵略朝鲜,正当中国人民欢欣鼓舞、高唱胜利凯歌之际,因此这种严重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命安危的行径,自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从而引发了当代中国文坛新的画面的出现。也就是说,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不管是亲身体验了战争生活的作家,还是那些只是通过新闻媒介或道听途说了解些许战争气息的文人,无一不是在上述意义上取材,抗美援朝的题材以及这个题材本身的政治色彩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压倒一切的主题,但却不能挖掘这个题材政治意义以外的任何其它诸如人性、爱情之类的素材。
在诗坛上,不少新老诗人以诗为枪,在抗美援朝的政治意义上奋笔疾书,并且形成了一股群众性的诗歌创作热潮。大批诗人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把朝鲜战场上的体验或见闻,用诗的语言迅速地传达给全国的人民。未央的《枪给我吧》、《驰过燃烧的村庄》等作品,都曾感动过亿万的中国人民。普通志愿军战士麻扶摇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由周巍恃谱曲以后更是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和朝鲜的前线后方。石方禹的诗作《和平的最强音》,也以高亢的音调,宏伟的气魄,犀利的语言,高唱着保卫和平、抵抗侵略的主题。然而,这些诗歌却缺少对处于和平时期的战争气氛下的中华民族的复杂心态的勾勒,因此阅读起来虽然若战鼓般铿锵有力,但缺少一种余音袅袅的后劲或魅力,其原因就是诗歌选择了过多的政治化的社会背景。
建国初期的散文园地里,影响更大的无疑也是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通讯、特写以及感怀性的作品。散文作家也象诗人们一样,匆促地在这种题材的政治意义上着笔和描绘,从而形成了数以千计的散文作品在思想主题上的一致,甚至在形式、风格方面都达到了统一。当时,许多新老作家深入抗美援朝第一线,创作了许多动人心弦的战地通讯和特写,如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刘白羽的《英雄城——平壤》、《我们在审判》,菡子的《和平博物馆》,以及华山、杨朔、碧野等人的通讯报道。这些散文写的事实抒的情真,读起来感人至深,但象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之类的那样善于发掘志愿军战士心灵的文章却并不多见。因此,虽然文艺界曾将这类题材的作品汇编成《志愿军一日》、《志愿军英雄传》、《朝鲜通讯报告选》等许多类型的大型文集或文册,但真正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著地位的文章并不多。也就是说,这些散文虽然构成了多彩多姿的军事史诗般的画卷,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强烈的社会反响,但由于过分从政治意义上着色,也就失去了文学的原本色泽。
当然,中国当代的作家并不是那样的缺乏远见卓识,象小说作家路翎就敢于在火光冲天的战争氛围中捕捉志愿军战士灵魂中升腾起来的爱情火花,但仅仅是那么些微的用笔,路翎及其作品《在洼地上的“战役”》就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攻讹,这样的政治环境还不令其他作家望而却步惊若寒蝉?也就是说,写抗美援朝虽然形成了文学创作的一股巨大的潮流,但这股潮流却并不具有浪花朵朵的绚丽场景,因为时代要求作家只能在这个题材的政治意义上运笔。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大都是从时代精神出发,写作家在朝鲜战场上的亲身见闻和感受,生动地反映了中朝人民在硝烟烽火中的生活经历,但点染出来的也只是生活的局部或片断。作家们虽然是把祖国的命运放在整个世界形势发展的趋势上抒写和思考,纵情歌唱着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情操,竭力强调着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保卫和平必然胜利的坚强信念,愤怒控诉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罪恶行径,但并没有去细致入微地描绘或勾勒人物的心理状态和生命流程。这些作品虽然成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生动记录,但由于政治对于文学的过分控制,它们也就失去了真正文学上的色彩和意义,因为文学毕竟是人学。
造成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背景的同一性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对文学的严重涉足,控制过严,干涉过多,造成建国以后一系列的错误的“文学运动”;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作家过份的政治崇拜,缺乏理性意识,很容易、也很自然地受命于时代的命题和政治的约束。既然政治和时代规定人物的感觉、感受、心理意识等灵魂深处的东西不能描写,那么就去反映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和惊天动地的政治斗争罢了。于是,纷纷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是战争题材和社会政治斗争题材(包括土地革命、土改运动、互助社与人民公社运动)。这些政治色彩浓厚的题材和主题,便被奉为十七年文学创作的圭臬。这样,文学创作活动就不再是一种复杂的创作主体的审美创造和审美体验,而是成为了一种对现实生活的简单的、机械的“反映”和政治概念的演绎,使得文学艺术家们拼命进行创作领域的“思想改造”,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以积极适应社会政治的要求,若不如此那就只能在极端的困惑或无情的打击之中消逝于当代中国的文坛。总之,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标准”,无情地制约和规范了当代中国作家的审美个性,严格地迫使着当代中国作家把自己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艺术个性淹没于一种崇高或壮美的艺术共性之中,从而使得当代中国十七年文学创作走入了一条狭小的路径。
三
其次,十七年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的阶级化、脸谱化的现象十分严重。
处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中,人们的阶级性比平时表现得更为鲜明,也许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让人觉得惊异的是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与当时中国整个政治形式配合得那么密切和默契。文学作品的艺术构思是以“阶级斗争支配一切”的因果命题和哲学思想来表现政治概念、推动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选择细节和描写自然环境乃至社会场景的,从而成为当时社会政治斗争的笨拙的形象演绎。
文学艺术一旦成为了社会政治的教科书,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就必然缺乏基本真实的“自然属性”,人物的一切就自然服从于它的“社会属性”,这样就给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描绘套上了“阶级化”、“英雄化”、“脸谱化”的缰绳和枷锁,从而失去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要求的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最起码的人性层次和心理层次。因此,阅读这个时期的大多数的文学作品时,就会毫不奇怪地发现其中的人物形象的身分是那么的泾渭分明:一条战线上站立着的是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或先进分子,另一条阵线上的势必就是反动人物或中间人物或不觉悟的人,他们的性格属性、个性特点好象是与生俱来、先天注定的,既没有性格的变化和发展,更没有灵魂深处的矛盾和冲突,以致文学批评界在评价作品、新闻出版界在介绍作品的时候,常常轻而易举或不约而同地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嵌入诸如此类的套语之中:“作品成功地塑造出革命的‘农民’或‘工人’或‘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或“其显著的特征是强烈的阶级爱憎和无畏的斗争精神”,这些评语是对正面人物的赏识;而“剥削本性”、“豺狼心肠”、“罪恶行径”等词语,不用仔细地品味,就知道这是对反面形象所贴的标签。至于对中间人物的评说,就还有一些“软弱”、“害怕”、“动摇”但“最终发生了转变”之类的大段套话。
从评论界、出版界对人物形象所作的阶级定性来看,当时的文学艺术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的阶级色彩是相当浓厚的。用“文必斗争”来描述当时的创作形势,也许并没有夸饰的因素。这从极具权威性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十七年前后所出版的一些长篇小说的“内容说明”中,就可以发现“斗争”确实形成了十七年时期文坛上的一种时髦的文化景观和思维属性。1950年,长篇小说《沸腾的群山》出版时的“内容说明”是:“这篇长篇小说,写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工业战线的斗争生活”。对文学作品以“斗争”一词予以描述的风气,一直延续到“十七年”以后,如1972年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出版时,它的“内容说明”依然是那种口吻:“描绘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战线的斗争生活”。由此可见,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习惯于以两条战线的两类人物的“斗争”做为文学作品描写的核心和重点。这样,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就势必呈现出概念化的面貌,阶级化的色彩。也就是说,十七年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过多地、过重地承负了政治符号所具有的功能,人物的阶级身分过分的显露和明确。
譬如,当时占有很大分量的长篇小说,它所塑造的中心人物必然是向正面的工农兵形象也就是所谓的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倾斜。因此,十七年文学艺术作品营构的人物形象长廊,扑面而来的都是光彩照人的正面人物的英姿和丰采,而中间人物或反面人物却不能在作品中担任主角。象名声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它塑造的人物形象的阵线是相当分明的,正面人物自然是具有“高、大、全”丰采的梁生保,他自然也就成为了作品浓墨重彩的人物主角,也成为了评论界予以高度注意的中心;而中间人物梁三老汉的血肉虽然比主角更具个性、更为丰满,但他只能成为正面人物的陪衬,也得不到批评家们的关注,若有评论家来指手划脚那么健在的评论家严家炎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就是对世人的一个有力的警戒;至于反面人物,则只能退出人物舞台的中心,完全只是正面人物或中间人物的点缀,更只能遭受批评界的讨伐和鞭挞了。而另一重要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由于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做为作品的主人公,就在当时的创作界、出版界和评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以至作品本身也不得不面临被修正、删改的命运。
总之,文学创作为了迎合政治观念的需要,不惜牺牲自己固有的艺术色彩,从而彻底抛弃人物形象的原有性格,以适应时代的需求、顺从政治的需要。在这种创作模式之中,正面人物没有缺点,是一些“高、大、全”之类的顶天立地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没有世情欲望的英雄人物;反面人物则只有一个本质:坏,彻底的坏,顽固不化,歹毒阴险;以至中间人物的塑造,都有一个较为“先进”或较为“落后”的分别。
人物塑造的单一的、机械的、僵化的思维方式,使得作家们固定以一种机械的眼光来看待人物的一切,纷繁复杂、斑驳陆离的大千世界只是由革命的阵营和反动的保垒这两个没有血缘联系的、保持森严界线的板块所构成。反动阶级只有“坏”这样一个基本的本质,革命的阵营也只不过有主要英雄人物和一般英雄人物的区别罢了。在这种模式化的结构安排中,一般群众有的只是“先进”与“落后”的划分,领导之间只有两条路线的分歧,个人只有“公”“私”矛盾的冲突。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的一面,要么是无产阶级的,要么是资产阶级的;每一个人物都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的一方,或者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或者是资本主义的道路。生活在这两条道路或两种思想之中的人们,没有个人的欲望,支配他们一切行动或生活的全是清一色的思想或政治路线,因此个人所具有的“人”的欲望与要求就全部被排斥在文学艺术的殿堂之外。
当作家们从政治观念出发而摒弃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审美感受时,他们就必然戴上了“阶级”的滤色镜和“斗争”的变色镜来反映生活,这即使在一些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中也难以避免。比如著名作家柳青的优秀长篇小说《创业史》,它虽然是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阶级界线是截然分明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正面人物是梁生宝,他虽然并不象有些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那样被描写成指手划脚、夸夸其谈的模样,但在尖锐的矛盾冲突发生时,只要他一出现矛盾便会迎刃而解,疑云和误解就会烟消云散。他一心为公,没有丝毫个人享乐的欲望,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的革命事业。小说这样描写他的这种心态:“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觉得带劲儿,才活得有味”,“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由此可见,人物的阶级性相当鲜明。而反面人物就是那三个被区分得清清楚楚的“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姚世杰,他们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在后面两个人物身上就好像具有一致的天然的属性,虽然他们的经历和行动都带有各自的特征,但作为阶级敌人的反动本性却具有相当一致的、鲜明的共性。总而言之,十七年时期的作家们的艺术构思习惯于以“斗争”为故事的框架结构,为人物贴上鲜明的阶级标签。
显而易见,“人物阶级化”的塑造方法,并不是文学家们天生就要重视的方法,它不是从审美的角度来描绘人物,而是一种庸俗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角度。从这种角度写出的文学作品,其“工具”价值就必然盖过审美价值。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力不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本能的生命或欲望的冲动,而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热情,一种政治性的急功近利的心理,他们一旦进入艺术的审美构造,就没有勇气抛弃他们平时笃信的政治主张的理论信仰,从而以这种世界观指导自己笔下人物性格的生成乃至发展。我们不得不为当代中国作家感到一种莫名的遗憾和惋惜,他们对政治观念的盲目屈从,使得他们塑造的人物形象流于政治符号化,缺乏艺术感染力。其实,只有克服这种人物塑造公式化、模式化的束缚和规范,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才会真正地充满生气和活力。
四
结构、线索的单一,也是十七年中国文学的一个让人批评和指责的毛病。
由于时代政治在作家真正投身于文学艺术创作之先就已牵制着作家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构思,并且以一股强大的力量制约着作家文学艺术创作的生成和发展,因此十七年文学不仅在背景上表现为同一性,在人物塑造上体现为政治化,而且导致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品味亦相对地匮乏,这首先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的结构、线索过分的单调。从上面提到的文学家们习惯于从“斗争”的角度来构思情节、塑造人物来看,批判什么,歌颂什么,都表现为一种公式化、模式化的形式,这些都已粗略地显示了十七年文学结构的浅薄和线索的单纯。作家们喜欢把文学的世界简单的一分为二,正面的和反动的。譬如,《山乡巨变》的正面为邓秀梅,反面就是龚子元;《红旗谱》的正面是朱老忠,反面就是冯老兰父子;《保卫延安》的正面是以周大勇等人为代表的人民英雄,反面则是国民党反动军队;《红岩》的正面是许云峰、江雪琴、华子良、齐晓轩等,反面则是徐鹏飞、甫志高;《红日》的正面是沈根新、梁波,反面就是张灵甫等。此外,如《林海雪原》、《李双双小传》、《不能走那条路》、《阿诗玛》、《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大多数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体现为这种正、反结构故事情节的方法。如果抽出其中的一方,对立的一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了。线索、结构的单一性特征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散文是一种缺少严格规范的文体,其文体的边界不在它于有一个共同的写作模式,而在于以其本质特征来规范文体的前提下,充分显示文类的自由、自在、自如的优势,散文创作应当有多种风格、多种写法。遗憾的是,十七年的散文创作却被提升到了一个规范性的高度,一个格式化的层面,正如秦牧在《散文创作谈》中表述的那样:“每一篇散文,它的中心总在宣传一个什么思想。正面讴歌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讴歌共产主义,鞭挞反动腐朽事物的散文固然是这样,就是剖析一件事情的道理,描绘山川风物,给人以开拓知识领域,温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或者获得美的感受、情操的陶冶的那部分作品,又何尝不是这样。”在社会政治对思想统一的要求日盛的背景之下,在对文艺工作者不断进行改造和思想单纯化教育的情况下,作家的心理结构日趋单一,导致散文创作在艺术结构、线索设置上日趋简单化,至今让人诟病的“杨朔模式”就是有力明证。杨朔散文几乎是千篇一律的面孔,先写景、写人,最后来一个情感升华,提炼出一个崇高的主题。当这种写法作为一个程式固定下来,在这种炉火纯青的大一统、超稳定格局中,散文的抒情本质和审美功能怎么不会日渐衰退?
而风格的单一化,也是十七年文学表现得过分单纯和片面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缺点。
虽然党的文艺政策在重视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个唯一的方向外,提倡文学艺术风格、形式、题材等方面的多样化,反对千篇一律、刻板和狭隘化,但客观上还是有人运用了行政命令的手段和方式对这些方面做出了严格的要求和制约,不仅强调写重大题材、写高大英雄,而且要求创作方法的统一,要求文学艺术作品具有高昂的格调,于是建国后十七年文学艺术的创作风格趋向豪放化、单一化,以至于其它类型的艺术风格则被禁止和扼杀,完全失去了生机和活力。我们知道,诗歌是一种最容易显现文学家艺术个性和风格的一种文体,但当代十七年时期的诗歌风格却并没有“百花齐放”。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文艺界不仅对诗歌的题材作了严格的限制,而且对诗歌的风格、形式都作了统一的要求。“西洋”式的不准创作,“自由”式的不能发表,清丽阴柔的不被欢迎,流行的只能是一味传统式的诗歌如民歌,其风格得如烈火,得如战鼓。凡此种种,使得十七年时期的诗歌拥抱世界的方式就比较的单一,诗人的艺术个性受到了严重的削弱。由于过分强调诗歌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加上五十年初期前苏联文艺思想的影响,使得既是思想原则又是创作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受到了高度的推崇,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唯一的创作方法。以描写现实生活现象和以抒写现实政治信念为主的诗歌,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得到了一个最大限度的发挥,而其它把握世界的艺术方法则受到了限制和排斥,尤其是现代主义的艺术方法受到了最为严厉的谴责,它被笼统地当做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艺术的同义语。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们不得不在诗歌中逃避表现“自我”,逃避对客观世界观察、感受的独特表现,回避对属于自己内心深处情感的抒发,而那些不满足于当时对生活场景进行描摩和作为政治“代言人”的激情宣泄而重视书写自我意识的诗人则受到了尖锐地批评,如艾青的《在智利的海岬上》,何其芳的《鹰》,郭小川的《致大海》、《望星空》,流沙河的《草木篇》,公刘的《迟开的玫瑰》,蔡其矫的《红豆》、《川江号子》等,由于这些诗歌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诗人艺术创造的个性化和艺术性的追求,就遭到了文艺界的不断升级的批评。这样,一大批富有独特艺术个性的诗人,有的不得不中断艺术创作,有的则不得不把牺牲自己的独特个性作为继续从事创作的重大代价。于是,原本最富有精神个性的诗歌风格,出现了类似口号式的豪放化,这种单纯的艺术风格模式限制了诗歌艺术风格多样化的发展。而其它文体如小说、散文、戏剧的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也受到了扼杀,譬如类似茹志鹃小说《百合花》那种细腻、委婉、俊逸的艺术风格发展的步履就相当的艰难。
综上所说,在为政治服务的社会文化背景里,十七年文学创作以极大的热情迎合政治,使得文学创作模式化艺术规范渐渐形成,在这样的文学世界里,我们看不到新颖的题材,多样的风格,精湛的结构,丰富复杂的文学世界被干巴巴的政治教条牢牢地控制着。显然,这样的文学状况是不能让我们满足和自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