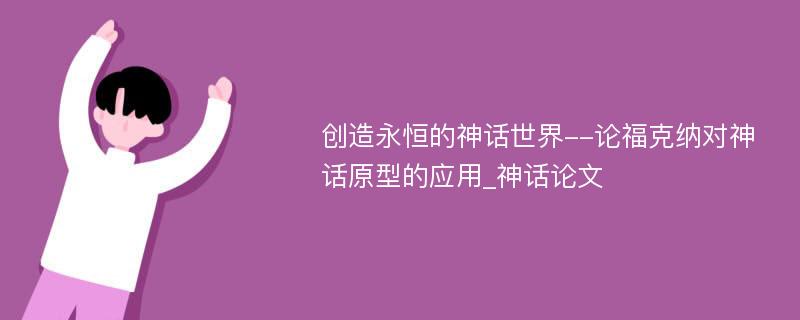
创造一个永恒的神话世界——论福克纳对神话原型的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话论文,原型论文,创造一个论文,福克纳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福克纳是一个善于运用神话和创造神话的作家,他总是“试图在集希腊——罗马,希伯来——基督教因素之大成的人类神话和现代历史之间建立一种普性的关系”。[①]他借助神话把对美国南方历史的反思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思索联系在一起,使得他独创的约克纳帕塌法神话世界不仅成为美国南方的缩影,而且成为全人类的象征。
一
福克纳运用神话原型时最常用的方法是为自己的小说安排一个对应的神话原型结构,也就是有意识地使其作品的故事、人物、结构与人们熟知的某一神话故事大体平行,由于隐含的神话参照系的存在,作品便突破具体的内容,获得一种超越时空的意义。他的主要作品《押沙龙,押沙龙!》、《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都运用了这一方法。
《押沙龙,押沙龙!》写的是主人公托马斯·塞德潘一生戏剧性的起落沉浮。四个叙述者共同创造了塞德潘的神话,由于他们视角的差异,使塞德潘的故事显得有些扑朔迷离,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浪漫传奇色彩。《旧约》中大卫王的故事和古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王的传说时隐时显地映衬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变化,使得塞德潘又像远古世界的悲剧英雄。塞德潘、大卫王、俄狄浦斯三人的故事都是由这样几个基本的故事构成的:①父子反目:A,波恩报复塞德潘;B,押沙龙反叛大卫王;C,波吕尼刻斯兄弟为争夺王位对父亲弃之不顾。②兄弟相残:A,亨利杀波恩;B,押沙龙杀暗嫩;C,波吕尼刻斯兄弟俩互相残杀。③兄妹乱伦:A,波恩和朱迪丝恋爱;B,暗嫩奸污他玛;C,波吕尼刻斯和安提戈涅有乱伦倾向。[②]三人的故事还蕴含着共同的主题:诅咒、命运、惩罚、报应等。古老的神话传说不仅为小说提供了宏阔的历史背景,而且暗示了主人公无可逃避的悲剧性命运。《押沙龙,押沙龙!》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劫数难逃的宿命气势,隐含的神话参照系的存在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旧约》中大卫王因霸占大臣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而受到耶和华的诅咒和惩罚。如果说大卫王的祸患完全是咎由自取,现世报应,那么俄狄浦斯王的命运则远在他出生之前就已注定。他杀父娶母是因为神要惩罚他父亲拉伊俄斯背信弃义,诱拐恩人的儿子,波吕尼刻斯两兄弟互相残杀,既是他们祖、父两代人罪孽的直接后果,又是这个家族不可避免的厄运,这个厄运在其祖先卡德摩斯建立忒拜王国之日便已注定,龙种武士的诅咒终于应验了。塞德潘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他把自己旺盛精力和超人的才智投入到一项注定要受到诅咒、要毁灭的事业之中。他在受到侮辱之后立即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伟大的规划:要打进上流社会,而且确定消灭贵族血统,建立一个永世相传的家庭王朝。他被自己的“规划”攫住了,身不由己,不能自拔,以致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观念,丧失了人性。不像是他选择了这种命运,倒像是命运选择了他。和俄狄浦斯王一样,塞德潘是命运的牺牲品。不同的是,塞德潘的命运就是他所处的环境,如果不是处在南方以白人为中心,注重血统和出身的文化背景下,他就不会那么看重自己的“规划”,他只是盲目地顺从了南方社会的价值规范。南方经济文化的核心就是奴隶制,所以塞德潘就是奴隶制的牺牲品。奴隶制不仅戕害了黑人,而且对白人也是一种伤害。塞德潘及其家族的毁灭就是南方历史的缩影,他的命运就是南方命运的象征。就像卡德摩斯在建立忒拜王国之初就受到龙种武士的诅咒一样,南方一开始就因为实行奴隶制而受到诅咒,所以天罚也就是不可逃避的了。
《喧哗与骚动》的故事和结构是以基督受难周的事件为原型的。小说中的1928年的三个日期,正是那年的基督受难日、复活节前和复活节,昆丁自杀的1910年的那个日期正是“圣体节”的第八天,康普生家的子女在复活周的行动和基督的生平有许多类似之处。作家用基督的传说作为康普生家故事原型的参照目的何在?主要在于借康普生家的故事表现美国南方的堕落与拯救,人类的堕落是由一个女人夏娃引起的,康普生家的堕落也与一个女人凯蒂有密切关联。小说的基本故事框架就是一个女孩的堕落以及她的堕落所引起的一系列后果。凯蒂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尽管她始终没有出场,却是几个人物的意识中心。她的堕落无疑是给衰败的康普生家雪上加霜。“凯蒂是心理上、美学上、也是道德上的失落。凯蒂是福克纳世界中失落的象征——天真、完整的年代顺序、人格和戏剧统一性的失落。”[③]凯蒂的堕落造成了笼罩整个小说的失落感,给康普生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班吉失去了唯一的关心和爱;昆丁失去了想象中的情人和家庭荣誉感而自杀;杰生失去了银行的工作,由于断送了一辈子的前程,他怨恨凯蒂一辈子;小昆丁变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在昆丁的意识流中多次出现这样的诗句:“那声音响彻在伊甸园的上空,人间的第一次婚礼。”她把妹妹看作夏娃,凯蒂本应是南方淑女的典范,却走上了堕落的道路,破坏了康普生家族的荣誉。南方淑女原是优雅、高贵、贞洁、完美的象征,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昆丁为此深感痛苦,他要设法对堕落的妹妹进行拯救。但他思想乖谬,竟然企图用乱伦和死亡为妹妹犯下的罪进行赎救。他在潜意识中把自己当做基督,所以在他独白部分不断出现基督的形象。他砸烂了自己的表,企图逃避历史的时间,但不断传来的报时声则提醒他无时无刻不在历史之中。“在长长的、孤独的光线里,你可以看见耶稣在彳亍地前进。”耶稣是孤独的,因为他超越了历史,而人却无法超越历史,历史只能是人唯一的存在方式,昆丁的痛苦和绝望正在这里。凯蒂沿着堕落这条路一直栽到地狱的最底层——她成了纳粹军官的情妇,她失去了一切,她已经再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拯救了。凯蒂的堕落象征着南方传统价值观念的彻底崩溃,昆丁的救赎也就成了自欺的虚幻之梦。耶稣基督的受难、复活拯救了全人类,康普生的子女连自救也不能,其中的反讽意义不言自明。
像福克纳的大多数作品一样,《我弥留之际》中的大部分人物和事件都具有双重的意义,除了在故事里的作用之外,他们又都是具有普通意义的隐喻和象征。这部风格奇异怪诞的作品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是美国南方穷苦白人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宗教性和象征性的故事。虽然地理背景在美国南方,却隐含着远古时代的意象,通过本德伦一家展现了人类共同的处境和命运。
《我弥留之际》的整个故事框架属于西方文学中流行的探求文学,古典文学中的《奥德赛》、《神曲》、《天路历程》都属于探求文学的典范之作,它的基本模式是主人公以超人的毅力经过漫长艰辛的旅程终于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探求文学又是传奇文学中的一类形式,按照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阐述的观点:从历时的眼光看,文学的发展表现为五种基本的形态,即“神话”、“传奇”、“高级摹拟体”、“低级摹拟体”和“讽刺”。在这五种形态中,神话是一极,其他文学形态不过是神话的递次的置换变形,讽刺则标志着各种文学形式循环的结束,转而返回神话。他说:“现实主义的虚构中出现的神话结构要使人信以为真就会涉及某些技巧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法则可统一命名为‘置换变形’。”[④]弗莱关于文学形态的五种分类和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体裁分类不是一回事,它主要表示主人公在类属或程度上与故事中其他人物及环境之间的关系和他的行为能力的高低。传奇文学中的主人公在类属上是人,但他在程度上要高于其他人和他处的环境,他往往具有非凡的勇气和力量,而且还有魔法般的武器,用超自然的力量达到目的。《我弥留之际》是传奇文学的再次置换变形式样,或者说是传统的探求文学模式的讽刺性摹拟。它的神话原型可以说是《奥德赛》和《旧约·出埃及记》。奥德赛海上十年漂泊和希伯来人在荒野中四十年的流浪便是《我弥留之际》隐含的神话原型参照。三者都显示了人类不可摧毁的忍耐力,揭示了坚定的信念在人类行动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正如俄康纳所说:“《我弥留之际》中的葬礼行列使我联想到摩西的《出埃及记》、约旦河的跨越、灵魂涉渡史梯河的艰辛,或迈向麦加或蒙古或西藏的圣地那漫长而神圣的跋涉。爱迪·本德伦的葬礼带有古代史诗的色彩,那是一个祭典,又是某种诺言的完成……”[⑤]
本德伦一家尊重爱迪的遗愿拖着她渐渐发臭的尸体去四十英里之外的杰弗生埋葬,这是一次苦难的旅程,全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传统的探求文学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单个的人,在这里变成了本德伦全家。《我弥留之际》没有《奥德赛》的雄伟和崇高,也没有《出埃及记》的神圣和庄严,我们从中所感受到的只是惨淡的幽默和嘲讽。但书中人物信念的坚定和忍受苦难的能力却并不比古代英雄逊色,作者也是把这次送葬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行为来歌颂的,福克纳说:“《我弥留之际》一书中本德伦一家也是和自己的命运竭力搏斗的。”[⑥]尽管这次奇特旅行的动机各不相同,尽管其中有许多愚蠢、自私、野蛮的表现,但本德伦一家却有共同的信念、责任和义务,正因为有了这些共同的东西,他们才能克服巨大的阻碍和困难,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弥留之际》揭示了生活中一些具有永恒意义的问题,除了上述的人类的忍耐力和信念之外,还有“终止了挫败一生的死亡,兄弟阋墙,驱使我们走向不同目的的五花八门的动机,庄严地承担下来的诺言的后果。家族的骄傲,家庭的忠诚与背叛,荣誉,还有英雄行为的实质。”[⑦]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大车里运载的本德伦一家其实是我们这个复杂得多的社会的有代表意义的缩影。”[⑧]
福克纳运用神话原型的另一种方法是在作品中设置具有原型意义的意象,构成复杂的隐喻和象征。在福克纳小说里出现最频繁的原型意象大多出自《圣经》,几乎从每一部作品里都可以发现基督原型,如耶稣基督、伊甸园、十字架、挪亚方舟、蛇、水、火等等。如果没有基督教为参照,就无法真正深刻理解福克纳的创作。耶稣基督是福克纳引用最多的原型意象,他往往用各种方法把小说中的人物和基督进行类比,如《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熊》中的艾萨克,《寓言》中的科尔普勒尔、《我弥留之际》中的卡什、《老人》中的大个儿囚犯等等,这些人物身上都或多或少带有耶稣基督的影子。他或者用基督的伟大和无私来反衬现代人的猥琐和自私;或者借这个原型表现自己对南方的堕落与拯救的思考,从不同的方面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水与火两个意象在福克纳小说中出现得也比较多,在不同情景中往往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火既象征神圣、光明、温暖、净化,又象征毁灭、灾难、惩罚。《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除了凯蒂留下的一只旧拖鞋,就是旺旺的炉火,火成了温暖和家庭温情的象征,所以躁动的班吉只要望着燃烧的炉火马上就会安静下来。火又是净化,昆丁一直希望自己和凯蒂的灵魂被地狱的火包围,希望地狱之火会烧尽旧世界留下的罪恶和新世界给他们蒙上的耻辱,使他们逃离这个喧哗与骚动的世界。《押沙龙,押沙龙!》是在一场大火中结束的,这场大火就是一个净化仪式,象征南方奴隶主罪恶的塞德潘大宅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瓦砾,大火不仅是塞德潘家族的毁灭,也是对南方历史的净化。
水既象征毁灭又象征净化。中篇小说《老人》中对大洪水的描写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气息,同时又蕴含着净化和再生。高个子犯人在密西西比河泛滥的大水中驾的一叶小舟如同挪亚方舟,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并勇敢地承担了责任,他让女人顺利生下孩子,而且保护母子完全逃脱了大洪水带来的灭顶之灾。高个子囚犯如同人间上帝,耶稣基督,而那个在大洪水中诞生的孩子无疑就是再生的人类的象征。《喧哗与骚动》中水的意象是洪水的变体,如雨、河等一样,它们都是不祥、堕落、灾难和死亡的象征。昆丁要凯蒂和达密尔顿断绝关系的一次谈话是小说中篇幅最长的谈话,正是这次谈话使昆丁对妹妹彻底失望。这次谈话是在夜雨中进行的,雨像不祥之雾笼罩着主人公,充满了死亡的阴暗气息。河在小说中是死亡的象征,昆丁自杀之前徘徊游荡在河边,最终选择了投水自沉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洪水与大火的意象在《我弥留之际》中也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本德伦一家的历险中最有戏剧色彩的是经历洪水和大火。两种意象都是净化的象征,是对爱迪·本德伦灵魂的净化。小说的题目已暗示了爱迪·本德伦是小说的中心,一家人不仅是去埋葬她的尸体,更像是送她的灵魂去赎罪。爱迪的一生就是一个苦难的旅程,她是个被生活挫败的人,年轻时,父亲常对她说:“活着的理由就是为长期的死作准备。”她因此变得悲观、自私、冷漠。她当过教师,但她既不爱自己的职业,也不爱自己的学生。她莫名其妙地嫁给了安斯,婚后不久便发现在她的心目中他已经死了。她和牧师惠特菲尔德私通,生下朱厄尔,惠特菲尔德的怯懦又很快让她失望。这个女人很像康普生夫人,对家庭、丈夫、子女她都没有真正地爱过。母爱是家庭温情的纽带,正是缺少这根纽带,本德伦家的几个孩子之间才难以沟通,甚至还互相仇视。康普生夫人经常提到自己娘家如何高贵,自己是大家闺秀,爱迪虽然没有高贵的家庭可以自夸,但她却希望和娘家人葬在一起,这个要求本身就表明了她和丈夫、孩子之间有隔阂。她说:“我每天的生活就是没完没了的认罪和赎罪。”“他(指朱厄尔——引者)是我的十字架,将会拯救我,他会从洪水中,也会从大火中拯救我。”十字架有双重的象征意义,一方面它象征犯罪和负疚,一方面又象征拯救和赎罪。朱厄尔在送葬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正是他从洪水和大火中救出了爱迪的棺材。朱厄尔是她犯罪的证明,又是拯救她灵魂的人物,其中颇有反讽的意味。
二
20世纪是神话复兴的时代,现代主义作家常常有意识地运用远古的神话原型作为自己作品的参照,这种倾向与20世纪西方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沧桑巨变,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人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解放。但是人们很快发现物质的丰富一方面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束缚了人的自由,人类越来越加重了对物质的依赖程度。在思想文化领域,自从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之后,传统的价值观念颠倒了,对于西方许多作家来说,这的确是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在这种情势下,“神话表明它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可以被用来赋予混乱的日常事件一种象征的、甚至是诗意的秩序。”[⑨]正如T.S.艾略特在评论《尤利西斯》的神话对位结构时所说的:“神话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实施控制,建立秩序,使处于全无益处的、无政府状态的、荒谬的现代历史获得某种形式和意义。”荣格从心理学的角度阐述了神话原型的审美价值。他说:“当原型的情境发生时,我们……就像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力所操纵,这时我们已不再是个人,而是全人类的声音在我们心中回响。”[⑩]“谁讲到了原型意象,谁就道出了一千人的声音,可以使人心醉神迷,为之倾倒。与此同时,他把他正在寻求表达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升到了永恒的王国之中。”[(11)]在荣格看来,艺术的创造过程就“包含对某一原型意象的激活……艺术家以不倦的努力回溯于无意识的原始意象,这恰恰为现代的畸形化和片面化提供了最好的补偿。”[(12)]从审美心理角度而言,现代读者通过对神话原型的认识而获得审美愉悦和审美享受,并学会对现代社会的认识。
福克纳小说的背景基本都在南方,他笔下的南方很像古希腊社会的解体时期、17世纪的英国、19世纪初期的法国和19世纪后期的俄国,那都是一个旧的社会日趋解体、新的社会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的时期,即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南北战争摧垮了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南方人虽然战败了,却依然坚持自己的传统观念,他们还没来得及思考如何重建南方,便发现自己面临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战后从北方背着钱袋到南方来的投机者,实质上比北方军队更有威胁性。抵抗北方军队,他们也许有自己的策略,可是面对咄咄逼人的新兴资产者的攻势,他们却束手无策。他们把北方资本主义冷酷无情的金钱原则和昔日南方宗法制的“伊甸园式”的种植园相比,怀旧的情绪便油然而生。他们在这场社会巨变面前迷失了途径,越是对现实不满,就越怀恋过去,把过去理想化。南方贵族的子孙更是对现代社会无法认同,成了无所依托的精神孤儿。他们沉溺在虚幻的历史荣耀和并不真实存在的过去之中。他们一方面需要“辉煌”的过去以慰藉孤独的灵魂,另一方面又觉得过去的力量如此强大,压得灵魂喘不过气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南方历史这个混乱而矛盾的大杂烩中,至少有一个特点从弗吉尼亚的建立到现在,一直恒定不变,这就是南方人态度和行为浪漫主义……南方人一直在其世界观中保留着某种疯疯癫癫的非现实成分。因为他比美国其他部分更坚定地相信,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不是现存的事物,而是那些应该存在,或那些据说过去存在的事物。”[(13)]这种疯疯癫癫的“非现实成分”和“浪漫主义行为”使南方人热爱神话并且自己也在创造神话。
福克纳是个地地道道的南方子弟,他几乎本能地留恋过去,反对现代文明。他说自己喜欢过去的日子:过去的日子的消逝对我来说是一种很伤心、很有悲剧性的事。那就是说,如果你有我这样一个乡下孩子的背景,那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不愿它变化。福克纳的曾祖父W.C.福克纳在他家乡是个神话般的人物,他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他的塑像至今仍耸立在奥克斯福的广场上。福克纳极为崇敬这位曾祖父,在他出版的第一部书中,他介绍自己是“《孟菲斯的白玫瑰》、《匆匆漫游欧洲》等书的作者,南部邦联军人W.C.福克纳上校的曾孙。”[(14)]福克纳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南方的乡下度过的,他住在古老的大宅里,在机械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他却养了成群的骡子。他显然不希望南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他看来,应该让南方自觉自愿地解决奴隶制问题,不应该用暴力去改变南方的社会结构。内战之后兴起的斯诺普斯主义是完全的自私自利,毫无人性。与过去相比,目前的状态更糟。总之,福克纳有着根深蒂固的南方意识,正是因为这种南方意识才使福克纳能更深刻地揭示南方的历史命运。
20世纪现代派文学创作中的神话化倾向,美国南方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福克纳作为南方子弟的特殊心态,三者形成了一种合力,促使福克纳大量运用神话原型作为自己作品的参照。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下新历史主义的“社会能量”和“协合”两个概念来说明福克纳对神话原型的运用。“社会能量”是个非常复杂而抽象的概念,但大体上说,“它是指社会和文化空间中一切能激起普遍情绪的东西。”[(15)]“协合”是新历史主义的核心概念,“它包含有协商、传达、调解、融合等意义,新历史主义用它表明不同范畴中的立体在社会能量或历史关系、文化网络中所起的沟通、协调作用,发挥这一作用的主体主要指作家……对于创作主体而言,协合(negotiation)是一整套操作程序。它大体上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它要把自己从社会直接获得的或是通过流通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的各种各样的经验材料协调起来,他要把自己的创作活动同当时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的总的状况协调起来,他还要把自己的作品同读者或观众的审美趣味和爱好协调起来,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协调活动,最后整合成一部艺术作品。”[(16)]福克纳就是这样一位“协合”者,他把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南方社会的种种矛盾和自己复杂的内心冲突协合起来,创造了自己的“约克纳帕塌法”王国,一个神话的世界。福克纳运用神话原型创造这样一个神话王国,是他企图将南方历史神话化的重要表现。
神话是人类通过想象对具体时空和自我局限的超越。人类不幸被框在线性时间之内,但人类又竭力用心灵的创造和想象超越时空。“通过体验神话,人们就从凡俗的年代学上的时间中突现出来,进入另一性质的时间,即神圣的时间。这时间立刻成为原始的和可以被无限寻回的。”[(17)]福克纳要作的就是寻回过去的时间,但他又不像一般的南方子弟那样沉溺在过去,在他看来,孤立地生活在过去之中,把过去和现在割裂开来,是对时间本质的歪曲,时间是一种流动状态,它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把三者协调起来的人才是健全的。神话既是历时性的叙述,又是共时性的象征,神话能够超越历史。在运用神话原型中,他克服了南方人的偏见,使小说超越了具体的故事情节,超越南方成为人类命运的寓言。
福克纳自觉地运用神话原型,标志着神话原型从无意识的显现转而成为一种创作方法的表征。神话原型的运用不仅大大深化了福克纳的主题,而且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毫无疑问,福克纳像巴尔扎克一样,是他自己时代和地理区域的忠实记录者。福克纳如实表现了南方贵族的日趋消亡、斯诺普斯主义的兴起、传统价值观念的毁灭和南方贵族子弟的迷惘和困惑。同时,他也揭示了现代人与历史、与命运的关系,突出了现代人的难以沟通、疏远和人性的扭曲。他把表现南方的历史命运、描写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和远古的神话传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表明他比前辈作家有着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显示出强烈的时代和深沉的历史感的统一。
福克纳一辈子都在自己“邮票般大小的故乡本土”上开掘,写那里的人和事,表现那里的乡土人情观念。他深深地扎根于这块土地,对它的山、水、森林、风土人情有深入的了解,而且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融入其中。一位画家说:“我对一样东西越是了解就越容易把它画好。并不是因为我越有所了解,新的发现就越少,而是新的可能性不断涌现……你对它同某个背景的关系越有把握,它就越具有原型意义,可以进一步发挥创造。你越把握住地区特色就越接近整个宇宙。”[(18)]福克纳准确把握住了南方的地区特征,突出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南方人对历史的深厚感情。福克纳通过广泛地引用与希腊、希伯来和基督教神话,把表现南方人对历史的感情置于宏大的文化背景之下,使浓郁的乡土人情和宏大的文化背景达到了和谐与统一。
注释:
① 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上),《世界文学》编辑部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28页。
② 杨正润:《人性的足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③ 《四十年间评论集》,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
④ 弗莱:《批评的解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18页。
⑤ 威廉·范·俄康纳编:《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张爱玲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2页。
⑥ 福克纳:《我弥留之际》,李文俊等译,见《福克纳访问记》,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461页。
⑦ ⑧ 克林斯·布鲁克斯:《威廉·福克纳简介》,耶鲁,1983年版,第88—89页。
⑨ 袁可嘉编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55页。
⑩ (11) (12)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0—122页。
(13) 罗德·霍顿和赫伯特·艾得华兹:《美国文学思想背景》,房炜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页。
(14) 大卫·敏持:《圣殿中的情网:小说家威廉·福克纳传》,赵扬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0页。
(15) (16) 杨正润:《主体的定位与协合功能——评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1期。
(17) 米尔克·艾里亚得:《神话与现实》,纽约,哈珀和罗伊出版社,1963年版,第18页。
(18) H.R.斯通贝克:《威廉·福克纳与乡土人情》,见《福克纳中篇小说选·序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2页。
标签:神话论文; 福克纳论文; 我弥留之际论文; 原型批评论文; 喧哗与骚动论文; 神话创造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奥德赛论文; 押沙龙论文; 康普论文; 剧情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