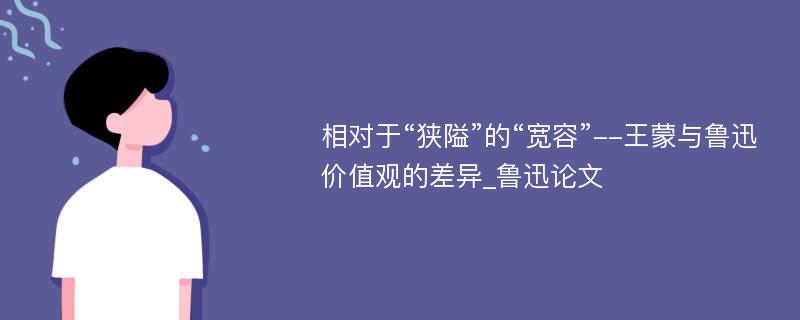
相对于“褊狭”的“宽容”——王蒙与鲁迅价值观的歧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褊狭论文,歧异论文,鲁迅论文,相对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如果有人要问我王蒙与鲁迅有什么区别的话,我要说,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在极力鼓吹“宽容”,而后者则“褊狭”,声称“一个也不宽恕”。尽管王蒙被称为“大师”,尽管王蒙比起胡适的建树要稍逊“三”筹,但他着实扮演了当年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兼容的角色——虽说这一角色的扮演者一代不如一代,但毕竟扮演了。王蒙是“宽容”的。
我也读了不少王蒙的作品,他不像许许多多当代的中国作家那样,是由鲁迅、由“五四”那一批作家的乳汗哺育成长的。据他表白,他的“情意结”是在苏联,他是在苏联的作家们哺育下成长的。早些时候,在我购买的王蒙的书中,几乎不见他提到鲁迅。我最初的印象,他与鲁迅是无涉的。中国现当代作家而能不受鲁迅影响,这应该说是一种超出常例的例外。他是幸运的,虽不能说是唯一,但他也是少数一些没有被“鲁货”“鲁化”的作家之一。
可是,后来他也“偶尔露峥嵘”了。他对鲁迅是深不以为然的。他假设了文坛有五十个鲁迅,于是发出了“我的天”的惊呼!
我们先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据1995年2月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王若谷的文章《鲁迅诱发地震》一文披露,王蒙在一次演讲中说:“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鲁迅也不好——那会引发地震!”不久,他在《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一文中又说:“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月版)
地震是一种灾难。鲁迅会诱发什么样的地震呢?或者说,鲁迅会引发什么灾难呢?王蒙没有说。我推测,王蒙所说的所谓地震,就是社会动乱。在王蒙看来,鲁迅激烈的、极端的思想是会造成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是会让人变得不“宽容”而又激进。
这里,王蒙忘记了基本的一条,他把旧社会和新社会看成是一个社会了。是的,鲁迅让人们不满黑暗的旧中国,鲁迅让黑暗的旧中国害怕。可是,鲁迅怎么也让行着“布礼”、高喊“青春万岁”并当过文化部长的新中国的王蒙害怕呢?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都不曾害怕鲁迅诱发地震,而且,毛泽东还自视鲁迅为知音,毛泽东以后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共领导人也都肯定了鲁迅而没有将其视作洪水猛兽,王蒙害怕什么呢?王蒙视鲁迅为灾难,如此先天下之忧而忧,是不是杞人之忧呢?
至于五十个鲁迅问题,我感到特别费解,中国文坛不是老在呼唤大师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目下没有鲁迅这样的大师,不是有人把王蒙也凑上,称之为“大师”了吗?既是这样,有五十个鲁迅不是大好事一桩吗?不是正可以证明我们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吗?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有世界上最为众多的人口,即便有五十个鲁迅这样的大师也不为多,我们也应该看作是国之幸事!目前,我们根本就没有鲁迅第二。王蒙的假设是没有任何实际和积极意义的。他说的鲁迅的很伟大之类也是充满了虚情假意,是一种出于“两点论”的需要、出于不被抓辫子的需要所不得不说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要惊呼“我的天”了。他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换言之,他为什么要这样假设呢?“我的天”,他为什么如此惊诧呀,我的天!
他不会因为鲁迅的小说而如此惊诧吧?他不会因为鲁迅的《朝花夕拾》等散文而这般惊诧吧?他不会因为鲁迅的小说史研究而这等惊诧吧?那么,他为什么惊诧呢?显而易见,他是为鲁迅的杂文惊诧。结合他平时不厌其烦的“宽容”论,他尤其为鲁迅的“骂人”文章、鲁迅的“褊狭”惊诧。他的言外之意是,如果出了五十个鲁迅这样不“宽容”的人,如果文坛上老是像鲁迅那样争吵,“我的天”!我以为,这就是王蒙的“天”的全部内涵之所在。
王蒙为什么会把鲁迅扯出来,做为王朔的反面并加以攻击呢?我是这样想的,也许王蒙被“惹”急了,很多批驳王蒙的人都是以鲁迅为思想武器的,于是,他想来一个“根本解决”,鲁迅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我把鲁迅也数落一番,看你也奈何洒家不得。王蒙提着一个“宽容”牌的袋子,这袋子“宽容”了王朔却“宽容”不了鲁迅。这是一个什么袋子呢?我怀疑它可能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垃圾袋。
2
王蒙的鲁迅会引发“地震”说与他“我的天”之惊呼,并非偶有所感。在新时期,他一开始的价值取向,就是与鲁迅不同的,就是与鲁迅唱对台戏的。他的那篇《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鼓吹在不同时代应该有不同政策的前提下,几乎把鲁迅批驳得“体无完肤”。他说:
五十多年以前,鲁迅先生提出了“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著名命题。当时,鲁迅先生大概不会想到,在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一篇名作得到了特别突出的、空前的宣扬和普及。“费厄泼赖”在1957年要缓行,在1959年要缓行,在1964年、1966年、1973年直到1976年仍然要缓行。看样子,缓行快要变成了超时间、超空间的真理,快要变成了“永不实行”,从而根本否定了“缓行”了。(《读书》1980年第一期)
鲁迅的文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被利用了。王蒙的言外之意是不是说,倘若当年鲁迅不是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而是像王蒙一样写《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那么,像1957年等等的历次运动可以避免“痛打落水狗”?我可以肯定地回答:王蒙绝不会有这样的意思。可是,王蒙的文章却有着不好的客观效果。他不讲历次运动与鲁迅无关,不讲鲁迅不能为他死后的事负责,不讲建国后一些人对鲁迅的利用,不讲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王蒙不讲这一切,客观上给人的感觉是鲁迅当年的“缓行”论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王蒙认为,时代不同了,鲁迅的“缓行”说应该遭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实行”。王蒙后来又说:“……我提倡费厄泼赖,不相信鲁迅的原意是让人们无休无止地残酷斗争下去。”(《我的处世哲学》)这里,王蒙把正常的思想斗争、思想批判等同于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残酷的阶级斗争了。王蒙行文的特色之一,就是杂糅,一锅煮。彼此混为一谈,让人批驳起来也格外费劲。
不是鲁迅时代,自然也就不需要鲁迅的思想,也不需要鲁迅思想的载体鲁迅式杂文。这种不是鲁迅时代,不需要鲁迅的杂文的观点,我似乎并不陌生,有似曾相似之感。1949年以前有这样的论调,1949年以后也有。随着时代的变迁,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就过时了吗?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就精确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了吗?
这里,我想问的是,建国后历次运动造成的灾难是“费厄泼赖”“缓行”的结果还是“实行”的结果?实行“费厄泼赖”,就是说要讲宽容。但是,宽容就是放弃批判吗?一对社会的不良现象进行批判,就是不宽容吗?建国以来,封建的东西、极左的东西,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可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基本上放弃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它们宽容了,“费厄泼赖”了,于是,终于暴发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国性的大灾难。实际上,历次运动中所实行的东西都是带有封建性的名堂,是专制的一种表现。而这种专制的东西之所以能在新中国改头换面地得以施行,是因为封建专制这个白骨精在新中国变成了一个美女,是中国人民对封建专制的吃人本性没有充分的认识,对封建专制缺乏彻底的批判,对封建专制太“费厄泼赖”了。所以,它变了一个花样,脱了长袍,穿上了中山装或西装,封建的意识加上封建的操作方法,对人民实行了封建专制。历次运动所发生的一切,不是不实行“费厄泼赖”的结果,而是在一个时期里全社会对封建专制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实行了“费厄泼赖”了。冻僵的封建之蛇,又咬伤了善良的中国农夫。如果说历次运动中的这些东西,是属于封建主义的话,如果说极左的东西与封建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的话,那么,对它们,不管是鲁迅所表述的还是王蒙所举例的,费厄泼赖,还是应该缓行。
重温一下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的结尾,是颇有启迪意义的。鲁迅说: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这里,鲁迅的“费厄泼赖”缓行说,已经超越了具体,是针对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社会要发展,就不断有改革与反改革斗争。对于反对社会变革的力量,就是不能立即就讲“费厄泼赖”,只有在他们丧失了反抗的能力的时候,才可由缓行而移易为实行。如此,社会向前了,但又有了新一层次的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又有了新的需要“缓行”的对象。从这一意义上说,鲁迅的“缓行”说,就是永恒的命题,换言之,“费厄泼赖”有其永远需要缓行的部分。
对于反对社会变革的力量,对于无聊和无耻,就是永不宽容,这就是鲁迅精神之一种。
王蒙的“宽容”,他的“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的误区就在于放弃批判。王得后在《从宽容到帮忙》一文中说:“宽容是好的。然而,一时出于政治考量,出于对运动的恐惧,出于对‘左’派的憎恶,竟向文艺批评要求宽容,向一切人要求宽容,而且把笔尖指向鲁迅。……人非木石,心非古井,人性决不能如道家所设想的恬淡,而文艺批评,尤其必须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批评本身,固有着是非的标准,爱憎的尺度。……文艺批评家不是和事佬,不是老好人,无论为了金钱,为了友情,为了义气,而牺牲自己的主见,于人于已,于公于私,都是害多利少,甚至有害无益的。”(《中华读书报》1998年3月25 日)文艺家拿起批评、批判的武器,这不是不宽容。具体地说,人们抨击王朔、批评王蒙,这不是不宽容。
何满子的《宽容骑士》一文,虽然是针对“一些”人的,但王蒙却被客观地包括了进去。何满子先是介绍了这样一些现象:
例如近年来迅速膨胀的市场大众文化中的庸俗趣味之泛滥,有人如果提点意见,向社会提点警告,宽容骑士就要出来说教了:不要太偏激呀,要尊重不同群族的精神文化的追求呀,其公允宽大之态可掬,而且动辄还以莫非还想回到“文革”时期的文化沙漠相恐吓;似乎要多样化就得让人吞咽一切污泥浊水,容忍一切乌七八糟的垃圾,连人们皱了眉吭个气的权利也应被剥夺。骑士们是提倡宽容的,怎么对别人的不合他们心意的言谈就没有宽容的雅量呢?
又如,有一种脏话连篇、耍嘴皮子调侃人生,将严肃的问题化为一笑的所谓“玩个梦”的文学,有人要写,有人要印,有人要读,也只好由它,舞台上有个把小丑,算不得什么,也算是多样化吧。可是有人对这类无聊的嬉皮笑脸表示不满,也该算是多样化的声音之一种吧?宽容骑士却又出来干预了,说这种人生调侃有重大贡献,它摧毁了往昔虚假的神圣、崇高、英雄观念,云云;却丝毫不提它在摧毁虚假的同时,把人生应有的庄严、神圣、崇高也连根摧毁了,它所呼唤的是一种否定一切的着地打滚的人生。
这里,何满子已经指出了宽容骑士们对谁宽容,对谁苛刻了;指出了他们的宽容的脆弱。对于这样“不辨好恶一律接纳的宽容”,何满子认为“确实是要修炼到一定的道行的人才能办到”。
何满子毕竟是有知人之明的,他看穿了“宽容骑士”的五脏六腑,接着,他对他们能否彻底“宽容”表示了怀疑:
我还怀疑,宽容骑士自身是否真能心平气和地宽容大度到底;当别人触犯了他们,对他们的“宽容论”表示非议时,是否真能沉得往气。如果也会气急败坏,暴跳如雷,那就证明骑士们宣扬对一切要有宽容气度,而他本人却并不对一切都逆来顺受,维持其宽容的矜持;则即使不便说骑士的“宽容论”是虚伪的,只是一种唱得令人欣悦、带有怀柔或绥靖味儿的高调,至少也说明“宽容论”有点什么破绽。人也不能和不该对万事都一律包容,想做彻底的犬儒主义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我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
王蒙不幸而被何满子言中,他与王彬彬等人的论战,多的是气急败坏,最少的就是宽容。这还得在这篇文章的后头,慢慢道来。
3
王彬彬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名人之嚏与“晚报文体”》,它对当代的散文、随笔热,持不以为然的态度。王彬彬认为,现在有的刊物“变成了一处专供名人打喷嚏的地方”,“大多数名家作品,都乏善可陈,许多文章,则干脆是一种扯淡。”接着,他摆出了一串“喷嚏”现象:“谈谈‘我’的喝酒或者戒酒,‘我’的抽烟或者戒烟,‘我’的喝茶或者喝粥,‘我’的儿子或者女儿,‘我’的胡子或者梳子,‘我’的名字或者八字,‘我’的作息时间起居习惯,等等。——这类文章,不是歌不是哭,不是笑不是骂,甚至不是‘无病之吟’,只能算是嚏;这类文章,没有血没有泪,没有苦没有痛,甚至也没有酸,只会有菌。”(《死在路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版)其实, 王彬彬的文章并无新意,它只是鲁迅关于小品文问题的论述的一种发挥,一种补充。
我们不妨看看鲁迅是怎么说的。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文学上的“小摆设”,“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鲁迅又说,“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应该说,鲁迅举的例没有王彬彬多,但旨意是一致的,而且,鲁迅要比王彬彬更为尖刻。如果说王彬彬的文章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针对对象。
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又惊动了王蒙。使得他忘了“宽容”,跳出来和王彬彬“过招”了。他对王彬彬的不以为然更加不以为然。在《沪上思絮录》一文中,他说:
最近又来了劲,什么猫呀狗呀家呀孩子呀又成了罪过了。乃至用一种下流的语言不分青红皂白地说什么名家写了小文章就是乱打喷嚏。名家也是人,不仅可能打喷嚏而且每天要大便小便。然而名家之为名家,至少大多是为了他们的某方面的特长与劳动成果,小文章也不是那么好写的,小文章也可以有多种意义与产生的历史依据,而写小文章大多与上呼吸道的分泌无关。企图吐一通口水就给自己够也够不着的众名家抹黑,那口水会落到什么地方呢?
是的,名家也是人,但是不是人的一切都可以写呢?诚然,一切名家都和王蒙一样“每天要大便小便”,可是,我就没有看到名家写大小便的文章,也许我孤陋寡闻,也许王蒙有《论大便与长治久安》之类的文章在,只可惜我还没看到就是了。
这几年,正是在“也是人”的名义下,在所谓的“真实”的名义下,性交文学泛滥,一个女人和若干个男人,一个男人与若干个女人的性游戏,充斥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便是《金瓶梅》,便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都为之逊色。不少名家,因为是名家,有时不够自爱,在那里不厌其烦地大写特写被王彬彬批评的那种“喷嚏文学”。打喷嚏而能成为文学,这完全可以证明我们的文坛感冒了!难道名家写的一律是上流文章?王彬彬对末流文学批评一番,怎么就“下流”了呢?难道要高呼“喷嚏好,喷嚏好,喷嚏就是好!”才算“上流”?
我理解,“喷嚏”只是一种代表,一种象征,它是指把一切琐碎、无聊都进行渲染的所谓文学。其实,我有很多旁证可以支持王彬彬的观点。不仅有“喷嚏文学”,还有“鼻涕文学”。我看到一个女作家写她儿子感冒了。鼻塞了,她将嘴对着她孩子的鼻子,把浓浓的鼻涕给吸出来了。若是在生活中,我听到这件事,我会感动,我会认为她是一个好母亲。但是,如此写成散文,我却觉得恶心,这样的母亲太“也是人”了,这样的散文太“生活”了,就像王蒙要大便小便一样,绝无美感可言。我还看到若干个女名家,写了若干篇她们的在闺房中穿着睡衣与情人嬉戏的文章。这是不是在教诲小姑娘们怎么骚呢?我将其称之为“穿睡衣的散文”。
王蒙的名人意识是很强的,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一次“捍卫”了名人并同时抨击了向名人“吐口水”的人。他说:“自从那年文坛出了一匹黑马靠大骂名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以来,现在又有效颦者了,以为到处吐口水便能树立一点什么形象——踩在名人的肩上嘛。过去我不太能理解杜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情感,总觉得火气太火,……最近的这个不得幽默的故事使我从原意上想起了它。”名人说不得,一说就是要沾名人的光,就是要踩在名人的肩膀上,真是莫名其妙,发的是名人特有的神经病。至于说谁的身与名俱灭,这却由不得名人了。轰响于当时、几乎造成名声污染而又很快成了过眼云烟的“大师”,在历史上也不鲜见。有的“大师”以为,文章写得多,就足以不朽,那就大错特错了。再多的文章,如果都是教人怎样“成熟”、“聪明”、“不偏不倚”乃至圆滑,即使著作等身,也是垃圾一堆。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有的“黑马”只出了一本书,甚至只有一篇两篇文章,但由于是发傻之作,是用心血用生命写成的,亦足以名垂千古!此外,谁是“不废”的、“万古流”的江河呢?王蒙在暗示着什么呢?
我还觉得,王蒙的强烈的名人意识,与他平常的潇洒状很是矛盾。我只能对他的潇洒表示怀疑,他是不是故作潇洒呢?他是不是在刻意表现潇洒呢?不是从心底自然而然流出来的潇洒的就是伪潇洒。若不是假潇洒,他怎么会在把别人看作“下流”的同时,觉得他以及他这样的名人们是高高在上,高上到别人够也不着的地步呢?他自己太看重自己的名人地位了,所以,才会觉得别人当不上名人很是“苦恼”,才容不得别人对名人的非议(这种时候,王蒙怎么就不说“名人也是人”了呢?这种名人高不可攀的感觉,让人觉得名人有点不像人,有点玄,有点神)。别人是武大郎,往王巨人身上吐口水都吐不到,结果口水还落到了自己的头上。当代社会,有如此之高的人和如此之矮的人?我不相信。目下大家都不缺钙,高矮相差太大是不大可能的。说到底,王彬彬的《名人之嚏与“晚报文体”》也是一篇散文,它与它所抨击的那些散文比,换言之,与名人的“喷嚏文学”比,哪一个更高、哪一个更底?在我这里是不言而喻的,我怀疑,王蒙并不高,只是站在一个什么台阶上,他自我感觉高大而已。离开了这个垫高物,他可能比王彬彬还要矮。
在同一篇文章中,王蒙为了彻底批驳“喷嚏”论,还大肆鼓吹“喷嚏”一类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他说:
其实文学的特点恰恰在于以小见大。而且一个国家生活愈正常气氛愈祥和作家就会愈多写一点日常生活,多写一点和平温馨,多写一点闲暇趣味。到了人人蔑视日常生活,文学拒绝日常生活,作品都在呼风唤雨,作家都在声色俱厉,人人都在气冲霄汉歌冲云天肝胆俱裂刺刀见红的时候,这个国家只怕是又大大的不太平了。(《沪上思絮录》)
不写“喷嚏文学”便只能写刺刀见红的文学吗?鲁迅的作品并不声色俱厉,并不刺刀见红,然而却与“喷嚏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王蒙惯用的伎俩是“一锅煮”,凡是他所不喜欢的,他便将其和“文革”现象一锅煮了。如此,可以唤起人们对“文革”的痛恨,他希望人们像痛恨“文革”一样痛恨“黑马”、“黑驹”。写小文章是太平盛世,写不小的文章便是乱世。梁实秋身在乱世,写的是小文章,周作人在敌人的铁蹄下,写的也是小文章。我是应该理解成乱世出小文章呢?还是应该理解成梁实秋和周作人处的也是“太平盛世”呢?
4
由于上一节提到的和另外一些别的原因,9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发生“二王之争”。大王者,王蒙也;小王者,王彬彬也。“二王之争”有很多可总结、可反思之处。王蒙的所谓“宽容”,在争论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全面、淋漓尽致。
王蒙说:“我最讨厌与轻视的是气急败坏,钻牛角尖,攻其一点,整人整己,千篇一律,画地为牢,搞个小圈子称王称霸。”(《我的处世哲学》)可是,王蒙还是修炼得不到家,他在与王彬彬的论战中,终于还是气急败坏了!我为他的自我轻视和不宽容而深感遗憾!
我以为,王彬彬以及王彬彬们对现实的关怀,他们的批判精神,是现代中国文坛最可宝贵的鲁迅传统之一种。王蒙与一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对立,某种意义上说,是与鲁迅传统的对立。
从“二王之争”看,王蒙这样的“宽容骑士”并不宽容。我以为,最能体现王蒙因不宽容而气急败坏的是所谓“黑驹”说。
王蒙在他的名文《黑马与黑狗》一文中说:
友人向我介一个文学青年的遭遇:他苦读寒窗多少载,好不容易获得了最高级学位,辛辛苦苦做学问,做文章,只是难投编辑大人们之心意,一篇也发表不出来。这样就积蓄了太多的“力比都”,愤世而又嫉俗,寂寞实在难熬。最近该青年乃改弦更张,改写“骂派”文字,专骂名家大家,骂他们的作品并非篇篇都是纪念碑与史诗,骂散文的兴旺,骂女作家琐屑而且乱开玩笑,骂晚报的文体,骂文章题目里动不动是“我的……”,骂中国作家太聪明,没有在政治运动中壮烈牺牲,骂评论家没有像他一样地骂……三骂两骂,“该同志”立即看好起来,“有噱头”哉!——在大街上如果有个人骂架,也会围拢一圈又一圈的人观看的,这也是国情之一种。于是约稿的也来了,姓名的出镜率也高了,稿费收入也大幅度增加了;时来运转,行市看涨,过去羡煞妒煞的频频有新作发表的作家名流,过去是够也够不着拉又拉不下来只能恨得牙痒的文坛骄子娇女,却原来根本不在话下!只消高高在上地拉开架式一骂,轻而易举地就与之同领风骚了乃至彩声四起了。真妙啊!多么快捷的途径,多么犯贱的文坛!骂而优则文,骂而狠则名,驾吐沫而升九天,乘恶言而游四野,各种效益丰收,俨然又一小黑马——应该算是黑驹——应运而生矣!
约摸十年以前,文坛上出现过一匹黑马,作叱咤风云、横扫千军之雄姿,吐目空一切、自我做古之大言,东杀西砍,左奔右突,强词夺理,信口开河,愈是名人愈要猛攻,愈是大家愈要谩骂,如入无人之境,若进有宝之房;高喊孤独而抢话筒,大颂死亡而邀名利,自吹自擂,自吆自卖,在引起窃笑的同时也还吸引了一些目光,更还受到了几个看着名人大家老是不忿,而又生不逢时,没有给名人大家戴高帽子游街的机会的胸中不平的年轻人的喝彩。
固一时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王蒙的文章一发表,就遭到批驳。张志忠在《我看“二王之争”》一文中指出:王蒙的反批评,同样让人感到那种辞浮气躁,意气用事心态。张志忠说:“他似乎比王彬彬更懂得为文之道,嬉笑怒骂,皆成文字,以语言的密集轰炸舒泄情感的愤激。他考证和挖苦‘一个文学青年的遭遇’,拉出当年的一桩公案来进行‘黑马’与‘黑驹’的高下比较,然后又一口气用四首打油诗给对手以‘毁灭性打击’,但是,在妙语连珠、气盛言直的背后,却也露出了破绽。那种‘好不容易获得了最高级学位’,却又‘一篇文章也发表不出来……’,未免过于刻薄和主观,却又以‘友人向我介绍’引出,既损了人,还不用负澄清事实的责任;对于‘黑马’,在当年可以互相论争的时候不曾记得王蒙说过什么,时移事异的今天,为了打‘黑驹’而拉出‘黑马’进行‘缺席审判’,未免有失公允;……便也底气不足,而徒有‘穷追猛打’、‘一举封杀’之气势。”(《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
王蒙提的所谓“黑马”,就是刘晓波。仅就刘晓波的文学见解而言,今天看来,也无大错。我记得,十年前,刘晓波得罪了一批文坛名流的文章,无非就是那篇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刘晓波是以中国现代文学做为当代文学的参照系的,他的基本观点是,当代有名人而无大家,更不用说大师了(他是不是没有想起王蒙是“大师”,从而得罪了王蒙呢?也未可知)。
今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20世纪的中国文学,似乎并非一无意义。不少文学史家和文学家都认为,本世纪中国文学最辉煌的时代,是“五四”以后的三个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认为是中国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这是不是觉昨而今非呢?平心而论,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优秀的知名作家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若是摆出名字,高晓声、陆文夫、邓友梅、张洁、汪曾祺、贾平凹、陈忠实、霍达、史铁生,等等,简直如新疆丰收的葡萄,一串又一串。单独地看,新时期的作家是优秀的。然而,若是以“五四”以后的三个十年为参照,在“五四”光辉的照耀下,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一律黯然失色了。这当中原因甚多,但最根本的一条是,新时期文学没有大师,没有像鲁迅、胡适、茅盾、郭沫若那样学贯中西的大师;新时期甚至没有产生沈从文、梁实秋、巴金、冰心、曹禺、叶圣陶、老舍、钱钟书这样高水准的杰出作家。名家倒是一大群,倒是产生了不少喋喋不休自封“文化名人”的沽名钓誉之徒,倒是像流水线生产电灯泡一样,生产了一大堆的“文集”和“全集”!
5
在价值观念上,王蒙还有一条是与鲁迅迥异的,这就是关于所谓走极端问题。
王蒙是反对“极端”的,他说:“以一种极端主义反对另一种极端主义,古人称之为‘以暴易暴’,识者不取。”(《沪上思絮录》)他又说:“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斗斗斗、杀杀杀之风席卷神州大陆,妥协、宽容、爱心、费厄泼赖(公平游戏)之属备受嘲笑。极端主义常常易于在我国走红,而平实和顺之论却被视为不中用的表现。”(《我们这里会不会有奥姆真理教?》)为了把矛头对准不肯放弃批判精神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王蒙还进一步发挥道:“一味地杀杀砍砍,只能给老百姓带来无数的痛苦,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与危机。不杀不砍了有的人却会失落起来,即眼见着民众庸俗乃至‘堕落’而无技可施。而一些比较有头脑,比较心气高的精英更是痛心疾首。他们中的最极端的一伙儿,由精神解构、空虚、饥渴而发展到极端的信仰主义,造神主义,从而站到了世俗人生的对立面,站到了普通人与平常心的对立面,站到了通常的社会秩序与群体规则的对立面——所谓一个人与全国全人类作战之类——也不是不可能的。”(《怀念六十年代?》)
这段话是很可以看出王蒙行文的特色的,他的行文的恶劣就在这里,人家谈的是人文主义,人家谈的是批判精神,他就扯上宣扬仇恨,宣扬好勇斗狠,宣扬“斗斗斗、杀杀杀”之类。这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这是把人往死里整。据我所知,在人文主义讨论中,绝对没有人宣扬王蒙所说的那些东西。王蒙动不动就说别人红卫兵习气,他这种把莫须有的东西硬给人扣上的做法,我与其说他逻辑混乱,不如说他自觉不自觉地有了红卫兵习气。
王蒙的“以暴易暴”让我想起了夏志清,夏志清也是反对“以暴易暴”的。他把千百万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用轻飘飘的观念解释为“以暴抗暴”。夏志清仿佛鼓吹一下不以暴抗暴,他就要成为托尔斯泰了。日本人打到中国来,能不以暴抗暴吗?专制统治者不让中国人活、要让他们死,能不以暴抗暴吗?建国前,在历次战争中死了几千万的中国人,他们能在“以暴抗暴”的结论下白白死去吗?不,他们是不死的,他们活在中国的历史之中,活在有血性的中国人民的心中,他们流的血,足可以把一千条一万条的怪论湮没。王蒙的不“以暴易暴”也是针对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他似乎犯了和夏志清一样的错误,要把百年的革命史在“以暴易暴”的结论下一笔抹杀。
近百年中国人民的“斗斗斗、杀杀杀”,反抗的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反抗的是外来侵略,为的是建设一个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有今天,不是无数革命先烈英勇斗争的结果吗?如果放弃各种各样的斗争,如果没有流血牺牲,中国的女人甚至还裹着脚,男人还拖着辫子哩,更遑论其他一切!反过来,王蒙所说的所谓“平实和顺”,不就是中国古老的中庸之道吗?不就是温良恭俭让吗?中国讲了几千年的中庸之道,也不见得就长治久安了,也不见得就国强民富了,事实不是已经证明“平实和顺”一类的中庸之道确实是“不中用”的了吗?
我不想否认,也不可否认的是,在正人君子看来,在学者教授看来,在这个“道”那个“道”的维护者看来,鲁迅确实是走极端的。且不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且不说提倡汉语的拉丁化,单是在那个关于“青年必读书”问题征答中,他提出不读中国书的论调,足以让一些爱国者把他判为汉奸。鲁迅还有“铁屋子”理论,他说: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鲁迅经常鼓吹的拼命走极端,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是一种看透中国尔后采取的一种策略。可是,王蒙除了看到极端的种种弊端以外,他能够理解极端之于中国的重大意义吗?一切新生的事物,相对于保守者都是极端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若是没有激烈的甚至也可以说极端的反极“左”精神,若是没有思想解放运动的巨大冲击;我们若是都像王蒙所标榜的那样“中正平和”,那么,我们有可能彻底否认“文化大革命”吗?我们会有股市吗?会有市场经济吗?
鲁迅的“极端”,是一种方法论,王蒙的反极端也是一种方法论。这个世界,极端的东西是很多的,王朔说,知识分子都是灵魂的扒手,这话极端不?极端。然而,王蒙不吭气;色情文学泛滥,包括王蒙吹捧过的女作家,作品中哼哼唧唧,铅印的木床上吱吱嘎嘎。我翻遍了西方文学,我翻遍了《金瓶梅》,也不见有如此直露的生理性的描写,这极端不?极端。然而,王蒙不吭气;有人怀着极端的偏见,在编排20世纪文学大师的作品时,居然可以没有茅盾而有了王蒙(长此以往,茅盾文学奖是不是要改成王蒙文学奖了?),然而,王蒙不吭气……可是,一有人出来抨击某些极端的丑陋和丑恶,王蒙便说抨击者是极端的。王蒙如此反极端,如果是他的“宽容”思想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我终于搞清楚了,他的宽容原来是一个硕大的垃圾箱,里面宽容了一切他认为应该宽容的东西。
王蒙的反极端,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证明他的“宽容”,就像鲁迅的掀掉屋顶是为了开窗一样。可是宽容与否,也不是谁标榜怎样便是怎样,这要看他的作为。要看事实。
6
曹聚仁说过,鲁迅“是千百年后嵇康、阮籍的知己。”(《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17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6月版)鲁迅与王蒙都对魏晋时代的嵇康产生过兴趣——虽然他们对嵇康研究的深浅不可同日而语。鲁迅花了极大的心血校过《嵇康集》,王蒙只是读了一本书(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书中的某些史料某些观点让他产生了兴趣而已——对比一下他们对嵇康的不同评价,也很可以看出他们在价值取向上的歧异。
王蒙在《名士风流以后》一文中说:
嵇康的故事脍炙人口。尤其是他的受戳前观日曩而奏文陵散,这种浪漫主义的无与伦比的风格才调真神仙中人也。看来还得感谢司马昭,他虽然杀了嵇康,毕竟还给他留下了表现与完成自己的浪漫主义结束曲的机会。杀人者亦有自己的“宽容”,嵇康不幸之中有大幸焉。
嵇康之所以还能奏《广陵散》,就在于司马昭这样懂知识分子的领导给了他一个“完成自己浪漫主义结束曲的机会”,否则,嵇康想浪漫也浪漫不得。嵇康之所以名垂千古,还不是因了司马昭的“宽容”!这就是王蒙的“宽容”!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理解,可能冤枉了这位管文化的前部长。可是,我们只要看一看他对所谓“权力中心”的膜拜与对嵇康一类“精英”的蔑视,就不难理解了。他在《我们这里会不会有奥姆真理教?》一文中说:“即使少数精英中有一点迹近极端偏执的调调,他们离权力中心还有十万八千里,因而其文化批判的积极作用最大最大,而变成排他的权力实践的可能性最小最小最小。”王蒙虽然把这腔调摹拟成了他人的“调调”,但仍然可以看出他潜意识中的思想活动。他的言外之意是,精英们尽可以像嵇康一样喋喋不休,可是,他们除了喋喋不休以外还有什么用处呢?宰人的刀还不是操在司马昭的手里?王蒙曾经离“权力中心”只有180米,他的长进就像林彪一样, 只是学会了“最最最……”这样“幽默”的表述方式。由此观之,他说的司马昭的“宽容”仅仅是一句反话、或仅仅是一句调侃的话吗?此外,王蒙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意思,你们反对我的宽容,可是,连杀人者都要讲宽容,我也讲宽容,难道讲错了吗?似有以此为自己开脱或是辩护的意思,若是这样,这也是一个绝对蹩脚的佐证。
王蒙说:“嵇康为什么被杀?罗氏认为是由于‘他太认真’‘性烈’‘在思想感情上把自己和世俗对立起来’,罗氏最精彩的论述是:‘以自己为高洁是可以的,以世俗为污浊则不可。’以致,他认为这是嵇康的‘性格弱点’。由于‘认真’‘性烈’‘与世俗对立’就要掉脑袋,这很可怕也很不好。另一方面,从嵇康本人方面探讨一下经验教训,并非没有话可说。”王蒙接着用他刻意装出来的而不是秉性使然的“幽默”语言说:“山涛向朝廷推荐嵇康代己为官,看不出有什么恶劣的用心,辞谢是可以的,写‘公开信’与之绝交,就有点不合分寸。”“辞谢”是那么容易的吗?与嵇康同时的刘毅,也是颇有声望的人。司马昭请做“相国掾”,他借病推辞,不肯就职。后来司马昭就要对他下手,刘毅害怕,只好答应上任。陈四益说:“对于司马昭这样的枭雄,杰出的人才如果不能为我所用,也决不能留给自己的对手。便捷的办法就是杀掉,就像曹操杀掉孔融一样。”(《乱翻书·嵇康之死》,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再接着,王蒙谈了一大堆如阮籍、陶渊明、孟浩然等也不是不想做官之类的话,也不知他是不是为了证明嵇康的辞官是假清高,也不知是不是为了证明他的当了文化部长也不是不清高。
嵇康的掉脑袋是因为“太认真”、“性烈”、“和世俗对立起来”、“以世俗为污浊”吗?至少不完全是。咸熙二年(265 )司马昭死,司马炎废曹奂建立晋明。从正始元年(240年)开始,二十多年间, 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司马氏得胜,曹氏集团中人几乎被杀绝。嵇康是曹家女婿,自然在被疑忌之列。嵇康的斥责山涛,仅仅是斥责山涛吗?显然不是。我们只要读过《与山巨源绝交书》并对其稍有研究,就知道《绝交书》不只是针对山涛个人,而是“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是一篇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声明,一篇反礼教的宣言。所以,鲁迅说:
古之稽康,在柳树下打铁,钟会来看他,他不客气,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于是得罪了钟文人,后来被他在司马懿面前搬是非,送命了。所以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拱作揖,让坐献茶,连称“久仰久仰”才是。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况且这位恐吓家的举例,其实也是不对的,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径”》)
鲁迅的话说得很明白,嵇康得罪了钟会只是外因,嵇康独立于司马集团之外、又是曹家女婿,这才是内因,才是致死的根本原因。没有钟会搬弄是非,也会有别人搬弄是非,总之,嵇康必死无疑,不管他认真与否,性烈与否,与世俗对立与否。
嵇康一案是钟会审理的,他认为嵇康该死的理由是:“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物,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不事王侯”、“不为物用”这才是要害所在。
嵇康被逮入狱时,三千多太学生上书,“请以为师”,许多人甚至愿意随他入狱。陈四益说,这些救援嵇康的行动,实则加速了嵇康的死亡。这样一个拒不合作而又广有影响的人物,不杀,司马昭睡得着吗?
退一步说,如果嵇康真的如王蒙所认同的那样,是由于“太认真”、“性烈”、“和世俗对立起来”、“以世俗为污浊”而掉脑袋,那么,王蒙不去谴责统治者的残暴,却在怪罪嵇康自己找死,这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像嵇康以及屈原这样“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忧国忧民者的形象,向来是崇高的。王蒙所“躲避”的崇高就是这样的崇高吗?王蒙对司马昭的凶残不置一词,却在那里对嵇康之死缺乏历史常识的胡扯,这不得不让人想起“三·一八”惨案以后,教授学者不去指责、声讨军阀的残暴,却在那里煞有介事地责怪学生怎么去蹈“死地”呢?王蒙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怎么与“正人君子”们如出一辙呢?
王彬彬在与王蒙论战时,写过《再谈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及其他》,其中一段话可谓痛快淋漓:
在做人之道的意义上,这的确表现了嵇康的“性格弱点”,表现了立身处世上的“不聪明”,但也正是这种“性格弱点”,这种“不聪明”,成就了嵇康一种堪称伟大的人格,使得中国文学史上有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倘若嵇康做人世故一点,聪明一点,懂得一点“分寸”,中国文学史上不是便少了一篇名作么?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史上,如果没有一群嵇康这样的人,不是便如头顶上没星辰么?要真正做到嵇康这样,当然不易。但要对这种人格表示敬仰,总还可以,后人对这种人格“虽不能至”,但总应该“心向往之”的。(《死在路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版)
紧接着,王彬彬也把王蒙对嵇康之信口开河与鲁迅联系起来,他说:“嵇康是鲁迅所喜爱者。鲁迅在思想、性格、文风上都颇受嵇康影响,也曾在二十年间十次校勘《嵇康集》。后人妄自‘粪土’嵇康,也正用得着‘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句诗。”(引文同上)
7
王蒙太聪明,总是对的。鲁迅从来就不能用对和不对来衡量。鲁迅与王蒙相反,用世俗的眼光看,以当局的需要来衡量,鲁迅总是不对的。有什么办法呢?
王蒙既掌握上头的政策,也理解下头的需要。王蒙人缘好。王蒙被广大的人们接受了,王蒙入世,王蒙随俗,王蒙终于仍是一个聪明的匠人。鲁迅是鬼,是狼,鲁迅被千夫所指,鲁迅“独战众数”(用王蒙的话说就是“站到了世俗人生的对立面,站到了普通人与平常心的对立面,站到了通常的社会秩序与群体规则的对立面——所谓一个人与全国全人类作战……”),然而,鲁迅是精灵,是游荡在中国上空的永远不灭的鬼的精灵。
王蒙是幸运的,他没有生活在30年代,以他的世故,以他的聪明,以他对无聊无耻的精神赞助……他若生活在30年代而不被鲁迅“骂”得狗血喷头,那肯定是文坛奇迹,那鲁迅也将不成其为鲁迅,那鲁迅便成了周作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