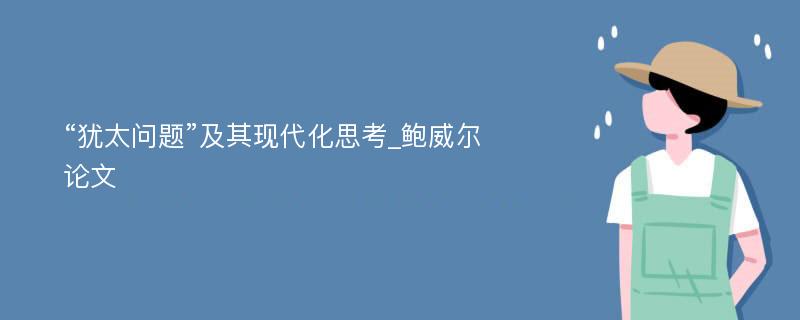
探问《论犹太人问题》及其现代性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犹太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2-0001-07 很难想象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享有那么令人瞩目的理论地位。这篇不到2万3千字的回应性文章竟然吸引了有着不同理论立场、不同理论背景的学者的阅读、研究,成为研究马克思政治、法权、宗教、市民社会、现代性等思想必须认真研读的一个文本,也是马克思的赞成者与批评者都难以绕开的一个文本。究其缘由,除了这一文本含蕴的问题深广且具有“承上启下”的理论地位以外,就是马克思借“犹太人问题”之思,切入了对“现代人问题”之思。 一、《论犹太人问题》文本的独特地位 对于马克思的哲学爱好者来说,马克思的很多早期文本,如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莱茵报》时期的论证性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都有着回味无穷的理论魅力。这些文本不仅哲学味浓郁,思辨性强,而且饱含理论的激情,深得理性与激情的相得益彰。但如就较多地透露了马克思思想的文本来说,我认为《论犹太人问题》是当然之选。这个文本堪称马克思思想的一个转折点,一个“过渡”,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此前思想的身影,而且可以看到他此后的思想发展,是了解马克思思想的一个较好的窗户。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论犹太人问题》就恰如马克思思想的一个“眼睛”。透过这个窗户或“眼睛”,马克思早期的很多思想以及后来的思想发展都可以得到较好的理解。比如,此前存在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莱茵报》时期的文章中的“自由”精神和“现实”诉求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还依然存在;存在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诸多理论论断——例如,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而不是相反——在《论犹太人问题》这里得到了应用和充分的发挥;而此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文本中关于国家、法律、宗教、市民社会等的剖析和共产主义描述等,也都能够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找到思想因子。 《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的两篇文章之一,它和另一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被列宁称之为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彻底完成”。①这两篇堪称姐妹篇的奇文都是马克思在历经《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问题的困惑后的思想结晶,是马克思退回书斋后,为期一年的“闭关”心得。如梅林所说,这两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同,但在思想内容方面却密切相关。②前者确如标题所表明的,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一个导言,目的在于归结《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思想观点和表述作者的思想诉求和阶级立场,认为德国社会的出路在于超越市民社会,而扛起这一历史责任的主体就是无产阶级;后者则是借助“犹太人问题”这一论题,切入了对市民社会的分析,暴露了市民社会的诸多弊病,揭示了犹太人的人格形象即为市民社会的“市民”形象,并已成为现代人的人格形象。因而,超越市民社会就是超越一个唯利是图、以金钱和利己主义为生活准则的社会。也因此,如果借用马克思后期的资本批判来理解这两个文本,那蕴涵在这两个文本中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对劳动(或无产者)与资本(或资本家)对立的把握,就已经具有了后期理论批判的雏形。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不仅饱含了马克思丰富的思想精华,表现了马克思娴熟的哲学技艺,而且透露出一种批判性的思想反思。我们知道,在此之前,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已经看到了当时普鲁士社会的诸多病症——现实中的国家和法无不受私人利益所支配,保护的无非是有产者的利益,穷人的利益却被排斥在外,以为这样的“病症”就是现实的国家和法律之病,但在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马克思意识到,表现在现实的国家、法律中的诸多病症并不是病根所在,因为这种表征在政治社会上的病症恰是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基础和核心的市民社会的病症的外部表现。在他看来,受市民社会所支配的政治国家和法律必定具有这样的病症,而要医治这样的病症,仅给政治国家和法律开出“正义”方剂的治标方式是无济于事,恰当的方式是直接诊治“市民社会”这一病根才有可能,而要诊治市民社会这样的病根就不是那种适合诊治政治社会的工具(比如正义、道德、法哲学等适合于诊治政治社会的理论工具)所能胜任,而必须运用那种能够把握市民社会的历史脉动和运作方式的工具才有可能。另据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的表述,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发现了他需要诊治的对象和用以诊治的工具——市民社会和政治经济学。③在这个意义上,《论犹太人问题》可以说是马克思这一“发现”的牛刀小试。它浓缩了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精华和未来的理论指向,且也许正是由于《论犹太人问题》这一文本的独特地位和丰富思想,国外、国内学者以不同的理论视野和立场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留下了大量有深度的理论成果和思索。④ 二、《论犹太人问题》开启的思考 正是《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理论地位,以及研究者众多的缘故,这一文本才开启了人们广阔的思维空间。以下就是对学界思考的一个简要的勾勒。 (1)关于马克思写作这篇文章的意图的探问。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马克思写作这篇文章是为了驳斥“鲍威尔关于犹太人的解放的诉求和鲍威尔对作为犹太人的政治身份的评价?”⑤还只是布鲁诺·鲍威尔的写作激起了马克思的回应?⑥是想借“犹太人问题”来批判鲍威尔,还是借鲍威尔的文章来阐述他所理解的“犹太人问题”?或他根本不在于探讨“犹太人问题”,而在于借“犹太人问题”这一论题,阐述他对一些问题(比如政治解放问题、权利问题、人类解放问题等)的看法? (2)关于马克思笔下的“犹太人问题”的思考。比如,犹太人怎么成了问题,特别是在德国成了问题?马克思所指的“犹太人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是种族问题,还是宗教问题,抑或是市民社会的问题,或者说是政治解放问题,还是人的解放的问题? (3)对鲍威尔犹太观的探问,及对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的原因的思考。比如,鲍威尔关于犹太人解放的观点是不是完善的?⑦或鲍威尔的观点是犹太人的社会解放依赖于犹太人的宗教解放?⑧还是鲍威尔认为犹太教次于基督教,因而犹太教的解放比基督教的解放要更为困难,相对于基督教的解放只需一步来说,犹太教的解放则需两步?⑨或鲍威尔是在为所有宗教团体的充分平等和所有建立在人权之上的、在宗教上中立的国家进行辩护?⑩ (4)关于如何看待马克思在这一文本中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批判的思考。比如,我们是否认为“纳粹时代的悲惨事件既不会使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经典分析变得无效,也不需要对其观点进行修正”?(11)或认为马克思在写这篇文章时,一点也不关心犹太人?(12)马克思是以其犹太人的方式写作(13),马克思对犹太教的批判只是延续了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对犹太教的批判?(14)或马克思试图把自己从犹太性(Jewishness)中解放出来?(15)马克思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在细节上是错误的?(16)或他在根本上和事实上都是错误的?(17)而争议最多的问题就是马克思是否是反犹主义者的问题之争。(18) (5)如何看待《论犹太人问题》这一文本的理论地位的问题。作品一旦面世,就有属于作品自身的命运。与《论犹太人问题》在今日备受瞩目相比,《论犹太人问题》在发表后的相当长时间并不为人们所重视,只是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引起人们的注意。(19)不过,自从其备受关注之日起,各种解释性的著作和文章就纷至沓来,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评价。比如,既有来自列宁、梅林等人的赞赏,认为“任何评论都将只是弱化其根本的考察,马克思这几页的文章胜过了已经出现的如山的文献”(20);也有来之达戈贝特·鲁内斯(21)、以赛亚·柏林等人的贬抑,认为它只不过是“乏味而浅陋的文章”(22)。它似乎是一座蕴涵多种矿产资源的富矿,有着挖之不尽的价值。各种不同的解释性著作和文章不仅未能尽现其丰富,展现其中奥秘,反而是使它陷于一种解释和争论的漩涡之中。因此,如何潜入这一漩涡,窥破问题所在,也成为解读的一大任务。比如,像尤利叶斯·卡勒巴赫(Julius Carlebach)就提出: 为什么马克思就犹太人主题写了两篇独立的文章,为什么他在《神圣家族》中几乎是重写了这两篇文章,在那,他承认了早期文章中的错误和他使用“哲学术语”所带来的含糊?马克思说他写的是德国犹太人的解放。难道他真的是指德国的犹太人,还主要是关心普鲁士的犹太人?谁在为犹太人的解放呼吁,谁又是阻止他们去实现?1842-1843年间有何特殊?在那么一个特定的时间,在关于犹太人解放的问题上激起了那么多的赞成者和那么多的反对者。(23) 马克思具有纯正的犹太血统,这是很多作家都重视的一个事实,但这一事实与马克思对待犹太人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又有什么相关性?马克思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是因为写的人是马克思,还是因为这篇文章给犹太人问题以实质性的解决?难道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最富有原创性的贡献:他试图把有血有肉的人转换成一个社会经济范畴?马克思的阐释是怎样有效的,以及它对后来十九世纪出现的政治的反犹主义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24) 看来,要潜入这一争论的漩涡之中而又不至于在漩涡中迷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研读者不熟悉《论犹太人问题》文本本身,或缺乏对解读的客观性追求,而是“自以为是”地一头扎进的话,更是如此。 三、关于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两个理解诉求 不可否认的是,不同的读者在研读《论犹太人问题》时,一般都会有自己的提问方式和理解,但不论提问的方式和理解如何纷繁多样,仅就《论犹太人问题》是一篇有驳有立的文章而论,至少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理解诉求:“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理解诉求;“择其要旨”的理解诉求。 (一)“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理解诉求 在我看来,这样的理解诉求并不局限于《论犹太人问题》,而差不多是所有解读者的一个理想诉求:比作者更为理解作者。具体到《论犹太人问题》这篇“有驳有立”的文章来说,就是研读者不仅要对马克思、鲍威尔的观点了如指掌,而且还要能够作为旁观者、评判者对双方的论战做出中肯、客观的评价;不仅要明晓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所要确立的观点和论证,而且要明晓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所有观点和论证,甚至对他们各自的整体思想和他们的时代背景等都要有一个合理的把握。如是,才有可能对论证双方做出中肯、客观的评价,这种理解的难处不在于理解马克思所要确立的观点,而在于较为合理、客观地理解鲍威尔的观点。这样的理解就意味着不能局限于《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所表述的鲍威尔,还要理解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没有被表述出来的鲍威尔”。这一点恩格斯就特别自觉,他在1893年10月3日致海尔曼·布洛歇尔的信中谈到:“关于布鲁诺·鲍威尔1843年以前的经历、他的遭遇和观点,您可以在卢格出版的杂志《哈雷年鉴》、即后来的《德国年鉴》以及布鲁诺本人的著作中找到说明。1844-1846年这一段,同样可以看他的著作和他的《文学总汇报》……我觉得,如果不在柏林呆一段较长的时间,不可能顺利写出论布鲁诺的著作,因为柏林保存有全部有关材料。”(25) 如是,在理解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争论上,要客观地做到“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确有些难度。因在研读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时,尽管研读者可能避免仅“听从”马克思一方的论述,并试图“同情”、“倾听”鲍威尔一方的论述,也“倾听”那些“为鲍威尔辩护”的研究,比如,兹维·罗森和道格拉斯的研究,以避免做出不利于鲍威尔的理解,但如果说,仅凭此就足以达致“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理解诉求,则难免有些自以为是。因而,以“择其要旨”的方式来对待《论犹太人问题》,就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选择。 (二)“择其要旨”的理解诉求 “择其要旨”的理解诉求不在于追求“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或面面俱到地把握文章各种显明的、隐藏的观点和论证,而在于把握文章的要旨。就《论犹太人问题》这篇文章而论,我认为其要旨是马克思在这篇论文所要确立的观点和论证,以及透过这篇文章我们所能读到的马克思潜藏的一些思想。(26)因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重要的不在于批驳,而在于立论,正如他自己在通信中提到的,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试图把“犹太人问题”带入“另一条轨道”。如是,我们就可以不必过于在意是否能够完全地掌握马克思的批驳对象鲍威尔的所有思想,而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所要“立论”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在理解鲍威尔方面上的不足就是可以容忍的。 而就正确把握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这一文本中所表述的思想来说,应推《神圣家族》的第六章,因马克思曾与恩格斯在这一章中精炼地表述了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思想和与鲍威尔的分歧。但假如我们不仅想知道马克思所告知的,还想探讨马克思所没有示知的;不仅想知道争论双方的当事人是怎么思考的,还想知道争论双方为何是那样思考的,那解读就不能仅停留于马克思在《论犹太问题》和《神圣家族》中的表述,还必须具体探问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的立论与论证,特别是当我们持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27)的成见时更是如此。 四、《论犹太人问题》的要旨及其反思精神 (一)《论犹太人问题》的要旨 在我看来,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的要旨是:从市民社会批判的视角出发揭示什么是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以此批判鲍威尔仅从宗教批判的视角出发去看待犹太人问题,“把‘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混为一谈的根本错误”(28),并以此论辩犹太人有资格获得政治解放和公民的解放。 非常有趣的是,在马克思对其要旨进行论证的过程中,却潜藏着关于“犹太人”的一组论证: (1)人权天然属于“犹太人”;(29) (2)现代人都是“犹太人”; (3)人的解放与希望在于告别“犹太人”,成为“新人”。 对于(1)人权天然属于“犹太人”的论题,我们只需要注意到马克思把人权视为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而“犹太人”就是利己主义的人,就可以看出人权天然属于“犹太人”的权利。 可以看出,“利己主义的人”成了联接“人权”与“犹太人”的一个中介,而作为这样的中介,也被表述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而这些,在马克思看来都是与“犹太人”相通的,因而,当把人权表述为“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的权利时,马克思已经把人权阐释为属于“犹太人”的权利,个中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笔下的“犹太人”被赋予了“利己的”、具有“占有性”的、“孤立的”、“封闭的”、“排斥性”的这样一些“市民社会”的人的特性。或者说,是用“犹太人”来象征和“比附”具有这样一些特性的人。 市民社会从自己的内部不断产生犹太人。 犹太人的宗教的基础本身是什么呢?实际需要,利己主义。 因此,犹太人的一神教,在其现实性上是许多需要的多神教,一种把厕所也变成神律的对象的多神教。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30) 这样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也就是“现代人”,是生存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离的人,或者说,就是生存于脱离了政治共同体的“市民社会”的人,即现代人成了马克思笔下的“犹太人”。而这样的“犹太人”(现代人)显然不是马克思所向往的,而是马克思所试图超越的。于是才有“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31),即现代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要从这种追求“实际需要、利己主义”的精神中解放出来,从而告别“旧人”,成为“新人”。 “旧人”是处在市民社会中的人,“新人”则是处在“社会化”的人(32),或生活在“共产主义”共同体中的人。(33) 这样一种“新人”的表述,很容易让人想到卢梭、费尔巴哈等思想家设想中的“新人”、尼采笔下的“超人”,甚至是基督教的“新人”。不过,马克思的“新人”绝不同于卢梭笔下的“新人”,卢梭等政治思想家笔下的“新人”只能是理想的政治世界中的“公民”,在马克思看来,这依然是立足于“市民社会”的“旧人”。而尼采的“超人”和基督教的“新人”,反而与马克思的“新人”有几分类似:都表现出对“已存在过的人”、当代人的超越。但马克思笔下的“新人”毕竟不同于尼采的超人,也不同于基督教的“新人”,尼采的超人虽然表现出一种追求个体生命拓展和不在乎是否被承认的“卓立不群”,但却表现出一种对个体生命的“占有”和反“社会化”倾向,这一点不同于马克思;基督教的“新人”与马克思的“新人”也的确有些形似,都表现出对世俗社会的批判,并要求从摆脱“旧人”的过程中走向“新人”,以及组成新的“共同体”:一个是天国,一个是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类似性还一度出现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之中。但马克思的“新人”显然不同于基督教的“新人”,基督教的“新人”虽然也强调“事功”的作用,但主要是强调只有通过“信仰”才能经由“旧人”而重生为“新人”,沟通“旧人”与“新人”的主要是信仰,而不是马克思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历史必然性。(34) 另外,马克思的“新人”也很容易让人想起毛泽东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特别是把这一“新人”理解为对“利己主义”、对占有性、排他性的超越时更是如此。但假如把马克思的“新人”理解为其后来的“共产主义”的人时,就有些不太一致。因为马克思笔下的“新人”是不需要身份认同、不需要道德评判、也不需要法权来给以承认的人,霍耐特那种需要“为承认而抗争的人”并不是马克思笔下的共产主义中的人。 共产主义中的人是这样的人: 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阿格尼丝·赫勒曾认为马克思的理论诉求在于理性,似乎马克思是带着理性的诉求在批判非理性的一切。(35)无独有偶,阿兰·麦吉尔在其《理性的负担——马克思为什么拒斥政治和市场》(2002)一书中,也把马克思对政治、市场的拒斥,视为马克思对理性的诉求,追求普遍性和必然性所致。但在我看来,与其赋予“理性”在马克思拒斥政治、市场以过多的比重,不如将马克思的诉求理解为:做一个不需要“被承认”的人。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市场无不意味着间接地以政治、市场给人以承认(36),以政治、市场的方式“承认”个人存在的价值,承认人是有可以出卖的人,承认是相互之间必须看为“有权利”的人,需要“相互防范”的人,假如这样,那人其实也是活得相当无奈和无趣的。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就指出: 《德法年鉴》已经向鲍威尔先生阐明,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认”无非是对利己的市民个体的承认,也是对构成这些个体的生活状况的内容,即构成现代市民生活内容的那些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失去控制的运动的承认…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意义。 也许对马克思来说,人最诗意的是,可以不需要承认(特别是那种经由政治、市场的承认),不需要攀比、评判,(37)自在地生活。这听起来有点像尼采笔下的“哲人”——可以自在地生活,但又不是神或野兽。听起来的确多少有些乌托邦的味道,但这样的一种乌托邦却历来是宗教家、哲学家等的期待与呼唤——做一个能够超越世俗社会的人,一个可以告别“旧人”的“新人”,并生活在由“新人”所组成的“天国”或共同体之中。只不过对于这样的一个“新人”和“新人的共同体”的到来,宗教家和鲍威尔等思想家更多的是赋予心灵的力量,即信仰或精神的力量,而马克思更多的是赋予社会物质生产的力量。不过,历经历史的检验,这两种力量都是不能偏废。 (二)《论犹太人问题》的反思精神 《论犹太人问题》还有一个独特之处是,这是一篇犹太人写的剖析、批判“犹太人”的文章,对此,有不少学者以此将马克思理解为是一个反犹主义者或自我憎恨(Self-hatred)者。但我认为,就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对“犹太人”的剖析和批判来说,与其把马克思理解为反犹主义者或自我憎恨者,不如把他理解为具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卓越的反思精神。萎缩或弱小的心灵不敢直面自身,只有伟大的心灵才有勇气和能力去反思自身。哲人都善于自省。身为哲人的犹太人马克思不可能不对自身进行反思,不可能不对犹太人这个族群进行反思。 而就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要剖析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可以以“犹太人”作为象征的“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来看,表现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马克思就不是一位反犹主义者或自我憎恨者,而是一位立足于“现代社会”的反思者和批判者。那种视他人为地狱,视金钱为上帝,视人生为利己的占有性的人生的现代性观念,一直是马克思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在我看来,这就是充盈于马克思字里行间作为哲学家、作为犹太人的“反思精神”。 善于反思是一个人的理性趋于健全,个性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趋于成熟的标志。以我拙见,人总要在反思中,吸取动力,奋然前行;民族总要在反思中奋进,在重温历史中找到精神的寄托与榜样,不重蹈不堪回首、耻于回首的身影和劣迹,从而警惕前行。 本文是即将出版的《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读本研究》一书的序言。因是序言,所论内容也大多只是提纲挈领性的。 ①《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3页。 ②[德]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85页。 ③顺便一提,马克思诊治“市民社会”并不是要完善市民社会,而是要废除市民社会,认为政治国家和法本身就是一种缺陷性存在,这种缺陷性恰恰是市民社会这种缺陷性存在的外部表现,因而,只有废除市民社会,才能消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从而解决政治国家和法本身的缺陷。 ④不仅有数以百计的研究性论文,而且有数以十计的研究性著作。仅以这一文本为研究主题的专著就有尤利叶斯·卡勒巴赫的《卡尔·马克思及其对犹太教的激进批判》(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Critique of Judaism,Routledge & Kegan Paul PLC,1978);D.K.费斯科曼的《流亡中的政治话语:卡尔·马克思和犹太人问题》(Dennis K.Fischman,Political Discourse in Exile:Karl Marx and Jewish Question,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1);而单就2015年而论,论述到这一文本的专著就有Idit Dobbs-Weinstein,Spinoza's Critique of Religion and its Heirs_Marx,Benjamin,Adorn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Norman Arthur,Fischer-Marxist Ethics within Western Political Theory_A Dialogue with Republicanism,Communitarianism,and Liberalism,Palgrave Macmillan,2015; Edward Royce,Classical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_Marx,Durkheim,Weber,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5;等等。 ⑤R.A.Nisbet,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London,1970,p.134.转引自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pp.1-2. ⑥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p.1. ⑦L.D.Easton and K.H.Guddat,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New York,1967,p.216.转引自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p.1. ⑧R.C.Tucker,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p.111. ⑨D.McLellan(ed,),Karl Marx:the Early Texts,Oxford,1971,p.xxv.转引自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p.1. ⑩W.Post,Kritik der Religion bei Karl Marx,p.147.转引自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p.1. (11)Karl Marx:His Life and Environment,p.99.转引自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p.2. (12)I.Deutscher,The Non-Jewish Jew,London,1968,p.49.转引自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p.2. (13)转引自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p.2. (14)Idit Dobbs-Weinstein,Spinoza's Critique of Religion and its Heirs_Marx,Benjamin,Adorn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93-107. (15)E.Wilson,To the Finland Station,p.121.转引自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p.2. (16)例如H.Liebeschiitz's ‘German radical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Jewish political attitudes',in A.Altmann(ed.),Studi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Jewish Intellectual History,esp.pp.156-159.转引自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p.2. (17)转引自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p.2. (18)对于此一问题,笔者将另外撰文论述。 (19)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Critique of Judaism,p.1. (20)Franz Mehring(ed.),AusdcmliterarischenNachlass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1841 bis 1850,vol.1,p.356.转引自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p.2. (21)1959年由这戈贝特·鲁内斯(Dagobert D.Runes)编辑的《没有犹太人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Jews)文集中,将其视为“反犹主义”的一个代表作。 (22)Franz Mehring(ed.),AusdcmliterarischenNachlass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1841 bis 1850,vol.1,p.356.转引自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London,p.2. (23)L.Schwarzschild,The Red Prussian:Life and Legend of Karl Marx.转引自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p.2. (24)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pp.2-3.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27页。 (26)当然,可能会有人认为对《论犹太人问题》中的鲍威尔的思想的理解,也可以理解为“择其要旨”的理解层次。但这种解读方式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择其要旨”的理解层次,不如说是“局部性理解”的层次。 (27)比如未曾把自己视为宗教哲学家的黑格尔却把费尔巴哈视为宗教哲学家,视为“犹太-基督”传统的捍卫者,试图将自己与宗教家、神学家区分开来的鲍威尔却被马克思视为宗教家、神学家,试图把自己与哲学家区分开来的马克思也被后来者视为哲学家。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4页。 (29)也许我们会认为,这里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人权,而不是人权本身,这里的人是指资产阶级,而不是指“现代人”,这样的理解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这样的理解,难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深刻性和彻底性。史蒂文·卢克斯最近在《新劳动论坛》发文《今日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2015)也指出了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的误读。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页。 (31)同上,第55页。 (32)参看《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十条。 (33)后面这一句听起来有点像循环论证,因“共产主义”共同体就是“新人”的共同体,而“新人”则只有处在“共产主义”共同体的人方可称之为“新人”。 (34)马克思这种把社会生产视为“旧人”与“新人”的联接,的确存在着一些缺陷。 (35)参看[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9—50页。 (36)“以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对国民经济学所进行的批判,承认人的活动的一切本质规定,但只是在异化的、外化的形式中来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70页。 (37)在我看来,马克思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一个思想——人与人之间应该只存在差异性,而不应该有平等或不平等的界分。这一点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平等”的论述就可以看出。标签:鲍威尔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论犹太人问题论文; 犹太民族论文; 现代性论文; 基督教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神圣家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