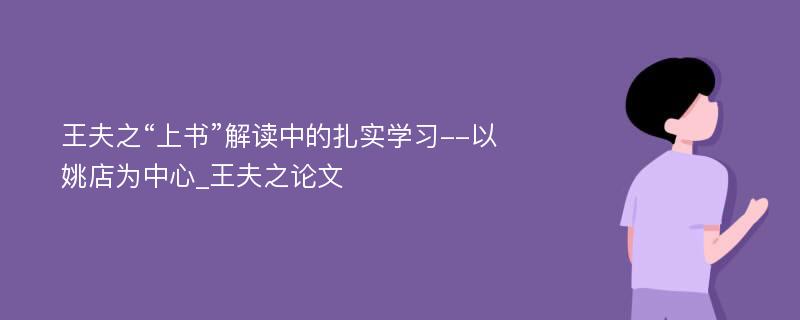
王夫之《尚书》诠释中的实心实学——以《尧典》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学论文,实心论文,尚书论文,王夫之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9)01-0019-09
王夫之身处明末清初社会大变动之际,备尝亡国之惨祸烈毒,自觉担负起总结明亡教训,重新塑造中国文化,为继起者提供新的思想形态的重任。这一愿望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尚书》的诠释中。王夫之的《尚书》诠释,涉及对理学根本观念如道体、性命、天人、义利、才情、名实、理势、诚神等的深入探讨,以及对明末弊政的抉发、对王门后学及佛道二教的批评等方面。通过对以上重要问题的推阐发挥,彰显他的文化理念和治世宏规。王夫之的以上活动,都立基于以诚明为中心的实心实学。本文以他对《尧典》篇的发挥为中心,来说明这一点。
一、“诚明”与“文思恭让”
《尚书·尧典》开篇一段,颂扬尧的品德和功绩,其中说:“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王夫之对《尧典》的发挥全在这一段话上,特别是其中的“钦明,文思恭让”几个字。这几个字的意思,郑玄解释说:“敬事节用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虑深通敏谓之思,不懈于位曰恭,推贤尚善曰让。”①王夫之于中最重视的是钦与明的关系。他将钦之“敬”的意思理解为诚,然后借《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及“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之意,将“诚”理解为天道,作为生起“明”的根据,“文思恭让”皆出于“明”。意在将人的观念与行为统辖于诚明之下。以人合于天,以天范导人,是王夫之的《尚书》解释的主要着眼点。
王夫之的解释从尧之德性开始,一步步推出明与诚的关系。他说:“圣人之知,智足以周物而非不虑也;圣人之能,才足以成矩而非不学也。是故帝尧之德至矣,而非‘钦’则亡以‘明’也,非‘明’则亡以‘文思安安’而‘允恭克让’也。呜呼!此则学之大原,而为君子儒者所以致其道矣。”②这是说,尧之“文思恭让”之德出自“明”,而明出自“钦”。以钦出明,以明出文思恭让,是君子获致其道的必由之路。世人有行文思恭让而不出于明者,亦有明而不出于钦者。文思恭让而不出于明,文是虚文,思是狂慧,恭是繁劳③,让是愚谦。明而不出于诚,明是浮明。在王夫之这里,诚是天道之本体,明是与天为一之精神境界所具有的证悟与明觉。他力戒世人勿居勿为的是“浮明”。浮明即无有天道性理范导的纯理智。而“明”即据天道诚体而行动的理性。此诚体即天即人,在天为天道,在人为性体,性体即在人心之中。王夫之根据《中庸》之“天命之谓性”,以及程颐、朱熹以来儒者的主流理解,认为性体是天赋的、绝对的,文思恭让所持守为根据的,即自己心中本具之性体。他说:“天下之为‘文思恭让’而不‘明’者有之矣,天下之求‘明’而不‘钦’者有之矣。不钦者非其明,不明者非其文思恭让也。‘文’有所以文,‘思’有所以思,‘恭’有所以恭,‘让’有所以让,固有于中而为物之所待,增之而无容,损之而不成,举之而能堪,废之而必悔。凡此者,明于其所以,则‘安’之而允安矣。”④王夫之强调的是天道、性体对人的范导,这种范导是通过人自觉心中的性理而实现的。性理“固有于中而为物之所待”,人自觉地服从性理的范导就是遵天而行。“天”在王夫之的整个哲学系统中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切价值的源头。性理作为人的价值源泉显现了天的内容,通过人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实现天监临人、范导人的作用。这一点,是王夫之修养功夫的起点,也是他的哲学具有特殊识度的基础,所以他非常强调人对性体这一价值源泉的省觉。明就是这种省觉。他说:“圣人之所以文思恭让而安安者,唯其明也。明则知有,知有则不乱,不乱则日生,日生则应用无穷。故曰:‘日新之谓盛德,富有之谓大业’,此之谓也。盛德立,大业起,被四表,格上下,岂非是哉!”⑤王夫之亟欲向人们昭示的道理是,人的一切有价值的行为,源于“明”,由“明”指导的行为,不仅因为贯彻了天理而有积极的效果,而且因为符合人的价值理想而心安。明首先表现为“知有”。知有即实知外界之物。对外界之物的实知是正确行为的首要条件,故知有则不乱,不乱则事物各循其理,生生不穷。“明”对人自身来说,是盛德之树立,对人的行为来说,是产生大业的基础。如果用《尚书》本文富于象征意义的话说,有“明”则光照四方,彻于上下。王夫之対《易传》“大明终始,六位时成。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一句的解释,或可为此处“明”的注脚:“大明,天之明也,六位,六爻之位。时成,随时而刚健之德皆成也。……以圣人之德拟之,自诚而明者,察事物之所宜,一几甫动,终始不爽,自穉迄老,随时各当,变而不失其正,益万物而物不知,与天之并育并行,成两间之大用,而无非太和之天钧所运者,同一利贞也。”⑦这可以说是对以上“明则知有”的天人合德的说明。
王夫之时时告诫人们、警醒人们严加区别的是未与天道合一的“明”。此明指人的耳目感官的固有性质,而无有性理之范导者,也就是离开了诚的明。此种明是人之天赋,不求即自然而在;而与天道为一之明、出于诚之明,却须由艰苦修养而得,故修身最为重要。他说:“虽然,由‘文思恭让’而言之,‘明’者其所自生也。若夫‘明’而或非其明,非其明而不足以生,尤不可不辨也。‘明”诚’相资者也,而或至于相离。非诚之离明,而明之离诚也。诚者,心之独用也。明者,心依耳目之灵而生者也。夫抑奚必废闻见而孤恃其心乎?而要必慎于所从。立心以为体,而耳目从心,则闻见之知皆诚,理之著矣。心不为之君而下从乎耳目,则天下苟有其象,古今苟有其言,理不相当,道不自信,而亦捷给以知见之利。故人之欲诚者不能即诚,而欲明者则辄报之以‘明’也。报以其实而实明生,报之以浮而浮明生。浮以求‘明’而报以实者,未之有也。”⑧此中对于诚、明的界说大有深意。“诚者,心之独用也”,指诚是心与道体为一而不杂于尘俗的状态,故称“独”。另外,诚体是自足的,超越一切对待,故称独。不杂于尘俗,故纯是天理;超越对待,故可供一切具体事物取资而己不取于他物。明本质上是指因耳目之聪明,理性之明敏而有的认识外物的作用。这种作用必须通过认识外物而显现。故孤零的、不与外物发生交涉的心不足谓之明。
在诚与明的关系上王夫之主张“诚明相资”:“诚”以“心与道俱”提供给“明”价值规范,使明不致离开诚而成为浮明。“明”以心的认识活动所以发生的根据提供“诚”得以显现的场所。在诚明两者中,明作为主体具有主动的特点。诚明可以相离,这种相离是因为明主动脱离了诚的规范而成为浮明。浮明不足以成为盛德大业的产生者。故王夫之强调心必须“慎于所从”,此亦重言孟子“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之意。抉择所从,须诚体作主而耳目从之,则耳目闻见皆在诚的规范之下。王夫之特别提醒的是,诚只有一个,而明则有两。真心求诚,不一定求得到,而求明则必然得明。因为无诚之明人天赋即有,而与诚为一之“明”则是修养的结果。
修养则“钦”字当先。在王夫之的诠释中,“钦”字担当的责任要比它的本义“敬”字大得多,它有顺承天道诚体并敬奉于身的意思,因而“钦”字即“诚”字。王夫之说:“‘钦’之为言,非徒敬之谓也,实有所奉至重而不敢亵越之谓也。……天之风霆雨露亦物也,地之山陵原隰亦物也,则其为阴阳、为柔刚者,皆物也。物之飞潜动植亦物也,民之厚生利用亦物也,则其为得失、为善恶者,皆物也。凡民之父子兄弟亦物也,往圣之嘉言懿行亦物也,则其为仁义礼乐者,皆物也。若是者,帝尧方日乾夕惕以祇承之,念兹在兹而不释于心,然后所钦者条理无违,而大明终始。道以显,德行以神。曾是之不容,则岂非浮屠之‘实相真如,一切皆空’,而‘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亦其所不恤矣。无已,其以声色臭味,增长人欲者为物乎?而又岂可屏绝而一无所容乎?食色者,礼之所丽也。利者,民之依也。辨之于毫厘而使当其则者,德之凝也,治之实也。自天生之而皆诚,自人成之而不敢不明。故以知帝尧以上圣之聪明,而日取百物之情理,如奉严师,如事天祖,以文其‘文’,思其‘思’,恭其‘恭’,让其‘让’,成盛德,建大业焉。心无非物也,物无非心也。故其圣也,如天之无不覆帱,而‘俊德’、‘九族’、‘百姓’、‘黎民’、‘草木鸟兽’,咸受化焉。圣人之学,圣人之虑,归于一‘钦’。而‘钦’之为实,备万物于一已而已矣。其可诬哉!其可诬哉!”⑧在这一大段话中,王夫之对实心实学之内容有深切的说明。首先,王夫之认为,以圣人为代表的理想人格所顺承敬奉者,是天道诚体,而天道诚体实表现为众多的具体事物。此事物包罗至广,大到天地刚柔,小到飞潜动植,广博至利用厚生,切近至日用伦常,天地人三才无不在其中。如此广大的内容,如果皆兢业敬守,足以使人一生刚健自奋,追求不已而无暇逸豫。而若真能奉守此诚,则天地万物所具有的条理即心的内容,道聚于身,德润于行。人是奉天而行其神化者,不是其心空无一物,以虚静与空寂的本体为一的佛道中人。在王夫之看来,在俗世中的人,如果奉行佛教的“实相真如,一切皆空”,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而不恤,即坏乱利用厚生之物,灭弃天地之正道。王夫之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他以顺承天道,敬守伦常为立身之本,以刚健有为,经邦济世为人生理想,所以对儒家理想人格给予高度褒美,对与此人生理想相违背的学说都给予批评。此点在后文中还要展开。此处对佛教的批评,其矛头所向,其实在那些吸收佛家思想,主张“其心收敛,不容一物”的儒家学者。他的这一长段话,是有感于尹和靖的退守、消极,不言天道之诚而言其心本空之议论而发的。王夫之以此纠正某些儒家学者消极退守、无所作为之偏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在肯定刚健有为的人生理想的基础上,王夫之也对儒家中因主张存理去欲而贬抑事物本身,及因严于义利之辨而视“利”为洪水猛兽的偏蔽进行批评。在一些人看来,声色臭味是应该遏绝的,利是君子所羞言的。但王夫之根据其“践形”、“重生”的学说明白宣示:食、色等是礼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利是民生之来源。食色依礼,兴利以供民生之用,是儒者的不二之道。王夫之从实心生实学的根本立场出发,认为物本身并非有善恶,关键在用物者能否有正确的抉择,使得用物的原则与天道诚体吻合。符合天道诚体的用物,物是凝德之体,利是民生之实。出于天道诚体之“明”才能成就物。人未有与天道合一之实心,故未有合理用物之实学。圣王之用物,遵其实理,取物之“文思恭让”为己之文思恭让,故能成盛德,建大业。取物之理为己之理,故己心即物理,物理即己心。万物皆受诚体之化而各得其所。这是以人合天的最高境界。王夫之的以上诠解,吸收了《中庸》关于“诚明”的思想,特别重视“钦”字所代表的实心实学,将圣人功化的一切,皆视为“诚”结出的果实,强调“圣人之学,圣人之虑,归于一钦”。而所谓钦,说到底,即“备万物于一己”,顺承天道而诚于己的境界。此境界是成就盛德大业的基础。
王夫之提倡的修养功夫是《中庸》之“因明致诚,因诚致明,诚明两尽”。他说:“圣人之‘明’,则以‘钦’为之本也。‘钦’之所存而‘明’生,‘诚则明’也。‘明’之所照而必‘钦’,‘明则诚’也。‘诚’者实也:实有天命而不敢不畏,实有民彝而不敢不祇;无恶者实有其善,不敢不存也;至善者不见有恶,不敢不慎也。收视听,正肢体,谨言语,慎动作,整齐寅畏,而皆有天则存焉。则理随事著,而‘明’无以加,‘文思恭让’,无有不‘安’也。”⑨这是王夫之实心实学的最鲜明的宣示。“明”以“钦”为本是“诚则明”,则这个诚不仅是心的诚敬状态,而实际上就是与天道诚体为一的境界。有这种境界自然能产生符合善的价值的明。反过来说,符合善的价值的明必然是与天道诚体为一的境界的表现。诚则明、明则诚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诚的境界是实心,由诚派生的明是实学的基础。而畏天命、敬民彝、存善去恶,乃至收视听、正肢体、谨言语、慎事为,皆实学。实学出自实心,实心出自与天道为一之诚。这就是王夫之的实心实学。这一基本思想不仅表现在他的《尚书》诠释中,而且贯穿、渗透在他的全部著作中,他对佛道及阳明后学的批评,他的重建中国文化的构想,都出自这一基本思想。
王夫之对以上钦与明的说明,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于“安”的强调。《尚书》孔安国《传》谓,“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这一句,乃“言尧仿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当安者”⑩。而所谓当安者,孔颖达《疏》认为即《尧典》下文之“九族、百姓、万邦、黎民”(11)。王夫之则解释为,“安安”者心安所当安,即心以与天道为一为安。在上面引用的那段话中,王夫之指出,在诚明两尽之后,理随事著,文思恭让皆到,文明盛大,无以复加,此时心乃安。这里王夫之强调的,实际是合价值与合理则、善的动机与好的结果的统一。不符合价值理想,不出于善的动机,固然心不安;不符合理则,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心亦不安。这表明,与天道诚体为一的实心不仅是行为之前的构画者、设计者,而且是行为之后的反省者、监察者。在王夫之的诠释中,“安九族、安百姓、安万邦、安黎民”变成了“安心”,政治措施变成了价值理想,变成了行为原则。和《尚书》的古代解释者相比,王夫之从一个相对来说较为狭窄的领域跳出来,将“安安”诠释为一个实心所具有的功能,一个实学所必需的保障。这里王夫之强调实心的价值本体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二、对背离诚明原则的批评
王夫之确立了“明从诚出”,诚既是天道又是性体,文思恭让归根结底出于诚明之心的原则之后,又对背离以上原则所出现的各种现象进行了分析,归纳出四种弊病,他说:“凡此者,明于其所以,则安之而允安矣;不明其所以,将以为非物之必待,将以为非己之必胜,将以为唯己之所胜而蔑不安,将以为绝物之待而奚不可。不明者之害有四,而其归一也。”(12)这四种弊病,一是道家的自然主义,主张人不可干预自然事物;二是法家的法治主义,主张一决于法而放弃人文、道德之教化;三是过分的自我主义,见心不见理,夸大、滥用人的能动力量;四是佛家过分的封闭主义,见到人文的弊害而欲以绝去人为规避之。王夫之认为,这四种弊害都是由于不理解儒家诚明相生、诚明两尽的真义而产生的。其形式虽有四,其实质则一。对这四种弊病,王夫之逐一加以分析评论。
针对第一种弊病,王夫之说:“以为非物之必待者曰:物自治也,即其不治者犹治也。以‘文’治之而物琢,以‘思’治之而物滑,以‘恭’治之而物扰,以‘让’治之而物疑。夫物固自治,而且治之,是乱物也,则莫若绝圣而弃智。此无他,不明于物之必待也。物之必待者,物之安也。”(13)此中“待”,指本性不自足,须倚赖他物。“非物之必待”,指物不必待人引导、不必待人治理。王夫之认为,此种理论有见于“文思恭让”的不当之用带来的恶果而力图克服之,这是其优长之处。但由此认为物可自治;待人而治,必导致物之滑乱,却是走入另一偏向。从物的整体谐调着眼,物必待人而治。只有人加入治物的活动中,对物进行调剂、平衡,物才各循其轨而为一和谐之整体,才能更好地为人所用。物之滑乱是误用人为的结果而非人为的必有后果。他指出,物不待人而治论可能引致苟简之弊:“且夫物之自治者,固不治也。苟简以免一日之祸乱,而祸乱之所自生在是也。若夫不治者之犹治也,是其言也,为欺而已矣。明于其必待,而后圣人固曰:物自有之,待我先之而已矣。”(14)放弃人之治物,让物自生,似乎很俭约,合乎道家“治人事天莫若啬”、“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的原则。但祸乱恰生于此种俭约。物不待人而治之说,是自欺欺人。儒家的原则是,物虽自有,但须有人之引导、治理。正确运用的文思恭让,即出于诚明之体的文思恭让,可避免道家以上所指斥的恶果。
王夫之这里对道家自然主义的批评,与他在其他著作,如《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等中总结明亡教训,倡导刚健、主动、崇有的精神,对消极退守、无所作为所作的批评是一致的。这里要强调的是,王夫之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一个卓越的见解,即在文明的演进中,人与物,物与人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物是人存在、发展的环境和参照,人是物和谐共处、协同发展的助缘。在两者的互相依持中,王夫之虽然更强调人文的价值,强调人与天地参,强调合理地取自然物为人所用,因而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但在人类文明已经如此成熟,人与自然已经长期共生共长,人的文明成果中已经无法将人为与自然剥离的情形下,依然主张人非物之必待,是昧于事物之真实情况与发展理则的。这一点在下文对佛教的批评中将有更加深入的论说。以王夫之的以上卓识,反观在环保上某些学派的极端主张,是大有裨益的。(15)
王夫之批评的第二种弊病是“以为非己之必胜者”,即不相信人能认识天道和世事的规则,不相信人能根据道德原则作出正确的措置,故一律诉诸刑名法术等外在的力量。王夫之举其观点之概要说:“以为非己之必胜者曰:道不可尽,圣人弗尽;时不可一,圣人弗一。是故尧有不令之子,舜有不谐之弟,夏有不辑之观、扈,周有不若之商、奄。尧有不令之子,胡亥之淫,非始皇之失教也。舜有不谐之弟,大叔之叛,非郑庄之养恶也。夏有不辑之观、扈,藩镇之逆,非卢杞之奸也。周有不若之商、奄,七国之反,非晁错之激也。然则天下者,时势而已矣。乘其时,顺其势,或右武以绌‘文’,或立断以废‘思’,雄才可任而不必于‘恭’,盛气能争而何容多‘让’。是故操之以刑,画之以名,驱之以法,驭之以术,中主具臣守之而可制天下。”(16)此中典故甚多,为避免文繁,不拟一一详加解释,只取大意而已。此派理论认为,世事繁赜,作为本体的“道”不能解释穷尽;时势纷乱,一术亦不能遍应。如此,则圣人就以不能穷尽不能遍应来看待它。尧舜圣人,却有不肖之子弟;夏商强盛,却有不受约束之诸侯。汉时七国之反,非仅以晁错削夺诸侯之议激起;唐之藩镇割据,亦非朝臣卢杞之奸恶造成。由此可知,天下事非有一定之理则,常在人控制之外。欲功成事遂,唯在乘时顺势。因此,文思恭让不可恃任。治理国家之利器,在刑名法术等外在的工具。执刑名法术,平庸之人亦可治国;而“文”、“思”、“恭”、“让”,非才能殊特而境界高迈之人不能。王夫之指出,以上议论都是无视人的精神力量,徒恃外在的致治之具的肤浅见解,它只看到人无法掌控时势的发展,没有看到人由体证天道之诚明而具有的道德力对事件的持续影响。正是由于时势的不可掌控性,因而更须突显天道诚体的轨则性、恒常性;正是由于人处理不断变化的外在事物需要不拘一格、灵活机动,因而更须突显内在的道德力的持久性、稳定性。也就是说,在时势无定的境遇中,最贵重的是人内在的定力。“文、思、恭、让”是人的定力最主要的内容。这是王夫之针对“非己之必胜”论提出的对治之方。王夫之论证说:“尧有不令之子而不争,舜有不谐之弟而不弑,夏有不辑之观、扈而不败,周有不若之商、奄而不危。是故质立而‘文’必生,物感而‘思’必起,退而自念,则自作其‘恭’;进而交物,则不容不‘让’。内取之身,外取之物,因其自然之成,能以坐消篡弑危亡之祸。明乎此,则何为其不胜邪!”(17)在危难厄逆中,不沮丧,不躁妄,相信自己内蕴的力量,以理则驾驭外在的事变。此时“文思恭让”有了极为实际的作用:立基于质朴而“文”必生起,应物而感时必加以慎“思”,处己必敬谨而“恭”,交物必自抑而“让”。这是转危为安的不二法门。王夫之在明清之际的战乱流离中观天运循环所得到的这个睿识,不仅对自己处逆境起到了训诫的作用,而且对遭受亡国之残祸烈毒的广大士人也是一种警示。
王夫之批评的第三种弊病是“以为唯己之所胜而无不安”,即认为人最殊胜、最特出,人的力量最大,可以离天而言人,离理而言心。演至末流,逞一己之妄,以为自己心中流出者即无渗漏,即可恃任。王夫之述此派理论说:“以为唯己之所胜而无不安者曰:‘文’日生也,‘思’日益也,‘恭’有权也,‘让’有机也。圣人之所为,天无与授,地无与制,前古无与诏,天下无与谋。可以为而为之,圣人已为矣。可以为而为之,我亦为也。其未为者,彼之未为而非不可为也。非不可为,而我可以为也。于是穷亡实之‘文’而‘文’淫,驰不度之‘思’而‘思’荒,貌以‘恭’而‘恭’以欺,饰以‘让’而‘让’以贼。”(18)这是说,在此派看来,文饰日益丰多,思致日益深密,恭敬是权变的工具,谦让是机诈的乘舆。故圣人之所为,非以天为范导,非以理为制衡,非以前史为昭鉴,非以民意为参照,而全凭一心之造作。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无用之虚文不胜其多,而出于诚明之文日益蚀损;不情之思逞其淫威,而中矩中度之思日益减少;貌似恭敬,而真正的恭敬被欺侮;饰以礼让,而真正的礼让被戕害。于是妄逞大欲者借“文思恭让”以售其奸:“蔡京以丰亨豫大为‘文’,曹叡以辨察苛细为‘思’,汉成以穆皇文致其慆淫,燕哙以禅授陆沉其宗社。此无他,不明于唯己胜者之非可安也。”(19)此中蔡京事指以“丰亨豫大”为倡导而华侈宫殿、都城,大量搜罗民间奇花异石,致以“花石纲”激起民怨,而国为之削。曹叡事,《魏书》谓其“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20),又谓其“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时明帝喜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致大辟者”(21)。汉成帝事,《汉书》谓:“成帝善修容仪,临朝渊默,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然湛于酒色。”(22)燕王哙事,指燕王将君位让于燕之相国子之,致军将不服,引起内乱,导致齐国干涉,而燕王亦国亡身弑。王夫之认为,此数人之失皆过信“唯己之所胜”,不揆天理,不察物情,不考前史,不听众论,因而误用文思恭让所致。他指出:“天无与授,而授之以宜其民,地无与制,而制之以当其物,前古无与诏,而考之也必其不谬;天下无与谋,而徵之者必其咸服。明于其故,必如寒裘而夏葛也。臧唯二耳,而白马固马也。”(23)这里表达出一个很简单但又容易为人所轻忽的思想,这就是,不可离天而言人,不可离理而言心;史鉴不可不借,民意不可不听。而天地以宜民、当物诏示于人,前史、世论所当采当从者,亦不过宜民、当物。宜民、当物即文思恭让所欲达成的理想。以为“唯己之所胜”,必导致败亡。这是王夫之在天人关系上的重要见解。
还有一点,王夫之在对以上所举弊病的批评中,表达了对心学的极端厌恶。王夫之在狭义上说是程朱学者,虽对二程、朱熹不能说绝无微词,但基本持肯定态度,他所着力批评者,在陆王。在其著作中,王夫之多处对心学大张挞伐,他甚至认为,明亡的责任,相当程度上要由王门后学师心自用、荡灭礼法造成的学风、士风的败坏来负。在《尚书引义》对“诚明”及“文思恭让”的阐发中,王夫之由对浮明的批评,连带批评陆王:“张子韶、陆子静、王伯安窃浮屠之邪见以乱圣学。为其徒者,弗妨以其耽酒嗜色渔利赖宠之身,荡闲蔑耻,而自矜妙悟。呜呼!求‘明’之害,尤烈于不‘明’,亦至此哉!”(24)此中不仅批评心学,连带对佛教一起批评。心学到底是否坏乱圣学,心学是否简单地窃取佛教而成,佛教是否邪见,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问题,此处不能详论。这里要说的是,王夫之对心学的批评,如果落实在“唯己之所胜”上,他实际的批评对象是泰州、龙溪。而泰州、龙溪最受王夫之诟病的是直任本体,轻弃功夫,自认开口即得本心,实则夹带私欲。结果是“弗妨以耽酒嗜色渔利赖宠之身,荡闲蔑恥”。泰州、龙溪自矜妙悟,可谓聪明特达之人,但其究不免于为害家、国。在王夫之看来,此皆过信“唯己之所胜”,明而无诚所致。
王夫之所批评的第四种弊病是“以为绝物之待而无不可”,即弃绝外物,独任心空。这实际上是指佛教。王夫之举此派理论说:“以为绝物之待而无不可者曰:物非待我也,我见为待而物遂待也。执我以为物之待而我碍,执物以为待我而物亦碍。徇物之华,‘文’以生妄;逐物之变,‘思’以益迷;欲以示威于物,‘恭’以增憍;欲以干誉于物,‘让’以导欲。欲四者之病不生,则莫若绝待。内绝待乎己,外绝待乎物,绝己绝物,而色相以捐。寂光之照,无有不‘文’也;参证之悟,无所容‘思’也;行住坐卧,如如不动,亦‘恭’也;货财妻子,喜舍不吝,亦‘让’也。乃以废人伦,坏物理,握顽虚,蹈死趣,而曰吾以安于所安也。”(25)王夫之指出,此派认为从外物与人的本性上说,物不待我,我亦不待物,是人之识见以为物待我,遂以此识见对待外物,执为常情,由此形成了物待我、我亦待物的情形。有此执著,物我两碍。须以佛教所谓真识照破此情迷,还物我两忘之本来面目。此情不破,逐物不返。若就文思恭让四者说,则生迷生妄,长欲长骄。欲绝此病,莫若破物待之执。破物待之执则内外两忘,唯余空无之性地。此时寂光之照是“文”,参证之悟是“思”,行住不动是“恭”,喜舍不吝是“让”。佛教虽与儒者之学大异,但文思恭让亦非无有。王夫之对佛教之不逐物欲、不徇荣华等虽亦赞赏其苦心,肯定其功用,但从出世入世、绝物待物、遵依彝伦超出彝伦这些大的方面着眼,对佛教持批评态度。特别是从儒者积极入世、刚健有为、奉守诚明之道之文思恭让这一点说,他是批评佛家的。
不仅物不可绝,而且在王夫之这里,物与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中有物,物中有人,人与物是宇宙这个整体中互相依赖的两个方面。王夫之说:“且夫物之不可绝也,以已有物;物之不容绝也,以物有己。已有物而绝物,则内戕于己,物有己而绝己,则外贼乎物。物我交受其戕贼,而害乃极于天下。”(26)王夫之说人与物不能相绝,不仅是从物为人提供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这一点着眼,即所谓“一眠一食,而皆与物俱;一动一言,而必依物起”(27),更是从人的文明获得,自然和人文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融合共生这一点着眼。因为不仅从理想上说,人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人的“致中和”可以使“天地位,万物育”,而且就人的活动的现实性来说,自然物每一时刻都在人化,就像人每一时刻都在物化一样。物是寄寓人的理想,展示人的创造、显现人的性质、特点最充分的地方。所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就不是人要追求的精神境界,而是一个现实的存在状况。这一点王夫之此处没有明白地昭示,但他的著作中透出的一贯的人文主义、一贯的理想主义,包含了这些意思在内。
由于重视物与人的一体性、不可分割性,自然地引出王夫之对这种一体性中人自己当负的责任的重视。他告诫人们,如果损害了物与人共生的平衡性,物对人的报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物对人的一切报复,归根结底都是人自己引致的。避免这种报复的唯一办法是补足物使之各得其所,恢复物与人共生的平衡性。他说:“不能充其绝而欲绝之,物且前却而困己,己且龃龉而自困。则是害由己作,而旋报于己也。故圣人因其所待而必授之:朴者授之以‘文’,率者授之以‘思’,玩者授之以‘恭’,亢者授之以‘让’。泰然各得其安而无所困,则己真有其可,而非其无不可,固知无不可者之必不可矣。”(28)这里王夫之阐述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承认物之有待是为了彰显人参与自然过程的必要性,彰显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的一体性。人对自然过程的参与是对此一体性补助其所缺。上面曾说到物对人的补足,这里是说人对物的补足。物与人在这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一体性中双方皆趋于完满。这才是《中庸》所说“赞天地之化育”的完整意义。此中的“朴者”、“率者”、“玩者”、“亢者”不仅指人类中的朴直、粗率、玩世不恭和骄横自高,同时也指物的不尽如人意的种种缺陷。人补之以文思恭让而使物谐调、均衡,因此而各得其安。人在与物的谐调与均衡中看到自己创造力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人的有限性,看到人非无所不能,从而抑制其虚骄自大。王夫之的这一观点有助于人在发扬人文主义,积极参与天地之化育的过程中抑制由于贪欲的膨胀导致的对人与自然的谐调和均衡的破坏。这就是“固知无不可者之必不可矣”一句包含的深意。
王夫之在对上述四种弊病批评之后,总结了它们产生的原因,认为总根源在于“无其明”。而“无其明”在于无其诚。他把不取资于诚的润沃而仅恃聪明才辨的明叫“浮明”。终其一生,王夫之指斥最为痛切、剖剥最为犀利的就是浮明。这是他有见于中国士人的突出弱点,参照儒家强调义利之辨、严于君子小人之分的特点有感而发的。在对《尚书》的阐发中,王夫之对“浮明”的批评仍然很尖利,他说:“‘浮明’者,道之大贼也。其丽于‘文’,则亦集形声以炫其荣华也。其丽于‘思’,则亦穷纤曲以测夫幽隐也。以言乎‘恭’,则亦辨贞淫于末节以致戒也。以言乎‘让’,则亦揣物情之逆顺以弗侮也。恍惚之间,若有见焉;窅寂之中,若有闻焉;介然之几,若有觉焉。高而亢之,登于九天;下而沉之,入于九渊;言之而不穷,引之而愈出。乃以奡岸于世曰:予既已知之矣。而于道之诚然者,相似以相离,相离以相毁。扬雄、关朗、王弼、何晏、韩愈、苏轼之徒,日猖狂于天下。”(29)对“浮明”,王夫之首先重言申明其为道之大害。其所以害道,就在于其以似是之非,背离了道之根本——诚,又以其貌似合道,毁道于无形。因具浮明者,皆聪明才辨之人,见闻博赡之人,敏利巧慧之人,故多有所见、有所闻、有所觉,世人亦多信从之、拥戴之,故难以察觉其背道处。王夫之以上所举的这几人,皆中国历史上不世出的学问家,所举荣华之文、幽隐之思、贞淫之辨、物情之揣,此数人皆当之而无愧,足为后世称美。但王夫之所着眼者,在有否体道之诚,有否出于诚之“真明”。王夫之在这里虽未明确指出此数人可指摘者究在何处,但综观王夫之其他地方的论说,可知他对扬雄的指摘主要在其《剧秦美新》文之作,逢迎当道,丧失操守。虽能“辨贞淫之末节”,而不能识儒者之大体。对关朗之指摘,在其以象数学解《易》,明布算于毫忽,而不识《易》中所包含的天人之际与道德教训。即能“穷纤曲以测夫幽隐”而不识天道性命之大。对扬雄模拟《周易》而作之《太玄》,批评亦在此(30)。对王弼、何晏之指摘,在其以“以无为本”、“得意忘言,得言忘象”等观念解《老》解《易》,巧慧辩给,但引发了魏晋时期虚浮狂放的学风与士风。即“能揣物情之顺逆以弗侮”,但抛却天道诚明。至于对韩愈、苏轼的批评,则主要在视其为“文人”而非儒者,指摘其文采可观而品行有亏。即能“集形声以炫其荣华”而德行不足道。王夫之与顾炎武一样,都对明代后期的所谓“文人”极其不屑,以为此等人以文字、书画为游戏,无与于身心性命之学,憨憨醉饱,浮浪一生。故服膺北宋刘挚“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不足观矣”之语(31)。此亦崇实黜虚、崇质黜文,力戒浮明之义。
综合王夫之以上对诚明关系的阐发,对背离诚明所产生的弊病的抉发与批评,可以看出,王夫之主张的百行生于明,明生于诚,诚明与道体一而不二,诚明之境界与万物即体即用等思想,是他的“实心实学”的根本之点,这一点阐发于《尚书》开篇之《尧典》,而实贯穿于他的整个《尚书》诠释中。他的天人、身心、性情、理势、名实、治乱诸论,他对明朝史事的评说,他对佛老的批评,乃至他的经学、史学、文学,他对明亡教训的总结、对理想的中国文化的重建,皆立基于这一原则之上,皆从这一理论中转出。王夫之以诚明为基础的“实心实学”,其义大矣哉!
收稿日期:2008-10-10
注释:
①李学勤主编《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②王夫之:《尚书引义·尧典一》,《船山全书》第二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37页。
③《论语·泰伯》:“恭而无礼则劳。”
④《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37页。
⑤《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40页。
⑥《船山全书》第一册,第52-53页。
⑦《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40页。
⑧《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41-242页。
⑨《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41页。
⑩《尚书正义》,第25页。
(11)《尚书正义》,第25页。
(12)《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37页。
(13)《船山全书》第二册,第137-138页。
(14)《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38页。
(15)参见拙著:《心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151页。
(16)《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38页。
(17)《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38页。
(18)《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39页。
(19)《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39页。
(20)《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第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6页。
(21)《三国志》卷三,第86页。
(22)《汉书》卷十,《成帝纪第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0页。
(23)《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39页。
(24)《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41页。
(25)《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39页。
(26)《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39页。
(27)《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40页。
(28)《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40页。
(29)《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41页。
(30)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649页。
(31)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文人之多》,及《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