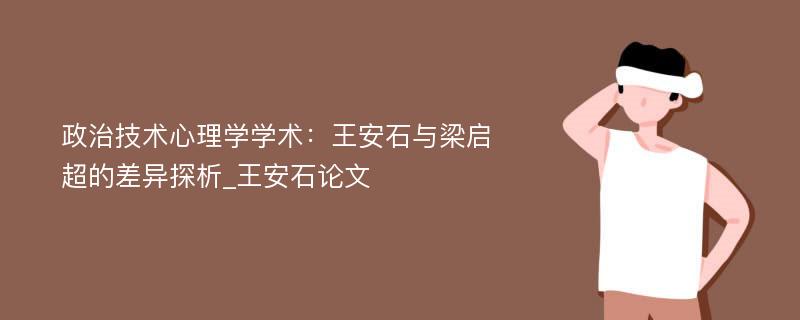
政术 心术 学术——梁启超、严复评王安石之歧异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歧异论文,心术论文,王安石论文,学术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09-12-16
在清末民初的文化舞台上有两位巨子,一位是梁启超,另一位是严复。章士钊晚年回忆说:“从晚清以至民初,二三十年间,以文字摅写政治,跳荡于文坛,力挈天下而趋者,唯严幾道与梁任公二人……几道规模桐城,字栉句比,略带泰西文律……使人望而生畏;任公有陶渊明之风,于政于学,皆不求甚解而止,行文信笔所之,以情感人,使读者喜而易近,因之天下从风而靡。”[1]2118章士钊的回顾给我们探察其时的人文生态以重要启示。我们此前曾略感梁、严两人心思门径风格各异,应予细勘,因有妄论梁、严评议卢梭、老子两篇小文[2-3];今读章著,更觉两人关于王安石的评议也有比较阐发之必要。从某种程度上说,梁、严评议王安石,较之两人对待卢梭、老子的态度,可比之处似乎更多。例如,两人恰巧都在1908年对王有了特别的关注,两人对王的政术、心术和学术等都有深入的研讨。
以往学界研究王安石变法的论著大都要论及梁启超撰写《王荆公》一事,更有学者以专文探讨,不过这些探讨多着眼于梁在内中所寄托的政治思想及其对“新史学”的开创意义,而对梁1908年刊发此书前后之语境和心态则缺少深究,因而对内中所表达的政治思想就不能有更准确的把握①。可以说,关于严复评议王安石,特别是将梁、严评议王安石作对比的研讨,迄今仍寡②。因此,本文拟就此问题略为置喙,以待高明。
一、梁、严评王安石之语境与心态
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载:1908年,“先生著《王荆公》一书成,该书凡二十二章,主旨在发挥王荆公的政术,所以对于王氏所创新法的内容和得失,讨论极详,并且往往以近世欧美的政治比较之”③。梁在《王荆公·自序》中说:“自余初知学,即服膺王荆公。欲为作传也有年,牵于他业未克就。顷修国史至宋代,欲考熙丰新法之真相,穷极其原因结果,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非欲为过去历史翻一场公案,凡以示伟人之模范。”[4]1这表明:其一,梁素来服膺王安石,其性情志向与王多有耦合,并非全由一时兴起或时局所需而著此书;其二,梁著《王荆公》虽有翻案的嫌疑,但他意不在此,而主要是要“示伟人之模范”。
上述第一点确乎不无道理。1905年前后,清廷重臣张之洞在注解其《学术》诗时即写道:“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5]10559康有为也曾创万木草堂招徒讲学,在《万木草堂口说》中就有“讲王介甫百年无事札子”等内容。康称:“王安石始用雇役,至今赖之,千年功德。保甲亦其遗法。”[6]245作为康门高足,梁对王安石的看法自然不可能不受其影响。1896年8月,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论科举》称:“荆公经义取士,虽未敢谓为善制,而合科举于学校,则千古之伟论也。”1901年,梁撰《李鸿章》一书,将李与王安石相提并论,但他更理解和钦佩的是王。他说:“安石得君既专,其布划之兢兢于民事,局面宏远,有过于鸿章者。”④与前面不同的是,这里所强调的不是其变法的具体措施,而是识见规模、得君既专、兢于民事和客观阻力等,可见梁所重视的是作为大政治家的王安石所特有的主观素质与客观遭际,也即前文所述的第二点——“示伟人之模范”。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燃起了新的希望。谋开党禁、欲归国主政、勤著述以糊口解困,大致可以概括梁这一时期的心境和情境。梁在《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中说:“谓吾不欲开党禁耶,此违心之言也,吾固日夜望之。以私情言……游子思归,情安能免。以公义言,则吾固日日思有所以自效于祖国也。”[4]56除了政治上的秘密活动外,要为开党禁造舆论,动用历史资源自然是不可少的,因此,梁有必要为王安石洗冤,梁也称《王荆公》是“洗冤录”。很显然,洗冤是为开党禁服务的,但梁的最大愿望并非在此,而在于归国主政。他说:“吾之能归国与否,此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强致也。”“吾数年来早有一宣言在此矣:若梁某某者,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也。然苟非能实行吾政见,则亦终身决不做国务大臣者也。”[4]561909年,梁启超在与其弟的通信中也称:“兄年来于政治问题研究愈多,益信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7]5979
梁既然以为救中国非他不可,在归国前就必须有所布置,除组织上的布置外,也需要舆论准备,需要借历史来树先进、立模范、增见识,借历史伟人来宣扬改革者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正是这样,王安石的改革精神契合了梁当时的内心渴望。
如果说“谋开党禁”与“归国主政”已为学界有所论及的话,那么梁撰《王荆公》时的另一处境则绝少有人提及,即当时梁氏所承受的经济上的沉重压力,迫其不得不勤于著述,卖文解困。这样一来,为尽速完稿,招徕读者,信笔之言,就势所难免了。
很有意思的是,与梁撰《王荆公》同一年,严复对王安石也给予了非同寻常的关注。据载:1908年8月26日,严复由上海至天津,“旅次,批阅《王荆公诗》,先后加批注200余条、和诗30余首,如《和荆公》、《和〈适意〉》、《和〈愍儒坑〉》等”⑤。严复这时是否读过《王荆公》,目前还难以断定,不过,既然这两位知识界巨子在同一年将各自笔锋指向同一目标,这其中必定有值得玩味之处。早在多年前,严复就在《原强》(1895)中称:“王介甫之变法,如青苗,如保马,如雇役,皆非其法之不良、其意之不美也,而昧者见其蔽而訾其法,故其心不服,因而党论纷淆,至于亡国而后已。而后世遂鳃鳃然,举以变法为戒,其亦不达于理矣。”[8]一,13如果仅就此看来,严复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看法可以说与梁启超确是差别不大,但问题是,严复对王安石的频繁评议为何不出在别时,而偏偏是集中于1908年后。在学界已有的论述中,几乎一致认为这些评议与和诗足以表明严对王的崇拜比梁有过之而无不及。曾克耑在为《王荆公诗评语》所作序中便说:“自新会梁氏为之传,而其学以显”,“独侯官严氏,以通儒雄笔,通贯中西学,既评释、老、庄以通其邮,复以其余力手公诗而评骘之”;“此老……圈识之不足则评赞之,评赞之不足,乃复取其谈禅论古之作,一一而追和之,魂游魄恋,上下千古”[8]1178-1179。
此说大可商榷。若说梁著《王荆公》确有翻案之意,那么对严复来说,则未必。至少严复当时的处境就与梁大不相同。戊戌政变后,严复照样译书执教,衣食无忧,其忧虑多为官民社会的蒙昧泄沓。他对变法的夭折虽也痛心不已,但正如章士钊所说,严复作文绝不像梁启超那样感情浓烈,而只是历史主义地论理说事,令人望而生畏。如果他想借此为戊戌政变翻案的话,也不必等到1908年来附和于梁之后。再者,严复当时也完全不存在梁著《王荆公》时那种谋开党禁、归国主政的心境及卖文糊口的处境。他当时不仅在学界声誉崇隆,而且在封疆大吏那里也常受礼遇。据载:1907年4月22日,严复由南京抵上海,“以徇陶斋尚书之命,为之整顿吴松复旦公学”⑥[9]302。1908年3月20日夜,郑孝胥应云帅⑦之约,“座有严又陵等”[9]318。同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聘严为“新政顾问官”,月薪三百,车马费两百[9]324。这一待遇显然相当可观,严接受了,于是8月26日由沪抵津。正是在此途中,严复开始点评王安石诗句。试问:此时的境遇能激起严复为王安石变法翻案的愿望吗?
梁启超素以管子、商鞅、王安石自喻,以为只要能归国主政,国家很快就有望振作起来。严复则不然。首先,他绝无梁那种梦寐以求争当国务大臣的雄心,当然这并非说严复就毫无“为王者师”之意。1907年7月14日,英敛之见“严又陵写八言联一付,词云:‘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9]311,此联足见严氏襟怀。但总的来说,严复的志趣主要还是“立言”,至于“立德、立功”,非他所求。严复不指望在政治上有较大展布,除志趣性格外,也和他洞悉清廷实情有关。1907年10月1日,严到学部处理相关事宜,19日与夫人朱明丽书言:“自初三日考事毕后,无日不是应酬,脑满肠肥,极为讨厌”。“吾看今时做官,真是心灰意懒也。”[9]3141910年2月3日,在与何纫兰书中,他再次强调:“至于升官,吾视若浮云久矣。”[8]841这些言语表明,严复显然并无攀高主政的雄心。
其次,严复多年沉湎于烟瘾,身体病弱,此时年过半百,精力远不如三十多岁的梁那么旺盛。1908年5月,严复自叹“以望六之年,精神苶短,加以气体素羸,风雨往来,肺喘时作”[9]321。可见,无论是主观的精神条件,还是客观的身体条件,都使严复自甘于学者“立言”的地位,没有雄心和精力去施行宏伟的治国方案。既然他根本就未想在政治上还要大干一番,那么,他与急欲在政治上大干一番的梁启超对曾大干一番的王安石的评议会一样吗?
二、梁、严评王安石政术之同异
梁著《王荆公》深入地讨论了“荆公之政术”、“荆公之学术”,可见“政术”、“学术”为其考察基点。《续资治通鉴》记王安石“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可见王安石当变法之初即注重“择术”,此处偏重于“政术”。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10]333-334。法尧舜,意在倡导“天下为公”,属心术;所谓至简而不烦、至易而不难者,当属学术。袁枚言:“荆公《上仁宗书》,通识治体,几乎王佐之才。何以新法一行,天下大病?读其《度支厅壁记》,而后叹其心术之谬也。”[11]1甘鹏云也说,唐代“专以《正义》一家之说齐天下,宋亦同病。故苏轼尝病王荆公以其学术同天下”[12]11。袁、甘等人的意见尽管可以商榷,但至少表明:清人从“心术”、“学术”的角度来考评王安石是常事。因此,依据历史情境和学术流脉来考察梁、严对王的评议,应是可行的。
先说政术。梁启超认为,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位大政治家之一,管仲、子产、商君、诸葛亮等,规模都不及荆公之宏远[13]163;他推行的新政,虽不能俱谓之成,但绝不能俱谓之败,“为救之计,利率逾于病也”[13]241。特别是他主张依法治国,重视经济手段,兴教育、排科举、倡修武,这类思想有放之古今中外而皆准的意义。王安石为盖世英杰,却一直蒙天下之诟,可见国人素来苟且,不恤国事,遂使千年如长夜。要尽早结束这漫漫长夜,就应当弘扬王安石的改革创新精神。
梁启超对王安石新政以赞誉式肯定为主,辅之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多抱同情之理解或强调外在阻力的态度。如对“青苗法”,梁说:“荆公既欲实施此法,然行之不可以无资本也。由国库拨给资本,力又有所不逮也。适有常平、广惠仓者,诸路诸州县莫不有之,而其所储,实弃置于无用之地,公乃变无用为有用,而利用之为资本,其用意之周详,其眼光之锐敏,至可佩也。”[13]171“保甲法体大思精,为公一生最用力之事业,其警察的作用,可谓有利而无病,其成效亦已章章可睹。”[13]242-243在梁看来,王安石新法之中,唯有“市易法”,无论得人与否,都不可行[13]180。“银行之性质,最不宜于兼营其他商务;而普通商业,又最忌以抵当而贷出其资本。今市易法乃兼此两种矛盾之营业,有两败俱伤耳。”[13]180-181
梁对王安石“青苗法”等新法的肯定与对“市易法”的否定,源于其治国理念中的干涉论与社会主义尚早论。他认为:大政治家都不外整齐划一其国民,如此既可充国力于内,又可扬国威于外,因此,就不能不行干涉之道。在当今世界,以放任不以干涉而能为治的,只有英美等两三个国家,然而它们也都曾施行过莫大的干涉才有今日的“放任”。在梁的政治理论构架中,“放任”、“威劫”、“干涉”等紧密关联于一体。“放任既久则有乱,乱则有亡,亡则有兴,有兴则有威劫,威劫既倦,则返于放任,如是迭为循环,若一丘之貉焉。”要跳出这个循环的魔障,只有在威劫与放任之间执中,走干涉一途。但在古代,对于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往往“利于洸洸之武夫以为舞台,利于碌碌之余子以为藏身数,而最不利于发强刚毅文理密察之大政治家”。梁认为,无论三代以前的政治家,还是欧洲现今的立宪国家,抑或王安石最初的试验,都是在小范围内采取干涉政策,易于收效。若在秦汉以降中国这样的大国,干涉政策难以推行,新法效果不佳也情有可原,“不足为荆公罪也”[13]164-191。
梁的意思很明了:干涉政策是突破由“放任—威劫—放任”这一恶性循环的必经之途,此途见效于古代小国,而难以见效于专制大国;但在交通发达的现代立宪国家,国不论大小,都是行得通的。因此,王氏的干涉政治有其现代意义。
在梁的理论框架中,除“放任—干涉—威劫”之外,实际上还有另一序列结构,即“放任—干涉—社会主义”。他认为王安石的“干涉”不是要滑向“威劫”,而是有滑向“社会主义”之势。梁的策略是肯定其“干涉”(至少在理论上),否定其趋向“社会主义”的因素。梁称:“其青苗、均输、市易诸法,皆本此意也。此义也,近数十年来乃大盛于欧美两洲,命之曰社会主义,其说以国家为大地主、为大资本家、为大企业家,而人民不得有私财……夫以欧美今日犹未能致者,而荆公乃欲于数百年前之中国致之,其何能淑?”[13]167他批评王的所谓“社会主义”弊端有三:一是国家垄断,不能竞争,缺乏活力;二是执掌国家机关的人甚难其选,集权既重,弊害易滋,盗臣自肥,腐败难以遏制;三是欧美各立宪国家倡行社会主义“犹以为难,而况在专制之代乎”[13]167?
清理上述思路后,再看严的评议就容易得其头绪了。严复对王安石的评议始见于1895年《原强》篇,《原强修订稿》中又有所增补。1908年评点《王荆公诗》后,他又评点了《古文辞类纂》,内含王安石文章若干。直到1917年,严复仍有此类文字。总的看来,严复对王安石的评议是前后一贯的,有肯定亦有否定。前文已知梁启超对王的政术也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那么梁、严之间的评议又有何同异呢?
从肯定的方面看,严复虽然不像梁启超那样崇拜王安石,但对其新法的合理性、法治思想、人才思想等都与梁有相同或相近的意见。法治思想方面,严在王《进戒疏》批语中就说:“秦以后,法度思想最多者,介甫一人而已。”[8]1213[14]661-662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时,在第32条按语中写道:“王荆公变法,欲士大夫读律,此与理财,皆为知治之要者。蜀党群起攻之,皆似是实非之谈。”对王安石的人才思想,严复也予以高度肯定。严复对其变法的肯定,还表现在对待变法成绩的态度上。1911年9月,严复批阅《王荆公诗》卷首本传时写道:“且以余观之,新法之害,必不如攻者所言之已甚也;果如攻者言,则他日绍述之说必无从起。”[8]1150-11511917年,严复又在一个小账本上记道:“荆公变法,一时贤者多与立异。然实不能一概抹杀,尽以为非。即如保甲,于古则有……青苗法,苏格兰常行之,民便而以成业者不可胜计。”[15]182
严复对王氏政术的批评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围绕自由问题;二是指导政治的思想方法问题。关于自由问题,梁批评王安石的地方几乎全集中于“市易法”,严的批评则不限于“市易法”。严在《原强修订稿》中指出:“管、商变法而行,介甫变法而蔽,在其时之风俗人心与其法之宜不宜而已矣。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8]26-27严复重视的是利民政治必须以民之自利、自由、自治为基础,王安石变法没有以此为准,所以虽欲利民,事与愿违。严复于1900年译完《原富》一书时,其按语第64条写道:“盖财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绝束缚拘滞而后可。国家每一宽贷,民力即一恢张,而其致力之宜,则自与其所遭之外境相剂。”“惜乎吾不能起荆公辈于九原,一与之深论斯事也。千古相臣,知财计为国之大命,而有意于理财养民者,荆公一人而已。其法虽病,然事难助寡使然。”[8]888可见,严复评议王安石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思想是:肯定其变法的动机,否定其违背自由原则的具体政策。
关于第二点,严复的基本看法是:王安石指导变法的理念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这种主观色彩源于某些理想成分,而后者与历史潮流是相违背的⑧。早在《原强》中严复就认为,王安石变法“其浸淫驯致大乱者,坐不知其时之风俗人心不足以行其政故也”[8]13。1911年9月,严复批阅《王荆公诗》卷首本传,对其变法为何出现如此后果进一步思考。他说这一教训最值得后人深思,因为王安石本人的经术、志愿、文章、节行都深得各方激赏;他又得到皇帝的特别信任,这个皇帝又有励精图治之诚;当时国家财赋未空、人才极盛;王安石大权在握,所推行的大都是善政,何以推行时那么难,效果那么有限?经过深思之后严复得出结论:“荆公之大蔽二:一不知政之宜于一郡一州者,不必宜于天下,犹之今日之法,其宜于甲国者,不必宜于乙国也;一不知人之攻我而立异者,不必皆奸人,而其助我而和同者,亦不必皆吾利。微论吾所重者非也……至于学术不同,信守互异,由是愤好之趣,烦然大殊。”“相时而后可,得人而后行,徒自信吾道而任众人之汹汹,吾未见其能济也。”[8]1150-1151“徒自信吾道”,这可视为严复批评王安石政术的基本结论。“徒自信吾道”往往使美好的愿望招致不良后果,严复要再三强调的即在于此。
很明显,严复是要借此教训来告诫当时的政治改革家,不能从理想观念出发,也不能迷信外国的模式方案;国家政治理当变革,但切忌轻举妄动,而应分析具体情况,制定可行的方案,推行渐进的改革。严复在总评王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时又对此作了精彩阐述:“执此篇之言以勘今世诸文明国之所为,则其用意、操术之异众矣。盖此篇所谓陶冶人才者,凡以为国家之用而已,凡以为人主之所取任而已。而今世文明国之所为不然。彼谓人道有宜完之分量,而人群以相生养而存。非教则无以合群,非学则无以完为人之量。是故教育者,欲人人知职分之所当为、性分之所固有已耳,非必拔植其躬以为人才、以为国家所官使,而修政临人也。”“国诚不可以无士,而无农商工贾焉,亦未见其能国也……然则一国之民既莫不待教矣,而养之、取之、任之者又谁属也?”“唯中国以专制为人群唯一无二之治体,其所以为教化者,遂与今日文明之治无所往而恰合。”“呜呼,可忧也已!”[8]1210-1211读完严复这段按语,再回想梁启超对王氏的崇拜心态,则梁、严评二人之差异已显露无遗。
三、梁、严评王安石心术之同异
所谓心术,意涵较微妙,难以确切界定,但大致是指道德观、价值观、襟怀视野之类。管子在《管子·七法》中指出:“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梁、严评议王安石,虽很少用“心术”一词,但涉及心术的内容不少。最值得注意的是,梁论及王安石之心术,称颂褒扬无以复加,而极少有批评;严论及王安石心术,有褒有贬,鲜加藻饰。
梁启超打心眼里崇拜王之人格,称“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纫之壁”[13]101;“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⑨;“体大思精,可以为立法家之模范”[13]184;“若其学识之精卓,规模之宏远,宅心之慈仁,则真千古而无两也”[13]167;“公之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以富其民而致天下于治”[13]166。并指出:“贫富不均之问题,实为数千年来万国所共苦而卒未能解决之一宿题。而欲解决之,则非国家振其枢焉而不可得也。其圆满之解决法,则如吾国古代之所谓井田,如泰西近世所谓社会主义,使人民不得有私财是也。未能圆满而思其次,则国家设贷貣之机关而自当其冲,使豪右居奇之技无所得施,则荆公所计划者是也。”[13]170“夫荆公创法立制,无一不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其不可与新莽同年而语,固不待辩。而末学肤受之辈,或见不及此,则盖取其结果而比较之。”[13]243类似这样的话在梁著《王荆公》中不胜枚举,列此足以证梁对王安石心术确已认同。那么严复呢?他又是怎样评议王安石心术的呢?
笔者将严复评议王安石之语与心术相关者一一辑录,计得14条,其中属正面肯定者6条,属负面批评者8条。两相权衡,大抵可约略窥出严氏对其心术的认同程度。就正面肯定一端来说,第一,严复肯定王安石变法“意非不美也”,虽然其实效不佳,反弹甚大以至于亡宋,此其故可深长思也[8]27。这是对其动机和出发点的基本肯定。第二,肯定王的卓识。严复批阅王安石《读汉书》诗时评曰:“此意真无人道过,盖前人只说小人误国,而不知君子之可以迷邦也。于此等诗最见此老识力,涑水、眉山岂能望其肩背?”[8]1167司马光、苏东坡等均系当朝重臣名流,在功业、文章等方面都多所建树,但仍不足以望其项背。这就不难表明,严复对其识见、格局是相当推崇的。第三,对王安石诗中“信诚”的赞同。严复说:“此是不朽语,今日又大可见也。”[8]1169[16]903第四,赞赏王安石那种“无惧”的“三不足”精神。他有《和荆公》诗一首:“无惧真为宝,非兹不得生。禅门讲座下,所得尽平平。国破犹能战,家亡尚力耕。生天成佛者,都是有牺牲。”[8]371[9]330第五,严复虽几次批评王安石“不知人之攻我而立异者,不必皆奸人”,但在王安石《老树》一诗上却批阅道:“此诗托意甚深,当是更张后作”。“公诗又有云:‘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评曰:三反四折,终是世故有情,非为己之叹也。”由此,他承认“公亦知异议者之多君子而忧其去矣”[8]1162。第六,和梁启超一样,严复也认为王安石的思想中具有后世称为“社会主义”的某些成分,其中就有主张强化国家整体调控能力,抑制豪强兼并,兼顾贫者弱者群体的利益,使四海晏安,远近协和等内容。严、梁实际上都不相信彻底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能够实行,但从道德价值的层面看,他们都认可其必要性,以为这不仅有利于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而且对社会的稳定也不无裨益。因此,严在评《王荆公诗》中也表露了这种思想。他说:“荆公胸中社会主义甚富。”[8]1157
从负面批评一端来看,严复与梁启超就大不相同了。在梁的论述中,王安石心术可谓洁白无瑕,完美无缺。严复则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宋明以来批评王安石的某些传统,如司马光说王安石用心太过,自信太重,性格倔,不晓事。严复在王氏《戏长安岑石》之“肯为行人惜马蹄”句下就批有“此人所以云其执拗也”[8]1170。1917年,严复在一小账本上再次表达了此意。他说:“众贤说介甫皆有太过处,唯温公说其执拗不晓事,最平允。嗟乎!使《群学肄言》早出,介甫见之,其主张当较谨慎也。”[15]182很明显,在严复看来,王安石心术确有偏激蔽塞之处,需要读《群学肄言》这样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著作。严复认为王安石心术有偏蔽,还反映在对王安石另一首诗《和王乐道烘虱》的批语里。严复很不客气地写道:“吾国人于洁清视为儿女家事,以此浊秽遂成性习,昧者且自以为高雅,不屑以之凌人,真去畜生道不远。嗟乎!治国亦犹此身而已,囚首垢面而谈相业,吾知其无能为也。”[8]1163严复在此的表面意思虽然是讲个人卫生和轻视外在形式问题,但据史籍记载,王乐道这个人品行不正,而王安石却与之交往甚密,王安石本人的品性自然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某种嫌疑。严复此语是否有某种言外之意,不得而知[16]282-283。梁启超《王荆公》中引有陆九渊、颜元之言,称荆公“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13]102-103可严复在评《王荆公诗》中却说:“荆公视富贵甚重,如此首结语与但愿一门皆贵仕等语,殊令人意恶。”[8]1165[16]589前文已提到,严复评《老树》一诗时也承认“公亦知异议者之多君子而忧其去矣”,但从严评王安石的整体思想来看,他认为王安石看人有偏向性或绝对化的毛病,他将此视为王安石变法未成的症结之一。正因为严复对王安石那种以我划线、是己非人的性格作风不以为然,所以当他看到“安石白帝曰:知县贾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和“安石曰:(欧阳)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等语句时,就挥笔批道:“此亦非所宜言”,“此又非所宜言”[8]1151-1152。同梁启超一样,严复也认为王安石的确是一位思想卓越的政治家,其经世济民的强烈愿望和敢作敢当的魄力,足为唐以后第一人。但严不同于梁,他不认为王安石的理想虽在古代社会无条件可实现,而到近代有立宪和交通的基础就可能实现。在严看来,王的理想本身是有问题的,在古代行不通,如果拿到今天,那更不知会闹出多少纠纷。严复说:“孔之均无贫,均得而各富也。荆公之意乃欲均取而以富国。”[8]1157又说:“吾不谓此老为无误,然有经世力虑,则唐以来一人而已。使公而生于今,移其所信于古以信于今,加以询谋,中国尚有豸乎!”[8]1157
四、梁、严评王安石学术之同异
梁启超评议王安石之学术,可以集粹、自得、大义、遵道、知命、经世、力行、思想自由与不自由等词语概括。其总体倾向是弘扬王安石学术,间亦略加批评。梁称王安石“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13]101;“以穷极古今之学而致之用,其得君而以道易天下,致命遂志而不悔……其大旨在知命”[13]127;“可以仕而仕,可以已而已,其一进一退之间,悉衷于道,自古及今,未有能过之者也”[13]233。总之,“荆公之学术,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13]287。知命厉节,经世致用,确乎是王安石学术的显著特色,梁启超对此十分赞赏。他写《王荆公》时特辟一章讨论王安石学术,认为中国的学术集中反映在经学的传承上,而经学传承不外重大义、重章句、重心性、重经世这几条途径,荆公之学更重大义、重经世。梁认为经学之正途即在于此:“讲求大义,实为治经者唯一之目的,玩索章句不过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误手段以为目的,则终其身无所得于经……夫必明大义然后乃可谓之经学。”“以此道治经者,创于先汉之董江都、刘中垒,而光大之者荆公也。”[13]289“传之以心,受之以意,切问深思,而资所学以施于世,公之所以治经者尽于是矣。”[13]292对求大义以经世的学术途辙,梁启超可谓与王安石志同道合,但梁毕竟是现代思想家,他崇尚思想自由和学术多元。他认为只要思想自由,人的性灵必然愈浚而愈深,就可能发古人未发之奥,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注解经典,甚至或可以补充经典之不足,所以应该鼓励在思想自由、学术多元的前提下去“求大义”。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上对王安石的批评颇多,指责王安石试图统一学术以正人心。梁启超对这样的指责亦表赞同,他认为如果王安石真是如此,那就不免为之深感遗憾了。他说:“考荆公平日言论,多以一学术为正人心之本,则史所云云,谅非诬辞,此实荆公政术之最陋者也。盖欲社会之进化,在先保其思想之自由,故今世言政治者,无一不以整齐画一为贵,而独于学术则反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而中国学术史上光耀顿减。以荆公之贤,而犹蹈斯故智,悲夫!”[13]214-215梁启超虽为王安石的“一学术为正人心”深感遗憾,但丝毫没有减弱他对王安石学术的认同。他在遗憾之余,很快又回到王安石一方,为之辩护起来。“考荆公当时,亦非于《新义》之外悉禁异说,不过大学以此为教耳。”“夫学者有其所主张之说,则必欲发挥光大之以易天下,非徒于理不悖,抑责任亦应尔也,于公乎何尤?”“(《周官义》)吾尝窃取读之,其精要之处盖甚多,实为吾中国经学辟一新蹊径,自汉以迄今日,未有能过之者也。”[13]215
严复评议王安石学术与梁启超大异其趣。梁启超评议王安石学术侧重在“经学”方面,而在“经学”中又更强调“求大义以经世”的特点;严复评议王安石学术虽偶尔涉及“经学”,如他在批阅王安石诗《寓言九首》时,就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均输法源于《周礼》卷四《地官司徒下》之“泉府”[8]1162[17]153-154,但此外没有更多议论王安石“经学”的文字。严复评议王安石学术,侧重点在文学和哲学两个方面。对王安石诗文的艺术性,严复大多十分赞赏,如在批阅王安石诗《车载板二首》时,他称赞“二诗皆雅健”[8]1154。批阅《谢公墩》时说:“此数语自非他人能作。”[8]1155批阅《酬王伯虎》时写道:“如此等诗,皆此老独步苏黄,与之比较,适成诗人诗耳。”[8]1157批阅《和吴冲卿雪》时评道:“全体学昌黎,落想新刻,可谓精能者矣。”[8]1157批阅《北客置酒》时叹道:“真写得意态出。使今人竭力尽气为之,非移汉作胡,即乞灵新名词矣。”[8]1158批阅《西风》时写道:“大家为诗,只是直写肝鬲,无一毫为人意,故工拙虽少异,皆传作也。”[8]1159批阅《思王逢原》时称赞:“此诗沉挚极矣,读之令人气厚。”[8]1159虽然,从文学意义上说,严复对王安石诗作也不能说全都欣赏,但从以上可看出他对王安石诗歌文学价值的肯定是无疑的。除诗作外,严复对王安石文章的文法亦甚称道。他在批阅《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时欣然写道:“先述德行,后著功效,所以百年无事之故即此晓然。其文成法立,独开生面,可谓精能之至者也!”[8]1212[14]657-660批阅《给事中孔公墓志铭》时,他更是赞叹不已,挥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感情饱满的文字:“先标事实,后加注考,遂觉用笔如利刃断麻。试入他人之手,闭目思之,不知此数行中当有多少葛藤。既出复入,既入复出。事既委折难叙,况益以所以然之故,作者只数行了之。不但斩截峻洁,难得神采焕发如此。此篇三‘尝’字,两‘盖’字,两‘果’字,两‘故’字,皆极可玩。”[8]1230[14]1529-1532
如果说严复对王安石在文学方面称赞居多,那么在哲学方面应当说批评就大大多于称赞了。由于严复对西学造诣极深,他在评议王安石时,有时会发出超乎一般的议论。实际上,他是从哲学或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来意会王安石某些极富创意的奇特思想的。王安石有首诗名为《秃山》,严复读后批曰:“抵得一篇马尔图户口蕃息论(按,今译马尔萨斯人口论)。此等思想皆非同时诸公所有。”⑩在读到《彼狂》一首时,严复更称“此篇是王氏天演论”[8]1163[16]278-279。不过类似这样的评论并不多,且不能代表严复在哲学和思想方法上对王安石的整体评论。其实,严复从哲学或思想方法的层面评议王安石,批评责备的文字可谓比比皆是。
严复批评王安石比较集中的一点是说王氏过度自信、不切实际、思想偏激。王安石有《众人》一诗,曰:“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乃知轻重不在彼,要知美恶由吾身。”这是王氏自比周公,自命圣贤的典型之作,表达了他那种只求诸己而不顾实情的倾向。严复在此诗上批道:“此老执拗之名所以著也。”[8]1163据释普济《五灯会元》记:蒋山赞元觉海禅师与丞相王安石甚友善,安石为之特奏章服、师号,并与之“萧散林下,清淡终日”[16]55-56。故王安石有诗曰:“白鹤声可怜,红鹤声可恶。白鹤静无匹,红鹤喧无数。白鹤招不来,红鹤挥不去。长松受秽死,乃以红鹤故。北山道人曰,美者自美,吾何为而喜;恶者自恶,吾何为而怒。去自去耳,吾何阙而追;来自来耳,吾何妨而拒。吾岂厌喧而求静,吾岂好丹而非素。汝谓松死而无依邪,吾方舍阴而坐露。”严复批道:“长松受秽何足道,如苍生何?此公之所以难辞祸宋之咎也。”[8]1153-1154《庄子·天地篇》记一故事:“子贡过汉阴,见一丈人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机械如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丈人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桔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愿而惭曰:‘始吾以夫子天下一人耳,不知复有斯人也。’”王安石据此题诗一首,名为《赐也》,诗曰:“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瓮区区老此身。”[16]859显然,王安石心向那位“丈人”,而看不上那位提倡采用机械的子贡。严复对王氏的这种思想不以为然,故在该诗末尾批道:“一肚皮不合时宜,尽于此等处流露。”[8]1167严复读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读到“《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一段时,愤然道:“此最是专制谬语,就令如此,治遂成乎?公特未之思耳。”[8]1171读到“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肄,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屏之而莫敢习者也焉”一段时,严复批了这么一句:“突厥之焚书也,其说正如此,舍《哥澜经》而外,皆异说也。”[8]1211当读到“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和“天下之人,亦渐渍于失教”等文字时,严复也觉得王安石这些指责有简单化、理想化的倾向,他认为,既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势必要受到科举考试这种形式本身的限制。所以他说:“课试所为仅能及此,不必訾也。”“资序易见而才具难知,固无足怪。”[8]1211除读《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这些批评外,其他地方亦有批评王安石简单偏激之语。如读王安石短文《原过》,对其中“天播五行于万灵,人固备而有之。有而不思则失,思而不行则废。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复得,废而复举也。顾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与“性失复得”等语,严复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有而不思则失,失其智也;思而不行则废,废其勇也。闻失智废勇者矣,未闻失性废性者也。介甫殆不识性,故言:性有失时。”[8]1190
以往学界在谈到严复和王安石诗这一现象时,总以为这表明严复与王安石心通意会。但如果我们细品严复的和诗,恐怕另有意趣,多与王安石心意相左。试举两例:
其一,王安石诗《即事二首》之二:“云从无心来,还向无心去。无心无处寻,莫觅无心处。”严复和诗:“无心即无云,有云因有心。所以云生灭,还向心中寻。”[8]1172这里实际上表达的是两种不同的哲学观念。按王安石之哲学,“心”与“云”是对立的,即主、客体是对立的;若按严复的哲学,“心”与“云”是统一的,即主、客体是统一的(11)。
其二,王安石《拟寒山拾得二十首》之二:“我曾为牛马,见草豆欢喜。又曾为女人,欢喜见男子。我若真是我,只合长如此。若好恶不定,应知为物使。堂堂大丈夫,莫认物为己。”之三:“凡夫当梦时,眼见种种色。此非作故有,亦非求故获。不知今是梦,道我能蓄积。贪求复守护,尝怕水火贼。自觉方自悟,本空无所得。死生如觉梦,此理甚明白。”严复和诗曰:“我曾为草豆,欣欣望春雨。及我身为男,梦想邻家女。我之知有我,正以有物故。物我各有需,纷然起好恶。若令无好恶,此我岂得度。”“人之生有求,只缘养身故。当其作梦时,此意仍未去。所以种种色,一若觉所遇。及其已死时,此身已无处。假令尚有求,宁与今殊趣。以死为梦觉,此理吾未喻。”[8]1172-1173从“之二”看,王安石将人之一身的物与我,也就是肉身与精神对立起来;而严复的哲学是“我之知有我,正以有物故”,物与我是统一的,肉身与精神是一体的。从“之三”看,王安石的哲学是“死生如觉梦,此理甚明白”;而严复的哲学是“以死为梦觉,此理吾未喻”。两人的观念恰恰相反。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王荆公》的最后一章《荆公之文学(下)》中,对王安石诗十分赞赏。他说:“荆公之诗,实导西江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在中国文学史中,其绩尤伟且大,是又不可不尸祝也。”[13]304在梁热情向读者推介的王安石诗数十首中,就有《拟寒山拾得二十首》中的之二和之四。梁的评论与严复不同,他完全是认同王安石的。他写道:“此虽非诗之正宗,然自东坡后,熔佛典语以入诗者颇多,此体亦自公导之也。若其悟道自得之妙,使学者读之翛然意远,此又公之学养,不得以诗论之矣。”[11]309
综上可见,梁启超、严复在对王安石的评议上确实多有差异,而其根源在于两者性格、文风、思想、学术乃至人格上的深刻分歧。这看似一个极其琐碎的细节,却多少能折射出晚清民国思想史极其微妙的面相,折射出历史的丰富与复杂。正是这种丰富与复杂告诉我们:在探研此时的人文生态时,仅仅把繁复多样的思想人物作简单的派系划分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内部差异都是很多很大的,在思想脉络上更是错综繁复,复杂万端的。只有厘清各种差异,才能进入当时思想的深处,进而才能真实地再现中西古今的相互联系,真切地体会到各种思想的内涵,为后人提供有益的借鉴。那种简单化、脸谱化的思想史研究,实与“原生态”的思想史相去甚远。它无助于洞察思想的内在脉络,无助于“知人论世”和对历史的“了解之同情”。
对梁、严评议王安石的比较,本文只是初步尝试。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严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方法。他们在态度、方法上的歧异,让我们不仅能体会文首所引章士钊的话,而且能对梁之“求用”与严之“求是”这两种迥异的思想风格有真切的体认。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偏向于“求用”的一脉,还是侧重于“求是”的一脉,都来源于近代中国的土壤,事实上也反作用于当时的思想生态。它们始终潜伏于近代中国的观念世界之中,并依循各自的“内在理路”不断交融、渗透和延展。作为一代巨擘,梁、严都名重当时,影响久远,对“五四”乃至此后若干代人物都产生了极为微妙而深刻的影响,这或许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国思想界的走向。甚至在20世纪后半叶的某些重要的政治文化人物身上,这两种思路的纠结与博弈也时有体现。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了。
注释:
①邓广铭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页)一书序言中说:“梁启超于清朝晚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所写《中国六大政治家》中之《王荆公》,则是全从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脱化而来,既未再作新的考索,自也不可能提出新的意见。”另可参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蔡崇禧《论梁启超的〈王荆公〉》,载《人文中国学报》2004年第10期,第303-340页;赖建诚《梁启超的国家经济政策主张——解析〈管子传〉和〈王荆公〉》,载《当代》2002年第178期,第56-67页,及2002年第179期,第66-85页;陈其泰《梁启超评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青格勒图《王安石形象的近代重塑与新传记史学的诞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依笔者所见,学界有关研究严复的论著目录,当以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两书搜罗最全。据以上两书所列,迄无论述严复评议王安石及比较梁、严评王安石的专文,唯个别论著略有涉及。
③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3页。据现有史料可知,在20世纪20年代,丁文江与林宰平一样,已被一些人公认为梁启超的传人;丁、梁二人在私人关系、学术理念、政治倾向等方面都极为契合,多有互动。关于这点可参欧阳哲生《科学与政治——丁文江研究》之“人际交往与友情天地”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136页)。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么《梁启超年谱长篇》所揭示的梁启超的学行踪迹、思想脉络、人事网络等,则更值得细究。据此深入比勘梁、严的人脉网络和论著详情的话,则能对两者当时各自所处的情境有更真切的把握。
④对此问题的论述详见梁启超《李鸿章》,见陈引驰编《梁启超学术论著集(传记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页。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梁对李鸿章的论述也与梁本人当时所处的具体情境有密切关联。
⑤参见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425页。笔者认为此说尚有疑问,因目前尚无可靠的文献可以证明所加批注、和诗全部完成于这一“旅次”。
⑥端方,字午桥,号陶斋,时任两江总督。
⑦岑春煊,字云阶,曾任两广总督,1907年调任邮传部尚书。
⑧严复《王荆公诗评语》称:“荆公相术如此。所谓清纯专制,到极好时便是父母朝廷,此在当时已做不到也。盖如大江然,既至荆扬而欲束之归峡,如在瞿塘滟滪之间,可复得耶?至于今日愈不必言矣。”参见王栻编《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56页;又见李之亮校补《王荆公诗注补笺》,(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17页。
⑨此为梁引陆九渊语,参见梁启超《王荆公》,见陈引驰编《梁启超学术论著集(传记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⑩严还称:“似喻天下生齿日众,吏为贪牟,公家无储积,而上未尽教养之方也。”参见王栻编《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64页;又见李之亮校补《王荆公诗注补笺》,(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350页。
(11)在对此问题的解读中,“心”是一个关键范畴。此处将唐诗中有“无心”一词的部分诗句辑出,以供理解王安石、严复诗作参照:钱起《江行一百首》第 75首:“秋寒鹰隼健,逐雀下云空。知是江湖阔,无心击塞鸿。”韩愈《赠同游者》:“唤起窗前曙,催归日未西。无心花里鸟,更与尽情啼。”司空图《上元日放二雉》:“婴网虽皆困,褰笼喜共归。无心期尔报,相见莫惊飞。”郑谷《闷题》:“落第春相困,无心惜落花。荆山归不得,归得亦无家。”皎然《送灵澈》:“我欲长生梦,无心解伤别。千里万里心,只似眼前月。”李贺《南园十二首》第10首:“边壤今朝忆蔡邕,无心裁曲度春风。舍南有竹堪书字,老去溪头作钓翁。”羊士谔《斋中咏怀》:“无心唯有白云知,闲卧高斋梦蝶时。不觉东风过寒食,雨来萱草出巴篱。”杜牧《送赵十二》:“省事却因多事力,无心翻似有心来。秋风郡阁残花在,别后何人更一杯?”司空图《狂题十八首》第16首:“有是有非还有虑,无心无迹亦无猜。不平便激风波险,莫向安时稔祸胎。”褚载《云》:“尽日看云首不回,无心都大似无才。可怜光采一片玉,万里晴天何处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