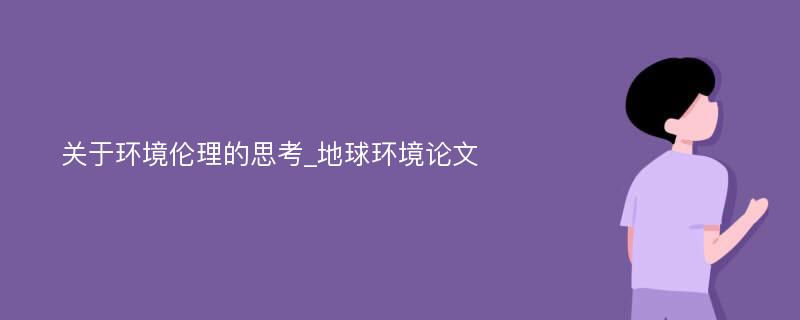
对环境伦理学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球环境危机是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在解决这一难题的实践中产生了环境伦理学(the ethics of the environment )的理论形式。它虽然是解决地球环境问题的实践的产物,但却和实践者的原始动机不同,也有别于政府的各种环境保护政策。它不再站在人类自身的立场上、以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为目标,也不从技术上研究人在环境中如何行动才有利于人的存在和发展,而是对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一种所谓的“本体论”解释,把人与环境的关系解释为伦理关系。当今,这种环境伦理学似乎非常时髦,一些人把它作为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地球环境问题的理论模式而予以阐释。那么,人与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何以能成立?如果我们否定环境伦理学的观点,否定它所设定的人与环境的“伦理关系”,是否意味着现代地球环境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1
众所周知,环境伦理学是以反传统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为宗旨的,把用以取代传统伦理学的“生命中心主义”作为理论前提。按照环境伦理学的观点,造成现代地球环境危机的根源正是传统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它只承认一个物种——人的价值,而否认人以外的任何存在物的价值。如果说有价值,也仅仅是作为工具的价值。这样,人类对其以外的所有存在者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的正当性与否,就完全取决于两个事实:一是这种结果是否有利于促进人类的利益;二是是否有利于实现人类的权利。所以,“它只承认,对人而且只对人具有道德上的义务和责任。即便我们可以考虑对地球上其他生命体的义务和责任,但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义务和责任都是基于人类价值的实现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义务和责任去保护我们之外的环境的存在和发展。”〔1〕根据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我们对地球环境问题的研究会被认为只是由于人类行为对地球的破坏,其结果反过来阻碍人类自身价值的实现。对此,环境伦理学认为这是犯了类似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物种歧视”的错误,使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为使地球环境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必须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传统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与传统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同,环境伦理学主张“生命中心主义”价值观。泰勒在他的《尊重自然》一书中指出:“环境伦理学所关心的是人与自然界间的伦理关系。规范这一伦理关系的原则决定着我们对地球及居住在地球上的所有动植物的义务和责任。”〔 2〕很明显,这里的“义务和责任”是伦理意义上的“义务和责任”,和通常意义上的保护地球环境的义务和责任不同,他是在将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设定为伦理关系的前提下讨论义务和责任的。用泰勒的话说,一切生命存在包括所有非人类生命体构成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因而它们无不具有内在价值。承认环境伦理学,“就是承认所有的非人类生命体具有内在价值”。而承认“所有非人类生命体的内在价值”也就是承认了环境伦理学〔3〕。 这种普遍“内在价值”说,就是依托于“生命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基础。
以“内在价值”这一概念为基点,使自然界的一切非人类生命体取得与人类平等的资格,并以此为由把人与环境的关系确定为伦理关系。因此人的行为的正当与否不再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人类自身价值的实现,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有益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即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地球上所有生命体价值的实现。那么,“我们保护环境,不使其污染的责任和义务本身就是为了地球生命体系统能够以它本身的自然状态存在和发展,这种义务和责任是不依赖于我们对人类的义务和责任的”〔4〕。 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行为可以同时完成这两种义务和责任,即对人类的义务和责任与对其他生命体的义务和责任,但这却是基于两个不同的事实,也就是说非人类生命体的存在和发展与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尽管同时被当作目的,然而它们毕竟各具独立的内在价值。
2
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点是认定一切生命体都有独立的内在价值。那么,什么是生命体的内在价值?在环境伦理学看来“价值就是需要和利益”〔5〕, 正如人的需要和利益构成了人的内在价值一样“生命体的需要和利益也就是它们的价值”〔6〕。 承认地球上其他生命体有需要和利益的存在,保证它们的需要和利益,就是赋予它们以内在价值。每一种生命体都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它的存在和发展作为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它的存在和发展能够被促进和破坏,本身就证明了它有需要和利益这一事实的存在。”〔7 〕这就意味着它是独立的,不需要以其他任何实体如人作为参考系来证明。这就是说,不管它是什么,只要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本身就拥有生存和发展的能力,经过各个正常的自然发展阶段,使其能量得到充分发挥,完成其自然的存在和发展过程而不受人为的干涉,这是它的需要和利益的实现,也是它的价值的实现。可见,既然它们都是拥有内在价值的实体,就应该把它们视作目的本身而加以保护,不应该把它们视作纯粹的客体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或者说,如将生命体作为手段,其价值则取决于其他实体——人的存在。据此,本来就不应该把自然作为达到人的目的的手段而加以利用,因为它是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本质上是属于它们自身的。基于这种内在价值,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体就有了道德上的权利,于是推出尊重自然是善,破坏自然是恶的伦理原则。
这样说来,人对自然界的所有生命体的任何行为也就有了正当性与非正当性的意义。而“这种正当性与非正当性并不产生于我们人类,而产生于生命体本身。因为它们是价值, 具有被善待或恶待的特性”〔8〕。很明显,如果说我们对不具有被善待或恶待特性的存在有道德上的义务和责任,那是不可思议的。如岩石、沼泽、河流、沙漠等,我们对它们就没有道德上的义务和责任。因为它们本身并没有需要和利益,也没有价值,所以我们对待它们的任何行为都谈不上有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性与非正当性。
但是,生命体以外的所有无机物,如岩石、河流、沙漠等,尽管它们本身没有需要和利益,不是价值,我们对它们没有道德的义务和责任,然而我们也应该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对待它们,以便去完成我们对依赖于它们才能够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生命体的义务和责任。这样,对待自然界中的无机物系统的任何行为也就从逻辑上推出其具有一定的伦理意义。因为我们无论采取何种行为对待其周围的无机物,都必然会影响生存于其中的生命体,包括人的价值的实现,所以人在环境中的任何行动也都具有伦理意义。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伦理关系。在通常的伦理关系中,人对人是互为主客体关系的。就是说,人既是道德的主体,又是道德的客体;既是道德的执行者,又是道德的承受者。这种双重性的角色,决定了人必然既是道德义务和责任的主体,同时又是道德权利的主体。人在尽自己的道德义务和责任的同时获得其道德上的权利,二者始终是统一的,而且首先是权利。然而,在环境伦理学所设定的人与其他生命体的所谓伦理关系中,二者却是分离的。它只片面强调人应该对其他生命体具有道德的义务和责任,却忽视了人的道德权利是如何在这一伦理关系中实现的这一根本性问题。对此既然不能予以合理的解释,则所谓道德上的义务和责任也只能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空话。
3
环境伦理学并未将其理论基点贯彻到底,因而陷于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伦理学史上的任何一种伦理学都以自己的基本原则去说明它所关心的对象的性质,并以其对象的性质作为原则确立的前提。比如,功利主义伦理学把具有体验痛苦和快乐的能力作为其伦理原则的决定性标准,康德伦理学则把能够进行理性的反思和自律的个人作为标准,从而给予具有这一特性的存在以伦理资格。但环境伦理学却没有为我们提供这种标准。根据环境伦理学的基本观点,生命体由于其需要和利益而使之具有内在价值,获得了和人一样的道德尊严。由人因其具有内在价值被看作目的、不被看作手段而逻辑地推出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体也应被看作目的,不应看作手段。按照这样的推论,应该说任何生命体都具有资格成为环境伦理学关心的对象,这也就意味着生命体本身就是环境伦理学的基础。然而这只是我们的理解,并非环境伦理学的真实逻辑。就是说,它并不认为一切生命体都具有同样资格而能够成为环境伦理学的关心对象,它所关心的只是生命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样,对于环境伦理学来说,生命体在资格上就不是处于平等状态,一些生命体有需要和利益,是价值,而另一些没有需要和利益,则不是价值。比如,家禽是一种生命存在,它有需要和利益,当然应该说是一种价值。但环境伦理学却不认为它是价值,因而它们不能成为环境伦理学所关心的对象。再如,动物园里的各种动植物与原始森林的动植物应该说同样具有需要和利益,是一种价值。但环境伦理学只把后者列为它所关心的对象,前者除外。为什么同样是生命存在却有不同的意义呢?在环境伦理学看来,似乎因为它们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即属人世界和自然世界,一种生命体之所以有价值,乃在于它是“自然的”,当它一旦脱离了自然界,进入人的世界,也就不再有价值。为什么?假如生命本身的需要和利益是价值得以形成的基础,那么任何生命体的需要和利益都应该成为价值。本来认为“自然的”生命是其原则的基础,为什么只有在“自然的”状态下才有价值?好像一块石头的价值就在于它是自然的,当用它来建筑一座大桥或房屋时,它的价值就会立刻消失。这确实无法理解。
果真这样,那艺术品也就不再具有价值了,因为任何一件艺术品都是人的创造物。如果环境伦理学还承认艺术品有价值,那它的价值取决于什么呢?是否取决于它对自然的真实模仿?如果是这样,一件复制品,其复制的高超技术足以使其以假乱真,为什么这件复制的艺术品就不再具有价值?我们只能说,艺术品或别的什么东西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人相联系。因此可以认为,价值本质上表征的是一种关系,是人与物之间的一种特有的评价关系,不是物与物之间关系。正是由于人的存在,世界才成为价值的世界,如果世界上没有评价者——人的存在,由于失去价值形成的条件,也就不会有被评价者——价值的存在。正如我们通常所设想的“最后一个人的争论”那样,假如地球危机毁灭了全人类,只有最后一个人的存在,这最后一个人当然也是唯一的评价者。那么,即使他毁掉所有的艺术品,他的这一行为也没有任何的不正当性,因为美的价值只存在于它和评价者——人的关系中,当评价者——人不存在时,美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所以美的对象本身并不具有所谓的独立的内在价值,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关系事实的一个构成要素。这证明人之外的一切存在物、当然也包括所有的非人生命体并没有所谓的独立价值。我们之所以要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存在和发展,是因为它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这并不能说明它具有独立的价值。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9 〕“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10〕
马克思从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的关系出发,对价值这一矛盾概念作了本质的规定。人由于其特有的内在尺度而成为主体,人的需要也因此成为能动的主体需要。主体依据自身的内在尺度对外物进行认识与改造,使之不断地向着“为我”的方向转化。因此人的需要是具有历史性的,是一个变数。人以外的任何生命体由于没有内在尺度而不能成为主体,对外界环境不能进行认识和改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动物与其外在环境根本没有“关系”。这并不是说动物不依赖环境而存在,而是说它仅仅依赖于环境而存在,其需要也就只能处在本能的层次而始终不发生变化。尽管可以说动物有需要,但它的需要却不是价值。我们说价值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并不是实体概念,这就意味着价值既不在外物中产生,也不在人本身中产生,它只能存在于人和外物的关系中,这就是价值与事实的对立统一关系。如果把价值理解为这样一种关系范畴,上述的环境伦理学的“自相矛盾”就能得到纠正。这就是,自然界的动植物和属人世界的动植物以及艺术品都具有价值,这是基于它们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人相联系,因此对于人来说,保护任何生命现象及其无机界环境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存在与发展的义务和责任本身仍然是为了实现人类自身的权利。
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系统,这表明生命体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意味着生命体的被消耗。如果按照环境伦理学的观点,自然界是一个价值整体,构成这个价值整体的每一个生命体都不能缺少,否则就会造成这个价值整体的毁灭,因此必须保护每一生命个体的存在。但实际的结果是,在自然界这个动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生命体的存在与发展,都是在与其他生命体的斗争中实现的,这就是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规律。生命体为了获得自身的生存,必须参与竞争,而强者的生存是以弱者的牺牲为条件的。比如,老虎扑食一只小鹿,而同时小鹿也吃掉大片的嫩草,按照环境伦理学的观点,这种现象无疑是一种价值的被否定。对于这些被否定的生命体来说,其能量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并没有完成其生命的自然发展阶段。对此,环境伦理学并不诉诸它的“生命中心主义”价值观,因为它认为这是合自然规律的,并没有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平衡性。这种看法如果能成立,那么人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与价值的实现,是否也可以如上述那样去对待周围的生命存在?既然环境伦理学承认人本质上是自然界有机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其他生命体是平等的,我们人所做的一切也就必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一推理如果正确,则人类对周围环境的利用与自然界中生命体之间的生存竞争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不合自然规律的。但环境伦理学却与此相悖,反倒认为这是不合自然的。那么,同样是“自然的”生命、自然的一部分,为什么人和其他生命体活动的结果截然不同?这是否由于环境伦理学的主观偏见使它连自己的理论基点都置之不顾了呢?
4
地球生态系统的原始平衡性被破坏确实是由于人的存在造成的,我们也只能从人的存在本身去寻求解决的方法。人既然也是自然界生态系统中的一种生命存在,为什么唯有人的存在会破坏自然的平衡性呢?
人作为生命存在,和其他的生命体一样,是生存于自然之中的,所不同的是其他生命体是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前提下生存和发展,在自然面前是被动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完全取决于给定的外在自然环境条件,所以它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人却是能动的,他是在使环境适应自己的过程中即在改造中去适应环境的。所以,人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给定的环境条件,而是取决于人对环境的改造。人是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才成为人本身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1〕就是这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这是人的存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是人的存在的本质。人的存在的这一特殊本质决定了人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改造原有的环境,而改造本身就意味着对原有的环境的某种影响或某种破坏。但人又不能因此而不改造环境。对于人本身存在的这种矛盾关系的认识是以人对外部环境的改造和对人本身的改造为前提的。但是,人对这一矛盾关系认识的自觉程度又反过来影响着人对环境以及对人自身的改造实践。因此,当我们对人类自身存在的本质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对立统一关系还不能自觉认识时,人类对其环境改造的实践也就不具有能动的自觉性。其结果必然要对自然系统本身造成某种程度的破坏,并对这种结果无所顾忌,因此也就不可能给它以有意识的补偿或补救。如果说早期人类对环境的改造实践所产生的某种程度的破坏依靠自然本身的再生能力还能够补救而使其恢复原状,那么人类今天由于对自然的改造而产生的破坏将无法依靠自然本身的再生能力来补偿。这就需要人类在对环境进行自觉改造的同时给自然以有意识的补偿。在这种改造与补偿的双重过程中,人获得其自身的真正的存在与发展,求得真、善、美的统一。而真、善、美的统一过程就存在于对人存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的认识与实践过程中。
总之,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我们保护地球环境的义务和责任都是指向我们人类本身的。正如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所指出的:人具有自由、平等以及获得生存条件的权利,为了这一基本权利的实现,人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和改善我们的环境。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宣言又指出:我们关心环境长期持续的存在和发展,而人类长期持续的存在和发展,则始终处于我们关心的中心。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可能否认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是目的这一客观现实。我们也只能在这一前提下来考虑问题,真、善、美的统一就是人类履行保护地球环境的义务和责任、实现人类与地球长期持续的存在和发展所必然要求的。环境伦理学所谓的“生命中心主义”价值观只不过是一种极端的反人道主义观点:“当最后一个人——男人、女人或儿童可能在地球上消失时,那也不会对其他动植物的存在带来任何有害的影响,反而会使它们受益。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对它们的生存所造成的破坏就会立刻停止。如果站在它们的立场上看,人类的出现确实是多余。”〔12〕因此,环境伦理学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和完整性,在可能选择的情况下,它必然要去抢救那些将要灭绝的苍蝇、蚊子和老鼠,而绝对不会去营救那些处于危机境地的人类,更谈不到促进人类对真、善、美统一境界的追求。
注释:
〔1〕 〔4〕〔5〕〔6〕〔7〕〔12 〕Andrew Brennan: TheEthics of the Environment(《环境伦理学》)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USA,p198、p198、p201、p201、p200、p208(1995).
〔2〕Paul W.Taylor:Respect for nature: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尊重自然》)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3(1986).
〔3〕〔8〕Paul W.Taylor:Respect for nature: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尊重自然》)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71、p17(199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3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8页。
[作者附记:本文的撰写汲取了北京大学谢龙教授提出的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