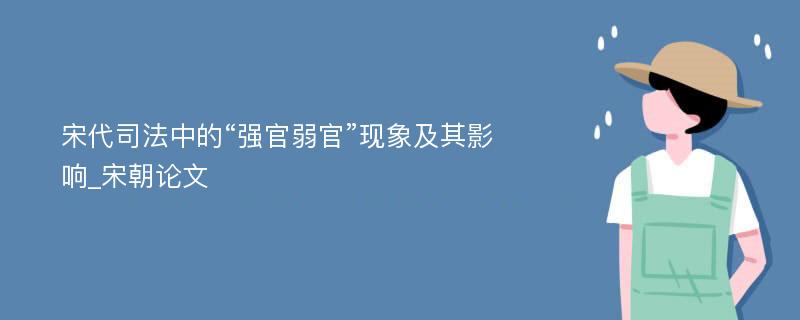
宋代司法中的“吏强官弱”现象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司法论文,现象论文,吏强官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典章制度方面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在结合“法律人”的实践来考察司法制度变迁方面却显得较为薄弱。以宋代为例,对这一时期胥吏的司法实践的讨论基本停留在近代以前士大夫的片面责难的层面上,①但是,既然宋代胥吏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突出,以至当时人有“吏强官弱,浸以成风”②之叹,而这种局面又延续至明清,前后达近千年之久,想必一定有其非常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或许对现代中国的司法包括当前的司法改革具有某种潜在的影响,因而,研究和清理这一层历史就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就以下几个具体问题略作归结,即宋代胥吏在司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表现、条件和影响,以期引起更深入的研究。
一、宋代司法中“吏强官弱”之表现
司法的基本功能在于适用法律解决纠纷,这种功能在宋朝是通过官员和胥吏两个阶层来实现的。官与吏的区别在司法过程中表现为胥吏负责与审讯和检控有关的具体事务,官员在其基础上对案件作出裁决。但这并不意味着承担具体事务的吏人没有司法权,长官的最终决定权也不等于司法权的全部。因为宋朝是一个法制化程度相当高的朝代,各级官府包括皇帝都有一套行为规范,在法律和习惯上,各个角色所主管的范围都受到相当的保障,即使卑贱如胥吏者,长官虽可以笞辱,但也不能无理施行。在宋朝特殊的司法运作过程中,狱讼裁决的方向在胥吏从事的具体事务阶段就已基本确定,再加上其它诸多因素的影响,胥吏在狱讼处理过程中发挥着异常突出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胥吏实际独占法律知识
胥吏在官府中的地位有赖于他们处理事务的能力。宋朝法制达到历代法制发展的顶峰,但在宋朝官府禁止民间私藏法书、私习法律,以科举进身的士大夫鄙视法律实务的情况下,胥吏实际上成为整个国家唯一充分掌握法律知识、精通法律实务的阶层,整个王朝的法律形象可以说是胥吏阶层的作品,这也是在宋代司法过程中胥吏对长官权力构成威胁的重要条件。胥吏从汉唐时期的刀笔吏发展而来,仍然保留着“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传统,元代印行的《习吏幼学指南》序直接指出:“吏人以法律为师,非法律则吏无所守”,③该书书首冠以历代吏师以显吏学师承,其后大部分词条亦皆与律令狱讼有关。因此,熟悉律令制度是作吏的基本条件,这类知识主要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谙熟吏道的资深胥吏的传授和自身在官府的长期历练。与儒家经典相比,吏学更像是独门秘传,科举或荫任出身的士人不愿接近也难以接近。宋朝法制趋于理性化、形式化、客观化,且复杂多变,从前朝承袭下来的律令体系和德礼意识形态与宋代社会现实存在巨大落差,这使得士大夫所修习的诗赋和经学在司法实务中几乎没有用武之地。④
宋朝士人对学习律令的抵触似乎根深蒂固,让苏轼险遭杀身之祸的诗句“读书万卷不读律”就诚实道出了当时士大夫的知识状况和对学习法律的消极态度。与宋初同时的南唐右仆射判省事游简言“躬亲簿领,督责稽缓,僚吏畏之,然暗于大体,不为士大夫所重”,⑤这显示士人躬亲庶务要冒“为同僚所轻”的风险,这种形势迫使游简言请求“辞职以谢”,北宋时期士风已至如此,遑论南宋。这种知识结构上的缺陷让宋朝士人在司法实务中捉襟见肘,不得不依赖对成案惯例烂熟于胸的吏人,官员很容易受吏人控制,以至与之狼狈为奸。⑥士大夫中间有不少人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南宋的叶适曾说:“国家以法为本,以例为要。其官虽贵也,其人虽贤也,然而非法无决也,非例无行也。骤而问之不若吏之素也,踅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举而归之吏。”⑦又言:“以天下经常之事立为成书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士大夫不习国家台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见侮于胥。”⑧朝廷也力图改变这种不利局面,神宗时期曾开创新任官员试刑法等制度,且不说这一制度实行未久,即使勉力贯彻下去,这种一次性的考试对提高官员法律素质的效果也令人怀疑,相对世代吏学相传的法吏,显然不足以改变士人在知识结构上的劣势。靖康变乱,北宋条法尽失,南宋欲重订法律,其内容有很大部分竟然来自三省胥吏的“省记”。士人在法律知识上的劣势也很难用道德态度来弥补,诚如叶适所言:“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刮席,条令宪法多所不谙,而寄命于吏,此固然也。然虽使得其人而居之,如昔之所谓伊尹傅说之俦而已,夫区区条令宪法仍为不晓,而与是吏人共事终亦不可。”⑨也就是说,士大夫之所以在司法实务中倚赖胥吏,主因不在于贤不肖,而在于不通法令。
(二)受成于胥吏之手
宋代发展出一套较严密的司法制度。以刑事案件为例,州一级狱讼的处理一般分为推鞫、检法两个环节,虽有诸参军分领,但其事务主要由胥吏承担,长官及其属员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如在推鞫结束后,长官要主持录问,定判之后又翻异的则要别勘,以防止官吏特别是胥吏舞弊。州级如此,县级更甚,因为科举出身或荫任的令丞簿尉较多初次为官,狱讼实务尤其不熟悉,而县级承担的狱讼事务又最繁重,所以不得不仰赖胥吏来处理。在此,法律规定与实际运作差距很大,如果只看宋朝法律,则县令必须亲自鞫狱,但实际上狱吏是真正实行鞫讯的人。对狱讼审判来说,与其择官,不如择吏,所以在现实行政中宋朝对胥吏阶层还是非常重视的,在制度上给予诸多保障,如南宋法律对参与司法的胥吏的入职条件作了较详细的规定,神宗时期建立的吏人试断案的制度也一直坚持下来,除州级机关实行所谓鞫谳分司外,南宋时县衙也增设专门负责检法的胥吏,⑩较大程度上实现了狱讼处理过程的分工和专业化。与宋朝中后期地方官员结构的超稳定相比,参与狱讼的胥吏在管理和职责上的发展显示胥吏在狱讼处理过程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唐宋以来形成的文书行政于无形中提高了刀笔吏的实际地位,士人的经学诗赋只是起到附属缘饰的作用。如南宋侍御史李鸣复言:“二府每困于多事,而僚属常病于阙员,以阙少之员临繁剧之务,胥吏环拥案牍满前,目不停视手不停笔,十未去二三,已报会堂矣,精力强敏犹能自出其己见,期限或迫,不免受成于吏手,否则淹延迟顿,至有逾数月不下者。”(11)宋朝冗官问题十分严重,造成官场升迁压力不断增大,仕途竞争牵扯了士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叶适曾说:士大夫“專从事于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惟吏胥之听。……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12)“今自检正都司六部列属以及寺监,皆纲目之所在也,受守吏手,……盖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13)南宋初法律重建有赖于三省胥吏的回忆,到了这种地步,无怪乎当时官场会出现“信吏不信官”的风气,胥吏把持狱讼的问题更为突出。高宗在一道诏书中承认:“今所谓县令者,旦朝受牒讼,暮夜省案牒,牒讼之多或至数百,少者不下数十,案牍之繁,堆几益格,其间名为强敏者,随事剖决,不至滞淹,已不可多得。”(14)南宋胡太初在《昼帘绪论》里也说:“在法:鞫勘必长官亲临,今也令多惮烦,率令狱吏自行审问,但视成款佥署,便为一定,甚至有狱囚不得一见知县之面者。”(15)中央部寺司法已是受守吏手,遑论州县。三五位亲民官临一县之务,赋税催督尚且应付不暇,狱讼受成于吏手也是情理中事。
(三)朝廷和士人的压制最终失败
宋朝廷对胥吏在司法中的作用不断进行限制,但效果并不明显。
录问、签押、翻异别勘、一衙两狱等制度都可以看作防范胥吏作弊的方法,如果这些制度得到切实执行,胥吏在司法中的活动空间就会被大大压缩,所谓吏奸的弊害也会大大减少。但是除了新法党人当政的短暂时期外,我们在宋代历史上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趋势,胥吏在司法中受贿枉法的情况似乎越来越多,士大夫对胥吏的指责也越来越激烈。士大夫中间的精明强干者也能对胥吏气焰有所压制,如北宋杜衍兼判吏部流内铨时,“敕吏函铨法,问曰:尽乎?曰:尽矣。力阅视,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诸吏无得升堂,各坐曹听行文书,铨事悉自予夺,由是吏不能为奸利。”吏部吏虽然一时辞谢赂请,却又告诉行请人:“我公贤明,不久见用去矣,姑稍待之。”(16)这一例表明宋代胥吏弊害的原因不单纯在于官不知法,即使像包拯这样的“法官”也不免为胥吏所卖。“包孝肃尹京,号为明察。有编民犯法,当杖脊,吏受赇与之约曰:今见尹,必付我责状,汝第呼号自辨,我与汝分此罪,汝决杖,我亦决杖。既而包引囚问毕,果付吏责状,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声诃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谓其市权,摔吏于庭,杖之七十,特竟囚罪,止从杖坐,以抑吏势。不知乃为所卖,卒如素约。”(17)从这一例中我们看到,胥吏对狱讼的左右往往是很隐蔽的,因为其久居官府,对官府制度和狱讼流程各环节的运作习惯了然于胸,能够把自身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在无形中实现对狱讼的控制,久而久之便成为司法上的惯行。
宋代胥吏也采取各种手段来抵抗士人的压制。有宋一代多次发生胥吏集体“罢工”事件,如仁宗景佑四年,苏舜钦言:“州县之吏,多是狡恶之人,窥伺官僚,探刺旨意,清白者必多方以误之,贪婪者则陷利以制之,然后析律舞文,鬻狱市令,上下其手,轻重厥刑,变诈奇邪,无所不作。苟或败露,立便逃亡,稍候事平,复出行案。设有强明牧宰,督察太严,则缔连诸曹,同时亡命,或狱讼未具,遂停鞫劾,赋税起纳,无人催驱。近年以来,习成此弊。”(18)以逃亡为手段刁难长官的事件主要发生在仁宗时期,说明北宋前期县官还有严督公吏者,北宋后期特别是南宋时,县官严治胥吏者日益减少,甚至为公吏指使。(19)也有向上级诬陷长官的,如南宋时黄平甫“干办江东茶事,司吏瞒取官物,平甫掠治之。旦日,吏告属官部専摔小吏。去将归罪,列僚俛首谢,平甫争不能得,即卧病丐去。”(20)在宋朝的官僚体系下,迫使官员去职本是很容易的事。胥吏久居衙门,其世故与阴狠也为士大夫所不及,如北宋“余靖初及第,归韶州,州吏尝鞫其狱者,往见之,靖不为礼,吏恨之,乃取靖案裹以缇油置于梁上,吏病且死,嘱其子曰:此方今达官之案,他日朝廷必来求之,汝谨掌视,愼勿失去。及茹孝标求其案,人以为事在十年前,必不在孝标,访于吏子,竟得之。”(21)
宋代胥吏对士人的压制有软、硬两种对策,其之所以得计还在于胥吏本身在官府事务中不可替代的功能和地位。南宋礼部尚书洪拟上书要求采取措施改变“吏强官弱”的局面,当时的孝宗对宰相说:“朕思此一事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舞文为奸。”宰相吕颐浩说:“缘官不知法,致吏得以欺。”孝宗虽然同意宰相的分析,但“其后刑部言:吏犯赃私罪已有正法,拟所请难行,事遂止。”(22)可见南宋胥吏在司法中的强势地位已经牢不可破,朝廷也拿不出更有效的对策。
二、宋代司法中“吏强官弱”之条件
地位卑微的胥吏要在司法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需要具备很多条件,这些条件在宋代“恰好”都已发展成熟。如官员对胥吏的控制力较唐及以前大为减弱,官员本身的行政权力也受到削减和牵制,唐宋社会转型导致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增大,法律制度发达而复杂,士人受科举制度等因素影响其精神转向内在的心性,总体上对行政和司法实务采轻视态度,“以法律为师”的胥吏在司法实务中的地位便渐趋重要,因此,宋代胥吏在司法中作用的增强是多种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胥吏群体规模膨胀,狱讼数量大幅增长。
宋初禁胥吏参加科举,吏与士大夫的界限趋于严明,渐成相对固定而卑下之行政司法阶层,同时,北宋中前期形成的官僚制度和科举制度造成官不久任、政务不精,“文吏高者,不过能为诗赋,及其已任,则所学非所用”,(23)政务司法多委于胥吏,加之中世贵族社会解体,社会生活趋于复杂化,行政事务日繁,政府对胥吏的需求不断增长。据《通典》,政府内的低级职员在晋时为11万余人,隋时为18万余,唐中期达到近35万,(24)可见隋唐时期已经出现胥吏阶层膨胀的趋势,北宋真宗咸平四年曾一次裁减诸路冗吏195800余人,(25)可见当时胥吏规模应该远超过前朝。与当时官员相比,胥吏在数量上更占优势,因为虽然宋朝亦以官冗著称,但官与差遣分离的体制使大量的官员并不亲临职事,而胥吏却全部在官府公干。以县为例,宋朝县级亲民官不过令丞簿尉等四五位,小县只有一两位,而县吏定额有数十人到一二百人不等,额外置吏的情形十分普遍。南宋时,正额吏员几次裁减,额外置吏却往往数倍甚至十倍于正额,以至叶适称当时州县为“公人世界”。实际上,吏人已然结成官府内的一股强大势力,为政府决策和官员施政的基本考量因素。而宋代狱讼数量亦呈不断增长的态势,南宋龙溪“县狱大概每年有大案(徒刑以上)数十件,而牒讼案件每日却可达到百余件。”(26)因民间细故而兴讼是导致案件剧增的主要原因,也是宋代获民风好讼名声的缘由,加之高宗、孝宗扩大越诉范围,各级衙门甚至刑部、大理寺也不堪重负。(27)有宋一代的地方行政,大率以理财为先,“今之为令者,知有财赋耳,知有簿书、期会耳,狱讼一事,已不皇悉尽其心。”(28)县衙几乎承担了全部狱讼案件的初审和最繁重的赋税征收任务,让少数几位亲民官躬亲狱讼显然很不现实,从县到省,大率类此。因而,即使精明强干的官员,在狱讼实务中也不得不倚重吏人。
其次,宋朝法禁细密,官员权力受到多方限制。
宋代虽号称儒学复兴,但其法制的发展达到历代顶峰。(29)宋朝设有专门编修法律的机构,据郭东旭先生统计,宋代编纂大型法典达到242部,其中规模最大的《政和重修敕令格式》达到530卷,神宗朝以后所修综合法典多卷帙浩繁。(30)南宋人陈亮认为:“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而欲一切反之以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而人固亦不能易。”“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31)同时的思想家叶适言:“国家以法为本,以例为要。其官虽贵也,其人虽贤也,然而非法无决也,非例无行也。”(32)宋代农业和商业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市民化,客观上要求国家行政司法步入常规化、可预测的轨道,官员自由裁量的空间越来越小,士人主导的官僚体制的实践与其理想日益背离。
宋初的改革解除了上下官员任用亲吏为官的权力,其它权力也被大大压缩,并且朝廷加强了对各级官员的监察,责官甚于督吏,故常有官员因胥吏申告而去职,胥吏集体“逃亡”事件也往往以长官调离甚至受责而告终。同时,行政与司法的分工至少在观念、习惯和较高层次上得到实现。北宋王安石曾以宰相身份议论刑案,遭到其它官员批评。(33)南宋孝宗曾下诏:“狱,重事也。稽者有律,当者有比,疑者有谳。比所顾以狱情白于执政,探取旨意,以为轻重,甚亡谓也。自今其祗乃心、敬于刑,推当为贵,毋习前非。”可见司法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已经相当的专业化,与其它行政事务区分日严,长官特别是高级官员在司法事务上的发言权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而对基层司法判断的独立性已相当重视。
法律对胥吏的选任、晋升、奖赏、职责等都有相当细致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官员管理胥吏的手脚。在《庆元条法事类》卷五十二《公吏门》中,朝廷对吏人差补、解试出职和停降都作了细致的规定,如“诸州推司法司吏人并指名选差”但又规定法司选差的顺序:先试中人后习学人;又如规定诸州院、司理院推司及法司吏人年满不犯私罪情重及赃罪并失出入人罪者听推赏,即使有失出入罪,在情节较轻时仍可推赏。与汉唐长官对吏人的专断处置权相比,宋代吏对官的依附关系基本解除,法吏的任用、迁转、出职、违法处分等等皆有明法可依,且归吏部或刑部都官统一管理,后期虽由各州县司官员检选,但在考试制度下须依凭客观的标准。宋太宗时,“张乖崖为崇阳令,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鬓傍巾下有一钱,诘之,乃库中钱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乃杖我邪,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乖崖援笔判云: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其首。申台府自劾。”(34)这一事件反映了宋代士大夫与胥吏间关系的复杂性,胥吏地位虽卑下,但也不是长官随意处置的对象,在法律上也有相当的权利,所以张乖崖虽专断,但也须向上级自请处分。后人以士大夫的立场肯定张乖崖的越权行为,并不能掩盖这种行为的违法性质,而该事例中的胥吏敢于对抗长官也是出于对宋朝法制的倚侍。
再次,胥吏在司法运作上拥有比较优势。
唐宋之际的社会转型使宋代的司法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宋朝基本上是一个由主客户构成的庶民社会,不同户之间以及官府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大大松弛,法令实施的等级强制色彩大为减弱,官府在狱讼中居中裁决、定分止争的功能地位上升,司法更具有知识化操作和理性化倾向。这一点可以从宋代法医技术和鞫谳分司、翻异别勘等司法体制的发展成熟等方面得到间接证明。在这种环境中,对司法所必需的知识的掌握就成为掌握司法话语权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虽然长官有法定的裁决权,但是如果他不具备必要的司法知识,就很可能沦为一个“画押”傀儡;如果当时的官员普遍缺乏必要的司法知识,掌握这样的知识的胥吏操控司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从上文中我们知道,宋代朝廷和许多士人都认识到官员法律知识上的贫乏,并认识到这种状况是导致所谓“吏强官弱”的重要原因,但风俗所向,竟也无可奈何。
宋初的体制改革造就内重外轻的权力格局,中央成为各项决策的中心,中央与地方的联系较前代大为频繁,这种联系主要采用公文的形式。地方重案的请谳也主要是递解案卷,而司法文书的起草、抄写、点检、批勘、收发、传送等均为胥吏之职责,故胥吏实为沟通地方和中央司法的桥梁。同时,宋代土地买卖频繁,财产的分割和转移加快,加上政府财政预算不断膨胀,征收赋税任务很重,而征税的依据全在簿书,所以,宋代与财产有关的登记、汇总报告和存档管理等文书工作较前代大大增加,这些簿书本身也可作为狱讼审理中的证据使用。因此,宋代司法逐步实现书面化、程序化、技术化,与文书处理息息相关的胥吏阶层在司法中占据重要地位。
胥吏之所以在司法过程中占据相当优势,还在于他们掌握司法不可或缺的“地方性知识”,这一点尤其为士大夫所不可企及。宋代承担司法事务的胥吏已经有很强的专业要求,体现在选任上,亲属或师徒间传承和引荐是普遍的做法,同时胥吏累世居住一地,于当地民情乡土最为熟悉,作为“官民交接之枢纽”,(35)渐成一种强大的地方势力。南宋的叶适则把这一现象概括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36)对于初来乍到、不久职任的“异乡人”(37)“亲民”官来说,委信胥吏既属不得已,也不失为一条施政捷径,有些吏人势力坐大,以至有称为“立地官人”、(38)立地知县(39)者,其间体现的吏人在司法运作中的比较优势却无可怀疑,甚至有被判罪后县官仍申请暂留职任者。(40)
最后,君主地位稳定需要一个既尊荣又无力的士大夫阶层,而从事司法实务的阶层又以其低贱的社会地位不可能挑战君主权力,士人与吏人在宋代官僚体系中共生“共荣”。
宋代士大夫从宋初经历了一个从能吏到进士的转型,(41)这显示出士人并不能扭转当时的时势,反要适应新型官僚制度的要求,满足于保身荣家的士大夫生活。实际上,宋王朝对文人的担心并不亚于武夫,其优容士大夫的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刻意的笼络。又宋代官僚体系本身存在很大弊病,内重外轻造成地方财政严重不足,官员俸禄又难以支撑士大夫的奢糜生活,所以通过胥吏从民间汲取财源是地方政府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条件。上引孝宗与吕颐浩的对话很有意思,几乎所有人都能指出问题所在,但都没有足够的意愿来解决它。之所以没有足够意愿改变,肯定是在现实中存在更深层次的利害,那就是整个官僚体系的运转包括它的财政基础实际上都要靠胥吏来支撑。一方面指责胥吏无廉耻却不愿给俸或只给薄俸,另一方面又以优渥的待遇养“高尚“士人之廉耻,宋代士人整体的市侩性质在胥吏问题上暴露无遗。(42)
儒家司法观念存在法义与法数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在宋代都获得具体的实行。超越常法,而独得法外之意,相较于胥吏墨守成例,不识大体,可以说是最能体现士大夫的优越性的地方。但宋代法制的发展似乎留给士人发挥法义的空间越来越小,且于不谙法数之际,法义势必流于空谈。宋代士人试图摆脱这种窘境的努力最终失败,这说明这种表面上不合理的官僚制度有其自身的生命力,这种官僚司法制度包容士人和胥吏两个角色,两者在地位、职责、待遇等方面皆相差悬殊,彼此处于对立和冲突的关系中。“古者以仁义为儒,以教化为吏,而儒与吏为一。后世以章句为儒,以法律为吏,而儒与吏为二。……夫惟儒与吏为二也,儒则从事于诵说章句之末,而目吏为俗也,吏则从事于法律刀笔之陋,而目儒为腐也。(43)这样的形势于君主政治的稳定极有好处,士人官僚既陷于自身的弱点和吏人阶层的牵制,复陷于本阶层内的空谈内讧,加上以文抑武政策的成功,于是君主反侧无忧矣。胥吏则受到自身素质的限制,并受到士人和庶民两方面的歧视,根本无望憾动王朝根基。终宋之世,叛乱局限于地方规模,与叛乱不能获得知识分子的支持和领导有莫大关系。
三、宋代司法中“吏强官弱”之影响
虽然宋朝及其以后的士人对胥吏专横和腐败深恶痛绝,但是吏人中间也不乏品行端正者。据《夷坚志》记载:“余杭县吏何某,自壮岁为小胥,驯至押录,持心近恕,略无过愆,前后县宰深所倚信。又兼领开拆之职,第遇受讼谍日,拂旦先坐于门,一一取阅之。有挟私奸欺者,以忠言反复劝晓之曰:‘公门不可容易入,所陈既失实,空自贻悔,何益也?’听其言而去者甚众。”南宋甚至有吏人之子割肝救父的事例。(44)对胥吏道德品质的指责并在制度上进行压制与士大夫所信奉的儒家伦理相去甚远,且士人官员在司法中的腐败并不逊色于胥吏,(45)更何况对处在司法行政体系中的胥吏而言,廉洁公正的风险成本常常较腐败更高,因此,单纯的道德指责对胥吏阶层是不公平的,也无助于司法状况的改善。姑且放下道德方面的争议不论,胥吏在狱讼中的重要作用对宋代司法乃至整个法制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首先,司法技术的明显进步以胥吏的司法实践为基础。
《洗冤集录》成书于南宋晚期,是宋慈对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这些经验不可能是宋慈一个人独自体验出来的,更多的应该来自从事狱讼检验的仵作的长期积累。在该书问世前,宋代已有《内恕录》等多种法医学著作出现,著者皆佚名,很可能是实践经验丰富的仵作或法吏所传,宋慈在博采诸书的基础上才写成了该书。(46)宋慈在《洗冤集录·序》中说:“重以仵作之欺伪,吏胥之奸巧,虚幻变化,茫不可诘。”(47)这段话似乎暗示作者撰写此书的动机与胥吏在狱讼中的作用有关,显示强干之士人对吏人独占司法知识的焦虑不安。
其次,司法体制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对胥吏专权腐败的防范。
宋朝司法体制在渐进式改革中不断完善,形成了如鞫谳分司、翻异别勘、检验格目等颇具特色的制度,而这些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与狱讼胥吏的活动密切相关。以鞫谳分司为例,据宫崎氏推测,推鞫和检断的分离应该是在神宗朝新法党时期实现的,(48)这一时期也正是朝廷对胥吏问题最重视的时候。南宋高宗时,周林上《推司不得与法司议事札子》说:“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然而推鞫之吏,狱案未成,先与法吏议其曲折,若非款状显然如法吏之意,则谓难以出手,故于结案之时不无高下迁就,非本情去处。臣愿严立法禁,推司公事未曾结案之前,不得辄与法司商议,重立赏格,许人首告。臣又见狱吏惨刻,动以缧绁捶楚为能,常在圜扉毒犹不广,至于使之预追呼之事,则虎而翼矣。出入间里,既无忌惮,罪无轻重,理无曲直,例遭侵铄,每见狱卒追呼,必持绳索挟鏁械携杖棰以示威力,用求贿赂。且以一夫犯刑干证之人多或数十少或三四,一概被毒,无得免者,又以入狱之后,捶楚为戒,无敢告诉,故其追呼扰民之患,尤非其它走吏之比。臣欲令州郡,追呼赴狱之人,在州则付厢界,在县则委令佐,遣诣郡治,然后付之狱司,庶几狱吏不能为恶于图圄之外,上广陛下爱惜黎元之意。”(49)从这一奏章中可以推知:巡捕、推鞫和检法议刑的分工,其动机主要是防范办案胥吏寻事虐民求赂。
最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也受胥吏活动的影响。
南宋初重订法律,三省胥吏的“省记”是其重要渊源之一。乾道初,“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从事,法当然而无例,诸事皆泥而不行,甚至隐例以坏法”。(50)“例”在宋代及其以后成为重要法源与胥吏在司法中作用增强有很大关系。孝宗因此诏令整顿律法,严格限制例的适用范围,编成《乾道敕令格式》和《淳熙敕令格式》,又以“其书散漫,用法之际,官不暇遍阅,吏因得以容奸”,重新编定《淳熙条法事类》,随事分门,开创法典编纂新体例。(51)由此可见宋代法律编纂与胥吏参与司法的方式和朝廷对胥吏活动的防范动机密切相关。宫崎氏认为,宋元时期士大夫法学、胥吏吏学和民间讼学在江西地区的某种程度的融合最终为《元典章》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其法律编纂模式实际上为明清律所承袭。(52)因此,狱讼胥吏的活动对宋以后法制的影响似乎应该得到更充分的重视和评价。胥吏在司法中作用的增强在产生巨大弊害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宋代不同以往的司法技术、体制和理念,对宋以后法制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今天推进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仍然有必要提防某种形式的胥吏司法重演,故仍然有必要回顾宋代以来胥吏司法的历史以吸取其经验教训。
注释:
①对宋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以台湾地区的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年版)为代表,大陆以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为代表,皆以典章制度的分析描述为主。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最先对胥吏司法进行深入研究。最近对胥吏的作用作出积极评价的文章主要是祖慧:《论宋代胥吏的作用及影响》,载《学术月刊》2002年第6期。
②脱脱等:《宋史》卷三百六十五《蔡居厚传》。
③徐元瑞等:《吏学指南(外三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④唐宋之际法律文化的巨变导致汉唐德礼系统在宋代的失效,有关论述详见宫崎市定:《宋元时代的法制和裁判机构——<元典章>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收于杨一凡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三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宋辽金元卷》。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开宝二年三月丁未。
⑥官箴书主张防范胥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胥吏过错会导致官员受罚。李元弼在《作邑自箴》里提醒官员“大率词讼,须是当厅果决,面谕罪名,不尔即生枝蔓。…若稍稽缓,吏人收赂遂成,枉法赃二十贯文,官员理当冲替。”
⑦叶适:《水心别集》卷十五。
⑧前注⑦,叶适书,卷十四。
⑨前注⑦,叶适书,卷十四。
⑩参见刘馨珺:《明镜高悬:南宋县衙的狱讼》,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468-469页。
(11)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八。
(12)前注⑦,叶适书,卷十四。
(13)前注⑦,叶适书,卷十五。
(14)刘一止:《苕溪集》卷十二。
(15)胡太初:《昼帘绪论》《治狱篇》。
(16)赵善臻:《自警编》卷八。
(17)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二。
(18)苏舜钦:《苏学士集》卷十一《五事》。
(19)苗书梅:《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载《文史哲》2003年第1期。
(20)周南:《山房集》卷五《黄平甫墓志铭》。
(21)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
(2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绍兴二年十一月庚午。
(23)王安石语,出自前注⑤,李焘书,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三月癸卯。
(24)杜佑:《通典》卷三十六、三十九、四十。
(25)参见前注⑤,李焘书,卷四十九,咸平四年六月癸卯。
(26)前注⑩,刘馨珺书,第74页。
(27)参见前注⑩,刘馨珺书,第6l页。
(28)前注(15),胡太初书,《临民篇第二》。
(29)相关评价较多,参见前注④,宫崎市定文,第49页;又见陈寅恪:《邓广铭〈宋史刑法志考证〉序》,收于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30)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第17页以下。其中引《元丰敕令格式》有2006卷,规模之大颇令人生疑。
(31)陈亮:《陈亮集》卷十一《人法》。
(32)前注⑦,叶适书,卷十五。
(33)参见前注②,脱脱等书,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
(34)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
(35)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五。
(36)叶适:《水心集》卷三。
(37)陆九渊屡次称地方官员为“异乡之人”,见《陆九渊集》卷八、卷九等。
(38)《州县提纲》卷一。
(39)《明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一《人品门·公吏·违法害民》。
(40)参见前注(39),卷十一《人品门·公吏·违法害民》。
(41)杨天保:《从“能吏”到“进士”——临川王氏一段家族史隐匿之因的社会学解读及其意义》,载《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42)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方式通常被范仲淹的那句名言所误导,以为大都有一股铁肩担道义的豪气,实际上,其日常生活可以用奢糜来形容,并与整个宋代的市井化的社会风气相匹配。毋宁说,宋代的士人反倒让市民给教化了。
(43)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八《儒吏》。
(44)参见前注(39),卷十《人伦门·孝·割肝救父》。
(45)参见前注②,脱脱等书,卷二百《刑法志二》。
(46)宋慈:《洗冤集录·序》:“遂博采近世所传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会而粹之,厘而正之,增以己见。”
(47)见前注(46),宋慈书,《序》。
(48)参见前注④,宫崎市定文,第44页。
(49)见前注(11),黄淮等书,卷二百一十七。
(50)见前注②,脱脱等书,卷二百《刑法志二》。
(51)参见前注②,脱脱等书,卷一百九十九《刑法志一》。
(52)参见前注④,宫崎市定文,第87页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