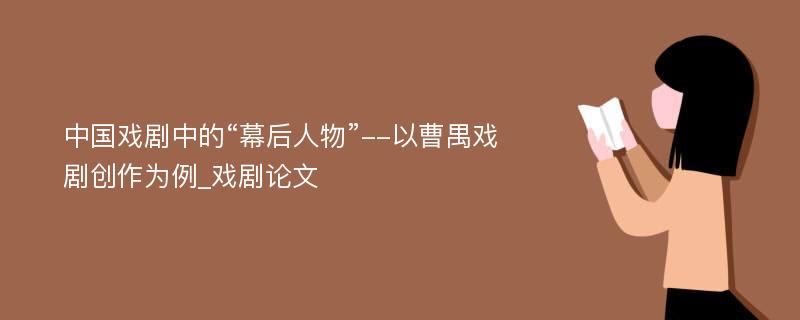
中国戏剧中的“幕后人物”——以曹禺的戏剧创作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幕后论文,戏剧论文,人物论文,中国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戏剧通常总是由一系列互相矛盾而又彼此关联的人物群体所组成的。由于该群体中的人物有主、次之分,在剧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尽相同,因此如何使他们在剧中各得其所、各尽其职、各显其能,从而构合成一个纵横交错、和谐统一的艺术整体?这一戏剧人物的设置问题,便自然成为戏剧创作不容忽视的一大重要课题。
一般说来,剧作家对戏剧人物的设置,可遵循有利于主题表达和人物性格刻划、有助于情节发展之多重需要的总体原则。但若就每部戏剧究竟应该设置多少人物而论,则恐怕很难并且也不可能一概而论,并无成规可循。我国戏剧界有句行话:“有戏不在人多”。其涵义是说要利用尽可能少的人物,来表现尽可能多的内容。应当承认,这种“省俭与集中”制,乃属于被古今以来中国戏剧艺术的长期实践所反复验证、契合戏剧艺术内在规律的行之有效的一种戏剧任务设置模式。
戏剧人物若从表演空间看,不外乎出场的与不出场的两大类。所谓出场者是指直接在舞台上出现的那一类角色;而不出场者则指那些并不直接在舞台上抛头露面、而躲在舞台画框以外的幕后活动的那一类角色。让人物直接出现于舞台之上,属于“明场”处理方式:由出场人物的一系列活动所构成的戏剧性情节、场景或事件等,一般称之为“幕前戏”。而让人物隐遁于舞台帷幕背后不显山露水,仅借助其他出场人物的叙述间接地告诉观众,则属于“暗场”处理方式;由不出场人物的一系列幕后活动所构成(披露)的戏剧情节、场景或事件等,一般称之为“幕后戏”。被剧作家以“暗场”方式处理、以“幕后”为其活动空间的那些不出场人物,我们不妨可命名为“幕后人物”。
如果我们遍览一下中国戏剧作品,便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那样一类别具一格、耐人寻味的特殊角色:“幕后人物”,他们构成了整个戏剧人物画廊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其面不曾识,幕后亦风流!这里不妨就让我们通过剖析一位著名艺术典型——即曹禺《日出》里的金八,以窥斑见豹,去领略一番“幕后人物”的风采神韵。
说到金八,举凡看过《日出》的观众,恐怕都很难忘记金八在与潘月亭进行生意大战的那一场“幕后戏”中精彩绝伦的表演:大丰银行经理潘月亭为支撑银行资金严重不足、生意周转不灵的局面,孤注一掷地对外大兴土木,摆出一副握有重金、底气十足的假象,以堵住大宗提款;暗地里却将房地产全部抵押出去;同时还通过大量裁员和无理克扣修房小工工钱的手段转嫁危机;甚至于连一旦破产就自杀的手枪都随时备揣在身边了。他在生意场上与金八尽量拉关系套交情,小心应酬而丝毫不敢得罪。然而纵使他使出浑身解数,到头来依旧未能逃脱金八设下的陷阱。具言之即金八故意先从大丰银行提走大宗存款,随后买进大量公债,暗中操纵市场,造成行情渐涨的假象,引诱潘月亭利令智昏,破釜沉舟地也跟着抛入四百五十万公债,窃以为这一下摸准了风向,很可以大发横财。殊不知此举正中了金八“请君入瓮”的圈套,最终落得个破产倒闭、身败名裂的下场。虽然金八始终没有在舞台上显露一下其“庐山面目”,但透过剧中其他出场人物的叙述,我们可以得悉他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旧中国金融买办与封建帮办的结合体,是当时社会黑暗势力的典型代表,一个极端残忍毒辣、卑鄙狡黠的铁腕人物!他仿佛一只硕大的毒蜘蛛,稳居于旧社会这张黑网的中心,而剧中其他人物的命运(事业、破产、自杀等等),都不过是这张黑网上劫数难逃的蠕动。剧作家巧妙地使剧中几乎所有人物都与他发生千丝万缕的某种联系:压迫(玩弄)与被压迫(被玩弄)的关系(如陈白露、小东西与金八)、奴才与主子的关系(如黑三与金八)、商场对手的关系(如潘月亭与金八)……即使是小职员李石清之所以敢与顶头上司潘月亭来一番勾心斗角,推究起来其实也仍旧与金八攸然相关——正因为金八在背后卡着潘月亭的脖子,令他难以有恃无恐,因此连对下属的“要胁”有时亦不得不暂且忍声吞气!剧作家将金八作为全剧结构的枢纽和推启戏剧矛盾冲突发展演变的强大动力:这个无影无踪的魔影笼罩全剧、左右一切,暗中主宰着剧中其他人物的行动及其命运;同时还将众多的人物与事件(如小东西的悬梁自尽、陈白露的服药自绝、大丰银行的倒闭等等)串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藉此深刻揭示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社会。
为什么戏剧中会出现金八之类的“幕后人物”呢?从戏剧美学理论视角而论,可以说戏剧中出现某些“幕后人物”乃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这一戏剧现象的原因,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现实生活的实际来看,由于现实生活本身是极其斑驳陆离、五彩缤纷、丰富多彩的,既有阴阳虚实,也有前后左右。无论是纵观历史还是横看世界,有在前台表演的,也有隐于幕后的,还有不得不退居于幕后的。如诸葛孔明所言: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千里之外。这句话里就十分明确而又形象地划分出了两类不同的人:足不出户、出谋划策的军师(属于“幕后人物”)和驰骋疆场殊死拼杀的士卒(属于“幕前人物”)。因此戏剧中既有活动于台前的出场人物,又存在着因某些原因而隐遁于幕后的不出场人物,就是非常自然而正常的事情,它属于戏剧文学对现实生活本来面目的一种真实反映。
(二)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舞台表演艺术,戏剧是以塑造直观可视的舞台人物形象为其主要特征的,是活人(指演员)扮演活人(指戏剧角色),且又直接表演给活人(指观众)看的。所以戏剧舞台之时空,总是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制约并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不可能让所有剧中的有关人物统统登上舞台,把故事情节发展的整个过程事无巨细、纤毫毕现地全部展示出来。这种限制性较之于小说、散文自不待言,即使是与同为表演艺术的电影、电视相比,亦相当明显突出。即以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例。该剧第六场所要展示的人物与场景是:关汉卿创作的悲剧《窦娥冤》正在上演,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各类观众对演出有着不同的评说。他们的评说不仅关系着这出戏能否继续上演,而且还直接牵系到关汉卿、朱帘秀等人的命运。如此庞杂的人物与宏大的场景,在电影、电视中可以毫不费力地借助现代高科技摄影技术作全景式、全方位的俯瞰透视,但在戏剧舞台上就实在难以如此这般地表现出来。鉴于戏剧舞台的这种时空限制,剧作家作了如下巧妙处理:把观众席上发生的很多事情略而不谈、隐入幕后,安排出场人物将这些隐去的内容逐步交代出来。
(三)“幕后人物”的设置直接与剧作家的艺术构思密切相关。对此问题我们又可以从三个具体的层面上来理解和把握。
其一,剧作家受其生活积累的厚重或轻薄,和由此带来的对所描写的对象的驾驭能力之大小、表现程度之高低优劣等某些因素的影响所致。如曹禺的《原野》中有一位重要的“幕后人物”——焦阎王,他与剧中的另一位主要人物仇虎构成冤家路窄、势不两立的矛盾对立面。按一般逻辑与惯例而论,矛盾对立双方需要正面交锋,双方无疑都应该出场。但曹禺却出人意料地对剧中这位不可谓不重要的角色——焦阎王作了幕后处理。为什么呢?曹禺本人曾就《原野》的生活背景问题指出:“这个戏写的是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混乱时期,在农村里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都知道曹禺的保姆就是一位农民,曾对他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他的故事断断续续讲了三年,令年幼的剧作家曹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另外曹禺在中学读书时每次回家度假,沿途也都常常目睹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卖儿鬻女的凄凉景象。这些生活内容构成《原野》的基本素材。然而这一点生活积累显然远远满足不了剧作家构思剧中有关人物与情节的需要。况且与曹禺对家族生活的熟悉了解与丰富体验相比,他对农村生活就相当陌生了。假如让焦阎王在剧中直接出现,势必会涉及到很多的农村生活场面,出现更多一些的农村人物。倘若那样,作者就难以得心应手地驾驭其欲描写的题材,不是扬长避短,反而成了以己之短、心力不足地在所欲表现的对象身上舞文弄墨,其刻划人物的表现力之高低优劣是不言自明的。曹禺熟谙此理,正是为了弥补自己生活积累之不足,扬长避短,才因此将焦阎王推置于幕后作了暗场处理。
其二,写“幕后人物”,也是剧作家为了“立主脑、简枝蔓”,尽量减少戏剧中可能有的较繁杂的头绪和线索(此即意味着减少了许多矛盾冲突),追究结构的紧凑严谨、情节的相对高度集中,同时遵循“有戏不在人多”的人物设置基本原则,使出场人物在数量上尽量做到“省俭化”与“集中化”,以便有的放矢,腾挪出更多的舞台时空、泼足了笔墨来刻划那些剧中出场的主要人物。譬如曹禺先生的《原野》,除了前已提及的作家生活积累厚重轻薄之影响因素外,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考虑。即焦阎王有一部迫害仇虎一家的罪恶史,仇虎则有一部倍受迫害的血泪史。但作为剧中一位主要人物的仇虎出场时,焦阎王已去世两年了。如果将时间提前两年,让二人“狭路相逢、冤家路窄”,展开正面交手,那无疑会是一部刀光剑影的复仇剧。那样处理其戏剧效果也许颇能扣人心弦,但如此铺排情节,很可能使仇虎以及其他某些主要人物的性格淹没于其中。有鉴于此,剧作家曹禺特意将焦阎王置于幕后,使仇虎出场伊始其对手早已不复存在,从而大大简略掉两人之间客观存在的外部冲突,将艺术的笔触潜入至仇虎的灵魂底处,对他精描细绘,并最终使这一出场的主要人物栩栩如生,给人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其三,安排“幕后人物”,从戏剧结构的另一视角来看,是出于剧作家为追求增强其剧作引人入胜、耐人寻味的戏剧性效果与艺术魅力而设置“戏剧悬念”的艺术构思需要。试问,为什么数以百计的观众甘愿耗费几个小时的时间端坐在剧院里,全神贯注、津津有味地观赏戏剧演出呢?其最根本的一条奥秘,即源自于“戏剧悬念”的神奇力量。所谓“戏剧悬念”系指剧作家利用观众关注事件发展与人物命运的迫切期待心理,有意在作品中设置下的某些不得其详、悬而未解的疑惑问题,它不失为剧作家安排情节、结构布局的一种重要技巧、手段。西方戏剧理论家贝克曾精辟地指出:“(戏剧)悬念乃是戏剧中抓住观众的最大魔力”。戏剧悬念仿佛一块巨大的磁石,紧紧攫住观众的心灵,诱发其强烈的兴趣与高度的注意力,以欲知分晓的迫切期待心理往下看,直至戏剧帷幕落下。一出戏剧之所以对观众富有那样大的吸引力,说穿了其实就是剧中的那些悬念时时刻刻令观众牵肠挂肚、摄魂夺魄、情不自禁,观众恰恰正是出于要努力解开剧作家在剧中所设置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悬念”之谜,因而才对剧中的人物事件产生迫切期待、欲知分晓的观赏兴趣(对此我们不妨可称之为“解谜心理”)。倘若没有了悬念,观众的兴趣必然会随之相应地丧失殆尽,恐怕也就将无人愿意再看戏了!从上述视角来看,设置幕后人物毋庸置疑地会造成强烈的悬念:因其不出场,反而使观众产生浓厚兴趣,愈想对他有所了解,想方设法地去探究他到底是何许人物?有何特征?甚至会借助于想象在心目中摹影绘形,勾画出其“音容笑貌”来。出场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一般或历经磨难或好事多磨,最终会有一个或悲剧性或喜剧性之归宿,因此伴随着出场人物的结局的来临,观众对有关事件的发展与人物的命运的悬念便顿然冰释。相比之下,由幕后人物所造成的悬念却不会尾随帷幕的落下而尽然消逝;幕后人物因其自始至终不“抛头露面”,观众尽管凭借剧中其他出场人物的述说品评,可以知其大概,但充其量是似乎已闻其声,而终未得见其人,难窥其“庐山真面目”。所以对此类幕后人物的“解谜”,只能说是解开了某些部分而非全部,因此仍然需要观众在落幕之后的时间里(也许短暂的数日,也许漫长的若干年),去不断地揣摩、体味、充实与完善,方可能较全面深入地“解其味”,并彻底卸下关于这位“幕后人物”的各种悬念!
(四)“幕后人物”的设置,还与剧作家受渊远流长的“虚实相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浸染、熏陶有着直接的同构影响关系。在渊源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产生了一种“虚实相生”的艺术观念及结构技巧——所谓“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象黄宾虹先生绘山水总爱多处用“云断”;齐白石老人画虾,常常不着一笔波纹,但其画却能妙趣横生、意境幽深,而观众自然能感受到其中“峰藏雾里、虾游水中”的无穷韵味,并体味出艺术家之良苦用心所在——即在其无笔墨处!剧作家写“幕后人物”与中国山水画“以虚白显妙境”的艺术观念及“虚实相生”的结构技巧一脉相通,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幕后人物”虽不直接出现在舞台上,但他(她)并非可有可无的多余人,而属于全剧人物群体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理,“幕后人物”所赖以活动的舞台时空——即“幕后戏”,尽管没有在舞台上被正面表现出来,然而它不是人们可以随意增删的无碍大局的细枝末节,而隶属于整个戏剧情节中不能分割的有机环节。就戏剧结构处理的技巧、手法而论,“幕前戏”属于“实写”,“幕后戏”乃为“虚写”;安排“幕后戏”的宗旨仍在于为了写好“幕前戏”。此正所谓实中有虚、虚为实设,以虚写实,相映成趣。我们不妨可以用反证法作一大胆的假设:倘若剧作家真的让焦阎王、金八等人物登场亮相,该会出现怎样一种情景与效果?岂非如同给黄宾虹的山水画塞满“云朵”,又给齐白石的虾游图填满“水纹”那样臃肿、直露,从而变得索然无味了吗?就拿金八来说吧。既然他是全剧结构之枢纽和牵系剧中各种矛盾冲突发生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那么如此一位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人物,剧作家为什么偏偏不作明场处理,让他直接登上舞台作尽兴表演,那样的话该剧中的矛盾冲突岂非更尖锐、激烈和突出吗?对此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假如剧作家对金八其人作明场处理,让他出现在舞台之上变成一位“幕前人物”,势必会使观众将相当多的注意力集中到金八所引致的各种事件与矛盾冲突方面,作者便难以腾出更多的笔墨去正面和直接摹写并渲染剧中原有事件与矛盾冲突在其他各种人物身上引起的各类情感反应。而作家从一开始构思《日出》一剧时,便十分明确地意欲表现别的人物(指金八以外)“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于是自然而然地就把金八隐遁到幕后作暗场处理。但将他隐遁幕后并非等于就是不写他,实际上幕前人物的行动仅仅只是果,幕后金八的作用方为因。这正是艺术辩证法互为映衬、相得益彰的妙用。恰如“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剧中陈白露、潘月亭等等幕前人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一不是在同时刻划着金八的阴险毒辣、狰狞恐怖。我国古典诗论非常推崇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金八这一戏剧人物正是如此:虽始终不曾露面,观众无法直观其人;却又那般的形神兼备、风流毕现。他令观众时时处处都能感觉到他在行动——他“行动”于别人的行动之中,并随心所欲地操纵和制约着其他人的行动;由此而似乎可以窥探到其狰狞凶残的面目、丑恶不堪的内心,并在心底对他产生强烈的震撼与极大的憎恨。
标签:戏剧论文; 曹禺论文; 中国戏剧论文; 曹禺现象论文; 幕后论文; 艺术论文; 设置悬念论文; 日出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