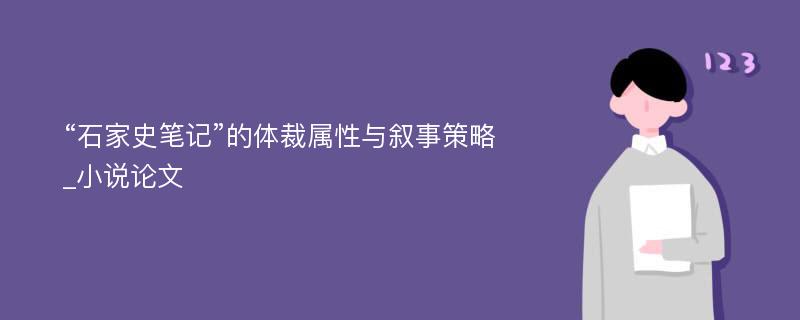
《斯通家史札记》的文类属性和叙述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通论文,家史论文,札记论文,策略论文,类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分类号:I71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2011)04-0096-05
0.引言
《斯通家史札记》(The Stone Diaries,1995)是加拿大小说家卡罗尔·希尔兹(Carol Shields,1935-2003)最著名的一部小说,1993年出版后好评如潮,相继获得英国布克奖提名、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美国全国书评界奖及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借此希尔兹蜚声于世界文坛。但正如加拿大评论家戴维·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所言,小说出版十多年后,也不乏对其“多样性的幽灵”的评论之声,争论的问题主要有:小说中有一个还是多个叙述者?小说中的“自我”是单数还是复数?小说的主体是一个被语言分裂的主体还是一个统一的主体?黛西是命运的行动者,“在叙事中根据知识与需要或欲望”进行迂回生存,还是社会势力的牺牲者,因为“她的存在被抹去”?她的一生是一出悲剧还是一部罗曼史?她是一个被生活所困无助的女人,还是一个利用潜在的力量重新组织各种现实和多重自我来进行对抗的女人?(2005:10-11)
国内学者的评论也是见仁见智。王玲、秦明利认为:“《斯通日记》①具有典型的后现代‘反情节’特征。该小说无论从事件的时间关系还是因果关系来说都具有鲜明的非连续性和碎片性特征。”(2001:67)《斯通家史札记》中文版的译者刘新民却认为,这部小说“具有栩栩如生的各类人物(如黛西、巴克、克莱恩廷、马格纳斯等)、鲜明严肃的主题思想、次第展开的时序结构及随处可见的等级话语”,“具有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与后现代主义小说不可同日而语”。(2002:95)另一位学者陈榕则认为:“希尔兹的作品围绕着普通人的生活,写作风格主要以写实为主”,“与纯粹的后现代小说有明显的不同”,“更像是一部自传,而不是虚构的小说。但是,一旦我们进入文本,却又不得不面对刻意放大了的虚构特征”。(2003:38-39)陈晶、孔英认为《斯》是一部“非写实性的自传文学”,“小说无论是主体框架的结构还是主题内容的表述都开创了自传体小说的先河”。(2008:168)
那么《斯》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是“札记”还是“日记”?是他传还是自传?是谁在讲述这个故事?是写实性还是“非写实性”?是现实主义小说还是后现代主义小说?
1.令人晕眩的文类
王玲、秦明利将这部小说译为《斯通日记》,似乎更接近于英文原意,但小说中我们却看不到日记,看不到每天记录下来的生活,所以它不是日记体小说。虽然小说中提到,黛西曾经写过日记,但她的旅行日记在和巴克结婚之前就遗失了。《斯》也不是中文译者说的“札记”,因为札记者,读书时摘记的要点和心得也;虽然它的目录明显记着黛西从出生到死亡的历史,但内容更多的是涉及黛西的亲人和朋友,所以倒更像是“斯通家史杂记”。《斯》呈现出奇怪的悖论:说它是日记体小说却没有写作主体;说它是自传,传主的身份却琢磨不定;说它是他传,“我”却时隐时现。它到底属于哪一种文类?
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认为:“类别的划分依据的是经验,而非逻辑。它们是作家、读者和批评家为了阐释和审美的需要而共同参与建构的一种历史假设。”(1986:210)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干脆将文类视为习俗。他说:“人们可能说,文类是一种语言习俗约成功能,一种联系世界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起到了引导读者在与文本的接触过程中的规范或期待作用。”(1975:136)“由于文类是作者与读者间的契约,所以文类带来的习俗和期待会影响到作者和读者。作者创作时选择了某一文类,他就要顾及此文类所带有的习俗以及读者在阅读此文类时滋生的期待,而读者在知道此文本属于哪一文类时,就会依据此文类的习俗而做出自己的期待。”(胡全生,2008:302)
小说中,希尔兹使用了如下自传习俗或曰叙述手段:1)使用了家谱;2)目录中按时间顺序把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3)在小说的开头使用了第一人称“我”(“我的”);4)在书(原著)的中间加上了注有书中人物和地点名字的照片等等。这些习俗或多或少地满足了读者对自传这种文类的期待。然而《斯》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自传。关于自传,法国自传理论家菲力浦·勒热讷在《自传契约》一书中下的定义是:当某个人主要强调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时,我们把这个人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称作自传。(2001:3)这里“某个人”是指真实的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自传中的传主、叙述者、人物应是同一个人,并且叙述的内容是真实存在的。而《斯》中的黛西却只是小说家希尔兹虚构的人物,它不是真实的自传,而应该是多瑞特·科恩(Dorrit Cohn)所说的“虚构的自传”(fictional autobiography)。科恩认为:“所谓虚构的自传,是指在一部小说中,虚构的叙述者回顾性地讲述叙述者自己的一生,而非小说作者的生活。这里我强调的是叙述形式,而不是叙述内容。”(1999:30)可见,从作者的一端来说,《斯》不是传统的自传。
从读者的一端来说,读者得到的印象也是如此,因为读者在阅读《斯》时,会逐渐发现希尔兹似乎在挑战读者的期待。首先,家谱中黛西的生卒时间列为1905-199?,对此读者会问黛西是哪一年去世的?为什么传主不讲明呢?小说开篇第一句:“我的母亲叫默西·斯通·古德维尔”(1)②,这第一人称叙述给读者以自传的印象,但第二章却出现了第三人称叙述,似乎他人——第三者——在为黛西作传。书的目录以黛西的一生为线索,但每章讲述的更多的却是他人的故事。而第六章则由信件组成,且都是写给黛西的,未见黛西自己的只言片语。书中提到并使用了大量的照片,却也不见黛西的。而且,文中的叙述者对自传或传记这一文类还不断地做出评判:“她的自传(如果写自传并非不可想象的话)将会是(如果真的有人来写的话)灰暗的虚无和不可填补的豁口”。(74)“传记、甚至自传,总是充满了系统性的谬误,充满了种种漏洞,若将这些漏洞连接起来,那便像一条弯弯曲曲、走势复杂的地下河流。”(192)“‘什么是传记故事’(the story of a life)③这一问题,是事实的编年史,抑或一系列巧妙编制的印象?”(344)听着这样的评判,读者禁不住要问《斯》是否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或许可以像英国学者温迪·罗伊(Wendy Roy)那样,认为《斯》“不是对自传这一文类简单的模仿,而是通过部分地颠覆它的习俗,对自传文类进行评判”,因此“可以把它称为元自传或者评论自传这种文类的文学作品”。(2003:116)或者用哈切恩的话说,《斯》是一部“元小说式的自传”(1994:293),通过极强的自我指涉性对个人生平或个人历史进行一种自觉的、自我观照的虚构。
除了写作自传同时又评论自传这一叙述特征外,《斯》的叙述者也幽灵一般地诡异。
2.幽灵般的叙述者
谁是《斯》的叙述者?就此争论很多,观点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作为小说人物的黛西,并非唯一的、复杂的和自我意识强烈得足以支撑起整个故事叙述的叙述者,而是由多种声音交织而成的。西蒙娜·冯提尔(Simone Vauthier)当是这一观点的代表,她认为小说中主要有3种声音:故事内的自传作者、故事外的传记作者和评论家。(1997:184)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黛西是唯一的叙述者,但采用了多种叙述声音。如澳大利亚学者凯瑟琳·威斯(Katherine Weese)就认为,黛西运用了各种女性主义叙述策略,使表面上看来处于失语和隐形状态的女主人公重新获得了声音,从影子背后走了出来。(2006:93)
就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声音分裂的问题,希尔兹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故意将所有的东西都通过黛西的意识过滤……至少在每章中有那么一次黛西是头脑清晰的,这时我就使用第一人称。但多数情况下,她是一个困惑的、不断追寻的第三人称人物,在她自称为她的传记建构中漫游”。(Hollenberg,1998:347)这似乎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意识中心理论不谋而合。詹姆斯认为:“小说中的一切叙述细节,都必须通过这个‘意识中心’人物的思想过滤,而这种过滤行为本身能更好地揭示这个人物心灵。”(赵毅衡,1998:120)作为“意识的中心”,黛西显然既可以叙述者—聚焦者的身份来观察和感知小说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也可以作为人物—聚焦者对自己的心理和其他人物的外在行为进行观察和感知。希尔兹在小说中写道,黛西“虽然生活在她的故事里面,但更生活在她的故事之外”。(121)她可以是故事的主人公,也可以是讲述故事的叙述者,她的叙述是个人的、作者的和人物的3种叙述模式怪异的混合体。作家赋予黛西的这种叙述方位,使黛西像幽灵一样出没于故事之中,若即若离,忽隐忽现,穿梭于生死两界。因此,威斯认为希尔兹在《斯》中采用了高度复杂的叙述角度。(Weese,et al.,2008:5)我们认为这种叙述角度主要体现在多重叙述手法的运用上。
多重叙述是不同人称之间的叙述转换。以萨克雷的小说《亨利·艾斯芒德》(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Esquire)为例,在这部典型的回忆录式的小说中,年老的艾斯芒德用第三人称来叙述自己青少年时代的故事,有时也用“我”来叙述,出现了两种人称并置的情况。叙述声音自始至终是艾斯芒德的,而叙述视角却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不断转换。叙事学家布赖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指出这种叙述手法由来已久,在现当代小说中更加普遍,甚至于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来指代同一人物。(2006:64)在小说的第一章开头,黛西使用了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这一传统方式,这在书信体小说、日记、回忆录或者自传中司空见惯,读者也不会感觉到视角上有什么变化。但当黛西讲述父母的情欲生活和邻居克莱恩庭·弗莱特的内心活动时,读者不免产生疑问:黛西从哪里知道这些事情呢?更有甚者,“我”目睹了自己的出生场景:“我”有强烈的冲动,要冲到“从我母亲双腿间挤出来的那个血淋淋的肉团跟前,将手搁在这团血光闪亮的浆状物中自己那颗跳动的心脏上,扁平的脑袋上,和柔嫩的双肩上”。(23)这里“人物兼叙述者突然说出他作为人物不应见到的情节,(他作为叙述者知道一切)实际上是一种‘跨层’”。(赵毅衡,1998:73)
同样“跨层”的还有时态的运用,如《斯》英语原版小说中的时态变化,对于回顾性叙述来说,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应该用过去时态。而小说中过去和现在两种时态穿插其中,时而现在时,时而过去时。这里,叙述者黛西显然不可能是经验自我,而是叙述自我,她不像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那样,因为视角的限制,只能讲述应该知道的事情,但引文中的叙述者却无所不知。
从第二章开始,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逐渐被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所代替,各种人称叙述并置的现象开始出现,比如时而出现“我”的身影。这一章还使用了带有包容性的复数第一人称,这表明作者想把读者(即“我们”)纳入她自己理解、组合和体验生活断片的过程中。“当我们似乎到达了一个安静之处,我们却在身体平稳的墨守成规的机能和欲破裂的需求之间被突然卷走。我们常做非理性的事情,荒唐的事情……”(71)甚至一句话中出现了多种人称并置的情况。黛西患麻疹独自躺在床上心事重重,“您也许会说,肯定是我发高烧才使我心神错乱的。……长期的与世隔绝和沉默无语,加之心中的烦闷,所有这些折磨着我,沉重地压在我身上,压在年轻的黛西·古德维尔身上,把她年轻的生命挤得空空如也”。(74)第二人称“您”(you)指读者或者受述者,第一个“我”做主语,第二个和第三个“我”(me)是宾格形式,“黛西”和“她”(her)都是宾语,表明黛西在生活中处于被动地位,是一个被生活“牢牢地钉住了”的女人(144)。这种叙述视角的不断漂移,对应了理查森所说的现当代小说极端叙述形式中叙述文本的二元分化,即“向心文本”(centripetal text)和“离心文本”(centrifugal text)的产生。所谓的向心文本一开始就生发出很多声音和立场,最后把这些声音和立场都压缩到一个叙述位置;而离心文本则不断地生发出很多不同的、异质的或对立的视角。离心倾向产生了更多的叙述可能性,并置了故事讲述的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以及其他视角,把额外附加的视角和位置都包括在叙述行为之中,其形式可以表现为多重声音或多重视角。(尚必武,2009:71)
《斯》是比较突出的“离心文本”:第三章以后黛西的声音似乎逐渐消失;第五章“工作”由一组单向书信构成,信都是写给黛西的,不见黛西的回信;第六章“悲痛”列举了黛西工作被挤掉后儿女、朋友、奶妈甚至很多不认识的人对她的悲伤进行阐释,可谓众声喧哗;最后一章“死亡”,黛西临终之际依然被各种话语和评价包围着。这些多重视角或多种声音的建构,“有助于作家在单一的主体性范围内,更为准确地再造许多参差不齐的叙述裂痕,为更加有力地界定或有效地摧毁不同人物之间、相互竞争的叙事世界,或故事与框架之间的传统差异,提供了一套完备的技巧。最重要的是,它们允许了多重声音的自由嬉戏,从而给予了更多的对话可能”。(尚必武,2009:72)以幽灵般的形式存在,黛西才有了更大的叙述空间。
3.虚构的真实
《斯》包含了多种叙述策略和文类形态:第一人称叙述、第三人称叙述、现在时态和过去时态的并用、书信、报纸文章、演讲词、物品单、文献记录、照片、菜谱、对话、讣告、结婚启事、电话对白等,所有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毫无意义的拼贴,实际上都是为了增强这部虚构作品的仿真性。作家为自己的虚构作品贴上自传或者传记、书信、日记等非虚构文类的标签,主要是为了增强作品的真实感,试图使小说的虚构世界与现实的真实世界取得同一性。
其中,照片的运用更加使作品呈现出亦真亦幻、虚虚实实的状态。西尔克·霍斯特科特(Silke Horstkotte)和南希·佩德里(Nancy Pedri)指出,文学中照片的运用几乎总是导致照片及其现实使用环境的类型产生变化。当照片从它原本所在的环境中被提取出来应用于虚构叙事中,它们本身也就具有了虚构的性质。反之亦然,虚构本身也明显地变得更加真实,即更加实体化。(2008:8)《斯》中的照片是在书即将完成之际希尔兹从跳蚤市场、旧明信片以及自己家庭成员的照片中挪用过来的。其中,霍德小时候的照片实际上是希尔兹的丈夫唐·希尔兹一岁时的照片。这些真实的照片运用到小说中,一方面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对所谓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融合了反讽的意味。小说中的叙述者也评论道:“如果我们说一个东西或一件事是真实的,我们就尊重它,即便它听起来虚虚实实,也别去管它;而如果说某事是虚构的——不管它看起来是多么真实、正确——我们都嗤之以鼻。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一个纪实的时代,似乎我们永远、永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事实。”(334)希尔兹把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照片挪用到小说中,不仅为人物添加了真实的元素,同时也让读者放弃了所谓的虚构和所谓的现实之间的区别,读者的视野得以延伸,从而超越了虚构的界限。
希尔兹在模仿传统文类的同时,添加了后现代魔幻现实主义和狂欢的元素。她把幻想和想象的成分掺入到现实主义的传统之中,这种掺入并不是试图颠覆现实主义原则,而是质疑它并试图突破它的局限。哈切恩在总结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小说特点时认为,其最显著特点就是利用现实主义的固有方式来挑战其自身。与更加偏激的美国“超小说”或者一些先锋派小说的语言游戏不同,即使在戏仿和破坏现实主义方式的时候,它们也总是自觉地从中吮吸它所有的能量。文本的自我观照和自我指涉使各种艺术形式和各种体裁之间的传统界限普遍消失,小说与非小说体裁的形式界限也不断被逾越。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元小说技巧也在不断地戏弄小说与历史、传记与自传之间的界限。故意混淆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小说与短篇故事集之间,譬如艾里斯·门罗的作品,而且还存在于小说与非小说相互渗透而产生的新形式之中,如一些虚构的传记或历史元小说。它们与传统形式的差异之处多在于作品自身表现元小说的自觉程度:“这些作品都是由词语组合而成的故事,是地地道道的虚构的艺术品,但它们依然致力于表现一种真实的、有史实凭据的场面。”(哈切恩,1994:291)希尔兹和很多当代女性主义小说家一样,如马格丽特·阿特伍德、艾里斯·门罗、马格丽特·德莱布尔、多丽丝·莱辛,她们把历史纳入视野,将后现代叙述技巧和现实主义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后现代实验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中寻找平衡的支点。她们不是进行纯粹的形式实验,而是吸收了后现代开放的空间所提供的氧气和能量,进而探寻更加真实的现实。
黛西来了又去了,现实中,她的生活如一块“被挤干的抹布”那般不幸(120),踏着自己“乱七八糟的历史”的“节拍”孤独前行,但她依然发现,“在她焦灼的心灵内部,仍存有一股如宝石般清凉、奇妙的力量——能偶尔观察这活生生的世界的力量”(186)。她可以用自己的幻想和想象穿越“故事的迷宫”,“也许她会从自己这些生活的故事中被挤出去”,但是她却拥有“一种惊人的能力,编织别样故事的能力”。(186)这种能力使黛西能够为自己的一生写下传记,树立起一座无形的丰碑,有如小说的题词页上黛西的外孙女写的那首诗《祖母的一生》:“她所做的/或所说的/远非出自本意/但她的一生/依然是一座丰碑/光影飘忽之中/恻然而立/渺渺的乐声中/舞姿翩然”。④
4.结语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斯》是一部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因为它“采用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追求细节的真实,营造出逼真的外表,但虚构的故事本身又对这种逼真进行了颠覆,从而使作品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真实细节与反现实主义情节之间的反差与张力。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有别于后现代前卫小说,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创新”。(王守仁、童庆生,2007:48)希尔兹运用后现代叙述策略使故事变得更加“真实”,更加准确地、真实地反映生活经验,并用元传记的技巧打破了自传的陈规旧约,通过将传统自传所关注的对象与后现代主义的形式实验结合起来,突破了自传的拘囿,开创了叙述游戏的新形式。
注释:
①原著的名称为The Stone Diaries,刘新民的中译本译为《斯通家史札记》,王玲和秦明利的文章称之为《斯通日记》,除此之外,该书的台湾译本书名为《石头日记》,意大利译本为In cerca di Daisy(意为“寻找黛西”),而法语译本La Memoire des pierres(意为“石头家族回忆录”),这些不同的译名也反映出这部小说的丰富内涵。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中简写为《斯》。
②文中译文均出自刘新民译《斯通家史札记》一书(详见参考文献[5]),以下引文只标出页码,不再另注。
③这里中译本原文为“生命故事”,笔者稍做改动。
④这首诗出现在原著的扉页,可惜中文译者没有译出,此为拙译。原文如下:“The Grandmother Cycle”:nothing she did/or said/was quite/what she meant/but still her life/could be called a monument/shaped in a slant/of available light/and set to the movement/of possible music.
